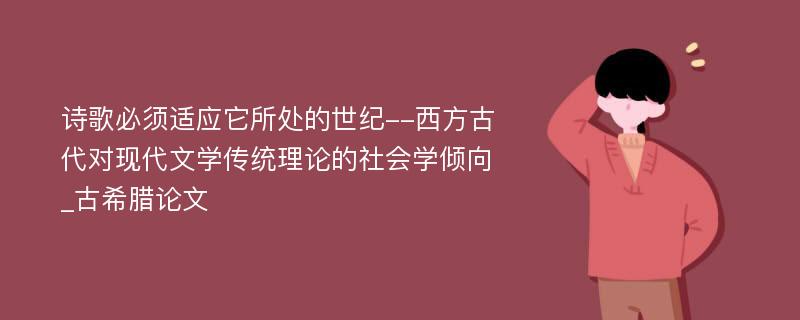
诗必须适应它所属的世纪——西方古代到近代文学传统论的社会学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近代论文,倾向论文,古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2-0139-07
一、贺拉斯所面临的矛盾
在西方文论中,文学传统的问题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然而古罗马人所说的“文学传统”主要是指古希腊文学延续下来的传统。这一做法本身又逐步演化成了一种传统,从古罗马到19世纪,古希腊的文学传统一直在西方人心目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言必称希腊”成为有学养功夫的标志,而每一个时代的新锐也往往将变革古希腊的规习视为第一要义。总之,“古希腊”在西方几乎成了“传统”的代名词,而始作俑者,则是古罗马人,其中尤以贺拉斯的《诗艺》为代表。
一般多将古罗马文论和美学归诸“古典主义”,这不无道理,贺拉斯《诗艺》中的箴言“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1],即为简明的概括。贺拉斯一方面主张改编古希腊文学的题材,另一方面主张仿效古希腊文学的体裁格式,而关键之处则在于大力推崇古希腊文艺追求和谐与得体的审美理想。贺拉斯主张将古希腊文艺崇尚统一、一致、恰到好处、合情合理的传统作为至上的楷模和标准。
但是,如果就此断言贺拉斯主张尾随古希腊人亦步亦趋,那也与事实不尽相符,在他的《诗艺》中恰恰不乏相反的见解,他也主张文学必须根据时代变迁和民族差异而对古希望的传统有所变革,有所创新。贺拉斯在肯定一批罗马早期诗人在文学创新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后指出,人们的语言习惯总是因时适变的,只要合乎当时的习惯,就完全允许诗人创造出古人没有的语言。贺拉斯还对罗马诗人植根于本国的现实生活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们正是基于对古希腊文学传统的变革创新才理所应当地荣膺显赫的名声。
这就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是主张对古希腊的文学传统谨守勿逾,另一方面是主张对于古希腊的文学传统有所变革创新,但这恰恰都出于同一人之手笔,在这里暴露出贺拉斯文学传统论的内在矛盾。贺拉斯生活在一个拟古之风盛行的时代,古罗马人普遍以摹拟希腊古典为时髦,其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语言的发展总是掩映在希腊文化的光辉之下。就文学而言,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在内容或形式上摹拟希腊的文学经典。正如后来罗素所说:“罗马在文化上就成了希腊的寄生虫。”[2]贺拉斯受时风熏染,持谨守传统的立场当在情理之中。但是罗马文学在若干世纪内特别是在中后期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所取得的创获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不能不使那些对文学发展持有切实眼光的人们改变世俗观念,突破流行时尚的限囿。正是追随时代发展、关注创作实际的社会学观点对贺拉斯既定的古典主义偏执起到了救正的作用。问题在于,贺拉斯对于古希腊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之关系的把握尚缺少一点辩证法,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容易走极端,在强调一面时往往不能顾及另一面,从而出现自相矛盾的漏洞。
其实贺拉斯所面临的矛盾正反映了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但如果在其中各执一端的话,那就有可能演化成尖锐对立、互不相让的争执甚至冲突,贯穿日后西方文论史的“古今之争”,可以说正是贺拉斯所面临的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展开。
二、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古今之争”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今之争”是这一矛盾的第一次遭遇战。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就是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重新被发现,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这些古代典籍中所揭示的文艺规律使得当时的意大利学者大开眼界,一时译者、注者、评者、释者蜂起,出版了一批同样名之以《诗学》、《诗艺》的论著,讨论的问题也往往不出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所论,如悲剧、喜剧、情节整一律、卡塔西斯、诗的恰当性、文艺的功用等。
说到底,这些意大利学者还是在如何对待古代希望罗马文学传统的问题上较劲,从一开始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进而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古今之争”。引发这场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文学创作的深刻变动,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抒情诗、薄伽丘的《十日谈》、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的问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典籍所总结的传统规则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些传统规则已经无法说明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功探索。于是,一方面是追随时代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是1000多年前建立的传统规则,是肯定前者而挣脱后者的束缚,还是固守后者而限制前者的发展,二者必居其一。每一个论者都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派意见认为,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所建立的文艺规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不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后人提出的新的诗艺尚不足以动摇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权威地位,没有一门艺术能够不遵从古人建立的规范而取得成功。在这一派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明屠尔诺。他对以阿里奥斯托的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罗兰》为代表的新型诗颇多訾议,认为与创造史诗的希腊诗人以及创立诗学的希腊学者相比,传奇体叙事诗的发明者只能算是化外之民,他们从来没有学问的名气,创作仿佛只是靠天启发,要从中寻找新型的诗艺,那就犹如在非洲沙漠中寻找绿树青草,“尽管这些人为了表现自己才华学问都很强,曾努力向世人介绍一种新的诗艺,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有这么大的权威,使我们宁可相信他们而不相信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他看来,这两位古人的权威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一次是真的,就必然在任何时代都永远是真的;尽管风俗和生活可以因时代的差异而改变,真理却并不因此就改变,时代可以更易,真理一成不变”。因此如果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依据荷马史诗而创立一种真正的诗艺,那么就无法想象还能够另立一种诗艺与之并存,例如诗歌创作因时代而发生的变化并不能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即诗可以采用多于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情节,并使其他各部分与之相协调。他据此认定:“哪一门艺术、哪一门学问、哪一种训练(不论是建筑、音乐、绘画、雕刻、军事或医学)里,一个人可以不努力步古人后尘而能够工作吗?不是愈紧密地追随古人就愈能得到称赞呢?”[3]
针对保守派对于《疯狂的罗兰》的诟病,钦提奥写了《论传奇体叙事诗》一文予以反诘,他指出,有判断力和熟练技巧的作家决不应该让传统束缚自己的自由,而只敢沿着前人所指定的老路向前走。他特别强调在意大利的此时此地与古希腊的彼时彼地之间存在着时代和民族的差异,因此在文艺创作上决不能拿彼时彼地的规矩法则来硬套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应作如是观。他指出,保守派要求传奇体叙事诗恪守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所定下的规则,却不考虑这两位古人既不懂我们的语言,又不懂我们的写作方式,这是不合情理的。例如情节,亚里士多德是主张单一情节的,但是有理由认为,诗人写传奇体叙事诗时,“他最好不限于一个人物的单一动作,毋宁使用一个人物的许多动作”,因为“情节的头绪多,会带来多样化,会增加读者的快感”。再如语言,他认为,意大利塔斯康尼诗人的作品在语言上的价值,比起希腊拉丁诗人的作品在语言上的价值并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应该拿希腊拉丁诗人的框子来约束塔斯康尼诗人。又如题材,他认为,不管是采用何种题材,都应该适应此时此地的现实需要,“尽管诗人所用的材料是古时的,也要使这些古时材料适应现时的风俗习惯,要运用一些不符合古时实况而却符合现时实况的事物”[4]。他觉得维吉尔的《伊尼德》就是一个好例子。史诗中的特洛亚战争,是诗人按照自己时代的意大利的习惯来描写的,其中有许多在史诗所描写的时代尚不存在的事物,尚不曾流行的风俗习惯。
不难看出,在钦提奥的论述中贯穿了一个主旨,那就是对于此时此地的时代生活和民族习惯的执着,在他看来,这才是制订文艺法则的根本依据,而从彼时彼地延传下来的文学传统只有与之相契合,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无视此时此地的时代生活和民族习惯,仅止于照搬惯例,墨守陈规,那么传统便只能成为文学发展的一种羁绊和障碍。必须指出的是,钦提奥强调文学必须因时适变、因地适变的社会学观点并不只具个人意义,而是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普遍倾向,正是紧扣时代生活脉搏的社会学观点使得这些意大利学者既为发现古代辉煌的艺术精神而倍感欢欣鼓舞,又对这种重新得到恢复的传统作出符合新的时代精神的突破和超越,继续推动文学艺术向前发展。
三、17世纪:第二次“古今之争”
其后一个世纪,在法国,“古今之争”烽火再燃,不过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形成了新的话题。
17世纪的法国文坛弥漫着新古典主义的沉闷空气,此时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逐步臻于鼎盛,将文化归于其严密控制之下,带有官方色彩的法兰西学院崇尚理性,鼓吹自我克制,宣扬个人需要服从国家利益,推行宫廷趣味和贵族趣味,在艺术上主张谨守古代法则,防范任何越轨行为。新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布瓦洛则进一步在《诗的艺术》中将官方的文化政策改铸成学术规范,要求诗人“首先须爱理性”,“一切要合乎常理”,告诫诗人不要“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让“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劝诱诗人“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你们唯一钻研的就应该是自然”。布瓦洛所说的这一切,从根本上讲都是指路易十四的王权统治,在他看来,路易十四的王权统治就是真理的化身,是符合人性之常、人情之常的最高原则。这也就决定了布瓦洛对于文学传统的保守立场,他以宫廷文艺代言人的身分自居,对于那种从官方立场看来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创作倾向表示反感,觉得必须制订文艺规范严加限制,他从古代希腊罗马延续下来的文艺规则中寻找依据,并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对于这些文艺规则穿凿附会的阐释僵固化、神圣化,将其奉为不得有丝毫违背的金科玉律,最突出的就是确立了“三一律”的法典地位。其实,所谓“三一律”的形成乃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原意,按说这一美学原则的提出在文艺复兴时期不无意义,具有总结艺术规律、规整创作行为的作用。但是到了布瓦洛手中却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曲解,制定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5]这一清规戒律,将其与维护王权统治的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并使之教条化、公式化,这就势必走向反面,成为束缚文艺创作、阻塞文艺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了。另外,布瓦洛还将古代希腊罗马的杰出作家悬为毋庸置疑的至上标准,认为他们享有这一崇高地位的充足理由在于他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博得了众人的赞赏,因此后人只有摹仿古代作家,才能在创作上取得成功:“我们法国最大的作家们的作品的成功正要归功于这种摹仿,您能否认吗?”“形成拉辛的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莫里哀是从普拉图斯和太伦斯那里学得他的艺术里最精妙的东西。”[6]
以布瓦洛为代表的保守思想遭到具有革新意识的学者的拒斥。法国作家夏尔·贝洛勒1687年1月27日在法兰西学士院宣读了《路易大帝的世纪》一诗,对固守传统、是古非今的新古典主义率先发难,诗中宣称:“我面对古人,不对之屈膝,他们伟大是确实的,但同我们一样也是人。”由于观点的严重龃龉,布瓦洛当场提出抗议并退席而去。此后贝洛勒又写了后来结集为《古今之比》一书的一系列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位作家封德奈尔也发表了《闲话古人与今人》一文以声援贝洛勒。在革新派中值得注意的是圣·艾弗蒙。他对于新古典主义的否定更加坚定,抨击更加有力,论理也更有说服力:“我们既不过分推崇古人,也不过分歧视当代,因而我们也不会再以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为当代戏剧创作的唯一典范了。”[7]在他看来,那种千古不变的永恒规则毕竟很少,要想永远用老规矩来限囿新作品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诗人想沿用古代的模式,按照已被时间推翻了的规则来写诗,那么他们只能写出一些坏诗。在这个意义上说,“荷马的诗永远会是杰作,但不能永远是模范”。他认为,任何诗都属于它的世纪,“假如荷马活在现代,他也会写出一些好诗,能适应他所属的世纪”。一旦时代变了,诗也应该随之改变,“总之,神祇,自然,政治,人情风俗,一切都变了。这许多变化不会在我们的作品里引起变化吗”?“宗教,政治机构,以及人情风俗的差别都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造成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把脚移到一个新的制度上,才能适应现时代的趋向和精神”[8]。总之,在以圣·艾弗蒙和贝洛勒为代表的革新派的意见中贯穿着一个非常有力的思想,那就是文学必须因时适变的社会学观点,惟其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做到厚今而不薄古,既肯定文学传统的意义,又确认变革传统的必要性。正是这一稳妥而不失通达的观点使之在17世纪的“古今之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18、19世纪之交:第三次“古今之争”
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各国相继掀起了一场文学运动,人们起始心存疑惑继而争先恐后地称之为“浪漫主义”,矛头所指,是其时仍有较强势力的新古典主义。
最早提出“浪漫主义”的是谁,这一问题至今仍有歧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德国的史莱格尔兄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浪漫主义”的褒扬与对于“古典主义”的贬抑,在史莱格尔兄弟的论述中是大量的,他们借此高张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弗·史莱格尔指出:“莎士比亚的诗歌是浪漫的,可是他的浪漫是真正的,不偏面的,不只是游戏性的,而且也是深刻、严肃和宏伟的,是最充实、完备的意义上的浪漫。至少在这一点上让他做我们的模范吧!”[9]奥·史莱格尔也说,现代文学史中真正划时代的作品“是同古代的作品相对立的,但却不能不承认它们是优秀的作品,……人们把古代文学称之为古典的,把现代文学称之为浪漫的;……这种称法是很恰当的”[10]。他还在一系列讲座的讲稿中对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文学作出评说,总的说来是称赏古希腊的艺术精神而批评古罗马的摹拟窥测,叹服中世纪的史诗、传奇和民间歌诗,盛赞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文学而否弃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
另一个推动浪漫主义在欧洲广为播扬的重要人物是斯达尔夫人,她在1813年出版了《论德国》一书,对德法两国的民族精神进行比较,并将德法两国文学放在西欧南北文学的大范围中进行比较。她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文学划归“南方文学”,而将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文学划归“北方文学”,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多神教与基督教、古代与中世纪、希腊罗马体制与骑士制度的区别,在文学上则形成古代趣味与现代趣味的分野。她沿用了史莱格尔兄弟的说法,将这两者称为“古典诗”与“浪漫诗”,并公开表明了对后者的偏爱。她在《论德国》中坦陈其偏爱的理由是:“对我们来说,问题并不是要在古典诗与浪漫诗之间作抉择,而是在机械模仿和自然启示之间作抉择”,“拟古的作家顺从趣味方面最严厉的戒律。因为他们既不能凭据天性,也靠不上自己的记忆,便不得不受制于若干戒律。”[11]可见她也是依据欧洲“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对于文学传统或因循守旧或锐意创新的殊异而作出褒贬的。
史莱格尔兄弟和斯达尔夫人上述论著所张扬的思想在西欧各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保守势力对他们横加指责,而激进势力则发出一片叫好之声,甚至还觉得他们不够大胆、不够带劲。这是欧洲继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之后爆发的一次规模更大的“古今之争”,法国有人将论战文章结集出版,仅1813年到1816年间的文章就编成近500页的一大卷书[12]。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英国作家卡莱尔指出:“在我们中间,在过去的三十年内,有谁没有提高声音,用双倍的力气赞美莎士比亚和大自然,咒骂法国趣味和法国哲学呢?”[13]这场争论在意大利也激起了波澜,老一辈人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而年青一代则起而捍卫这些“浪漫主义”的施洗者,浪漫主义诗人白尔谢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把古典主义诗歌叫做‘死人的诗歌’,把浪漫主义诗歌叫做‘活人的诗歌’”[14]。总之,在这场“古今之争”中,不管保守派如何招架,浪漫主义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决了新古典主义用古旧的规矩法则构筑的堤防,一泻千里而横绝于世。
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史莱格尔兄弟还是斯达尔夫人,他们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对峙、厮杀之时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其立足点置于一种历史主义精神、一种社会学倾向,这就是说,他们总是从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之中去寻求这种价值判断的根据。弗·史莱格尔一再说过“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历史”,“每门科学的完成往往无非是其历史性的成果”,同时对任何非历史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做法表示厌弃,进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肯定浪漫主义兴起的合理性:“只有浪漫主义的诗像史诗那样能够成为整个周围世界的镜子,成为时代的反映。”[15]奥·史莱格尔也说:“古代趣味和现代趣味的这种巨大的普遍的背反,是由历史提出来的,只能留待理论来解决。”[16]在这方面斯达尔夫人的观点更值得大书一笔,她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1800)一书一般被认为是文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此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即“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17]。这种富于历史主义精神的社会学方法也成为她文学传统论的准则,成为她衡量浪漫诗与古典诗的标准,她在《论德国》中就一再表达这样的观点:“古代文学对今人而言是一种移植的文学,浪漫文学或曰骑士文学却是在我们自己家里土生土长的,使浪漫文学桃李竞放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宗教与制度。”[18]由此可见,浪漫主义文学挣脱新古典主义的束缚,在18、19世纪之交的“古今之争”中取得决胜,终于蔚成掀天动地、席卷整个欧洲的时代之潮,可以在文学社会学在此时的真正确立之中找到原因。
五、小结
从以上对古代到近代几个时期西方文学传统论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见出这样几个问题。
在西方文论史上,“古今之争”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虽然它有时表现为隐性的(如贺拉斯),有时表现为显性的(如后三个时期),但都说明文学传统问题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脑际,这确实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人们只有恰当选择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才能找到进一步发展的路。这就使得一部西方文论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围绕着文学传统问题所展开的“古今之争”的学术史。在上述历次“古今之争”中,有时保守派的势力显得比较强大,但在争论中占据真理因而代表着一定时代文学传统论的前进方向的往往是革新派。其原因在于后者能够拒绝那种固守既定观念而无视活生生的创作实际的僵硬做法,密切关注文学创作的进展,接受创作实践的启示,从而对于文学传统问题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和选择,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的朝气蓬勃,18、19世纪之交浪漫主义锐意创新的兴会风发,都为当时主张变革传统的激进人物输入了足够的底气和激情,甚至对一度持保守态度的人们也起到纠偏的作用,像史莱格尔兄弟最早对于浪漫主义是持有异议的,但由于能够直面浪漫主义勃兴的生动局面,受到这一文学新潮的积极感召,终于在立场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些革新派也能不失时机地顺应新时代精神气候和审美需要的嬗变,在文学观念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突破旧有的规矩法则的限囿,例如钦提奥放弃从古希腊延传下来的戏剧体诗只能表现单一情节的规则,主张应该允许表现复多情节,就是以满足当时读者新的审美趣昧为充足理由。
革新派在“古今之争”中先声夺人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大多并不仅仅就事论事地探讨文学传统问题,而是更加注重解决问题的原则、规范和方法。韦勒克在评论奥·史莱格尔的贡献时指出:“他没有失去对一套原则和规范的把握。不讲原则和规范,批评家就不再是批评家而变成了单纯的考古家。”而奥·史莱格尔所把握的原则和规范就体现在“他所想到的却是他的时代和创造性艺术的需要”[19],也就是说,像史莱格尔这样的革新派非常重视社会学方法的运用,总是用时代生活的需要来衡量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问题,这就使其文学传统论往往表现出一种犀利而坚实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古代到近代西方文学传统论的社会学倾向乃是一脉相承。虽然文学社会学的真正确立以斯达尔夫人1800年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为标志,但其萌芽可以上溯到很早,贺拉斯、钦提奥、贝洛勒、圣·艾弗蒙等都作出过有关论述,例如贺拉斯说每个时代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圣·艾弗蒙说诗必须适应它所属的世纪,弗·史莱格尔说浪漫诗是时代的反映等,都是体现着文学社会学思想的精彩表述。因此斯达尔夫人的文学社会学思想的形成虽然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实在也是以前人的思想成果为起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可见梳理西方文学传统论的演变过程,也不失为透视文学社会学发展脉络的一个独特角度。
〔收稿日期〕2000-07-03
标签:古希腊论文; 贺拉斯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罗马市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诗学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