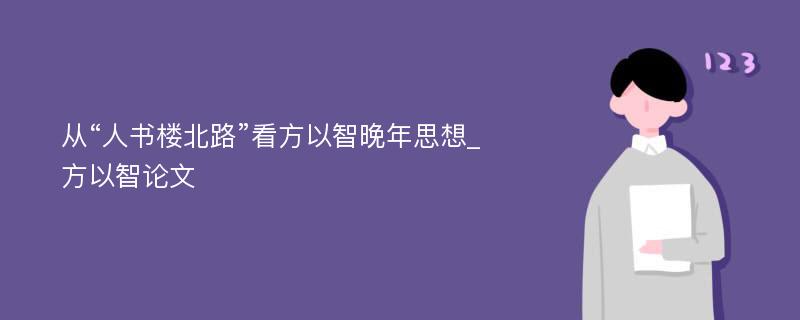
从《仁树楼别录》看方以智的晚年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思想论文,仁树楼别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以智(1611-1671)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其学行与气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呈现出相当清晰的面貌①。唯因方氏思想繁杂,行文晦涩,多数作品未获整理②,所以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亦复不少。
其中,方氏的晚年思想归属即是分歧较大的一个。最极端的看法认为,方以智“为僧后的著作以及语录,除了例行仪式上虚应故事外,毫无坐禅佞佛的迹象”③。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方以智禅学思想兼具理论与实践,在禅宗史及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④虽然多数学者相信,方氏最后选择的是一条以儒学为主、会通三教之路⑤,但也不乏“任何将药地思想划归派别的尝试终归徒然”这样的斩截之论⑥。
分歧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不管怎么说,解决争论的最有效途径,都仍然是回到文献本身。下面选取由方氏门人笔录的一篇短文《仁树楼别录》加以分析,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些许的助益。
《仁树楼别录》是一篇对话体短文,收录在《青原志略》卷三。全部内容加起来,仅有六千五百余字。之所以选取此文来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该文虽收在佛教的寺志中,但讨论的话题却集中在儒学。所以由这篇文字,可以了解方以智逃禅之后对待儒家的态度。
《青原志略》起初由净居寺住持笑峰大然编修,笑峰死后,书稿交到方以智手中,并得以最终成书。笑峰的原稿篇幅很短,所收内容仅“就净居柱壁存者耳”⑦。方以智在施闰章的建议下,扩大收录范围,新增了“书院”、“杂记”等卷,所以不少内容已经超出了佛教的范围。
书中特辟“书院”一卷,主要与江右王门讲学此山有关。青原山是唐代高僧行思驻锡之所,所以净居寺一直被看作禅门祖庭之一。明朝中叶,王学兴起,该寺又成了阳明弟子邹守益、罗洪先等春秋会讲的场所。从史志的角度讲,增列“书院”卷自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它也的确为身处佛门中的方以智,提供了一个重新检讨儒学话题的机会。
“书院”全卷共收文四篇,第一篇《传心堂约述》(郭林)摘录了与青原山有关的数十位儒者(主要是王门后学)的言论。末两篇分别叫《青原藏书议》(宋之鼎)、《青原山传心堂翼楼乞书公启》(方中履),讨论的都是关于藏书的问题,题目前面已经标示了它们的附录性质。真正构成全卷中心,并能彰显方以智本人思想的,其实就是《仁树楼别录》一文,这是该文值得认真对待的主要原因。
第二,《别录》的编者是方以智亲炙的弟子,参与对话的人既有方以智自己,又有他最为器重的朋友,这足以保证记录的可靠与准确。
关于此文的编者和参与者,《别录》题下有一段小字附注:“郭林、方兆兖因左藏一寓此,以朝夕所闻宓山老人者,汇其要而录之。”郭林和方兆兖都是方以智的弟子,左藏一本名左锐,字右錞,是方以智的同乡兼好友,“宓山老人”则是弟子们对方以智的尊称。从附注可知,郭、方二人乃《别录》的实际执笔者,他们从事笔录的机缘在于,左藏一来到了青原山作客,并与方以智进行了持续的交流,文中所记载的,正是两人对谈的要点。
方兆兖的情况,文献记载不多。但郭林、左藏一与方以智的关系,皆非寻常可比。《青原志略》卷五收有《随寓说》,乃方以智专为郭林所作,其中有言曰:
随寓者,郭入冋之行鄣也。入冋年四十矣,不婚不宦,如刘讦、邢量,抗行不苟,而好读书。自汋林从愚者游,至青原,居紫海堂。携一奚童,灌园炊爨,此外闭门不轻过人。……施先生既修传心堂,翼以仁树、见山,留此守之。……居青原馆且五春秋矣。初读书,见古今人聚讼不快,读《通雅》而大快。已读先人《周易时论》所衍象数约几,孜孜学之,时有所触发。已读《鼎薪》,半解半不解。已读《炮庄》,则不可解矣。……揭子宣刻我中年之《物理小识》,入冋大好之,因与子宣穷天学,究物理。自中年授徒,方以智所收弟子可分教内教外两类。教内者如兴种、兴斧、嗒然等等,教外者则有戴移孝、揭子宣、吴山舫、胡映日诸人。郭林显然属于教外弟子中的一员。与通常的俗家弟子不同,方以智的这些教外门生多数不是为学佛而来,他们观天象、察物理、明医术、究乐律,对格物之学的关注远远大于生死解脱问题。这一点从郭林好读《通雅》《物理小识》但却不解《炮庄》《鼎薪》即可看出。可惜的是,狷介之性使郭林并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⑧。
与郭林相比,左藏一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此人不但名号繁多,而且与方家渊源颇深。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方氏作品如《周易时论合编》、《药地炮庄》、《物理小识》之中。《青原志略》卷五收有他的一篇短文,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或问中五之说于宋山子,宋山子曰:难言也。錞少见王虚舟先生衍河洛,犹以为一端也。中年降罔,乃始究心性命。极物而知其则,不定中定,《易》其至矣乎。世出世法,近愈离跂。吾乡方野同廷尉公,与吴观我太史公,辨析二十年,而中丞公潜夫先生会之于《易》。合山栾庐,得从药地大师盘桓,始知圣人之神明如是,我之神明亦如是,而乃自负耶。据此文可知,左藏一还有一个别号叫宋山子。他早年曾经问学于易学家王宣,而王宣正是方以智年轻时的老师。当方以智庐墓合山、为父守丧之时,两人开始正式交往。方以智本人对左藏一的学养和气节似乎同样不能忘怀,下面这句话就是他从青原山发出的盛情邀约:“青原荆沥杏仁,正慰妙叶。穷崖多骨立之士,我翁何不来此共盘桓耶?”⑨
最后,《别录》完成的时间在方以智入主青原之后,最足以作为其晚年思想的实录。
方以智著作很多,但要么属于中年以前的作品如《东西均》、《易余》、《通雅》、《物理小识》⑩,要么从中年时期就已经开始编写如《药地炮庄》(11)。由于不断地进行增删,要判断书中哪些内容在先,哪些内容在后,非常困难。
《别录》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一则它的篇幅很短,内容相对集中,二则时间也可大致推定。
据前引方以智《随寓说》,“仁树楼”乃“传心堂”的翼楼,捐建者为方以智好友施闰章。方以智正式入主青原在康熙三年(1664)的十一月(12),与他一起上山的还有弟子郭林。郭林最初的住所既然叫“紫海堂”,说明此时仁树楼一定尚未完工。所以,由郭林所录的《仁树楼别录》,成文时间决不会早于康熙三年的年末。
并非巧合的是,左藏一也于同年的冬天来到了青原山。方以智从叔方文《嵞山续集》卷一有诗《喜左又錞见访有赠》:“君去青原山,言访炮庄老。淹留历冬春,禅学共探讨。当机忽开悟,胸中竟渊灏。便应裂儒冠,相从苾刍好。何为复还家,尘缘惹烦恼。……君今婚嫁毕,室又无綦缟。青原有同心,自合归三宝。性命事非轻,口腹何足道。”方文此诗作于康熙四年(1665),左藏一既然能够在青原山“淹留历冬春”,那么他一定是在康熙三年的冬天入山,住到第二年的春天才离开。除非左藏一此后还有另外一次青原之行,否则与他和郭林都有关系的《仁树楼别录》就只能完成于康熙四年年初的数月间。此时距离方以智辞世,还剩下不到六年的时间。
和方以智本人的后期作品相比,《仁树楼别录》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没有明显的禅味。这可能与对话的参与者有关,比如郭林、左藏一,皆非好禅之人。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所谈论的话题集中在儒学。
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曾引述其曾祖方学渐的一段话,说明三教言说方式的不同:“孔子尽性知命而罕言,言学以正告者也。老尊命以殉性,反言者也。佛尊性而夺命,纵横倍仵者也。”(13)所谓正告,就是用正面的、明晰的、让人容易理解的语言陈述自己的主张。反言和纵横倍仵者就不同了,它们可以借助于机锋、拈提、冷语和棒喝。反言和纵横倍仵不是没有作用,它可以救俗儒之拘,但儒者若“慕禅宗之玄,务偏上以竞高”,就会带来“六经委草”的恶果(14)。方以智既有此自觉,在涉及儒学问题时,他显然不愿自蹈覆辙。
《别录》的正文,可以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篇幅较短的,是全文之引言。后面一部分按照讨论的问题,分成十三个相对独立的段落。方以智本人的观点,主要就集中在这个部分。
下面这段话,便是第一部分的开场白:
左子曰:皖桐方君静廷尉公(大镇,万历己丑进士,魏踏时罢,号野同),与吴观我太史辨析二十年,而王虚舟先生合之(金溪王宣化卿)。潜夫中丞公(孔炤,丙辰进士,以连理之祥号仁植。在职方,忤魏忠贤。抚楚剿贼,忤枢辅),晚径《周易时论》,发挥备矣(15)。
熟悉方以智作品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段被人重复了无数次的话。从序言到凡例,从师长到旧友,从门生到子嗣,凡提起方以智者,很少有不联系到他的家学(祖方大镇、外祖吴观我、父方孔炤)和师承(师王宣)的。
这种持续的重复,一方面当然是要提醒我们,方氏家学对于方以智来说,决非可有可无,离开方家的世传易学、吴观我的三一论、王虚舟的河洛说,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方以智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它似乎也隐藏着另一层含义,即形迹上的遁入空门,并没有影响到方以智通过别样的方式恪尽孝道(16)。方以智自己说过的一段话,就是最好的明证:“吾将聚千圣之薪,烧三世之鼎,炮之以阳符,咒之以神药,裁成之以公因反因,范围之以贞一用二,时当午运,秩序大集,使天下万世晓然于环中之旨、三一之宗,谓方氏之学,集儒、昙、道教之成,克尽子职,所以报也。”(17)“克尽子职”这样的话,出自青原山净居寺住持之口,多少还是有点让人意外的。
为了说明方氏家学的贡献,引言中摘录了不少方大镇、吴观我和方孔炤的言论。由于三人的著作都残缺不全,所引言论的归属并不总是十分明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言论或多或少都与后面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关。把三个人的说法综合考虑,可以看出核心的内容在以下两点:
第一,“好学”是“觉悟”的前提:“学而不厌,所以享其不学之能也。若倚不虑不学,早已失矣。又况黠智不学而能,正智便用不出,复令高榜呵学,能无惧乎?”“仁智好学,偏见乃忘,学固所以游息而养之也。”
第二,易象蕴涵着普遍的秩序,是圣人效法的对象:“《易》以象数端几徵性中天命之秩序,非文词理语、情识机锋之所能增减造作也。率其秩序,因物还物,生死还生死,我不动心,总一大物理而已。”“圣人极深而体寂感之蕴,因物而悟生成之符,观器而悟裁成之法,极数而尽天下之变,视曜纬山川以为官肢经络,就呼吸寤寐而定元会死生……尧舜知历数而授允中,孔子举扐闰而明大衍。兴礼乐,制数度,成变化,行鬼神,橐龠在此。”
崇尚实学本是方氏家学的老传统(18),表彰易数则与方孔炤、黄道周狱中切磋有关(19)。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几乎成了方以智回答任何问题都要诉诸的前提。
作为全文的中心,《别录》十三段对话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如何衡定宋明儒内部之争?陆象山、张子韶是否学禅扫文字?经世的圣人如何了生死?身心锻炼是否有效?受命之说如何验证?有无纷争如何统一?世出世各为一门,何以互相牵引?儒释道三教异同如何?孔子言知命、知礼、知言,孟子何以但讲知言?易学之地位如何?怎样处理博约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成了交谈的内容。
由于文本的性质本只是随意交流的实录,所以这些问题看上去显得杂乱无章,近似的内容并没有合并一起,少数地方还有些重复的迹象。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触及到了那个时代儒学的命脉。经过刀光剑影的洗礼之后,儒学的正途何在早已成了那一代人苦苦思索的问题。追问儒家内部之争如何衡定,追问博约关系,追问三教异同,显然都离不开这个大的背景。
方以智的回答,有一些与他人并无大的差别,譬如当他说“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时,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有些则源于他个人的思考。但最难得的是,无论与别人是异是同,他总能保持思想或观点的一贯性,并回归到他家学的传统之中。
下面是对几个比较重要问题的问答,值得我们特别地征引在这里:
(1)问:“朱陆诤,而阳明之后又诤,何以定之?”曰:“且衍圣人之教而深造焉。圣教小学大学、小成大成,总以文行始终之,《内则》、《学记》详矣。息焉游焉,言乎文行之相须兼到也。朱子曰:‘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矣。’《周礼》三物六艺,乃六德六行之日用器具也。博文约礼,成德达才,而化雨一贯矣。”
朱陆之争是宋学的大问题。无论是各执一端,还是曲为调停,后世儒者很少能够自居于这场争论之外。阳明后学亦然,同属浙中的龙溪、绪山已经不同,更不要说还有什么江右王门、泰州学派等等。儒家内部如此多的分门别户,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判定是非?
对于这个问题,方以智的回答是,必须回归孔子“文行忠信”的教导。《礼记》中《内则》篇对洒扫应对、言谈举止的规定,《学记》篇对论学取友、知类通达的分辨,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力行”和“学文”必需“相须兼到”、缺一不可。
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说“学文”是“力行”的前提,“三物六艺”是“六德”“六行”的基础。这大概也是朱子那句话“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矣”的意思。
(2)问:“陆象山、张子韶学禅扫文字,然乎?”曰:“陆象山亦指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病。张子韶曰:‘久不以古今灌溉胸次,试引镜自照,面目必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二先生甚言书之不可束也。世议以为落空,非矣。天竺小学诵《悉昙章》,长通五明:曰声明,即声律文字也;曰医明;曰巧明,即养身、历天、务民、宜物、制器之类也;曰谓因明,即治教辨当诸义所出也;曰内明,是身心性命之理也。……《法华经》曰:‘治世语言,资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悖。’《华严》五地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世间辞赋该练,历律伎艺,莫不通晓,故能涉世利生。……谁谓佛入中国而不能通此方之书乎?达磨对彼时经论支蔓、福祷功德之病而药救之,指出心体,尊正法眼也。孰是由专而通者,遂举一而废百哉?程子呵谢上蔡玩物丧志,是程子亦扫文字矣。上蔡后见程子读书精细而讶之,犹不悟耶?盖谓读书者,贵求实际也。半静坐半读书,朱子法也。
自朱子判象山为禅后,持此说者可谓比比皆是。张子韶因与大慧宗杲的关系,更被视为以禅滥儒的典型。不过,方以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不但引用陆、张二人反对“束书不观”的言论,证明世俗说法的错误;而且特别指出,佛教内部同样有着重读书博学的传统,《法华》之“治世语言”、《华严》的“五地菩萨”都是明显的例子。达磨面壁,实际上是为了救正佛学内部“经论支蔓”、“福祷功德”之弊。正如程子之呵斥上蔡“玩物丧志”,实际上针对的是上蔡的“死记硬背”。禅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舍弃义学,程子本人读书精细的程度也并不亚于上蔡。问题的关键在于,阅读经典必须“贵求实际”,确实有益于自己的身心性命才行。
(3)曰:“世出世分门,何相牵引?”曰:“同此宇宙日月,同此身心性命,称谓有方语,正宜通而互征之。……自阳明以来,诸大儒皆穷究而互征也。三间之喻,以堂、奥、楼分合之,更明矣。鄙愿茅塞,浮才苟偷,忽有杨宗黄帝、墨宗禹,犹芝草也。徐斡不忧异术而疾恶内关,何待阳明激发乎?圆机之士,分合皆可。乘愿补救,正须互穷。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参过甚深之宗,乃知层层利害,不为人惑,而时用为药耳。
这段话讨论的是三教关系。作为会通论的支持者,方以智的回答与其他人的说法并无实质的区别。所谓“同此宇宙日月,同此身心性命”,都是从人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入手。因此,儒佛之异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语言学(方语)的问题。借助“通而互征”,不同的学说和系统甚至可以起到互相补救(芝草)的作用。
文中提到的“三间之喻”,是指王阳明下面这段话:“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20)阳明的本义也许是要强调,儒家性命之学无所不包,不必外求于佛老,妄分三教反而会让自家的门厅狭窄,但这段话看上去更象是主张三教一家,完养此身之仙、不染世累之佛,皆不悖于圣贤之道。阳明后学纷纷走向儒佛不分、亦儒亦释,恐怕与这种说法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方以智对阳明三间说并不满意,他自己提出了新的堂、奥、楼三分法。此说的原始出处不详,但大意保存在少子中履的一段引述之中:“《浮山闻语》曰:新建三间之喻未也。明堂必南,而为天地理其家事者也。北奥者,守黑者也。骑危者,虚空座也。尊主者曰:屋以栋为主乎!辨实主者曰:屋以基为主乎!两扫者曰:栋与基皆非也,屋以虚空为主者也。……理者曰:人适时乎筑基构栋之屋,藏坐卧焉。……时乎屋而屋处……时乎晦息则奥,时乎诵读则牖,时乎治事享客则堂……时其时,位其位,物其物,事其事,是虚空之中节也,是不落有无之屋理也。……虚空之屋主,适统御于明堂,是明堂之政,乃主中主也。”(21)
文中的“明堂”代指儒家,“北奥”代指道家,“骑危”代指佛教,“理者”则指方以智本人。儒家以栋梁为屋之主,道家以地基为屋之主,佛教以室中虚空为屋之主,三家互不相让,纷争无已。但在方以智看来,各家皆有其时用,正不必以此非彼。风雨之时处屋,晦息之时居奥,治事待客选择明堂,各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因此不执一端,应时而动,才真正合乎“不落有无”的“屋理”。
和阳明三间说相比,方氏此说的侧重点显然已经不同。阳明的重心在于说明“二氏之用,皆我之用”,方以智强调的则是三教各有其用。阳明突显的是儒家之大、二氏之小,方以智表达的却仍然是他一贯的“乘愿补救,正须互穷”的大道理。
不过,也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方以智视作三教平等论者。引文末尾那句“明堂之政,乃主中主也”,早已曲折地披露了他的心迹。只是,与那些恪守道统的儒者不同,他更愿意相信佛、道皆有其并行不悖的价值而已。
(4)深几而言,为物不二而代明错行,尚不信欤?夫不得不两,不得不参,皆大一之所布濩也。愚故统征之以《易》,而藏天下于学。因果费隐,即二是一。才三备万,谁不具乎?然不发愿,不好学,终不能知,而又不能藏诸用也。骤而告之,能免孙休之诧惊哉?然午会全彰,雷雨出云,因缘时节,知罪任之。烧四炷香,一求有余者养贤,一求学者虚受,一求方正人穷知其故,一求畸颖人藏悟于学。
如果说“堂奥楼三间说”只是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那么上面这段话无疑算得上是一种公开的自白。“愚故统征之以《易》,而藏天下于学”,出自堂堂的净居寺住持之口,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开头数句即所谓易道之核心,方氏家学更喜欢用“公因反因说”来表达它。所谓“为物不二”,太极(太一)之本体也,是为公因。所谓“代明错行”,阴阳之变化也,是为反因。阴阳变化中不得不然秩序,皆为太极本体的表现,是为公因藏于反因之中。了解阴阳变化的秩序必须诉诸于“学”,但几微难测之理必须借助于“悟”。由“学”而“悟”的过程,即所谓由“质测”而“通几”。否则,必然堕于空虚无实之途。
(5)曰:“必言象数,何也?”曰:“《易》以象数为端几而作者也。虚理尚可冒曼言之,象数则一毫不精,立见舛谬。盖出天然秩序,而有损益乘除之妙,非人力可以强饰也。本寂而中节,确不可欺者也。”曰:“多言历、律、医、占,何也?”曰:“征几也。不以实征,则何以知天地四时之筋节,人身运气经脉之代错乎?上古无书,即以天地身物为现成律袭之秘本,而神明在其中。……夫生千圣之后,不能收千圣之慧;受天地之中,不能明天地之符,成变化,行鬼神,制作礼乐,反似诞妄。果可以苟免之,凡夫讪圣人多事矣。周、孔之徒不知律袭三才,所谓百官宗庙专恃虚言杜撰乎?除却鬼窟,火不离薪。实学虚悟,志士兼中。故曰河洛中五之纲,乃羲农尧舜禹文周孔征信秩序之天符也。
这段对话同样讨论的是易学问题。方氏家学上承邵、蔡,属于易学中的象数一系,所以双方谈论的话题自然也就围绕着象数历律医占而展开。方以智的说法,如“象数则一毫不精,立见舛谬。盖出天然秩序,而有损益乘除之妙,非人力可以强饰”,如“不以实征,则何以知天地四时之筋节,人身运气经脉之代错”,与上段话的意思大体一致,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比较有针对性的是后面数句:作为周孔之徒,不知“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怎能知道自己的“百官之富”、“宗庙之美”?难道专靠虚言杜撰就可以了吗?这种反问,与黄道周的名言“如此,学问止于《中庸》,行事尽于《论语》,《诗》《书》《礼》《乐》《春秋》何故作乎”(22),意义正同。它们针对的,其实都是晚明以来的空疏学风。
末尾“实学虚悟,志士兼中”,就是上文“藏悟于学”的另外一个说法。“河洛中五之纲,乃羲逐尧舜禹文周孔征信秩序之天符也”,则再一次强调了《河图》《洛书》在儒家学统中的重要性。
以上大概就是《仁树楼别录》的主要内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仅凭该篇短文并不足以彰显方以智晚年思想的复杂性。方以智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面相完全没有触及,他登堂说法所留下来的文字要超过《别录》很多倍。不过,从《别录》的有限材料,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方以智对知识的关注并没有因为逃禅而丢弃,钱澄之的说法需要更正。
在《通雅序》中,钱澄之这样写道:“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犹不肯废书。独其所著书多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若所谓《通雅》,已故纸视之矣。”(23)这与《别录》下面的话显然互相冲突:“故拈提与考究,原自两路。制欲消心之言,与备物制用之学,亦是两端,偏费则皆病矣。”(24)
第二,青原山住持的身份仍然没能使方以智忘掉儒者的关怀。荒江野岭,三五僧俗,谈的是朱陆之争、孔孟之别、格物之则、与民正语,本身就是值得回味的事儿。施闰章不愧为方以智的知己:“药公非僧也,卒以僧老。其于儒言儒行,无须臾忘也。”(25)方中通替父亲法语所作的后跋,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本传尧舜禹汤文周之道,转而集诸佛祖师之大成,而尧舜禹汤文周之道寓其中,时也,非人也。教以时起,道以时行,何莫非异类中行乎?何莫非因法救法乎?”(26)
第三,三教会通不意味着学无宗主,“统征于易”即为方以智的自觉选择。晚明以来盛倡三教合一者极多,其中有和尚,有道士,当然也有儒生。但通常情况是,论者皆以自家学说为纲宗,进而再统摄另外两家之学,鲜少等视三家,不分彼此者。方以智也不例外,只不过身份的特殊使他难以表白而已,《别录》下面这句含“苦”带“笑”的话就是明证:“闲人笑曰:别路三不收,牛马听呼耳。且以象数医药为市帘,山水墨池逃硎坑。冷眼旁观,有时一点缘不得已之苦心,固不望人知也。”(27)
第四,二十年的僧人生活也并不能全看作“虚应故事”。最初的逃禅当然实非得已,但深入禅学之后,方以智发现佛教内部也有很多复杂的论争。他相信三教各有其用,所以在表彰象数易学、批评俗儒不学之余,也曾经花费大量精力修寺建阁,并抨击狂禅之无实。做一位普通的僧人当然可以“虚应”,但在禅门祖庭担任住持,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作是纯粹的应付之举。中通跋语中那句“转而集诸佛祖师之大成”,就是颇值得我们细加玩味之语。
注释:
①较早的代表性作品有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1957)、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1972)、张永堂《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1977)、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1987)等,晚近如庞朴《东西均注释》(2001)、谢明扬《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2000),就相关专题皆有精彩的论述。
②方以智著作甚多,整理出版的仅有《通雅》、《东西均》、《药地炮庄》等数种而已。
③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33页。
④邓克铭:《方以智的禅学思想》,《冬炼三时传旧火——港台学人论方以智》,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
⑤譬如,蒋国保就认为:“就哲学思想而论,方以智是以易学为核心,改铸老庄、援引佛道,从而构成了一个以儒学为中心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哲学体系。”(《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⑥廖肇亨:《药地愚者禅学思想蠡测》,《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第176页。
⑦方以智:《青原志略发凡》,《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台湾丹青图书公司,1985年,第45页。
⑧方中通《陪诗》卷三“同郭入冋、吴舫翁喷雪轩侍坐”称:“郭善听受,每日退书老父所语,一字不遗,已成帙矣。”所成之帙,疑即《传心堂约述》及《仁树楼别录》二篇。
⑨方以智:《与藏一》,《青原志略》卷八,《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台湾丹青图书公司,1985年,第421页。
⑩《东西均》、《易余》均作于顺治九年(1652)前后,方以智刚过40岁。《通雅》写作时间更早,崇祯末年已有初稿,方以智当时才30余岁。《物理小识》原附在《通雅》之后,方以智亦自称为“中年”之书。
(11)《药地炮庄》始作于闭关南京之时(43岁左右),此后或作或停,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由萧伯升捐资雕版。
(12)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31页。
(13)庞朴:《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第144页。
(14)庞朴:《东西均注释》,第177页。
(15)《青原志略》卷三,《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第163页。
(16)方氏世代恪守孝道,庐墓几成惯例:方大镇衰年庐墓,过哀而卒。其子方孔炤继之,亦庐墓尽孝。孔炤卒,方以智破关奔丧,庐墓合明山三年,以和尚身行儒仪,远近轰动。
(17)此段话由密之座师余飏转述,见氏著《芦中全集》卷五《方氏报亲庵纪》。
(18)密之曾祖方学渐与东林高、顾多有往还,对王门现成良知说,驳之不遗余力。其讲学之所,名字就叫“崇实堂”。
(19)《周易时论合编》卷首有黄道周“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对两人的交往有过较详的追述。
(20)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22页。
(21)方中履:《周易时论合编跋》,《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9页。
(22)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凡例》:“何羲兆问漳浦先生曰:‘圣贤言理耳。如落象数,则算手畴人矣。’先生曰:‘如此,圣贤事天,当废日星。落日星,亦台官稗史矣。’木上云:‘象数则不同。何思何虑,无不同者。’先生曰:‘如此,学问止于《中庸》,行事尽于《论语》,《诗》《书》《礼》《乐》《春秋》何故作乎?’”
(23)钱澄之:《通雅序》,《田间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第228页。
(24)《青原志略》卷三,《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第179页。
(25)施愚山:《吴舫翁集序》,《学余堂集》卷五。
(26)方中通:《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跋》,《明嘉兴大藏经》第3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7年,第837页。
(27)《青原志略》卷三,《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第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