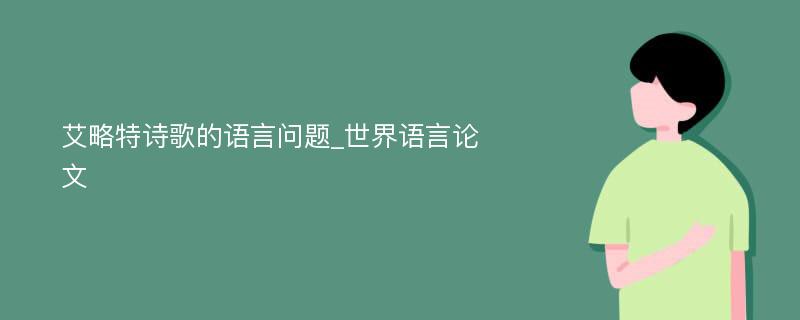
艾略特诗歌的语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略特论文,诗歌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体学的兴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路,尤其是其定量分析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更多的科学性,避免了随意性,这些优点和长处都是毋庸置疑的。诚然如此,这种形式主义批评方式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文学风格虽然在体现形式上主要是一个关于作家如何措辞造句的问题,但反推一步,则是作家如何去感受和体验生活的问题,感受和体验的方式决定了表达这种感受和体验的语言风格。也只有这样反推一步,我们才能在探讨诗歌语言的形式之美的同时能深入到诗歌的内容之中,从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之中,或者说从内容与形式的化合当中去体验诗歌之美。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视角。本文将从以莱考夫为代表的当代学者们“重新发现”的能兼顾形式与内容的隐喻理论出发,来探讨现代诗歌的语言问题。
根据莱考夫等人的观点,人类在共同的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概念,而用于表达概念的语言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因而概念都是隐喻性的。这是因为“隐喻的本质就在于通过某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不同类型的事物”,而且“由于我们语言中的隐喻表达方式是系统地和隐喻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用隐喻性的语言表达式来研究隐喻性的概念的本质,来理解我们行为的隐喻本质”。①反过来说,隐喻又是我们理解自己的经验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比如意象图式结构和隐喻结构就是人类思维结构的重要部分,是人们进行新的联想、形成新的体验的基本方式。莱考夫等从“经验论”出发,认为通过“共同经验”和抽象概念进行的所谓“自动认知”其实就是一种用“已知结构”映射“未知结构”的隐喻过程。②同理,诗人也是先有了得自感知体悟的经验,然后才会“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地寻找表达的方式,而只要这种经验是新的或者个人化的,这种表达方式也就往往是隐喻式的。
一
艾略特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作家一样深切感受到了语言危机和表征危机。当然,这并不是说语言危机是现代作家所独有的, “许多诗人在此时或彼时都曾感觉到确定的诗歌用语的不足,而且,由于个人原因或者更广泛的文化原因,他们都迫切需要创造新的手段来利用语言资源。”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诗人对现代社会的感受和体验发生了激变。前辈作家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完整结构的一部分,这个结构的各个部分协调一致,可以相互解释。然而,现代作家却感觉到这个结构正在分崩离析,不再具有任何实质上的统一性。③
艾略特的前期诗歌如《普鲁弗洛克》、《荒原》、《小老头》、《空心人》等表达的正是这种分崩离析的体验与感受,他追溯到玄学派诗人、但丁、远古神话,为的就是寻找到分崩离析的现代社会中不复存在的传统与秩序。然而,诸神的复活拯救不了堕落的现代世界,古代的秩序毕竟只能以一种隐喻的对应结构若隐若现地潜藏在深处,诗人不得不面对和表现的仍然是支离破碎的现实。理性失落之后的危机感并非艾略特所独有,而是现代派作家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经验被剥去了理性的圣衣之后,自然成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成了波德莱尔的腐朽衰败的“熙熙攘攘的都市”,成了艾略特只剩下“一堆破碎的意象”的荒原。与既有的经验——推而论之就是既有的文化——一道失去的还有用来表达这种经验和文化的语言。庞德认为,现代诗人的神灵都锁在石头里,换言之,“真实”的世界已经堕落到了极其令人怀疑的地步,艺术的任务就不可能是再现这个堕落的世界,所以,现代诗人的语言不再是附庸于经验之上的一件霓裳,不再像古典时代的语言一样从它预想和歌颂的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中吸取力量并与这种结构保持一致。相反,它获得了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其本身就成了某种有目的性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诗人不希望重返理想中的伊甸园。艾略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不得不直面腐朽堕落的经验现实,但是但丁式的理想世界又时时萦绕心中,于是,在《荒原》等诗作中就像在《尤利西斯》中一样,古代的秩序就成了现代荒原的反向参照系。布鲁克斯所谓现代诗人最主要的技巧就在于重现发现了隐喻并充分运用隐喻,④其意义在于:现代诗人将语词从言语所处的传统地位上抽取出来并将它们重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它们被遗忘的次要潜力,诸如含蓄的特征、节奏上和听觉上的可能性、与其他词语的相似性等等,变成主要的东西。⑤艾略特要拯救现代荒原,拯救现代文明,其方法之一就是拯救语言;而且他也明白,诗人实际上是不可能以一己之力真正拯救现代荒原和文明的,所以拯救语言就成了现代人的首要任务之一:
除非他们继续造就伟大的作家,尤其是伟大的诗人,否则他们的语言将衰退,他们的文化将衰退,也许还会被一个更强大的文化所吞并……在某种程度上,诗能够维护甚至恢复语言的美;它能够并且也应该协助语言的发展,使语言在现代生活更为复杂的条件下或者为了现代生活不断变化的目的保持精细和准确,就像是在过去或者一个更简单的时代一样。⑥
在此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艾略特诗歌中丰富驳杂的典故。典故的广泛运用是诗人防止语言与文化的衰退、“维护甚至恢复语言的美”的一种努力。典故在艾略特诗中不仅是一种文化历史的参照系,也是一种语言的参照系;语言的形成不是朝夕之功,尽管将语词和典故从历史典籍中抽取出来加以重新组织之后,通过与表现现代经验的现代语词之间的隐喻互动可以产生新的含义,尽管它们仍未脱尽原文中的胎记,但如此一来,现代语词和作为典故的历史语词之间既显示出了一种延续性,也为各自预留下了一种想象的空间,而围绕在语词周围的想象空间同时也赋予这些语词一种意义的光轮。⑦
罗兰·巴特曾在《零度写作》中将文学语言区分为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在古典语言中,意义是连续的、线性的,一直延续到最后;同时思维是随着语词而向后活动的,语词的活动使人产生快意。而在现代诗歌中, “像真理的突然显现一样使人产生快意和满足”的则是语词本身,语词之间失去了古典语言中那种约定俗成的相互联系,但语词也正是因此而获得了一种魔力,成了一种自足的主体。巴特认为,此类语词“形成了一种充满断堑和光亮的话语,这种话语充满空白而又营养过剩,缺少了意图的预见性或者稳定性,因而与语言的社会功能非常的对立,仅仅求助于不连贯的语言就是打开了矗立在自然之上的一扇门”。现代诗歌语言预先假定了其本质是非连续性的,存在“一种碎片化的空间,由孤独可怕的客体构成,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可能”。⑧
巴特对现代诗歌语言的上述概括可以在艾略特诗歌中得到印证,尤其是他强调的片断性和非连续性、语词之间的断堑、语词的自足性等。从当代隐喻理论的角度看,语言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正如读者反应批评家们所强调的,摆放在藏书架上的只是文本,只有通过读者的参与和解读才成其为文学,我们注意力转移到了保罗·德曼所谓的“言后领域”(the perlocutionary realm),⑨即语言的语用效果和读者的阐释,而非其“本身”所具有的语义结构。为了明晰起见,我们举《荒原》第三部分“火的说教”中有代表性的一段来做具体分析:
可是在我背后的冷风中,我听见
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声从耳边传到耳边。
一只老鼠悄悄爬过了草丛
把它湿粘的肚子拖过河岸,
而我坐在冬日黄昏的煤气厂后,
对着污滞的河水垂钓,
沉思着我的王兄在海上的遭难。
和在他以前我的父王的死亡。
在低湿的地上裸露着白尸体,
白骨抛弃在干燥低矮的小阁楼上,
被耗子的脚拨来拨去的,年复一年。
然而在我的背后我不时地听见
汽车和喇叭的声音,是它带来了
斯温尼在春天会见鲍特太太。
呵,月光在鲍特太太身上照耀
也在她女儿身上照耀
她们在苏打水里洗脚
哦,听童男女们的歌声,在教堂的圆顶下!
(《荒原》第185-202行[查良铮译文])
对于这样的诗歌语言,传统的理性思维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按照那种思维模式,我们为了理解它自然会问这样一些问题:诗中的说话人是谁,这段叙述要表达的旨意是什么,等等。这样的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在艾略特的诗中难以成立的预设,即语词的背后有一个不依赖语词而独立存在的世界,或者说语词仅仅是依附在经验世界之上的一袭薄纱。熟悉这首诗的读者也许并不觉得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对第一个问题可以回答是提瑞西斯(Tiresias)。然而这样的回答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与其说这是回答问题还不如说这是在提出更多的问题,因为尽管如艾略特自己在注释中所说,提瑞西斯是统帅全诗的人物,但他并不像经典小说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一样可以真正统帅全诗的内容,在不同的片断中只有将他还原为说出每一段(或行)诗的人物,如佛、斐迪南王子、奥维德、魏尔兰,等等,它们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每一行诗的意义只存在于具体的语词之中而不存在于语词之外。而对第二个问题,诗人的直接目的似乎只是从奥维德(197-198行)、魏尔兰(202行)、圣杯传奇(189、197-198行)、澳洲民谣(199-200行)、玛维尔《致他腼腆的情人》(185-186行)、《暴风雨》(192行)、约翰·戴伊的《蜜蜂会议》(197-198行)、米德尔顿等出处摘引了这些语词,像意识流小说中一样根据某种表层关系拼贴在一起,形成一幅存在于读者心中的风景画。但这幅画是根据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拼贴出来的,上面各行中的语词既是一种作为“对应物”的具体实物存在;也是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和体验而存在,是主客观的共同体。我们也可以说,即使断定了诗中语词的言说者的身份,我们也未必能明白语词的“确定的”意义,因为与语词相对应的并非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物,或者说这里的“客观对应物”只存在于语词之中。同样,整段引诗——甚至整个《荒原》——中的意象、人物、艺术效果也无法脱离诗中的语词而独立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诗歌中的语词与诗人感受到的存在之间不再存在一层介质,而是融为了一体;诗歌语言不再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是感性经验本身。也正是因为如此,诗歌语言必然是隐喻的,它给与人的不只是新奇的形式,而是一个感性世界。这就正如I.A.瑞查兹所说,诗歌“是直觉语言的一种中介,它可以实体地传递感受。它总是竭力吸引住你,并且使你不断看见一种物质的东西,防止你滑入一个抽象的过程。它选用新鲜的描述语和新鲜的隐喻,并不是因为我们厌倦了旧的,而是因为旧的词语不能传达物质的东西,而且已经变成了抽象的阻碍”。⑩不过当我们强调诗歌语言的自立性时,不能忘记这种自立性只是相对而言的,语言毕竟还必须是人类经验的一种表达或者体现的形式。在艾略特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典语言通过典故的广泛运用实际上在现代语言中得到了复活,成了现代诗歌语言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诗人在表达自己的感知体悟的经验时,语言是如何获得这种相对的自立性的呢?这里我们可以回到奠定艾略特诗学理论基础的博士论文《布拉德利哲学中的知识与经验》中来,从他对关于经验与语言的关系的观点谈起。艾略特认为,“只有在直接经验中,知识与其客体才是合而为一的。”“除了在非常权宜性的情形之下,我们没有权利说我的经验,因为我是从经验之中建构起来的,是经验的一种抽象化。”“唯一独立的真实就是直接经验(immediate experience)或者感受(feeling)。”“‘我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说当然是我的。但这是因为我就是这种感受。”(11)从上述论断可以看出,艾略特认为,在未经过理性的梳理和逻辑的分类与抽象概括之前,人类经验和原始人的思维一样是处在混沌状态的。
从列维·斯特劳斯、布留尔、卡西尔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起源的分析我们知道,这种主客体未分的人类经验正是神话、语言与诗的共同的起源。我们的语言为了表达日益丰富的经验而日渐抽象,脱离了直接经验的母体而沦为一种纯粹的介质,就如卡西尔所概括的,“语词首先必须以神话的方式被设想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而后才能被理解为一种理想的工具,一种心智的求知原则,一种精神实在的建构和发展中的基本功能。”(12)在文明社会中,当神话消失、语言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之后,诗就成了人类的这种最初始的直接经验的最后的捍卫者,诗歌语言就成了这种直接经验的表达者。艾略特在博士论文中有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混沌状态的直接经验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在描述直接经验时,我们必须用语词来为主体或客体提供一种隐秘的暗示。当我们说表象(presentation)时,我们想到的是一个主体,用表象以一种客体的形式将这一主体呈现出来。当我们说到感受时,我们想到的是一个主体对一个客体的感受……相应的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情境是一种经验,它既不能完全定义为客体,也不能完全被当作一种感受去经历,而是其被观察到的组成部分既可以呈现这一方面也可以呈现那一方面。(13)
这段话虽然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广泛的直接经验,但完全适应于用语言来表达诗歌体验的情形。这也说明在诗歌之中感受(或感情)与客体(或艾略特所谓“客观对应物”)和语言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我们不妨继续以上面“火的说教”中的那段引诗来说明这三者是如何转化的。引诗中的一连串意象(“白骨”、“老鼠”、“尸体”、“汽车”等等)作为一种表象,其客观性只是貌似真实的,其语言也只是在“提供一种隐秘的暗示”,海滩上的尸体、阁楼里的白骨、爬过草地的老鼠等,与其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不如说是在说话人心中留下的一种感受。当老鼠爬过草地时它就钻进了语词里,它作为一种动物的生命就终结了,在语词中生发出来的就是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感受的转化。这种观点不仅符合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也符合唯心主义哲学的一贯思路。按照他们的观点,自我总是要逃离一切被创造之物,从一种否定逃离到另一种否定中去,自我拒绝承认客观世界中的就是自我本身——这也正是艾略特说“我们没有权利说我的经验,因为我是从经验之中建构起来的,是经验的一种抽象化”的原因所在;只有当客观世界转化为了主观的世界,被理解了的客体都转化为了主体,它们才能为自我所接受。正因为如此,在象征派诗人看来,外部世界中的经验客体只是经验主体通过语言、象征、隐喻的一种外在的表达形式。从这一角度来说,能为自我认识到的自我就是语言,语言是诗人唯一的家。
了解了艾略特诗歌中语言与经验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他诗中碎片化语言的连贯问题。通过语言的片断化和意象的跳跃来打破普通语言的逻辑与语法规则,从而获得形式主义者所说的陌生化效果,这是古今诗歌语言的通则,现代派诗人只不过是将这种片断化发挥到了极致。当语言片断化后,语词与语词之间就留下了许多空白或者断堑,诗歌之美不仅体现在优美的语言与新颖的意象中,同时也体现在这种“无言”之中,这种“无言”之美也就是刘勰所谓“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之“隐秀”。语词之间的空白与语词自身的充盈其实是相克相生的,语词与意象的充盈固然能激发读者,空白和断堑同样在呼唤着读者,呼唤读者参与到诗的不自足中,去“课虚无而责有,叩寂寞以求音”。对如何“捡起这些碎片”来支撑起他的“荒墟”,我们可以借用艾略特在博士论文中的一段话来做阐释:
[唯我论的]观点(或者有限中心)有一个始终一致的世界作为客体,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有限的中心能够是自足的, 因为一个灵魂的生命并不在于对一个始终一致的世界的沉思,而在于将不和谐和不相容的多个世界(或多或少地)统一起来的这个痛苦的工作中,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两种或多种不协调的观点上升为一种以某种方式包含和改变它们的更高的观点。(34)
如果我们将上面引诗中出自澳洲民谣、圣杯传奇、《暴风雨》等地方的片语还原到它们的出处之中,它们自然就是“不和谐和不相容的多个世界”了。但将它们抽取出来植入同一首诗中之后,这些片语作为一种新的体验就不再完全从属于它们原来的世界,而是成了诗人浑然无隔、流动变幻的经验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火的说教”这段引诗中还是在整个《荒原》中,将片断的经验化合为一种更高层面的统一的经验,都是艾略特用以连贯这些语言片断并且消弭语言片断之间断堑的一种基本策略,他显然就是为这一目的而为诗中的人物“提瑞西斯”做注释的。(15)
从当代隐喻理论的角度看,这种超越提瑞西斯的意识只能是诗人对一种新的体验的新的“命名”,或者说将这种新的体验投射到具体的意象之上,从而形成了诗本身。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体验就是语言本身,是一个集万千意象与形象于一身的宝库。在艾略特看来,这种情况下的语言已超越了普通的“言”,上升为了上帝的“道”。在这种意义上来看待语言,将独眼商人、卖葡萄干的商人、费迪南王子、腓尼基水手都化合为提瑞西斯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16)
不过单纯从这一角度似乎还不能解决艾略特诗中的语言问题,因为如果说语言等同于初始的体验,那么这种体验完全有可能转化为概念而不是诗,正如艾略特有可能像布拉德利一样成为哲学家一样。对哲学了解甚深的爱略特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他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那就是,初始经验这种“既无主体也无客体的状态”在化作语言之前可以体现为一种节奏, “一首诗或者一节诗在以语词表现出来以前可能倾向于以一种特定的节奏来实现它自己,这一节奏可能导致一种观点和一个意象的产生。”(17)的确,节奏在艾略特的诗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上面的那段引诗中,出自马维尔《致他腼腆的情人》的第185行“可是在我背后的冷风中,我听见……”与前面出自斯宾塞《贺新婚曲》的一段相比有一个明显的节奏的变化,使诗的语调一下深沉起来;出自魏尔兰的十四行诗《帕西法尔》("Parcifal")的第202行“哦,听童男女们的歌声,在教堂的圆顶下!”(18)引出后面写泰罗斯强暴菲洛美的一段,与前面几行相比也有一个明显的变奏。这种节奏的变化意味着艾略特仍然是忠于原作的节奏和感受的,但与此同时引文中语句又必须融入艾略特自己的诗歌语境和诗歌体验中来。语词的这种双重属性正是它们进行隐喻建构活动的基础,它使语词(即引诗中的诗行)能突破语法和句法的束缚,能在二者之间来回游走;与此同时,由于它们既不完全属于原作又不完全属于诗人自己的感受,既不完全是主体也不完全是客体,这就为消弭语词之间的断堑奠定了基础。
分析了语词之间的关系后我们就可以来考虑语词之间的组织,即诗歌的“语法”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词与语词之间的断堑只不过是原作的“个性”与“自我”的泯灭,而并非语言的失败,相反,这种断堑正是诗的“无声”的“秀隐”之美。就如艾略特自己所说的,“言词,在言说之后,进入/那片寂静”(《烧毁的诺顿》(五)),或者像奥·威·施莱格尔所说,“美即无限的象征的显现。”所谓无限就是指“表象后面的奥秘和我们自身内部的奥秘:它是一种宇宙性的、隐晦的东西,是‘心灵启示性的裁决,即深刻的直观认识,我们的存在这个哑谜似乎从中迎刃而解了’。”(19)换句话说,不管意象和语词本身是多么蕴涵丰富,那都是有限的,只有空白和断堑才包蕴着无限,因为这种沉默只会诱发和暗示,却不直接言说;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潜伏着莫名的情绪和神秘的奥蕴。除此之外,这种空白和断堑打破了固有的语法束缚,还开拓了新的物理时空和心理时空,语言概,念的确定性、语言的有限性、语言对世界的分割等等,都在这种空白和断堑中化为乌有。
如此一来,我们又回到了艾略特评论《尤利西斯》时所说的“神话方法”,因为照我们的理解,只有神话方法才能挣脱时空与因果逻辑的锁链。艾略特在使用语词和组织语词时首要的任务显然不是遵守语法和逻辑的规则,相反,在他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表面上的经验的真实往往是欺骗性的,而真正的真实则蕴含在没有确定的空白之中。通过模糊主客体之间的界限,艾略特的诗歌语言就能够以“神话方法”超越时空、逻辑和语法规范来组织语词。这种“神话方法”正是在隐喻思维指导下的写作方式。
不过,尽管艾略特的诗歌语言模糊了主客体的界限,成了感性的初始体验自身,但神话毕竟已经离现代社会远去。现代诗人必须通过写作与他的同时代人交流和沟通,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从事神话写作,所以,所谓“神话写作”本身也只可能是一种隐喻。同样,尽管我们说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但这并不是否认艾略特诗中主体与客体、经验与语言的客观存在:在艾略特的诗中语言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媒介而存在。
三
在现代诗歌中,语言是一种兼具主体性和媒介性的存在物,它既是一种经验,同时也是经验的一种隐喻载体。在下文中我们将以《四个四重奏》第二部分“东库克”为例来论证。作为诗人的艾略特一生都在与语词进行斗争,《东库克》第五章的开头一段就是对这一斗争经历的概括:“每次冒险/都是新的开端,是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进攻,/用的是日益破败不堪的装备……”在此艾略特以少有的坦率直陈了自己作为诗人的困惑,作为思想的载体的语言在人类从商业书信到教堂祈祷的各种运用中变得日益陈旧,成了“破败不堪的装备”,因此诗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创新诗歌语言。然而在众多的文学前贤面前,艾略特直至晚年也仍然感到信心的匮乏,他只能尝试着去恢复丧失了的表达人类经验与精神的可能性。(20)与早期相比,后期的艾略特在体验生活和表达这种体验的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对早期“非个性化”理论的修正。他在这一时期认为“非个性化”是指成熟的艺术家“能用强烈的个人经验,表达一种普遍真理;并保持其经验的独特性,目的是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象征”。(21)不过无论以艾略特的哪种“非个性化”理论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都难以说《东库克》实现了他的艺术理想,因为他的体验既没有完全融入“客观对应物”之中,也没有完全转化为一个“普遍的象征”。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体验——也就是诗中要表达的主题——和他用以表达这一体验的媒介,即诗歌语言,常常平行出现在诗歌之中。
《四个四重奏》的主题可以用赫拉克利特的几句话来概括:
“开始和结束是共同的。火生于土之死,气生于火之死,水生于气之死,土生于水之死。”(22)《东库克》的题旨也是这样一种生死循环的朴素辩证观点。艾略特就是使用语言来映射这种生命的无常与存在的无限的。生命中包含着死亡,尽管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它通过我们精神的再生而获得永存: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接连地
房屋矗起、倒下、坍塌、扩展、
移动、毁坏、修复,或在它们的地基上
是一片空地,或一座工厂,或一条小径。
(第1-4行)
流畅的自由诗体暗示出,诗人确信,生命之始便是个体生命的死亡之始。将“房屋”这一看似牢固的意象与“毁灭、修复”的永恒的循环并置在一起,这表明诗人清楚地意识到生与死的循环是相克相生的,与此相对应的是语词上的对立:“开始/结束”、“矗起/倒下”、“毁坏/修复”等。房屋如此,“在空空的寂静中沉睡”的大丽花、“船长、商业银行家、卓越的文人,/慷慨的艺术赞助人、政治家、统治者”等等,人类同样是“吃吃喝喝,粪堆和死亡”。甚至天上的群星也像人类在战争中毁灭一样,燃烧在“毁灭的火焰中”。尽管毁灭是痛苦的,但艾略特并不是在哀叹而是在颂扬个体将短暂的生命奉献给了通过循环而获得的永存的生命。因此,该诗的实质在于一种内在的形式的整一感,而不在于文本表面的典故——《荒原》等前期诗作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典故只是在诗的结构中起一种功能作用,而其自身并非一种崇高或者玄奥的目的。与诗中丰富的典故并行的是艾略特还使用了多种语言形式来取得丰富的效果。正如他关注生命的存与毁一样,他也关注语言的使用与复活,他在诗中重新使用在现代语言中已经废弃的词语,以此与物质存在的毁灭与再生形成对应:
In daunsinge,signifying matrimonie-
A dignified and commodious sacrament.
Two and two,necessarye coniunction,
Holding eche other by the hand or the arm
Whiche betokeneth concorde...(23)
一般认为这一片断出自斯宾塞的《贺婚曲》(Epithalamion)。艾略特将这种古色古香的语词纳入其诗中只是为了表明历时语言既有局限又有无限潜力。将不同时期的语言融入诗中就与诗中诸如“生—死”的对立统一体形成并列:人之生与死和语言之变化与演进就形成了一种隐喻关系。这样一来,艾略特就将生死循环投射到了语言的变迁与变异上,同时也使敏锐的读者意识到语言的变迁和生与死的存在状态是平行一致的,或者可以归纳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尽管意义已随时代而变迁或者淘汰,但伊丽莎白时代的语词依然以古语的形式存在,并且通过诗而获得再生。这是语言获得永生之途,不也正是生命获得拯救之途吗?
古往今来,语词的冲击力都是由语词的组织形式而非其意义决定的,因为意义从来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和稳定不变的。相反,它会因背景和过程而衰微或者流变。所以在艾略特看来,语词是人类不精确的和有局限的工具,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产生强烈的表达力。通过将上述充满古典词形和拼法的诗行融入现代诗歌中,艾略特旨在证明语言是可以丰富起来,同时,通过古今语词的融合,语言之轮就可以转化为一种不断向上的螺旋,只要诗人锐意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语言就能获得拯救。诚然语词和文学可以通过创新而进步,个体生命之死也能换来人类的演进,但我们不能忘记死亡仍然是“吃吃喝喝,粪堆和死亡”这一生命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自从人类从伊甸园堕落人间以来不得不接受的不可能完美的生命循环的特点;同样,语言这一用来理解和表达生命的媒介也是充满讹谬的。对于语言的局限与生命(经验)的缺陷,艾略特在《烧毁的诺顿》中作了类似的类比:
语词运动,音乐运动
只是在时间中;但那仅仅是活的事物
才仅仅能死。语词,在言说之后,进入
那片寂静。
(第138-141行)
引诗中艾略特重复使用“仅仅”一词目的就是要强调生命个体的生与死在横扫一切的残酷的存在面前是何其无足轻重。所以,正如生命堕入死亡一样,语词也堕入了寂静;生命的自然进程也正如用来表达这一进程的语言一样,是“粪堆/死亡”、“吃吃/喝喝”、“开始/结束”这一循环的一部分。语言是顽强的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然而又是脆弱的:“语词绷得紧紧/断裂而且不时破碎”。对艾略特来说,语词会衰变,其形式和意思也会发生变迁,但作为能指的语词仍然以所指的形式存在着等待复活,正如上述《东库克》中引用的斯宾塞的诗行一样。活的语词与死的语词在诗中并存而且相互激活。正如在生命的生死循环中一样,在语言之中衰败和退化同样是语言演化循环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当一个衰败了的过去与一个探索中的现在碰撞在一起,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未来就在久经磨损的语言中破壳而出,于是语言就犹如凤凰涅槃一般得到了新生。
艾略特觉得语词这一诗人的工具不足以表达生死循环的悲剧,诗人可以改善语言,把它作为一种媒介来掌握,但他避免不了语词的局限;诗人的文学成就也无法弥补他对那“大多数荒废了的二十年”的人生经历的理解和表达的失败。因此,即使“老人(也)应该是探索者”,探索不仅是为死亡做准备,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索死之不可避免从而改善生的现状,并且将死之凄凉转化为迎接基督给与的复活的欢欣的积极态度,从而完成那个神圣的循环,于是全诗以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座右铭来结束:“在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可见,整个《东库克》可以看作是艾略特对充满矛盾的人生处境的一种诗性表达,他通过描述生与死、食物与粪堆、再生与衰败的生命循环来将各种不谐和融入诗中。与此同时,他通过将典籍中的引语、古语、《圣经》典故等诸多成分汇入诗中来表达生命循环中种种不谐和,从而使诗歌语言成为生命循环中种种矛盾的一种隐喻。
注释:
①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The Metaphor We Live b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3-7.
②George Lakoff and Mark Turner,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p.50-52.
③⑤理查德·谢帕德:《语言的危机》,见《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298-300,302页。
④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见《“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377页。
⑥(21)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243-245页。
⑦Denis Donoghue,"The Word within a Word",in T.S.Eliot:Critical Assessments,Vol.II,ed.Graham Clarke (London:Christopher Helm Ltd.,1990),p.239,p.167.
⑧Roland Barthes,Writing Zero Degree,trans.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London:Hill & Wang,1967),pp.54-55.
⑨Paul de Man,"Semiology and Rhetoric",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eds.R.C.Davis et al.(Lnndon:Longman,1989),p.253.
⑩转引自霍克斯:《隐喻》,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109页。
(11)T.S.Eliot,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H.Bradley (London:Faber & Faher,1964),pp.19-31,pp.22-25,pp.147-148.
(12)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泽,三联书店1988年版,83页。
(13)(14)T.S.Eliot,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F.H.Bradley (London:Faber & Faber,1964),pp.22-25,pp.147-148.
(15)《荒原》第218行的注释为:“提瑞西斯虽然只是个旁观者,而并非一个真正的人物,却是诗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贯穿全篇。正如那个独眼商人、那个卖小葡萄干的化入了腓尼基水手,后者与那不勒斯的费迪南王子也并非完全不同,所有女人因此是一个女人,而两性在提瑞西斯身上融为一体。提瑞西斯所看见的实际上是这首诗的本体。”见《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沈阳出版社1999年版,81页。诗中作为主客体融为一体的语言并非出自提瑞西斯,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参与到诗中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情感之中去,所以艾略特所谓“更高的观点”显然不可能是提瑞西斯的观点,而必须要超越于提瑞西斯的意识之上。
(16) Denis Donoghue,"The Word within a Word",in T.S.Eliot:Critical Assessments,Vol.II,ed.Graham Clarke (London:Christopher Helm Ltd.,1990),p.335.
(17)T.S.Eliot,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57),p.38.
(18)魏尔兰的这首十四行诗写的是帕西法尔抵挡住女巫的诱惑,变得谦卑澄明,女巫为他濯足,准备让他进入圣杯城堡。他在那里治愈了渔王,自己也成了帝王。这首诗后被瓦格纳改写成歌剧,在歌剧结尾处,孩子们在教堂里高唱赞美耶稣的颂歌。这与前面几行斯温尼来到波特太太开的妓院,妓女们在苏打水里洗脚构成了鲜明的讽刺。
(19)转引自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54-55页。
(20)Curtis Bradford,"Footnotes to 'East Coker' ",in T.S.Eliot:Four Quartets,ed.Bernard Bergonzi (MacMillan,1993),p.63.
(22)转引自James Johnson Sweeny," 'East Coker':a Reading",in T.S.Eliot:Four Quartets,ed.Bernant Bergonzi (MacMillan,1993),41页。
(23)T.S.Eliot,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71 ),p.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