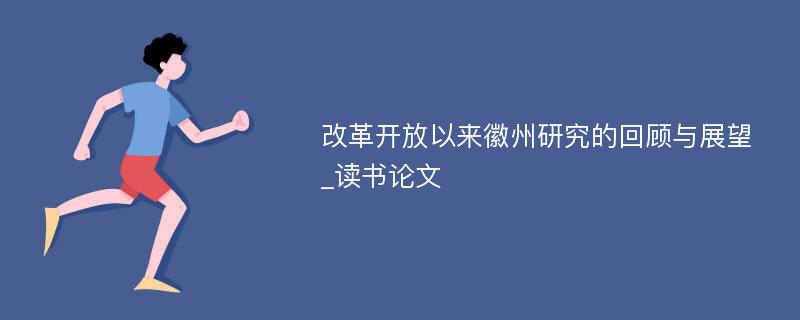
改革开放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7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6-0005-012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社会科学研究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不仅已有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拓展,而且还催生了不少新的学科。其中,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徽学学科的形成尤为令人瞩目。
一 改革开放前的徽学研究
徽学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但徽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对徽州社会经济史及徽州历史文化等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当我们叙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徽学研究时,对此前的徽学研究有必要做一简略回顾。
由于徽州历史文化的光辉成就和重要价值,早在20世纪初即有学者对徽州的历史人物和文化进行研究,此后渐及其他方面。至70年代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有:徽州历史人物,县乡镇志、乡土地理志及乡邦文献,徽州方言,徽州建筑,新安画派,徽州版画,徽班进京及徽剧,徽州庄仆(佃仆),徽州奴变,徽州宗族与族谱,徽商及徽州社会经济等等。其中比较突出者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徽州历史人物研究。主要是对明末清初抗清义士金声①、数学家汪莱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清末理财家王茂荫③、绩溪经学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④、思想家俞正燮⑤、徽派朴学家程瑶田⑥ 等的研究。其中不乏一些著名史家的论说,1936年郭沫若发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⑦,为最先研究王茂荫之作。1937年吴晗著文《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⑧,1938年商承祚著有《程瑶田桃氏为剑考补正》⑨,1944年陈垣写有《休宁金声传》⑩。(二)徽州乡土志书及乡邦文献的编撰。除徽州县乡镇志、乡土地理志、徽州书院志等的编撰外,成就卓著、影响后世的是民国时期许承尧所撰《歙事闲谭》(11)。该书系许氏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歙县志等书之际,对有关徽歙历史、沿革、山川、名胜、人物、典籍、经济、风俗、物产之类文献广泛辑录,以笔记形式汇成的巨制,实为一部全面展示徽歙历史文化而具有学术见解的史料长编,被誉为徽学研究的先导与开山之作(12)。(三)新安画派研究。现代国画大师徽籍人黄宾虹,对新安画派有精深的研究,1924年出版《黄山画家源流考》(又名《黄山书画佚史》),1926年在《艺观》杂志发表《黄山画苑论略》,1935年在《国画月刊》发表《新安派论略》等等,对历史上的新安画派做了系统考察和探究,为现代关于新安画派研究的开拓性论述。其后,著名书画史专家汪世清又进一步研究新安画派,1964年,他与汪聪编纂的《渐江资料集》出版(13);20世纪70年代后期,陆续发表了对新安画派渐江、程邃以及其他明清画家的研究论文,考辨严谨,见解独到,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与高度评价。(四)徽州建筑研究。1953年,著名建筑史研究专家刘敦桢对歙县西溪南乡古建筑进行了考察,发表了《皖南歙县发现古建筑的初步调查》(14)。其后,张仲一、曹见宾等组成调查研究小组,对徽州20余处古民居建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研,出版了《徽州明代住宅》专著(15)。殷涤非的《歙南古建筑调查中的一些认识》(16)、胡悦谦的《徽州地区的明代建筑》(17),探讨了徽派建筑的特色。(五)徽州奴变与佃仆制研究。1937年,吴景贤著文《明清之际徽州奴变考》(18),对顺治年间徽州地区爆发的以宋乞为首的佃仆反抗斗争做了专题研究,文中叙及徽州佃仆制的内容,为现代徽州佃仆与奴变研究之先导。1957年,刘序功发表《略谈清初徽州的所谓“奴变”》(19);1958年,程梦余又发表《宋七与徽州“奴变”》(20)。此后,关于徽州佃仆制的研究逐渐展开,1960年,傅衣凌发表《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21);1963年,魏金玉著文《明清时代佃农的农奴地位》(22)。这些研究对徽州佃仆制度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成为当时徽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六)徽商研究。1947年,傅衣凌发表长文《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23),对徽商活动的时间、地点、经营领域、资本出路及其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诸多问题做了系统而深入的考察,资料翔实,富有创见,成为徽商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傅氏又撰文《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24),进一步加以论述。1958年,陈野著文《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试以徽州一地为例来论证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25),以徽州一地为例,论证了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以上主要是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这一时期还应提到的是国外学者对徽学的研究。日本学者很早就对徽州予以关注,并在徽商、宗族、庄仆制等多方面开展研究,相当活跃,成绩斐然。20世纪40年代,藤井宏在有关明代盐商的长篇论文中已有较多篇幅涉及徽商问题(26)。1953~1954年,他发表了《新安商人研究》(一)、(二)、(三)、(四)之系列论文(27),乃系统考察和研究徽商的又一力作,成为徽商研究的开拓性论著之一,一直影响后世。1968年,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28) 中,论述了宋代徽州商业的发展;1972年,他又发表《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29),以徽州作为江南山村型的典型,对其历史地理、移民与经济开发等做了全面考察。1975年,重田德在《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中,以“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为题(30),对清代徽商做了专门论述。早在1940年,牧野巽发表《明代同族社祭记录之一例——关于〈休宁茗洲吴氏家记·社会记〉》一文(31),1956年,多贺秋五郎发表《关于〈新安名族志〉》一文(32),这些研究开启了徽州宗族与族谱研究的先河。1960年,仁井田陞的名著《中国法制史》出版,其中辟有专章论述《明末徽州的庄仆制——特别关于劳役婚》(33),实为徽州佃仆制研究的开山之作。1976年,美国学者居密发表《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地主制溯源》(34),论及徽州的世仆与佃仆。
此外,改革开放前还有一个与徽学相关的重要事件,这就是徽州文书的发现、收藏与研究。徽州文书的面世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流落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徽州人开始把一些契约文书拿到市场上出售。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方豪在南京即购到一批徽州文书。其后,他以“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为副标题,将其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共12篇报告发表在1971~1973年台湾复刊的《食货月刊复刊》上。(35) 而徽州文书的大规模面世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契约文书本是官府或民间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直接产生的文字资料。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徽州已是可与苏杭相比肩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之地,公私交往频繁,产生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契约文书。其地山限壤隔,战乱较少;徽州宗族发达,世代相承不断,多个世代积累的文书以人户为中心而被保存下来。这些成为徽州地区有大量契约文书被遗存下来的根本原因。1949年解放以后,在时代变迁这一大背景之下,特别是当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之后,历史上原本作为物权书证或交易凭证的契约文书已失去了它的法律效用,一度从家珍变成了“弃物”,被当做废纸卖给造纸厂,开始大量面世。这引起了有关领导和有识之士的关注,于是开始组织收购和从造纸厂中进行挑选抢救,然仍有相当大数量的契约文书被作为造纸原料毁掉了,被抢救出来的只是一部分。当时在徽州本地收购徽州文书的,主要由余庭光负责的屯溪古籍书店进行,而后转给北京的中国书店售给各收藏单位。亦有收藏单位到徽州直接收购的,然数量有限。这一抢救和收购活动延至1960年代“文革”之前。这批文书,今主要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以及黄山市属各县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徽州文书的主要特点,诸如数量大、种类多、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代长和研究价值高等,在这批文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批文书总量估计在10万件(册)以上,其中各种簿册类文书达数千册,现今遗存徽州文书所属宋元明时期文书的绝大部分,都在这批文书之中。20世纪50~60年代发现的这批徽州文书,为徽学学科的确立和徽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资料基础。
综观改革开放前的徽学研究,不难看出以下倾向与特点:第一,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显示了综合性学科的倾向。其研究以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而涉及了广泛的领域,虽以社会经济、法制史、社会史等为主,但亦包含语言、文献、艺术、戏曲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在内。第二,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开放性的,它不是单纯的地方学,许多中外学者是在研究中国历史、探究中华帝国的视角下关注徽州的,或者把徽州当做研究明清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傅衣凌先生说:“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三十年代。那时对于中国奴隶制度史研究感到兴趣,曾从事于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嗣又见到清雍正年间曾下谕放免徽州的伴当和世仆,唤起我的思索。特别是接触到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等等,发现有关徽商的记载甚多……50年代末,徽州民间文约大量流入北京,为徽州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我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展开了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阶级结构、土地租佃关系诸方面的探索。这些研究,使我对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为我以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和山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36)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关于徽州庄仆制的研究,则是从探索19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农奴制转型、作为中国法制史的一部分而展开的。第三,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带有国际性的,不仅众多中国学者已对徽州做了相当长时间的研究,而且不少外国学者亦参与其中,他们的研究也是具有开拓性的。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前的徽学研究,从资料和学术研究等多方面为改革开放后徽学研究的兴起做了准备。
二 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徽学学科的形成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徽学研究迅速兴起。有关徽学的学术问题成为热点,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机构纷纷建立。徽学研究何以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呢?
首先,改革开放促进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学者们对此前的研究开始进行反思。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探索,是否就只有大框架的、自上而下的这样一种宏观模式呢?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人们在思考新的视角,寻求新的切入点,尝试新的方法。于是,区域史研究趋于热门,社会经济史的考察也出现了新的方法等等。具有雄厚资料、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占有重要地位的徽州,自然进入人们的视野,很快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其次,改革开放使中外的学术交流成为现实,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日本学者、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家鹤见尚弘1982年来访中国,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接待的首位外国研修学者,来到历史所后,指名要看徽州文书,他以鱼鳞图册为中心对徽州文书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考察与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并与中国学者做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学者亦在改革开放前开始关注徽州,改革开放之初即发表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居密于1979年发表《主与奴:十七世纪的农民怒潮》(37),1982年又发表《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和宗法制度》(38);荷兰学者宋汉理于1984年发表《徽州地区的发展与当地的宗族——徽州休宁范氏宗族的个案研究》(39),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于1986年发表《明清徽州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40) 等等。与此同时,《江淮论坛》编辑部和刘淼教授分别组织出版了《徽商研究论文集》(41)、《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42),使这些成果很快被介绍到国内,为中国学者所了解。这些成果与国内学者的研究交相辉映,大大推动了徽学的发展繁荣。同时,这种形势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一种紧迫感。如众所知,敦煌文书在1900年被发现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国内的研究一度滞后,致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加紧研究,会不会也出现“徽州在中国,徽学在国外”这样的局面呢?这是当时学者们常常议论的一个话题。加之改革开放前的徽学研究和徽州文书的发现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于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徽学研究迅速兴起。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徽学研究很快在徽州佃仆、徽商、徽州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徽州宗族等方面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研究可以说是此前研究的继续,因为其在过去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不过,即使在这些领域,改革开放以后的研究已有很大不同,展现了新的面貌。进入1990年代之后,徽学研究则进入了全面发展繁荣的新时期,在资料搜集、领域拓展、学术交流、理论建构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徽学研究的突出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着眼于学科的长远发展,重视资料开发。改革开放前的徽学研究,多是仅抓住某些问题写出一些论文。与此不同,改革开放后的徽学研究已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长远考虑,全面规划,把资料开发放在首要位置。无论徽学研究本身,还是学科建设需要,遗存下来的数十万件徽州文书档案资料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徽州文书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发现,随后因遭遇“文革”,即在各收藏单位原封不动地束之高阁。徽学研究若要有大的发展,徽学学科若要真正确立,那么对徽州文书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利用就必须提到日程上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共同协作,拟定将各单位收藏的徽州文书全部整理编辑成集,名曰《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分册出版。后因各种原因,只出版了安徽省博物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两集(43),仅占整个徽州文书的极小一部分。此后,历史研究所继续在做徽州文书的整理工作,至1980年代末基本完毕。那么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呢?是采取保守的做法,仍然藏之深阁,仅能为少数人利用,还是出版发行,公布于众,为大家所用呢?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和徽学研究者秉持开放的理念,决定以影印原件的形式,将其公布于世,遂出版了大型文书档案资料丛书40卷本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该书的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推动徽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张海鹏、王廷元为首的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群体,在1980年代之初确定徽商研究这一课题时,并未急于发表文章,而是先用多年时间,“利用教学之余,冒寒暑,舍昼夜,到有关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以及徽州各地,访求珍藏,广搜博采,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进行爬梳剔取,初步摘录近四十万言,编辑成册,定名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44)。同样,该书的出版在国内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推动徽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为该群体其后成果斐然的徽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21世纪,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所藏徽州文书亦出版面世,该中心还组织编辑“徽学研究资料丛刊”,整理出版了一批典籍文献资料。
(2)秉持开放理念,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改革开放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交流的条件和机遇,徽学研究者以开放的理念从事学术研究,徽学研究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相当活跃,十分频繁。改革开放使中外学者互访成为可能。徽州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研究价值,磁石般地吸引着海外学者来到中国,走访徽州;国内一些徽学研究者也多次出访,宣传徽州,倡导徽学。这种互访交流在1980年代已很频繁,它大大促进了徽学研究的发展。1990年代初,韩国高丽大学朴元熇教授到北京大学研修,而后来到黄山(徽州)考察,感受到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遂决定将研究方向转为徽州宗族研究,其弟子们攻读的硕士、博士课程亦均选徽学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以“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名义及与徽学相关名义召开的各种大中型会议就有十多次。如1998年在绩溪召开的“98国际徽学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7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来自日本京都大学、京都橘女子大学、大正大学、关西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福冈大学、早稻田大学及韩国高丽大学的学者14位,有来自中国台湾的学者2位,还有来自日本的一位华侨学者等等,中外学者济济一堂,就徽学研究的多项课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于1994~1996年在历史所多次举办过徽学研讨班,参加者有日本、韩国学者多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黄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黄山学院等也开展了多项有关徽学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这些会议和国际交流活动,对徽学研究的发展,扩大徽学的影响,加速其走向世界,无疑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建立,学术刊物发行,研究队伍发展壮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徽学研究的兴盛,有关徽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纷纷建立。作为徽学研究的学术机构,最早是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成立的徽州文契整理组以及同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的徽商研究课题组。1985年,徽州地区正式成立了徽州学研究会。同年,安徽省徽州学研究会在合肥成立,这是最早成立的徽学研究学术团体。1989年,在徽商聚居地之一的杭州成立了杭州市徽州学研究会。2003年,浙江兰溪徽学研究会成立。至1990年代,正式的学术机构纷纷建立。1992年安徽大学创建了徽州学研究所。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成立,同年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成立。1994年徽州师专建立了徽州文化研究所。1999年安徽大学组建徽学研究中心,并经申报、审核、批准,当年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外,1990年代以来,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的徽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有10余项之多,表明徽学研究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以上这些学术机构和团体,或主持徽学研究课题,或创办徽学研究刊物,或组织与徽学相关的会议及其他活动,成为开展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如由徽州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徽州社会科学》,自1980年代以来,登载了大量徽学研究论文,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同时,在这些机构周围团结和凝聚了一批徽学研究者,他们是活跃在徽学研究舞台上的主力军。这些学术机构和团体,乃是改革开放以来徽学发展繁荣不可或缺的组织机构。
(4)徽学学科名称的提出与学科理论建设的开展。有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黄宾虹、许承尧等人已提出了“徽学”、“歙学”的概念,可看做是徽学的萌芽和起步。(45) 而作为具有学科意识、体系严谨的徽学(或徽州学)概念的提出,乃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随着徽学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叶显恩、张海鹏等先生已提出“徽州学”的概念。1985年,叶显恩发表《徽州学在海外》一文,其中说:“面对徽州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去年夏天在纽约,周绍明博士和贺杰博士就曾同我谈及建立国际性徽州学研究会的问题。我认为,徽州学的研究热潮正在日本、美国等国家兴起,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为了交流研究成果,共推这一研究课题,国际性徽州学研究会的诞生不是不可能的。”(46) 同年,张海鹏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前言中说:“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致力研究徽州社会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门具有地域特色的徽州学。它既说明徽州社会史值得研究,也反映对徽州社会史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徽州学的内容,除要研究徽州的政治沿革、自然环境、语言、风俗习惯、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宗教制度、历史人物、阶级斗争等等课题外,还有诸如‘新安学派’、‘新安画派’、‘新安医派’这些大的研究领域,更有待于学者们的纵横驰骋。”(47) 随后,在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的前言中亦指出:“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徽学’(又称‘徽州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48) 20世纪90年代之后,徽学研究全面展开,十分兴盛,“徽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提法日益普遍,且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徽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亦随之展开。这期间,关于徽学学科本身的理论研讨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1993年,赵华富先生在黄山举行的首届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49),对徽州文化的特点及徽学的研究对象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2000年,周绍泉发表《徽州文书与徽学》(50),着重阐述了徽州文书对徽学兴起的价值与作用,探讨了徽学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了较大影响。接着,张海鹏发表《徽学漫议》(51),对有关徽学的名称由来、形成原因、涵盖内容、学科性质等诸多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阐发。而后张立文发表《徽学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一文,认为“所谓徽学,是指以徽州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52),强调其理念、学说和精神这一层面,并指出徽学的研究方法依次是象性分析、实性分析、虚性分析。这一年,由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组织编撰、姚邦藻主编的《徽州学概论》也付梓面世。(53) 该书分为两篇,上篇“徽州学通论”,下篇“徽州学分论”,为首部全面论述徽学学科体系之作,自成一家之言,而具先导之功。2004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徽学的内涵与学科建构”研讨会召开。学者们围绕徽学学科的界定、建构、研究方法及相关的各种理论问题各抒己见,展开研讨。会后出版了《论徽学》(54) 文集。栾成显在《徽学的界定与构建》一文中认为,“徽学是以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文献、徽州文物遗存为基本资料,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进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并论述了徽学构建体系的三个层面:基本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各个学科的基础性研究,理念性的概括与总结。该文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55) 徽学学科本身理论建设的开展,是在徽学研究发展繁荣的形势下出现的,另一方面,其对徽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徽学学科形成的标志之一。
(5)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研究大为深化,推出了水平较高的新论著;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视角的更新,又取得了一批有分量的新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许多原有的徽学研究,如徽州佃仆、徽商、徽州土地制度、徽州宗族等领域的研究,遵循科研规律,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先做专题研究,而后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推出了水平较高的新论著。1990年代之后,徽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从以徽州社会经济等为主扩展到其他方面,诸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教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建筑、徽州科技等等,有关徽州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的研究全面展开。与此同时,随着整个学界学术视野的扩大和视角的多样化,徽学研究的视角多有更新,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文化地理学等研究视角和方法亦被应用于徽学研究之中,徽学研究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30年来,徽学研究已取得了一批有水平、令人瞩目的新成果。其主要学术成果详见下节。
重要资料的开发,学术交流的加强,学术机构的建立,学科理论建设的开展,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的取得,这些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徽学研究的突出进展,也是徽学学科形成的显著标志。
三 徽学研究成果概述
学术研究成果是徽学发展繁荣的集中体现。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徽学研究著作达100余部,论文2000余篇。这里仅举其要者略做概述。
(1)资料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56),是由历史所徽州文书课题组在1980年代初整理的基础上,又经多年整理编辑而成的。全书分为宋元明编和清民国编,共40卷,是一部大型文书档案资料丛书。该书曾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等一系列奖项。它是首部经过研究整理、公开发行的徽州文书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学者鹤见尚弘发表评论,认为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的中世及近代史研究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跃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57) 另一部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徽学研究资料是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58),该书广搜博采,涉猎各类书籍230余种,在抄录百万字的基础上选编了40万字,为徽商研究乃至整个徽学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对推动徽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1993年,周绍泉、赵亚光以《窦山公家议》万历本为底本、汇集其他版本补葺的《窦山公家议校注》出版。(59) 2005年之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60) 相继出版,这批资料多保持了原文书的归户形式,具有特色;该中心还组织编辑“徽学研究资料丛刊”,先后整理出版了《太函集》(61)、《新安文献志》(62)、《新安名族志》(63)、《休宁名族志》(64)、《茗洲吴氏家典》(65) 等一批典籍文献资料。陈智超撰著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66),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一批珍贵的明代徽商手札发掘出来,公布于世,并详加考释,为徽学研究以及明清社会变迁的探索提供了重要资料。王振忠教授在出版《水岚村纪事:1949年》(67) 一书之后,又发掘出珍贵的徽商小说稿本——“末代秀才”詹鸣铎所著《我之小史》,与朱红共同整理校注出版。(68) 此外,在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69) 和田涛等编著的《田藏契约文书粹编》(70) 中,徽州契约文书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2)基础性研究专著。改革开放之初,叶显恩先生在其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71) 专著。该书采用文献资料、契约文书、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明清徽州社会做了全面考察,对徽州佃仆制进行了深入探索,是首部解剖和探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力作,具有开拓性。《徽商研究》(72),是由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等组成的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所主持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也是徽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课题。研究者从搜集资料做起,而后进行专题研究,历经十多年工夫,最后写出专著。该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专题探索的突破和新资料的利用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把徽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该书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等一系列奖项。陈学文所著《徽商与徽学》(73),对徽商的资本运作、徽商比较研究以及有关徽商的日用类书研究多有开拓性的阐发。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多次到徽州考察,所著《徽州商人研究》(74) 对徽州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徽州的典当与典当业经营、徽州的宗族关系、身份继承、家产分割等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研究是徽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的基础性课题。赵华富先生自1990年开始专攻徽州宗族研究,多年坚持到全国各大图书馆抄录族谱,深入徽州一府六县实地调研,从个案研究做起,再进行专题研究,历经十多年工夫,最后完成《徽州宗族研究》(75) 这一力作,成为首部全面、系统而深入探索徽州宗族的专著。刘道胜所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76),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对徽州宗族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系首次系统利用文书资料研究徽州宗族之作。韩国学者朴元熇所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77),以徽州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对明清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契机、宗祠转化、徽州商人与宗族组织、徽商方用彬以及方氏族谱等各专题做了深入探究与阐述,成为徽州宗族个案研究的一部力作。章有义先生自1970年代起即着手徽州文书档案研究,改革开放之后,连续推出《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等专著(78),作者利用徽州文书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逐一做个案剖析,一改过去经济史学以摘引文献为主的归纳演绎之法,对明清及近代徽州土地关系做了具体而深入的探索,成果丰硕,受到高度评价。黄册制度是有明一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基本制度,以往学界依据文献资料多有研究。栾成显以徽州文书之中新发现的黄册文书为基本资料,运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写出《明代黄册研究》(79) 一书,厘正了中外学界对明代黄册原本的误判,对黄册制度本身诸问题提出新的阐释,并论及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取得了新的突破。该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并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图书。长期以来,有关徽派朴学大师戴震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很多,而关于其考据学成就的论述甚少。徐道彬著《戴震考据学研究》(80),从戴震考据学的背景及特点、成就、方法、思想等诸多方面对戴震的考据学首次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阐述,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3)综合性研究丛书。进入21世纪,为总结20世纪以来徽州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作出新的探索与研究,安徽省委组织了省内外素有研究的徽学专家30余人,规划和实施了“徽州文化全书”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其最终成果,出版了20卷本、600余万字的“徽州文化全书”(81)。“全书”不设主编,各卷独立成书。“全书”取广义文化的视角,对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做了全方位的展示,物态文化方面,有《徽州商帮》(王廷元、王世华著)、《徽州科技》(张秉伦、胡化凯著)、《徽州建筑》(朱永春著)、《徽州村落》(陆林、凌善金、焦华富著)、《新安医学》(张玉才著)、《徽州工艺》(鲍义来著)、《徽菜》(邵之惠、洪璟、张脉贤著)等卷;制度文化方面,有《徽州宗族社会》(唐力行著)、《徽州土地关系》(刘和惠、汪庆元著)、《徽州教育》(李琳琦著)等卷;行为文化方面,有《徽州方言》(孟庆惠著)、《徽州民俗》(卞利著)等卷;观念文化方面,有《新安理学》(周晓光著)、《徽派朴学》(洪湛侯著)、《新安画派》(郭因、俞宏理、胡迟著)、《徽州篆刻》(翟屯建著)、《徽派版画》(张国标著)、《徽州戏曲》(朱万曙著)、《徽州刻书》(徐学林著)、《徽州文书档案》(严桂夫、王国健著)等卷,丰富多彩,洋洋大观。“全书”富于创新,其中有许多卷实为该专题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而属常见专题各卷,则有新的结构和体系。“全书”既是以往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总结,同时也是新时期探索创新的一次集中展示。另一部由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黄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编撰的系列丛书《徽州五千村》(82),共12卷、200余万字。该书“精选了徽州数千村落中具代表性的550多个村落,抓住其最辉煌的历史瞬间,自唐宋到明清,或记人,或叙事,或反映建筑特色,或记录民俗风情,以村落文化的个性魅力展示徽州文化的丰富内涵”(83)。
(4)新视角下的徽学研究论著。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理论并存,研究方法多样,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社会史研究重新兴起,法制史、文化史研究成为热门,历史人类学亦被大力倡导等等,徽学研究很自然地受到这些新潮流的影响。而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亦为不同理论方法的探索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徽学研究出现了不少在新视角下探索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唐力行所著《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84),即是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徽州宗族、徽州商人、徽州文化及徽州整体社会进行透视分析之作。王振忠所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85),着力阐述徽商的经营发展对社会变迁带来的巨大影响,被誉为“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著作”。卞利所著《明清徽州社会研究》(86),也体现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明清徽州的社会变迁、社会结构、徽商与徽州社会、民俗与徽州社会、法制与徽州社会、徽州的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做了深层次的阐述,从整体上对古代徽州社会做了剖析。同氏另一部著作《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87),以利用徽州各类资料为主,综合使用了史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国家和社会的冲突与整合的视角,将明清两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与当时的农村基层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全面系统地探讨和研究了明清时期国家政权与乡村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韩秀桃所著《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88),则是以法制史的视角和方法,解读古代徽州遗存的丰富的法律文献,进而对中国古代的法理文化做了深刻的阐释。日本学者中岛乐章所著《明代乡村的纷争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史料》(89),利用徽州文书中的珍贵资料,对明代基层社会的诉讼纷争做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明代乡村秩序的实态。阿风所著《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90),以徽州契约文书等为基本资料,对“家族共产制”、“父权家长制”、“女子分法”、“强制继嗣”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之不同层面论述了明清时代中国妇女的地位与权利。王振忠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他独树一帜,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所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91),对新发现的民间档案文书进行了剖析,笔调清新,阐发入微,开辟了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徽州文书档案的新领域。周晓光教授别开生面,所著《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92),取徽州的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突破传统的徽州学术文化研究模式,首次依据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空间和区域的角度,对12世纪中叶以后的徽州学术文化体系做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视角新颖,资料翔实,考证缜密,堪称徽州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
改革开放以来徽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不能全部举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成果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不能仅限于徽学范畴之内加以评判,它对改革开放以来其他学科的发展繁荣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徽学研究的展望
温故而知新。改革开放以来徽学研究既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它们都对今后徽学研究的发展予以重要的启示。若要推动徽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恐怕不能不加以关注。
第一,资料开放问题。徽学研究具有雄厚的资料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徽州文书的整理、公布与研究,曾大大推动了徽学研究的发展。然迄今已整理公布的徽州文书数量大约还不到所藏总量的1/10,还有大量文书档案资料仍被深藏馆阁,研究者难以窥见。如众所知,其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这里面还有一个体制和观念上的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但封闭的保守的观念和做法依然存在。殊不知,对资料只有开放,公布于世,研究的人才会多起来;而一种学问研究的人愈多,则愈兴旺发达。古今中外的学术发展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敦煌学之所以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与其研究资料早已公开、能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利用是分不开的。最近,我国敦煌学者编撰的“敦煌文献合集”已陆续出版(93),这是一部汇集国内外收藏的集大成的敦煌文献合集,也就是说,有关敦煌学的文献即将全部公布于世,它不仅为敦煌学科,而且将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资料。与敦煌文献相比,徽州文书资料的整理公布还相差甚远。对那些大批仍被束之高阁的徽州文书采取何种态度和做法,将是影响今后徽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毫无疑问,在这些大批尚未公布的原始档案资料之中,蕴涵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具有广阔的学术开发前景。若能将其逐步整理公布于世,对于推动徽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嘉惠学林,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基础性研究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尽管它不以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但它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长远效用已是众所周知。基础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一个学科若没有雄厚的基础性研究,最终是难以立于学术之林的。徽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整体上看,其基础性研究还相当薄弱。然而,目前在课题的选择上多有忽视基础性研究的倾向。或为了申请项目,竞相争报那些大而空疏、缺乏实际内容的课题;或为了追赶某种潮流,去搞那些看上去很时髦的选题;或选取一些细枝末节、意义不大的题目。其实,徽学之中许多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几乎没有展开,而在业已开展的领域之中,如徽商研究、徽州宗族研究等,其基础性研究仍有很大余地。如徽商资本研究,徽商与明清市场研究,徽州典商、布商、木商研究,人口流动与徽州宗族的形成,徽州宗族个案研究,徽州族谱研究等等,这些课题都尚待开展。此外,在研究之中缺乏力度和深度,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即使选择了基础性课题,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已发表的徽学论著数量极为可观,但亦毋庸讳言,其中相当一部分论著并未怎么下工夫,题目多有重复,内容并无新意,既没有发掘新的资料,更未作出深入探索,多是在已研究过的层面上炒来炒去。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徽学研究,不难发现,凡是那些研究深入、成就突出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论著,都是肯下工夫,先从全面搜集资料做起,再进行专题研究,最后才推出质量高的论著,都是历经多年时光、反复打磨的成果,而不是那种东拼西凑的急就篇。我们应该向那些踏踏实实、刻苦钻研的研究者们学习。基础性研究对于新兴的徽学学科来说既是十分迫切的,更是关乎徽学长远发展的大问题,具有战略意义。徽学若要牢固地立于学术之林,只能建立在雄厚的基础性研究之上。
第三,研究理念与视角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研究中必须坚持开放的理念。这一点在今后也必须坚持下去。徽学是有一定地域性限制的一门学科,但徽学研究则不能关起门来搞,做封闭式研究,而必须秉持开放的理念,实行开放的做法;必须加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学习它们成熟的经验;必须关心国外学者的研究,借鉴他们优秀的研究方法;必须了解整个学术界的动态,汲取新的营养;而各个徽学研究者之间更要加强对话,互相交流,切磋研讨,互相启发。在具体研究中,则应有开放的视角和广阔的视野。在徽学研究中,既要防止泛化的倾向,不能把与徽州历史文化无关的东西也拉到徽学研究中来,也要防止地方化的倾向,对徽学学科本身的定位应有正确的认识。那种把徽学与藏学、敦煌学一起称为“三大地方显学”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须知藏学和敦煌学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称为地方学,敦煌学从有其名伊始即称之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94)。徽学也不是地方学。如今,徽州的西递、宏村古民居也与敦煌莫高窟一样,早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又怎么能把徽学定位于地方学呢?徽学的研究对象虽有一定的地域性限制,但徽学的内涵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性质往往要超出地方本身,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此,对徽州文化的研究不可只局限于地方范围之内,要有广阔的视野。当然,在徽学研究中既要阐述其普遍性价值,又不可忽视对徽州文化特点的提炼。愈是属于徽州特点的则愈具世界性。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研究也很薄弱,亦亟待加强。
第四,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问题。作为徽州历史文化的载体,遗存至今的不仅有文书档案和文献典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在原徽州一府六县地区内遗存的大量的文物古迹。诸如古城、古村落、老街、民居、古建筑、祠堂、牌坊、石雕、砖雕、木雕、碑刻、古桥梁、古塔、水口、竭坝、匾额以及其他文物等等,都有丰富的遗存。这些遗存不仅数量多,颇具规模,而且价值高,极为珍贵。许多遗存都属顶级文物,堪称中国历史文化之精华;已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者,不止一处。特别应指出的是,这些文物遗存并非一个个互不联属、孤立存在的点,而是互相联系,关系密切,构成系列,交相辉映,在相当程度上还保存着原有的文化生态。它们分布在原徽州一府六县的广大区域内,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区。这是弥足珍贵的。这种整体性的文化遗存,更能让人们感受到那逝去的历史原韵。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去寻找这种整体性的遗存已越来越难了。然而,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又不可避免地对传统文化生态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徽州地区也是如此。近来,由学者倡议经国家正式批准,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已经设立。而要切实保护好这一文化生态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对徽州文物予以普遍而系统的调查、登录、整理、抢救,对这一珍贵的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即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开展对徽州丰富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也是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上所述,迄今徽州文书与文献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形之下,徽州文物方面的研究则很薄弱。徽州文物的丰富遗存,构成了相当完整的系列,对这一“徽州文物大系”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已经提到日程,亟待展开。采取多学科研究相结合,运用不同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对徽州遗存的丰富的物质文化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必将迎来徽学研究发展的新局面。
从根本上说,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徽学学科的形成,乃在于徽州文化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极高的研究价值;在于徽州文化拥有丰厚的遗存——徽州文书、徽州文献、徽州文物;在于这些重要研究资料的重新发现。正是这些,为徽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为学科理念的提炼提供了可能。而另一方面,研究者们的努力与奋斗亦不可或缺。回顾徽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使我们认识到,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拥有丰厚的资料遗存和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学科形成的根本条件。前二者乃为客观属性,后者则是在一定时机下人为努力的结果,三者缺一不可。改革开放则为徽学研究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大好时机。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徽学学科的形成,是几代学人、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徽学研究的发展,仍取决于研究者们的努力。从长远来看,徽学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它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和拓展空间,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愿徽学同仁共勉。
本文撰写的参考文献有: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辑的《徽学论文总目》(95)、薛贞芳编辑的《徽学研究论著目录》(96)、卞利所撰《20世纪徽学研究的回顾》(97),一并致以谢忱。
注释:
① 熊鱼山:《金正希先生年谱》,《神州丛报》1913年第1卷第1期,1914年第1卷第2期;吴景贤:《金正希与抗清运动》等4篇论文,载《学风》第5卷第1、6、8、9期,1935年。
② 钱宝琮:《汪莱衡各算学评述》,《浙江大学科学报告》第2卷第1期,1936年。
③ 张明仁:《我所知道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6年;谭彼岸:《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问题》,《岭南学报》第2卷第9、10期,1937年;王璜:《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9期,1937年;王璜:《王茂荫后裔访问记》,《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10期,1937年。
④ 王集成:《绩溪经学三胡先生传》,《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6期,1935年;沈筱瑜:《绩溪三胡氏学通论》,《中日文化》第3卷第8、9、10期,1943年。
⑤ 梁园东:《清俞正燮的史学》,《人文月刊》第4卷第2期,1933年;柳雨生:《黟县俞理初先生年谱》,《真知学报》第2卷第3期,1942年;同报第3卷第1期,1943年。
⑥ 朱芳圃:《程瑶田年谱初稿》,《河南大学学术丛刊》1943年第1期。
⑦ 郭沫若:《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光明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6年。
⑧ 吴晗:《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3期,1937年。
⑨ 商承祚:《程瑶田桃氏为剑考补正》,《金陵学报》1938年第8卷。
⑩ 陈垣:《休宁金声传》,《真理杂志》第1卷第4期,1944年。
(11) 许承尧《歙事闲谭》,撰于1930年代,原为未梓稿本,2001年由黄山书社出版。
(12) 诸伟奇:《(歙事闲谭〉序》,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
(13) 汪世清、汪聪:《渐江资料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984年修订再版。
(14) 刘敦桢:《皖南歙县发现古建筑的初步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3期。
(15) 张仲一等:《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业出版社1957年版。
(16) 殷涤非:《歙南古建筑调查中的一些认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17) 胡悦谦:《徽州地区的明代建筑》,《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
(18) 吴景贤:《明清之际徽州奴变考》,《学风》第7卷第5期,1937年。
(19) 刘序功:《略谈清初徽州的所谓“奴变”》,《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1期。
(20) 程梦余:《宋七与徽州“奴变”》,《安徽日报》1958年5月25日第3版。
(21) 傅衣凌:《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60年第2期。
(22) 魏金玉:《明清时代佃农的农奴地位》,《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23)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1947年第2期;后收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4) 傅衣凌:《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
(25) 陈野:《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试以徽州一地为例来论证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5期;后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版。
(26) 藤井宏:《明代盐商之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一)、(二)、(三),《史学杂志》1943年第54编第5、6、7号。
(27) 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一)、(二)、(三)、(四),《东洋学报》第36卷第1、2、3、4号,1953至1954年。
(28)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68年版。
(29) 斯波义信:《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2年版。
(30) 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章第3节《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版。
(31) 牧野巽:《明代同族社祭记录之一例——关于〈休宁茗洲吴氏家记·社会记〉》,《东方学报》第11册,1940年。
(32) 多贺秋五郎:《关于〈新安名族志〉》,《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956年第6期。
(33)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第五章《明末徽州的庄仆制——特别关于劳役婚》,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版。
(34) 居密:《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地主制溯源》,《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1976年版。
(35) 方豪:《明万历年间之各种价格——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一》,《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3期,1971年;《明万历年间富家产业抄存》,《食贷月刊复刊》第1卷第5期,1971年;《乾隆五十五年自休宁至北京旅行用账》,《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7期,1971年;《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杂账及嫁装账》,《食货月刊复刊》第2卷第1期,1972年;《乾隆二十二年汪朱氏丧事账》,《食货月刊复刊》第3卷第1期,1973年;等等。又参阅卞利:《徽州契约文书之三次外流》,《光明日报》2002年7月9日B3版。
(36) 傅衣凌:《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序言》,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版。
(37) 居密:《主与奴:十七世纪的农民怒潮》,(美)《明史研究》第8期,1979年。
(38) 居密:《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和宗法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39) 宋汉理:《徽州地区的发展与当地的宗族——徽州休宁范氏宗族的个案研究》,荷兰汉堡莱登大学《通报》,1984年。
(40) 基恩·海泽顿:《明清徽州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41) 《江淮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2) 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
(43) 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4)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前言》,黄山书社1985年版。
(45) 鲍义来:《早期徽学浅见》,《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14页。
(46) 叶显恩:《徽州学在海外》,《江淮论坛》1985年第1期。
(47)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前言》。
(48)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前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9) 赵华富:《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张脉贤主编:《徽学研究论文集》,黄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1994年编印。
(50) 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51) 张海鹏:《徽学漫议》,《光明日报》,2000年3月24日C3版。
(52) 张立文:《徽学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光明日报》,2000年9月12日B3版。
(53) 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4) 朱万曙主编:《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5) 栾成显:《徽学的界定与构建》,《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7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期全文转载。
(56)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57) 鹤见尚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日)《东洋学报》第76卷第1、2号,1994年;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4期。
(58)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59) 周绍泉、赵亚光:《窦山公家议校注》,黄山书社1993年版。
(60) 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一辑(10册)、第二辑(1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6年版。
(61) 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
(62) 程敏政著,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黄山书杜2004年版。
(63) 戴廷明、程尚宽著,朱万曙等点校:《新安名族志》,黄山书社2007年版。
(64) 曹嗣轩著,胡中生、王夔点校:《休宁名族志》,黄山书社2007年版。
(65) 吴翟著,刘梦芙点校:《茗洲吴氏家典》,黄山书社2006年版。
(66) 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7) 王振忠:《水岚村纪事:194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68) 詹鸣铎著,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9) 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0) 田涛、[美]宋格文、郑秦编著:《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
(71)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2)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3) 陈学文:《徽商与徽学》,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
(74) 臼井佐知子:《徽州商人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版。
(75) 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6) 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7) 朴元熇:《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首尔:知识产业社2002年版。
(78) 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79)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又,《明代黄册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80) 徐道彬:《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1) “徽州文化全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2) 程必定、汪建设等主编:《徽州五千村》,黄山书社2004年版。
(83) 程必定、汪建设等主编:《徽州五千村·出版说明》。
(84) 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5)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86) 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7) 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8) 韩秀桃:《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9) 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的纷争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史料》,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版。
(90) 阿风:《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91) 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92) 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3) 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全11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其他各部文献合集将陆续出版。
(94)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之四,1931年版。
(95)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网站发布,网址:http://www.huixue.org/hxlwjs.htm。
(96) 薛贞芳:《徽州藏书文化·附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7) 卞利:《20世纪徽学研究的回顾》,《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