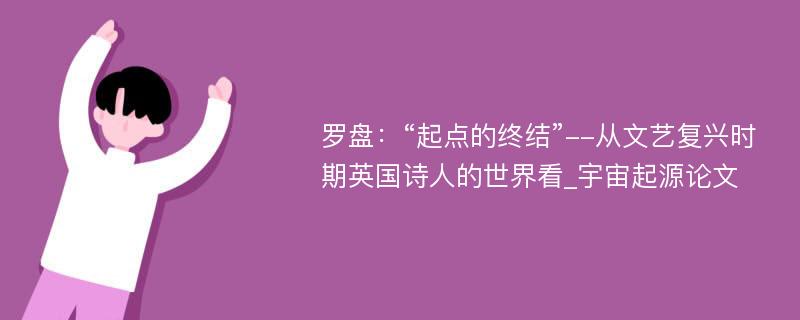
圆规:“终止在出发的地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宇宙观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宇宙观论文,圆规论文,英国论文,诗人论文,地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611年冬,约翰·多恩随其恩主罗伯特·特鲁里爵土出使巴黎,临行前写了《告别辞:莫伤悲》一诗赠妻。全诗九节,最后三节采用“圆规”的意象来表现一对情侣圆满的精神之爱,说明他们的两个灵魂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多恩采用圆规意象的那三节诗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灵魂即便是两个,
那也与圆规的两只脚相同,
你的灵魂是圆心脚,没有任何
动的迹象,另只脚移了,它才动。
这只脚虽然在中心坐定,
如果另只脚渐渐远离,
它便倾斜着身子侧耳细听,
待到另只脚归返,它就直立。
对于我,你就是这样,我像另只脚,
必须倾斜着身子转圈,
你坚定,我的圆才能画得好,
我才能终止在出发的地点。
这个圆规意象被公认是玄学派诗人最负盛名的奇思妙喻(conceit)。女方是圆心脚,“在中心坐定”,男方是圆周脚,倾斜着身子围着中心“转圈”。前者暗示女方的坚贞不渝,后者也以同样的忠贞爱她。“你坚定,我的圆才能画得好”,表明完美的爱情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样,一对精神情侣虽然即将分离,但他们心心相印,精神融合,犹如圆规的两只脚,紧紧相连。值得注意的是,这三节诗还与开头一节诗具有内在的联系:
有德之人逝世,十分安详,
对自己的灵魂轻轻说,走,
有些悲伤的亲友则高声讲,
他的气息已断,有些说,还没有。
这个开头似乎十分突兀,但细想一下,其含义也很清楚。诗人把一对精神情侣的离别喻为死亡,即生离如同死别。但对死亡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德之人”关注的是“灵魂”,因此镇定“安详”地面对死亡;而“悲伤的亲友”关注的只是肉体(“气息”),因此惶惶不安,以致“高声”争辩。诗人以此来劝慰对方“莫伤悲”:他们对待离别应像“有德之人”对待灵魂归天那样,镇定安详,默无声息,不应像“悲伤的亲友”那样惶惶不安,高声叹息、哭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把离别喻为死亡,而死亡又意味着另一种“离别”,即离别今生,进入来世。这就形成了一种“离别—死亡—离别”的模式,仿佛绕了一圈,画了一个圆。这个隐含的圆和最后一节中圆规所画的圆前后呼应,形成对照。在这个意义上,全诗以圆开始,以圆结束,正是“终止在出发的地点”,完成了自身的圆。当然,这还远非事情的全部,因为它具有更为深层的多重含义:圆在这里不仅暗示精神之爱的圆满,而且由此也象征灵魂的完美和生命的永恒。[①]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寓义都源自“圆规”这个意象。
多恩不仅在诗歌中,而且在他的《拉丁布道文》中也常用圆规意象。譬如,他用这意象来解释复活的问题,他说,基督确立了复活的模式,复活构成了上帝的圆。上帝首先创造了亚当的肉体,因此人的肉体是上帝“圆规”的一只脚落在上面的起点,随后上帝把圆规转了一圈,又落在人的肉体上,在复活中使之荣耀。又如,他还用圆规意象来解释今生和来世的不同,他说,尘世的生活是用“圆规”逐步画出的一个从点到点的圆;来世的生活是已经印好的圆,一开始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完美的圆。总之,圆规的意象似乎紧紧攫住了多恩的想象。然而,尽管多恩可能是把圆规意象引进英国诗中的第一位诗人,但就此意象本身而言,却绝非是他的独创。与他同时代的约瑟夫·霍尔早先就采用过这个意象。霍尔说,一颗虔诚的心灵不能没有基督徒的慷慨之手,即“博爱”和“忠诚”,它们构成一付完美的“圆规”,可以达到基督徒心灵的真正纬度。随后他解释道,“忠诚是一只脚,定在中心不动,博爱则沿着仁慈的圆周运行”,这两只脚是从来不曾、而且也绝不能分开的(《书信集》第二卷第一章)。16世纪意大利诗人瓜里尼还把他自己比作一付“圆规”。他说,他把一只脚固定在神——他的中心——那里,另一只脚则受命运车轮的支配,不由自主地围绕着神旋转(《情歌》,46首)。据有些注家考证,圆规的意象早已见于11世纪末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柔巴依集》(旧译为《鲁拜集》),后来才传入欧洲。[②]哈亚姆采用圆规意象的那首诗如下:
你同我都是一个圆规的形骸——
虽有两只脚却只有一个脑袋;
当圆弧的中心我们一旦确定,
两个脚尖我们就并它在一块。[③]
对照来看,多恩的上述几节诗和哈亚姆的这首诗的确如出一辙。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把圆规的意象一直上溯到基督教《圣经》。《圣经》中有这样几句话:“他(指神)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放上圆规”(《箴言》8:27)。显然,根据基督教传统,神原来是用圆规设计宇宙、并完成创世这一壮举的。无怪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流传着这样的格言,“神以几何学原理工作”。[④]对于用圆规创世的神话,弥尔顿在《失乐园》中作了更为具体的描绘:
他手拿金制的双脚圆规,
是神的永恒金库所备,
做为规划宇宙万物时用的。
他以一脚为中心,另一脚
则在幽暗茫茫的大渊上旋转一周,
……
天神就这样创造了天和地。[⑤]
(第七卷,224—232行)
既然宇宙是用圆规创造的,它自然呈现为圆形。这与公元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所描述的圆形宇宙一致。但丁的《神曲》和弥尔顿的《失乐园》都采用了托勒密宇宙结构作为全诗的框架。根据托勒密天文学,宇宙呈圆形,地球也呈圆形,处于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地球外围有七颗行星,构成七重天,而行星外围则是恒星天。到了中世纪,神学家们在恒星天外面又加上水晶天和原动天(宇宙的外壳),从而构成“十”这个圆满的数目。然而,这只不过是可见的宇宙。在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看来,在那些可见的星体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抽象的、概念的宇宙。正如柏拉图所说,星空“虽是最美丽、最完美的可见事物,但应被认为远逊于真实的事物”,或“只有通过理性而不是视觉才能领悟的事物”。[⑥]也就是说,可见的宇宙虽美,但不可见的宇宙更美,这是最高的现实,即理式宇宙。客观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式世界的摹本,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领悟那种理式世界。柏拉图的理式世界很容易就被转变成了“神”或“上帝与天使”的居处。这样,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宇宙总共有了十一重天:最外面的是上帝和天使居住的无限空间,即无形的宇宙;而有形的宇宙则包括十重天,按它们到地球的距离由近及远的顺序是:月亮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水晶天、原动天。月亮天上方称月上世界;下方称月下世界,即尘世,是宇宙的基本区,这里有土、水、气、火四种元素。月上世界的九重天都围绕地球这一中心旋转,因此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一个“圆规”意象。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圆球形是“最美的形体”。[⑦]柏拉图也说,神以自身的形象创造宇宙,把它做成了圆形,这是所有形体中“最完美、最自我相似的形体”。[⑧]柏拉图还说了如下一段话:
这是永恒之神的设计,他给予即将产生之神以一个平滑而又连续不断的表面,从中心到各个方面都等距,并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实体,它的各个构成部分也都是完整的实体。神把灵魂放在中心,并使灵魂扩散到整个实体,把它包住。于是神建立了一个圆球形的宇宙,作圆形运动。[⑨]
亚里士多德认为,动力因有两种,一种是固定不动的,另一种是推动它者、本身又被推动的欲念。他说,“在车轮上,有一点必须固定,必须由它开始运动。”[⑩]不难看出,在这些观念之中都隐含着圆规的意象。
圆规意象至少涉及三个主要方面:圆形、圆形运动和中心。
“圆”究竟具有什么属性呢?首先,圆是无始无终的;其次,圆周线上的任何一点到中心的距离相等;第三,倘若把圆周线当作直线距离考虑,那么它就包括最大的面积。[(11)]这些属性综合起来便构成了神的形象,因为神不仅是“无始无终”、“亘古长在”、“无所不包”的,而且也是一个没有圆周之圆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又是“无所不在”的。正如约翰·海登所说,有些古代哲学家“把神界定为一个光球,一个圆,它的中心无所不在,而任何地方也没有它的圆周线。这种描述当然不可能有其他意思,无非是说神的本质是无所不在的,具有那些令人钦羡的属性,即无限性以及绝对完美的善、知识和力量。”[(12)]因此,“圆”是神的象征,是统一、完美和永恒的象征,而神“自身的形象”就体现在他所创造的圆形宇宙之中。
中世纪哲学家认为,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仿照宇宙的圆形模式。譬如,耶路撒冷城当时被认为是处于北半球圆形大陆的中心,因此该城建成了圆形,城中心是圆形圣殿,圣殿的中心放置了一块瓮形石,表明这是“世界的中心”。英国14世纪作家曼德维尔曾经写道,世界的中心是由耶路撒冷圣墓中神殿里的一块石制“小圆规”标明的;那块石头的放置之处正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把耶稣遗体背去为之清洗伤口的地方,从而表明人是世界的中心。不仅如此,曼德维尔还观察到,圣墓的圆形被重现于世界其他各地的神殿设计之中,那些神殿不过是对“真正”的耶路撒冷神殿的一种模仿罢了。他说,“可以想象这样的图案,有一个大圆,大圆的中心又有一个小圆……大圆代表苍穹,小圆代表地球。”[(13)]在他看来,这种建筑模式均是天国之城新耶路撒冷的摹本。斯宾塞在《仙后》第四卷中所描绘的“维纳斯神殿”可以说就是这种宇宙模式的再现。诗中写道,维纳斯女神是生殖、繁衍和丰饶的象征,她的神殿座落在一个圆形岛屿的中央(第十章,6,21节),神殿内有“一百根大理石圆柱”和“一百座神坛”(第十章,37—38节),而这些圆柱和神坛又都围绕在神殿中央一座闪光的神坛四周,在这神坛上则站立着美丽的女神维纳斯,她的目光向四方不断地放射出影响(第十章,46—47节)。不难看出,这里隐含着圆和中心的意象。斯宾塞的这个例子可以阐明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们所崇尚的“模仿自然”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认为诗人是创造者,但由于他本身也是一个以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小宇宙,他的创造不过是一种小规模的重复行为,是对神的创世行动的一种模仿而已。因此,他的作品必然以创造出来的宇宙为模式,而神圣的宇宙则是一切形式的源泉。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来说,宇宙是神为人而创造的。神不仅以自身的形象创造了大宇宙,还以自身的形象创造了小宇宙(人)。大宇宙和小宇宙有很多相似之处:物质世界中有四种元素,人体内则有四种体液;宇宙有精神世界,人则有理性灵魂,与神相通。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和尊严。至于人的灵魂,在柏拉图看来它是“世界灵魂”的摹本,在新柏拉图主义观念中它则是起源于或发射自世界灵魂。[(14)]因此,和神一样,灵魂也是由圆来象征的。斯宾塞在《仙后》第二卷中说到“阿尔玛城堡”的建构时有如下一段十分奇特的描绘:
它的构架似乎部分是圆形的,
部分是三角形,哦,神圣的作品;
最前和最后的部分就是这两个,
一个不完美,终会腐朽,属阴,
另一个永不腐朽,很完美,属阳性,
作为基础的正方形,处在中间,
按七和九的比例,分配均匀;
九是设置在天空上面的圆,
一切汇成了一个音域,美妙而委婉。
(第二卷第九章,22节)
实际上,这座城堡的设计暗示一个人体结构。圆形代表灵魂,三角形代表肉体(头和双腿构成三角),两者之间的方形代表人体内的四种体液。此外,灵魂是“形式”,属于阳性,肉体是“物质”,属于阴性。“七”和“九”则分别代表人体的两个部分:前者指与七颗行星对应的、分成七部分的头脑,后者指与九级天使对应的人的灵魂。[(15)]如果说斯宾塞在这里采用了寓言手法把灵魂形容为“圆形的”,那么多恩在《挽歌:致哈林顿勋爵》一诗中就径直地把灵魂与圆等同了:“哦,灵魂,哦,圆呵,你为何这样快就终止,你的生与死,在你里面闭合?”
传统上认为,圆形内接一个方形的图案是意味深长的。方形由四点构成,代表冷、热、干、湿四种基本素质,这些素质又按四种可能的结合(冷干、冷湿、热干、热湿)而组成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了世间万物,构成了有形的宇宙。因此,方形可以代表四种元素、四种体液、一年四季、人生四个时期,等等。总之,方形是物质世界或肉体的象征。至于圆形,它代表灵魂和神明,代表无限和永恒,因而是精神世界的象征。由此看来,内接方形的圆说明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它即可代表包含物质世界和神明世界的宇宙,又可代表具有肉体和灵魂的小宇宙(人)。任何变圆形为方形的企图都意味着把无限变为有限,把精神变为物质。多恩在《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和他的妹妹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翻译〈雅歌〉颂》一诗的开头说:对于永恒的上帝,没有任何人敢于寻找这么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即“变圆形为方形”,把“无角的、无限的”上帝塞进“贫乏才智的角落”里面。安德鲁·马维尔在《阿普尔顿宅邸颂》一诗中也说:“圆形里的方形”在各种意象里都等同于“人”。另一方面,任何变方形为圆形的企图则意味着把方形的边无限地增多,使不连续变为连续,使物质变为精神,从而达到完美。正如马维尔在同一首诗中所说,“把方形弄成了圆形”。在这个意义上,圆形内接方形的图案表明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相互转化的关系。也就是说,神(圆)是无限的,物(方)是有限的;神无所不包,是一,物是部分,是多元;神是抽象的,物是具体的。然而,无限和有限如何联系?一和多元如何联系?抽象和具体又何联系?这就必须通过神秘的创造。神创造了有形的宇宙,一创造了多元的世界,无限创造了有限,抽象创造了具体。反过来说就是,由具体可知抽象,由有限可知无限,由多元的世界可知一,由有形的宇宙可知无形的宇宙——神。
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们似乎习惯于以圆形来思考问题。意大利诗人卡斯蒂利翁的著作《朝臣之书》于1561年由托马斯·霍比爵士译成英语,颇受欢迎。书中的人物本伯先生说了这样几句话,“美来自上帝,象一个圆,善是它的中心。因此,就像没有中心就不可能有圆那样,没有善也就不可能有美。”多恩更是如此,他的短诗《告别辞:哭泣》几乎通篇是圆形意象,如地球、月球、钱币、泪珠。斯宾塞的史诗《仙后》则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以仙国的首府克勒俄波利斯作为潜在的中心,其周围有一串较小的圆形结构,如“阿尔玛城堡”(第二卷第九章)、“阿多尼斯花园”(第三卷第六章)、“维纳斯神殿”(第四卷第四章)、“伊西斯神殿”(第五章第七章)等都处于圆形(或圆规、轮盘)的中心。其实。世间有很多物体的形状并非圆形,但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也总以圆形来思考它们。最典型的例子恐怕是托马斯·布朗了。他写过一部著作,书名为《居鲁士花园》,又称《古人园林中的五点、菱形、网眼形,从艺术、自然、神秘角度加以考虑》。居鲁士是公元前6世纪波斯皇帝,他在征服巴比伦后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装饰一新,树木都栽成“梅花五”格局,正梅花五是方形,扁梅花五是菱形或网眼形。由此类推到古代建筑,如砌石是上面两块、中间一块、下面两块;房屋分成房基、隔墙、门窗、房间、屋顶五部分;房柱有五种格式,等等。此外,还有自然界的众多现象,如星辰和花草都与五有关,即使六角形的峰窝也可划分为三个菱形,甚至人的皮肤也呈网状。最后布朗以一种寓有“圆形”含义的方式解释道,“一切事物的开始都是有秩序的,也应当如此结束,然后再这样重新开始,这就是按照秩序的规定者和天国的神秘数学行事。”[(16)]尤其在评论花瓣和树叶时,他似乎作了总结性的说明:“自然界的高级几何把圆分为五个幅(radii)”,[(17)]而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也都是模仿自然而制成的。不管怎么说,布朗把世间众多不同的形状最后都归结于神秘的“圆”。这足以说明圆形意象在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思想中占有怎样的支配地位。
前面已经提及,圆的意象不只是一种静止状态,它还暗示圆形的运动。在宇宙中,月上世界的天体围绕地球做圆形运动;月下世界的四种元素做直线运动,如火与气向上、水与土向下运动。四种元素做直线运动是由于每种元素都有其“对立物”,而天体做圆形运动则表明它们没有“对立物”。有对立物的东西就必然有产生和朽腐的过程,因为一切产生的事物都是由其对立物产生、随后又朽腐而转变成对立物的。因此,四种元素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而做圆形运动的天体则是永不朽腐的。此外,从物质和形式的角度来说,一切可朽事物都是因形式不能完全渗透物质而具有潜能,于是就产生运动。但天体由于形式充满了物质的全部潜能而不具有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潜能,因此做适合于它们的圆形运动。[(18)]总之,圆形运动表明事物的不朽性,直线运动则表明事物的可朽性。然而,即使由产生到朽腐的这种直线运动本身也是循环往复的,如火变气,气变水,水变土,或逆向变化,总之是不断地循环往复,从而又构成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圆形运动。[(19)]法国哲学家拉·普里莫达耶曾以拟人手法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他说:四种元素既相互一致又相互冲突,既紧密联系又各具特质,所以他们每个都像长有两只手,彼此手拉手,“围着圆圈跳舞”。[(20)]这可视为表现宇宙圆形运动所常用的隐喻“宇宙舞蹈”的一个例子。其实,宇宙舞蹈是在不同层次上不断重复的。在文学中这类例子几乎举不胜举,如弥尔顿描写各星体绕太阳舞蹈,“众星宿按着日、月、年的计数顺序,有节奏地跳着舞蹈而运行,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运动中,迅速地转向太阳这个万物所喜爱的明灯,或者是受他的磁光吸引而旋转”(《失乐园》第三卷);又如,天使围上帝舞蹈,大海随月亮舞蹈,太阳绕地球舞蹈,世间万物、甚至包括砂石和植物也都参与宇宙舞蹈。[(21)]宇宙舞蹈的模式最初见于荷马史诗《伊利昂记》第十八卷中所描绘的“阿克琉斯之盾”上。火神伍尔坎为阿克琉斯铸造了一个坚固的大盾牌,用铜、锡、金、锡、铜铸成五层。盾面上绘有大地、海洋、天空、太阳、圆月和诸如昂星团、毕星团、猎户座、大熊座等星座。盾的边缘是一圈无穷无尽的海溪(宇宙的边缘)。中间绘着两座城市、农田、王室领地。此外,更有一个“舞池”,在这舞池中,小伙子和姑娘们手挽手排成长串,“优美地绕着圆圈,迅疾地旋转,犹如陶工弯腰试转时的转盘。”这一画面充分表现了人和宇宙的关系,人的圆舞象征宇宙的舞蹈和圆形运动。
在文艺复兴时期,圆形运动常被用来表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再生”或“复活”模式。复活是死而复生,这本身就是一种循环或圆形运动。根据基督教人文主义观点,世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也都隐含着完美性。它们当初被创造时都是完美的,最终也必将达到完美。造物主是一切运动的根源和归宿,因此万物的运动都呈现为圆形模式。人也必然以一种超然的方式”进行圆形运动,力求恢复自身中亚当原本具有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性在基督的完美形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人类的堕落使这一运动变成了一个“艰苦的圆”。[(22)]但是,倘若人能坚持信仰,他就能画出一个完美的整圆,“终止在出发的地点”。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都表现了这个主题,即完全依仗上帝以及灵魂中的能力,在神的佑助下获得再生。[(23)]这个模式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屡见不鲜的,就像《圣经》所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传道书》1:9)。复活主题可用多种方式加以表现。有些诗人喜爱采用自然象征,像日落日出(如弥尔顿的《黎西达斯》)、冬去春来或花谢花开(如斯宾塞的《四月牧歌》、乔治·赫伯特的《花朵》);有些喜爱采用禽鸟意象(如莎士比亚的《凤凰与斑鸠》、亨利·沃恩的《鸡啼》);还有些喜爱精神游历模式(如亨利·沃恩的《再生》和《退路》)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采用精神游历来表现“复活”主题的模式占有重要的地位。德马雷指出,有一种按中世纪“T+O”型地图来描写精神游历是相当典型的。这种地图把耶路撒冷绘在世界的中心,近旁是西乃山。但到10—11世纪时,西乃山被画成一个小三角,处于《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从红海到耶路撒冷的路线上。当时的地图仅包括亚、非、欧三洲:亚洲包括西乃山、死海和耶路撒冷,位于圆形的上部;非洲包括巴比伦(现在的开罗)、尼罗河和红海,位于圆形的右下部;欧洲包括泰伯河畔的罗马,位于圆形的左下部。地中海以圣坛状的“T”形把下部分开。直布罗陀海峡位于T形底端较低点上,通向围绕整个圆形陆地的大洋。根据《旧约》,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逃出埃及,最后抵达耶路撒冷。根据《新约》,中心则转到了耶稣布道的罗马。这样就构成了“埃及—耶路撒冷—罗马”的路线,或“非洲—亚洲—欧洲”的模式。[(24)]这种模式不仅暗示精神的再生,而且也表明绕地球转了一圈,画了一个圆。但丁的《神曲》被认为就是遵循这种模式的。到了斯宾塞时代,尽管地图以及宗教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他在《仙后》第一卷中描写红十字骑士的精神游历时,基本上仍以寓言手法遵循“埃及—耶路撒冷”的圆形游历模式,虽然那终点已不再是欧洲的罗马,而是象征尘世和天国的新耶路撒冷的英国了。红十字骑士随乌娜走入“错误之林”,杀死一条大蛇;那蛇吐了遍地肮脏东西,犹如尼罗河漫出埃及的山谷,退潮后便留下大堆大堆的泥沙,从中长出了无数可怕的怪物。这个比喻暗含早期教会的传统观念,把世俗的埃及与尼罗河看作是极端丰饶、傲慢和罪恶的象征。红十字骑士离开这个区域,逐步走向最后的精神再生。他遇到诸如伪装的隐士、香客、异教和基督教骑士等各种邪恶的化身,抵制了“骄傲之宫”女主人卢西弗拉的诱惑,并在“神圣之宫”得到精神的恢复。在这里,他登上圣山,知道了通往天国之城的路。最后,他击败恶龙,与乌娜在一座伊甸城堡定婚,接着出发前往天国的“新耶路撒冷”,而这新耶鲁撒冷既类似于尘世的耶路撒冷又暗示仙后的首府克勒俄波利斯(均与英国伦敦相联系)。[(25)]
可以发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有许多作品都暗含这种圆形的游历模式。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写了葡萄牙航海家拉斐尔从比利牛斯半岛出发旅行到另一个岛国(即当时几乎仍不为人知的新大陆),随后返回葡萄牙,从而构成了从一个半岛(或岛屿)驶向另一个岛屿(或半岛)的循环模式,亦即一种圆形结构。约翰·李利在《尤菲绮斯或智慧的剖析》中采用了近似的模式,他把基本故事情节的时间和地点移到了希腊半岛,随后又返回英国。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主人公米兰公爵从亚平宁半岛上意大利的米兰出发,遭遇风暴,海上沉船,被洪波冲到一座岛上,在那里建立了乌托邦式的和谐,最后又返回米兰。弗朗西斯·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也采用了前往一个虚构的本塞勒姆岛游历的模式。在这类结构中,斯宾塞的《仙后》也许更具代表性。这部史诗以仙后格罗丽亚娜和她的宫廷为中心,在每年一度为期十二天的宴会中每天都从宫中派出一位象征一种基本品德的骑士外出除害安良,他们除了从一个岛屿驶向另一个岛屿之外,还从一座城堡走向另一座城堡,或从一处山林溪泉走向另一处山林溪泉,等等。总之,他们从一次冒险活动转向另一次冒险活动,但在完成各自的冒险活动之后又都返回仙国,形成了围绕一个中心的圆形运动。格列斯比评论说,《仙后》的基本情节和情境是:
一个主人公或一批主人公从一个冒险活动到另一个冒险活动,从一个岛屿驶向另一个岛屿,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这种基本情节和情境,也见于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时期、甚至18世纪那些不可胜数的描写探求活动的教诲传奇,不论它们的背景是能够辨认的现在,或是遥远的异国或往古的时代。(26)
但是,这种循环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循环,可以说它是一种首尾并不相接的圆。它隐含着不断的进步和一系列变化,而一切变化都有其终极目的,即追求完美,达到永恒。斯宾塞在《仙后》第三卷第六章中这样来描写“阿多尼斯花园”:在这“乐园的中央”,隆起一个土丘,丘顶上有一座精致的小屋。在这小屋里,象征物质丰晓和天堂之爱的维纳斯女神“占有”着按季节变化死而复生的阿多尼斯(46节);他虽然“逃不脱终有一死的命运”,但却“在变化之中获得永恒”(41节)。在小屋下方的园中,有一位具有变化和永恒“双重性质”的“老守护神”,他给“赤裸的婴孩”穿上永恒的真实“形式”(31—32节),然后送他们出去旅行,穿越那条呈现为圆形的生命之路。那些婴孩穿上了“形式”的衣服,“再次进入富于变化的世界,直到重返他们当初的出生地,像一个车轮,从老到新地旋转不已”(33节)。但是,当那些婴孩在生活中像轮子那样旋转而变化时,他们的变化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方式”,而“实质上是永恒的,而且永无变化”(37—38节)。这种“变化—永恒”的主题同样表现在《仙后》第七卷“变化章”里。总之,循环变化将导向永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永恒”是中心,而“变化”则围绕这个中心旋转不已,形成了一种圆形运动。
由此也可看到“中心”的意象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中心就不可能有圆,更谈不上什么圆形运动。但是,围绕中心的圆形运动往往也同时隐含着一种直线运动,即半径的延伸和缩短。譬如,在上面所引多恩的诗里,圆心脚在“中心”坐定,圆周脚“渐渐远离”,待到它“归返”,圆心脚就直立。这里便综合了两种运动:一是圆形运动,但同时也暗示半径在不断伸长,直到画出最大的圆周线,接着半径缩短,圆也随之缩小,直到最后“终止在出发的地点”。诗人的圆在圆周线上当然是既无起点又无终点的,它只是随着半径而做延展和缩小的运动,最后达到起点和终点的重合。这种重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达到“永恒”。“永恒”本身就是一个圆,但谁都不可能说清它的半径究竟有多长。正如前面已经提及,“永恒”是一个无限的圆,其中心无所不在,但任何地方又都没有它的圆周线。这种特征只不过说明中心和半径的同时性而已,没有任何有限的圆能够表现“永恒”的无所不包的范围,也没有任何特定的中心能够暗示它自己的无所不在。从现实来看,它只能用一个没有纬度、没有面积的点来表示,而这个点同时既是中心又是圆周线,即两者重合。因此,返回“中心”也就意味着返回“永恒”。另一方面,与“永恒”的圆不同,人的圆则是有限的,它的半径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它总是倾向于自身的目标,总是朝着完美的中心不断运动。当圆最终闭合,它也就没有了半径的延伸,从而与无限的永恒重合在一起了。因此,灵魂的圆规是以时间开始、以永恒终止的,它总是围绕着中心运动:中心既是它的起点,又是它的终点。[(27)]
然而,对于基督教人文主义诗人来说,这个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中心”实际上就是“神”。神不受空间限制,因为他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神也不受时间限制,因为他是“无始无终”、“亘古长在”的。神由于包括一切时间,也就超出了时间之外。在无限时间和直线时间当中,只有后者才能称作“时间”,[(28)]而前者则是“永恒”。永恒之神既是圆周线又是中心。因此,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宇宙观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世界的中心,但这不过旨在提高人的地位和尊严、说明人可与神相通而已,并不意味着人等同于神。在宇宙的“存在之链”上,人毕竟是处于天使和兽类之间的,充其量只是神以自身形象创造的“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罢了。归根到底,人是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上说,神“在大地的中央施行拯救”(《诗篇》74:12)。但丁在《新生》中把“爱”描绘为一位天使,他向诗人显现,并给自己下了一个神秘的定义:“我是一个圆的中心,与圆周线上的所有部分都有相等的关系;但你却不是如此”(第十二章)。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大天使拉斐尔对亚当说,“神是天的中心,同时又向万物扩展;你在中央接受从诸天发来的光”(第九卷)。因此,正如高级天使日夜围绕上帝旋转那样,人的灵魂也应始终围绕上帝和天使旋转。
从现实世界来看,城镇有中心,神殿有中心,花园有中心,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宇宙神圣模式的再现。伊利亚德在分析建筑的中心象征时说道,圣山,即天、地相交之处,是世界的中心;每一神殿或皇宫——延伸而言,每一皇室居住的城市——都可视为一座圣山,因此也是世界的中心;圣城或神殿,由于是世界的中心,也都可视为天、地相交之处。在传统上,神殿被看作是世界的意象,神坛被看作是宇宙本质的再现,这些观念都溶进了欧洲基督教的宗教建筑模式之中。[(29)]其实,文学作品何尝不是如此。诸如圣山的象征,升天的象征,生命树的象征,以及各种“探求中心”的象征,也都同样以众多方式清晰地表现在文学作品里。譬如,希腊神话中描写伊阿宋探求金羊毛的冒险,赫拉克勒斯寻找赫斯珀里底斯看守的金苹果的历程,以及穿过迷宫的艰难;又如亚瑟王传奇中讲述寻找圣杯的故事,《仙后》中描写各个骑士追求完美品德的冒险活动,以及其他各种探索自我之路的描写,等等。然而,毫无例外的是,通向中心的道路总是迂回曲折、充满艰难险阻的,因为中心乃是一种神圣的区域,一切所谓绝对现实的象征。实质上,一切对于探求活动的描绘都旨在表明:
寻找中心是从世俗到神圣、从短暂到永恒、从人到神的过渡。到达中心则意味着神圣化,意味着昨日的存在让位于一个新的、真正的、持久而永恒的生命。[(30)]
因此,返回中心也就意味着达到灵魂的完美和生命的永恒,犹如画了一个整圆,“终止在出发的地点”。这或许可以说明文艺复兴时期充满理想的诗人们为何对“圆规”的意象如此情有独钟的缘由吧。
注释:
①参见柰杰尔·福克塞尔:《十首诗歌分析》,佩格曼出版社1996年版,12页。
②参见王佐良、李赋宁等编:《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249页。
③译文引自《柔巴依集》,黄杲昕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51页。
④保罗·H·科切尔:《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科学与宗教》,圣马力诺1953版,150页。
⑤本文中《失乐园》译文均引自朱维之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⑥柏拉图:《理想国》529,本杰明·朱厄特英译本,纽约1968年版。
⑦转引自朱光潜《西方学美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33页。
⑧ ⑨柏拉图:《蒂迈欧篇》33B—34B,R.G.布里英译本,伦敦1952年版。
⑩亚里士多德:《灵魂论》Ⅲ.x.,R.D.希克斯英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07年版。
(11) (28) 参见S.K.赫宁格:《美妙的和谐》,圣马力诺1974年版,111,214页。
(12) 约翰·海登:《世界的和谐》,转引自赫宁格《美妙的和谐》,141—142页。
(13) 曼德维尔:《曼德维尔爵士之书》,转引自约翰·G·德马雷:《宇宙和史诗表现》,杜基斯尼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02—103页。
(14) 参见P.M.格雷戈里奥斯:《宇宙的人:神圣的存在》,纽约1988年版,15页。
(15) 参见A.C.汉密尔顿编:《斯宾塞:仙后》,朗曼出版社1977年版,251页。
(16) (17) 托玛斯·布朗:《医生的宗教和其他作品》,伦敦1928年版,229,199页。另参见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38—140页。
(18) 亚里士多德:《产生与朽腐》,参见《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科学与宗教》,149页。
(19) 巴西尔·维利:《十七世纪背景》,伦敦1934年版,18页。
(20) 拉·普里莫达耶:《法兰西学院》,转引自《美妙的和谐》,176页。
(21) 参见E.M.W.蒂利亚德:《伊丽莎白时代世界图景》,伦敦1943年版,94—99页。
(22) 参见谢尔曼·霍金斯:《变化与月份的循环》,载威廉·纳尔逊编:《埃德蒙·斯宾塞诗中的形式和传统》,纽约1961年版,79页。
(23) 参见《弥尔顿英语诗歌》(选自《弥尔顿百科全书》条目),伦敦和多伦多1986年版,115页。
(24) (25) 参见《宇宙和史诗表现》,8,122—148页。
(26) 吉列斯比:《欧洲的小说的演化》,胡家峦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13—14页。
(27) 参见约翰·弗雷切罗:《多恩的圆规意象》,载《英语文学史》,1963年12月第4期。
(29) (30) 米尔西亚·伊利亚德:《永恒再现的神话,或宇宙与历史》,纽约1954年版,15,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