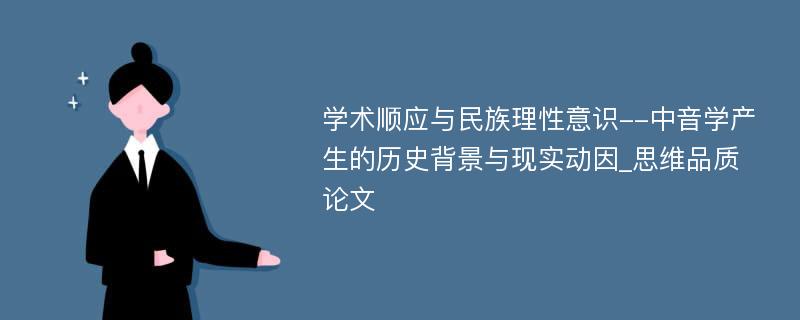
学术遵命与民族的理性自觉——中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历史背景论文,中华论文,自觉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进程一直伴随着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
当由美国学者倡导建立并以本国国名命名的学科——美国学,业已发展成为显学的时候,中国学者无疑有一种深刻的悲哀: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居然没有一门旨在以科学理性认识自己国家民族并以自己国家民族命名的学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知名学者萧君和先生才率先提出了建立“中华学”的主张,并出版了《中华学初论》,对中华学的涵义与价值取向,研究对象与内容以及研究角度和方法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明与界定[1]。《中华学初论》问世以后, 立即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纷纷撰文支持这一意义深远的倡导,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2]。
正如伟大的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者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就中华学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作了深入的探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连开教授认为:中华学的出现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研究的深化和中华民族新的理性自觉[3]。我们知道, 任何一门学科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一门学科的产生背景和动因往往决定了这门学科的前景和生命。那么,中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动因又是什么呢?
1.中华学创立者的主观原因:深层次遵命
忧国忧民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秉承的优良传统。1932年12月,鲁迅先生在为自己的《自选集》作序时,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之为“遵命文学”。鲁迅就此说到,他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4]。他在为革命呐喊助威的同时, 也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5]。自鲁迅之后, “遵命”一词,常常被后人尤其是中国学者视为自己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良知。
萧君和先生是一个历尽沧桑、富有传奇色彩的知识分子,他把包括创立中华学在内的学术探索视为一种“深层次遵命”。很显然,这是对鲁迅先生的“遵命”说的一种继续和深化。他在谈及写作《华魂论》的初衷时曾经说到:“我总觉得,面对世纪末的风风雨雨,应该遵历史时代之命,遵祖国民族之命,投身到发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行列中去。这种优秀传统太需要发掘了。惟有发掘出这种优秀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才能自信、自立、自强,进而坦然自若于世界” [6]。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萧君和所提出的“深层次遵命”,并非是对鲁迅先生的简单重复或者机械套用,而是源于自己的坎坷经历和生命中的深刻体验。萧先生自幼就有热爱思考的品质,在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向报刊投稿,勇敢地阐述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在那个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他的人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灾难的境地:两次考上大学,两次遭到除名,他作过搬运工,当过流浪汉,“文化大革命”时候,他又因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而被视为“异端学说”,直至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直到1979年才平反出狱。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12年的萧君和始终没有停止过探索和思考,他热爱中华山水和勤劳勇敢的人民,而沧桑的人生经历,则更加刺激了他对自己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进行思考的激情。正是因为如此,在他刚刚出狱的时候,他就发誓要以自己的学术探索为中华振兴服务。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他最初以文艺理论为突破口潜心研究,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出版了《美的奥秘探寻》、《现代人的艺术系统》等五部专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1984年,他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要将中国艺术写意传统、意境理论和西方的艺术写实传统、典型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的目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一目标的提出和为此所作的努力和实践,就是他日后创建中华学的思想的发端。1991年初,萧君和出版了旨在探索中华民族灵魂深层次结构的《华魂论》。从建立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到探寻中华民族灵魂的深层次结构,已为中华学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
而萧君和所说的“深层次遵命”。其实质就是要感受时代风雨,抓住事物的本质,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学者自己最关切的国家民族进行再认识。“我们应该建立从理性上认识和研究我们国家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理性反映的学科。”由此可见,中华学的创立,不仅是他探究中华民族灵魂的延伸和继续,而且是他十多年学术研究的心愿和归宿。
2.中华学创立的客观背景:中华民族整体研究的发展及其总结
中华学的提出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不仅仅只是“深层次遵命”的逻辑结果,而是中华民族的整体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无疑也是中华学创立的一个非常客观而重要的学术背景。
中华文明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虽然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早在元朝时期就已经奠定,但却长期处于一种“自在”状态,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有所变化。陈连开教授认为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研究——也即是中华民族由“自在”进入“自觉”的进程中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年代,以孙中山和梁启超为代表的两种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其结果最终形成了“五族共和”的主张,使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有了历史性的飞跃;第二次引起对中华民族研究的关注并形成高潮的是在抗日战争前夕,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结构展开了辩论,有的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分汉族和少数民族,应统为一体,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必须承认中国境内有许多少数民族,要肯定并正视他们的存在。毛泽东于1938年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号召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第三次掀起对中华民族作整体研究的高潮则是最近的20年间的事。其标志是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观点[7]。
陈连开教授对中华民族研究历史的梳理具有相当的深度和高度,其“三个高潮”的结论无疑是令人信服的。但是,我仍然想指出的是,陈先生在对历史上出现的中华民族整体研究高潮进行划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在我看来,这堪称为中华民族由“自在”转入“自觉”的最重要的标志。因为在此之前,有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成员结构、民族成分以及民族称谓一直是处于混淆不清的状态。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即组织大批科研人员和民族工作者分赴各民族地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就各个族体的族称、分布地域、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社会历史等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各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族称,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调查地区之广泛和深入,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为这次民族识别的最重要的成果,至80年代,经国务院正式确定公布的共有56个民族。这不仅基本解决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族属问题和民族成分的结构问题,而且为中华民族理性自觉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事实上,作为这次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的主持者之一,费孝通教授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科学论断。费先生的核心观点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 而这个“一体”是一个以从事农业为主,逐步融合中原各民族而形成的汉族为中心,形成覆盖全境的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个“格局”具有六个特点:一是存在一个凝聚的核心“华夏族团”——汉族;二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面积占全国一半以上;三是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少部分有自己的文字,但汉语是通用语言;四是导致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五是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所以是多元结构;六是中华民族形成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作为费教授“进入成熟阶段树立的学术高峰”,“多元一体”概念的确立无疑在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民族研究已由分析研究进入综合研究阶段,并将成为民族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这当然也成了中华学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
在费先生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启示下,萧君和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族体论”,他认为:“中华民族族体就是以汉族为中心,以中国少数民族和世界华人为不可缺少的部分,再以中华全息为‘细胞’,加以联系、贯穿而成的网络系统[9]。”较之以往,“中华族体论”的提出, 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更加明晰。这时,萧君和已注意到:“中华”是一个人与自然相统一、中华民族与中华自然相统一的实体。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在对中华民族进行总体研究的时候,始终围绕着“华”,也即是围绕着“人”做文章,而有关“中”的问题,也即是中华自然问题或者中华环境问题。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说明国际社会已就世界环境问题形成了共识:地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环境问题,都可能对全球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必须通力合作,共同创建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人类新文明。当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的时候,人们才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人和自然平等对话、同步协调发展,人类才会获得可持续发展。中华自然是世界自然的一部分,爱护自然、保护环境不仅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而且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前途。事实上,中华自然既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自然条件和自然保证,也是铸造中华民族性格的熔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萧先生认为,既然要凸现“中华”,就必须凸现“中华民族”和“中华自然”,并将中华自然提升到事关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高度。“中华学”也因此获得了出现和存在的根据,因为“中华学要实现的就是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将中华民族、中华自然综合起来研究,或者说,把中华民族研究成果、中华自然研究成果综合起来作进一步的研究”[10],其主旨和目标就是要探究和揭示中华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学是对“中华”深入认识、由具体到科学抽象的产物,它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中华学的研究对象——“中华”既把握了中华民族,又提到了中华自然以及中华民族和中华自然变换物质的产物——中华文化,这是对“中华”范畴里各种具体事物的最高程度的抽象。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11]。中华学的诞生,中华学研究对象——“中华”的确定,就达到了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抽象”,而这个抽象反映了“中华”范畴的确定,就达到了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抽象”,而这个抽象反映了“中华”范畴的“自然”,即中华范畴里的各种具体事物及其规律。
这里也顺便说说,中华学对中华研究的高度概括和抽象,也符合客观的认识规律,也即是马克思所指的“第一条道路”:认识世界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12]。既然如此,中华学掌握群众也就有了必然的可能。
3.中华学出现的现实动因:振兴中华需要深刻的自知自觉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是中国的古训,其中最重要的是“知已”,没有深刻的“知已”,就不可能很好的“知彼”,孙子所要强调的实质上就是理性思维。对此,恩格斯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3]”。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实践理性丰富,但理论思维、科学理性精神匮之。由此而引发出英国人李约瑟博士的“天问”:“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者亚洲其它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14]”在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讨论的时候,许多中国学者包括像周光召院士这样的著名科学家,都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技术而无科学”,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而理论思维、科学理性精神的匮乏,不仅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科学的落伍,而且也严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这不能不引起中华儿女的全面反思。
应该承认,当西方的坚船利炮荡开近代中国的国门以后,也曾经引起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反思。陆续有人开出了振兴中华的药方:张之洞主张“中体西用”,亦即所谓“旧学为本,新学为用”,谭嗣同则激烈地抨击和否定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主张“全盘西化”,而康有为则更多地立足于个体自由,主张渐进地改变现存秩序,五四先贤如陈独秀、胡适等则大声疾呼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痛感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里没有这两样东西。但是,他们的倡导和主张并没有治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病根。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多次出现感情用事,头脑发热,忽左忽右,激动盲从的非理性局面,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一次次灾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只局限于一般的自我认识,没有很好地凸现出科学理性、理论思维的地位和作用,更没有注意到对民族思维结构的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感性认识方式,也就是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思维模式对中华民族影响非常巨大,已经成为民族思维结构中的痼疾。因此,要想实现现代化,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就必须对民族思维结构进行改造。这种改造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深刻地自知自觉的过程,而科学理性思维,是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前提和根本。这时候,人们期待能有一门学科来体现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科学理性精神。萧君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建立中华学的倡导,无疑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因为建立中华学的目的就是要在学科建设的角度上彻底解决我们国家民族“知已”——“自己认识自己”的问题,在保持和发扬实践理性的同时,弘扬科学理性的大旗,从理论上思考、认识自己国家民族,使我们国家民族发展的更快更平稳。其道理正如萧君和所说的那样:“中华学是我们中国人建立的从宏观的、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认识自己国家、民族,亦即研究、认识中华及其规律的综合性学科[15]”。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已为中华学的催生和壮大铺设了温床和土壤。中华学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深层次遵命”的学术成果,而且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自知自觉的呼唤和理性思维的必然产物。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为已任的中华学,其价值和意义也必然将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得到充分的认同和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