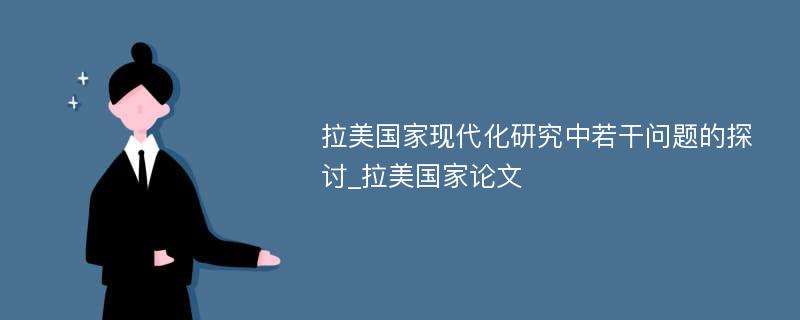
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研究若干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2—0079—08
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于19世纪初期就取得政治独立,并在19世纪中期以后陆续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现代化的“先行者”。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拉美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就实现了人均GDP1000美元,到1999年,整个拉美地区(5.08亿人口)的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 从拉美自身前后来比较,其发展似乎是很可观的。但是,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作某种横向比较,却又是另一番情景。据有的学者研究,墨西哥和巴西分别于1974、1975年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和韩国、马来西亚(均在1977年)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大体同步。但20年之后,墨西哥、巴西的人均GDP水平已远远落后于韩国和马来西亚。阿根廷是拉美率先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经过20年之后,按等值美元计算,实际人均GDP反而下降了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 拉美国家既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又是现代化的“落伍者”。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流行着诸如“拉美化”、“拉美病”、“拉美陷阱”等说法,其中心意思是说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或发展)进程遭遇了挫折,落入了某种陷阱。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参与有关“拉美化”的讨论,而是根据我们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初步研究,就其中的一些重要现象或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或许对于我们加深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整体了解不无裨益。
一、关于拉美国家现代化的起始时间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究竟起始于何时,国内外学术界大体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二是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是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第一种观点以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即拉美结构学派)为代表,主要是强调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才作为部分拉美国家的一种“国家意识”或国家发展战略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内方面,部分国家前期的经济发展为启动工业化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一定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并引起了初步的社会转型,其中特别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在国际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沉重打击了拉美国家推行了数十年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取国外制成品的办法难以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深了外来制成品供应与国际运输的困难。上述内外环境促使一些拉美国家开始由本国生产某些制成品来取代进口商品,从而“自发地”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并在30~40年代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应当说,拉美结构学派从当时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把部分国家新当权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将工业化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作为现代化启动的标志,是有其科学依据的。因此,这派观点战后几十年间影响很大,我国拉美研究界也都采用这种说法。
认为拉美国家现代化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既有一些西方国家学者,也包括拉美的依附论学派。这派观点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影响也比较小。某些激进的依附论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放松了对拉丁美洲的统治,使拉美国家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机遇。这种观点显然受所谓与西方发达国家“脱钩”的思想影响,并不符合实际。就拉美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主要变化是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成为拉美的主要资金与商品供应国。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起始于1870年的观点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为代表。这部权威性著作的作者们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是,在1930年以前,部分拉美国家的现代制造业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生产和组织上富有革新精神的趋向来看,证明有些领域现代工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最明显的是智利和巴西。本国制造业性质上的变化,在阿根廷和墨西哥也可以看到:在某些特殊部门正日益增多地参与当地本国制成品消费的供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秘鲁和哥伦比亚也扩大了制造业生产活动。”因此,“不能再把1930年说成是拉丁美洲现代制造业的起点了……拉丁美洲的现代制造业应从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时期算起。”② 统计资料显示,1928年前后,拉丁美洲有6个国家现代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0%,其中乌拉圭达到15.6%,阿根廷达到19.5%,这两国的人均制造业产值分别为93和112美元③。此外,相关国家的经济普查数据也反映了1930 年以前现代工业的发展规模。例如,1935年,阿根廷已拥有工业企业40613家, 平均每家企业用工12.9人,拥有动力50.2马力④。巴西1920年拥有工业企业13336家, 工人总数27.6万人⑤。墨西哥1906年工业企业就超过6000家;智利1926年有大、中型工业企业3000家。
鉴于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部分拉美国家现代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剑桥拉丁美洲史》将拉美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定在1870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过,我们并不赞成把1870~1930年这个阶段笼统地称为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而是倾向于用“早期工业发展”或“早期工业化”阶段的提法。我们采用这个提法所要强调的问题主要是:①1870~1930年期间,拉美各国实行的是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即所谓“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时期”。当时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是农、矿业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带来的一种结果,如初级产品加工工业和部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的发展。②当时拉美国家当权的自由派地主阶级大都没有提出国家工业化的战略方针及其相关政策,甚至也缺乏利用大宗出口收入来建立现代工业的自觉意识。③当时拉美各国所进行的“自由改革”都是服务于实施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即便某些改革措施客观上也有利于工业发展,那也只是一种间接的效用。④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市场已经呈现出对初级产品出口不利的长期趋势,但没有任何一个拉美国家因此而提高工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依旧执行扩大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方针,终于受到1929年大萧条的沉重打击。
二、发展模式转换的“钟摆现象”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1870~1930)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1930~1982)阶段;外向发展模式(1982年以来)阶段。我们把这种“外向——内向——外向”的变化称为模式转换的“钟摆现象”。这种每隔50~60年才出现一次的模式转换显然既不取决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愿,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如果转换得比较成功,甚至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问题在于,拉美国家这种钟摆式的发展模式转换每一次都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1870年开始实施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在前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一模式已明显地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不相适应。但是,当时在拉美国家当权的大农牧业主集团恰恰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不但没有及时地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反而继续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这样,1929年大萧条前夕,拉丁美洲各国继续遵循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它们在世界初级产品市场的不利条件下极易受到伤害。”⑥ 这种伤害表现为1929~1933年拉美发展史上经历的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英国经济史家罗斯玛丽·索普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在调整发展模式方面出现了一次“大延误”。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的主要利益集团受自身利益的驱使,在国际环境已经变得不利的情况下,还继续把原来的发展模式推向某种极端,最终只能在一场严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转换发展模式,实行180度的急转弯。
同样,拉美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在20世纪30~40年代是比较顺利的。到50年代初,一些率先实行这种发展模式而国内市场又相对狭小的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就开始出现工业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即便是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拉美地区的大国,到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其内向工业化模式也陷入困境。与此相反,亚洲“四小龙”在战后初期也是实行进口替代模式,但它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转入外向发展模式,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拉美国家却在1973年之后又走上“负债增长”之路,继续在进口替代模式下挣扎,直到1982年以债务危机为表现形式的严重结构性发展危机的爆发,延续了50年之久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才走向终结,又一次被迫地实行180度的急转弯, 并造成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破坏。拉美发展模式转换的第二次“大延误”有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受益的社会集团要保护其既得利益,再次将一种发展模式推向了某种极端,导致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
三、工业化进程的大反复
从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终结以来的20多年,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经历了一次大反复。其主要表现是:①在经济持续衰退中制造业首当其冲。1980~199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1%,其中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为0.1%,是衰退最严重的部门;1991~2003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6%,制造业继续在低水平上徘徊,工业部门失去了作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的地位。②工业化程度倒退。拉美地区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24.1%降至2000年的18.9%。③工业部门创造就业的能力严重下降。90年代期间,拉美新增就业岗位的60%靠非正规经济部门提供。④制造业结构的变化。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拉美国家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方针,对制造业结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墨西哥、中美洲及部分加勒比国家采取重点发展客户工业的“生产专门化”模式;南美洲国家采取重点发展资源加工产业的模式。这个结构调整过程使原来的一些制造业部门被大大削弱或被拆除。有的学者认为:“巴西是惟一保留了大量工业生产结构的国家,而其他所有国家都被拖入了一种‘去工业化’(des-industrialización)境地。巴西也是惟一保留了重工业的国家,从而可以生产和吸收先进技术,在其他所有国家重工业都被拆除了。”⑦ 此外,拉美国家绝大部分被保留下来的工业企业已经私有化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些变化?80年代初债务危机发生后,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逼迫拉美国家按期偿还债务。为了克服对外支付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牺牲制造业,以争取外贸盈余。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先是拉美各国快速地拆除关税与非关税保护,开放市场,使长期在高保护下成长起来的大批工业企业在“雪崩式”的外来商品竞争中纷纷破产。然后,各国又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形成以客户工业或资源加工业为主的专门化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前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回归。
不论是以客户工业为主还是以资源加工产业为主的“生产专门化”,从理论上说似乎都有道理,因为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但这两种专门化模式在实际运作中都出现了问题。墨西哥地理上与美国相邻,又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安排,因而成为发展客户工业的典型,并从中获得了不少益处。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第一,墨西哥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过高(接近90%),墨西哥经济摆脱不了美国经济荣衰变动的影响;第二,客户工业的发展集中于墨西哥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个产业发挥不了拉动和整合国民经济的作用,近年来墨西哥南、北两大地区发展的差距明显加剧。智利是发展资源加工业的典型,20世纪90年代由于农、林、渔、矿产品出口繁荣,智利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6.6%,在拉美地区可谓“一枝独秀”。但智利这种专门化模式的问题也已开始显现。其一,农、林、渔、矿业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与其他产业之间缺乏联动效应;其二,这个产业主要被一些私人大企业控制,这些企业仅以占20%的就业比重提供全国95%的出口产值;其三,由于国内生产和供应能力有限,出口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又转变为进口需求。综上所述,拉美国家目前所采取的生产专门化模式能不能推动国民经济较快的、可持续的增长,还很值得关注。
四、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拉美国家的传统农业是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商品农业和以印第安人为主的生存农业并存的二元农业经济。大庄园制、种植园奴隶制、分成制、印第安人村社制等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在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1870~1930),拉美国家为适应处于工业化高潮期的欧洲国家对食品和原料的巨大需求,普遍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各国当权的地产主阶级纷纷实行“自由改革”,如建立土地交易市场,大规模兴建铁路等基础设施,引进外国资本,建立海关、邮电、银行等。在土地问题上,拉美各国采取了没收天主教会地产,印第安人社区土地私有化,取消印第安人保留地,废除永久租佃制和长子继承权,拍卖公共土地,实行土地勘界等多种措施,使国内权势阶层和外国公司获取了大量土地资源,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大地产制度。大批丧失土地的印第安人和其他下层劳动者被各国政府以多种形式强制进入劳动市场。因此,尽管这个阶段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有力地带动了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地产主阶级势力进一步壮大,农村社会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在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农民为获得土地而举行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就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焦点。
当拉美进入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后,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自身的力量相对弱小,不能不在政治上对传统的地产主阶级采取某种妥协态度;另一方面,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农业部门的支持。在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拉美国家早就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并在50年代初期出现两种观点之间的公开辩论。“第一种主张认为,分配问题是中心问题,农村问题如果不通过改革将资源大量地从一些集团转移给另一些集团,是不可能解决的。改革就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也面临政治上的困难。第二种主张力图尽量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走一条技术变革的道路,并认为技术变革的好处将会逐渐地扩散开来。”⑧ 就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言,本来社会变革与技术变革两者是不可或缺的。在拉美地区的这场辩论中,二者竟然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选择,并且最终是主张通过技术变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观点占了上风。因此,在拉美地区,自1915年墨西哥颁布第一部土改法以来,土地改革虽然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十年,但实际成效非常有限。除古巴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外,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尼加拉瓜征收的土地只占农业用地的50%左右;哥伦比亚、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征收的土地只占全部用地的1/6~1/4;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等国征收的土地就更少;委内瑞拉土地改革所涉及的土地不仅面积有限,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有待开垦的荒地。根本就没有实行过土改的拉美国家也不在少数。在进行过局部土改的国家,或因政府的后续支持不够,或因农户经营管理不善,实际效果往往不太理想。在某些国家,右翼政府上台后宣布原来的土改无效,将已征收的土地又归还原主。正如英国学者罗斯玛丽·索普所说:“尽管(土地改革)这个课题在60年代的政治问题中具有突出地位,但土地改革在现代化和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和间接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拉丁美洲的许多土地改革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后导致大庄园制度的消灭,相反,它导致了大庄园的现代化并改造成资本主义的农场。”⑨
拉美农业现代化所选择的“技术变革”道路,主要就是在保持大地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绿色革命等来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通过所谓“资本主义局部渗入”方式来改变农业部门的生产关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不断地扩大农业边疆也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拉美地区耕地面积已由1950年的5000多万公顷扩大到1980年的12000万公顷。在这种农业现代化模式下, 中小农户因土地资源被高度垄断而失去发展空间;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快速地从现代农业部门排挤出来;传统的农业二元经济演变为现代大型农业经营单位与个体小农并存,并在二者之间形成出口农业与内需粮食生产的产业分工;由于现代农业经营单位普遍规模过大,生产效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拉美出口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而依赖小农生产内需粮食的局面造成粮食供应能力提高缓慢,其结果是,农业部门由过去能提供大量外贸盈余转为外贸逆差,从而丧失了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外汇支持的能力。
五、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
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1920年为22%,1950年为41.6%,1980年为65.5%,1999年为75%。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9年,拉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率为2.50,在世界各个地区中是最高的。拉美城市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许多国家50%或更多的人口集中于一个城市,例如,1980年,海地、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巴拿马、智利、乌拉圭、阿根廷等国首都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均在44%~66%之间。拉美城市化的加速期出现在1930~1980年,大体与这个地区工业化的高潮期同步。不过,拉美城市化过程的加速除了城市地区工业化的“拉力”外,农村地区的“推力”和人口爆炸的“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前所述,拉美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加速地将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排挤出来,一方面使农业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造成由农村向城市自发的移民潮。拉美各国政府不但对城市提供就业的能力缺乏科学的预计,而且把这种自发的移民潮视为缓解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渠道,因此,对这种劳动力的无序转移没有采取调节措施。1950~1980年,拉美总人口增加1倍,劳动力总量由5468万增加到1.18亿,增加1.16倍,同期城市人口增加4倍。墨西哥城人口由1950年的300万增加到1980年的1500万,同期圣保罗人口由250万增加到1350万,里约热内卢由290万增加到1070万,利马由110万增加到470万。
大批农村劳动力自发地流向城市以后,城市却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加上各国政府规定的“创业门坎”过高,更加剧了就业难题。早在60年代,拉美城市就业就出现所谓“第三产业化”和“非正规化”的现象,即大量无法就业的劳动力只能从事各类自谋生计的传统服务业。根据拉美14个国家的统计,1950年靠“非正规部门”生存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13.6%,198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20%,即由700多万人增加到2300多万人。城市的社会贫困现象迅速增加。1980年,拉美城市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6290万,比农村贫困人口(7300万)少1000万左右, 到1990年,城市贫困人口(1.354亿)是农村贫困人口(7390万)的1.8倍。早在70年代初,拉美城市的贫民窟现象就非常引人注目,其中几个重要城市住在贫民窟的居民占的比例如下:利马40%;加拉加斯42%;墨西哥城46%;布宜诺斯艾利斯50%;圣菲波哥大60%⑩。
六、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化
拉美国家的传统社会是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其社会结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岛人”,他们作为殖民统治者虽然人数不多,但集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权力于一身。其次是土生白人,即出生于拉美殖民地的白种人,其人数在拉美独立战争前夕已占当地白种人的98%以上,经济上很富有,但政治与社会地位远不及“半岛人”。再往下是以梅斯蒂索人为主的各种混血种人。金字塔的底层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及其后代。拉美国家独立后,土生白人地产主取代“半岛人”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并将以土地资源为主的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到他们手里,其他社会阶层的地位并未发生变化,包括奴隶制被废除之后黑人奴隶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拉美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历时130 多年的现代化进程自然伴随着一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1870~1930),拉美国家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的大繁荣和早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这个阶段社会分层化尽管比较缓慢,但在拉美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到1930年前后,“在最大的城市里高度集中了土地或商业精英、牧师、自由职业者、外国侨民,以及为他们服务并建筑了大城市基础设施的各阶级——各种各样的家庭仆人和劳工。”(11) 上层社会除了土地精英和商业精英外还有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在劳工阶级中,普通劳工、街头小贩、家庭仆人等占大多数,但在诸如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出现。当时的城市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有小工商企业主,居住在城市的中等农场主,以及律师、医生、教员等自由职业者,也包括某些商业机构的职员和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员。可以说,到1930年为止的这些变化还只是社会分层化的初期阶段。
1930~1980年是拉美工业化的高潮期。这个阶段拉美工业化的特点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工业部门的扩展(如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的兴起和家用电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原来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中美洲国家)逐渐被卷入工业化的潮流中来。新的工业化浪潮加速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带动了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城市的就业机会,并伴随着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和城乡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就业分层趋向于简单化,农场主和农业工人逐渐成为主体,小农往往兼有独立劳动者和临时工的双重身份。城市就业分层则趋向于多样化。城市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大、中型企业作为提供就业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例如,在1960~1980年期间,受雇于大、中型企业的工人占就业工人的比例,墨西哥由51.9%增加到60.4%,智利由52.7%增加到63.2%。②国家提供就业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与当时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分不开。阿根廷(1980)公共就业占城市正规就业的33.8%,巴西(1982)占29.3%,哥伦比亚(1982)占21.2%,秘鲁(1981)占49.1%。③服务业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工业化带动了金融、商贸、行政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诸如小商业和个体服务等传统服务业以及文教卫生、社区服务等的需求增加,其中许多流入城市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城市中产阶级中,原来的小企业主、独立手工业者等的重要性明显下降,受雇于公共部门和工商企业的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独立从业的律师、医生等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中,由于债务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和经济改革的冲击,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中产阶级缩小的现象,即各国都有比例大小不一的一部分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滑落到社会下层。
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早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前,拉美地区经济处于持续增长状态。1950~1980年,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倍多,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观察这个发展进程就发现一个普遍的特点(尽管国家之间存在某些差别):资产占有高度集中,收入分配有利于社会的中、上层。”(12) 20世纪70 年代国际上出现的“有增长而没有发展”的观点就是针对拉美国家讲的。根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在70年代初,拉美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还极少,当时阿根廷等拉美10 个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已分别在0.44~0.66之间,其中20%最低收入家庭占总收入的比重,最低的只有1.6%,最高的也只有4.4%,而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最高的达58.7%,最低的也占35.2%。因此,拉美地区被称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当时拉美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40%。从那时以来的30多年间,大多数拉美国家经历了由人均GDP1000美元(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3000 美元的过渡,但社会的贫富分化状况却未见缩小,2003年拉美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到2.266亿,占总人口的44.4%(12)。拉美国家经过13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出现这样一种社会局面,是值得引起人们的警觉的。
七、政治现代化的曲折经历
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国家的经历似乎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政治稳定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这或许与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现代化直接相关。拉美国家在19世纪初期刚刚独立建国时,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政治精英确实想通过政治西化的道路,如引进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以法国和美国宪法为蓝本制订本国的宪法,等等,以期建立起强大的民主共和国。但是,这种移植过来的民主制度却在拉美遭遇到“水土不服”的尴尬,不但没有带来“大治”,反而引起“大乱”。各国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动乱之中。19世纪中期以后,拉美国家陆续涌现出一批独裁政权,既有像阿根廷、智利等国由传统的土地贵族和出口商联合建立的寡头政权,也有像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那样的考迪罗个人独裁政权。这些政权对内起着维护稳定与秩序的作用,对外充当外国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人,从而为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创造了基本条件,迎来了1870~1930年拉美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可见,在建国后头100年左右(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历史上,拉美国家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它的第一个发展周期,一个由“乱”到“治”、由“民主”到“独裁”的周期。
拉美国家经历的第二个政治周期大致以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为起点至70年代末期结束,总共60年左右,与拉美第二次现代化浪潮(1930~1982)大体同步。墨西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映出墨西哥经过第一阶段的现代化发展阶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城市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的力量明显壮大,并发动了争取民主的斗争,推翻了统治墨西哥长达34年的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政权,建立了拉美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众主义政权。在其他拉美国家虽然没有发生类似墨西哥的革命,但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冲击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政治危机,导致了政权的更迭。在这个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在拉美涌现出以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政权、巴西的瓦加斯政权和阿根廷的庇隆政权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众主义政权。这些政权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众主义、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所谓民众主义(populismo)是学术界对这类政权的民众动员方式和政权组织方式的一种概括。这类政权往往都是在卡利斯玛(carismático)式的领袖人物(如瓦加斯、卡德纳斯、庇隆等)领导下,举起争取民主与社会正义的旗帜,把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广大工农民众广泛地动员起来,并通过工会、农会和其他行业组织(即所谓“职团主义”,corporativismo)形式将这些阶层吸纳到政党和政权结构中来。这些政权无一例外地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强调国家的独立、主权和自主发展。例如,庇隆主义就以“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作为三大旗帜。墨西哥于1917年制定了第一部革命民族主义的宪法;卡德纳斯政府于1938年将17家英、美资本控制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这些政权都把实现工业化提升为国家战略。“在30、40和50年代,工业化在拉丁美洲超越了部门的范畴,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项发展战略的重心。更有甚者,工业化成为许多社会运动的旗帜。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这些社会运动(如阿吉雷·塞尔达,卡德纳斯,德拉托雷,庇隆,瓦加斯)都反映了民众的现代化向往。”(14) 这些政权也无一例外地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作用。实际上,民众主义政权的出现反映出拉美国家实力相对弱小的资产阶级需要借助民众的力量来强化其政权的社会基础,以便能够主导本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基于拉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民众主义政治制度只出现在一部分国家,其他国家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基本上形成一种民选的文人政权与军人独裁政权轮番交替的局面,其中尼加拉瓜、海地、巴拉圭等国更出现由某个家族或个人长达数十年的专制独裁统治。从50年代末期起,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拉美地区出现一股强烈的革命与变革潮流,对各国右翼保守势力形成巨大的冲击。作为对这股变革潮流的防范和反击,60年代初,厄瓜多尔(1963)、巴西(1964)、玻利维亚(1964)等国相继发生军人政变,从此,军事政变之风几乎席卷整个拉美大陆。到1976年阿根廷军队推翻第三届庇隆政府为止,拉美依然由民选的文人政府当权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这一批新出现的军人政府在政治上无一例外都是独裁专制的,如解散议会、取缔政党、禁止罢工,等等,有些国家的军政府在镇压左翼力量方面的残酷程度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批军政府有一个不同以往的特点,即普遍强调发展经济。它们在通过强力统治实现国内稳定的同时,启用部分文人专家治理经济,强调积累,限制收入分配,主动利用外资,发展外贸。巴西在军政府时期出现了1968—1973年的“经济奇迹”。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军政府于70年代启动了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20世纪初期民众主义在拉美的出现似乎为政治民主化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民众主义影响的范围相对有限,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到60年代又被军事独裁统治在谋求稳定的名义下所取代。
拉美国家第三个政治周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政治民主化”浪潮。这次民主化浪潮固然受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恢复民主和美国卡特政府推行人权外交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拉美国家内部。其一,拉美国家的军政权对左翼力量的残酷镇压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抗,而且在国际上造成了严重侵犯人权的恶劣形象。其二,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拉美国家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各国政府采取大量举借外债的办法虽然暂时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正在日益迫近。军队交出政权,返回兵营,成为挽救军队自身和避免一场政治与经济双重危机的出路。从1978年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主动将部分权力交还给文人政府开始,各国军政府通过多种形式向民选的文人政府交权的过程延续了10多年。到1990年智利军政府交权为止,拉丁美洲已经成了“一片民主的大陆”,民主化进程进入了巩固与完善的阶段。不过,广大民众对民主政治的热切期望很快就被失望所取代。先是80年代的债务危机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大量增加,社会贫困化程度空前加剧。进入90年代以后,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宏观经济剧烈波动,银行与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大批企业倒闭或被私有化,失业率创历史新高,社会贫困化程度有增无减。随着民众不满和反抗的增加,许多国家的政局日益动荡。自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4 个国家的7位总统在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下台;阿根廷在2001年底爆发经济危机时, 两周内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对18 个拉美国家的调查,有56.3%的民众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更重要;有54.7%的民众认为,如果一个专制政府能够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将支持专制政府(15)。可以说,在拉丁美洲,“民主”与“市场”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八、结束语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整体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在本文中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论述也只是一种初步的探讨,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研究和讨论。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想就两个问题谈一点看法。第一,关于在现代化研究中如何运用指标体系的问题。运用某种指标体系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展加以衡量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我们在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时发现,如果过分依赖于指标体系去判断问题,很可能会使研究工作陷入某种误区。例如,整个拉美地区1999年的经济(GDP)结构为:农业占8%,工业占32%,服务业占60%。其中部分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比地区平均值更高。如果据此就判断多数拉美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了以服务业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那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拉美地区人均GDP已超过3800美元,其中阿根廷已超过7000美元,但是,这个平均数掩盖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拉美的城市化率已接近于发达国家,但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容忽视,如此等等。第二,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问题。我们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总结了不少关于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现代化进程是有益的。但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国情等背景下进行的,从这些进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即便是客观、严谨的,也不可能为当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现成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认真去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对拉美国家发展进程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照搬照抄外来模式是不会成功的。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应当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
收稿日期:2006—01—20
注释:
① 郭克莎:《人均GDP 1000美元后的长期发展进程——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及其启示》,《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
② 科林·M.刘易斯:《1930年以前的拉丁美洲工业》,载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第318~320页。
③ 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文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第227页。
④ Ricardo M.Ortiz,Historia económica de la Argentina.Editorial Plus Ultra,4a edición,Buenos Aires,1974,pp.553—554p.576.
⑤ Caio prado Junior,Historia económica del Brasil.Editorial Futuro,Buenos Aires,1960,pp.296—298.
⑥ 维克多·布尔默-托马斯:《拉丁美洲经济(1929~1939年)》, 载《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第六卷(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第73页。
⑦ Aníbal Quijano,El laberinto de América Latina:Hay otra salida? en Tareas,N°116,Panamá,enero-abril 2004,p.63.
⑧ CEPAL,Las transformaciones rurales en América Latina:Desarrollo social o marginación? Santiago de Chile,1979.p.57.
⑨ Rosemary Thorp,Progreso,pobreza y exclusiòn:Una historia económica de América Latina en el siglo XX,BID y Unión Europea,1998,p.167.
⑩ Gonzalo Martner(coordinador),América Latina hacia el 2000,opciones y estrategias,Editorial Nueva Sociedad,Caracas,1986,p.40.
(11) 奥·德奥利韦拉、 布·罗伯茨:《拉丁美洲的城市扩展和城市社会结构(1930~1990)》,载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第六卷(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第265页。
(12) CEPAL,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nos 80,Santiago de Chile,1979,p.90.
(13) CEPAL,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2002~2003,p.7.
(14) Fernando Fanjnzylber,La industrialización trunca de América Latina,Editorial Nueva Imagen,México-Caracas-Buenos Aires,1983,p.149.
(15) UNDP,Ideas y Aportes:La Democracia en América Latina:Hacia una democracia de ciudadanos y ciudadanas,Nueva York,abeil de 2004.WW彭书贵XXCK
[1]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中译本第四卷)[D].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2]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中译本第六卷上)[D].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 CEPAL,25 anos en la agricultura de América Latina:Rasgos principales,1950~1975,Santiago de Chile,1978.
[5] CEPAL,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nos 80,Santiago de Chile,1979.
[6] Fernando Fajnzylber,La industrialización trunca de América Latina,editorial Nueva Imagen,Méxuco-Ca-racas-Buenos Aires,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