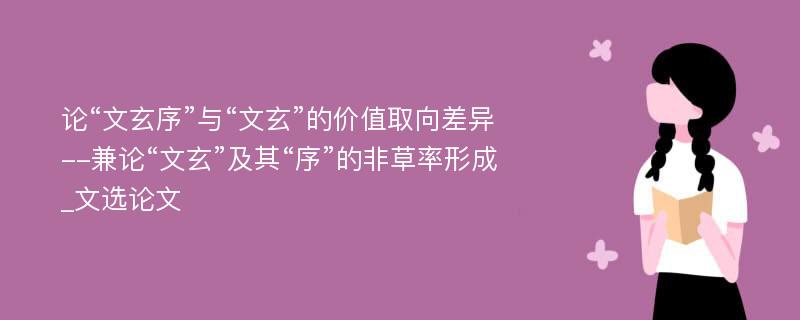
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兼论《文选》非仓卒而成及其《序》非出自异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仓卒论文,而成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理论上说,编者自序其所编的书,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应是不存在任何差异(矛盾)的。而实际上,当“序”与其所序者取之角度或范围不同时,差异便随之出现。了解了这一点,《文选序》与《文选》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若干差异,就不难理解了。其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是最近之事,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文选》出于众人之手说与“蜡鹅事件”对《文选》的编撰产生极大的影响说而来。因之,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文选序》与《文选》何以存在着价值取向之不同,而且,其与《文选》之编者问题及“蜡鹅事件”对《文选》编撰是否有影响,影响如何等,均有很大的关系,故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
一
就文体而言,《文选序》论及的有赋、骚、诗、颂、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38种(注: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李注胡刻本)。),而《文选》则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39体选录诗文(注:参拙文《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失序”与“彼此失照”问题》。(将刊)关于《文选》文体的分类,时下主要的还是三十七类与三十八类两说(笔者发表于1999年初的《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一文,亦用三十八类说)。另外,“在1993年4月17日于台湾成功大学召开的‘第二届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选之难体》乙文,提出《文选》分体三十九类之说”(《文选综合学》注释[7]的游志诚先生,在2000年8月于长春师范学院召开的“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文选综合学》一文又创新说,其云:“其实,《文选》体类实不止三十九。明清所见《文选》俗本有于‘哀策文’析分‘哀文’‘策文’二体者。曩昔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述六朝文体分类说时,已采用之。……惜乎未参之王应麟《玉海》所载《中兴书目》之《文选》资料,致不分檄难为一类。今若信王伯厚所见,则《文选》之分体实应当有四十类。而不是旧说之三十七、三十八,与吾所创之三十九。”(《〈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546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我们认为,四十类说是难以成立的。不过,这不影响我们的讨论,故此不赘。)。显然,两者不论涉及的文体之类还是文体之名,均不尽相同:一、《序》所提及之戒、诰、记、誓、悲、碣、三言、八字、篇、引10体,出《文选》之域外(注:近故的屈守元先生《萧统〈文选序〉章句》释“次则箴兴于补阙……碑碣志状”云:“以上箴、戒……记……篇……引、碑、碣、志、状各类杂文。《文选》各体皆具”(《文选导读》第158-159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屈氏乃当代“选学”名家,熟精《文选》,而有是言。事实上,《文选》并不立此中之“戒”“记”“篇”“引”“碣”五体。又,屈公仅据“日本所传古抄卷子本《文选》,萧统的《文选序》有旁注说:‘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便云:“这条旁注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即萧统的著名古代文论经典著作《文选序》,也出于刘孝绰的代笔。”(同上,第29页)是亦略失慎重。);二、《文选》设置之册、上书、启、弹事、移、难、对问、连珠8类,《序》则撇开不提;三、有些文体,如《序》之“答客”、“指事”与《文选》之“七”、“设论”等,两者提法有异(注: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文选序》注释[20]云:“‘答客’,指假借答复别人问难,用以抒写情怀的一种文体。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高步瀛云:“吕延济曰:‘……指事,《解嘲》之类。’曾钊曰:‘指事,盖七类,如《七发》说七事,以发太子是也。’……曾说是。”(《文选李注义疏》第2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今按:曾钊说是;而今人赵福海说此“即《文选》中的‘七’体”(《昭明文选研读》第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尤可谓善断。)。此外,《南史·梁武帝诸子列传》载“蜡鹅”事发,帝“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注:李延寿《南史》第131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唐代以还有人说过刘孝绰等参编《文选》(注:如人们所熟知的《文镜秘府论·南集·集论》引“或曰”之“……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宋王应麟《玉海》卷54“梁昭明太子《文选》唐李善注《文选》……”条引《中兴书目》之“《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所著赋、诗……志、行状等为三十卷”,而文末有双行小字云“与何逊、刘孝绰等撰集”(《四库全书》本)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动摇不了《文选》为昭明太子萧统独撰之说(参拙文《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这就很自然地给人们那么两种强烈的印象:《文选》或“仓促成书”,或与《序》所出不同。由此,便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两种相应的新说。前者如俞绍初先生认为,“由于成书仓卒,就不可避免地使《文选》留下一些草率的痕迹”:
目录中所标举的各类文体与《文选序》所叙列的不完全相符,有《序》提及而为目录所无,也有目录中有而为《序》所未提的。这大概因为《序》撰写在先,而编集在其后,又由于匆促间来不及据实际所收去修订序文,或者据序文来调整作品,因而出现彼此失照情况。(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与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第7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略后,王晓东先生承俞先生说而为《〈文选〉系仓促成书说》一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第一个依据就是《文选序》与《文选》之不相合问题(注:俞先生所说的另两端是:“作品的篇题及编次间有错误”,“所收普通间的作家作品未能全、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成就”(《文选学新论》第74页)。这些,王晓东先生在其《(文选)系仓促成书说》(《文选学新论》)一文中均作了发挥。不过,笔者仍认为《文选》非“仓促”而成,参《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失序”与“彼此失照”问题》(将刊)等拙文。)。后者如傅刚先生根据上述情况而云:“这似乎表明实际操作者刘孝绰在文体的选录上与萧统小有差异”(注: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萧统《文选序》所举文体与《文选》实际收录文体不符的现象,应该值得注意,考虑到刘孝绰协助萧统编撰的事实,这种不符可以理解为萧统大概只在确定指导思想,制定体例等方面总体把握了此书的编撰,实际上的操作或由刘孝绰执行”(注: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1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俞、傅二先生均为学殖深而笃实严谨之中古文学专家,故其说虽异,然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过尽管如此,是两说似均有所未照。
(一)“仓促成书”说难以成立
《文选序》云: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注: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李注胡刻本)。)
“今之所撰”、“今之所集”、“都为三十卷”、“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云云,显然是编集在先,而《序》撰写在其后。因为编集成,才有“所撰”如何,“所集”如何,“都为三十卷”之说。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昭明太子〈文选序〉考》云:“通常,序文是在编著完成以后概括作品编著的动机、目的、方针以及内容和构成等附载于卷首或卷末。……在六朝末梁代编辑的《文选》的序文也是同样情形,是在《文选》的编辑完成以后,由其代表人物昭明太子概括说明编辑的动机、目的,以及采录作品的方针、编排等而置于卷首”(注:清水凯夫《六朝文学论文集》第47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文选》的序文”,写“在《文选》的编辑完成以后”说,是符合实际的。总之,“《序》撰写在先,而编集在其后”之推测是难以成立的。准此,“成书仓卒”说,便失去了全部的依托(参后)。此其一。其二,既然《文选序》写在《文选》编集完成之后,“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云云,便不仅说明了《文选》显非“成书仓卒”,同时又极为有力地证明:“蜡鹅事件”对昭明太子编撰《文选》没有影响,至少没有大的影响。因之,《文选序》与《文选》之矛盾,并非“仓促成书”所致。
(二)《文选序》与《文选》存在之不合,非由异出所致。
既然萧统能总体把握《文选》之编撰,刘孝绰“实际操作”或“执行”中果真出现了“偏差”,其便不可能听之任之。纵使刘孝绰不改,昭明亦会“正”之。除非“总体把握了此书的编撰”之萧统连已编成的《文选》稿目也不得看或不能看,然这是不可能的。就前者言,只是“实际操作”者的刘孝绰怎能不将“编好”的《文选》“目录”先呈给作为“总体把握”者的皇太子萧统审定呢?就后者言,“总体把握”者既然有时间为《文选》写序,便不至于连看其“目录”之闲也没有。我们知道:《文选》与其他的专著不同,仅看其分量小小的目录部分,便可知其是否与原定的“指导思想”与“体例”出现“偏差”。万一出现了“偏差”,处理起来亦易如反掌,不象其他的专著与原定的“指导思想”与“体例”出现“偏差”而要纠正那样,时或牵一发而动全身。况且,萧统在《文选序》中明白地说自己“居多暇日”。反之,如果刘孝绰在“实际操作”中果真出现那么多的“不合”,他还是萧统最信任的人吗?而这些“偏差”如果在萧统看来不是问题,我们便无从证明其必由异手所致。准此,“刘孝绰协助萧统编撰的事实”云云,便失去了一根“支柱”。此其一。其二,据刘孝绰今存诗文,其有明确之文学主张者,仅见于《昭明太子集序》,尤其是其中之“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云云(注:萧统《梁昭明太子文集》卷首、卷3,四部丛刊本。)。而大致在刘孝绰写此序的同时,萧统写了《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俞绍初先生《昭明太子萧统年谱》(《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系于普通三年,即与孝绰的《昭明太子集序》同年。俞先生云:“智藏于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湘东王绎为制碑铭,则确知其时绎自会稽而还,已在京邑,盖闻昭明文集新成,欲兼《诗苑英华》求而观之,昭明作此书以答。”其说可从。),是书之“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俘。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注:萧统《梁昭明太子文集》卷首、卷3,四部丛刊本。)数语,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此时的文学思想。显而易见,两说若合符契。当然,据此还不足以证明刘孝绰与萧统的文学思想如出一辙。不过若非如此,便说明了刘孝绰在为萧统编集而写的序里,申述的是萧统的文学思想。如其《上虞乡亭观涛津渚学潘安仁河阳县诗》云:
昔余筮宾始,衣冠仕洛阳。……游谈侍名理,搦管创文章。引籍陪下膳,横经参上庠。……烹鲜徒可习,治民终未长。……离家复临水,眷然思故乡。……溯洄若无阻,谢病反清漳。(注: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第1830-183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这里的“余”,为刘孝绰所“扮演”的潘岳而非孝绰本人。既然刘孝绰的文学思想或与萧统如出一辙,或为萧统编集时趋同于萧统,故退一步说,刘孝绰真的是“协助萧统编撰”《文选》,《文选序》与《文选》间所存在的差异,亦难以断其因出“异手”所致。其三,《南齐书》卷52为《文学列传》,而其《传论》(即“史臣曰”)以“文章”代替“文学”,此其两者之异一也;《传》中所收的檀超、王逡之、王圭之、祖冲之、贾渊等,主要是史学家,而《传论》云:
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无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若陈思《代马》群章,玉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为争鹜……(注:萧子显《南齐书》第907-908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
显然,《传论》所论是从纯文学的角度说的;而《传》实际上是合史学于文学。此两者之异二也。然众所周知,整篇《文学列传》均出萧子显之手。根据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文选序》与《文选》之矛盾,亦非如傅先生所说那样,是“总体把握”者与“实际上的操作”者在“文体的选录上”“有差异”所致。
二
那么,出现这一矛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由于《文选序》是就《文选》而写,目的是阐明其关于“文”之演变与范围、选文标准等等,故其与《文选》之价值取向本是一致的。然如前所述,《序》与所序者之间因角度、范围等之不同,两者有所差异便是很自然之事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序》提及之戒、诰、记、誓、悲、碣、三言、八字、篇、引等10体,《文选》何以没有选录其作品?相反,《文选》设置之册、上书、启、弹事、移、难、对问、连珠等8类,《序》为何又不提及呢?
首先,《文选》乃“文之选”,而非入选者方得称“文”。今人赵福海先生《试论“文选理”》云:具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而《昭明文选》只选了一百三十家的七百五十五篇作品”(注:赵福海《〈昭明文选〉研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是甚启人思。《文选》之“类”是建立在“大文学观”的基础上的,故其自然欲尽“类”之所有;而“选”以“纯文学”为前提条件,故又自然无法囊括尽“文”之体。明此,我们便知道,从“体(类)”所显现之“文”的价值方面看,“戒、诰、记、誓、悲、碣、三言、八字、篇、引”与“册、上书、启、弹事、移、难、对问、连珠”是没有本质上之差别的。这些文体总的说来“文”不多,用不着细加论述。故其中某体若有作品入选,《序》便可略之;反之,若某体无作品得入选,则于《序》稍及之。此可谓相补相成,正是昭明之细密处。故我们说:这本来就不是问题。易言之,这既非关出于“仓卒”,又非因序与编撰出自异手。
其次,《序》云:“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而《文选》收宋玉赋4首,荀子赋却1首也不收。这本是说明《文选序》与《文选》间价值取向差异的佳例,而今竟成了一个问题。《文选》何以不收荀赋呢?有的学者从《文选》体例之角度考察,认为:“荀卿著作属于子书,限于体例,《文选》不收”(注:穆克宏《〈昭明文选〉研究》第1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因为《文选》不录‘子书’,所以不收‘荀卿赋’”(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与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第11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孤立地看,这是很有道理的。不过,由于《文选》体例本身有例外,而荀赋即在此中,故我们认为,是说又似未尽然。这一点,比观《文选》之收《毛诗序》、《过秦论》等,则思过半矣。又,傅刚先生云:“《汉书·艺文志》分明以荀卿赋置于《诗赋略》,作为四类赋之一,而萧统《文选序》也说:‘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后。’(之按:“后”,似当为“末”)明以荀卿为赋家,怎么说是子书呢?”(注: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2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们认为,这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萧统《文选序》所说,未必“明以荀卿为赋家”(参后)。《文选》以“文”选文,故乏采的荀赋自然落选。易言之,在萧统看来,荀赋虽具有“史”之重要意义,却不具备“文”之条件。惟其有“史”之重要意义,故《序》及之;而惟其不具备“文”之条件,故《文选》未选。退一步说,即使不收荀卿赋完全是“限于体例”,而《序》及之,同样说明两者的价值取向有所差异。请看另一例子,《文选序》云: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裁?(注: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李注胡刻本)。)
这表明《文选》不选“经”。然《文选序》释“诗”与“颂”时,却又分别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即《大雅·烝民》)、季子有‘至矣’之叹”(注: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李注胡刻本)。)。即正面提及了《诗经·周南》之《关雎》《麟之趾》与《大雅·烝民》。这说明在“选”中不能“加以剪裁”的“经”,在“序”中从史的角度阐述问题时可以提及其中的某些部分。此亦两者之异也。
不过,傅先生又云:
不录荀卿,也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萧统《文选序》明明说过“荀、宋表之于前”的话,这说明实际操作者与萧统还有不一致的地方。(注: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2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是则似有所未照。如前所述,《序》在这里是就赋之史说的,故不能不顾及最初以赋命文题之荀子与宋玉。而《文选》以“文”作为其选文之标准,故宋玉赋之得入与荀卿赋之落选,全由他们作品文采之多寡来定,非关他也。概言之,《文选序》提及荀卿与《文选》不收荀卿赋,是说明不了“实际操作者与萧统还有不一致的地方”的。同一人所为而因角度不同而不同的例子,不知凡几。如《诗品序》和《诗品》皆钟嵘所作,而两者亦多有差异者。《诗品》分别置曹操、曹丕于“下品”与“中品”,入曹植、刘桢与王粲于“上品”;“三张、二陆、两潘”中仅张协、陆机与潘岳入“上品”,余者或入“中品”、“下品”,甚至如张亢不得入“品”(注:“三张”,清人张锡瑜《钟记室诗平》曰:“‘三张’本谓张载兄弟。……但亢诗无闻,品所不及。则此‘三张’,内当有茂先而无季阳。‘中品·鲍照’条以景阳、茂先并称‘二张’,可证。”按:张氏因没有注意到《诗品序》与《诗品》价值取向的差异,故有是说。实际上,此“三张”内当有季阳。);郭璞、刘琨、谢混三人,仅入“中品”等等。而《诗品序》在从史之角度论诗时却云: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注: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第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在这里,“三曹”中除后面以“为建安之杰”“殆文章之圣”称陈思,而说明其最杰出外,不看《诗品》,我们无以知其余两人谁在记室的眼里“品位”高些;而“羽翼”之于“文栋”,则显然是前者之“品位”低而后者高(实仅“文栋”中之“平原”与“羽翼”同品。)此其一。其二,《诗品序》没有提及的阮籍,却优入“上品”。其三,从“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说法中,没法分辨他们各自在《诗品》中“品”之高低;而仅看“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或以为太冲次彼三人一等,藩岳、张协又要低士衡一品。其四,“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谢益寿斐然继作”云云,这种评价,尤其是对前两者之评价至少不低于对公干、仲宣、安仁、景阳与太冲,特别是太冲之评价;其五,与仲宣同为“羽翼”与“辅”的公干,又与子建一起被推为“殆文章之圣”,而“太康之英”与“元嘉之雄”仅得“体贰”;等等。显而易见,《诗品序》与《诗品》存在之差异远比《文选序》与《文选》所存在之差异大。甚至《诗品序》本身前后之说法,也多有不协之处。据此可知,《文选序》提到荀子与《文选》不收荀赋这一做法,正说明了一人所为之两者,时或因体异而用异,却证明不了这两者必为不同之人所为。曹丕《典论·论文》云“……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不知学者们从其“异者”而观之,有何感想。
三
关于某些文体,《序》与《文选》的提法有差异之问题。王晓东先生云:
个别文体,《文选序》和《文选》的提法不同,如《文选》中的“史论”,《序》中称“赞论”;“序论”,《序》中称“序述”等。(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与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第7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王先生以此作为其《文选》“仓促成书”说的主要理由之一。乍一看,这似乎很有道理,然进一步研讨,我们认为是说亦未为圆照。首先,《文选》之“史论”类共收班孟坚《公孙弘传赞》、干令升《晋记·论晋武帝革命》和《晋记·总论》、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宦者传论》和《逸民传论》与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倖传论》9文。其中8篇“论”,只有1篇“赞”,而《汉书》之“赞”与其后史书之“论”,实质上都是论体。《文选》之称“史论”,盖以此也,即据其性质命“类”。《序》中称“赞论”,则就“选”之角度说史书之部分。其所以如此,盖因此前已说过“史”(“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而《文选》之“史述赞”类,收班孟坚《述高纪第一》《述成纪第十》《述韩英彭卢吴传第四》与范蔚宗《后汉书·光武纪赞》,据同样的理由可知,“序述”即“史序述”之省称。因之,“序述”之于“史述赞”与“赞论”之于“史论”同。《文选》之“史述赞”以“史”之“述”与“赞”合为一类,而《序》的“序述”说明“序”之“述”有可录者。其次,由于“赞论”“序述”合起来,指史书可录之范围,故其实际上指“赞”“论”“述(序之述)”三者。可见,“个别文体”“提法不同”非关“仓促成书”,而是《文选序》与《文选》因角度不同所造成之取向差异(是非问题另当别论)。
况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序》之“赞论”与“序述”只是指史传之部分,而不是被作为文体来看。因之,其并非真的与《文选》之“史论”“序述”提法存有差异。另外,由于序文本身具有随意性,故其“先天”地与“选”之“认真”存在着某些差异。如《文选·赋》的“京都”类收《西京赋》与“田猎”类收《上林赋》,《序》则分别以“凭虚”与“亡是”说之;《文选·诗》的“杂诗”类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序》却作“降将著‘河梁’之篇”(注: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李注胡刻本)。);等等(注:在这里,“凭虚”“亡是”,是用作品中的主人公代该作品;“在邹”“河梁”(此不讨论“李陵诗”的真伪问题),则是用创作地点代作品之称。正因为“随便”,故其点到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与《诗经·国风·周南》的《关雎》《麟趾》(《麟之趾》)时,又用原题。)。此其一。其二,《序》与《文选》关于某些文体提法之差异中,几乎都是有前提的。如上面所举例子,便可作为佐证。如《文选》有“设论”一类,而《序》称为“答客”。在这里,“设论”为类之共同点,“答客”为该类文章之祖篇《答客难》的省称;而作为文体名,不管是“设论”还是“答客”,其时还未取得如“诗”“赋”“颂”等文体那样的规定性。其实,类似“提法不同”的情况不知凡几。试以《文心雕龙》为例,其既于《辨骚》中以《楚辞》为独立之一体而以“骚”名之,又分别于《明诗》中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即以《离骚》为“诗”),于《祝盟》中云“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即以《招魂》为“祝”);李斯《上书秦始皇》(用《文选》所名,下同),《文心雕龙》之《论说》云“李斯之止逐客”,而《才略》云“李斯自奏丽而动”(“止逐客”与“自奏”,均指《上书秦始皇》;潘勖《册魏公九锡文》,《文心雕龙》之《诏策》云“潘勖《九锡》”、《风骨》云“潘勖《锡魏》”、《才略》云“潘勖……绝群于《锡命》”;《吕氏春秋》,《文心雕龙》之《史传》云“故取式《吕览》”、《诸子》云“取乎《吕氏》之《纪》”、《论说》云“不韦《春秋》”(注: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范文澜注本)。)等等。这里,所举的虽多以篇名为例,却可以证文体之体名或类名。
《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还表现于这一“矛盾”中:《选》入“凭虚”(《西京赋》)于“京都”,入‘亡是’(《上林赋》)于“田猎”,而《序》则云:“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高步瀛先生注《文选序》引清人张杓语云:“《子虚》《上林》二赋,昭明列“田猎”类,而《序》云‘述邑居’者,以上篇述‘云梦’,下篇述‘上林’,皆言苑囿也。”(注: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上)第1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亦说明了这一点。至于《文选》所录的某些作品与《文选序》所说的选录标准不相侔或有所不协的问题,那主要是实践与理论(理想)之差异所致。因篇幅关系,这一点得待另文,此不赘。
综上所述,可知《文选序》与《文选》间所存在之种种不合,主要是由于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的差异所致。其次,这跟实践与理论之“天然”差异亦有关。当然,这些不合,从“仓促成书”与《文选》出于众手之角度考察本是合情合理的,然就前者言,由于《文选》之“失序”多出在其前面部分,并且,萧统在其完成《文选》之编撰后所写的《文选序》中明白地说自己“居多暇日”,故此说实际上是无以成立的。而就后者言,因为萧统“居多暇日”与刘孝绰代萧统编撰其文集所作之序表现出的文学思想与萧统其时的文学思想完全一致,故退一步说,即使“刘孝绰协助萧统编撰”《文选》之说是事实,“这种不符可以理解为萧统大概只在确定指导思想,制定体例等方面总体把握了此书的编撰,实际上的操作或由刘孝绰执行”云云,最终同样也是无法成立的。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再举一个例子:清人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序目》之“序跋类”中云:
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百,序之最工者也。(注: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而实际上,《古文辞类纂》除录司马迁《史记》6篇表序(注: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序》与《五代史·职方考序》外,还录了欧阳修《五代史》的《一行传序》《宦者传论》《伶官传序》(注: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及班固《记秦始皇本纪后》《汉诸侯王表序》(注: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据此可知,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卷6及卷8所录之方与其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之“序跋类”小序中说之不符,实远出《文选序》与《文选》间所存在不符之“右”。然我们知道,《古文辞类纂》虽姚鼐以一己之力而花仅一年多的时间纂成,然在此后的30多年中,他“非有疾病,未尝不订此书”(注: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此其一。其二,姚氏于此书初纂成后所用的工夫,主要的是在文字的审订、文章的评注与圈点方面,而文章的编目更改很少。即过了30多年,他几乎还完全认可自己当初仅用一年多时间纂成的那本《古文辞类纂》。故就姚氏纂此书而言,一年多的时间不算仓促:这与30多年的时间几无差别。于此,我们希望持《文选》出于“众手”说的学者们,能充分的注意到这一点。
标签:文选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诗品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