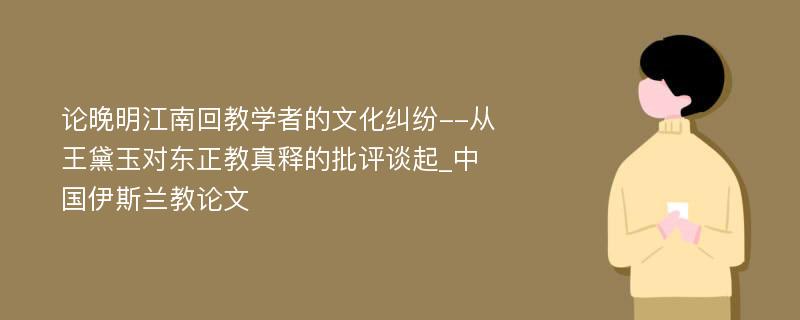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正教论文,江南论文,纷争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末清初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蓬勃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开始出现了汉文伊斯兰教著述,这新出现的一批著述或译或编或著,表达了中国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们对周围文化的态度。这一时期,汉文伊斯兰教学术的发展尤以江南地区的南京、苏州为中心, 而明末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师、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和张中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二人各自留下了数部汉文伊斯兰教作品,王岱舆的作品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等,张中的作品有《克里默解》、《归真总义》、《四篇要道》等。于是在对晚明江南伊斯兰教界的研究中,学者便把目光集中到了王岱舆和张中身上,除了清代前期的又一位江南伊斯兰教学者刘智之外,可以说王岱舆和张中是获得最多声誉的两位江南伊斯兰教学者,他们的学说也为后代所继承。但是这两位著名的学者有没有学术上的交流?他们在学术上有没有讨论甚至争论?如果有讨论或者争论,那么讨论、争论的是什么?他们的讨论和争论对中国回回伊斯兰教思想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对于这些新的思想体系发展初期非常重大的问题,目前的学术研究尚未关注。本文从王岱舆所撰《正教真诠》中批评的一部汉文伊斯兰教典籍《证主默解》说起,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试图较完整地认识晚明江南伊斯兰教学术的状况。
一、《正教真诠》对其他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批评
在王岱舆写作汉文伊斯兰教著作之前,便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以汉文写作或翻译的伊斯兰教宗教著述,因为在王岱舆所撰《正教真诠》中就明确地提到了他所见到的两部汉文伊斯兰教译著。
《正教真诠》成书于明末崇祯年间,通行的版本有两种,一为嘉庆六年(1801年)广州清真堂刊本,后来的镇江清真堂本据之,另一为1931年中华书局刊本,两本差别很大。前者内容较后者为多,特别是还保留了多篇序跋文字,198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振贵先生点校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合刊本,收入了《正教真诠》的这两个通行版本,颇便利用。
《正教真诠》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40篇,有的在于宣教,有的专事批评,可谓是有立有破,梁以浚《〈正教真诠〉叙》所谓“或有以辩难而成,或有以明理而作”[1](p.4),正指此。《正教真诠》的破是针对当时教内外的现实的。
其中有“易真”一篇,专以辟教内之“异端”为务,开篇曰:
所谓易真者,若播糠眯目,皂白不分,上下四方,自然易位。兹缘吾道之异端,外托正教之名,而内演空玄之理,以讹易正,泾渭不分,合同异随人之所欲,统众理诸教为一家。但灼见真知者少,以耳为见者多。若门外汉目之,则愈染愈深,迷不可治,良可悲也。或有粗知汉学而稍习经旨者,间亦注书于世,无非肤语浅训,不过修身而已;或有两不相通,惟以道听途说,妄自纂而成编者,若《省迷真原》是也。观之莫不窃笑;作者竟不知耻,岂不有辱清真之至道哉!然浅近者无害于浅,但得其正,何妨其妄作者,一览便知,犹不足论,譬如云掩日光,倾之自散,何害于明;惟恐精于文翰,而鲜知经义者,纵然资性明达,惜乎未经正指,遂以异端之学,搅乱清真,虽然似是而非,但其巧媚能夺人之心志,此清真之最恶,正人之深忌者也,若《证主默解》是也。[1](pp.43—44)
王岱舆在这里将他所要批评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译作分成了三种类型。
白寿彝先生早就注意到王岱舆的这段论述,在1947年他所撰《中国伊斯兰经师传·王岱舆传》中(注:他为《回族人物志》所作的《王岱舆传》系因袭原未刊布的《中国伊斯兰经师传》而来。),根据王岱舆的书和其他著述考证道:“(王)岱舆以前,已有关于伊斯兰的汉文书。”[3](p.447)他还指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伊斯兰教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解答。同时,穆斯林中也有一些人读了一些汉文书籍,而不懂得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但想懂得伊斯兰教义。于是,关于阐述伊斯兰教义的汉文著作和翻译就成为必要的了。在明末清初,王岱舆和张中是这种新学风的倡导者,而岱舆的著作刊行更早。”[3](pp.446—447)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一股用汉文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阐述的潮流。虽然王岱舆和张中的著译不是最早的,但大浪淘沙,他们的作品作为精华留存了下来。
不过在这个潮流中被王岱舆批评的三类著译的详细情况却很少被人谈起,甚至被王岱舆认为危害最大的第三类著译的代表《证主默解》的作者也不清楚,以至于长久以来关于明清时期汉文伊斯兰教译著运动的研究,往往从王岱舆开始谈起。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了解当时各种汉文伊斯兰教著译的情况呢?进一步的了解对深入认识中国回回伊斯兰教早期思想史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对于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的进一步研究为我们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二、《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张中所撰《克里默解》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介绍了三类他认为应予反对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后接着说:“且试举数端,以证其谬。”[2](p.44)随后他又具体地一条条引述要反驳的言辞,再作出批驳。这显然是针对第三类著述而言的,因为一、二两类在他看来并不值得一驳,“以证其谬”之“其”以第三类著述的代表《证主默解》最合适担当。
为了反驳,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节引了《证主默解》一书的部分内容,从而使我们可以看到《证主默解》的某些内容。
广州清真堂本《正教真诠》在“且试举数端,以证其谬”一语之后引述了要反驳的《正主默解》的数条言辞:
万殊一本,彼此不分,岂特人类而已,虽鸟兽昆虫,莫不与造物一体,略无差别。[2](p.44)(注:余振贵点校广州清真堂刊本《正教真诠》认为“万殊一本”四字是《证主默解》所云,其后“彼此不分,岂特人类而已,虽鸟兽昆虫,莫不与造物一体,略无差别”数字是王岱舆的话,但细读原文,我以为这段文字当同属《证主默解》所云,其后“非迷乱之至,孰敢如是哉!”才是王岱舆的话。)
万事万物,即若以金造器,体质本金,惟名相不同。但名相有时败坏。到得冰消泡散之时,依原成水,绝无彼此对待。[2](p.44)(注:中华书局本的引文为:“万殊一本,彼此不分,虽鸟兽昆虫,莫不与造物一体。譬如以金造器,体质本金,惟名相不同,及至名相销亡,依然是金。”显然把广州清真堂本中分作两处的引文合成为一处了,但主旨相同,文辞也多有相同之处。)
眼耳是我,观听是主。[2](p.45)(注:中华书局本完全相同。)
但一有了我这名相,便有个主仆之分。[2](p.45)(注:其原文为:“彼常与知己言:‘我至圣,乃主宰显化,开示迷人,普济万世。’故云:‘但一有了我这名相,便有个主仆之分。’即此义也。”这段引文前面所引述的是《证主默解》的作者常说的话,后面才是《证主默解》中的话。中华书局本几乎完全相同。)
主宰备有万物之性,为万物根本,为万物大父。无主宰则无万物,物自主宰而生,主宰不从万物而出。[2](pp.45—46)(注:中华书局本完全相同。)
如此,可见广州清真堂本《正教真诠》引《证主默解》共有五处。但在谈及明末清初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译时,学者并不重视《证主默解》一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此书受到了王岱舆的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可能是把这部书和王岱舆同时批评的《省迷真原》一书都当作已经散佚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注:《回族人物志》所附“回回人著述传知见目录”未列此两书,或因著者不详。又,我以为《省迷真原》一书也未佚,当另文专考。)而更重要的是,无人因王岱舆所引来进一步看看《证主默解》一书的内容。
那么《证主默解》是否真的散佚了呢?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而它的作者很可能就是张中。
明末清初的著名经师张中的著作中《归真总义》和《四篇要道》两书流传较广,而他的《克里默解》的流传则大不如前两书广,白寿彝先生早年曾以为张中有一部有关克里默的著作,但书已佚,[3](p.444)后来他又说到此书流传较少。[4](p.924)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 《克里默解》重新被发现,《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2期报道了此事,并完整地刊布了全书的内容。此书是青海西宁的一位“多斯提”马国良寄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据介绍,“被再发现的这部珍贵史料,是手抄的‘重录’本,字迹挺拔秀丽,而非刻版原书(原书是否刻版,尚无从根据),是咸丰十年(1860年)根据嘉庆十九年(1814年)洮阳(甘肃临潭)马天庆抄本重录的。重录者未留下姓名。”书中所包括的《克里默解》本文和介绍文字又为《回族人物志》全文转录。[4](pp.1077—1088)此书前有崇祯四年(1631年)春正月望日穆景修撰《序》,后有崇祯四年(1631年)中秋学圃生撰《跋》,正文分为上、下两卷,但内容并不多,只有数页。
经仔细阅读,可以发现王岱舆所引述并批评的《证主默解》的内容有一半可以在《克里默解》中见到,试以广州清真堂本《正教真诠》所引《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作一比较:《正教真诠》所引《证主默解》曰:“万事万物,即若以金造器,体质本金,惟名相不同。但名相有时败坏。得到冰消泡散之时,依原成水,绝无彼此对待。”《克里默解》相关文句为:“譬如水中显的冰泡,以水为体,了不离水,到了冰消泡散时,依原是水,决无彼此对待也。”[5](p.1084)“譬如以金造器,体质本金,只是名相不同。但名相有时败坏(原作怀,误)。”[5](p.1085)可见,《正教真诠》所引《证主默解》系综合《克里默解》两处文句而来。再如《正教真诠》所引《证主默解》曰:“但一有了我这名相,便有个主仆之分。”《克里默解》相关文句为:“真主原是止一无二的,但一有了我这名相,便有个主仆之分。”[5](p.1087)《正教真诠》所引《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完全相同。
这样的相似性说明,《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很可能是一书。此外,《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的书名也是非常接近的。克里默为阿拉伯文kalima的音译,复数形式为kalimāt,原意是“说出的话”,也可以引申为“对话”、“诗”的意思;在《古兰经》中常常出现kalima或kalimāt这两个词汇,通常的含义是Word of God。[6](pp.508—509)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辞典》说“克里默解”是“克里默舍哈德题”经的译释,意为穆斯林表白信仰的作证词。[7](p.122)书名《克里默解》以表音的“克里默”为主,《证主默解》一名则是表意的。同样的书名取法还见于张中的《归真总义》又称《以麻呢解》。至于还有不见于《克里默解》的三句引语,则有可能是在文献流传的过程中《克里默解》的文字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也有可能《正教真诠》所引杂入了其他书的内容。但我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较大。现存的《克里默解》的下卷似乎内容并不太连贯。穆景修撰《序》中说:“主且可证,何况圣人?犹然拘牵我相,谓:‘圣凡不同,凡难希圣。’试读‘足同履、目同视、口同味、耳同听’诸语,而圣奚异凡乎?”[8](p.1080)似乎“足同履、目同视、口同味、耳同听”数语应即是谈主可证、谈圣同凡的《克里默解》中的话,但实际上《克里默解》并无如此数语,但其中有“我之眼、耳、口鼻、四肢,既与圣人一般”[5](p.1086)这样的话。这很让我疑心以上用于和《正教真诠》所引《证主默解》比较的现在所知的唯一存世的《克里默解》是一节本。
如果上考可信,那么也可见《正教真诠》的广州清真堂本是比中华书局本更接近它的原貌了。以上所考,也为确定《正教真诠》的写作时间下限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即《正教真诠》的成书当在《克里默解》成书之后,即大约在崇祯四年(1631年)之后。
三、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分歧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经师传》以及《回族人物志》中就王岱舆、张中和伍遵契这三位明末清初的江南伊斯兰教学者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作了个比较:“王岱舆、张中和伍遵契,在译著上所走的路数,显然不同。王岱舆是自有看法,自立间架;张中是就着原书的材料, 原来的间架,而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伍遵契在译述之外,不肯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三位经学家的学风,可以说是大不相同的。”[3](p.445)[4](p.925)
如果上面对于王岱舆《正教真诠》中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的考证大致不误的话,还可见王岱舆和张中之间在译作和著作的“路数”上,除了“间架”即著述方式的不同之外,还有更深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可以从他们两人的著作中更多地看出。
王岱舆素有“四教博通,诸家毕览”[1](p.4)之誉,“四教”即是指伊斯兰教、儒家、佛教、道教四家的学说,但他在《正教真诠》中表现出鲜明的斗争意识,将批评矛头一是对着教内那些“曲解”、“误解”伊斯兰教的学说,另一是对着教外的不如伊斯兰教高明的学说。《正教真诠》“易真”一篇是专门针对教内的那些不明真理的言论的,如前所述;“昧真”一篇是反驳佛教的;“似真”、“性命”二篇有批评理学家言之处;“迥异”一篇还归纳了伊斯兰教不同于其他学说的七个方面。
《正教真诠》专门针对理学发言的“似真”篇的主旨,是说“理”也是真主创造的,不可以真主创造之物为天地万物的根本。在“迥异”篇中王岱舆摘引了《性理大全》中的三处言论进行分析,以说明伊斯兰教与之不同之处。在“性命”篇中王岱舆批评了儒家的性命之说,主要是二程的用理性、气性之分的理论来解释善恶的说法,这缘于他看到作为理学大原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得不透彻。而“昧真”篇的写作大略是总述、分论、总述的模式,在分论部分摘引了六段言论,第三至第六段出自佛典。从“似真”、“昧真”这样的篇名看,王岱舆对佛教的否定程度要甚于儒学。
但是张中不仅没有表现出王岱舆那样的批评,还恰恰处处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以为宣说伊斯兰教之助。张中,字时中,或谓又字君时,[4](p.920)他的名与字,出自《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9](p.19)这样的取名,表现出张中或他家庭的文化倾向。张中的写作口吻或近于理学家语,或近于佛家语,较少使用音译词汇,使用音译词汇时大多还会附上汉文的意译。姑举例看看所谓近于理学家语和近于佛家语。
《克里默解》上卷卷末有这样的一段话:
吾人既证得万物原无,惟有真主,又须要晓得“我自己”也是一物,这个关头不通,便不得归真,反为归罪了。若识破这个窍妙,即当将此躯壳放在主的要为中,下一段苦死工夫,毕境(竟)造到干干净净、光光明明“我无”归真的田地,这才是完完全全一个道理,才到得“止一无伴”。[5](p.1085)
这里的“关头不通”和“下一段苦死工夫”,何似宋明理学家语。
而《归真总义》的《标题译解》开篇的一段话:
“以麻呢穆直默勒”是本经之名,此云“归真总义”,乃吾圣人总万法而归一真之妙谛也。经文共四句,其间顿渐错综、天人互发,苟非明眼人,其孰能辨之。若夫说我、说真、说归、说顺处,有点铁成金之妙,读者更宜留神。颂曰:我为真照破,工夫依本做。于中一物无,哪有归真路。[9](p.1)
“此云”是佛教徒在翻译佛经、将梵文等域外文字的词汇解释成汉文时习用的一个词,“妙谛”也以佛教多用之,“顿渐错综”的“顿渐”无非是顿悟、渐悟之谓,而末了的“颂曰”则更是非佛家莫属了,果是四句五言的颂语,颂语也很有点佛家的味道。
在词汇方面,《归真总义》也使用了不少佛教中的词汇,除了以上所举之外,还有“无上”、“慈悲”、“尊者”、“入定”、“真常”、“三千大小世界”等等。虽然也用“万物皆备的我”这样出自儒家的成语,但频频使用佛教词汇则是张中著书的明显特点。 所以白寿彝先生在张中传中明确说“他(张中)的作品中使用了一些佛教词汇和佛教作品的表述形式”。[3](p.441)[4](p.921)
《归真总义》中还引用了禅诗:“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10](p.5)这是晚唐禅僧元安的诗句,《五灯会元》录有元安禅师这两句诗[11](p.138),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录有这两句诗,谓是“禅机中绝类诗句者”。[12](p.138)张中拿它来比喻世人蒙昧、不明其本智慧的模样。
《归真总义》载:“《恩达经》云:滔黑得与以麻呢,总是一理。既立两名,别有义乎?曰:江空水涸,孤月独明时,谓之滔黑得。春潮浩淼,月在万川时,谓之以麻呢。”[10](p.3)“滔黑得”为阿拉伯语词汇tawhīd的音译(多音译为“讨黑德”),表示安拉的独一、统一和单一,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述中译为“习一”。[7](pp.179—180)“以麻呢”为阿拉伯语词汇īmān的音译,意为“(对真主的)信仰”[13](p.662),指穆斯林对安拉赐予穆罕默德的“启示”及其基本信条的确认和承认。[7](p.1)
“江空水涸,孤月独明时”、“春潮浩淼,月在万川时”、“万川皆涸,孤月独明”,这都是从佛教常用的“月映万川”的比喻而来的。“月映万川”的比喻也常为理学家所借用。[14](p.243)张中借用了这个著名的比喻,以“孤月独明”来比喻真主之独一。
如果相信《克里默解》成书早于《归真总义》的话,可以看出张中汉化的学术倾向还有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在把一些阿拉伯语词汇或句子译成汉文时,《克里默解》中称“译曰”,到了《归真总义》中则称“此云”。而《克里默解》以其非汉文名行世, 《以麻呢解》却以其汉文名《归真总义》行世了。
以上的发现和比较,说明在明末崇祯年间,汉语伊斯兰教学说最为繁荣的江南地区,穆斯林学者之间分歧之大。这种分歧不是在教内的精英和一般教众之间的分歧,而是当时教内最杰出的学者之间的分歧。 这似乎是以往的研究者在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富于生气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时不太注意到的一面。
关于王岱舆晚年离开南京去往北京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清人蓝煦在咸丰二年(1852)所编的《天方正学》中的说法,称王岱舆“尝会试旅于北京”,就此,孙振玉《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一书推测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因为这一年开考;一是1937 年金吉堂《王岱舆阿衡传》中的说法,称顺治初年清兵下金陵时,王岱舆“罹浩劫,益觉萧索,乃飘然北上”。[15](pp.5—6)这都是几百年后的人的说法,且未说明根据,难以让人遽信,疑点也很多。参加会试的话,应该已经是举人了,但这在其他文献中不见丝毫迹象,倒是有清光绪年间的唐晋徽明确称他为“处士”。清兵下金陵便北上北京,无缘无故。从以上所考看,明末南京的伊斯兰教界内部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王岱舆身处其中,他去往北京是否也有江南地区教界内存在分歧这么一个因素在内呢?
王岱舆,南京人,张中,苏州人。南京、苏州二地相去不远,彼此有交流。清初的南京经师伍遵契就曾在苏州讲过学[4](p.924);而张中在《印度师以麻呢解缘起疏》中说:“崇祯戊寅(十一年,1638)春,游学南都(指南京)。”[17]正是在南京,他遇上了印度经师阿世格, 并从学三年,看来张中在南京居住了较长的时间。王岱舆、张中二人因为伊斯兰教学问的分歧,存在当面的交锋也是可能的。
而我隐约觉得当时的江南伊斯兰教界,张中是有较大影响的,因为从交际的网络看,张中似乎比王岱舆要广。他的表弟周士骐是苏州的一位掌教,康熙十一年(1672)他为南京经师伍遵契《修真蒙引》作《弁言》时已经“摄掌教四十余年”,[18]则他至少在崇祯五年(1632 )已经是掌教了,而且二人在伊斯兰教学说方面是有交流的,而伍遵契和周士骐也是有交谊的,伍、张二人相识也未可知。张中在南京居住了较长时间,必因他和南京伊斯兰教界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在他的《印度师以麻呢解缘起疏》中提到他相识的临潼经师张少山,[15]正因为张少山的推荐他才会就学印度经师阿世格门下,使自己的宗教学问有了大的长进。清康熙年间成书的《经学系传谱》中有张少山的传,据此书可知张少山为胡太师(登洲)的再传弟子,传中称他曾“设帐长安、金陵等处”,“应聘于金陵之净觉寺中,开设义学,名重一时”,而在他的传入中就有张中。[20](pp.41—42)看来,张中就是在南京师从张少山学习的。清初,张中还曾在扬州讲学,是很得扬州的教人推崇的。[21][22]
四、余说
王岱舆、张中二人都是为后来的汉文译著家所推崇的最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他们的汉文著作也在教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很大,但后人没有提及王岱舆、张中二人的分歧,特别是距王岱舆、张中二人生活的明末清初未远的人士,如刘智等清康熙、雍正、 乾隆年间伊斯兰教界——尤其是江南伊斯兰教界——的重要学者,应该熟悉二人的著述,但也没有提及此事,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对此,我根据前面的考察,提出一个猜想,即清初以来教内学人对早期教内学者的分歧刻意淡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有助于说明清代中国回回民族的一些特点,对于认识中国回回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中国回回伊斯兰教思想史的发展,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