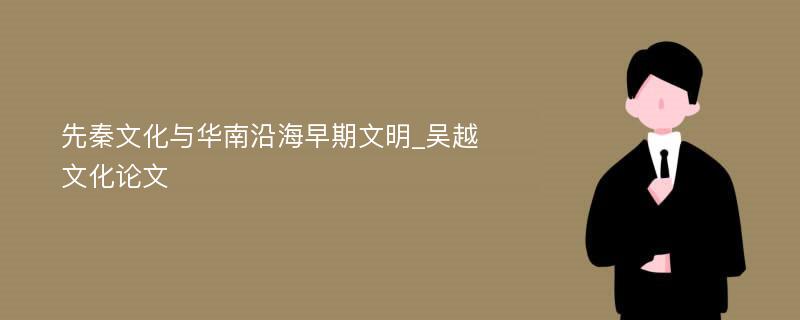
华南沿海的先秦文化与早期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先秦论文,沿海论文,文化与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南大陆沿海的闽、粤、桂地带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一环,但该地带位于武夷-南岭山地这一南北间自然与人文重要分水岭的东、南一隅,是我国早期古文化发展过程中地域特色非常浓厚的一个区系,先秦文化的发展不同于商周模式,也不完全相同于分水岭以北的百越系统的北部地带。一般认为这一时空的社会文化落后于中原,但承认先秦某时已建立了青铜文明[1],只有少数认为整个先秦都没有脱离原始社会[2]。完全对立的一类看法是不承认这一时空文化的阶段性滞后,认为商周时期这里与中原的青铜文明基本同步[3]。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具体、历史地考察这一时空社会文化的发展,重申先秦的华南向青铜时代和国家文明渐变过程的看法。
一、夏商时期原始文化的持续发展
在中原和长江流域相继进入青铜文明的夏商时期,武夷-南岭的东、南沿海一侧古文化的基本格局却表现为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持续发展,没有青铜文化和国家组织形成的证据。
1.新石器文化的持续发展
华南沿海夏商两代的古文化基本延续龙山时代的区系格局。在闽江流域,分别以下游地区的昙石山上层类型和黄土仑类型文化为代表。昙石山上层类型集中分布于闽江下游及闽东北沿海,浙南和福建全境其它地区都有该类型文化因素的波及。黄土仑类型分布于闽江下游,闽西、闽北地区可见该类型文化的影响。此外,与这两类文化基本同时、在闽北地区是马岭类型-白主段类型文化的先后发展[4]。
在珠江三角洲和北江流域分布着河宕(晚期)类型、东澳湾类型遗存和石峡中层类型。河宕类型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北部地区,自龙山时代延续至夏商前后,东澳湾类型、石峡中层类型分别是夏商时期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和北江流域地区的古文化[5]。
在九龙江、韩江流域,夏商时期的古文化类型也逐步得以认识。在粤东,普宁虎头埔窑址、池尾北山遗址代表了本地区夏代前后的文化面貌;平远水口山窑址的内涵以往视为西周遗存,从该遗存中与昙石山上层类型相似的彩绘陶和与石峡中层类型等类似的印纹陶器看,应不晚于商代。在闽南,夏商时期的遗存见于惠安蚁山和云霄墓林山(早期)[6]。
西江流域地区早期古文化的编年较薄弱,确认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很少。但桂南地区以钦州独料、隆安大龙潭等遗存为代表的、以大石铲特点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在绝对年代上很可能已晚到夏商时期或更晚[7]。
在上述各区系类型中,技术发展水平还相当原始,可靠地层和典型遗迹单位中共出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特点,不见任何青铜器具。闽江流域各类型常见小型石锛、镞及骨、贝器等工具;珠江和北江各类型也多是西樵山式的中小型石锛、有段石锛、有肩石器等,东澳湾更多石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而石峡中层多是一些适于农耕的大型和长身石器。这些工具组合均没有向青铜工具形态过渡的迹象,两区系内零星采集的青铜器中也无明确早至商代的铜器。因此夏商时期的闽、粤、桂等华南沿海地区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确凿证据,仍然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的发展水平,这是制约早期文明发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2.基本封闭的土著文化格局
上述各时空文化的核心仍是本地区土著文化的延续,夏、商王朝等文明中心区的文化影响是次要的。
在闽江流域,昙石山上层类型以赭衣和黑彩的橙黄陶和几何印纹灰硬陶共出为特点;黄土仑类型以拍印、刻划几何纹与仿铜纹样的灰硬陶为特点;在珠江三角洲与北江流域,石峡中层类型、河宕类型均以几何纹和仿铜纹样的印纹软陶为特点;东澳湾类型以绳纹软陶为特点;粤东闽南及西江流域同期各类型文化也有类似的陶系特点。这些文化类型的陶器在组合上均以圜底器、圜凹底器、圈足器为特点,常见器类主要是圜(凹)底的釜、罐、甗、尊、壶、钵及圈足壶、簋、尊、豆等,极少见三足、袋足器,更不见中原夏商式的鼎、鬲、甗、斝等器,构成一个基本不同于夏、商文化的古文化地带,这一传统实际上是昙石山文化、金兰寺下层文化等这一地区龙山时代及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业已形成的土著文化的延续。这些文化类型应就是吴越文化传播、形成融合型的“闽越”、“南越”等百越文化之前,这一地区原住的“闽”、“粤”、“瓯”等土著民族的文化遗存[8]。
这些土著文化陶器中也出现了象云雷纹、回纹等仿商周铜器纹样,大口陶尊等个别有夏、商文化特点的造型,但这类文化影响非常有限,更没有出现夏、商文化的鼎、斝等青铜礼器组合,没有改变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土著文化格局。这一基本封闭的文化格局是本地区社会发展滞后、夏商王朝中心区成熟的奴隶制形态难于在这一区系中影响或“嫁接”的基本文化背景。
3.采集渔猎为特点的经济形态
夏商时期华南沿海各区系的经济形态仍然维持相当原始的内容,同样成为制约社会组织演进的重要因素[9]。
在福建沿海,依据海积-冲积、泥碳剖面的孢粉组合和高海面侵蚀时期海滩岩的研究成果,龙山时代至夏商时期这一地区持续温暖,资源丰富,为采集、渔猎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天然食物来源,制约了农耕活动的长足发展。昙石山上层-黄土仑类型中的生产工具仍在延续昙石山下、中层类型的特点,以中小型石锛、镞等为特点,许多小石锛长仅2厘米左右,很难作为单体工具,更不可能是农耕工具,这些细小石器应是本地区适于采集狩猎活动的组合工具。贝丘堆积仍然是该阶段沿海地区的主要遗址类型,大量的海生软体动物躯壳、鱼类、野生陆生动物遗骸等的发现,都是这一以“攫取”天然食物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活动的反映。
在珠江三角洲,河宕、东澳湾类型的生产工具均以中小型工具为特点,缺乏或极少大型农耕工具,东澳湾类型中还有不少网坠、石镞等,两类型的遗址分别以贝丘和沙丘堆积为特点,野生动物遗骸大量发现,可反映农耕活动的遗存非常有限。在北江流域,石峡中层类型的中小型工具形态与大型石锛、长身石锛等适于农耕的工具形态共出,可能与北江流域的河岸低地农业的发展有关,但从总体看采集和狩猎活动也仍是重要的经济内容。
4.原始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的缓慢进展
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发展水平、偏离夏商文明中心区的封闭的土著文化环境、攫取经济突出和生产经济的不发达,决定了这一时空社会的发展也应是缓慢的,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不会太高。
在聚落形态上,闽江流域的上游河谷、平原类型和下游河旁、沿海贝丘类型基本上代表了福建夏商时期聚落分布的两种形态;在广东,北江谷地类型、珠江三角洲北部河旁贝丘类型和南部沿海沙丘类型是三种基本聚落分布形态;这些分布形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适应生态环境和经济活动需要的群落散布。缺乏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的那种围绕中心遗址分布的等级结构。从分散发现的单体房屋遗迹看,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干栏式、洞居、岩棚、窝棚等多样类型,都是因地制宜建造的小型居所,缺乏大中型和结构完善的基址。这些聚落形态只能是原始社会中的比较平等的群团——氏族、部落成员的居住遗迹,与复杂社会还有一定的阶段距离。
墓葬遗迹也有类似的线索。在福建,黄土仑墓地发现的都是小型土坑墓,均随葬陶器,多者21件,少者一无所有,在广东,石峡中层墓地发现单人墓葬32座,其中13座没有随葬品,3座墓有堆放石块等略为复杂的加工,多数随葬少量实用陶器和明器;河宕墓地发现77座浅穴土坑墓,有随葬品的仅28座,每墓多随葬一至三件,女性多用纺轮,男性多用石器生产工具。这些墓葬的共同特点是社会剩余财富的积累非常有限;社会成员之间已有一定的差别,但差别的程度没有超出氏族社会中的群团首领与成员之间的正常范围,不属于阶级对抗的范畴。迄今为止,华南沿海夏商时代考古中还不见结构与内涵都比较复杂、或伴随杀牲与殉葬的大、中型墓葬,没有出现“奴隶主”或“统治阶级”的迹象,国家文明还是遥远的事情。
二、西周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与社会
在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两周文明和长江流域上的楚、吴、越等方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青铜文化初现于华南沿海,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也在变动中。
1.青铜文化的初现
西周春秋时期闽江上、下游流域的古文化面貌基本统一,因早年发现的政和铁山墓葬较有代表性而称为“铁山类型”,在典型遗址中的层位代表是东张上层、溪头上层,故也有称之为“东张上层类型”,所指对象基本一致。[10]
所谓“夔纹陶类型”是这一时期岭南地区古文化代表,分布中心在珠江三角洲和北江流域,粤东闽南、桂东北等地都有同类遗存的影响;典型遗址中的层位可以石峡上层为代表[11]。
粤东闽南地区处于闽江、珠江两个区系之间,早期古文化比较复杂,交叉分布有夔纹陶类型遗存和铁山类型遗存;但商周时期土著文化的代表是浮滨类型,该类型上限可能为晚商,主要发展期为西周春秋,含有此类遗存的闽南云宵墓林山(晚期)的C-14年代为2450±65B.P.和2635±75B.P.,代表了该类型所处的年代[12]。
上述诸文化类型中出现了华南沿海早期青铜文化的内涵。
东张上层、溪头上层、石峡上层等西周春秋时期的典型地层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青铜镞、短剑、矛、钺、锥等兵、工类器具,仅石峡上层就发现23件[13]。
墓葬中的青铜文化资料更为明确,如武鸣马头元龙坡350座西周墓发现铜盘、卣、刀、矛、钺、斧、匕、镦、镞等计110件,与陶、玉、石器共出;南安大盈寨山西周墓出铜戈(戚)、矛、锛、铃等20件,采集铜斧1件,附近发现了具有浮滨类型特点的石、陶器;政和铁山蚌山春秋墓出铜剑、矛等3件,与铁山类型陶、原始瓷器共出[14]。
此外,这一带考古发现中还有大量零星出土或采集的没有共出关系的青铜器,内涵特点与上述地层及墓葬所见大体一致,也应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存。重要的如福建建瓯的3件西周铜铙(甬钟);广东信宜光头岭1件西周铜盉,曲江马鞍山1件西周铜铙,连平彭山春秋甬钟、淳于各1件;广西灌阳的1件西周铜铙,宾阳木荣村西周铜罍、钟各1件,荔浦马蹄塘、陆川塘城春秋铜罍各1件等[15]。
粤东饶平联饶顶大埔山浮滨类型墓地曾采集一件直内无胡铜戈,因与吴城二期等晚商时期同类器相似,以往一般将该铜器视为商代粤东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据。现在看来,浮滨类型延续时间很长,分期还有待探索;且在闽南大盈寨山遗址中类似的早期形态铜戈与周代特点的铜器共出,说明这些具有“晚商”特点的铜器在闽、粤地区的出现或延续使用主要是周代。类似的情形还有广西武鸣马头、兴安发现的窑藏“晚商”提梁卣2件、直内戈2件,形态与殷末铜器类似,但这几件铜器均无共出的陶器等物,也不应视为华南沿海青铜文化上限到商代的证据[16]。
2.外来与土著文化的复合结构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华南沿海早期青铜文化主要是在吴越等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并与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福建铁山、大盈两类型青铜文化的内涵均很明显地表现为外来与土著两组文化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复合结构:(1)铁山类型的器类和造型是以吴越文化为主、土著文化为辅的组合。圆茎剑、两翼矛是铁山类型最常见的青铜器类,也是吴越文化占绝对优势的兵器组合,剑、矛、戈、斧、铙、凿等器类及总体造型均与商周及江南土墩墓为代表的吴越文化相同或相似;但个别器物的造型或装饰具有地方特点,如光泽浔江铜矛上的镞形纹、宁德猫头山铜戈上“人”字形堆饰等。两组因素的构成在铁山类型物质文化的其它类别上也有体现,如石圹、石床墓,席纹硬陶瓮、罐和釉陶碗、豆等,正是江南土墩墓文化代表性内涵;而延续使用的有段石锛,陶甗形器、单鋬罐等器类,则是昙石山上层-黄土仑类型或更早地层中的新石器土著文化因素延续。(2)大盈类型的青铜器除明显的商周、吴越等外来因素外,有更多土著文化因素。直内无胡戈、方銎斧、铃等主要器类是商周和吴越文化常见的,造型也大致相同或相似;钺形戈(戚)不见于商周文化,但见于浙江袁家汇早期吴越文化中。但该类型的本地特征多于铁山类型,如戈的内端内凹、援中起脊,钺形戈的台阶状栏部和网络纹饰,有段铜锛纹饰简化,兽目和倒“八”字眉须的瓦状斧、铜铃上的几何纹饰等,均是商周文化和吴越文化铜器所不见的,却大多可在本地区浮滨类型及更早的原始文化的石器、陶器上找到同类特点[17]。
两广青铜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与商周、吴越等外来青铜文化的相当共性,但也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如各地出土的铜卣、盉、罍、盘、钟、铙、剑、戈、矛等均与商周及吴越同类器基本相同;但武鸣元龙坡西周春秋墓地刀、钺、匕首、镞等器则富有地方特色。此外,在作为这些青铜器主要共出关系的、具有浓厚岭南土著文化特点的夔纹陶类型的陶器组合中,也可看到一些吴越文化的痕迹,如石峡上层的原始瓷豆、钵等与江南土墩墓中典型的同类器相同,但是,陶器上所能看到的这些吴越文化因素要远远少于青铜器上所见到的。元龙坡墓地的陶器更主要是火候不高的素面、绳纹和朱绘的软陶,地方特点更浓厚。
根据这些分析,西周春秋时期华南沿海的民族文化仍主要以闽、粤、瓯等土著文化为基础,吸收吴越等文化因素形成的融合形态,即“闽越”、“南越”的早期文化。而他们的青铜文化除具有土著文化的痕迹外,主要是在吴越文化的影响下、或商周青铜文化通过吴越文化为中介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
3.经济与社会形态的考古推测
随着青铜文化的出现、土著文化封闭格局的打破和先进的吴越文明的传播,两周时期华南沿海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
首先,农耕与畜养等生产性活动开始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两周时期是全新世时期的一次最严重的气候持续转寒期,这一生态剧变既是诱发吴越文化向南推进的一个原因,同时气候的转寒还减少了自然的赐予;对主要依靠天然食物的攫取式的原始经济形态是个极大的压力,成为迫使生产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吴越文化的传播带来了青铜斧、钺、刀等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悠久的稻作文化与技术也随之传入,成为农耕经济较之前一时期有重大发展的基础。但是,这些青铜农具还与石器共出,不见犁、锄等农具,说明农业经济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不能与长江、黄河流域发达的农耕文化水平相比较。
其次,随着商周与吴越文化的传播,上层社会的生活制度、典章法式也不同程度影响或传入。建瓯、灌阳等地发现的西周铜钟(铙)与同期江南各地发现的用于军旅集会或祭祀山川的南方大铙相同,青铜兵器中常见剑、矛、戈,与吴越文化兵器组合规律相同,这些说明吴越等文明社会的礼乐制度、宗教祭祀、军兵法式已经影响到这一地区。福建南安发现的12件成套石锛,大小递变,出土时分三层依次排列,没有砍、凿使用的痕迹[18],这是仅见于本地区的专门仪式用器,说明闽越上层社会的生活模式并不全同于商周、吴越文化。无论如何,这些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夏商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所不见的。
最后,阶级分化、冲突正在发展,文明社会的一些现象正在起源。大盈、铁山等以随葬青铜兵器为主的墓葬不是一般的平民墓葬,应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处于社会上层的部落首领或军事头目;元龙坡的一些墓葬不但发现了兵器,还随葬铜卣、盘等精美贵重的盛食器,可见这些上层贵族的社会生活与一般平民的距离在扩大。这些线索表明,夏商时代的那种社会分层不明显、组织结构简单朴素的土著原始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出现了只有文明社会才具有的一些复杂现象。
但是,这种初步的文明社会现象还只是萌芽阶段的,上述各铜器墓葬的规模所对应的只能是小地域内集权贵族——群团首领或部落酋长一类。这一时空考古中始终缺乏较大型的墓葬和城址的发现,说明具有较大范围控制能力的“王国”社会还没有出现,大致处于国家文明的起源阶段。
三、战国前后青铜文化的鼎盛与方国文明的出现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的又一重要转折点,通过诸候国间的兼并融合逐步形成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雏形,对周边民族产生更强烈的影响,加速了包括华南沿海在内的边远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1.考古文化的类型与特点
继铁山类型之后,闽江流域的考古文化表现为富林岗类型和庄边山类型两类,约属战国至西汉前期。富林岗类型以几何印纹陶釜、瓮、罐、瓿、匏壶等类似于同期江南“百越”文化的土著因素为主,以仿铜陶鼎、香熏等汉文化因素为辅的二组因素组合,是在前期铁山类型青铜文化基础上受楚、汉文化影响的闽越文化的延续体。庄边山类型则是以仿铜陶鼎、豆、盒、壶等楚汉文化为主,兼出富林岗式几何印纹陶器为辅的二组因素组合,应是移居闽越地的楚、汉人受到当地土著文化影响的融合形态,只是某一特殊历史事件的产物,不是闽江流域文化的主体。
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两广,夔纹陶类型晚期不同程度地延续至战国早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战国时期“米字纹陶类型”,该类型延续至秦汉初并发展“方格纹加戳印陶类型”。粤东闽南地区的同期文化基本接近于珠江三角洲。
就是说,表现在日用陶器的组合和造型上,“闽越”、“南越”文化仍是战国前后华南沿海民族文化的主体。
2.青铜文化的鼎盛及铁器文化的初现
华南沿海战国时期的考古文化是在前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延续发展的,相继处于青铜文化的鼎盛阶段,并向铁器时代过渡。
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夔纹陶类型墓葬中,青铜文化达到了鼎盛阶段。清远马头岗M1、M2出铜鼎、罍、缶、钟、钲、镦、矛、斧、剑、戚、镞、人首柱形器等计64件;四会鸟旦山M1、高地园M1、M2出青铜鼎、盉、铎、鉴、洗、戈、矛、剑、钺、斧、人首柱形器、半球形器等计76件;罗定夫背山M1、南门洞M1、M3出铜鼎、鉴、盉、缶、钟、钲、钺、镰、戈、矛、斧、剑、镦、人首柱形器等计235件;怀集栏马山M1出铜鼎、斧、人首柱形器等计7件;和平龙子山M1出铜鼎、钺、戈等5件。以上各墓均与夔纹陶类型陶、原始瓷器共出。此外,恭城秧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残墓出铜鼎、罍、尊、钟、短剑、戈、斧、镞、兽首柱形器计31件[19]。
在米字纹陶类型中,青铜文化继续鼎盛并向铁器文化过渡。德庆落雁山战国晚期M1出土铜鼎、铎、矛、剑、斧、越、镦、镞等15件;罗定南门洞战国晚期M2出铜剑、矛、刀等4件;肇庆北岭松山战国晚期(或秦汉初期?)墓就出土鼎、壶、三足盘、编钟、提桶、斧、锛、铲、刻马、镜、人首柱形等青铜器108件;广宁铜鼓岗战国M2-M22发现铜鼎、盘、剑、矛、钺、斧、凿、锄、锸、削、镞、半球形器等295件;宾阳韦坡村战国晚期M1、M2共出铜鼎、钟、剑、斧、钺等计20件;始兴白石坪战国遗址的铁斧、锸是该类型发现铁器的最早地层;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晚期(秦汉初?)110座墓发现377件铜器与181件铁器[20]。
上述青铜、铁器文化中,周、楚及吴越等外来青铜文化因素仍占主流,不同程度的地方特点是次要的。首先,铜兽足鼎、卣、盉、罍、缶、鉴、洗等容器,钟、钲、铎等乐器,戈、矛、剑、镞、斧、钺、镰等兵器、工具类,及铁斧、锸等器均与周、楚及吴越地区所见相同或相似。其次,青铜淳于、提桶、外撇足鼎、靴形斧等器类,仅见于江南的楚、越文化及邻近地区。再次,恭城、罗定、四会等墓所出周、楚及吴越文化造型相同或相似的尊、矛、钺、斧等器类,器身装饰蛇、蛙纹或“王”字符号,地方特色浓厚。最后,兽首或人首柱形器、半球形器等器物是两广仅见的。
福建的青铜文化内涵比较贫乏,闽西、南的武平、大田、漳埔零星发现春秋战国的青铜剑、斧,属于铁山类型的延续,富林岗类型青铜器与犁铧、锄、锸、耙、斧、刀、镰等铁器共出。这些铜、铁器与吴越及楚汉地区所见无异。
可见,主要由于周、楚、汉及吴越文化的影响,华南沿海青铜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并向铁器时代初期过渡,技术发展水平的这一明显进步成为社会形态向更高形态进化的基础。
3.“闽越”、“南越”等王国社会的出现
据《史记》载,汉高祖元年,赵佗在番禺自称“南越武王”、立“南越国”,直至元鼎六年被汉灭。高祖五年,无诸于东冶称“闽越王”,在元封元年灭国。目前虽无闽、广越人建立王国政权更早的明确记录,但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带由小国寡民的酋邦社会向能控引一方的王国社会的发展应早于汉初,出现于战国时期。
首先,秦汉初闽越、南越王国社会的重要经济基础是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标志着华南沿海地区稻作农业已逐步赶上楚、汉地区的发展水平。但是,这一技术史的进步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其次,秦汉初闽越、南越王国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是模仿楚、汉文明,接受以礼乐制度为代表的等级制,这可在两广汉墓成套青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的使用中得以说明。但是,春秋晚期以来随着周、楚、吴越文化的进一步传播,特别是战国以后强大的楚国对江南大部分地区的军事控制促使楚、越文化的接触日益增多,越人土著上层所仰慕的北方文明社会式的生活制度已经全面、深刻地传入。以青铜鼎为代表的礼器的使用成为战国以来两广铜器墓的重要特点,这在西周和春秋早中期的墓葬中是没有的,有些墓还直接使用周、楚式的兽足鼎,虽然没有周、楚式严格的用鼎制度,但用鼎数与墓葬规模也相一致;清远、罗定、博罗等地[21]墓葬和窖藏使用成套编钟,虽没有象周、楚编钟的规律可寻,但也大小相配。可见,在周、楚地区渐趋衰弱的“周礼”从战国前后开始确实在华南沿海地区发育,成为这一边缘地带社会历史发展步伐逐渐靠近岭北的重要标志。
再次,社会分化更加激烈、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之中产生以“王”为最上层的国家社会的组织结构。四会、罗定、清远、怀集、恭城、肇庆等地发现的含青铜器和礼乐器的大、中型墓葬,均随葬具有仪仗性质的铜人首杖头,部分杖头及矛、钺上铸有“王”字符。这些墓葬的规模和内涵都已不是春秋以前的部落首领或酋长墓所能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贵族墓,而应是与王国最高统治者“王”或宗室有密切关系的上层人物的墓葬。其中恭城秧家春秋晚至战国早期残墓发现铜器31件,用鼎数5件,兽首杖头2件,随获器物还有散失,这应是岭南最早的一座高规格墓;肇庆松山墓长8米,宽4.7米,深6米,木椁漆棺,随葬铜、陶、金、玉、石、琉璃器139件,用鼎5件,人首杖头4件,这是岭南最早的一座大型墓。中型墓更多,如罗定夫背山M1墓室长4米、宽2米,随葬品116件,其中铜鼎2件,墓底两端各竖立2件人面朝外的杖头,后端2件杖头及矛上有“王”字符;罗定南门洞M1规模与之一样,随葬品达137件,用鼎3件,人首杖头4件,矛、刀上有“王”字符。依周礼,五鼎“少牢”是仅次于诸侯王的卿大夫一级的特权,三鼎“少牢”是士大夫的特权,《国语·楚语下》载:“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礼以特性”。上述五鼎墓“很可能是属于‘君王’一级的南越郡国上层统治者”,二或三鼎墓“大概属‘将’一级的南越上层统治贵族”[22]。这些现象说明,约从战国时期开始,岭南地区已经出现了只有王国社会才可能有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文明社会的组织结构。
最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都有两汉闽越、南越王国延续先秦古国发展而来的线索。依《史记·东越列传》,在秦统一天下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被“皆废为君长”,汉五年“复立”为闽越王和东海王。可见,闽越及东海是先秦时期业已存在的古国。闽越都东冶旧址今福州一带的秦汉遗存也多上限至战国晚期;闽越的另一政治中心崇安城村古城可能是余善割据政权“都城”,但该城也有始建于战国时期的证据[23]。南越国也有类似的历史过程,《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兵攻打南越时发丘五十万,“三年不解甲驰驽”,《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还说:“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可以想象,南越人的抵抗并不是部落社会的弱族,可与强大的秦国大军抗衡的应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卫国之师。南越国都番禺也不是短短的汉初几年建成的,《人间训》载秦丘来攻时兵分五路,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可知也是早已繁荣的先秦古都[24]。
就是说,约从战国时期起,华南沿海的社会文化面貌、历史进程与北部地区的周、楚、汉文明已经基本接近,建立了闽越、南越民族的“国家”政权,很可能就是汉初“复立”的闽越、南越等王国的直接前身。
四、两点思考
(一)要恰当评估先秦时期华南沿海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必须将这一时空文化看成一个动态整体,具体、历史地考察它的发展变化过程。华南沿海约于周代进入青铜时代,战国时期建立起国家文明社会,分别要落后于中原地区达1000年和1500年以上。可见,夏商周文化并不代表中国文明的统一步伐。我们不应忽视华南沿海地处华夏青铜文明的边缘这一基本事实,过高估计了中国先秦社会历史的统一性,将夏商周青铜文明模式等同于边远地区的早期历史。如将华南沿海地区商周时期的遗存等同于“商周青铜器时代遗址”和“奴隶社会阶段”,将几何印纹陶文化笼统看成华南青铜时代或“文明时代”的文化,都不是历史事实。
华南沿海的先秦史还告诉我们,青铜文化并不等同于文明时代。青铜时代是技术史序列中的一个阶段,“文明”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高级阶段。“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25]。虽然文明社会的产生是以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文明史和技术史间没有具体的、必然的和全球一致的联系,如欧洲大陆文明史都是伴随着成熟的铁器时代文化而出现的,美洲的玛雅文明则是以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文化为基础的,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则与青铜文化一同肇始。华南沿海国家文明社会的确立要比本地区青铜文化的出现晚得多。
(二)华南沿海早期文明进程的明显滞后有自然和文化的多方面原因。
首先,华南沿海地处南亚热带和边缘热带,湿热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种群,为早期人群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食物来源,制约了生产性经济的发展。由前述可知,直到夏商前后,这一地区采集渔猎仍然是原始居民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西周春秋前后农耕经济发展水平仍远不及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在先秦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缺乏文明社会所应具有的起码的物质文化基础。
其次,土著先民文化的特殊性,也是社会发展道路有别于华夏等其它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百越及其先民不但在物质文化、而且在精神文化传统上不同于其它民族,除吴越、干越等百越北部族系因地域关系较早接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外,华南沿海的闽越、南越等群体的民族文化特殊性更为强烈。如果不是来自北部的华夏等先进的青铜文化和文明组织模式的强烈介入,加速了土著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和进程,华南沿海地区的文明史可能还要推迟到来。
最后,东亚地区古代文明的中心在黄河中下流域即“中原”,这一看法并不因为文明因素多元起源的考古发现而受到挑战。外部、主要是夏商周文明因素的介入是加速华南沿海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武夷-南岭山地的强烈阻隔延缓了华夏等先进文明的影响速度,故北部地区的文明不能同步带动华南沿南早期文明的产生。
注释:
[1]林惠祥:《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4期;何纪生:《略论广东东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及其几何印纹陶》,《文物集刊》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徐恒彬:《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载《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出版;俞越人:《福建南安发现的青铜器和福建的青铜文化》,《考古》1978年5期。
[2]区家发:《广东先秦社会初探——兼论38座随葬青铜器墓葬的年代与墓主人问题》,《学术研究》1991年1期;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4期;黄展岳:《两广先秦文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3]陈龙等:《试谈黄土仑印纹陶器的时代风格和地方特色》,前引《文物集刊》第三辑;陈国强等主编:《闽台考古》(第三章),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简明广东史》(第二,三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杨式挺:《岭南先秦青铜文化考辩》,载《铜鼓和青铜文化的新探索》,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4][10]林公务:《福建史前文化遗存概论》,《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吴春明:《闽江流域先秦两汉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2期。
[5]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广东出土先秦文物》;李岩:《试析东澳湾遗存》,《考古》1990年9期。
[6]同[4]林文;[5]朱文;吴春明:《粤东闽南早期古文化的初步分析》,载《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7]蒋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蓝日勇:《建国以来广西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广西文物》1991年1期。
[8]吴春明:《闽文化刍议》,《厦门大学学报》1990年3期。
[9]吴春明:《对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史前文化聚落形态研究的几点思考》,《考古与文物》1996年3期;同[5]。
[11]同[1]徐文;徐恒彬:《广东几何印纹陶纹饰演变初步认识》,《文物集刊》第三辑。
[12]同[6];朱非素:《闽粤地区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发现和探索》,《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13]陈存洗等:《福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学报》1990年4期;朱非素:《马坝石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广东《文博通讯》第三期(1978年)。
[14]广西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2期;庄锦清等:《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考古》1977年3期;铁山中学等:《福建政和县发现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和印纹陶器》,《考古》1979年6期。
[15][16]王振镛:《福建建瓯县出土西周铜钟》,《文物》1980年11期;徐恒彬:《广东信宜出土西周铜盉》,《文物》1975年11期;彭绍结等:《马坝发现西周晚期铜铙》,《广东文博》1985年1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1984年9期;蒋庭瑜等:《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7]吴春明:《福建先秦青铜器文化类型的初步探索》,《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1期并见[1]徐文;[2]黄文;[15]蒋文。
[18]张仲淳等:《福建南安县发现成套石锛》,《中国文物报》1987年10月1日。
[19]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1963年2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清远的东周墓葬》,《考古》1964年3期;《广东四会鸟蛋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2期;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4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1期;《广东罗定夫背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3期;广西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1期。
[20]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9期;《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11期;《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学集刊(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宾阳县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2期;莫稚:《广东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考古》1963年10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2期。
[21]邱立诚等:《广东博罗出土一组青铜编钟》,《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
[22]邱立诚:《广东东周时期青铜器墓葬制刍议》,载《广东出土先秦文物》。
[23]吴春明:《闽越故冶地望的新探索》,《福建文博》1994年1期;崇安城村古城及其邻近的聚落遗址群内涵属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富林岗类型,古城C-14年代数据为距今2375±80年和2630+125年。
[24]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