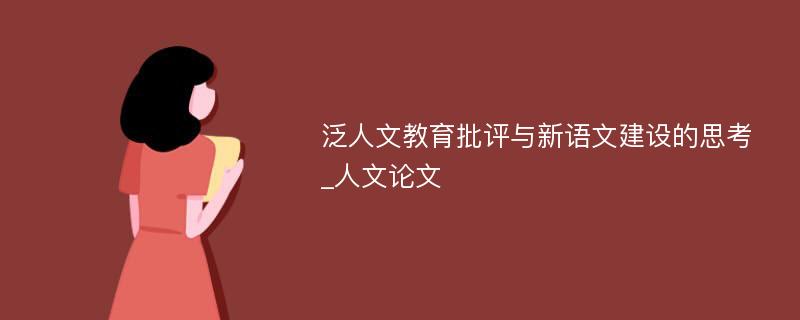
关于“泛人文教育”的批判及新语文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及新论文,语文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反思新课程语文教学时,一些语文教育专家开始关注现阶段新课程语文教学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新课程语文教学存在着“泛人文教育”的弊病,主张语文教育要回归原生态,回归本色教学。
“泛人文教育”提法的内核是指责现阶段新课程语文教学过于重视人文性,忽视语文基础,忽视听说读写基本能力的培养。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课程改革之后所流行的语文课越来越好看,但越来越空洞且不实用而言的。发现并批评新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新课标所强调的“人文性”,角度看似比较新颖,实质上仍然是深陷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而不能自拔。恢复语文教育的原生态、恢复本色教学的说法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关键在于是要恢复什么时候的原生态、什么样的本色教学。课程改革的8年语文、改革开放的30年语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90年的现代语文、千年的中国语文,哪一个是最原生态、最本色的语文呢?
“工具性”不等于是语文的本源,强调“工具性”的本意也并不在于单纯的语言训练。“工具性”出现在《教学大纲》中至今也只有半个世纪。从1956年《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中引用列宁的语录“语言是人类交际极重要的工具”,把语文定义为“汉语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重要的、有力的工具”,到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把语文定义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再到1978年及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是在重温领袖语录的基础上逐渐把语文定位在“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层面上。“工具性”的定义一直是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教学大纲》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语文“工具性”的定义并不是单纯强调语言训练,而是一直隐含着政治思想教育。在此之前,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则一直把学习本国语言文字与了解固有文化、培养民族精神相联结。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提出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在“工具性”的基础上添加了文化的内涵,从百年课程标准沿革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对“文化性”的回归。但从2000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把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开始,这两个“性”所引发的学术争议却至今未平。从“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角度来看,关于“泛人文教育”的批判,其本质是语文工具论的回潮。
“泛人文教育”是把“工具性”与语言训练等同,而把“人文性”与思想教育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缺失辩证法。语文要学习的语言并不是抽象的语言,而是形象的语言、鲜活的语言,是依托于文化的语言。有文化内涵的语言,才是最好的语言;闪烁着人文魅力的文章,才是最适合学习的范本,也就是最好的语文学习的工具。我们常说“文以载道”,语文教育应当反思的是文章应载什么样的“道”,应当反思的是教材、中考和高考试卷中有多少不载道的东西。
所谓语文的原生态和本色教学,不等于是工具论教学,也不能简单地与语言教学画等号。语文的原生态和本色教学涉及教法问题,而教法又是最自由、最个性化的。课程改革之初,在一些高校课程改革专家的大力推动下,有效教学、生成教学等教学法似乎成为新课程教学的标志,不使用这些新法的课就不是课程改革的课。其实哪有什么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教学法!就语言学习而言,古人所言的熟读、精思、勤练,远比什么几步几法要高明得多,有效得多,也本色得多。只要路走得对,怎么走无所谓,不一定要踩着别人的脚印前进。
语文教学研究,最缺乏的就是理性。就现阶段而言,影响语文教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仍然是动辄断章取义、支离破碎地引用某些教育家语录的教条主义和大摆课程改革姿势的形式主义,这也是课程改革过程中最具危害性的。动辄专家说怎样怎样,动辄课改应怎样怎样。其实该怎样就怎样,是什么就是什么,教学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课程改革的教学研究,不要太严肃,太死板,要有点幽默感。幽默是一方良药,是消灭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最好办法。如果你具有了幽默感,能够自嘲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失误,怎么还可能成为一个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呢?其实嘲笑自己,是在用别人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用别人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看待事物,能够使你更清醒,更理性。
二
改革开放至今,语文教育一直在强调“工具性”,具体来说就是狠抓语言训练,但为什么结果却令人失望呢?原因很复杂,因为语文教育不仅仅是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它也掺杂了复杂的社会教育因素。就语文教育本身而论,现行的语文教育理念和体系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呢?是否缺失重要的东西呢?
现行的语文教育理念和体系一直在强调“听说读写”,一直在避谈“思”,似乎一提“思”就陷入了政治思想教育之中。其实“思”应当成为语文教育的核心,缺少“思”的语文教育是没有灵魂和内涵的学科教育。中国语文教育的理念和体系本应是全面而系统的,应当是“听说读写思”俱全,而不应当一味地在语言技术层面上打转。因为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思”是很重要的。何谓“思”?就是指正确的思想以及思想的能力和思维方式等,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没有“思”的“听说读写”,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意义的“听说读写”;没有“思”统领的“听说读写”,只会流于语言表面,缺乏内涵。对于人的发展而言,缺“思”的后果是严重的,缺“思”则缺“德”。
新世纪最时髦的研究课题是中外母语比较研究,有些人似乎总想从洋人那里汲取营养、寻找论据,总想让中国语文与世界接轨,特别是与西方世俗教育接轨。殊不知,中国语文教育的特殊性就在于“文化性”,以及其所承担的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西方的语文教育,就本质而言是脱离了宗教思想的世俗教育,更强调纯语言技术层面的教学。而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中国文化又远较西方宗教更复杂,因此中国的语文教育是不可能超脱于中国文化的。
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课程改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课程语文教学强调人文性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在教学实践中蜕变成了形式主义。对新课程语文教学人文教育的反思与批判,并不意味着需要重新恢复到独尊工具论的时代。“泛人文教育”这种提法还是有一些现实的针对性的,“泛”正说明新课程语文教学的人文教育太泛,不集中,不深刻,还受到政治思想教育的局限,没有贴近中国文化的内核与灵魂。
中国文化最讲究修身,中国人传统的修身方式是要通过学习和自省来达到的,即“学而时习之”和“吾日三省吾身”。中国人的“自省”与西方人的“忏悔”是不同的:中国人的“自省”是要说给自己听,要用自己内心中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西方人的“忏悔”是要说给神父听,要由上帝来评判。中国人的“自省”,不是简单的“忏悔”,需要有坚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这其实就是《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现代的中国人不是接受人文教育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具备的人文思想不是太深刻了,而是太肤浅了;中国语文教育不是强调人文性太多了,而是强调得还不够,还不到位。
2009年是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宣称: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那是一场带有全盘西化倾向的文化运动,所有据守中国文化的人都被统称为“复古”,就连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试图从中西文化中寻找交汇点的人也都被斥为不合时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引进外来文化与发掘自身固有文化之间似乎是永恒的矛盾,但有时候引进外来文化越多,越能唤醒一个民族对自身固有文化的自信。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万众一心的“击缶”中,从余音不绝的《论语》的诵唱中,中国人似乎又从历史的纵深中找回了文化的自信,让世界也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在“重建中国文化自信心”的大背景下,中国语文教育也面临着为中国文化奠基的任务。因此,无论是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角度,还是从人的健康发展角度来看,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应当成为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是语文教育亟须重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新语文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突破视野的局限,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由课程改革的8年、改革开放的30年,上溯至90年前、甚至是千年前,重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文教育构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