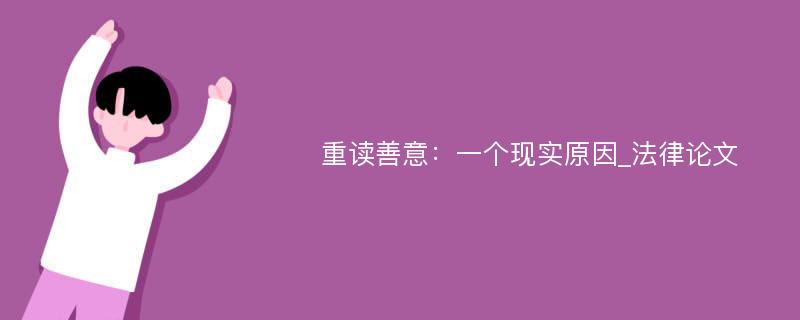
重读善意:一种实践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善意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善意及诚信原则的通常理解 善意,英文表述形式为good faith,不过最常用的表述形式还是沿用至今的拉丁文bona tides,一般说来,bona tides的意思,就是诚实行事,不知道也无理由相信其主张没有依据①;诚实、公开、严谨;不欺骗;真实而不矫作②。 善意往往被放到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契约关系或条约关系的语境中讨论,这时它就成为了诚实信用原则。因而很多学者认为善意与诚信是一个意思,甚至直接将有关的西文表述译为“诚信”③。徐国栋先生指出,fides来自动词fieri,为“已经做成”之义,后来西塞罗把它解释为“行其所言”;至于bona,是“好”的意思,起强化fides的作用,两者合为“良信”之义,但人们惯于将其翻译为“诚信”④。科勒尔认为,罗马法上原有格言pacta sunt servanda,即约定必须遵守(即使约定不符合法定的形式),罗马帝国的法学家们在正义、平等、信义等理念的基础上,扩充了其内涵,将其发展为诚信(善意)原则⑤。以“约定必须遵守”为主要内容的诚信原则对民法具有极端重要性,因而在罗马私法上,诚信原则又被尊为“帝王规则”。 今天,善意原则(涵盖诚信原则)已经广泛地进入了实在法。首先,诚信原则已经成为民法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普通法上虽然没有关于诚信原则的明确定义,但已经有足够多的判例规定了这一原则。因而英美法系的学者一般认为,诚信原则是来自契约必须信守和其他明显直接关系到诚实、公平和合理的法律规则的基本原则,它就是诚实地、公平地对待合同当事人的意思⑥。具有准立法性质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3条也规定:“对本法范围内的任何合同或义务,当事方均须以善意做出履行或寻求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其次,善意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法上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2款规定:“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保证全体会员国加入本组织而发生之权利。”《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该国善意履行。” 二、善意原则在古代法哲学的源起 柏拉图认为,善是最高的理念与价值,是一切具体事物和行为的终极原因,是人类所有认知的前提、基础与目的,正义的秩序通过人们对善的理念的追求来实现。善的理念和现实的最终基础是一致的,现实和善最终会合为一体⑦。他还在《法律篇》中借雅典人之口指出,最好的不是战争或内战,而是和平与人们之间的善意⑧。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不遗余力地推崇与强调“善”,甚至认为正义都是隶属于善的。他指出,善是所有事物的目的,国家的最终目的是对人而言的至善;如果善意被抽去,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就将不复存在⑨。与柏拉图关注普遍的、终极的、超然的善不同,亚里士多德将关注重点放在具体的善上。他认为一切具体的行动和职业活动,都在追求某种目的,在实现某种具体的善;普遍的善与个别的、特殊的善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个别的、特殊的善,就无所谓普遍的、绝对的善或至善⑩。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行为需要符合善意原则。 由于斯多葛学派主张“顺从自然”的生活,因而该派学者对善的界定是殊途同归的,基本上,西塞罗在《关于最高的善和最大的恶》中所提到的“最高的善即依循自然而生活”这一界定可以概括这一学派的观点;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包括第欧根尼(Diogenes)的“善即具有自然的完整性的事物”等(11)。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在对待善的问题上,斯多葛学派还特别强调诚实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罗马法发展出了诚信原则。《法学阶梯》所列的三大法律戒规中,第一条就是“诚实地生活”(to live honestly)(12)。显然,这与诚信原则在罗马私法中的重要位置有关,但是不难看出的是,这条戒规并不仅仅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还适用于一切社会关系,它意味着只要人在社会上生活,就应当诚实,实际上这条戒规正是善意原则的初步表述。 阿奎那认为,善也是一种习惯,是人与生俱来的行事能力;精神上的善是与理性相称的;在那些一般性的自然法规则中,最基本的规则就是行善避恶。他指出,任何人都有按理性行事、意即依善行事的自然倾向,每个人的理性会自然地命令他作出善举(13)。可见,阿奎那已经开始尝试讨论善的来源,他把善归结为理性(reason)与德性(virtue)。 可见,在古希腊时期,善意原则已被初步表述,而古罗马将作为这种初步表述的诚信原则付诸了实践。到了中世纪,善意的理性来源被提了出来。 中世纪后期,许多国际法学者对善意原则进行了研究。 苏亚利兹指出,善意是自然法的一项原则,其基础是自然理性,无论是神还是人都要遵守之。但是他认为,善意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只有客体正确,才有适用善意的必要。苏亚利兹肯定说,一般来讲,善意要求遵守协议,即使对敌人也不应毁约,但是如果对方违背善意原则或者出现了导致履行不能的情势变更,另一方就可以完全解除履行义务,当然他应该将此情况通知对方(14)。苏亚利兹不仅明确提出善意是自然法的原则,而且界定了善意的基本内容——约定必须遵守,并阐述了善意的限制。 真提利在他的几部著作中都对善意原则作了阐述。在《使节论》中,他指出,一方面,国家要善意地保护使节,即便其身处敌人武器的重围之中也应保障其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使节也要依据善意原则在驻在国行事(包括避免从事间谍行为、违法犯罪以及侵犯主权的行为等)以及为派遣国尽忠,因为“只有表现出善意才有资格主张善意”(15)。在他的代表作《战争法》中,真提利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对善意原则的主张。他明确指出,善意原则不仅仅包括“约定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这一戒律,而是以该戒律为其特有元素的一项更为广泛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善意原则不仅仅是部门国际法(如条约法、外交关系法、战争法)的原则,而是一般国际法的原则。真提利关注国际协定的真实意图与精神,他指出,条约(foedus)这个词原本是由信义(fides)这个词衍生而来,善意原则的主要意思,就是合理地、公平地执行条约而不是生硬地遵循约文。他否定任何与约文的不符之处都导致条约义务解除的说法,认为只有重大、根本违约才导致这样的后果。真提利坦言,他所说的善意原则涉及理性、公平、平等、宽仁等诸多重大范畴,但是善意原则并不包括这些范畴,而是要遵循这些范畴。比如,当敌人无条件投降时,即使没有协议,善意原则也要求给他自由。不过,在如何遵循这些范畴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前后是不一致的,比如,他赞成那种一旦城邦毁约,就要完全摧毁之的激进主张(16)。可见,真提利对善意原则的适用范围作了较为准确的界定,他指出,善意原则不仅适用于契约或条约,而是一般性的规则。他就善意地解释与执行约文作了阐述,并指出了善意原则的界限与限制。事实上,善意确实需要遵循一些更高的范畴,不过,由于真提利没有搞清楚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才导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前后不一致。 可见,国际法学者一般在条约的范围内讨论善意的问题,他们研究了善意的表现形式、善意的界限与限制。但及至中世纪末期,已经有人洞悉到,善意不限于部门法,而是一般性的规范,善意需要遵循一些更高的规范。 总之,在古代,善意的内容、形式、界限、来源以及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一定探讨,部分善意原则还被付诸了司法实践。 三、善意原则在近代法哲学中的发展 格老秀斯认为,善意原则是整个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它尤其适用于条约关系。在他所提出的五项自然法主要原则中,有一项就是“遵守合约并践履诺言”;尽管另一项原则要求“归还属于他人的东西并用我们自己的财物使他人的财产恢复原状”,但他指出,如果当事人是善意占有他人的东西,且该物已经灭失,就不必赔偿。格老秀斯坚信,善意是正义的一部分,维持和平的要求正是出于善意的神圣性。他指出,即便是与奸诈的、不守信用的敌人订立的协议,也应善意履行而非弄虚作假;违背被迫订立的契约是正当的,强迫他人以达损人利己之目的是不允许的;基于善意的神圣性,和平协议不论其条款如何都应得到坚决的维护(17)。格老秀斯不仅论述了善意原则在合约或条约中的适用,还论述了善意原则在其他领域的适用,尤为重要的是,格老秀斯正确地指出了善意原则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正义。 在霍布斯所宣称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戒律中,有两项涉及善意原则:信守协议;若有人基于你的诚信给予你某项利益,毋失信于人。他还特别指出,守信应当对针对所有人而无任何例外(18)。 普芬道夫认为,善意对于协议的缔结方而言,乃是自然法之下的绝对义务,人们必须善意地履行其承诺和协议的条款。承诺和协议需要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而同意以理性的运用为前提。他推崇“约定必须遵守”,但又主张由无缔约权者、误解、欺诈、胁迫所订立的协议是自始无效的。他还主张,人们只有义务去履行具有可行性的协议条款,而没有义务去履行违反法律的条款(19)。科勒尔指出,在善意问题上,格老秀斯与普芬道夫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善意原则是一项已经被转化为实在法的自然法原则,而且这种转化是不全面的(20)。应该说,这种观点道出了善意原则再转化为实在法过程中的尴尬,善意的主要部分——诚信往往被转化为实在法,但其他部分则容易被忽略。如今,这种状况在国内法中得到较大改善,而在国际法中仍然延续着。 沃尔夫强调,善意对于条约关系有着最为至关重要的意义,善意是遵守条约的独立的神圣基础。他认为,实现和促进善意增进了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光荣,这与宗教无关,而是建立在国际社会共同福利的基础上。沃尔夫认为,宣誓不会产生一项新的条约义务,但是有必要对善意履行做出保证;在战争中,即便是对敌人、强盗和歹徒,也应当遵守善意并履行承诺(21)。 法泰尔视善意为条约之基础,并称条约之诚信(the faith of treaties)为“国家间之圣物”(things sacred among Nations)。法泰尔指出,只要条约是在善意之下订立的,即便其执行将给某一方带来比预料更多的负担,条约也是有拘束力的——以条约未对国家造成毁灭性伤害为限;相反,非在善意之下订立的条约是绝对无效的。他认为,如果一国不批准一项未经授权签订的条约,那么根据善意原则,该国不能保持沉默而导致另一方履行协议;除了特殊情况之外,该国还应当返还从未批准的条约中得到的不当得利(22)。 总之,在近代,善意原则的构成因素得到了较好的梳理,并因而更多地进入了法律实践中。善意原则的可转化性及其在转化中的问题被注意到,善意的直接理论渊源被提出。 四、善意原则在现代法哲学中的深化 很多现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善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界定。在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善作为一个自由而平等的人的道德能力之一,被定义为明确个人有关人生价值概念的一组有序的人生目标(23)。菲尼斯把“善”(good)作为其自然法学的核心要素并推崇“共同善”(the common good);他指出善是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ableness),他认为实践原则体现了基本的善,而基本的善的框架和方法论上的实践理性设想就体现在法律制度的详细规则之中(24)。 可见,对于善的界定,现代学术界开始呈现多进路、多角度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派学者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善的本质在现代已经被基本准确地概括了出来。詹姆斯曾经论证说,善的本质就是满足需求。庞德对此做出了修正,加上了“需求产生于文明社会生活中并且需求的满足以代价最小为条件”的限制。而博登海默将前人的论述扬弃性地总结为“满足合理需要”。 那么,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善意的本质呢? 值得注意的是由康德提出并在现代为诸多学者所接受的“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概念(25)。根据康德的论述,纯粹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就是实践理性(26)。这一概念是富有创见性的,它把理性思辨与实践运作、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结合了起来,不仅为自然法指导社会实践、而且为实在法调整社会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理性”的概念为我们认清善意原则的本质提供了基本素材。 杜威反对从抽象的角度去谈论善行,强调以实行、效果来看待善的问题;他指出,道德的善存在于行动之中,善的目的只有通过“做”来实现,也只有以行为和结果来检验善(27)。可见,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极为强调“善”的实践性,甚至到了只关注实践以及功利的程度,这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对于理解实践理性之于善意原则的重要性,也是可资借鉴的。 在国际法学界,随着对作为正式国际法渊源的条约的关注,善意原则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叶,被严格限定于条约法的范围内,不再被作为一般国际法原则讨论。只有到《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将一般法律原则列入正式国际法渊源之后,善意原则由于被认为是一般法律原则,才重新得到重视。但是,将善意界定为一般法律原则并非准确,而且,由于一般法律原则的尴尬地位,善意原则在国际法院没有得到适用,只有经由它推演出来的部分一般法律原则得到了一些用武之地。除此以外,对善意原则的研究,主要还是在条约法领域。 应该看到,“善意地行使权利”作为一项从善意原则中推演出来的一般法律原则,已经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一定运用。比如,“科孚海峡案”(Corfu Channel Case),(28)“在摩洛哥的美国国民权利案”(Rights of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Morocco),(29)“印度领土过境权案”(Right of Passage over Indian Territory Case)(30)等,其中,在“科孚海峡案”中,阿尔法瑞茨(Alvarez)法官声称,关于权利滥用的规则是善意的一个方面,而且如今该规则已经在实在法中找到了位置。同时,另一项从善意原则中推演出来的一般法律原则“禁反言”也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运用。比如“隆端寺案”(The Temple of Preach Vihear Case)(31)、“北海大陆架案”(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32)等。 作为自然法学派的代表,菲德罗斯非常重视善意。他认为,善意是国际条约的基础;善意限定国际法上的权利;善意是国际法上制裁的基础;各国对法律的道义上的承认也主要以善意为基础。菲德罗斯因而归纳说,全部国际往来建筑在诚实和信用上,如果无视善意,那么实在国际法的全部建筑物就会崩溃(33)。 郑斌认为善意这一范畴是难以被界定而只能被列举的。他指出,调整国际关系的善意原则规范国家权利的行使,只要将善意原则适用于权利的行使,就存在关于权利滥用的一般规则或理论,而且这一规则或理论是为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所认定的。他论证说,条约与善意原则紧密相连,即便不说是条约建立在善意的基础之上,也可以说是善意原则从条约的制订开始到失效为止都调整着条约关系。他还举出了一些适用善意原则的其他后果,包括:政策变更的通知义务、维持现状的义务、禁反言、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益、欺诈无效(34)。 科勒尔相信,善意原则一般性地适用于国际关系,包括条约、法律权利的行使、平等法律权利的冲突、法律上有疑问或难以界定的义务等方面,因而即使不存在有拘束力的条约,善意原则也是需要被遵守的。科勒尔同时指出,只有当存在一项法律义务,且该义务在法律(实在法)上不能被准确界定时,国际法庭才会援用善意原则;法律(实在法)体系越发达,适用这一原则的空间就越小。科勒尔还尝试为善意做出定义。他说,国家法上的善意原则是一项基本原则,与诚实、公平和理性密切相关的“约定必须遵守”以及其他法律规则都从中派生而来,在任何特定时候,这些法律规则的适用都由当时在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主要的诚实、公平和理性标准决定(35)。 帕尼森相信,善意即便不是最基本的、压倒一切的国际法则(因其不是强行法),也是各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国际条约关系中遵循善意的义务见诸很多国际协议之中。他还指出,善意原则的必要推论包括:公平、禁反言与默认、约定必须遵守(已成为习惯法)、禁止滥用法律(36)。 而即便是非正式渊源的国际“软法”,其得到遵守也与善意和实践理性不无关系。正如何志鹏所指出的,国际软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实践中却能得到有效遵守。国际软法的内在理性是国际软法产生效力的客观原因,国际主体的行为理性是国际软法得以遵守的主观原因(37)。 总的来说,在近代及其以前的时期,对善意原则的讨论比较热烈。到了现代,由于善意原则已经成为实在法的基本价值与原则,因而学者多转而关注善意原则的实际运用,而对原则本身的探讨则减少了。对善意原则的理解,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善”、“诚实”等概念的含义,有的学者把它们等同起来,善意原则因而就等于诚信原则。尽管多数国际法学者都在条约的领域内讨论善意原则,这时也可以说它是诚信原则;但仍然有学者指出,善意原则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这时它就不仅仅包括诚信原则。无论如何,在现代,描述善意本质的基本要素逐渐被揭示出来。善意原则派生的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法上得到了一定的运用,善意原则对国际法的重要性被普遍认识到,“约定必须遵守”已经深入人心。 五、善意原则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法律文化史上,也存在类似于西方善意观的遗迹和残片。 老子认为“上善若水”,因为“水善利万物又不争”。他主张“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38)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因此要“言而有信”,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9)。儒家学者进一步阐释道:“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君子诚之为贵”(40)。孟子说:“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41)司马迁推崇“乐善而好施”(42)。 中国文化中的善实际上不仅仅包括诚实信用,也不仅仅意味着合理需求,而且要求社会主体的谦让与付出,这才算得上《大学》所倡导的“至善”,正所谓“守约而博施者,善道也”(43)。老子主张的“上善”,孟子主张的“与人为善”以及司马迁主张的“乐善好施”,莫不是这个意思。 可见,中国古代的善意观不属于西方那样的法学范畴,而主要是道德范畴;即便是其中的诚信方面,也主要是与个人道德修为有关,而非私法原则。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的发展之后,一方面,对善意的直接理论渊源以及描述善意本质的基本要素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对善意的特点有一些较为准确的论述,善意原则的组成部分被越来越多地落实到司法实践上,“约定必须遵守”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对善意的性质与内容、善意与诚信之间关系的理解仍然普遍存在偏差,这使得善意原则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这表明,在当代,善意观发生飞跃性的质变,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六、对善意原则的扬弃 上述种种关于善意原则的理论渊源中,有以下因素是需要继承的:“与人为善”,善意的来源、界定及其理性基础,实践理性的概念;善意与诚信的联系,善意的基本内容——约定必须遵守;善意的界限和限制,善意与其他自然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善意所衍生的一般法律原则对国际关系的补充适用。 有以下因素是需要被扬弃的:善意与诚信的等同;善意与道德的等同;善意被认为仅仅是实在法的原则或价值;善意被认为是一般法律原则;善意被认为无法界定;善意与其他自然法基本原则关系的含混。 1.与人为善 正如格老秀斯所指出的,善意乃是源于正义。正义就是各得其所,扬善抑恶,不难发现,善意原则实际上直接出自正义原则的“扬善”要求。 既然善就是满足合理需求,那么,在实践中贯彻善意原则,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与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意思,就是在合理的限度内作为或不作为,包括提出、满足合理需求或者拒绝不合理需求,从而有助于正义的实现。 概言之,与人为善是善意原则的核心内容,它要求在实践中维护与满足合理需求并拒绝不合理需求。比如,一项无因管理行为,一方面维护了被管理人的权益,另一方面以债权的形式保障了无因管理人提出的合理的费用要求,这些都是与人为善的体现。再如,当电子商务刚刚兴起的时候,各国的有关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有的人利用这些法律漏洞,将知名企业的商号或商标抢注为域名,再高价叫卖,这显然是违背善意原则的行为。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通过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或电子商务法),制止恶意的抢注行为,则是与人为善的体现。又如,2002年,美国政府仅凭主观好恶,就将毫无关联的三个国家指责为“邪恶轴心”的行为,是违反善意原则的。因为,只有经过有凭有据的公正裁判,才能够合理地确认有关主体的法律状态。由此,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假定有关主体没有实行违反法律的行为,才是与人为善的。 2.诚实信用 诚实信用,简称诚信,是指社会主体之间诚实地履行约定。诚实信用是善意原则的主要内容。鉴于诚信与善意被混淆的情况非常严重,本文对诚实信用的论述将在其与善意原则的比较中展开。 首先,在词源上,善意与诚信并不是等同的。 从词源上来看,bona fides译为善意是最准确的。因为bona相当于英语的good,有“善”、“好”的意思,尤其在哲学上good仅指“善”(44);fides则相当于英语的faith,有“信义”、“诚意”的意思。两个拉丁文合起来,可以译为“善意”、“良信”,但后一种说法几乎未被使用过,而前一种说法在法学界则具有相当范围的认同度,故而应当被采用。博德曼指出,西方文明中的善意(good faith)理念,正是从罗马的善意(bona fides)概念中移植过来的(45)。两相对照,更加表明bona fides最准确的意义应该是“善意”。即便是将bona fides这个词作为“诚信”使用的徐国栋先生,也指出该词准确的译法应该是“良信”,而这其实是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善意”的同义词。并且,拉丁文中有表示诚实的词honestum,如果真的想表示“诚信”而不是“善意”,那么应该表述为honestum fides而不是bona fides。更何况,与bona fides对应的拉丁文是malus fides,意为“恶意”,而“恶意”所准确对应的,显然应当是“善意”而不是“诚信”。当然,如果采用西塞罗对诚实的界定,那么诚实就无所不包,也就可以说,善意就是诚信了。但是这种宽泛的界定是少见的,尤其是今天,诚实所指的仅仅是真实与不欺瞒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说善意就是诚信,则是缩小了善意原则的内涵与外延。 其次,在内容上,善意涵盖的范围比诚信要广。 诚信的作用范围限于协议关系,不论是民事合同、行政合同还是国际条约,不论是书面协议、口头协议还是要式协议,也不论是单务合同、双务合同还是诺成合同,只要有协议,就应当诚实地履行。比如,要约一旦被接受,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就应当真实地履行合同,对因自己的过错造成违约的,有关当事人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再如,一项单方面的馈赠协议,尽管在协议生效(一般是交付生效)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协议,然而一旦协议生效,赠与人就不得再反悔。又如,流行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控辩交易制度的要旨,就是一旦双方达成协议,被告就将承认协议中约定的罪行,而控方也不再寻求就同一案件对被告起诉其他罪行或者课以更重的刑罚。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控辩双方是不平等的当事人,然而一旦达成协议,也要承担诚实履行的义务。由此可见,在流行以协议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现代社会,诚实信用确实是与人为善的主要内容所在,诚信原则确实涵盖了善意原则的主要范围。 在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诚信原则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因为归根结底,一切正式的实在国际法渊源都是国家合意的产物,国际条约自不必说,国际习惯也被认为是国家间的默示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仅在实在国际法的语境之下,那么所谓“善意履行国际义务”中的“善意”就单指“诚信”。 然而,说诚信是善意的主要内容,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善意的全部内容。 善意要求对所有的社会主体都做到与人为善,无论它们之间有没有协议,只要是合理的需求,就要维护与满足,只要是不合理的需求,就要拒绝。试想,如果没有协议的约束,没有信义的规范,是否就可以置合理需求于不顾而任意妄为呢?显然,回答是否定的。与人为善尽管常常通过协议来实现,但也不排除其他方式实现的可能。 由此可见,仅仅有诚信原则,是不足以在实践中贯彻正义原则的,因为很多权利义务的产生与发展不以协议的存在为前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民法上除了有合同之债以外,还存在无因管理之债制度、不当得利之债等制度;在刑法上则大量存在“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保障被告人合理权益的制度;而众所周知,宪法上的公民权利与义务是不得以协议的方式来处分的。在国际法上,《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6款之所以规定,“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也是为了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更合理地调整国际关系。 应该看到,在非平等主体之间通过协议来约定权利义务的情况毕竟不多,即便有,也只能在法律允许的基础上有限地这样做。对于这一类社会关系,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因而必须依据更广泛的善意原则来调整之。这种情况下的与人为善,主要是指,上位主体要满足下位主体的合理要求,下位主体要配合上位主体的合理管理。比如,公民为了表达某种合理意见,可以进行游行示威,有关部门应当准许;但同时,公民在游行时要服从国家主管部门的合理管理。再如,实在国际法虽然是国家之间的合意,一般不涉及国家与其所属国民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可以任意地侵犯本国国民的人权或者非人道地对待国民,与人为善要求国家合理地对待其国民。目前,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穿透了国家绝对主权的面纱,倡导国家合理地对待国民,正是善意原则在国际法上的体现。20世纪末国际社会对当时采取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实行了综合制裁与禁运,尽管缺乏条约法与习惯法的依据,但却是符合善意原则的做法。 可见,诚信只是善意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善意原则而言,与人为善是适用于所有社会关系的,诚实信用则专门适用于通过协议产生的社会关系。 同时,诚信原则是从善意原则中推演出来的一般法律原则。 与人为善,落实到具有协议关系的社会主体之间,主要就是要讲诚实、守信用。可见,诚信是善意的应有之义。无论是在公民之间的协议中还是在国家之间的协议中,诚实信用都是与人为善的具体表现,其主旨就是为了维护与满足协议主体之间的合理需求并拒绝不合理需求。目前,诚信原则已经成为各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价值,各国合同法上也存在很多保障诚信原则的具体规定,这体现了一般法律原则对实在法的转化作用。同样的道理,在实在国际法领域,我们所说的“善意”原则其实就是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诚信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国际法学者把“善意”视为一般法律原则,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无论是《联合国宪章》第2条的规定,还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的规定,其中的“善意”都主要是在条约的范畴之内起作用的,这实际上就是“诚信”。并且,诚信原则被转化为实在国际法的情况也很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很多具体规定,比如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第31条)、关于欺诈与贿赂的规定(第49条)、关于强迫的规定(第51条和第52条)、关于意外履行不能的规定(第61条)等,都是诚信原则的具体转化与展开。 最后,诚信原则以“约定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为基本内容。 前已述及,诚信原则专门适用于有协议的社会主体之间,而对协议来说,“约定必须遵守”是贯穿始终的基本因素。没有它,就没有有效的协议:订约时,它是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履约时,它是当事人的行事标准;违约时,它是损害赔偿的依据。当然,诚信原则还包括其他内容,但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约定必须遵守”展开的。比如,关于订立协议的要件的规范,无非是为了防止当事人以约定不存在或无效为理由,破坏“约定必须遵守”。再如,关于解释协议的方法的规范,无非是为了澄清协议的真实内容,保障“约定必须遵守”。 科勒尔所作的罗马法学家将“约定必须遵守”扩充为诚信原则的言论,不应当被理解为诚信原则是从“约定必须遵守”中演绎出来的,而应该说诚信原则是从“约定必须遵守”及其适用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也就是说,诚信原则可能是先被认识到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再逐步被全面认识的,因而“约定必须遵守”是包括在诚信之内的。上面提及的很多学者都指出,“约定必须遵守”是以诚信(善意)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约定必须遵守”是诚信原则的必然要求。 总之,诚实信用,是指社会主体之间诚实地履行约定。它是善意原则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善意的全部内容,它是从善意原则中推演出来的一般法律原则。诚信原则以“约定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为基本内容。 3.实践理性 笔者认为,正义原则是一种积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公平原则是一种消极的利益与价值调和,平等原则是一种形式要求。那么,除了具有自然法基本原则的共性之外,善意原则的特性是什么呢? 前面已经提到,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概念对阐明这一问题非常有价值,本文认为,可以以此概念来归纳善意原则的特性。当然,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已经对其作出了必要的扬弃。扬弃后的“实践理性”概念,不是依附于纯粹理性的某种一般理性,而是指一种着眼于社会主体实践的理性。 如果说,正义、公平、平等三大原则是一种偏重于价值判断的理性,主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话;那么,善意原则就是一种偏重于实践的理性,主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善意原则是在符合上述三大原则的基础上,直接从正义原则的一部分出发,着手构建在实践中如何扬善的问题。 显然,在一个体系健全的自然法基本原则之中,仅仅有偏重于指导社会主体思想的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偏重于指导社会主体行为的原则。尽管这两者实际上是相通的,其作用也是彼此交叉的;但是,任何原则都有且应该有其主要适用的领域。在知道了什么是正义、公平与平等之后,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在实践中贯彻它们。善意原则告诉我们,不要仅仅坐而论道,还要切实地做到与人为善、诚实信用;不要仅仅关注理论中的理性,还要关注实践中的理性。 实际上,一个健全的自然法基本原则体系,应当对社会关系有全面的涵盖能力;也只有既含有价值判断的理性又含有实践理性的理性,才算得上是全面的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只有积极调和手段、消极调和手段、形式要求、实践理性一起作用,才能保障社会主体正确地认识与贯彻社会规律并推动社会朝着符合规律的方向发展。否则,既然从正义原则可以推出其他所有的自然法基本原则,那只要这一项岂不就足够了? 可见,善意原则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以正义、公平、平等三大原则为基础,从实践的角度直接阐发正义的扬善要求。 因此,善意,就是与人为善,诚实信用,它是一种实践理性。 4.善意与其他范畴的关系 善意与其他自然法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一方面,善意原则的界定依赖于其他基本原则,正义是善意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善意原则必须遵循正义、公平、平等这三项原则,实践理性必须符合价值判断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的学者认为善意是无法界定的,这是没有了解自然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结果,其实,在认识前三项自然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就可以正确地界定善意原则。同时,这也意味着善意原则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其界限与限制的。善意只是实践理性的一种,它不能囊括所有的实践理性,更不能代替价值判断理性。因此,在实在国际法上,善意只能成为基本原则之一,而不能代替最基本的原则——主权平等。同样的道理,诚信原则只能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成为全部国内法的基本原则。 当与前三项自然法基本原则发生冲突时,善意原则就要退而求其次。比如,善意原则要求真实履行合同,但是如果发生天灾导致不能履行,那么根据公平原则,就不必真实履行,此时善意原则所能够要求的,仅仅是合理地、及时地通知而已。这就是体现在各国民法上的“不可抗力”规范。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2条所规定的“情势变更”(rebus sic stantibus),也是依据公平原则,在特定条件下免除真实履行条约义务的典型例子。再如,国家依据善意原则,应当合理地管理国民,满足其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但是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为了实现正义,国家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并限制上述需求。 另一方面,正义、公平、平等这三项原则需要善意原则的保障。价值判断理性需要落实到实践理性,若没有一个实践中的行为指南,那么正义的所有要求就都将成为空谈。正是因为有“诚实信用”的作用,合同当事人才能够“各得其所”;正是因为有“与人为善”的作用,每个人作为“人”所应满足的合理需求才被强调,国际人权的主张才能深入人心。 此外,善意作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它可以转化为实在法的价值、实在法原则以及道德,但是这不能掩盖其自然法的属性,这也是本文所一再强调的。其实,目前得到转化的,主要是隶属于善意的诚信原则。正如格老秀斯所指出的,善意原则还没有被充分地转化为实在法,因此,应当进一步促进这种转化,并充分发挥善意原则的指导、评价作用。可能正是因为目前主要是诚信原则在实在法上起作用,因而善意往往被等同于诚信;也可能因为《国际法院规约》只给了抽象法以一条出路——一般法律原则,因而善意往往被等认为是一般法律原则,但这确实是不准确的。善意是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它不像一般法律原则那样,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直接适用于国际关系,它是高度抽象的,它只起指导、评价、转化的间接作用。而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国际法院适用的一些与善意有关的原则,都是从善意中推演出来的一般法律原则,而不是善意原则本身。 总之,善意是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与人为善,诚实信用,它是一种实践理性。 注释: ①《牛津法律大辞典》(第5版),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 ②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5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79,pp.160. ③梁慧星:《诚信原则与漏洞补充》,载《民商法论丛》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61页。 ④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⑤(20)(35)J F O' Conner:"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Law",Dartmonth Publishing Co Ltd,1991,pp.23,pp.66,pp.107-124. ⑥J F O' Conner:"Good Faith in International Law",Dartmonth Publishing Co Ltd,1990,pp.11; Charles Fried:"Contract as Promise,A Theory of Contractual Obligation",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74. ⑦"The Republic of Plato",Cornford translat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5,pp.212-220. ⑧"The Law of Plato",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628d. ⑨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Penguin Books,1976,pp.63. ⑩何良安:《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差别》,《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1)Cicero:"On Moral Ends',Oxf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75、pp.126. (12)"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J B Moyle translat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13,pp.3. (13)St 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Oxf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23,2006,pp.5-7、pp.15、pp.153-155. (14)Francisco Suarez:"Selections from Three Work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4,pp.231-265. (15)Alberico Gentili:"De Legationibus Libri Tres",Gordon J Laing translat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pp.96,pp.111-121,pp.162. (16)Alberieo Gentili:"De Jure Belli Libri Tres",John C Rolfe translat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33,pp.145-150、pp.360-366、pp.427-433. (17)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Francis W Kelsey Translat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p.13,pp.324、pp.409-410、pp.414-429、pp.613-622、pp.862. (18)Thomas Hobbes:"On the Citizen",Oxf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43-44. (19)Samuel Pufendorf:"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Oxford:Clarendon Press,1934,Vol.3,pp.402-428. (21)Christian Wolff:"Jus Gentium Methodo Scientifica Pertractatum",Joeph H Drake translat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34,pp.194-222、pp.414. (22)Emer de Vattel,Le droit des gens:"ou Principles de la loi naturelle appliqués a In conduite et aux affaires des nations et des souverains",Charles G.Fenwick translated,Washionton: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1916,p.188、pp.161-175. (23)See John Rawls:"Justice as Fairness",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9、pp.58-61、pp.116、pp.141-142. (24)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nd edition,2011,pp.86-89、pp.100-126、pp.154、pp.290. (25)关于实践理性概念在法哲学中的接受与运用情况,参见葛洪义著:《法与实践理性》,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2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14页。 (27)杨寿堪:《杜威哲学的改造与现代哲学的转向》,《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28)ICJ Reports,1949,p.4. (29)ICJ Reports,1952,p.176. (30)ICJ Reports,1960,p.6. (31)ICJ Reports,1962,p.6. (32)ICJ Reports,1969,p.26. (33)菲德罗斯等著:《国际法》,李浩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77-778页。 (34)Bin Cheng:"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Oxf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6,pp.121,pp.137-158. (36)Marion Panizzon:"Good Faith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WTO",Oxford:Hart Publishing,2006,pp.11-13,pp.20-30. (37)何志鹏、尚杰:《国际软法的效力、局限及完善》,《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38)《老子》第八章。 (39)《论语·为政》,《论语·学而》,《论语·子路》。 (40)《礼记·大学》,《礼记·中庸》。 (41)《孟子·公孙丑上》。 (42)《史记·乐书二》。 (43)《孟子·尽心下》。 (44)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416页。 (45)David J Bederman:"International Law in Antiquity",Oxf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