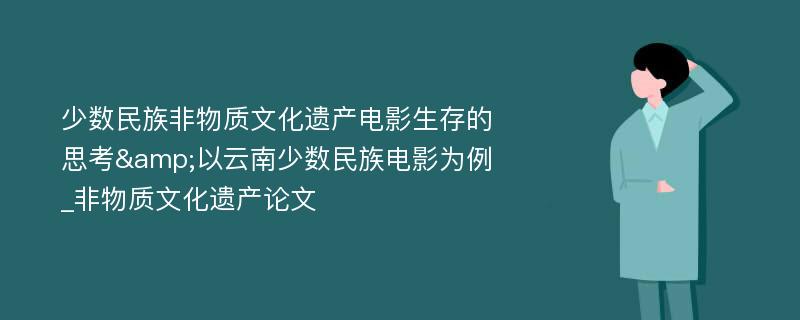
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影化生存之思——以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电影论文,云南论文,为例论文,文化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3)02-0066-0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以此类推,有研究者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支,认为它是指“各个少数民族人民世代相承、与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传统文化实践、表演、知识、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场所或其他文化空间”[2]。可以说,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中积淀而形成的民族精神,包含了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少数民族的灵魂”[3]。所谓“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影化生存”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它主要是指以电影为媒介保存下来的那些活态遗产项目,是各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认、保护与传播的重要手段。其次,它还指那些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为创作要素的电影作品,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本文主要从民族文化传播的角度,以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切入点,就电影这一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一、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影化生存方式
云南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云南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方面归功于政策与制度的保障,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与文化、民族工作各部门之间的密切协作,还有一点不容小觑的是,以云南少数民族为表现区间和主要内容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五朵金花》《阿诗玛》《青春祭》《孔雀公主》《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碧罗雪山》等,不仅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形象和边疆生活风貌,通过电影重塑了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更重要的是,这些影片还折射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如果按照电影的类别加以区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参与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非虚构型
非虚构型又可称为纪实型,即以非虚构的手段进行拍摄,将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呈现在影片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满足当时政治需要,调查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由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合作,于1957~1966年间拍摄了22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后又被称为“民族志电影”)①。这批民族志电影中,以云南少数民族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有七部:《佧佤族》《苦聪人》《独龙族》《景颇族》《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它们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云南佤族、拉祜族、独龙族、景颇族、傣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状态,包括生产、节庆、婚葬、建筑、文化艺术等,成为后人研究这些族群的珍贵影像资料。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云南电视台等专业影视机构又拍摄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4]。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哈尼之歌》《纳西族和东巴文化》《傈僳族风情》、云南电视台郝跃骏的《山洞里的村庄》和《最后的马帮》、刘晓津的《关索戏》和《田丰和传习馆》、谭乐水的《巴卡老寨》、昆明电视台周岳军的《阿鲁兄弟》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影片中既有展现傣族孔雀舞、泼水节,佤族木鼓舞,哈尼族民歌,纳西族东巴画、东巴造纸技艺、关索戏,景颇族目瑙纵歌和傈僳族刀杆节,独龙族卡雀哇节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有呈现独龙江乡、瑞丽市、陇川县、西盟县、永宁温泉村、大等喊村、丙中洛村、奔子栏村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场所和文化空间的,它们用真实记录的方式,为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类影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二)虚构型
虚构型主要是指以虚构的手段(即故事片)进行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根据影片内容和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运用的具体情况,又可将之细分为“再现型”和“表现型”两种。
“再现型”指的是用视听语言再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内容或主题围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二次创作”的影片。最有代表性的如《阿诗玛》《孔雀公主》《婼玛的十七岁》《碧罗雪山》等。《阿诗玛》作为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影片本身就取材自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片中展现的彝族火把节、彝族刺绣、大三弦舞等,同样是国家级或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拍摄于1982年的《孔雀公主》,是根据傣族民间传说《召树屯与楠木诺娜》改编的,傣族叙事长诗《召树屯与楠木诺娜》200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影片中还展现了傣族泼水节、孔雀舞、象脚鼓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章家瑞导演的《婼玛的十七岁》,以哈尼族女孩婼玛的青春故事为主线,通过展现哈尼族梯田农耕礼俗、哈尼族栽秧山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凸显民族传统文化对人物性格心理成长所起的作用。荣获201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三项大奖的《碧罗雪山》,则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马吉乡古当村(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外景地,展现了位于碧罗雪山腹地的傈僳族传统民居建筑、民族服饰、民族歌舞、婚俗等传统民族文化风貌,并且探讨了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些影片都是依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二次创作”的典范。
“表现型”指的是创造性地运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作为影片的点缀,用电影语言表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种类型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拘泥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活态性,只是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和趣味性。如《五朵金花》《芦笙恋歌》《花腰新娘》等都属于这一类影片。《五朵金花》中表现的大理白族三月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影片并没有完全真实地记录三月街的各种民族文化习俗和活动,只是借三月街这样一个白族传统节日,安排了男女主人公的相识和相恋,引出一个充满喜剧性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芦笙恋歌》中拉祜族的芦笙舞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影片只是将芦笙作为影片的一个重要道具,将芦笙舞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加以呈现,影片中的主题曲是经过再创作的流行歌曲,并没有按照真正的拉祜族音乐来进行演绎。《花腰新娘》则着重表现了彝族海菜腔、彝族烟盒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种表现并不是原样照搬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而是进行了现代化的加工和润色,使影片更具视听娱乐和享受。上述电影作品中,“影片创作人员将‘非遗’元素嫁接到影片故事叙事的时空中,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成为构建影片文化身份、提升影片文化内涵、促进影片情景叙事,乃至吸引观众的重要‘文化帮手’”[5]。这些影片注重的是影片的表现性和情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真正的“文化目的”,“它往往只是把文化拿来,借以进行它的情节”[6]。因此,这些影片通常都比较赏心悦目,是“非遗”与电影艺术“嫁接”的产物。
二、电影创作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影响
客观地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其弊端。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电影创作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影响
首先,电影的纪实性和复制性有助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保存。按照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的观点,电影是对“物质现实的复原”,其功能是记录和揭示我们周围的世界[7]。姑且不论他对电影本性理解上的偏颇,单就电影的功能而言,克拉考尔的理论强调了电影最主要的功能之一——记录功能。而这恰恰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让观众看到了爱斯基摩人已经失传的捕猎海豹和建造冰屋的过程,那么中国的电影人则通过《佧佤族》《景颇族》《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等民族志电影,让人们认识了50多年前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态。事实证明,时间愈久这些影片的价值愈发突出,它们已经成为无数国内外从事民族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第一手资料。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加速消亡的今天,运用电影手段进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显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其次,电影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参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弘扬。作为一种视听综合的艺术,电影具有传播的直观性、形象性和通俗性的特点,恰当运用电影参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就能最大效度地发挥电影的传播特性,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更多人所认识、了解、保护和利用。以《阿诗玛》和《孔雀公主》为例,正是因为两部影片对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和叙事长诗的成功改编,才使得“阿诗玛”、“召树屯和楠木诺娜”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借助影片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云南省成功地将叙事长诗《阿诗玛》和《召树屯和楠木诺娜》申请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过来又促进了彝族和傣族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继承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年轻人的参与,在当今这样一个以视觉文化占主导的时代,电影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再现和表现,将会激发和调动“非遗”主体和客体的积极参与性,培养出一批热衷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众投身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事业中。
另外从电影创作本身而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为电影艺术提供创作的源泉、提升电影作品的民族文化品格和文化内涵。《五朵金花》《阿诗玛》等早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正是因为生动地展现了大理白族和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独特的民族习俗,用动人的少数民族歌舞点缀全片,才成为“十七年”电影创作的经典;《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正是借助富有特色的哈尼族和花腰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表现,唤起了一定群体的“文化记忆”,赢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云的南方》《碧罗雪山》是以纳西族、傈僳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创作灵感,赋予了影片深刻的民族文化反思精神和较高的思想文化内涵,而赢得学术界和创作界的一致认可。
(二)电影创作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极影响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作为媒介工具的电影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了项目的保存、传播与弘扬,但从电影的文化消费品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与整体性来看,电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利用也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弊端。”[5]具体来看,这种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电影艺术的真实性不等于客观真实,它是一种根植于现实本质之上的审美化的真实。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是民族志电影,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人类学片也是一种建构的‘事实’,或是一种展现”[8]。因此,电影创作的主观性与艺术加工,有可能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那批民族志电影,虽然在拍摄时非常强调科学记录的真实性,但因为受到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指导思想的影响,影片仍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影片都配有大量解说词,不用同期声。而且据参与拍摄的杨光海、徐志远等老摄影师回忆,在表现一些历史现象和社会问题时,他们用了故事片的拍摄方法,先写剧本,再找人来扮演②,因而这些影片没有能够做到对原始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图景的本真记录,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一手资料是有所损益的。更不用说“再现型”和“表现型”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为是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次创作”或“嫁接”使用,影片的故事性和艺术性往往会削弱文化记录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大部分影片难以承担建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基因库”的重任。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和整体性特点,但电影的时限性和文化消费属性不利于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电影拍摄会受到时空的限制,不可能无时无刻完整地记录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加之电影艺术是“蒙太奇”组接产生的艺术,它不可能完全按照现实生活本身的样子加以呈现,必然要经过剪辑进行二度创作。再加上电影与生俱来的文化消费属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在影片中应用时往往要服从于影片创作目的和观众审美需求。如电影《神秘的旅伴》和《山间铃响马帮来》中都有少数民族群众劳动生活的场面和载歌载舞的呈现,但这些苗族服饰、生活场景、婚恋场面的表现都只是“碎片化”的呈现,这些影片更像是穿着民族服装的政治剧,表现的是少数民族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展生产建设,与土匪特务作斗争的主题,不可能真正反映出少数民族群体社会生活生产的活态性和整体性。
第三,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电影创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观赏心理和认同机制,影片中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的不当改编和创新,易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读和误认。如张艺谋导演的《千里走单骑》因为将贵州的“安顺地戏”(影片中称“云南面具戏”)移植到了云南丽江,而使大批观众误认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来自云南,还因此被告上了法庭[9],即便是《阿诗玛》这样一部改编相当成功的经典之作,由于掺杂了大量的移植、改编、删减、拼接等创作手段,经典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模式化和定型化的过程,这样的传播一方面扩大了“阿诗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同时也会使原本丰富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变得单一而刻板化。而这样的经典文本的广泛传播,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民间叙事传统的鲜活本真,对那些不了解撒尼文化的“他者”而言,可能会存在某些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误读,从而发生非本土化或去本土化的误认[10]。
三、电影参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构想与建议
从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今,全国已经有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其中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约占1/3。但与如火如荼的“非遗”项目申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链条正在中断,面临着断代的困境。目前,影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影视工作者走向田野,承担起了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播的重任。但如何才能切实地加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真正有效而有益地将“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资本”,对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1.保护和利用的统一。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资源流失严重,传承后继乏人,保护工作日益严峻。有学者指出,要真正有效地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把我们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的传统文化等等文化资源转变为一种文化资本,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发展的‘文化生态’”[12]。这里说的“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与此同时,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13]。影视艺术作品具有与生俱来的文化消费性和商品性,以电影化方式存在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可以转变为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但在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资本时,必须注意保护和利用的统一。即保护是第一位的,不能为了项目的经济效益而贬损了其文化价值。电影工作者为增强影片故事性、观赏性和艺术性而依托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故事建构”和“二次创作”是可以的,但在创作时还须持谨慎态度,应严格遵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遵循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避免将错误的文化信息和零散化的文化碎片呈现给观众。
2.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着的文化形态,是有生命的文化体系,是具有体系结构和丰富内涵的文化“生命”体。所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应注意其“活态性”和“整体性”。当运用影视手段加以呈现时,应遵循真实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这就要求影视创作者将科学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相结合,在不违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前提下,尽量保存其完整性。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时,不能曲解和破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应做到内容真实和思想真实。在这方面,“非遗”题材的民族志电影做得较好,但这类影片往往为了呈现项目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又忽略了电影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因此,在进行“非遗”题材电影创作时,创作者应明确影片拍摄的目的和意义,如果是作为科学研究和资料性质的影片,就应该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谨性,艺术性的要求次之;但如果是作为商业片或艺术片,就应该在尊重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同时,进行适度的艺术加工和再创作,凸显其艺术价值。在这方面,新世纪以来的一些少数民族电影如《季风中的马》《静静的玛尼石》《碧罗雪山》《斯琴杭茹》等做得较好,实现了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3.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传承史上的“明珠”,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它是中国各少数民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我国现已成功申报36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其中不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运用影视媒介参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能促进世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但必须注意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这里指的是影片要体现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为价值取向,选材上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记录,艺术上体现民族的情感方式和对民族艺术传统的开掘,制作上达到高水准的视听效果。
综上,笔者以为,电影工作者与民族文化工作者、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深入交流和紧密协作,深入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和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之乡进行田野调查和实地拍摄,将有助于以上三个统一的实现。《碧罗雪山》的导演刘杰在影片筹备拍摄之前,就曾多次深入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最终选择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来参与演出拍摄,并且用傈僳族母语作为影片的主要语言,使影片具有了朴实、自然的原生态审美叙事特点,透射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当然,要真正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为具有文化内核的“文化资产”,使之有效形成文化品牌,最终实现“以文养文,以文兴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道路,这不仅需要文化传播工作者的努力,还需要政府、学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收稿日期:2013-01-23
注释:
①本数据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编,《影视人类学论文、译文和资料选编》,1995年,第58页;其他的论文中具体数字略有不同。
②笔者在2010年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人类学记录影像年度论坛”上对杨光海、徐志远老师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