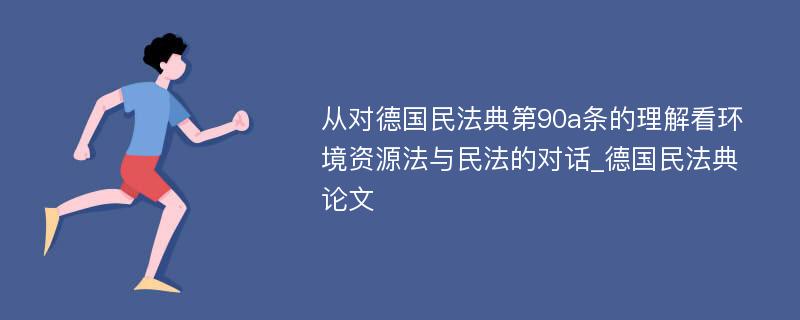
从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解展开环境资源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法典论文,德国论文,法学论文,民法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2.6 D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32(2006)04-0001-15
一、引言
近几年,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的一些常务理事所在单位相继举办了以环境资源法学为主、兼与其他部门法学进行共同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学术研讨会,影响较大的有福州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东南法学论坛、清华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举办的环境法论坛。同时,一些民法学者开始积极研究环境资源保护和环境资源法中的一些问题,期望对传统民法进行修正以适应当代环境保护的需要,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比较有影响的有徐国栋教授的绿色民法典[1]、崔建远教授的自然资源准物权论[2]、杨立新教授的法律物格论等。例如,杨立新教授在清华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举办的环境法论坛上,作了《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的讲座,提出了“法律物格”的思想。他说:“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实际上是我想把民法上的物加以类型化,我本人反对赋予动物人格权的思想,因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权,它违反了民法的一些基本原理,破坏民法社会的基本秩序;反过来,我同意从物格的角度来把物加以类型化,即把物分成几个不同的格。从而把那些有生命的物放到民法对物的最高保护地位,让民法对它们作出一些特殊的规定,防止人们滥用对物的所有权,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的非法损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物”,保护动物。所以,通过以物格制度对动物等物加以保护,避免人格权在物的领域中不恰当的行使所有权损害动物的福利,同时也不会违反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不会与民法社会及市民社会的基本秩序相冲突。”[3]
笔者注意到,首先,杨教授反对赋予动物以人格权,是“因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权,它违反了民法的一些基本原理,破坏民法社会的基本秩序”,他并没有说“因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权,它违反了环境资源法的一些基本原理,破坏环境资源法社会的基本秩序”,也就是说,他是从传统民法的基本原理和民法秩序来对待动物权利问题,他没有论及行政法、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理和行政法、环境资源法社会的基本秩序。其次,他说:“我同意从物格的角度来把物加以类型化,即把物分成几个不同的格。从而把那些有生命的物放到民法对物的最高保护地位,让民法对它们作出一些特殊的规定,防止人们滥用对物的所有权,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的非法损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物’,保护动物。所以,通过物格制度对动物等物加以保护,避免人格权在物的领域中不恰当的行使所有权损害动物的福利,同时也不会违反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不会与民法社会及市民社会的基本秩序相冲突。”[3]这种思想在民法学界是非常宝贵的,即他承认动物在法律中的地位(被法律保护的“保护地位”),他认为民法不仅要保护人,还要保护动物,不仅承认人的福利和利益,而且承认动物的利益或福利;防止人们滥用对物的所有权,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人的利益,也是“最大限度地保护‘物’,保护动物”。特别可贵的是,他之所以设置物格制度,是为了对动物等物加以保护,是为了“避免人格权在物的领域中不恰当的行使所有权损害动物的福利”。这与我们某些民法学者的某些极端观点相比,显然具有很大的差别。某些民法学者认为,动物没有动物自己的利益、没有动物自己的福利,民法的基本出发点仅仅是为了人,不可能既为人也为动物。另外,他认可“为环境伦理学保护动物的先进学说”[3],主张“民事权利主体对动物行使权利时,应当尊重动物的生存、生命、健康,不得以违背人道主义的态度残酷地对待动物”,并建议对动物设立保护人、设立福利基金,这与某些民法学者根本否认环境伦理学先进性以及“对动物谈不上尊重”、“对动物无所谓残酷与人道”的人类沙文主义态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作为一个环境资源法学者,笔者十分注意和赞赏杨立新教授等民法学者与时俱进的精神和那些有利于维护环境资源法基本原理和建立环境资源法社会的基本秩序的见解。但是,对杨教授某些基于传统民法的陈见,本人则持保留态度。现对杨教授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如下:
二、环境资源法学和民法学学者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不同理解
在“人、物二分法”或“主、客二分法”范式约束下,传统德国民法一直将动物视为物、将人与动物的关系视为主体人与客体物的关系。在环境保护运动和保护动物的强大呼声和压力下,德国为了解决民法对动物保护不足的问题,制定了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门法律,在动物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环境资源法对传统民法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保护动物专门立法与传统民法的冲突,1990年8月20日修订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不得不作出重大革新:它将原《德国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编中的第二章“物”更名为“物,动物”;在第90a条中明确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4]。上述法律规定,立即引起了法学界特别是环境资源法学界与民法学界对动物法律地位及其有关法学理论问题的争论。笔者认为,这种争论对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对轻视和贬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观点的质疑
《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是民法(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变革,它宣布了民法的一种新理念,突破了现代民法的“人、物二分法”和“主、客二分法”,引起了全世界民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关注。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一向奉德国民法为榜样和渊源的我国民法学界,不少人对第90a条持轻视、贬低和反对态度,较少有民法学者对其持肯定、赞扬态度。民法学者杨立新教授在《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中谈到了他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看法,通观他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反应和理解可以发现:
1.杨教授认为第90a条主要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是向环保主义者让步的权宜之计。
他说,“在修改《德国民法典》时,执政的绿党就是主张环境保护的政党,如果民法典的修改一点也不接受环保主义者的主张,这样的修改很难通过”[3]。他显然没有看到和把握《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理论突破、创新、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没有注意一向固执民法传统理念、坚持民法神圣原则的德国民法学界为什么要接受环保主义者的主张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对德国民法典的重大变革或重要进步,仅仅从一时的权力斗争或“权宜之计”进行分析,而不从更深更广的环境资源问题、环境保护形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要求、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高度进行挖掘,未免有失偏颇。其实,《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新理念,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德国民法学与时俱进的精神的体现,是大陆法系民法学博大精深、永葆青春活力的体现。
2.杨教授虽然承认第90a条受到了某些新理论或新观点的影响,但仅仅局限于环境伦理学的影响。
他认为,“首先,《德国民法典》的这次制订,深受到环境伦理学的影响”,“同时,德国民法的修订也要反映当代社会的进步,将进步的思想吸收进民法典,环境伦理学保护动物的先进学说也要反映到民法典中”[3]。其实,《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诞生不仅仅受到环境伦理学的影响,也受到当代其他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环境学、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科学)的影响,它是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和创新的体现,是当代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环境学、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科学)与以笛卡尔的“主客二分化”为特征的现代科学(包括自然、人文、社会科学)长期斗争或论战的产物。现代科学证明,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具有人力无法支配、控制的能力和特性(包括具有生命活力、健康疾病、苦乐快感、思想感情、语言信息、意志、目的、利益、内在价值和社会性等),它们不是传统民法中人可以任意占有、支配和控制的“物”。
(二)对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是特殊物”的质疑
《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明确规定“动物不是物”,但杨立新教授却认为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是特殊物”。杨立新教授是这样表述的:“我个人认为,该条文是想表明动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而是一种特殊的物,这一结论可以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其他内容来分析。这一条文首先说‘动物不是物’;接下来,它规定:‘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把这一条文的其他内容联系起来分析,也就表明,它所说的含义是:动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是一种特殊的物,应以特殊的规则来规定它。例如环保法的相关规定。”[3]对这种理解,笔者提出质疑如下:
1.杨教授没有看到《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所做出的明确结论。
笔者认为,第90a条明确宣布或告诉人们的结论是:“动物不是物”,动物也不是人,动物既不是民法中的人,也不是民法中的物,动物就是动物。“动物不是物”是对传统民法理论中“人、物二分法”的突破,是对传统民法学中“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的创新,即新修订的《德国民法典》承认世界除了民法中的人与民法中的物之外,还存在着既不属于民法中的人也不属于民法中的物的其他东西,例如动物。无论是在德国法学界或任何一个客观对待法律条文的学者都知道,“动物不是物”这一法律条文或其法律含义是十分明确而肯定的,这就是《德国民法典》已经明确无误地认定“动物不是物”,至于某些学者出于自己的固有的观点或先验的观点,硬要将“动物不是物”解释为“动物不是物,但是动物是特殊物”,或者将“动物不是物”解释为“动物是人”,或者将“动物不是物”这一严肃的民法典中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理念解释为当代民法典中的“权宜之计”、“挂羊头卖狗肉”、“障眼法”,但这仅仅是个别人的解释或观点,而不是《德国民法典》中的本意。对于死抱着“主、客二分法”或“人、物二分法”的民法学者而言,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仅仅由人与物这两种东西组成,任何东西不是人就是物或者不是物就是人;当《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明确规定“动物不是物”时,他们“一是迷惑”,二是竭力将“动物不是物”这一明确而又违背其固有理念的法律规定进行“自圆其说”,其代表性解释之一就是“动物不是物,但动物是特殊物”。笔者钦佩这些学者对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理论中“人、物二分法”或“主、客二分法”的坚定信仰和忠贞不贰,但是笔者不得不指出:这种解释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会大大降低民法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人们会提出如下问题:既然法律明确规定“动物不是物”,你为什么又说“动物是特殊物”,“难道特殊物不是物吗”?
杨教授认为,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表明动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而是一种特殊的物”。但是,笔者横看、竖看、反复看第90a条,始终得不出“动物不是物,动物是特殊物”的结论。笔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的规定,具有如下重要含义:(1)它表明《德国民法典》改变了对动物的传统看法,即确认了“动物不是物”。传统民法中的物包括一般物、特殊物、有体物、无体物、抽象物等。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包括动物既不是一般物,也不是特殊物等含义。因此,《德国民法典》中关于“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的规定,不仅不能解释为“动物不是物,而是特殊物”,而且恰恰进一步明确地说明,“动物既不是物,也不是特殊物”。 (2)它表明《德国民法典》承认民法调整范围的有限性,说明《德国民法典》是实事求是的、是谦虚的。民法虽然博大精深,并且在保护动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民法和民法理论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无论是用传统民法及其理论还是用当代民法及其理论都很难完全包揽或独自完成保护动物的任务。所谓动物由特别法加以保护,主要是指动物由环境保护法加以保护,这给环境保护法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和用武之地。环境保护法是不同于民法的新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学是不同于民法学的一个新的法学分支,环境资源法有其更适用于保护动物的研究范式、调整机制、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环境保护法在保护动物方面具有民法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3)“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第90a条之所以采用“准用有关物的规定”这种措辞,这不仅不能说明动物是物或动物是特殊物,而且再次强调动物不是物。笔者理解第90a条上述规定的涵义是,如果环境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对动物保护做了规定,此时对动物保护不适用于民法有关物的保护的规定,而应该适用于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动物保护的规定;如果环境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对动物保护没有规定,则准用民法有关物的保护的规定。“准用”的本意就有“动物不是物”的含义,之所以“准用民法有关物的规定”是因为其他法律没有有关保护动物的规定,之所以“准用民法有关物的规定”而不是“适用民法有关物的规定”,也是因为“动物不是物”,如果“动物是物”则根本不需要“准用”。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准某”首先表示与某的区别,其次表示与某的相似,例如:行政法将行政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中行使的行政调解、裁决手段称之为“准司法权”,首先表示这种行政处理不是人民法院行使的司法权,其次表示这种行政处理权在某些方面与司法权有相似之处。解决跨国民事纠纷中的准据法,首先表示所选用的准据法不是国际条约法,其次表示准据法与处理跨国纠纷的国际条约法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4)将第90a条的规定解释为“动物不是物,动物是特殊物”在逻辑上说不通,是一种相互矛盾的悖论,对于具有明确性、刚性的法律条文特别是民法典而言,同时规定或包含“动物不是物,动物是特殊物”的相反含义是不可思议的。在人们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学中的物具有物质性、实在物的含义,世界由物组成,自然资源、环境要素和财产都是物,连人也可以看做物(如人物),物有不同的种类或类型,例如动物、植物、人物、大人物、小人物、死物、活物等。但是民法中的“物”是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的,民法中的物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自然科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物。(5)某些民法学者认为,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是“权宜之计”、“障眼法”,第90a条关于“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才是实质。笔者的结论恰恰相反,笔者认为,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是明确的、肯定的、刚性的、实质性的,第 90a条关于“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才是“权宜之计”。“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动物就是物或特殊物,更不能改变动物的动物属性或动物的法律地位,它仅仅意味着在处理与动物有关的问题时可以准用或权宜性地采用民法中有关物的规定。
2.杨教授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出发,提出的“法律物格”理论,是与“动物不是物”背道而驰的理论。
首先必须指出,笔者赞赏杨教授关于建立法律物格以加强动物保护的良苦用心,也赞成把民法上的物加以类型化的主张。但是,笔者很难同意将民法中的物泛化或无限制地扩大的倾向,即不同意将动物或其他生命体、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统统归之于物的主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不仅仅由民法中的人与物这两种实体构成,世界由民法中的人、民法中的物,以及既不是民法中的物也不是民法中的人的其他东西组成,其他东西包括动物或其他生命体、水和大气等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环境。《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已经勇敢地迈出了“动物不是物”的第一步,为什么杨教授还要坚持“动物是物或动物是特殊物”、还要坚持将动物纳入法律物格的主张呢?笔者认为,法律应该追求和维护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秩序,主张采用“法律地位”这一概念来表示人、物和其他东西在法律中的位置和作用。人格表示人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物格表示物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他东西的法律地位(如动物的法律地位)表示其他东西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谓法律物格,应该是指物在法律中的法律地位,民法中的物太多,应该将其进行分类,使不同的物在法律中有不同的法律地位,这是由物之所以不同于人的属性所决定的;但是“动物不是物”,因而将动物纳入“法律物格”是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当代民法概念背道而驰的理论。如果可以将“动物不是物”理解为“动物是特殊物”,也可以将人理解为“人是特殊物”。例如,马克思曾指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5](页167)那么,人、动物与物的界限就有可能会消失。
值得指出的是,关于动物不是民法中的物的观点一直是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民法和民法学是古老的,环境资源法和环境资源法学是年轻的,环境资源法和环境资源法学是在继承包括民法、民法学在内的其他部门法和部门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当代环境法兴起时,法学界曾经讨论过环境法和环境法学与包括民法和民法学在内的其他部门法和部门法学的关系,当时法学界 (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是将环境与民法中的物、自然资源与民法中的物相区别的。例如,美国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没有采用民法中物或财产的概念,而是直接采用自然环境的概念,自然环境包括人为环境或改造过的环境,“包括但不限于空气和水——包括海域、港湾、河口和淡水;陆地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森林、干地、湿地、山脉、城市、郊区和农村环境”。澳大利亚1979年的《环境规划与评估法》将环境定义为“影响人类、个人或人的社会群体之周围事物的所有方面”。在大陆法系国家,为了将环境资源法中的环境、资源与传统法律中的物、财产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日本公害对策法》(1967年)和日本《环境基本法》(1993年)第2条均规定:“本法所称‘生活环境’,是指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财产,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和植物,以及这些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韩国1978年《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系指作为自然状态的自然环境和与人类生存有密切关系的财产,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和植物,以及这些动植物所在的生存环境。”它们都将动植物以及动植物的生境与民法中的物(即财产)区别开来,环境资源法中的环境的某些要素或成分(如土地、森林)可以成为民商法中的财产,但环境还包括不一定属于财产即物的范围的动植物,以及大气、水流和海洋等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也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不仅环境资源法律或环境资源法学不主张将民法中的物或财产范围泛化,许多民法学者也反对“物的泛化”和“所有权的泛化”,有的民法学者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了人、物、财产和其他东西的概念。例如,曾世雄先生在《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指出,民法以生活资源为本位(权利仅仅是生活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仅仅是法律规定的部分内容),生活资源主要包括权利、法益和自由资源,权利是民法提供完整保护的资源,法益是民法提供局部保护的资源,自由资源是纳入民法范畴但却不为民法所保护或民法对其放任自流的特定资源(如公海、荒山之兽等)。法律上的主体,是指依法律规定,享有或负担生活资源变动效果之实体;法律上的主体起码应该包括权利的主体、法益的主体和自由资源的主体等三种;权利的主体并不等于法律主体。他强调:“法律上之主体,指依法之规定,得享有或负担生活资源变动效果之单位实体。从法律适用于何者之角度,即法律规定之适用对象,从生活资源变动之角度言,即变动效果归属之单位实体。生活资源之变动,有享有之一面,有涉及权利、法益,亦有涉及自由资源者,范围广泛”;而“权利(义务)之主体,虽然包容有权利面及义务面,但仅涉及生活资源中之权利,并不及于法益及自由资源”[6]。杨教授在论及徐国栋的《绿色民法典》时认为,“我个人认为如果民法典是绿色的话,那就是一个环保的民法典,但是如果一个民法典仅仅体现一个环保的特点,那么它就不是民法典,而是环保法。所以我不太赞成这种提法,但是我也没有写过文章反驳过。我认为人家有权利提出自己的主张,就像我有权利提出物格这样一种概念一样。当然,我认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当中要充分注重环保意识,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因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但如果把民法典仅仅体现一个‘绿色’,我觉得这就有一点偏了,因为环保并不是民法典的全部内容”[3]。笔者认为,制定绿色民法典并不意味着“环保是民法典的全部内容”或者是要将民法变为环保法,而是指民法典“要充分注重环保意识,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同理,笔者主张民法、物权法要考虑环境保护,也不意味着主张民法、物权法将包括动物在内所有环境资源要素都纳入民法中“物”的范围或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纳入“法律物格”的范围。如果包括动物在内所有环境资源要素都可以纳入民法中“物”的范围或“法律物格”的范围,环境资源法是否会变成民法呢?总之,笔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较妥,它既考虑了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又没有企图将包括动物在内的所有环境资源要素都纳入“物”的范围;它既染上了绿色,又没有包办代替环境资源法。根据第90a条的规定,在社会生态化和建设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时代,无论是传统的民法还是新生的环境资源法都大有用武之地,都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三)对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是人”的质疑
杨立新教授在对《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进行分析时,一方面认为该条表示“动物不是物,动物是特殊物”,另一方面又认为该条表示“动物不是物,动物是人”。同一个人在同一篇文章中对同一项法律规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使笔者很难理解。前面笔者已对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是特殊物”进行质疑,下面对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是人”的观点提出商榷。
1.杨立新教授在分析《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时,表面上他将其理解为“动物不是物,动物是特殊物”,但实质上他将其理解为“动物不是物,动物是人”。
这不是笔者强加于他的观点,而是基于如下事实和理由:(1)杨教授如果真的将“动物不是物”的法律规定理解为“动物是特殊物”,他会全力支持、肯定这一法律规定,因为他的确认为动物是物,并且认为动物是需要加以特殊保护的物。但是,从总体上看,杨教授对“动物不是物”的态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实质上他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是权宜之计、是立法上的败笔。也就是说,在他心目中,规定“动物不是物”就意味着“动物是人”。(2)从杨教授所强调的民法基本理念看,他的确是将《德国民法典》第 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是人”,因为他认为:“从民法的基本方法论或者说民法的哲学立场观察,民法社会的基本构成结构,是人与物,这是市民社会的两种基本的物质表现形式,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物质形式的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也是建立在民法社会‘人与物’的二元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他既然抱定民法社会“人与物二元结构”即“人、物二分法”的坚定信仰,既然认为除了人就是物,除了物就是人,他不可能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明确规定理解为“动物是物”,他只能将其理解为“动物不是物,动物是人”,否则就是他不愿将民法的基本理念具体运用到他的法律解释实践之中。(3)杨教授虽然没有明确将“动物不是物”理解为“动物是人”,但从他强调和批判的重点看,他似乎认为“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导致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错误认识即“动物是人”。他在论述“动物人格权概念提出的背景”时,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视为动物人格权的渊源或根据。他在分析“动物不是物”的法律规定时多次申明,“我本人反对赋予动物人格权的思想,因为赋予动物以人格权”,“正是基于对动物赋予人格权以对动物进行保护的主张的不恰当性,促使我从物格角度来把握关于物的保护问题:即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他在“从环境伦理学角度分析‘动物人格权论’的基础”时得出如下结论:“动物人格权论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这些环境伦理学的观点反映到民法学上,就提出了动物人格权的主张。这也就产生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动物不是物)”。也就是说,他认为“动物不是物”的法律规定直接来源于动物人格权,即“动物不是物”的法律规定来源于“动物是人”的主张。他明确指出,“我个人认为,提倡动物人格权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在整个民法界,除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以及《奥地利民法典》等少数国家民事立法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外,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并没有类似的规定”。分析这段话发现,杨教授似乎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以及《奥地利民法典》等少数国家民事立法规定“动物是人”。其实,《德国民法典》第90a条以及《奥地利民法典》仅仅规定“动物不是物”,并没有规定“动物是人”,也没有作出“动物是人”和“动物人格权”的相关规定。说《德国民法典》第90a条以及《奥地利民法典》规定了“动物是人”或规定了“动物人格权”或作出了相关规定,仅仅是某些人的理解,而不是法律规定。
2.无论是赞成《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还是反对“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将“动物不是物”理解为“动物是人”,或者将“动物不是物”的法律规定理解为“动物具有人格权”的法律规定,都不符合《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的本意,甚至可以说是对第90a条的曲解。
某些主张“动物人格权论”的学者认为,“动物不是物,那么动物就是人”。杨立新教授对此提出批判,这是对的。我认为,主张“动物人格权论”的学者将“动物不是物”的法律规定理解为“动物是人”的法律规定,是一种误解;主张“动物人格权论”的学者不可能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中找到其法律依据。本人从不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意味着“动物是人”,也不主张赋予动物人格权,因为动物不是人,当然不能赋予其人格权。同理,笔者也不主张赋予动物以物格或物格权,因为动物不是物。
3.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是人”,这是基于“人、物二分法”的研究范式。
如果死守“人、物二分法”的研究范式,从“动物不是物”必然得出“动物是人”的结论。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仅有民法中的人和物,现实世界是除了民法中的人与物之外,还有既不属于民法中的人又不属于民法中的物的其他东西。《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本来是对笛卡尔“人、物二分法”或“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的突破,如果仍然沿用笛卡尔“人、物二分法”或“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对其进行分析,当然会得出“动物不是物,动物是人”的错误结论。
4.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是人”,并进而将主张动物权利理解为主张动物有人格权,这是基于“只有人有权利,除人以外的动物或其他生命体都没有权利”的先验模式。
杨教授反对赋予动物人格权的思想,笔者表示赞同。但是,笔者不同意杨教授将赋予动物人格权与赋予动物法律权利混为一谈的思想。据笔者所知,目前法学界或环境资源法学界,只有极少数的人主张法律赋予动物以人权或人格权,并且往往是打引号的“动物人权”或“动物人格权”。大多数学者主张赋予动物以法律权利即主张“动物权利”。“动物权利”与“动物人格权”或“动物人权”具有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动物权利,另一个是人的权利。“动物权利”主要指动物的生存权、行动自由权、被人类保护权、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免受人类折磨权等。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则是动物权利的理论基础之一;《德国民法典》第 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则是动物权利的法律根据。不知什么原因,杨教授从不谈“动物权利”,而只谈“动物人格权”。笔者揣摸,他不可能是反对“动物人格权”而赞成“动物权利”,他只能是认为“动物权利”就是指“动物人格权”,或者他所谓的“动物人格权”就是指“动物权利”。笔者认为:动物不是物,动物也不是人;法律可以规定动物有权利,但法律不能规定动物有人格权。笔者主张赋予动物以法律地位和动物权利,不能将动物权利理解为人格权或物格权,动物权利就是动物权利,动物权利既不是人的权利,也不是物的权利。笔者认为法律上规定的人、物或其他东西都有其法律地位(包括主体地位和客体地位等),从理论上讲不仅人有人权,动物也可以有法律权利;至于是否通过立法明确动物的权利,何时规定动物的权利,这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主要取决于人们或立法者对动物和动物权利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或立法者或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从法律上明确动物的权利,就可以从法律上明确动物的权利;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或立法者或大多数人反对从法律上明确动物的权利,就不可能规定动物的法律权利。
杨教授之所以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有关“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理解为“动物是人”,并进而将主张动物权利理解为主张动物有人格权,这是基于他头脑中存在的“只有人有权利,除人以外的动物或其他生命体都没有权利”的先验模式。也就是说,杨教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即凡是讲权利都是指人的权利,权利只能是人所特有的,除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 (包括《德国民法典》中的物和动物)都不可能有权利。话说到这里,也就没有了理论讨论或争论的余地。因为杨教授的结论(只有人有权利)也就是他结论的出发点、前提或理由。笔者在《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一书中曾经指出:“一些人反对自然体的权利,理由非常简单而毫无研讨余地,即权利只能是人的权利,动物等自然体不是人,所以法律不能赋予其权利。对于这种不容讨论的定论,主张动物等自然体权利的人可以用同样口气来回答:权利不仅仅指人的权利,动物等自然体也有权利,所以法律应该确认动物等自然体的权利。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主张动物等自然体权利的一方和反对动物等自然体权利的一方,并不以‘不容研讨的定论’方式进行辩论,而是陈述各种理由,力图证明自己主张的合理、正确、有利,都希望用自己的道理来说服对方,这就为动物等自然体权利问题的讨论创造了条件。”[7]杨教授也不是那种不容讨论的人,他为反对动物权利或动物人格权提出了如下理由:“为什么?就是因为人是有意志力的,人是可以自主地支配、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而动物无论如何没有这种意志力,它也就不能支配、控制自己的行为。由于人具有意志力,使得人可以控制自己,不去伤害已经获得了人格权、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的动物,那也就是不吃肉、不喝牛奶、不用动物搞试验,等等;但是,动物却无意志力,没有这种自制力,它不会因为自己已经获得了人格权,与人是平起平坐的民事主体,因而控制自己,不去伤害人。一方面,人在约束自己,而动物无法约束自己,人的约束更为动物创造了机会。因此,赋予了动物人格权,就会使这个世界成为了混乱的世界:即人要尊重动物的权利,但是动物却可以随便伤害人,主体中的人就会随之减少,主体的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也就会丧失动力,例如喝奶、吃肉等日常行为都必须禁止。如果以这种逻辑推论,今天我们给了动物以人格权,那么我们明天也许会给植物以人格权,如此下去,这世界势必混乱、毁灭。总的说来,如果赋予动物以人格权,那么也就破坏了整个民法社会的秩序、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秩序。因此,我个人认为,提倡动物人格权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在整个民法界,除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以及《奥地利民法典》等少数国家民事立法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外,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并没有类似的规定。”[3]对于杨教授的上述观点,笔者提出商榷如下:(1)杨教授说人之所以有权利,是因为人有意志力,人可以自主地支配、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不全面和不符合法律现实的。人权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意志力、不能自主地支配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的人,如胎儿、婴儿、无行为能力的小孩、精神病人、白痴、植物人等,也享有法律权利;甚至非现实存在的后代人、死人、法律拟制人也有法律权利。既然对人赋予权利都不强调其有意志力,可以自主地支配、控制自己的行为,杨教授却以动物不具有意志力、不能自主地支配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为由而反对赋予动物以权利,即对动物提出比人还要严格的权利标准,未免有失公平。(2)杨教授认为,如果赋予动物权利,就意味着人“不吃肉、不喝牛奶、不用动物搞试验,等等”,如果赋予了动物权利,“就会使这个世界成为了混乱的世界:即人要尊重动物的权利,但是动物却可以随便伤害人,主体中的人就会随之减少,主体的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也就会丧失动力,例如喝奶、吃肉等日常行为都必须禁止”。如果真的是这样,还有哪个笨蛋主张动物权利呢?主张动物权利岂不是主张消灭人类(包括消灭主张动物权利者本人)。据笔者所知,主张动物权利并不意味着人“不吃肉、不喝牛奶、不用动物搞试验,等等”,并不意味着“动物却可以随便伤害人,主体中的人就会随之减少,主体的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也就会丧失动力,例如喝奶、吃肉等日常行为都必须禁止”,我不想说杨教授在散布一种恐怖气氛,但可以肯定杨教授对“动物权利论”和“权利”缺乏全面了解。大家知道,主张某人享有权利并不意味着该人可以随便伤害其他人,其他人的日常行为都必须禁止;主张人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人“不杀人(如处死罪犯)、不喝人奶、不用人搞试验,等等”;众所周知,用人体进行医疗、医药试验古今中外一直存在,最近国家医疗机构还在用人体进行防艾滋病药的试验。当代许多学者主张的动物权利大都建立在生态学的基础上,强调按照自然生态规律赋予动物权利;法律规定的任何权利都是有限制条件的,对动物赋予权利当然也应该有限制条件,条件之一就是不能侵犯或损害法律已经规定的人的权利,要求人“不吃肉、不喝牛奶、不用动物搞试验,等等”首先是侵犯了法律规定的人的现有权利;另外,当两种不同的权利发生冲突或矛盾时,法律可以做出公平的解决权利冲突的规定,法院也可以做出解决权利冲突的公正判决。例如,如果享有生存权的某人要杀害或伤害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完全可以自卫,法律或法官会理所当然地支持另一个人的自卫行动。同理,如果法律赋予大熊猫以生存权利,当大熊猫要吃人或伤人时,这属于侵犯人的生存权的行为,人有权进行自卫即正当防卫,法律或法官会理所当然地支持人的自卫行动。所以,杨教授担心赋予动物权利会导致“动物却可以随便伤害人,主体中的人就会随之减少,主体的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也就会丧失动力,例如喝奶、吃肉等日常行为都必须禁止”,不仅是多余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3)杨教授认为,如果赋予动物权利,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仅破坏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秩序,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现实社会的基本秩序,破坏了自然界的基本秩序”,“如此下去,这世界势必混乱、毁灭。总的说来,如果赋予动物以人格权,那么也就破坏了整个民法社会的秩序、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秩序。因此,我个人认为,提倡动物人格权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在整个民法界,除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以及《奥地利民法典》等少数国家民事立法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外,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并没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杨教授的观点未免“危言耸听”。对这种过激的言词,笔者不想过多评论,世人自有公论。按照他的说法,在整个民法界,除了《德国民法典》第90a条以及《奥地利民法典》等少数国家民事立法对此作了相关规定外,大多数国家民事立法并没有类似的规定。2000年笔者曾经去欧盟国家进行学习研究,据笔者掌握的信息资料和实地观察,对动物权利作了相关规定的德国和奥地利,不仅没有因此“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没有“破坏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秩序”、不仅没有“破坏了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不仅世界没有“混乱、毁灭”,而且这两个国家的市民社会基本秩序和自然界的基本秩序非常好,去过德国和奥地利的人大都十分赞赏他们的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德国联邦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7日,以543票赞成(19票反对、15票弃权)通过了对《德国宪法》(又称为德国基本法,1949年5月23日通过)的修订,修订后的《德国宪法》第20a条规定:“为了后代的利益,国家负有保护生命和动物的自然基础的责任。”德国国内法学界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该宪法条款确认了动物的宪法权利,使德国成为承认动物的宪法权利的第一个欧盟国家①。目前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动物权利的国家还有哥斯达尼加,1998年颁布的《哥斯达尼加生物多样性法》第9条“普遍权利”第1款明确规定:“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所有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与其是否有实在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无关。”②据笔者掌握的信息,哥斯达尼加并没有因为规定动物权利而破坏了该国的社会基本秩序和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也没有造成世界的混乱和毁灭,而该国的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却得到了加强。也就是说,杨教授有关赋予动物权利就会造成世界混乱和毁灭的预言或担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三、环境资源法学和民法学学者对“人、物二分法”、“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的不同理解
同一个民法学者(如杨立新教授)在同一篇文章或讲话中(如杨立新教授《关于建立法律物格的设想》,清华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办的《资讯动态》2005年第12期)对同一个法律条文(如《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竟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如一方面认为“动物不是物”表示“动物是人”,另一方面又认为“动物不是物”表示“动物是物或特殊物”),这引起了人们对素以逻辑严密、概念严谨著称的民法学的怀疑,也引起了法学界对更深层次的法学理论问题即法学研究范式的关注。
(一)传统民法学奉行的是“主、客二分法”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历史主义者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目前范式这一概念已经超过库恩的原意,或已被赋予多种含义。一般而言,范式表示某一学科共同体(即该学科的专家学者所组成的集团)所共有的信念、传统、价值标准、基本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包括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道德观、理论背景和理论框架。通俗地说,范式就是指研究、讨论问题的共同规范和指导思想。范式的主要功能和意义是形成学科研究的内聚力,促进学科研究的常规化、系统化和群体化,通过新旧范式的更替实现科学理论的变革和学科的革命化,是标志一门学科成为独立科学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8]。近现代科学、近现代工业社会的研究范式是以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这种“主、客二分法”是近现代民法的根基,也是以传统民法为代表的主流法理学的研究范式。这种“主、客二分法”范式包括“人、物二分法”、“心、身二分法”和“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二分法”,其基本含义如下:(1)将整个世界截然划分为人与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这两大部分,不承认或不研究介于人与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其他东西(例如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物质、因素、条件或力,介于人与物之间的高等动物、上帝等因素),不重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转化和统一。(2)将人截然划分为人的心(心灵、思想、精神、意志)和人的身(身体)这两个方面,不重视人心和人身之间的相互联系、转化和统一,不承认或不研究介于人心和人身之间的其他东西(如人的语言、行为等)。(3)将所有关系截然划分为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不承认或千方百计地化解介于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之间的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4)认为人是主体,人永远是主体,人不能是客体;物是客体,物永远是客体,物不能成为主体。(5)认为人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人的心(心灵、思想、精神或意志)形成物并决定物。(6)认为人有内在价值和意志自由,有法律主体资格或法律主体地位、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物没有内在价值和意志自由,物没有法律主体资格、法律主体地位,没有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7)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只能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体现和运作。
“主、客二分法”范式反映到民法学上其主要内容如下:(1)将民法社会的结构截然划分为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这两大部分,不承认或不研究介于民法人与民法物、民事主体与民事客体之间的其他东西(例如将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物质、因素、条件或力,介于人与物之间的高等动物、上帝等因素),不重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转化和统一。(2)将民法人截然划分为人的心(心灵、思想、精神、意志)和人的身(身体)这两个方面,不重视人心和人身之间的相互联系、转化和统一,不承认或不研究介于人心和人身之间的其他东西(如人的语言、行为等)。(3)将所有关系截然划分为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不承认或千方百计地化解介于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之间的人与物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4)认为民法中的人与民法主体是合二为一的即“主体人”,民法中的物与民事客体是合二为一的即客体物,人永远是主体,人不能是客体;物是客体,物永远是客体,物不能成为主体。(5)认为人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人的心(心灵、思想、精神或意志)形成物并决定物。(6)认为人有内在价值和意志自由,有法律主体资格或法律主体地位、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物没有内在价值和意志自由,物没有法律主体资格、法律主体地位,没有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人支配物。(7)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只能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体现和运作,民事法律关系只能是人与人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法”是近代民法的根基,“主体等同于人、客体等同于物”是传统民法学理论的底线。杨立新教授也认为,“从民法的基本方法论或者说民法的哲学立场观察,民法社会的基本构成结构,是人与物,这是市民社会的两种基本的物质表现形式,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物质形式的存在。其中,人在民法社会中处于主体地位,支配着整个世界;而物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是民法社会的客体,人对物具有支配的权利,然后才能改造世界,推动社会的进步。在民法社会中,我们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分析民法社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民法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民法哲学问题。因此,我们看待民法社会的时候,就要从主体、客体与内容等角度进行阐述,这也说明以民事法律关系来分析民法社会,它是最基本的方法。而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民法社会“人与物”的二元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即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二者是支配关系”[3]。
笔者认为,环境法学者与民法学者之所以在对待环境资源问题和环境资源保护问题上产生许多分歧,其根本的或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门学科所奉行的研究范式不同。环境资源法学奉行的是“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即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反映了环境资源法学所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构成了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的基础。所谓“主、客一体化”,是指将主体与客体或者主观与客观这两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主、客一体化”就是综合的(全面的、辩证的)考虑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既关注人,又关注物,还关注不属于民法中的人和民法中的物的其他东西,并且将人与物和其他东西联系起来;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又研究物与物的关系,还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将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
(二)“主、客二分法”的弊病和缺陷
近现代科学、近现代工业社会的研究范式是以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在法学上的反映就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心灵与身体、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的二元对立和分割。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的二分或对立,体现了某些法学家对人与自然、人与物的概括性理解。“主、客二分法”和民法的基本方法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缺陷和弊病也日益明显。一些法学家将法律主体理解为“所有存在事物的一种尺度,并赋予他无限的不真实的意志自由,它把世界变成了有利于实现主体利益和欲望的静止的状态”[9]。随着人类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在有关环境危机根源的探讨中,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主、客二分法”。例如,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T.White)在1967年发表的被称为环境危机经典的论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为西方社会对待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伦理学体系的根源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犹太教—基督教对目前生态危机负有罪责。“与古代异教及亚洲各种宗教(也许拜火教除外)绝对不同,基督教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而且还主张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开发自然是上帝的意志。”③澳大利亚生态哲学家帕斯莫尔(J.Passmore)在1974年发表的《人对自然的责任》一文也认为,《旧约》确实为人对自然的绝对独裁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基督教主张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关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法”对法学的决定性影响,我国民法学者徐国栋教授曾有过相当精彩的论证,他认为:“民法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极为一致,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这是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式的思考确立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二元论的成果。人法与物法的二分,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二分的法律化。人文主义的民法——大陆法系的所有民法,除了德国法族的以外,都属于这一类型——认为主体是第一性的,客体是第二性的。因为人是这个世界的出发点,‘某一纯粹的自然物,若无主体介入,对它作出某些规定,那么作为客体而言,它还不存在’,而是作为纯粹的自然物存在,因此,外在的物质世界存在于与人的关系中,是人化了的。……物法是人的意志投射于外部世界的表现,是人的活动作用于此等世界的结果。出于人的本质是意识的考虑,民法还极为强调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现代民法之轴心的处理主体与客体之关系的法律行为理论和制度,不过是哲学上的自由意志理论在民法中的沉降。即使是所有权,也不过是人的意志作用于物的结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是所有人之意志的定在,由于它,人的自由获得了外部的领域。正由于所有权中‘心素’的存在以及它相对于‘体素’的优先地位,即使物脱离了所有人的占有,它仍不失为所有人的,一旦有机会,所有人将正当地收回之,此乃所有权的绝对性的表现,这是意识的胜利。”④德国法理学家阿图尔·考夫曼在其所著《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说》中也指出:“后现代思想首先应该克服现代的两元论,即: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一切欲望的冲动抑或自由释放之间的选择以及(人们极为看重!)唯理性和非唯性之间的对立。”[10](页8)“当人们奉守主体、客体图式时,认识中的客体与主体是严格分开的。……在取向于意义内涵的知性科学(不同于解释因果关系的自然科学)中,主体、客体图式原则上不起什么作用。”[10](页32)“一个想要理解某种意义的人完全必然地将持先人之见,从而也首先将其自我带进理解过程。这样一种理解并不是对象性的(因为意义并非实质),但也不是主观的(而是反射的和取向于传统的,如同取向于情境一样)。相反,它始终是主体、客体同时并存。任何一种要把知性科学中的唯理性和知性个性分离开来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0](页33)法国思想家德里达指出:“传统的‘二元对立’之所以必须被颠覆,是因为它构成了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等级制和暴戾统治的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策略,‘解构’在批判和摧毁‘二元对立’的同时,又建构和实现原有的、‘二元对立’所不可能控制的某种因素和新力量,造成彻底摆脱‘二元对立’后进行无止境的自由游戏的新局面。”[11](页305)美国“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大卫·雷·格里芬教授指出:“二元论自身证明了它很难从理论上得到坚持,尤其是当进化论观点为人们接受之后就更是这样”,“绝大多数现代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二元论是站不住脚的”[12](页220)。
现将民法学所奉行的“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的弊病,举例分析如下:
1.民法学对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僵化的、绝对的划分的弊病。
民法学将民法世界截然而僵化地划分为人与物两个部分,而事实告诉人们,在民法人与民法物之间存在着既非人亦非物的其他东西。由于坚持僵化的“人、物二分法”,民法学者无法科学、正确地回答如下问题:“动物不是物,动物是什么”;“克隆人、试管人、冷冻人是什么”;“胚胎是什么”;“人体(人的身体、器官、血液以及按照自然规律从人出生时就寄生在人体内的微生物和细菌等)到底是人还是物”;“人的权利到底是人还是物”;“人的行为到底是人还是物”;等等。
根据《德国民法典》关于“动物不是物”的规定,表明动物既不是民法中的人,也不是民法中的物。高等动物(包括今后出现的人工人、克隆人等)既具有民法中“物”的某些特性,又具有民法中某些“人”的特性,它可以作为人与物之外的第三种实体出现。所以新修订的《德国民法典》修改了动物属于物的僵化概念,明确规定“动物不是物”,对动物必须既遵守有关动物特别法的规定,又在没有相应特别法时准用有关物权法 (民法)的规定,所谓“准用”恰恰是民法没有对动物作出专门规定之时的“权宜之计”。瑞士于1992年通过的《瑞士民法典》修正案,也明确承认动物不是物 (things)而是beings,笔者理解,这里的beings表示动物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其本身目的和内在价值的客观存在物,是一种既不同于物也不同于人的生命体。在法律上规定“动物不是物”,但没有规定“动物是人”,这表明德国民法已经承认在人与物之间存在第三种状态。但是,由于一些法学家固守“人与物二分,非人即物,非物即人”的“主、客二分法”,《德国民法典》明明已经规定“动物不是物”却仍然自我安慰地坚持“动物不是物,但动物却是特殊物”悖论。
当代克隆技术和遗传工程对法律如何维护或废除民法中的人与物界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包括自然人的生命从何时开始、体细胞核移植导致的细胞融合算不算受精、克隆权与生命权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界限⑤。例如,按照德国法律,人的生命始于受精卵,这样,提供胚胎干细胞的早期人类胚胎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从早期人类胚胎中提取干细胞之后,该胚胎往往会死亡。按照德国法律,上述提取活动相当于谋杀。因此,德国完全禁止胚胎研究。按照英国法律,人的生命始于怀孕14天后受精卵着床之日,该 14天前的人类胚胎不算一条人命;这样,在人类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中杀死早期人类胚胎并不违法。英国于1990年通过的《人类受精与胚胎法》(简称HFEA)规定,在体外创造、储存、处置、使用人类胚胎必须申请许可证。某些行为(例如把人类胚胎放入动物身体)完全被该法禁止。在美国,多利羊诞生的消息发表一周之后的1997年3月4日,克林顿总统宣布:美国联邦机构不得支援、资助、从事人类克隆研究。接着有25个州拟定了禁止生殖性和治疗性人类克隆研究的法案,但只有几个州的法案获得议会通过。如1998年6月,密歇根州通过了一部永久禁止全部人类克隆行为的法律。但美国联邦没有通过任何规范人类克隆技术的法律(尽管已经提出过20多个相关法案)。最高法院在Roe v.Wade案⑥中认为:法院不能回答人的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接受过医学、哲学、神学专业训练的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目前人类的知识限度内,司法机关不适合扮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猜测者的角色”。虽然美国法院的判决不讨论未出生的胎儿是否是“人”的问题,许多判决隐含的结论是:未出生的婴儿不受宪法第14修正案的保护。在Roe v.Wade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在堕胎问题上为了保护母亲的隐私权而允许其“杀死”(即堕胎)另一个生命(胎儿)。 1992年,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对夫妻就经过体外受精程序的冷冻胚胎的监管问题发生冲突并提起诉讼,即 Davis v.Davis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再次拒绝对未出生的婴儿提供宪法第14修正案的保护。该法院引用的“美国生殖协会道德委员会”的一个报告也认为:基于医学结论和法律先例,“胚胎”不同于“受精后14天以下的受精卵(pre-embryo);受精卵应当得到更强的法律保护,因为与一般的人类组织相比,其有潜力变为一个人;但是其不能被当作一个人来尊重。该法院的判决认为:受精卵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或者“财产”,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并有权获得特殊尊重的一种东西⑦。与《欧洲专利公约》和《欧盟生物技术保护指令》不同,美国成文法没有限制人类克隆技术可享专利性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在美国排除人类克隆技术的可享专利性没有宪法和专利法的依据,“在美国,人类克隆发明属于可享专利性的主题”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未出生的胎儿不是我国民法的民事主体,未出生的胎儿不享有生命权。在医疗实践中,我国人工流产的数量历年均居世界第一。我国法律与英国、德国不同,但与美国类似,即规定人的生命始于出生之后。
与冷冻胚胎相似的还有因冷冻人产生的法律问题。目前,在美国人体冷冻中心“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里,有67个“客户”人(中心的病人)正躺在8个不锈钢罐中。这些钢罐每个高10英尺,里面充满着液态氮,温度在零下200多度。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深信,当将来细胞再生、纳米技术、克隆或者其他一些使人起死回生的科技出现的时候;这些冷冻的人有可能“起死回生”。被冷冻的“客户”人,在法律上到底是属于主体还是客体,对“主、客二分法”的法学理论而言,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民法学中主体、客体概念与人、物概念合二为一的弊病。
民法学坚持主体人和客体物的僵化观念,为维护人不能成为客体的“底线”,逐渐将人的身体、人的器官、人的行为、人的权利义务、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等都排除出人的范围,结果导致人的抽象化,而现实中的人或法律案件中的人却是活生生、身体与灵魂、器官与意识相统一的人。民法学为了维护除了人就是物的逻辑,开始了“物化世界”的进程(十字军远征),逐渐将人的身体、人的器官、人的行为、人的权利义务、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克隆人都界定为物,结果导致物的泛化(包括物的所有权的泛化)。对于民法学中这种“物的泛化”以及“物的所有权的泛化”的倾向,特别是某些民法学者把所有自然资源(包括水流、大气等)和整个生态环境(包括生物多样性、遗传多样性、迁徙性动物等)都视为物,将所有自然资源权利和生态环境权利都视为物权的倾向,环境资源法学是很难接受的。笔者认为,这不仅在环境资源法学领域行不通,对民法自身的发展也不利,甚至有可能破坏民法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秩序。例如,有些民法学者提出水资源物权、大气资源物权的理论后,甚至连一些资深民法学者也感到不可理解。他们提出,如果确立水资源国家所有权(水资源物权),长江、黄河的水流到大海是不是国有水资源的流失?这个问题提得好,可以说击中了水资源物权的要害。但是,有的民法学者(如崔建远教授)竟然解释说:“对于长江黄河水的流失,能否看成是传统所有权自身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即权利主体放弃自身权利的表现,这是法律所允许的。”[13]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可取的。根据民法理论,民法中的物是人力所能控制、支配的物,物权是人所能控制的权利,物权主体放弃自己的权利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主动的、自觉的行为,而长江黄河水流向大海是人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不管人是否同意或是否放弃,长江黄河的水都会流向大海,如果人要阻止其流向大海,只会对人自身造成损害。因此,我们不能用物权主体放弃其权利来解释长江黄河水流向大海的问题。如果用物权主体放弃自己的权利来解释,那么民法就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大气流、日月星辰宇宙)都可以视为民法中的物,都可以建立物权,即使人力所不能控制的自然力、自然现象、自然规律都可以用物权主体放弃自己的权利来加以解释。这样,物和物权也就失去了民法的物与物权的严格含义。
为了维护“客体与主体、人与物是严格对应的一对概念,非此即彼,没有什么中间状态”的观念,传统或主流法学始终不承认在人与物之间还存在第三者或第三种状态,结果导致了如下矛盾:将单位(公司、企业、学校)、城市、国家甚至动物等也视为或拟制为人,结果使法学中的人失去了自然人的本性和本意;将人的行为、人的权利、人的义务、人的身体都视为物,结果使民法中的人变成了抽象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抽象人,使法学中的物失去了自然物的本性和本意;将高等动物(包括今后出现的人工人、克隆人等)或规定为物,或规定为人,结果使高等动物(包括今后出现的人工人、克隆人等)失去了其既不同于物又不同于人、既类似于人又不类似于物的本性和本意。更广泛的后果是使民法学中的人、物、动物、主体、客体等常用概念与现实生活常用语言脱钩,与当代语言学、语义学、行为科学、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应概念脱节,与多元化、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不相符合。例如,当新的《德国民法典》规定动物不是物时,持“主、客二分法”的民法学者马上会产生动物是人的意识(因为他认为不是物就是人)。
3.民法学者对类似法律条文在解释中采用双重标准的弊病。
以传统民法学为代表的某些法学理论为了维护其“主体只能是人,客体只能是物”的僵化观点,当遇到客体是人、主体是物的情况或者法律中的同类规定时,往往采用自相矛盾的不同标准和不同概念,将客体是人解释成客体是物,将主体是物解释成主体是人。例如,将法律“禁止买卖妇女”中的妇女解释为主体,而将法律禁止“买卖大熊猫”中的大熊猫解释为客体;将法律“禁止虐待妻子”中的妻子解释为主体,而将法律“禁止虐待牛马”中的牛马解释为客体;在精神病人、白痴病人、婴孩致人损害时,将精神病人、白痴病人、婴孩解释为主体,而在大熊猫、老虎致人损害时,却不将大熊猫、老虎解释为主体;在某甲打伤某乙时,将某乙解释为主体,而在某甲打伤某狗时,却将某狗解释为客体;在某甲监护的某精神病人致人损害时,将某甲监护的某精神病人解释为主体,而在某甲监护的某老虎致人损害时,却将某老虎不解释为主体;在解释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20条、1994年的《技术标准协议》中有关“保护人类、动物及植物的生命、健康和环境”的规定时,将保护人类理解为目的、人为主体,而将保护动物、植物和环境理解为手段,动物、植物和环境是客体。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以传统民法为代表的主流法理学形成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使人们对法学的正义理念、公平理念和逻辑严密性大打折扣。
4.民法学中侵权行为、维权行为和侵犯人、保护人的概念的弊病。
为了维护“人永远是主体,人不能成为客体”的观念,传统民法学将侵犯人改为侵犯人的权利,包括将侵害人的精神和身体视为侵犯人的人身权、将侵犯人的行为改为侵权行为,以防止出现人成为侵害对象即客体。因为如果承认侵犯人或侵犯人的行为,就等于承认人是客体;而说侵犯人的人身权利或侵权行为,不存在人成为客体的问题,因为权利(包括人身权)在民法中被认为是物。同理,传统民法学将保护人改为保护人的权利,如将保护妇女、儿童、婴儿、精神病人等称为保护妇女、儿童、婴儿、精神病人的权利;将保护人的行为改为维权行为。因为如果承认保护人或保护人的行为,就等于承认人是客体;而说保护人的权利或维权行为,不存在人成为客体的问题,因为权利(包括人身权)在民法中被认为是物。其实,“法律对权利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那些主张权利的人的保护”[14],侵犯人身权就是侵犯人,人可以成为其他人行为的客体。
同样,为了维护“人永远是主体,人不能成为客体”的观念,传统刑法学认为杀人、伤人、强奸、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人身权利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人本身。
推行上述理论的结果是使以传统民法学为代表的主流法理学离常识和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因为它将包括丰富内容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与其人身、意志、权利和义务相分割的抽象的人。
5.民法学所坚持的“只有人才有权利”的观点的弊病。
某些法学家为了维护其“物不能成为主体、物不能有法律权利”的观念,当出现物特别是高级动物成为法律主体或享有法律权利的事实或案件时,往往不惜采用“以我为人的代表”、排除异己的蛮横的、武断的态度。例如,当古代法律出现将动物规定为人即主体的情况时,某些法学家说这是法律落后的表现;当当代法律出现规定动物具有权利时⑨,某些法学家说这是少数国家的法律、个别不能代表一般;当古代出现以动物名义起诉、为动物权利辩护的法律案件时⑩,某些法学家说这是落后的胡闹;当当代社会出现以动物名义起诉、为动物权利辩护的法律案件时(11),某些法学家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现象;当神权法中规定动物有权利时,某些法学家说这是迷信;当当代动物福利法规定要人道主义对待动物时,某些法学家说这是刽子手的仁慈;当一些人要求法律保护东北虎、大熊猫等野生动物或要求法律承认动物权利时,某些法学家说这是空想、不以人为本,甚至质疑这些人为什么在还有几千万贫民的当代中国不去为贫民争取权利而热衷于保护动物;当某个学者提出动物权利时,某些法学家说这是个别人的胡闹,当占人类多数的宗教人士(如佛教、基督教人士)提出动物权利时,某些法学家说这些人不懂法;当现代科学举出一些高级动物也有思想、感情、苦乐、利益、语言、学习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内在价值和社会性,一些人反而没有思想、意志、苦乐和行为能力,甚至一些动物还比一些人更加聪明、更有能力时,某些法学家就说再聪明的动物也比不过最聪明的人。总之,某些法学家将所有规定动物权利或主体资格的法律都说成是落后的法律,将所有主张动物权利或主体资格的法学理论都说成是落后的理论。因此,某些法学家经常强调的人的思想、意志、理念和理性对物的决定性或优先性,实质上仅指持“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的人的思想、意志、理念和理性对物的决定性或优先性,而没有包括持“主、客一体化”研究范式的人的思想、意志、理念和理性对物的决定性或优先性。这种贬低不同学术主张或学派的态度和作法,从反面证实了持“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的某些法学家的某种片面性、局限性。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主张的是“动物的权利”即动物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更不是主张法律将动物变为人或将动物规定为人。“动物的法律权利”与“动物的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人故意将动物的权利混同于动物的人权,进而污蔑主张动物福利的人是将动物等同于人,这些人不是将自己的僵化认识强加于人,就是对动物的权利和动物的人权这两种说法缺乏起码的认识和区别。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种现象:在奴隶没有权利的时代,当有人主张奴隶的权利时,反对者认为这是将奴隶变为奴隶主,会引起奴隶主世界的混乱,因为在反对者的心目中的权利就是指奴隶主的权利;在女人没有权利的时代,当有人主张妇女权利时,反对者认为这是将女人变为男人,会引起男人世界的大乱,因为他们心中的权利仅指男人的权利;在黑人没有权利的时代,当有人主张黑人权利时,反对者认为这是将黑人变为白人,会引起白人世界的大乱,因为他们意识中的权利仅指白人的权利。根据1990年《德国民法典》和1992年《瑞士民法典》的规定,动物不是物也不是人,因而动物的权利既不是传统民法中人的权利也不是古代法律中物的权利,而是新的民法典中“动物的权利”。关于动物的法律地位和权利问题,在过去的10年里,德国国内一直在进行辩论,德国联邦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7日,以543票赞成(19票反对、15票弃权)通过了对《德国宪法》(又称为《德国基本法》,1949年5月23日通过)的修订,修订后的《德国宪法》第20a条规定:“为了后代的利益,国家负有保护生命和动物的自然基础的责任。”德国国内法学界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该宪法条款确认了动物的宪法权利,使德国成为承认动物的宪法权利的第一个欧盟国家(12)。必须指出的是,法律上的权利并不一定要在法律上明确写上权利“二字”,关键是要明确规定表征权利存在的具体内容。例如,如果一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则表明人有言论自由权;反之,即使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人有言论自由权”,但同时规定“发表言论必须经过批准”,则表明该法律并没有确认言论自由权。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某组织可以自由占有、使用、转让土地”,则表明该组织享有土地所有权;如果法律规定“某组织有土地所有权”,但同时规定“该组织不能自由占有、使用、转让土地”,则表明该法律没有真正规定该组织的土地所有权。一般认为,法律上的权利就是指法律认可的地位、资格、自由、利益和权力。从语义学上看《德国宪法》关于“为了后代的利益,国家负有保护生命和动物的自然基础的责任”这一法律条文,正如“保护人的自然基础一样”已经肯定人是主体一样,保护“动物的自然基础”这一法律语言已经明确表明动物是自然基础的主体,因而保护人的自然基础表明法律承认人的权利,保护动物的自然基础表明法律承认动物的权利。从法律逻辑看,不能认为“法律保护妇女、婴儿、残疾人”、“不准虐待妇女”这些法律规定表明妇女、婴儿、残疾人享有权利,而类似的法律规定“保护野生动物”、“不准猎杀野生动物”和“不准虐待动物”却不能表明野生动物享有权利。又如,美国的《自然保护区法》(1964年)、《国家野生动物庇护区系统管理法》 (1966年)和《濒危物种法》(1973年)并没有明确规定动物的权利,但是该法明确规定不“允许一个物种的种群数量的减少超过这样一个限度,以致它们不能在所属的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的功能”、“禁止猎杀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等内容,所以美国许多法学家认为,这些法律实际上已经规定动物的权利。例如,约瑟夫·皮图拉(J.Petulla)认为,“在美国,被列入保护名单中的非人类栖息者被赋予了某种特殊意义上的生命权和自由权”(13)。从总体上看,并与以往的法律相比较,该法还是为某些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存权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保护。其一,该法适用于所有动物(甚至无脊椎动物)、昆虫和植物。只有那些“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威胁”的细菌、病菌和蝗虫被排斥在外。列入该法保护名单的大多数生物几乎完全不为人知,对人的有用性并不是纳入保护名单的标准,它们被保护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生态学家和生态神学家所理解的生命世界的一部分。其二是它把对物种的伤害不仅理解为对该物种的成员的杀害,而且理解为对它们所依赖的环境的破坏。该法引入了“重要的栖息地”概念,意味着不仅有机体而且生态系统也拥有合法的存在权利。那些侵犯了这种权利的人将被罚款和监禁。该法还禁止联邦政府机构参与甚至资助那些对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有害的活动,并给予个人和环保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前纽约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J.L.Buckley)曾多次谈到这一点,他认为,“在人类认识其对完整的自然界的道德责任方面”,《濒危物种法》“代表的是一次巨大的飞跃”[15]。人们惊喜地发现,自克里斯托夫·斯通于1972年主张把动物、植物甚至自然区域的利益纳入美国的司法制度以来,1973年的《濒危物种法》可视为朝这个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又如,不少美国人认为,《海洋哺乳动物法》(1972年通过)规定受法律保护的动物行动自由,等于从法律上明确了动物所享有的行动自由和不受人们干扰的自由生活的资格,这种动物行动自由和自由生活的资格,实质上是对动物权利的法律确认。事实上人们也是这样对待这类法律规定的,据报道,2005年9月,美国加州纽波特比奇市的海港发生了一起“人与海狮之争”,该市40多只海狮在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上晒太阳,它们乱闯乱撞,甚至弄沉了一艘帆船,它们还发出很大的吼声,吵得港口居民难以入睡。由于美国《海洋哺乳动物法》规定,海狮是受保护的动物,人们不能伤害或是骚扰它们。为此,人们在忍无可忍和情况下,该市海港委员会于2005年9月14日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委员会决定请求美国政府通过一项法律,从今以后,禁止任何人喂海狮或往港口倾倒鱼类的“边角料”,用这种办法使海狮无食可吃而迫使海狮离开港口[16]。目前各国的动物福利法大都已经确认动物在动物福利法法律上的地位(指受法律保护的地位),已经承认和保障动物的生存资格、动物的活动的自由、动物的福利和动物对人的正当需求,因而实际上动物福利法已经确认动物的自然权利。意大利已制定相关法律保护家养动物的“权利和义务”。从实质上看,动物福利的基本需求就是动物福利法认可的动物基本权利。1998年《哥斯达尼加生物多样性法》第9条“普遍权利”第1款明确规定:“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所有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与其是否有实在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无关。”所有这些都对笛卡尔和传统法学的“主、客二分法”和“人、物二分法”范式提出了挑战,并间接证实了“主、客一体化”的范式的存在。在许多法律法规中,更不用说在具体的法律事实和法律案件中,人与物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客体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但说主体是动物时并不意味着动物是人;人不仅是自己认识自己、自己改造自己的客体,一些人也是另一些人的行为作用对象即客体,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当代哲学、行为科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共识。
收稿日期:2006-03-08
注释:
①引自http://www.fass.org/fasstrack/news-item.asp?news-id=526,英文是:“The state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protecting the natural foundations of life and animals in the interest of future.”
②英文原文如下:Biodiversity Law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1998),Article 9 General principle,1.Respect for all forms of life.All the living things have the right to live,independently of actual or potential economic value.
③怀特:《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科学》155 (1967,3,10)。CF.,lynn White.Jr.,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155 Science,(March 10,1967).怀特的这一论文在基督教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荣获了美国生态学会米斯(Mercer)奖。
④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法律思想网:http://www.law-thinker.com/detail.asp?id=9942。
⑤克隆(clone)这个词来自希腊,最初的意思是无性繁殖。目前克隆是指:回避正常的繁殖过程,使用来自单个亲代个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各种生物材料,例如分子、细胞、器官、植物和动物等;并且上述遗传物质主要来自普通成体细胞,而不是生殖细胞或者胚胎干细胞。植物克隆早已取得成功。动物克隆开始于1960年。例如,第一个用成体细胞的DNA于1996年7月5日克隆出来的多利羊,其遗传物质来自一只雌性山羊的一个乳腺细胞。实施上述无性繁殖的人工技术就是克隆技术。1997年,英国的一个科研小组制造出了一头叫做Freddy的无头青蛙,这项技术意味着可以制造无头克隆人,从而用克隆技术生产出供器官移植用的人体组织或者器官。人类克隆技术主要包括两种:人类体细胞移植、人类胚胎分离。我国克隆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技术水平与美国科学家不相上下。2001年,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将一名7岁小孩的包皮细胞移植到家兔卵母细胞中,成功克隆出100多个人类胚胎。同年,无锡、上海的几家医院相继宣布已经克隆出人的脑细胞。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于2000年培养出了11个克隆胚胎,其中3个发生卵裂并发育到桑椹胚阶段。该实验结果于2002年在国外发表后,国外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对人类克隆技术的研究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一些人认为这成为美国政府、立法机关对人类克隆技术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原因。
⑥See Roe v.Wade,410U.S.113,159(1973).
⑦Se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Fertility Society,FERTILITY & STERILITY,June 1990,at 31S-36S.
⑧魏衍亮,叶东蕾:《人类克隆技术的专利保护研究》,《东海大学法学研究》2003年第17期,第320页。See Free the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February 20,2002,I'm H.R2505.http://www.freedom.gov/library/technology/d50-clone.asp,2002/11/5.
⑨1998年《哥斯达尼加生物多样性法》第9条“普遍权利”第1款明确规定:“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所有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与其是否有实在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无关。”英文原文如下:Biodiversity Law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1998),Article 9 General principle,1.Respect for all forms of life.All the living things have the right to live,independently of actual or potential economic value.
⑩1480年法国普罗旺斯省的农村,鼠灾非常严重,但农民们不敢杀死一只老鼠,而是联名向动物法庭提出了公诉。奥杰纳主教认为这是“民事诉讼”,便对此案进行了审理,除了起诉人之外,还有老鼠的律师巴·西亚利奈以及23名法官出席。本来应由被告出庭,可是西亚利奈一开庭便指出:“被告无法出庭。因为第一,农村中的老鼠居住得太分散,无法接到出庭的通知;第二,它们都住在深穴暗洞中,通知也无法送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被告如果要来出庭,则须穿过森林,翻过高山,通过河流和沼泽,而这中间的每一步都埋伏着可以使它们丧命的猫、猫头鹰、黄鼠狼等,所以它们根本不能出庭。”西亚利奈的辩护获得了成功,奥杰纳主教只好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听取了公诉人的公诉和证人的证词,而后做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判决。他庄严地在法庭上宣判道:“缺席的被告们,你们也是神的造物。大地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本不希望加害于你,但你却巧取人们的财物,毁灭人们的葡萄园,盗走了人们的食物,一句话你夺走了人们的劳动果实。我陈述了你的罪状,祈求神的慈悲,告诉你应该去的地方,不要再在我们这里居住。”这个无可奈何“驱逐出境”的判决,立刻遭到西亚利奈的反对。他发表了热烈的演说:“这种判决不是公正的,法庭要尊重事实,就是说对老鼠不能一概而论,要确认每只老鼠和具体罪行,区别对待。”毫无疑问,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可是法庭又反驳不了他,结果这场官司不得不以老鼠的胜利而告终。西亚利奈一下出了名,成了为老鼠辩护的专家。
(11)从1974年至1979年期间,许多公民以受污染的河流、沼泽、小溪、海滨、物种、树木的名义向法庭提交了许多诉状。其中,有一个物种是夏威夷的一种小鸟,即帕里拉(Palila)属鸟,它的栖息地急剧减少,只剩下芒那火山(Mauna Kea)的一小块斜坡。1978年1月27日,色拉俱乐部法律保护基金会和夏威夷奥杜邦协会代表仅存的几百只帕里拉属鸟提出了一份诉状,要求停止在该鸟类的栖息地上放牧牛、绵羊和山羊。该案的名称叫“帕里拉属鸟诉夏威夷土地与资源管理局”。1979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为帕里拉属鸟做出了裁决,要求夏威夷当局必须在两年内完成禁止在芒那基火山放牧的工作。这是美国法律史上一种非人类存在物(鸟类)第一次成为法庭中的原告,并且获得胜诉的案件。
(12)引自http://www.fass.org/fasstrack/news-item.asp?news-id=526,英文是:“The state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protecting the natural foundations of life and animals in the interest of future.”
(13)约瑟夫·皮图拉:《美国的环境主义:价值观、策略与优先问题》(德克萨斯州立大学,1980)P51。
标签:德国民法典论文; 人格权论文; 民法典论文; 民法调整对象论文; 民法基本原则论文; 法律主体论文; 动物论文; 法律论文; 二分法论文; 环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