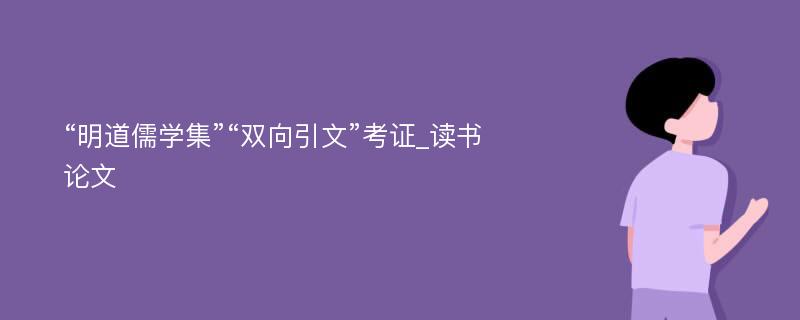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录论文,诸儒鸣道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诸儒鸣道集》是南宋无名氏编的一部理学丛书,凡七十二卷,共收录了宋代十二位理学家的十五种著作,包括周敦颐的《通书》,司马光的《迂书》,张载的《正蒙》、《经学理窟》与《语录》,程颢和程颐的《二程语录》,谢良佐的《语录》,刘安世的《语录》、《谭录》和《道护录》,江公望的《心性说》,杨时的《语录》,潘子醇的《忘筌集》,刘子翚的《圣传论》,张九成的《日新》等著作。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南宋端平二年(1235)黄壮猷修补本,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该书的最早刊本。
关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和成书年代,陈来先生有详细的考证[1],这里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讨论的是该书所收录的《二程语录》,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除朱熹所编《二程遗书》和《二程外书》之外,又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二程语录本子,因此,弄清楚它的编著者及与朱熹所编《二程遗书》之间的关系等,就显得尤其重要。对此,陈来先生曾从卷数、题解、注文等方面,与朱熹所编《二程遗书》进行了比较,并作出如下推论:“《鸣道集》本《二程语录》可能稍早于朱熹编定的《遗书》或于朱子同时,但非出于《遗书》。”[1] 笔者认为这一推论还值得商榷,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二程语录》与《二程遗书》的异同
统观两书,我们发现《二程语录》与朱熹所编《二程遗书》同中有异,并且其相同的地方是主要的,具体表现为《语录》的内容(包括正文、题解与注文)、篇目名称、各卷之间的前后编排顺序等,绝大部分都同于《遗书》。但亦有许多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卷数分合不同。一方面,《遗书》中的某一卷在《语录》中可能被分为数卷,另一方面,《遗书》的某几卷在《语录》中则变为一卷,详情见下表:通过下表我们可以看出,《遗书》二十五篇除卷二十三《鲍若雨录》不载于《语录》外,其他二十四篇均见于《语录》,只不过是卷数分合有差异,所以《遗书》为二十五卷,而《语录》为二十七卷。
《二程遗书》 《二程语录》
卷一 卷一
卷二上卷二、卷三、卷四
卷二下卷五
卷三 卷六
卷四、卷五卷七
卷六 卷八
卷七、卷八卷九
卷九、卷十卷十
卷十一卷十一
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二
卷十五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
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六
卷十八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
卷十九卷二十二、卷二十三
卷二十、卷二十一上、卷二十一下卷二十四
卷二十二上卷二十五
卷二十二下、卷二十四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三 无
卷二十五 卷二十七
其次是内容的差异。这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正文的差异。除《遗书》比《语录》多《鲍若雨录》一卷外,各卷中亦有部分内容为《语录》所无,如《遗书》卷七中的“须是无终食之间违仁”与“不偏之谓中”两条语录就不载于《语录》。特别是卷二十二上《伊川语录》中有近一半的条目不见于《语录》,如“《乡党》分明画出一个圣人出”、“居敬则自然简”、“仁者先难而后获”等。而《语录》中的有些内容,《遗书》亦无,如《语录》卷十六所附“杂说”三条,卷二十五中的“莫大于性,人自小之,非性然也,故圣人闵之”及卷二十七中的“或问文中子,曰‘愚’。问荀子,曰‘悖’。问韩愈,曰‘外’。愚、悖、外皆非学圣人者,扬雄其几乎?”等,皆不载于《遗书》。此外,就是同载于两书的内容相同的一条语录,文字也存在着差异,如《遗书》卷六中的“君实笃厚,晦叔谨严,尧夫放旷”一条语录,在《语录》卷八中则为“君事兄嫂,晦谨严,尧放旷”。卷二十二上中的“先生曰:‘孔子弟子,颜子而下,有子贡。’伯温问:‘子贡,后人多以货殖短之。’曰:‘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世之丰财,但此心未去耳’”一条语录,在《语录》卷二十四中却为“孔门颜子而下有子贡,人多以货殖短之,子贡非若后世之丰财也,但此心未去耳”。二是注文的差异。一方面是一些注文往往是彼有我无,如《遗书》卷二上“当春秋、战国之际”一条语录中有“恃此中国之福也”一句,其中的“恃”字下注曰“一本无‘恃’字”,句末则注曰“一本‘此’字下有‘非’字”,此两条注《语录》皆无。而在同一条语录内的“今日堂堂天下”一句句末,《语录》注曰“元本作‘唐唐’字”,但《遗书》却无此注。另一方面就是同一条注文,文字亦有差异,如《遗书》卷十八“士未仕而昏”一条语录中有“况古亦有是”一句,句末注云“士乘墨车之类”,而《语录》卷二十一则在该句下注曰:“庶人乘墨车之类。”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此为正文,在彼却为注文,反之亦然。如《遗书》卷十八“大则不骄,化则不吝”一条语录中的“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此莫是甚言骄吝之不可否?’曰:‘是也。若言周公之德,则不可下骄吝字。此言虽才如周公,骄吝亦不可也。’”一段文字,在《语录》卷十八中却成了注文。而《遗书》卷十九“先生在经筵时”一条语录中的“岂有今日乃为妻求封之?”一句下有注文曰“其夫人至今无封矣”,而此条注文在《语录》卷二十三中则属正文。
另外是两书对应篇目的一些相同语录条目的排列次序不同。如《遗书》卷一、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上、卷二十二下等中的一些语录条目的排列次序,都与《语录》对应篇目的排列次序不同。不仅如此,甚至还有一些在《遗书》中本属此篇的语录条目,在《语录》中却被移入了彼篇,如《遗书》卷十八与《语录》的卷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和二十一相对应,卷二十二上与《语录》的卷二十五相对应,但《遗书》卷十八中的“尧、舜、汤、武事迹虽不同,其心德有间否?”一条语录和卷二十二上“孔子弟子,颜子而下,有子贡”一条语录,都被移入了《语录》卷二十四中。此外,每条语录的划分亦存在差异,有时在《遗书》中为一条语录,在《语录》中却变成了两条语录,反之亦然。如《遗书》卷十五中的“《论语》有二处”一条语录,在《语录》卷十五中被分成了“《论语》有二处”和“是集义所生”两条语录;而《遗书》卷十八中的“人或倦怠,岂志不立乎?”与“邵尧夫临终时”两条语录,在《语录》卷十八中则被合成了一条语录。
二、《二程语录》与《二程遗书》的关系
综上所述,尽管《语录》与《遗书》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其相同点还是主要的。因此,笔者推测两书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否则,不会在选材和组织材料方面有如此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语录》很可能亦由朱熹编定,而且就是朱熹所编《遗书》的初稿。其证据如下。
第一,朱熹所编《遗书》是以其家藏旧本数篇为基础,然后以类访求,方得二十五篇,其《程氏遗书后序》云:“始,诸公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浸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编。熹家有先人旧藏数篇,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首尾通贯,盖未更后人之手,故其书最为精善。后益以类访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闻岁月先后,第为此书。篇目皆因其旧,而又别为之录如此,以见分别次序之所以然者。”[2] (P3937)也就是说,在朱熹编《遗书》之前,当时世上还没有一本收录比较完备的二程语录本子流传,更不用说与《遗书》二十五篇内容、篇目、次序基本相同的作品了。而这二十五篇中除《鲍若雨录》不见于《语录》外,其他二十四篇均载于《语录》。如果两书不是出自朱熹一人之手的话,这种情况是很难解释通的。
第二,《语录》早于《遗书》。《语录》卷十六《己巳冬所闻》后附《杂说》三条,并附语云:“右《杂说》三章,旧《集》有之,今附于此。”卷二十四《周伯忱录》后则附有《答问手帖》(即今本《二程文集》所载《答周孚先问》)、《答鲍若雨书并答问》和《与金堂谢君书》,并附语云:“右答鲍、谢书,《集》中不载,今附之《答周伯忱手帖》之后。”这些内容均不见于《遗书》。其中的《集》,陈来先生认为指的是胡安国家藏本《二程文集》[1],笔者认为此说有误,因为《杂说》、《答问手帖》、《答鲍若雨书并答问》和《与金堂谢君书》,均载于今本《二程文集》,并注曰:“胡本无。”如果《集》指胡安国家藏本《二程文集》的话,就与《杂说》后的附语相矛盾。事实上,《语录》中所提到的《集》指的是当时世上颇为流行的《伊川大全集》,如朱彝尊《程颢中庸解》引康绍宗语云:“昭德《读书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载此卷。”[3卷151] 而《文渊阁书目》卷二亦著录有《程伊川大全集》一部五册。由此可知,所谓《伊川大全集》当是一种有关程颐作品的合集,今《外书》卷十《大全集拾遗》就是从此书中辑录出的有关程颐的语录。《遗书》后来之所以删去《杂说》、《答问手帖》、《答鲍若雨书并答问》和《与金堂谢君书》等内容,原因是《遗书》修订完稿时,《二程文集》的重新校补工作也已完成,并补全了胡本《文集》之疏漏。
第三,朱熹在编辑《遗书》时曾先编辑了一部初稿,而此初稿编成后即付梓,他在与何叔京的信中谈到过此事,说:“语录倾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辄有移易。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2] (P1842)当朱熹拿到刊印的初稿本子时,发现了许多原来没有发现的错误,其《与平父书中杂说》云:“《程氏遗书》细看尚多误字,盖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参之,乃觉其误耳。”[2] (P1838)于是决定对初稿重新进行校订。但由于自己有许多事务缠身,校订工作时断时续,所以后来他在写给何叔京的另外一封信中说:“语录比因再阅,尚有合整顿处。已略下手,会冗中辍。它时附呈未晚。”[2] (P1846)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决定委托许顺之等人对《遗书》初稿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他写信给许顺之说:“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指同安)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2] (P1781-1782)并在答复许顺之的信中对校书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曰:“承上巳日书,知尝到城中校书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2] (P1782)而这一工作直到乾道四年(1168)才完成。
第四,《遗书》中保留有数处明显由初本改正而来的痕迹,如《遗书》卷二上中的一段话: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佗。然据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清谈盛而晋室衰,然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谈,又岂若今日之害道?今虽故人有一(初本无一字。)为此学而陷溺其中者,则既不可回,今(初本无今字。)只有望于诸君尔。直须置而不论,更休曰且待尝试。若尝试,则已化而自为之矣。要之,决无取。(初本无此上二十九字。)其术(初本作佛学。)大概且是绝伦类,(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会,大率谈禅’章内,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异时有别锓版者,则当以此为正。”今从之。)世上不容有此理[4] (P23-24)。
这段话在《语录》卷二中为: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佗。然据今日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如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清谈盛而晋室衰,然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谈,又岂若今日之害道?今虽故人有为此学而陷溺其中者,则既不可回,只有望于诸君尔。佛学大概且是绝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5] (P399-400)。
再比如《遗书》卷二上中的另外一段话:
圣人之教以所贵率人,释氏以所贱率人。(初本无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学佛者难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余见‘昨日之会’章。”)学佛者难吾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无仆隶”。正叔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所愿也;其不为尧、舜,是所可贱也,故以为仆隶。”[4] (P37-38)
这段话在《语录》卷四中则为:
学佛者难吾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无仆隶”。正叔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所愿也;其不为尧、舜,是所可贱也,故以为仆隶。”[5] (P431)
上面所引《遗书》中两段话的括号内的文字当为校订时所加的注解,由这些注解我们可以看出,《遗书》校订前的面目正好与《语录》一致,《语录》当为《遗书》初稿无疑。
第五,《遗书》附录中的《伊川先生年谱》多次出现“见《语录》”字样的注文,这里的《语录》当指《二程语录》,因为从《程氏遗书附录后序》中我们得知该序作于乾道四年夏四月,也就是《遗书》修订完稿时,换句话说,《遗书》附录一卷及附录后序编写于《二程语录》刊行之后,故《语录》未载这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就是《程氏遗书后序》亦作于《遗书》修订完稿时,朱熹在乾道四年写给王近思的信中说:“校书闻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略见编纂之意。”[2] (P1798)这里的序当指《程氏遗书后序》,此时王近思正与许顺之等人受朱熹委托在同安城校订《遗书》。并且在该序写成后,朱熹还就此征求过其他人的意见,他在写给林择之的信中说:“《文定祠记》、《知言序》、《遗书》二序并录呈。……三序并告参祥喻及,幸更呈诸同志议之。既欲行远,不厌祥熟也。”[2] (P5456)其中《遗书》二序指的就是《程氏遗书后序》和《程氏遗书附录后序》,所以《语录》亦不载《程氏遗书后序》。
总之,《二程语录》与《二程遗书》为同一书,都是由朱熹编定的,只不过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订稿。该书之所以后来未能像《遗书》那样广为流传,可能是经过校勘后的《遗书》本子比其更加完善,该书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了。而《诸儒鸣道集》之所以收录这个本子,原因是当时《遗书》的修订稿尚未完成。但令人不解的是,平生治学严谨的朱熹为什么会让这样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二程语录本子匆忙面世。笔者推测朱熹之所以这样急于发表自己所编的《二程语录》,很可能是想建立他在二程思想诠释方面的权威地位,并借机削弱其他学派,特别是胡安国家族在这方面所施加的影响,从而使自己在争取道学正统地位的斗争中能处于有利地位,我们从他对刘珙、张栻于乾道初年刊于长沙的以胡安国家藏本为底本的《二程文集》所持的强烈批评态度中,也能看出这一点。事实也就是如此,朱熹正是通过对二程著作的整理和编辑活动,牢牢地控制住了二程思想诠释的话语权,并毫无争议地成为宋代道学的正宗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