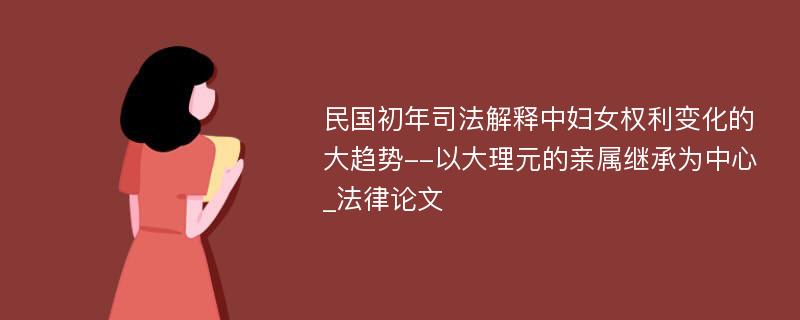
民初司法判解中女性权利变化的总体趋势——以大理院亲属、继承判解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理论文,民初论文,亲属论文,司法论文,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8)02-0108-05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社会重宗法父系等级,所以男尊女卑的性别不平等延续了数千年始终未被打破。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及民事法律近代化的一个特殊时期。由于民事基本法仍然适用传统的《现行刑律民事部分》,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女性权利在这一时期“因袭多,变化少”。笔者对此种观点充满疑窦,诚然,由于民初民事基本法仍然适用《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情况下,女性权利在制度层面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应该指出,民初是一个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社会观念剧烈变化的时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动态的司法实践,是否真能面对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及民事法律近代化的潮流而置身事外?民初女性权利是否真如一般学者所言在这一时期确实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司法判解作为社会制度实践方式之一,必然受到社会变革及社会总体近代化趋向的影响,也更能灵活多变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弹性地回应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观念意识的变革呼声,并逐渐与之趋于一致。同时民事司法判解作为民事法律制度在实践层面的表达,其必然受民法近代化甚至整个法律体系近代化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必然反映其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在民初静态的制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司法判解言说的观察,才能发现民初女性权利本身的发展变化脉络,并进而观察民初民法近代化乃至整个法律体系近代化及民初整个社会近代化过程中女性权利变化的总体趋势。
二、民初司法判解中女性权利变化的总体趋势
民国初年,由于民事基本法律继续适用《现行刑律民事部分》,而该法集中体现了维护尊卑长幼、亲疏嫡庶、男尊女卑的宗法伦理特点。这不仅与当时世界司法发展的主旨相背甚远,即使与当时国内的宪政民主政体及妇女运动的呼声也相冲突。所以民初大理院受妇女运动及近代西方民法人格平等、个人本位等价值理念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应势权变,通过判解对现行律的规定进行了变通解释,这种变通与传统法律相比,使女性权利总体上体现出了以下发展趋势:
(一)体现出在制度上确立女性独立法律人格的趋势。人格者,独立法律地位之体现也!中国社会数千年的传统文明史中,女性在社会上从无独立地位,所谓“妇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即是对女性附庸地位的准确描述。“三从”下的妇女当然不可能在法律上拥有独立人格。而民初,由于受西方近代民法人格平等理念及女权运动的影响,女性独立人格开始受到关注。这种关注在大理院的司法实践中,体现出在制度上确立女性独立法律人格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
1.女性的独立意志开始获得法律的尊重。民初大理院司法言说的实践话语来源于西方法律制度之中。契约思想在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渗透极为普遍,大理院很容易就借鉴契约范畴来进行相关裁判活动。在契约语境下,女性独立意志的表达顺理成章地获得了法律的尊重,并被赋予相应的效力。在大理院的司法裁判中,女性独立意志被尊重的情形主要体现在婚姻关系的缔结及解除之中。
按照民初仍然有效之《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按照这一规定,婚约以父母、祖父母或尊长为主体,婚约成立以父母之意愿为实质要件。男女双方并非婚姻的主体,可以说他们是被结合者。[1](P220)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女性和男性一样没有意志自由,仅是婚约中的“客体”,只能被动地接受父母的安排而没有丝毫权利。
而大理院在判解中却明确“婚姻之当事人本为男女两造”(七年上字第972号判例)。并从契约的一般理论出发,明确“订定婚约,依一般契约之通例,要须定婚两造有一致之意思表示,否则虽具备形式要件,亦难认其婚约为已成立”(八年上字284号判例)。按照大理院的以上解释,显然将女方和男方视为婚约之主体,婚姻应该经得男女双方同意才能成立。甚至在女儿与主婚权人的意愿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女儿的意愿也处于可以对抗主婚权人意愿的优先地位。如十一年上字1009号判例谓:“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所订婚约,子女成年后如不同意,则为贯彻婚姻尊重当事人意思之主旨,对于不同意之子女不能强其履行。”由此可见,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定立婚约,而不再是被动地被安排的“客体”。
大理院除了在婚约的定立中强调女子的个人意愿外,在婚约的解除上也强调当事人的个人意愿。不仅将婚约的解除权利完全赋予了婚约双方当事人,明确“婚约成立后经双方合意可以解除”(如四年上字第844号判例),而且限制主婚权人的滥行干涉,明确“子女已成年,其父母为之退婚而未得其同意者,其退婚不为有效”(七年统字第906号解释)。这些判解使女性在婚约的定立及解除中均成为主体,其个人意愿得到了法律的尊重。
2.女性不再被视为“物”,开始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女性获得独立人格的观念障碍体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主体观念的缺乏使旧时代的中国女性在法律上被视为“客体”,不仅是男性的附庸物,而且是可以被法律强制执行的“物”。这一点从历代法律关于悔婚的规定中可见一斑。例《唐律·户婚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婚者,杖六十。虽无婚书,但受聘财亦是。但男家自悔者,无罪,财礼不追。若更许他人者,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2](P1009—1010)。明律、清律于此均有相同规定,只是处刑稍微减轻而已。可见婚约之效力在传统法律上非常强大,婚约一旦定立,就有了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履行即成婚,这种强制性有力地约束着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
民国初年的《现行刑律民事部分》是清律例的延续,关于“许嫁女悔婚另嫁”的规定也同样将悔婚女子的命运交到前夫手中,赋予“第一个许婚者有收回该女或者抛弃该女,并收回聘财的选择权”[3](P381)。婚约的这种强制效力,实际是将女子的人身作为强制执行的客体,像债权契约中的物品一样,只要男方坚持娶她,就无条件的被当做婚约之客体强制送归前夫之家,女子的生死与意愿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民初大理院受西方民法人格平等观念的影响,在司法裁判中明确“婚约义务,系属于不可代替行为之性质,在外国法理,概认为不能强制履行”(五年统字第510号解释例),从而创设新例,不再强制悔婚另嫁女子归前夫。不仅如此,大理院还在具体的判解中,完全以女性自己的意愿为主来决定其在前夫和后夫之间的选择,甚至对于下级法院按现行律做出的强令悔婚女归前夫的判决强行予以纠正。
大理院的判解显然体现了将女性视为与男性一样的“人”来看待,而非可以任由前夫处置的物品的价值理念,昭示着女性从无独立人格向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转变迈出了重要一步。
3.女性独立人格在司法话语中开始被独立表达。在民初的司法判解中,女性独立法律人格的确立不仅可以从上述两方面的实质内容中体现出来,而且直接反映在大理院司法言说实践的话语脉络中。如在离婚诉讼中,大理院不仅吸收近代西方离婚法中的新概念,将“不堪同居之虐待”、“重大侮辱”、“重婚”等作为女方提起离婚的理由,尤其是在解释“所谓重大侮辱”,“当然不包括轻微口角及无关重要之詈骂而言,惟如果其言语行动足以使妻丧失社会之人格,其所受侮辱之程度至不能忍受者,自当以重大侮辱论”时(五年上字717号判例),运用“人格”这一近代民事法律概念,明确将男性以言语或行为使女性“丧失社会之人格”的情形作为女性提起离婚的法定理由,女性人格在法律层面得到了明确表达及承认。此外在民国十五年第1484号判例中也宣示:“夫犯奸通常固不可与妻犯奸并论而迳许离异,但若已因犯奸被处刑则情形又有不同,为保护妻之人格与名誉计,自应许其离异。”同样以“女性独立人格”为逻辑,认为丈夫的通奸行为对妻子的人格和名誉有影响,所以允许女性以此为理由请求离婚。不仅如此,大理院还明确,“离婚原因如果由夫构成,则夫应暂给其妻以相当之赔偿或慰抚费“(八年上字1099号判例)。明确赋予了妻子的过错离婚赔偿请求权,使女性不仅由原来被动的、被男性休弃的客体变成了离婚诉讼中的主体,而且使女性因为丈夫的过错导致离婚而受到的人格侵害通过经济的补偿得到了一定的抚慰。
所有这些判解的变化显然将女性视为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而非纯粹的客体,承认并明确保护女性的独立人格。这既是女性法律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也体现了在制度上确立女性独立法律人格的发展趋势。
(二)体现出男女平等的发展趋势。法律上实践男女平等是近代世界各国法律变革的总体趋势,始于晚清的法律继受显然无法置身于这场变革的潮流之外。在西方近代民法人格平等理念及民初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司法判解中女性权利的变化也体现出男女平等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
1.女性开始获得一定的与男性同等性质的法律决定权。
首先,如前所述,在婚约的定立与解除判解中广泛导入“协议”这一具有近代“契约”性质的概念。将婚姻中的男女双方置于对等的位置上协商婚约的成立与解除。认为婚约必须是男女双方有一致之“合意”才能成立(八年上字284号判例)。同时明确“婚约成立后,经双方合意可以解除”(四年上字第844号判例)。
其次,在离婚中也强调“协议”离婚,并明确双方可以就离婚所涉问题进行协商。这种“协议离婚”与封建法律中的“和离”有质的不同。封建法律中的“两愿离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协议离婚”,因为在传统法律中,男性与女性没有对等的人格,夫妻双方根本不可能具备近代契约属性的对等地位。所以所谓“两愿离婚”之“和离”实际上还是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并且大多以夫家一方的意愿为转移,妻的合意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和离”多数成为夫家为避免出妻、弃妻的恶名及家丑外扬而逼妻离婚的一种手段而已。[4](P115—116)而民国初年的大理院,由于受近代西方民法契约平等、婚姻自由原则的影响,在离婚中也引入契约概念,明确“合意”离婚权属于双方当事人,排斥主婚权人的干预。如民国六年上字第735号判例谓:“男女婚姻之主婚权虽属于祖父母父母等,而协议离婚则必出于为夫妻之两相情愿而后可,自不得牵引主婚之律条以为口实。”此外,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与监护,大理院也明确承认“夫妇离婚时,得以协议定子女之监护方法”(三年上字269号判例)。
这样的判解不仅使男女双方的地位具有了现代契约概念下“平等、自由、合意”的痕迹,而且使女性的意志在婚姻关系的缔结及解除中受到与男性同样的尊重。这是男女法律地位渐趋平等的重要表征。
2.女性开始获得一定的财产继承权。在传统法律中,家庭财产的承继、流转是以男性为坐标、按照宗族谱系来确定的。女性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必然无法参与到财产继承关系之中,只有在户绝无可承嗣之人的情况下,才能承受父亲的财产。
而民初大理院在其司法裁判中明确规定:“亲女苟为亲所喜悦应酌分财产,若父母生前俱未表示意思而亲属会协议分产又未允洽,则由审判衙门斟酌两造情形及遗产状况为之核定。”(三年上字第669号判例)。按照大理院的这一解释,亲女只要能证明为亲所喜悦,即可要求酌分财产。这事实上已经赋予了女儿的财产继承权。特别是在民国十四年上字第3447号判例中进一步明确:“母于亲女酌给财产系法律上应有之权利,其数额苟未轶出法定范围,即无庸得嗣子之同意或追认。”这一解释使得女儿,无论已嫁未嫁,事实上都可以通过母亲的“酌给”行为而获得或继承父亲的部分财产成为可能,而且亲女所得的份额在本案中与嗣子所得份额完全相等。
由以上判解可以看出,民国初年的司法实践中,女儿们虽然“对家产承受权的体现不像男子那样直接明露,而是以间接方式为主。但我们应该拓宽思路,注意到尽管女性直接承受娘家父母家产的机会很少,但用无继产之名、有继产之实的间接方式承继家庭财产的途径却并不狭隘”[5](P127)。特别是1926年后,最高法院在十六年第七号解释例中明确:“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女子有财产继承权。”这一解释在法律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女子有财产继承权。这“可谓于吾国法制史上放一异彩矣”[6](P9—12),开创了“中华民国女子在法律上和男子一样待遇的新纪元”[7](P6—9)。这些变化使得民国初年的女子财产继承权,无论在司法实践层面还是法律制度层面均体现出了男女渐趋平等的发展趋势。
(三)体现了女性身份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趋势。中国传统法律理念立足于家族本位和男权本位,强调女性遵从于男性,将女性视为义务主体而非权利主体。而民初大理院在司法实践中,因受西方近代民法人格平等、权利本位理念的影响,在涉及女性权利纠纷的司法判解中不仅明确使用“权利主体”一词,而且赋予了女性广泛的民事权利。这种判解言说体现了女性身份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
1.女性在夫妻关系中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传统社会,女性在夫妻关系中只有履行义务的资格而没有权利可言。但民国初年的大理院通过判解明确“妻关于日常家事有代理其夫之一般权限”(五年上字第364号判例),并第一次明确“夫妇互有同居义务,亦即互有请求同居之权利”(五年上字第444号判例)。按照大理院的解释,同居是夫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妻有权利在夫不履行同居义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对方与之同居。同时赋予了妻子请求与丈夫别居并获养赡的权利(三年上字第454号判例)。这些权利的享有使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由纯粹的履行义务者变成了一定权利的享有者,尤其是女性获得了请求丈夫与自己同居的权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是对女性婚姻生活中独立人格的认同与维护,同时对于那些在民国初年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任意冷遇妻子的男性而言也不能说不是一种限制。
2.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离婚权。传统的以“七出”为核心的离婚制度集中的体现了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的特点,离婚权完全属于丈夫,妇女根本没有离婚权可言。法律虽然也规定妻子在丈夫“逃亡三年以上”、“夫殴妻至折伤以上”、“夫典雇妻妾”及“抑勒妻妾与人通奸”的情况下,可以提起离婚。但由于传统的礼俗对妇女再嫁存在偏见,所以“官方所赋予已婚妇女的离婚权利很少为妇女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她们即使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如被嫁卖等,多数妇女表现出对丈夫安排的屈从。即使有不满,也多借助于民间手段来解决”[8](P27)。妇女社会地位之低在离婚方面的体现最为明显。
而大理院在现行律关于女方可以提起离婚的理由基础上,通过判解不仅明确将“妻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七年统字828号解释)、“妻受夫重大侮辱者”、“夫重婚”(九年上字第1124号判例)、“夫通奸被处刑”(十五年上字第1484号判例)等作为女方提起离婚的理由,而且对“夫殴妻至折伤”以上、“妻背夫在逃”及“七出”等都作了合理性解释与修正。并从“条理”立论,坚持离婚中的有责主义,明确“限制有责配偶的离婚请求权”(九年上字第809号判例)。虽然这些理由是针对男女双方的,但在当时夫妻双方经济、社会地位及身体力量等都不对等的情况下,这些离婚理由的引人对于女性的意义远远胜过男性。这些判解变化不仅使女性的离婚权利明显扩展,使妻子成为离婚中的权利主体,而且对于传统的“妇人义当从夫,夫可以出妻,妻不得自绝于夫”的旧观念也是一种颠覆。
3.女性开始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权,经济上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传统的礼经强调“子妇无私蓄、无私货,不能私与”,即使是妻接受别人的赠与和自己的嫁奁也归夫家所有,根本没有私有财产权。
但民初大理院受西方民法人格平等、权利本位理念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判解明确宣示“为人妻者得有私产”(二年上字33号判例),并将“夫或家长给与妻或妾之衣饰,也认为妻妾所有”(九年上字第11号判例)。大理院不仅在制度上赋予了女性一定的财产私有权,而且在具体的判解中将女性描述为“权利之主体”(二年上字33号判例),使女性真正成为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享有者。
虽然民初司法判解中女性还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完整的财产权,但大理院通过司法裁判首次承认了女性的独立财产权,强化了女性独立的经济地位。这对女性获取独立法律人格、成为民事权利主体具有重大意义。
所有这些司法判解态度的变化,不仅受到了社会观念变革的影响,同时也吸收借鉴近代西方权利本位的司法话语体系,将原来以履行义务作为天职的女性视为和男人一样的人,并通过判解赋予了女性一定的权利,明确其是权利的享有者,体现了女性身份由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发展趋势。
三、结语
笔者通过对民初大理院司法判解的详细解析,发现大理院以“法言法语”式的司法言说实践方式,追随当时社会变革的步伐,在关涉女性利益的司法裁判活动中,以开放的姿态为女性赋权,使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观念形态的社会价值诉求在法律制度上得以逐步确立,进而使民初女性权利在法律近代化的整体变迁过程中,体现出独立、平等及权利本位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趋势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变革在婚姻家庭、继承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反映,也是近代法律移植过程中吸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民法典中相关条文并付诸实践的结果。但因为与女性权利密切相关的“婚姻、家庭、继承法是法律体系中最具民族特色、与国情民风联系最为直接、密切的部分,无论是法律制度的渐进式演变、革命性变革,还是移植式引进,婚姻、家庭、继承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本国文化的传统因子,并展示其保守性、稳定性。传统中国,重宗法血缘伦常关系,婚姻、家庭、继承制度尤其受到宗法文化的影响而具有独到的坚轫性”[9],所以尽管清末以来,社会思想观念对女性权利变化的呼声迭起,但法律近代化变革中紧关女性权利的身份法律制度的变化却是“进一步,退两步”,使得民初女性权利的变迁体现出“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