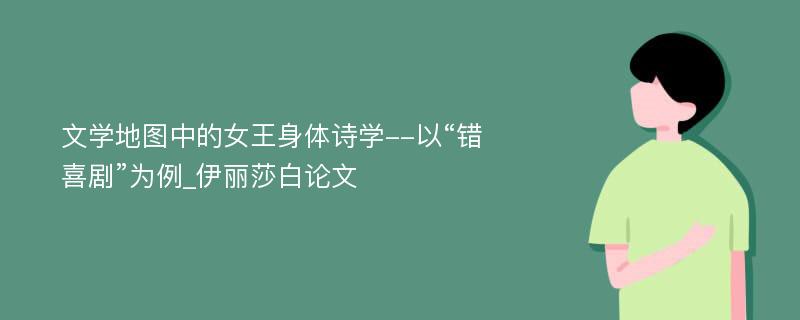
文学地图中的女王身体诗学:以《错误的喜剧》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为例论文,图中论文,女王论文,喜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英美文学地图研究界,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中男仆大德洛米奥所绘制的女仆露丝的身体地图非常有名:“她的身体像个浑圆的地球,我可以在她身上找出世界各国来……”①尽管学者们从多种角度对此描写进行了解读,但并未对露丝的女仆身份提出质疑。②而问题在于,此种逻辑下的女仆身体地图极度偏离了当时的身体描摹的空间常规,大德洛米奥隐喻的真是露丝吗?
事实上,有如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女神(女王)身体才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地图界的描绘对象,墨卡托等顶级地图学家都曾把欧罗巴等女神雕像置于地图册的首页,海因里希·本廷等人直接在欧洲地图上绘出了女神的空间轮廓,而英国著名的制图师撒克逊、皇家肖像画师乔治·高尔和小马库斯·海拉特则创造出多幅经典的伊丽莎白一世身体地图。③这些特殊的地图意象既是古希腊和中世纪隐喻地图的延续,④图中的人物依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由于土地隐喻的需要,女神和女王逐渐取代上帝成为文艺复兴地图关注的焦点。但不同于女神地图的是,具有政治世俗性的女王身体地图还是“国王二体”论(The King's Two Bodies)的地图空间变体。作为柏拉图“身心二元论”、中世纪“基督二体论”和王权至上的绝对主义政治思潮混合而成的神秘主义政治身体诗学,⑤“国王二体”论认为“国王有两种身体,即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其自然之身是肉体之躯,像其他的肉身一样有缺陷……但是他的政治之身不可见,也触摸不到,致力于政策民生,为民谋利……完全免于生老病死”⑥,从而得以上升为超验的上帝之身。尽管这种“国王二体”论一开始只是为男性统治量身定做的护身符,但急需进入主流政治话语的女王同样需要神圣政治身体的庇护。她宣称:“我知道我有一名女性羸弱的身体,但同时我也拥有一位国王的心脏和胃口,我也是英格兰之王。”⑦显然伊丽莎白希望和男性国王一样拥有神圣的政治身体,最终成为一种超性别的神灵代表。这种女性化的“女王二体”论为伊丽莎白的政体找到了神圣的宗教托辞,从而创造出政治领域“道成肉身”的神话。从这种意义上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女王地图隐喻的并不是伊丽莎白的肉身,而是代表国家的政治身体。换言之,我们同样可以将《错误的喜剧》中的露丝的身体地图视为逃避苛刻的女皇新闻审查而由男性杜撰的身份伪装,⑧大德洛米奥真正讽喻的应该是伊丽莎白一世本人,⑨剧中的女性身体地图表面上仍然符合流行的空间常规和文学风尚,⑩而这正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但问题绝非以上的分析这么简单,文艺复兴时期的女王身体地图至少涉及性别规约、国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思潮、殖民探索和地图传统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寓意深刻的文学地图变异。鉴于此,本文以新历史主义的地图史料考证为依托,从身体地图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错误的喜剧》中女仆露丝和女王伊丽莎白的共通之处,旨在揭示女性与地图、身体与国土、地图与欲望之间特殊的跨空间映射及其深刻寓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作者同意凯特·米利特关于西方两性关系的一个研究预设:“虽然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基于和谐的和理性的原则之上的人类生活组合,并彻底消除由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行使权力的观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政治状况并非如此。这正是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11)
一、妖魔化的女王身体地图
在进入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细察《错误的喜剧》中露丝身体地图的全貌:
大德洛米奥:从她屁股的这一边量到那一边,足足有六七呎;她的屁股之阔,就和她全身的长度一样;她的身体像个浑圆的地球,我可以在她身上找出世界各国来。
大安提福勒斯:她身上哪一部分是爱尔兰?
大德洛米奥:呃,大爷,在她的屁股上,那边有很大的沼地。
大安提福勒斯:苏格兰在哪里?
大德洛米奥:在她的手心里有一块不毛之地,大概就是苏格兰了。
大安提福勒斯:法国在哪里?
大德洛米奥:在她额角上,从那蓬蓬松松的头发,我看出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
大安提福勒斯:英格兰在哪里?
大德洛米奥:我想找寻白垩的岩壁,可是她身上没有一处地方是白的;猜想起来,大概在她的下巴上,因为它和法国是隔着一道鼻涕相望的。
大安提福勒斯:西班牙在哪里?
大德洛米奥:我可没有看见,可是她嘴里的气息热辣辣的,大概就在那里。
大安提福勒斯: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呢?
大德洛米奥:啊大爷!在她的鼻子上,她鼻子上的瘰疬多得不可胜计,什么翡翠玛瑙都有。西班牙热辣辣的气息一发现这些宝物,马上就派遣出大批舰队到她鼻子那里装载货物去了。
大安提福勒斯:比利时和荷兰呢?
大德洛米奥:啊大爷!那种地方太低了,我望不下去。
(《错》:3.2.416-417)
这是一幅由言语绘制的形象而生动的女性身体地图,但所表达的语义却远远超出了揶揄的范畴,这种人体和地图之间的类比探索是通过纳入和排除、边缘和中心的特殊地图手法来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只是女仆露丝所映射的伊丽莎白女王成为了讽刺的牺牲品,此时大德洛米奥至少采取了妖魔化和色情化两种歧视性的地图想象策略。
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文艺复兴时期地图页面的空间分配并非单纯地图关系的表达,更多时候是古希腊和中世纪描绘宇宙秩序和投射自我价值观念的延续,地图的焦点空间与价值判断具有趋同性。当身体进入地图后,制图者需要在地图中心和身体中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基本原则依然存在,与作者价值观念相悖的空间条目,比如女性和蛮夷等,(12)会有意识地移向身体地图的远端,有时甚至达到非常夸张的程度,妖魔化的空间表征应运而生。中世纪“帕萨尔特地图”中就有两只巨大的野兽匍匐于地图之外,而O型中心区域的右侧绘有无头人、食人族和女妖等各色各样的怪物。(13)这样的描绘是蒙昧时期的开明人类对未经教化的蛮夷歧视性的表征和忧惧,也是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在男性基督徒的眼中,充满物欲的女性和蛮夷具有先天性的生理和心理缺陷,因此需要经过炼狱般的罪恶洗礼后才能恢复正身,升入天堂。此时边缘化的地图空间与丑陋的女性和怪诞的蛮夷相互映射,共同书写了一段男性文明至上的歧视性地图传奇,影响了撒克逊等著名地图学家,被J.B.哈利称为地图界的“民族中心主义符号”(sign of ethnocentricity)。(14)
大德洛米奥也采取了同样边缘化的空间策略,他所绘制的女性身体地图勾勒了爱尔兰、苏格兰和法国三个“蛮夷之地”,并分别用“沼地”、“不毛之地”、“乱七八糟”来形容,这是英格兰民族中心主义和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投射到地图上,则是妖魔化的女性野地意象。从历史上看,爱尔兰的盖尔文和不列颠是两种争斗不断的凯尔特岛民文化支系,其独立存在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成为空间边缘化的借口。在托勒密构建的第一幅古不列颠地图原型中,爱尔兰被彻底排除在视野之外,连现身地图边缘的资格都被剥夺。(15)尽管1518年乔治·里利印制的第一张英国地图将其列入其中,但不规则的轮廓显示出空间秩序的缺席,不完整的区域则暗示了征服和教化未竟的事业,被斯宾塞喻为“野蛮的爱尔兰”(16)。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尔兰的地图历程是女性屈辱历史的镜像表达,从经验空间之外走向文明边缘经历了近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尽管伊丽莎白女王从出生(1533年)到登基(1558年)只用了25年的时间,但过程却相当曲折,也经历了被男权社会排斥的痛苦历程。在第一版《继位法》和第二版《继位法》中,伊丽莎白和玛丽公主一起被列为“非法的继承人”(bastard),从而被逐出了男权社会的话语王国。尽管1543-1544年颁布的第三版《继位法》作了修改,但依然被排在爱德华王子之后,在男权社会的边缘地带“苟且偷生”。(17)即便加冕后女王依然受到男性的抵制,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曾在《共和国六书》中写道:“我们觉得王权应该传给子嗣,考虑到女性政权有悖于自然法则,男性天生就该凌驾于妻子之上,拥有力量、勇气和权力来进行统治,并剥夺女性的荣誉。”(18)从这种意义上说,女王的性别地位和爱尔兰的民族身份一样饱受侧目。与此同时,大德洛米奥从描绘“污秽”的露丝臀部开始,既为整个女性身体地图定下了一个歧视性的空间坐标和基调,同时也象征着女王政权和爱尔兰一样低劣而龌龊。此时违反传统的女王政权、边缘化的国家身份和女性身体不洁的部位由逻各斯民族中心主义拼凑在一起,被男性主导的早期现代文明放逐为荒凉的野地和文化的他者。
尽管在不列颠国家集团中苏格兰的地位比爱尔兰要高,但依然备受打击。伊丽莎白曾囚禁苏格兰的玛丽女王长达19年,最后将其处死,其间苏格兰发生了诸多暴乱,两国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因而在地图中受到排挤也就理所当然——如果托勒密误将苏格兰描绘成东西走向还可以归咎为空间知识缺乏的话,那么1579年撒克逊绘制的《英伦图》无疑是有意为之:苏格兰被置于地图主页的背面,除了稀疏的河流等空间标识外,就是整片浅黄色的荒地。(19)《错误的喜剧》中苏格兰的荒原意象显然秉承了撒克逊的空间疏远政策,被置于远离大脑和心胸地带的手心,但其意义更耐人寻味。一方面,男性绘图者将其表征为“不毛之地”,既讽刺了政治对手的贫瘠和荒凉,也暗示女王生殖能力的匮乏,没有为英国留下合法的子嗣。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作者仍然希望女王将苏格兰牢牢控制在手掌之中,最终彻底纳入英格兰的版图之内,蕴藏其间的二重矛盾心理跃然纸上。
相比之下,法国与英格兰“隔着一道鼻涕”(英吉利海峡),距离更加遥远,两国争斗历来有之,(20)加剧了英国人对其的敌对情绪,在地图中变成显而易见的贬损部分。比如撒克逊《英伦图》中的法国只占据了右下角非常小的位置,手写体的GALLIA PARS(即高卢地区)花哨而拥挤,显得非常杂乱,恰似《错误的喜剧》中露丝额头上“蓬蓬松松的头发”——“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巧合的是,就在该剧完成之前的1592年左右,侨居伦敦的荷兰地图师洪第乌斯也刻制了一幅“英伦图”。像中世纪圆形地图中的上帝一样,女王的头像被置于画面上方的正中央,(21)额头上的头发尽管被镶嵌珠宝的头饰压紧,但卷曲的头发显得蓬松甚至凌乱——在此男性制图师和文学家一样,延续了女性地图的“涂鸦”传统,既贬低了政治对手,又丑化了女性的容颜和品格。
但对于女性而言,比国家丑化更为严重的是女性和野地的结合会生产出荒野中的女魔头。可以想象的是,当一个胖如圆球、肥得流油的女性臀部长着很大的沼泽地,手里拽着一块不毛之地,额头上还刻着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而且披头散发,这不是魔鬼是什么?难怪大德洛米奥感叹道:“我想她一定是个妖怪。”(《错》:3.2.417)事实上整个剧本都笼罩在妖气四溢的空间氛围中:有对陌生男人的身体了如指掌的“妖怪”女仆露丝,有找巫师品契来为丈夫小安提福勒斯驱魔并将其五花大绑的“魔鬼”阿德里安娜,还有比“魔鬼还可怕”的“母夜叉”、“扮作婊子来迷人”的妓女等(《错》:4.3.427)。正如大安提福勒斯催促的那样:“这儿都是些妖魔鬼怪,还是快快离开的好。”(《错》:3.2.417)这种远离欧洲文明、由女仆、妻子和妓女混合而成的女怪将女性贬斥为父权文化语境下的不祥之物,使得男性有足够的理由将其践踏后坦然离去,不用承担任何道德的重负。
即便作为一国之君的伊丽莎白仍旧难免成为妖魔化的性政治策略的牺牲品。1598年由一位荷兰匿名制图师雕刻的“作为欧罗巴的伊丽莎白”地图中,女王的身体上同样刻着欧洲各国,但没有左乳的伊丽莎白看起来特别恐怖,类似于古希腊的女斗士亚马逊——为了便于拉弓射箭和投掷标枪,后者生生地将自己的左乳切下来烧掉。(22)此时伊丽莎白俨然变身成骁勇善战的女战士,但这种崇尚暴力的极端自残行为也将女王隐喻为亚马逊一样的女魔,与“帕萨尔特地图”中残缺的野人如出一辙。但不敢具名的男性绘图师用锋利的雕刻刀将女王的乳房切掉,象征性地废除了其重要的哺育功能,而身世不明的大德洛米奥(23)将“女王”露丝的腹部和臀部极度拉扯成与身体等高的“无头”女怪,从而在经验空间中将女性的权威扼杀,手段之阴险残忍,令人触目惊心。
追根溯源,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是罪魁祸首,正如露西安娜劝诫阿德里安娜的那样:“只见雌的低头,哪见雄的服小?/……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是天经地义。”(《错》:2.1.393-394)相较而言,苏格兰宗教领导人约翰·诺克斯的观点则更具代表性,他认为:“提拔妇女来管理一个地区、控制一座城市或领导一个帝国都是有逆天道、有辱神灵和有违意志和传统的行为,从而颠覆了和谐的社会秩序和一切的平等和正义。……[没有任何怪物的身体比]执政帝国的女性身体更怪异,因为它要么缺乏合法的大脑,要么它就是真正头脑的虚像——即徒具大脑的外形,但缺乏其代表和期待的美德和力量。”(24)在诺克斯那里,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母权是对创世纪起源观念的背弃和男性主导地位的挑战,这和露丝用暴力强迫大德洛米奥成为夫婿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但“桀骜不驯的结果一定悲惨”(《错》:2.1.393),从而激起了大德洛米奥(莎士比亚?)对露丝(伊丽莎白)的厌恶情绪。与此同时,“女王二体”论既为女性统治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借口,但同时也将伊丽莎白置于怪物的不利局面之中——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经验世界里,不男不女的“第三性”都是一种偏离常规的异端,妖魔化的形象描绘在所难免。
总之,莎士比亚笔下露丝圆球般的身体就是诺克斯怪物般的女王政体言论的反映——要么代表理智和权威的头脑被削掉,要么缩入体内,变成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脑”圆形权力怪胎,象征爱尔兰、苏格兰和法国这样的“野蛮”之地。佩奇·杜波依斯尖锐地指出:“作为他者,异族、女性和兽类被排除……在文明和城市的边界之外,是地位相差无几的同类。”(25)在这样歧视性的文明与野地的二元对立中,男性日益成为权力的核心,女性则被逐出地图文明的中间地带,成为不毛之地和妖魔鬼怪的代名词,连万人景仰的女王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伊丽莎白的政治之体失去了应有的神性和美德,被打回普通女性的丑陋原形的传统描绘。
二、色情化的女王身体地图
女性妖魔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厌女症的出现,问题也随之产生:大德洛米奥会由此而禁欲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他的目光随即移向了代表西班牙的“热辣辣的嘴”,并最终停留在象征荷兰和比利时的女王下腹。但为了营造一种从厌恶到性想象的空间氛围,男性构图者臆造出了天使般的女性身体。面对天仙般的露西安娜,大安提福勒斯赞叹道:“你是我的纯洁美好的身外之身,/眼睛里的瞳人,灵魂深处的灵魂,/你是我幸福的源头,饥渴的食粮,/你是我尘世的天堂,升天的慈航。”(《错》:3.2.414)体现在地图中,则是“女王”的下巴。雪白的多佛岩壁等同于女王圣体的洁白无瑕,而高耸的岩壁护卫下的英国相当于撒克逊《英伦图》中受神恩庇护的女性“封闭花园”(Hortus Conclusus):英格兰被鲜花、水果和商船簇拥着,衬托出和谐安宁、繁星昌盛的人间天堂氛围,从而将女王身体隐喻为“《赞美诗》中的花园颂歌,处女之身的教会之体”(26),于是白垩庇护的多佛开创了不列颠历史的浪漫传奇。(27)即便是肥丑的露丝,仍然和伊丽莎白一样是待嫁的“女孩”之身,身上仍然还有一处白净的地方,从而极大缓解了大德洛米奥的厌女情绪,为接下来的性暴力提供了想象空间。
具体到“露丝”的身体地图中,西班牙与美洲看似构成了殖民征服的主体和客体,但同时也是女王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至少涉及西班牙与美洲、女王和美洲、西班牙与女王三组复杂的关系。自从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资助下发现新大陆以来,肥沃的美洲被喻为“一块令人想往的、凝视的和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处女地”(28),像丰腴的露丝身体一样蕴藏着大量的“宝藏”,成为西班牙大肆索取的对象,所以“西班牙热辣辣的气息一发现这些宝物,马上就派遣出大批舰队到她鼻子那里装载货物去了”(《错》:3.2.416)。从另一方面看,伊丽莎白和美洲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29)雷利爵士眼中的圭亚那像女王一样是“一个亟待被吮吸、翻转和压榨的处女国家”(30)。甚至美洲一些地区的命名也难脱干系,比如用以形容伊丽莎白的Virginia和Maryland,连以Charles(查理一世)和George(乔治一世)等国王命名的殖民地也被女性化为Carolina和Georgia,(31)色情想象不言而喻。但美洲并非西班牙的唯一目标,英国和伊丽莎白女王也是欲望的对象,菲利普二世企图以联姻的方式达到占有女王和英国的双重目的,却未能如愿。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战败,但这并不妨碍西班牙继续对女王抱有幻想和压榨新大陆(女性身体)的特权地位。
西班牙的强势显然引发了英国地图学家和艺术家们的忌妒甚至憎恨,于是身体地图成为挖苦对手和欲望满足的绝佳手段。1589年詹姆斯·李作品的卷首地图就是其中的范本,画面右下角大批西班牙舰队随时准备向英国和北美洲进发,半裸的美洲仰躺着,等待西班牙人再来“勘探和挖掘黄金;/强迫富裕的印第安人退却”。伊丽莎白女王则手拿一面国旗,坐在英国国土上,念着“耶稣,我唯一的希望”的祷词。(32)被西班牙强暴的美洲和面临失身威胁的女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问题在于,露丝“鼻子上的瘰疬多得不可胜计”却为何被喻为“翡翠玛瑙”,引得西班牙派大批舰队来搬运呢?而和露丝脸上一样留有痘痕的伊丽莎白女王(33)为何仍被西班牙国王胁迫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尽管女性的面容是丑陋的,但在贪婪的眼睛看来,痘疮也变成了宝石,更何况是热辣辣的肉体和与之对应的广袤而肥沃的处女地。由此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表征显示出女性身体和大陆之间的类同关系,于是针对女性化土地的探索、入侵和征服经常与引诱、插入和强暴联系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哥伦布的新大陆探险之旅、以菲利普亲王为首的西班牙对美洲的掠夺和对英国的入侵、大德洛米奥对美洲和西印度洋群岛的身体映射,都是隐喻的色情想象和欲望投射行为。
但镶有“宝石”的鼻子和热辣辣的嘴仍然不能满足旺盛的生理欲望,所以女性身体地图上的色情探索需要继续。于是大德洛米奥的目光从露丝的上半身移向了下面,此时比利时和荷兰成为天然的空间托词。大德洛米奥说:“那地方太低了,我看不下去。”这是一句非常形象的双关语。海拔很低、洼地众多的两国俗称为“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而它们恰好位于露丝身体地图的下腹,所以大德洛米奥认为该地方不堪入目。但他真的这样害羞和纯情吗?在小德洛米奥眼中,同胞的哥哥就是他的镜子:“看见了你[大德洛米奥],我才知道自己是个风流俊俏的小白脸。”(《错》5.1.449)可见大德洛米奥腼腆纯洁的背后是风流倜傥;尽管他的眼睛没有往下看,可心思却是下流的。同时比利时和荷兰被置于露丝身体的中心仍然包含了地图学的因素。从16世纪30年代伊始荷兰制图业迅速崛起,当莎士比亚创作《错误的喜剧》时,荷兰已经成为欧洲地图科技的中心。(34)此时大德洛米奥和荷兰的男性地图师的目的不谋而合,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建构了同一种欲望对象,形成了女性身体中心和地图中心合二为一的奇异空间意象。
从另一方面看,《错误的喜剧》中色情化的女仆身体地图也是“作为欧罗巴的伊丽莎白”地图的翻版。在古希腊神话中,贞洁的欧罗巴最后被乔装成公牛的宙斯玷污,(35)这其实已经暗示着后来女性不可逃脱的命运,即便是权倾一时的伊丽莎白也不例外。从视觉意象上看,丰腴半裸的女王仰躺在欧洲地图的母本上,仿佛在召唤甚至引诱异性的靠近。而为了逃避传统仁义道德的指责和制裁,这位手法精湛的制图师像宙斯和大德洛米奥一样改头换面,不同的是,宙斯凭借强大的超自然之力摇身变成一头白色的公牛,而世俗的画匠只能隐去象征自己身份的名字,大德洛米奥则不得不假借露丝的身份来免除后顾之忧。但无论他们如何刻意掩饰自身的外形标识,都不能遮蔽压抑已久的力比多爆发,宙斯采取威逼引诱的策略迫使欧罗巴就范,制图师利用象征性的刻刀完成了臆造中的女性殖民,大德洛米奥则依靠女仆身体地图将女王隐喻为生理欲望的对象,传说中的公牛是三位不同时期男权主义者的绝佳写照。
有的读者可能对圣洁的女王成为欧洲男性色情想象的论断依然心存芥蒂,乔尔·萨马哈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释疑。在调查了当时埃塞克斯郡的平民犯罪记录后,萨马哈发现了与女王名节相关的几起案例。1580年莫尔登镇的脚夫托马斯·普雷费尔宣称:“女王和莱斯特伯爵有染并育有两名私生子。”1590年农夫罗伯特·加纳更是坚信“莱斯特伯爵将他们扔进了烟囱烧死”。一位科尔切斯特镇的下人托马斯·温顿直言女王就是“一名清高的妓女”(36)。尽管这些造谣中伤的下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却印证了英国普通大众心目中对“淫荡女王”的揣测。既然有如此流行的民间诽谤传统,再加上戏剧角色的掩护,就不难理解同为下人的大德洛米奥的不敬之举了。更何况伊丽莎白女王一生与欧洲的王公贵族多次传出绯闻,无论是一种政治联姻策略或是真情流露,其圣洁的形象也因此大打折扣。这种不洁的名声、劣等的性别以及违背传统的母权社会制度都为主流社会所不齿,这是像大德洛米奥一样地位低下的男仆胆敢污蔑女王贞洁甚至意淫女王身体的深层次原因。而远离官学约束的社会底层恰好是进行巴赫金式身体嬉戏的理想场所,因为“狂欢是荒诞身体的庆典:丰盛膏腴的筵席,烈性酒、纵欲在这样的场景中官方文化被完全推翻巅灭”(37),从而生产出淫荡女王的性政治怪物。
从身体诗学的角度看,《错误的喜剧》中的女仆身体是对“女王二体”论的文学反拨,图中代表女王政治身体的神性被极端地妖魔化和色情化,从而降格为污浊、肥胖和淫荡的女仆肉身。这种文学化的地图戏仿后果无疑是毁灭性的,它彻底摧毁了女性仰仗的最高权威,也从反面证明了母权社会的虚构性。但和普通空间生产不同的是,地图由于女王身体的介入而添加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为打击异性和讽刺政治对手的理想场所。大德落米奥的空间想象由女性的奇特身形激发,在根深蒂固的女王身体地图传统的掩护下,女性身体部位的高低、洁浊、肥瘦和开合,转换为一种文明与野地、特权与臣服、亲近与疏远、纯洁与淫秽的二元性政治秩序——这的确是一项设计巧妙的文学地图创举,最终演绎成一种代表国家好恶的性政治地图学,同时建构了具有政治和人种学意义的身体地貌学。
在女性身体的地图隐喻中,大德洛米奥还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环球航行的另类探险者,他用伶牙俐齿而非坚船利炮开始了女性身体的描绘,从臀部开始,经过手心上升到额角,并在下巴、嘴和鼻子迂回一圈后,再下降到女性的腹部,从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绕体探索之旅。在此过程中裸露的女性变成了沉默的地图,任由男人凝视、蹂躏和勾勒,从而复制了一次带有暴力推进路线的史诗般的英雄救赎之旅,其终点往往是由女性把守的神庙或洞穴等超自然密闭中心,在剧中则指向“圣洁女王”的下体:“在此英雄得以重生。……为了女人,英雄必须历经野地的危险和探索女性身体——神庙或洞穴——的秘密,以实现繁殖的诺言。”(38)在这种浪漫化的英雄图式中,女王既是名义上的“仲裁者”(arbiter),也是男性冒险主义的牺牲品。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始积累中,女性成为整个男性民族歧视和殖民统治王国中的标志和代理,所以史蒂夫·派尔认为:“身体成为男性战利品的一个强点,权力的强大意义在此被激活,文化代码获得了显义的连贯性,而本体和他者的疆界被无情划定和接受。”(39)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女王身体和地图的诠释既是一种相互映射的文化行为,也预示着对土地探索和评估所带来的地理学欲望和愉悦:“无论运用何种图形装饰,欲望都是人体地图意象自身固有的属性。”(40)但《错误的喜剧》中的文学制图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男性欲望之旅,这种探索既是对女性身体各个部位的渗透,也是对身体内在的一种特殊评估——这种身体、土地和地图之间的类比成为现代早期欧洲性政治的一种焦虑和欲望的化身,于是地图提供了一种审视世界的专业化的政治学,涉及性别角色定位、国家身份转型和人类宇宙地位等重大历史命题,而戏剧恰好为此提供了完美的角色扮演和自我审视的舞台。从这种角度看,形象勾勒女仆身体地图变形记的“《错误的喜剧》并不是常人所说的简单甚至浅薄的闹剧和戏剧新手粗劣的习作,而是非常精妙和精确地利用戏剧媒介来审视困扰了莎士比亚一生的问题”(41)。
注释:
①引自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六卷本,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三幕第二场,第428页。本文《错误的喜剧》的引文均来自该译本。后面的引文只随文标出该剧名称首字和引文幕次、场次、页码,不再另注。
②据弗朗西斯·拉罗克考证,女仆地图极有可能取材于1588年塞巴斯蒂安·米尼斯特《宇宙志》中的女神地图;在佩奇·纽马克看来,露丝身体地图是“特定时空中的一种新型奇喻的身体图示探索”,藉此莎士比亚努力建立一种戏剧、地图和身体之间的跨空间映射(See Francois Laroque, "Shakespeare's Imaginary Geography," in Andrew Hadfeld and Paul Hammond,eds.,Shakespeare and Renaissance Europe,London:Nelson,2004,p.199; Paige Newmark,"'She is Spherical,like a Globe':Mapping the Theatre,Mapping the Body",in Shakespeare in Southern Africa 16[2004]15)。
③See Paige Newmark,"'She is Spherical,like a Globe':Mapping the Theatre,Mapping the Body",pp.15-28.
④身体和地图的结合最早也许可以回溯至古希腊,大力神阿特拉斯(Atlas,后转指地图册)力举天庭的神话可能是最为原始的空间雏形,二世纪的托勒密则经常采用天使口中的气流来代表地图的风向,而浑然一体的上帝、天使和地图则完美诠释了中世纪宇宙的乐园意象,并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See Leo Bagrow,History of Cartogra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p.1-76)。
⑤因为灵魂和肉体的甄别关系到世界本质的认知和真理的获取,所以柏拉图劝诫人们“不论老少,使你们首要的、第一位的关注不是你们的身体或职业,而是你们灵魂的最高幸福”(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基督二体论”认为,尽管耶稣的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另一身体因与上帝合一而得以永生,所以耶稣是“双体合一”(gemina persona)的典范。同时虔诚的信徒们相信教会也是耶稣身体:“它[教会]象征着一个神秘身体,头是耶稣,而耶稣的头是上帝。”这些观念为“国王二体”论的形成提供了哲学或宗教基石(See E.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p.49-147)。
⑥ E.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p.7.
⑦Lisa Hopkins,Writing Renaissance Queens:Texts by and about Elizabeth I and Mary,Queen of Scots,Newark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2,p 35.
⑧这种伪装是多方面的。改编自普劳图斯《孪生兄弟》的《错误的喜剧》的空间背景由埃庇丹努斯移向以弗所,与伦敦相去甚远。剧中的露丝胖得太过夸张,而原本就非常苗条的女王由于“歇斯底里”等症成为御医眼中“瘦骨嶙峋”的代表,两人的体形大相径庭。同时男仆大德洛米奥讽刺的对象是同为奴仆的女性,并没有违反以下犯上的道德禁忌,而任人蹂躏的女仆和号令天下的女王是很难联系起来的。同时第一对开本中的女仆分别被称作“Luce”、“Nell”和“Dowsabel”,用以混淆视听(See Stephen Greenblatt,et al eds.,The Norton Shakespeare,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Inc.,1997,p.685; Peter Blayney,The First Folio of Shakespeare,Washington,D.C.: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1991)。
⑨有诸多证据表明女仆露丝和女王的共通性。小德洛米奥在谈及露丝时将其比作“vestal”,即“负责在灶神庙宇中护火的圣女祭司”。尽管讽刺语气溢于言表,不意间却表明神圣的女王与“圣洁”的女仆(女祭司)之间类比的可行性。伊丽莎白也曾反复强调自己非常乐于扮演上帝的“女佣”和“侍女”。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上帝既可以指代耶稣,在现实生活中则等同于男性,所以伊丽莎白被贬低为仆人并没有破坏传统的性别秩序,何况女仆的肉身和女王的政体合一也暗合“女王二体”论的政治哲学(See Stephen Greenblatt,et al eds.,The Norton Shakespeare,p.719)。
⑩在英国文艺界女王地图意象非常流行,比如《仙后》中女骑士布丽托玛特说道:“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地图指引,/远离故土大不列颠,来此祈祷福祉。”她背井离乡却没有误入歧途,只因受惠于更为准确和神圣的航标指引,藉此斯宾塞显示出对宇宙秩序和神圣地图的景仰和称颂,同时表达对美和善的化身——伊丽莎白女王的崇敬和赞美(See Arthur F.Kinney,Shakespeare's Webs:Networks of Meaning in Renaissance Drama,New York:Routledge,2004,p.122)。
(11)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12)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曾说,他有幸得到上天的三种赐福:“人类而非畜生……男性而非女人……希腊人而非蛮夷。”(Page duBois,Centaurs and Amazo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1)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文明的宇宙图式中女性已经开始与野兽和蛮夷并置在一起。
(13)Evelyn Edson,Mapping Time and Space:How Medieval Mapmakers Viewed Their World,London:British Library,1997,p.135.
(14)See J.B.Harley,"Text and Contex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aps",in Paul Laxton,ed.,The New Nature of Map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34-49.
(15)Leo Bagrow,History of Cartography,p.162.
(16)L.Tommaso,"'Th'receiving earth':Shakespeare and the Land/Woman Trope",in Textus 18(2005)272.
(17)See Kenneth J Panton,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Monarchy,Plymouth,UK:The Scarecrow Press,Inc.,2011,pp.456-465.
(18)Jean Bodin,The Six Bookes of a Commonweale,Richard Knolles,trans.,K.D.McRae,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746.
(19)See John Gillies & Virginia Vaughan,eds.,Playing the Globe:Genre and Geograph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Lon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98,p.14.
(20)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了英格兰,1347年英国占领加来港,1558年法国将其收复,1562-1563年英国又强占了勒阿弗尔港(See Leonie Frieda,Catherine de Medici,London: Phoenix Press,2005,pp.170-191)。
(21)See Paige Newmark,"'She is Spherical,like a Globe',Mapping the Theatre,Mapping the Body",p.18.
(22)从词源学上看,Amazon来自amazos,意为“没有乳房”(See "Amazon":J.Simpson& E.Weiner,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3)大德洛米奥是埃必丹农一家客店里的“穷人家的妇女”所生,此后沦为奴仆(《错》:1.1.386)。
(24)John Knox,The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1558,rpt,New York:Da Capo Press,1972,pp.9-19.
(25)Page duBois,Centaurs and Amazons,p.1.
(26)Margaret W.Ferguson et al.,eds.,Rewriting the Renaissance:The Discourses of Sexual Differ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130.
(27)多佛白崖是英国历史的象征,不列颠的古名Albion(白色)就是取自于此。凭借紧靠欧洲大陆的地理优势,多佛在古罗马时期就是战略要塞,也是凯撒大帝登陆英伦时的桥头堡,日耳曼部落大规模移居不列颠时多佛则是一个主要的定居点。而在《李尔王》中多佛既是王朝的终点,也预示着另一个统一时代的来临,所以萝莉·玛格伊尔认为多佛是不列颠国家身份的开端(See Laurie Maguire,Studying Shakespeare:A Guide to the Plays,Oxford:Wiley-Blackwell,2003,p.42)。
(28)Christopher Columbus,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Four Voyages of Columbus,Cecil Jane,trans.,and ed.,London:Hakluyt Society,1930,p.12.
(29)1584年华尔特·雷利受女王委派到北卡罗来纳海岸成功建立了罗阿罗克殖民地,1585年约翰·怀特受命去弗吉尼亚探险,最终绘制出实用的探索地图(John Gillies & Virginia Vaughan,eds.,Playing the Globe:Genre and Geograph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pp.63-64)。
(30)Walter Raleigh,The Discoverie of the Large,Rich,and Bewtiful Empyre of Guiana,Neil L Whitehead,ed.,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96.
(31)See John Gillies & Virginia Vaughan,eds.,Playing the Globe:Genre and Geograph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p 63.
(32)See Kristen G.Brookes,"A Feminine 'Writing that Conquers':Elizabeth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 in Criticism 48.2(2006)230.
(33)1562年29岁的伊丽莎白患上天花,虽然有幸存活下来,脸上却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痘痕,从此不得不用浓妆来掩盖/(See Jonathan B.Tucker,Scourge:The Once and Future Threat of Smallpox,New York:Grove Press,2001,p.14)。
(34)See J.R.Short,Making Space:Revisioning The World,1475-1600,Syracuse,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8-29.
(35)See Richard Buxton,Forms of Astonishment:Greek Myths of Metamorphos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0.
(36)Joel Samaha,"Gleanings from Local Criminal-Court Records:Sedition Amongst the 'inarticulate' in Elizabethan Essex",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8.4(Summer,1975),p.69.
(37)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38)Jeanne Addison Robe rts,The Shakespearean Wild:Geography,Genus and Gender,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1,pp.27-28.这也是《错误的喜剧》整个空间轨迹的缩影:来自文明中心叙拉古的孪生兄弟为了身份的认同而流落到了蛮夷之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并在“道行高超”的女尼把守的庵院了解到自己的身世,最终续写了缺失多年的男性历史。
(39)Bruce McLeod,The Geography of Empire in English Literature,1580-17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26.
(40)John Gillies,"The Scene of Cartography in King Lear," in A.Gordon & C.Bernhard,eds.,Literature,Mapping,and Politics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91.
(41)Stephen Greenblatt,et al eds.,The Norton Shakespeare,p.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