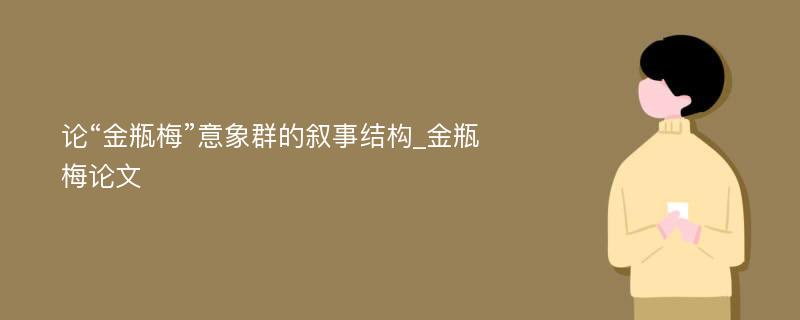
论《金瓶梅》的意象群叙事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意象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4)06-0109-11 一、引言 关于《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人言言殊,从一个角度证明了“第一奇书”的艺术张力,正在于阐释无穷尽。亦由于阐释无穷尽,使得任何一种阐释都难以臻于圆满。所以,通过这部小说的意象群分析,从文本内部来解读《金瓶梅》的叙事结构,或为探究这部巨著艺术魅力的途径之一。 作品的叙事结构,从来都不仅仅是艺术形式问题,它必然同时是思想内涵的表现。《金瓶梅》的叙事结构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当之无愧的范本,它包涵了深邃的人生哲学命题和深刻的社会生活本质,开创性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这部小说以五大意象群作为其叙事结构的基础,正表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说《金瓶梅》以意象群为主要叙事结构,只是阐释这部小说的一个视角,其有理或无理,愿听高明赐教。 一方面,缘于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的渊源关系,史传的结构或曰体例,深远地影响着小说结构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并成为与思想内容不可分割的整体。如《史记》的五种体例,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卓越历史观,也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局面。张竹坡之所以在《金瓶梅》评点中以《史记》为参照,亦因他参透了这两部在各自领域中划时代巨著的结构方式,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后者借鉴了前者而运用于通俗小说的创作。所以,叙事结构是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所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不仅在其《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的开篇,连续十条集中谈论这个问题,而且在一些回评中亦屡屡提到,唯恐读者不能领略作品的艺术匠心及其中的意蕴,真可谓用心良苦。形式与内容的相互依存,结构和思想的相互呼应,不是评点家的臆想,而是小说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诗国,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使后来成熟的小说和戏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诗化的倾向。中国古典小说不仅与史传有渊源,它同时还与诗歌传统密不可分,是学界早已有之的论断。意象理论,亦是从诗歌进入到小说批评领域的。作为一部世代累积、最终经文人写定的小说,《金瓶梅》的意象群叙事结构,使小说可以更好地演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世态人情,从而也能够更好地彰显小说艺术的传承和进步。 在先秦哲学中,“意”“象”概念已经分别提出,这是意象论的起点。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1]。这主要指理性的、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够完全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所以,需要通过鲜明具体的形象,表达难抒之情、难言之理,进而造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不过,《周易》中的“象”指卦象,基本上属于哲学范畴。后世文学理论借用“意”“象”并引申之,“象”已不是卦象所显示的抽象符号,而是用来寄托“意”的、具体可感的物象。在文学理论批评中,刘勰最早使用“意象”一词:“独照之象,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2]“意象”从此进入到文学批评中,后起的小说创作和评点,也受到其影响。但这也和意象范围的扩大有关。在诗词中,意象之“象”的摄取,由大自然中的四季变迁、山川风物等扩展到人类社会,取象的范围更大了,各色人物、生活场景、情节史实、人文古迹……所有的“事”,都可以是“象”。由此可见,意象理论进入到叙事文学的批评中,是极为自然的。再者,正如使用比喻这一手法,既可以用单个的喻体去描绘本体,也可以用一连串的喻体(博喻),从不同的角度去描绘本体一样,意象既有单个的,也有成系列的(意象群)。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的意象群叙事结构,是作品匠心独运的艺术杰作,也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金瓶梅》中的意象正如这部小说所表现的生活一样,林林总总,气象万千,故本文“群”而论之,以“五”为数,即深知难以尽其大略,只不过是绎其中重要者而已。要之,宗教意象群具有形而上的地位,统摄了小说劝世意图与叙事结构的对称效应;心理意象群具有张本作用,预示了人物命运的大体走向;时间意象群具有推进作用,形成了人物和家庭命运发展的大致时序;空间意象群具有写实意义,呈现了人物关系和场景发生的典型环境;人物意象群具有核心地位,承载了主人公及其家庭由暴发至没落的完整过程。以上意象群最终构建了《金瓶梅》线性与网状并行不悖的综合性叙事结构,推动了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并使《金瓶梅》具有了现代小说的主要特点,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向现代转变的代表。其实,早在《金瓶梅》成书之时,已经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因而成为《红楼梦》的重要借鉴。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个人语境中,人们对作品的阐释必然会有所不同,但在一脉相承的文化背景下,面对同一部作品,古代批评家慧眼之所见,对今天的研究不会毫无益处。古代评点家的批评方式是直觉感悟式的,其精彩之处往往犹如电光火石般耀眼,对现代小说批评仍有借鉴意义。不过,它终究存在评点这一古代文学批评方式难以避免的缺陷,故不应成为我们的门限。此乃《金瓶梅》意象群叙事结构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二、宗教意象群 在《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中,宗教意象群具有形而上的地位,统摄了小说劝世意图与叙事结构的对称效应。小说以它被世俗化了的人生哲学形态,诠释主要人物和家庭命运兴衰终始的原因,其载体则主要是二寺一观和三个僧道人物。这一意象群叙事层面,与小说想要表现的世俗人生哲学是基本对应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金瓶梅》宗教思想的表现是比较复杂的,其中道、释并行而以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最为突出。这既是《金瓶梅》表现世俗人生的需要,也是其叙事结构的需要,二者在小说中相互对应,和谐统一。 (一)寺观意象是大关键处 《金瓶梅》笼罩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这一状况是毋庸置疑的。世俗化的佛道思想渗透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表现为西门庆及其家人和市井、僧道各色人等的迷信活动和幻境呈现,作为小说叙事结构的主要意象,则以玉皇庙、永福寺这两个道佛寺观最为显著,其次还有报恩寺。玉皇庙和永福寺意象,在《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中所暗示的西门庆及其家庭兴衰终始,是极富象征意义的。 永福寺在《金瓶梅》材料来源之一的《戒指儿记》中也曾提到,但这个短篇只是一笔带过,而在《金瓶梅》中,它却成为重大事件发生的重要场地之一。对此,张竹坡说道: 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齐说出,是大关键处。[4](《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接着,他又一再点明这两个地点在小说叙事结构中所处的关键地位: 玉皇庙、永福寺,须记清白,是一部起结也。明明说出全以二处作终始的柱子,乃俗批‘伏出’,可笑,可笑。[5](第一回张竹坡夹批) 玉皇庙、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结。[6](第四十九回张竹坡回评) 如果我们放眼看全书,便可知张竹坡此言不虚。二寺的出现,在全书中竟涉及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崇祯本共涉及二十回,词话本共涉及十九回)。由于它们在小说的结构中位置极为重要,曾有学者对这两个寺庙在小说中的出现进行过梳理。② 崇祯本改第一回为玉皇庙热结十兄弟,张起了西门庆这个市井暴发户的旗帜(词话本永福寺始见于第十四回),而两个版本相同的部分,如第三十回,西门庆得子加官,在玉皇庙许了“一百一十份醮”;第三十九回,腊月里玉皇庙的吴道官送来了四盒礼物,正月初九西门庆又在玉皇庙中修斋建醮,为官哥儿寄名,表现了他生子加官后的泼天富贵——且不说那场面和气派,只看西门庆那身“大红五彩狮补吉服,腰系蒙金犀用带”的装扮,即可知道他此时是何等的志得意满。作品鞭辟入里地批判了西门庆坏事做绝,却以为只要有钱贿赂佛祖,即可保其荣华富贵的市井暴发户无赖嘴脸:早在第四十九回,西门庆极其得意地在永福寺为蔡京的义子、新科状元、巡按御史蔡蕴摆酒饯行之后,小说就埋下了一个伏笔,这天西门庆在寺中忽遇胡僧赠之以春药,为李瓶儿之死及其自身最终纵欲身亡的祸根。然而西门庆并不知祸已不远。第五十七回小说专写永福寺,又特为写吴月娘劝丈夫少干几桩贪财好色的事体,积下些阴功与官哥儿,西门庆却回答说: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7] 西门庆的贿佛行为显然没有任何结果,正是:“虽千金之施,何益身命?止足为败亡之因。”[8](第五十七回张竹坡回评)第八十八回,潘金莲被春梅收尸埋葬在永福寺,接下来第八十九回,清明节,吴月娘、孟玉楼给西门庆上坟而误入永福寺,遇见了已为周守备夫人的庞春梅,今非昔比,尊卑颠倒。最后一回在永福寺中西门庆被普净法师超度而去,其唯一的儿子孝哥儿亦被幻化。无论玉皇庙曾有过多么豪华的场面,但在永福寺中,一切曾经的荣华富贵,到头来都只不过是大梦一场。 值得注意的是,除这一观一寺外,清河县还有一个报恩寺,亦为小说多次提及,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第六十七回,把它和玉皇庙、永福寺合在一起说: 篇末将玉皇庙、报恩寺、永福寺一总。夫玉皇庙,皆起手处也;永福寺,皆结果处也;至报恩寺,乃武大、子虚、瓶儿念经之所,故于此一结之。是故报恩者,“孝”字也,惟孝可以化孽……[9](第六十七回张竹坡回评) 报恩寺供武大郎、花子虚、李瓶儿诸人烧灵、化纸、念经,张竹坡认为这表明“惟孝可以化孽”的理念。但这个说法比较牵强。如第八回,西门庆教王婆到报恩寺请了六僧,在家做水陆道场超度武大,并晚夕除灵;第十六回,李瓶儿单等五月十五日,妇人请了报恩寺十二众僧人,在家念经除灵;第五十九回,官哥儿死了,到三日,请报恩寺八众僧人在家诵经;第六十七回,李瓶儿“六七”,那日玉皇庙,永福寺、报恩寺多送疏。这些情节全然与礼教之“孝”无关,是点评者为沉溺于“酒色财气”者开出的一剂自我救赎良方,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这完全不管用。报恩寺在作品中被淹没在玉皇庙的闹热和永福寺的冷清之中,是超度一般死者、宣扬六道轮回的宗教意象。只有主张《金瓶梅》“苦孝说”的张竹坡,苦心点出了他所理解的报恩寺意义。在前八十回中,玉皇庙和永福寺的场地及僧道,用途虽是生死交织的,但且不说在玉皇庙为得子加官之类办的庆贺喜事,即使是为死者举办的法事,都是西门庆势焰的表现。然而,此后的五回(直到全书结束),笔墨全在借永福寺及其僧道,写西门庆死后家一败涂地的景象。作品似乎表明,西门庆气焰胜时,鬼魂且要退避三舍,而当其衰败之后,永福寺寒气逼人,最终成了“阴风凄凄,冷气飕飕”鬼魅世界,从而代替现身说法,完整地诠释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世俗人生哲学。 (二)道释人物意象是大照应处 和寺观意象一样,三个宗教人物意象在全书中的出现,也是小说带有强烈市井气息的宗教意识与叙事结构相称的表现: 先是吴神仙,总揽其胜;便是黄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净师,一洗其业。是此书大照应处。[10](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张氏评语。就《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而言,这三个角色无疑是次要的,但在其叙事结构中,他们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意象。这正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一样,你可以说她是次要的,却不能说她是不必要的。在崇祯本中吴神仙首次出现于第一回,在词话本中则首次出现于第二十九回,这一回和第四十六回、第七十九回,则为二本所共有。吴神仙在这部小说不同的版本中究竟出现了几次,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前几回出现在西门庆气运蒸蒸日上之时,他最后一次出现时西门庆却已无可救药,最终一命呜呼,故吴神仙“总揽其盛”。黄真人就不同了,当他出现在第六十六回的时候,李瓶儿已经死了,他来西门家就是做法事超度李瓶儿的。这时西门庆在朝中的靠山杨提督也死了,预示了西门庆的大势已去,其家亦由兴盛而走向衰落,故黄真人“少扶其衰”。普净法师出现在小说的第八十四回,预约下十五年后度化孝哥儿,最后出现在全书收官的第一百回,超度了西门庆等众生,并幻化了孝哥儿,他是人鬼通灵的桥梁,故“一洗其业”。这三个宗教人物作为意象,出现在西门庆及其一家由兴盛而走向衰败的关键时刻,这既是作品叙事结构的精心安排,也是作品思想内容的艺术呈现。 三、心理意象群 在《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中心理意象群具有张本作用,预示了人物命运的大体走向和最终结局,其中包括命理意象和梦境意象两种基本类型。 我们之所以把这类意象称为心理意象群,是因为人物命运的走向,以心理暗示的形式被作品预伏于前,而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则被验证于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也受到心理暗示作用的影响,即如潘金莲对算命的感觉是:“说的人心里影影的。”[11](第四十六回)在《红楼梦》出现之前,心理意象已广泛地见之于小说和戏曲,但很少有人以大段的篇幅,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像《金瓶梅》这样用心理意象群来结构作品,亦为鲜见。心理意象出现在人物已经登场,而前途未卜之时,为人物的命运做出预言。由于心理意象群在《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中地位非同小可,所以,用通常的伏笔这一名称,不足以表明其重要性。关于张本式叙事结构,早在史传评点中就有人指出。如《左传隐公五年》道:“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晋代杜预注:“晋内相攻伐……传具其事,为后晋事张本。”唐代刘知几《史通浮词》更为明确地说道:“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疎,错综逾密。”《金瓶梅》以心理意象群为叙事结构的方式,为后来的《红楼梦》继承并加以发展。《金瓶梅》中的命理分析和人物梦境意象,有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所见“金陵十二钗”图册和文字,以及王熙凤梦见秦可卿、梦见与人夺锦等梦境,构成了作品独特的心理意象群,成为全书主要家族和重要人物命运发展的提纲。当然,由于章回小说的发展和个人创作高度成熟的缘故,《红楼梦》对这一结构技巧的使用,要比《金瓶梅》更为复杂,艺术含量也更高,可谓后来居上,后出转精。看到《金瓶梅》心理意象群的内涵,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把握其叙事结构,感受到人物命运发展在作品整体结构中的审美效果。 (一)命理意象是主要人物命运走向和终结的大纲 在人物的命运走向中,命理一般指生死和贫富,必然与偶然的遭遇。在其最原始的意义上,或许应当称之为卦象。但《金瓶梅》的这类意象,表面上虽然是指算命和算命之术,但究其实,则是作品安排人物命运走向的大纲。换言之,这是小说叙事结构的方式之一。在《金瓶梅》中,人物命理意象出现过三次:第二十九回、第四十六回、第九十六回。 第二十九回写吴神仙给西门庆及其众妻妾算命,张竹坡批评道: 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12](第二十九回张竹坡回评) 张竹坡的这个理解不错,但作品如此安排,显然并非简单地唯恐下文“或致错乱”,而在于众人命理意象的神秘指向,正是以西门庆为中心的人物群体及其家族命运的走向。命理意象处于小说的中部,为上二十八回已一一写出来的主要人物“遥断结果”,显然不是从篇幅而是从叙事结构着眼。在《金瓶梅》的这一叙事结构中,人物、事件和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同织网般纵横交错,进而在全书主要人物命运内驱力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走向各自应有的结局,家族命运亦如此。在吴神仙相人这个场景中,不仅西门庆及其家中的主要人物都集中出场,而且之后通过吴月娘和春梅对算命结果所发的议论,进一步强化了命理意象在作品叙事结构中的重要性,给读者留下了的深刻的记忆。在送走吴神仙后,西门庆与吴月娘、庞春梅分别有如下对话: 月娘道:“相春梅后日来也生贵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孙也看不见。我只不信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也轮不到他头上!”……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说戴珠冠,教大娘说‘有珠冠只怕轮不到他头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13](第二十九回) 作品还不失时机地再次突出了潘金莲的心理,用以强化其命理意象的结构意义: 刚打发卜龟卦婆子去了。只见潘金莲和大姐从后边出来,笑道:“我说后边不见,原来你们都往前头来了。”月娘道:“俺们刚才送大师父出来,卜了这回龟儿卦。你早来一步,也教他与你卜卜儿也罢了。”金莲拉头儿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说毕,和月娘同归后边去了。正是:“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14](第四十六回) 吴神仙相面和卜龟儿卦,都发生在西门庆运势上升之时,故未涉及陈经济。到第九十六回叶头陀为陈经济相面,才全面补出其命理。这是因为陈经济在“正经香火”[15](第三回张竹坡回评)西门庆死后,成了《金瓶梅》的男主角。所以,这次相面和前两次不同,陈经济的命理意象,前面是对其已往运程的印证,后面是对其结局的预言,表现了作品在叙事结构上的艺术匠心。 (二)梦境意象是主要人物命运结局的强化 “自古梦是心头想”[16](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这话没错。《金瓶梅》梦境意象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 第六十七回,西门庆第一次梦见瓶儿,瓶儿劝说他没事时少在外头过夜,早早来家,张竹坡在评点中指出,“此回瓶儿之梦,非结瓶儿,盖预报西门之死也”[17](第六十七回张竹坡回评);第七十一回,西门庆又梦李瓶儿,仍是切切交代前梦所言,此时离西门庆死期已然不远。这两个梦本为李瓶儿指点迷津,回头是岸,但“西门不死,必不回头”[18](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意味着大厦将倾,势无可回。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命在旦夕,吴月娘再次请来吴神仙看其命运如何,吴神仙说已无回天之力,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如何?”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吴月娘只好求其圆梦: 月娘道:“禽上不好,请先生替我圆圆梦罢。”神仙道:“请娘子说来,贫道圆。”月娘道:“我梦见大厦将颓,红衣罩体,攧折碧玉簪,跌破了菱花镜。”神仙道:“娘子莫怪我说,大厦将颓,夫君有厄;红衣罩体,孝服临身;攧折了碧玉簪,姊妹一时失散;跌破了菱花镜,夫妻指日分离。此梦犹然不好!不好!”月娘道:“问先生有解么?”神仙道:“白虎当头拦路,丧门魁在生灾。神仙也无解,太岁也难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19] 这梦境迫使吴月娘最终把孝哥儿交给了普静,草蛇灰线,伏脉数年,至此才完结了西门庆断子绝孙的结局,而作品的回末诗,也在心理上圆满地实现了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愿望。市井妇孺皆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被安排得极其耐人寻味,表现了之前长篇章回小说所未达到艺术效果。 四、时间意象群 在《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中,时间意象群具有推进作用,形成了人物和家庭命运发展的大致时序,其中包括了年代、数字和春夏秋冬等基本类型。《金瓶梅》的时间意象群,最为充分地表现了小说与史传的渊源关系。关于这一点,张竹坡是这样说的: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开口云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乃卒于戊戌。夫李瓶亦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此书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月某日请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捱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账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眯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20](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不论人们作何解释,时间的流逝,在《金瓶梅》中都确实存在不合情理的“参差”现象③,但对于小说而言,这一般是可以不予追究查实的。④不过,虽然张竹坡在时间上把《史记》和《金瓶梅》进行模拟,但他也明显地感觉到了小说毕竟不同于史书,明显地感觉到了《金瓶梅》中的时间,带有意象性和追求叙事艺术效果的特点,并非如同史书那样确凿真实,此即作品“故为参差之处”、“故特特错乱其年谱”的用意之所在。在时间上,《红楼梦》显然比《金瓶梅》更为“错乱”,却取得了比之更为模糊的审美效果,可见这是小说艺术的进步。一方面“不敢以小说目之”,这是张竹坡对《金瓶梅》地位的抬高;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它毕竟是小说,这指出了《金瓶梅》时间意象有不同于史书之“神妙”。本文不论一般时日和主人公年纪,只说其中的春夏秋冬,以阐明时间意象群在这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重要意义。 《金瓶梅》中的春夏秋冬是顺其自然的,如描写春天。“春者,天之和也。又春,喜气也,故生。”(《尔雅·释天》)“春者何,岁之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所以,《金瓶梅》常以春的意象来表现西门庆的运势上升。小说前半部第十五回、第四十二回、第四十六回三次写元宵节,无论是豪客玩斗烟火,佳人高楼赏灯,还是西门庆妻妾夜游遇雪雨,景象全是一片春光旖旎,呈现了其家运势如春之勃发,欣欣向荣的情景。特别是第十五回的元宵节,西门庆众妻妾登楼笑赏元宵灯火,街坊众邻指着潘金莲和孟玉楼二人,道是“阎罗大王的妻,五道军将的妾”,从侧面表现了此时西门大官人的势焰熏天。又如描写夏季的第二十七回,暗示西门庆即将有子嗣以延香火;第三十回则西门庆既生子又加官,双喜临门,表现了他炙手可热的权势。这两回的季节描写,都应合了炎夏之象。 但《金瓶梅》并不完全以常理来描写春夏秋冬,而往往运用逆向描写,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第十回写西门庆利用其下达知县,上通天庭的恶霸势力将武松发配到孟州后,叫下人“收拾打扫后花园芙蓉亭干净,铺设围屏,悬起金障,安排酒席齐整,叫了一起乐人,吹弹歌舞,请大娘子吴月娘,第二李娇儿,第三孟玉楼,第四孙雪娥,第五潘金莲,合家欢喜饮酒。”[21]这时的节令虽为秋天,场景却毫无萧瑟之气,一片花团锦簇,表现了西门庆心情畅快,志得意满的样子。又如冬季本来是肃杀的,但第二十一回描写吴月娘和西门庆和好,大家扫雪烹茶,可谓内外和谐,家运兴隆,冬的逆象被反转过来了。又如上文说到作品三次写正月十五的意象,都表现了西门庆运势的上升,但正月新春的意象,在《金瓶梅》中也有大大的例外。如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之死:“到于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时分,相火烧身,变出风来,声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捱到早辰巳牌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 四季轮回,象虽为一,兴衰的意义却可以完全不同。《金瓶梅》非常善于运用四季意象的不同内涵来结构小说,打破了陆机、刘勰四季轮回、心物感应的表象,而更接近于钟嵘四季轮回与人事变迁的深层感应。⑤冷中有热,热中有冷,《金瓶梅》的四季意象,令人无限悲凉地领略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深刻人生哲理,更何况在《金瓶梅》中,四季意象的每一次出现,都有意无意地暗合着主要人物的命理意象,充分表现了这部小说叙事结构之精巧。 五、空间意象群 在《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中空间意象群具有写实性,呈现了人物关系和场景发生的典型环境,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论者所说的象征意义。 从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过程看,把故事情节作为叙事结构的主要模式形成最早,其后是在情节向前运动中表现人物性格,把环境作为小说描写的重点,让人物活动于其中并刻画个性,要到《金瓶梅》才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已注意到此。他说: 读《金瓶》须看其大间架处。其大间架处则分金、梅在一处,分瓶儿在一处。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处。金、梅合而瓶儿孤,前院近而金、瓶妒,月娘远而敬济得以下手也。[22](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这里虽云“大间架”,但究其实,在这部小说的整体叙事结构中,它只不过是一个角度而已。《金瓶梅》的空间意象是一个群体,它是多层次的,张竹坡说:“因一人写及一县。”⑥“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23](第七十回张竹坡回评)话说到此,已揭示了《金瓶梅》空间意象的群体特点。张竹坡所言“大框架”,实际上可视为《金瓶梅》空间意象群的基础。西门大院是中心,包括内屋的前后院、前后花园,让家里的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穿穿走走,做这些故事也”⑦。西门大院外是市井(主要有清河、临清二处):围绕西门庆及其家人而出武大、花子虚、乔大户、陈洪、吴大舅、张大户、王招宣、应伯爵、周守备、何千户、夏提刑、王六儿、贲四嫂、林太太等人家和丽春院。没有这些人家和丽春院,就画不出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和市井风貌。市井之外是朝廷及大大小小官吏:以蔡京为首,其下蔡御史、宋御史、杨提督、府县等各级官吏皆与西门庆往来,庇护其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包揽诉讼,欺压良善。小说以层次极为丰富的空间意象群,以三维交错的空间结构,展开对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式描写。在此前的中国小说中,从未出现过这样复杂的空间结构,因而也就没有展现过如此丰富而厚重的现实生活。《金瓶梅》的空间意象群之宏大,在中国小说的古典时代,唯有《红楼梦》可以与之相比。 作为《金瓶梅》空间意象群基础的西门大院花园,在小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叙事意义,对此张竹坡在“第一奇书”评点的《杂录小引》中作过详细的分析。他指出小说居室安排的实质,是为了表现西门庆家中众妻妾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仪门外花园内,一院里住了潘金莲和春梅,另一院住了李瓶儿。一个花园内“金瓶梅”俱全,非如此不足以表现三个女主角(实际上是金、梅和瓶儿双方)之间的斗争,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与此相反,吴月娘住在离花园较远的仪门外上房,非如此不能够在西门庆死后,为陈经济插足等后面的故事和人物刻画留下余地。西门大院外市井和朝廷这两层空间意象的意义,则在于表现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随着人物活动范围的扩大,小说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张力也就更为强大了。 还有必要说一说临清这个空间意象,这是《水浒传》里所没有的。《金瓶梅》与临清的关系可谓伏脉千里,终成结穴。临清在全书出现过二十余次,集中于最后八回。前面只在第五十八回(临清钞关)、第七十七回、第八十一回中出现过,多关商贩货运之事。到最后八回,临清成为《金瓶梅》的主要叙事空间。由清河的西门庆家转向临清,作品主要叙事空间的转移,具有两重重大意义:第一重意义为以全书男主人公的转换,强化作品轮回、果报的劝世意图。第二重意义为扩大作品的叙事空间,进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 《金瓶梅》的空间意象群,架构了小说叙述故事的典型环境,各个层次的人物在不同层次的空间中自如活动的同时,命运又有所交集,小说也从而自如地描写了人物的共性和个性。西门大院→市井→朝廷,在这个三维空间中,《金瓶梅》的各色人等演绎着各自的俗世人生,展示着各不相同的个性特点。 六、人物意象群 在《金瓶梅》的叙事结构中,人物意象群具有核心地位,承载了主人公及其家庭由暴发至没落的完整过程。全书主要人物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纵横交错,在相互牵扯中走向各自的结局。这一叙事层面极为复杂,可以涵盖人物塑造最广义的内容,然而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它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意义。 按照张竹坡的说法,《金瓶梅》的人物描写运用了两分法:“千百人总合一传”与“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24](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我们说《金瓶梅》的人物意象群,主要是指后者。从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中各抽取一字合成书名,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并不是第一部⑧,在外国文学史上则未见之。外国小说如果要以书中的人物作为书名,往往是取主人公的姓名。《金瓶梅》的命名与外国小说的不同之处,还有它虽以书中的主要人物来命名,但全书的中心人物是西门庆,而并非书名上的三个女性。《金瓶梅》这书名本身就是一个人物意象群,可以引起读者的无限联想,从而衍生出诸多解释。在这个书名的后面,隐藏着真正的主人公。在对这个书名的诸多解读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张竹坡的解读: 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25](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张氏说人家是“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其实他自己也是劈空从这三个人入手,开始对这部奇书之点评的。他把这个点评置于其“第一奇书”批评的开篇,确实深中肯綮。金、瓶、梅三人在这一部大书中,分别承担了西门庆及其家庭地位上升、鼎盛、衰败等三个不同阶段的重要角色和叙事功能,见证了全书“正经香火”西门庆及其家庭由暴发至没落的全过程。她们是仅次于西门庆而环绕西门庆、绾合《金瓶梅》众多人物的主要角色,西门庆和她们三人的命运既是这部小说的主线,又在与其它人物命运的共时空交错中,产生出一个个新的故事,构成一个个结点,从而表现出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基本风貌。这样的叙事结构在此前和之后的长篇小说中都是鲜见的,《金瓶梅》却以创新取得了比较圆满的艺术效果。 《金瓶梅》写了家庭、市井、朝中的不止一类人物意象群:女性如妻妾、使女、妓女;男性如帮闲、戏子、大小官吏;僧道如三姑六婆,和尚道士——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丰富多彩,但作为书名,小说只抽取了金、瓶、梅三个人物的名字形成意象。作为对全书人物意象群的总概括,这并未削弱《金瓶梅》对“正经香火”西门庆形象的塑造。⑨相反,“金瓶梅”作为人物意象群的代表形成书名,其象征性及其所带来的阐释无穷性,更增强了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 七、结语 《金瓶梅》的五个意象群是相互交织、有机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承载这部小说厚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叙事结构。有别于“四大奇书”的其它三部,《金瓶梅》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长篇小说的描写对象,这决定了其叙事结构不可能是单线型发展模式(如《三国演义》按历史发展、《西游记》按唐僧、孙悟空传和八十一难来结构小说,《水浒传》以逼上梁山为主线缀以英雄传),而必需以多侧面的呈现,打破此前中国长篇小说的单线型结构模式,构建起以综合立体为特点的叙事结构,这样才能够充分表现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人物性格的生成和发展。在这个综合体中,传统小说追求故事情节艺术的趋向已然淡化,更谈不上曲折到引人入胜,对于这部洋洋百回的大书,鲁迅只不过用了二百来字,就将其情节概括出来了: 书中所叙,是惜《水浒传》中之西门庆做主人,写他一家的事迹。西门庆原有一妻三妾,后复爱潘金莲,鸩其夫武大,纳她为妾;又通金莲婢春梅;复私了李瓶儿,也纳为妾了。后来李瓶儿、西门庆皆先死,潘金莲又为武松所杀,春梅也因淫纵暴亡。至金兵到清河时,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到济南去,路上遇着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佛法感化孝哥,终于使他出了家,改名明悟。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26](《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 虽然情节的地位在《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中已然淡化,但其极富创新意义的叙事艺术,却为小说展开了无穷无尽的描写天地,本文所述五大意象群,是《金瓶梅》全书综合叙事结构的基本呈现。所以我们不妨说,早在《金瓶梅》出现之时,中国小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就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这部小说因而成为《红楼梦》创作最为重要的艺术借鉴。鲁迅对《红楼梦》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著名论断,其实是就清代小说而言,并不包括产生了《金瓶梅》的明代,但他对《红楼梦》这个方面的评论,同样适合于《金瓶梅》⑩,后者之于前者实在是青出于蓝。清代以来都有评论家指出《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借鉴,如说:《红楼梦》“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壸奥。”[27](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由《水浒传》而衍出者,为《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28]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有学者专门致力于《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11),对二者之间不可否认的前后相承关系,从各个角度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令人信服的阐述,叙事结构是其中说不尽的话题之一。对此学界高论甚多,本文仅略陈一孔之见。 注释: ①鲁迅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307页。 ②如大冢秀高作、柯凌旭译《从玉皇庙到永福寺〈金瓶梅〉的构思(续)》:第一回,玉皇庙十友结拜(仅存改订本);第二回,花子虚在永福寺被拘捕,潘金莲生日西门庆在玉皇庙打醮;第二十八回,西门庆永福寺送贺千户升迁;第三十五回,西门庆永福寺会荆都监等,玉皇庙打中元之醮;第三十六回,蔡状元寄居永福寺;第三十九顺,(庆)祝官哥诞生玉皇庙打醮,命(寄)名吴应元;四三十九回,西门庆永福寺送宋乔年,从胡僧处得到壮阳药;第五十七回,永福寺长老为集改建资金访西门庆,得银五百两;第五十九回,吴道官庙里举办官哥葬礼(备送三牲来祭奠、差了十二众青衣小道童儿来,绕棺转咒,生神玉章,动清乐送殡);第六十二回,西门庆为李瓶儿在玉皇庙求符无效;第六十三回,吴道官在西门庆家做李瓶儿的首七;第六十五回,吴道官在西门庆家做李瓶儿的二七、永福寺道坚长老在西门庆家做李瓶儿的三七、吴道官十月十一日白天挂李瓶儿的遗像;第六十七回,玉皇庙、永福寺为李瓶儿的六七送疏;第七十八回,吴道官在西门庆家做李瓶儿的百日、吴道这正月初三访西门庆家,送初九的年例打醮之帖;第八十回,二月三日,吴道官在西门庆家做西门庆的二七;第八十八回,春梅葬潘金莲的尸体于永福寺、陈经济寄存父亲的灵柩于永福寺,做了断七,并吊慰了潘金莲;第八十九回,吴月娘祭扫西门庆之墓后,在永福寺见到春梅;第九十八回,送赴济南的周守备、陈经济去永福寺;第九十九回,陈经济被葬于永福寺,韩爱姐上坟;第一百回,永福寺普静荐拔,吴月娘托孝哥于普静(《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除第一回外,其它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补注) ③徐朔方先生在其《金瓶梅成书新证》中列举了多条论据来证明此书非文人个人创作,见《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 ④如徐朔方先生所说:“小说不是历史。即使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也未必可以按照历史事实加以编年。《金瓶梅》不是历史小说,北宋末年的历史事实作为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只要大体可信就行了。小说的好坏并不取决于此。”(《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评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05页。 ⑤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金涛声《陆机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卷十《物色》第四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钟嵘《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戌,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杨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曹旭《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⑥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附录二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30页。鲁迅则说《金瓶梅》“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52-153页)。 ⑦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附录二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杂录小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2133页;又同书第2134页《西门庆房屋》所言西门庆家中居所更为详尽。 ⑧如《金瓶梅》之前的中篇艳情小说《娇红记》,即得名于女主角娇娘和飞红的名字。 ⑨文禹门(龙)云:“《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第七十九回文龙评,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705页) ⑩此言见本文脚注。鲁迅又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04页)“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06页)但其论的所指时代是很明确的:“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且介亭杂文》之《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二版,第14页) (11)如: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沈大佑《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庆善,于景样主编《红楼梦与金瓶梅之关系》,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鲁歌《红楼梦金瓶梅新探》,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