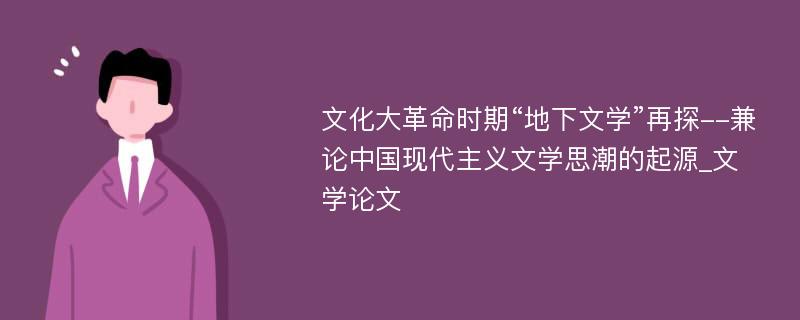
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再探——兼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现代主义论文,思潮论文,缘起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我写过几篇文章。写于1987年的《“文革”时期文学新论》[1],是想说明,文革时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公开的文学和“地下”的文学,而“地下文学”在文学史上具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意义。写于1988年的《“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初探》[2],我将这一时期的地下文学归纳为两大类别:个人私下创作和大量“口碑文学”,并重在论证“地下文学”与新时期解放文学的血脉关系。写于1990年的《样板戏启示录》[3],是想把“样板戏”作为文革时期公开文学的一个活标本,剖析其显在的文学状态、潜在的文学观念及其亟需发掘的文学史意义。而写于199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散点透视”》[4],则把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考察,从宏观的史论角度,说明其在当代文学史辩证演变中的“反题”地位,强调它并非如过去的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描述的是一个“断裂代”。
现在这篇文章,之所以在“初探”后又作“再探”,是想把思考的“焦距”定在一个热点问题上:过去被理论界普遍认为产生于新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到底产生于哪一时期?这一文学思潮曾被普遍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借鉴、“拿来”的结果,它到底缘何兴起?这一论题,虽然我在《“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初探》一文中已亮出观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就其‘本体起源’来说,在地下文学中;就其‘异起起源’来说,在“文革”的历史现实中”,但那时并未就此作展开论证。加之当时资料奇缺,也缺乏充分的论据。
在展开论证之前,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对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作出界定。
所谓“地下文学”,我指的是那种为当时的极左政治所不容、与当时的主流话语相渭泾、与当时的公开文学相抗衡的文学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们,压根就没想到过创作是为了公开发表,他们甚至害怕被“公开”。冯骥才在《命运的驱使》一文中曾说到:他在“文革”中曾听到一些令人灵魂颤抖不已的故事,于是禁不住把这些写成稿子。而这些稿子如被发现,是可能家破人亡的。于是他到处藏稿子,或塞进砖缝、楼板中,或一层层糊起来,外面糊上宣传画,甚至把它们塞在自行车横梁管里。但他为这些稿子成天心惊肉跳、恐慌不安,最后只好用火烧了。于是心情平静了,但也留下茫然和沮丧。冯骥才的话,为“地下文学”作了一个精彩而准确的诠释。1993年,杨健出版纪实性作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5],书中披露了大量的“地下文学”史料,使我获益匪浅。但他把“红卫兵文学”等也纳入“地下文学”,对此我却不能苟同。尽管当时红卫兵的那些文学作品没有国家承认的刊号和书号,然而它们却并非产生于“地下”。这里有一个核实文学作品的观念问题。
被当时普遍认为产生于新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其第一个呼啸而至的潮头,便是出现于1979年的一批“朦胧诗”。朦胧诗虽面世于是年,但其中的许多却创作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北岛的《回答》、《结局和开始》,顾城的《生命交响曲》、《星月的由来》,舒婷的《致大海》、《船》等等。当时诗歌界已经浮出了芒克、多多等“白洋淀诗派”的影子,但几乎没有人知道郭路生(食指)这个名字。我在1989年第3期的《海南纪实》月刊上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此刊载有陈小雅的《北京知青历程回顾》一文,文中有关郭路生只有寥寥几句,却使我知道了朦胧诗的真正源头和缘起。此文还附有食指的一首诗《愤怒》:“我的愤怒不再是泪雨滂沱/也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怒火/更不指望别人来帮我复仇/尽管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我的愤怒不再是忿忿不平/也不是无休无止的评理述说/更不会为此大声地疾呼呐喊/尽管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虽然我的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尽管我还说不上是一个强者/但是在我未完全成熟的心中/愤怒已化为一片可怕的沉默”。今天,郭路生已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他描写1968年12月20日乘火车离开北京下放农村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写于下放地山西农村、曾受到江青点名批判的《相信未来》也开始收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因此,朦胧诗肇始于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学中已成不争的事实。
与上述朦胧诗同时出现于文革地下文学中的,还有为数众多、流行甚广的“知青歌曲”。其中有的抒发知青作为社会边缘人、漂泊者的悲凉情怀:“秋风吹来阵阵凉,世事记心上。走在大街无人理,我内心多孤寂”(《四季歌》);有的以悲愤心情、感伤心态,悲诉自己被异化、被扭曲的“变形记”:“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没,有谁同情我”(《精神病患者》)……这些歌曲与朦胧诗相比,带有明显的“大众化”特点和“口碑文学”性质,因而其先锋性不及后者,并且在时过境迁后遗失得十分厉害。但其先锋气息和现代派情怀,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
小说创作中的有关现代主义的热烈争鸣是由王蒙的《夜的眼》、《春之声》等所谓“新六篇”而掀起的。“新六篇”当然并不是创作于文革时期。对王蒙的这些创作,孟繁华先生说:他的“新六篇”“虽然大量地运用了意识流,并在评论界还没有充分认识现代主义文学的情况下,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但他‘先锋性’的形式所表达的仍是他青年时代的‘精神’,他仍没有超出‘形式服务内容’或‘体用论’的古旧思想,这一策略的考虑,本身就与‘现代’无关[6]。”对此我深表赞同。在新时期最早代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并得以公开发表的小说,我以为是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赵振开的《波动》。《公开的情书》由四个男女青年从1970年2月至8月的半年间所互通的43封信组成。有人因其没有故事情节(其实是没有显在的、完整的情节)而否定它是一部小说。其实这种“反传统”的“无情节”小说恰恰是其“先锋”性的特征之一。而且作品对“带着镣铐的爱情”的抒发和对“只有一次生命”的婉叹,相对传统的意识观念而言,也流露出一种“非理性”的意味。赵振开(北岛)的《波动》被杨健认为是“‘地下文学’中已知的反映下乡知青情感生活的最成熟的一部小说”[7]。这部小说以几个主要人物的内心独白方式组接,“是在黑暗和血泊中升起的诗的光茫,是雪地上的热泪,是忧伤的心灵的颤动,是苦难的大地上沉思般回荡的无言歌。”[8]这部小说相当淋漓地流露出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气质。《公开的情书》1979年9月作者改定后发表于《十月》,但写于1972年3月;《波动》正式发表于1981年第1期的《长江》,但初稿完成于1974年11月。两者都属于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地下小说”后未能公开出版,但却作为文学史料被发掘出来的有毕汝协的《九级浪》和佚名的《逃亡》。这两部作品被杨健认为“奠定了文革中‘地下文学’的基石。”[9]但同时又被他认定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九级浪》也许确实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色调,但女主人公司马丽的“自毁”,是不是作者对“生存无意义”、“人生很荒谬”的悲观流露?杨健对此也有察觉。况且作者在小说中还片断地提到过“存在主义”,这可视为作者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动。至于《逃亡》,作品记述几名在东北插队的知青扒火车返城,他们在一拉煤的空铁皮车厢卷缩成团,在凛冽寒风中进入回忆,这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好片断,这些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作品结尾,这几名知青被冻僵的尸体相拥在一起,灵魂却在睡眠中消失于寒夜。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从艺术手法上看,它都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
谈到文革中的地下文学,绝不要忘记了当年曾大量涌现、且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口碑文学”。这是一个内容十分庞杂、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的文学领域,其中有许多甚至还不完全具备一篇文学作品的规模、规格。但作为文革时期出现的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学现象,我们却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严肃认真的对待。因为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的时代心理、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生活欲求。在这里,传统的文学观念并没有那种决定性的意义。从表面看来,口碑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似乎无缘,但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即艺术格调、审美趣味上,两者却有着一种无法开解的血缘关系。
口碑文学中有一些政治笑话、民间故事在新时期与新的文学意识融合,直接溶解在新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笔者在文革中当下放知青时曾亲耳听到一位当事人讲过一个故事。故事大意为:一位河南少妇请一位解放军战士抱一会儿新生的婴儿,说自己去买一点东西即回。不曾想这位少妇一去不返。这位战士惶恐不已,从婴儿的随身包裹中找到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孩子的爸爸没良心,孩子的妈妈是知青,孩子是革命的好后代,献给亲人解放军。”这则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笑话后在全国广为流传,并被不断地丰富一些细节。而它后来竟出现在梁晓声的长篇小说《雪城》中。而根据小说《雪城》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还在全国一度热播。
又如,史铁生的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中,述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农民进城,遇到一队红卫兵,红卫兵手握皮带,扣住其衣领问曰:你是保县委的还是反县委的?此农民本无明确的倾向,但“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于是答道:保县委的。然而遭到这队红卫兵毒打。痛疼未消,没走几步又遇一队红卫兵,以同样的方式问同样的问题。农民因“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故答曰:反县委的。却又遭毒打——这队红卫兵恰是保县委的。农民实在不知对此问题该如何作答,急中生智,卸下自己腰间皮带,扣住一迎面而来行人,以红卫兵口吻问道:保县委的还是反县委的?他以为这人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谁知此人应答如流。他的回答是:我们是一个革命战壕的战友。这则故事提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西方现代哲学问题: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可站。其实,这也是文革中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
有些口碑文学作品曾在新时期得以面世,如由橙实等编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革笑料集》(1988年8月第1版),四川《龙门阵》选录的一些小故事等。但大量的口碑文学已经遗失或正在遗失。笔者在文革中还听到过这样一则故事:基辛格访华时,提出要到北京胡同走走。我外交部门遂派一翻译随从。基辛格来到一胡同,只见一群人围着一圆肚形的机器,圆肚机器下是一火灶。只见有人把一点大米放入圆肚,将圆肚机器在火上摇了摇,“嗵”地一声,半口袋的大粒大米便出来了。基先生颇为诧异,问道:"What is this?"翻译灵机一动,答曰:此名为“粮食扩张器”。基特使一听大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搞法,我说他们怎么还有饭吃呢?原来他们发明了“粮食扩张器”!象这则笑话所流露出来的荒诞感、呈现出的黑色幽默格调,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美学意义。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前面我们从文学史实上证明了文革时期地下文学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这种血缘关系的“存在”,下面我们欲从理论上证明地下文学中所具有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本质”。
在论证前,同样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要做:为“中国现代主义”一词作出界定。
我所谓的“中国现代主义”,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对应同时也相区别的。我指的是那种在中国的历史、现实环境中产生出来,从中国的文化、文学的土壤中衍生出来,同时又以“非理性”、“反传统”为特征的文学思潮。这一思潮虽然在“非理性”、“反传统”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应合,但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之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所“非”的这个“理性”并非是西方现代主义所“非”的那个“理性”;中国现代主义所“反”的这个“传统”并非就是西方现代主义所“反”的那个“传统”。按说,这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学在对本民族的现实作非理性思考时,怎么可能对另一民族的现实作非理性思考呢?更奇怪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在反传统时,只可能反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怎么可能反到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上去呢?人家的文学传统本来就不是你的文学传统。因此,我认为,如果非要用西方现代主义的严格标准来衡量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现代主义,也没有什么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这也许正是王蒙的“新六篇”一度被称为现代派,其后又被指认为非现代派,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一度被判定为中国第一篇现代派的作品,其后又被斥之为“伪现代派”的内在原因)。
当中国现代主义思潮显现文坛之时,正是我国对外开放、向外借鉴之机。西方现代派的理论和文学作品纷纷涌入。这种不期而遇,自然使当时的评论界众口一词:中国现代主义是从西方借鉴的产物,是我们“拿来主义”的结果。我们当时忽视了中国现代主义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派涌入之间的“时间差”而造成的认知上的错位。非理性、反传统本来就不被阅读习惯、审美定势所接纳,何况它又与使中国人心情十分矛盾、复杂的“西方”“现代主义”搅混在一起,于是我们看到,当时只要文坛上出现现代派的东西,势必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议。但争议的焦点历来是: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引进西方现代派?是只能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还是对其文艺思想观念也可引进?若要引进西方现代派,如何使之与中国的文学传统相融合?当大家纷纷攘攘地、情绪激动地争论着这些问题时,一个被视为定论其实却并非定论的大前提却被束之高阁:中国现代主义是不是从西方引进“拿来”的?中国现代主义是不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
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学在借鉴另一民族的文学时,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想拿来就可以拿来的。任何借鉴都需要一种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心理机制。我们做一个心理试验:让一个成人和一个三岁小孩一起看一部激情片。当银幕上出现男女深接吻镜头时,你检测小孩的瞳孔,其瞳孔并无变化;而检测成人的瞳孔时,他的瞳孔会迅速放大、放大四倍。为什么呢?因为成人有着与银幕上的人物相同的心理机制,而小孩则没有。小孩当然也会学成人样去接吻,但那还是有其形而无其神。(尽管弗洛依德认为小孩也有性意识,也确实有,但两者还是有质的不同。)这只是模仿。这也是新时期文坛上,在出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时,出现许多有现代派之“形”而无现代派之“神”的模仿之作的内在原因。
那么,为什么恰恰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却出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呢?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原来,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自我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着同一条道路。正是文化大革命这种畸形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与当年形成西方现代主义心理机制相似的社会心理机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荒诞现实的真实写照。然而,年青一代一直受到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理性教育,当文革时期中国大地阴云笼罩时,诗人怎么可能不对“天是蓝的”作出非理性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深受理性教育与荒诞现实发生严重对峙和冲突的煎熬,年纪轻轻的童话诗人顾城竟写出如此悲凉的诗句:“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长时间处在这种变形的社会中,人就会觉得自己被异化了。于是郭路生在1974年写出了《疯狗》:“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显然,正是文化大革命铸就了整整一代人的荒诞意识。这就正像“二战”铸就了西方一代人的荒诞意识一样。
这就使我们看到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被认为在新时期文坛上最早显露出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是宗璞的《我是谁?》。作品描写从海外归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学者韦弥在文革中被诬陷为“特务”、“反革命杀人犯”。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罪名,以及数不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韦弥在弥留之际精神恍惚,对自己作为一个人也产生了怀疑,似乎自己真的变成了“牛鬼蛇神”,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一条“虫”。这篇小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而这篇小说恰恰是写文化大革命的。她类似的小说还有《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即使是王蒙的“新六篇”,其中的《夜的眼》、《春之声》等,未尝没有文革在现实中的投影;而《蝴蝶》中,主人公张思远觉得“人的位置比人更重要”,觉得自己的“魂”丢了而去“找魂”,这种“庄生晓梦迷蝴蝶”式的惶惑感不正与他文革中的经历息息相关吗?因此,我认为,中国现代主义“就其‘异体起源’来说,在‘文革’的历史现实中。”
读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我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生出几丝困惑:本来读的是现代主义的文本,然而读着读着它们似乎又不那么现代主义。北岛的《回答》一诗,开头就对“世界”作出了大胆的、根本的怀疑——“我不相信!”但诗的最后还是“相信”了“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郭路生表达的并不是彻底绝望,他最终还是“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顾城并未对人生绝望,他还是坚守那被破损了的理性——“我用它来寻找光明”。当西方现代主义沉浸在悲观绝望之中时,中国现代主义却坚守了对光明理想的亟盼;当西方现代主义张扬着人生的虚无时,中国的现代主义却大声疾呼人性的回归。我们之所以对此困惑,是因为我们以为既然都是现代主义,那么它们就应该是一样的。然而因为一个是“西方”现代主义,一个是“中国”现代主义,所以两者其实并不一样。对中国现代主义的思潮特征,孟繁华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同人道主义的时代潮流叠合起来,从而成为人道主义的盟友。”[10]他将此称为“现代主义的东方化”。我更愿意称之为“东方化的现代主义”。
我始终坚持把中国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区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西方现代主义是“二战”后出现于西方的形形色色的各个流派的一个总称,它有数十年深厚的历史背景,有其长期的酝酿、实践过程,尤其还有宏阔的哲学体系作底蕴。而中国现代主义有的只是十年浩劫的一幕历史悲剧,它虽然也是一个总称,却并没有下属诸多流派(理论界所提出的那些下属流派实在过于牵强),也没有一种哲学上的“格”的意义,也远不如西方那样成形、成熟、成流、成派。中国的意识流并未“流”得那么远,那么彻底,中国的存在主义也并未那么明显、触目地“存在”。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引起激烈争议,并不仅仅是其反映出的思想观念,还有它们那种反叛传统的艺术形式。像内心独白、感觉变形、象征手法、内视角、无序的情节、奇特的意象、反嘲……经常拿来被认定是中国现代主义源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诸多佐证。西方现代主义确实十分重形式,但西方现代文论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形式即内容。正如爱尔兰现代诗人威廉·叶芝的诗所说:“我们怎么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事实上,地下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作者们当初在运用各种新的手法、形式时,与其说是在进行一种新的探索、试验,还不如说这种对旧形式的蹂躏,本身就是对文革现实的一种挑战姿态,一种叛逆情绪的流露。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主义的这些手法、形式,是文革现实土壤使之滋生的。“红花/在荧幕上绽开,兴奋地迎接春风/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片血腥。”(顾城:《眨眼》)荧幕上红花绽开,现实中一片血腥,不正是文革的这一社会真实酿就了这首诗的感觉变形、朦胧诗风吗?所以扬炼说:“我的诗是生活在我心中的变形。”[11]象《波动》中出现的内心独自:文化大革命时不准人“乱说乱动”,“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黄永玉:《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人与人之间无法正常交流,否则祸从口出,中国人怎么可能不进入到“内心独白”状态,这时“内心独白”势必就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寄托于文学创作时当然就形成了一种所谓“先锋”的艺术手法。再如黑色幽默:文革的现实是如此荒谬,屈从、沉溺于荒谬,人将无法存活,超脱荒谬的唯一途径就是发狂一笑——于是黑色幽默出现了。王蒙就说过:荒诞的笑是对荒诞现实的一种抗议。准确地说,这时的黑色幽默,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人生的坚守。正如作家徐星所说:“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上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里注定的。”[12]
文革中的地下文学是否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有证据表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如地下小说《九级浪》中就片断地提出过存在主义。但这一影响在一个闭关锁国的年代和社会,无论是就其影响的范围还是影响的程度都十分有限,远远不足以影响到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新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否确实借鉴、引进过西方现代主义?答案是肯定的。王蒙的“新六篇”本来就是他“吃蜗牛”的结果;而刘索拉、徐星、刘西鸿等的先锋创作尤其还有马原的那些叙事革命的创作,与文革关系不大而与西方现代主义有更多的契合。(尽管王蒙的“体用”式借鉴与刘索拉等的“思潮”上的契合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外,残雪的现代主义创作显得更为复杂,她的那个几乎充满荒诞与绝望的“感觉”世界,既与文革有着斩截不断的牵连,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有着深度的默契。但不管如何,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来说,都只是“外因”而绝非“内因”,都只是“流”而绝非“源”,都只是“末”而绝非“本”。正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悲惨世界”戏剧性地成为了中国现代主义滋生的土壤;正是在文革的“地下文学”中,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以悲壮的姿态绽出了新芽,正是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在那个异化了的历史年代,以异化了的面目完成了一次文学自由的回归。
文化大革命既不是与中国历史绝然相悖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时期,也不是中华民族安之若素、司空见惯的恒常历史状态。理解这一点,对研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衰落、成就与失误、形态与观念、演绎与流变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公开的情书论文; 波动论文; 九级浪论文; 朦胧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