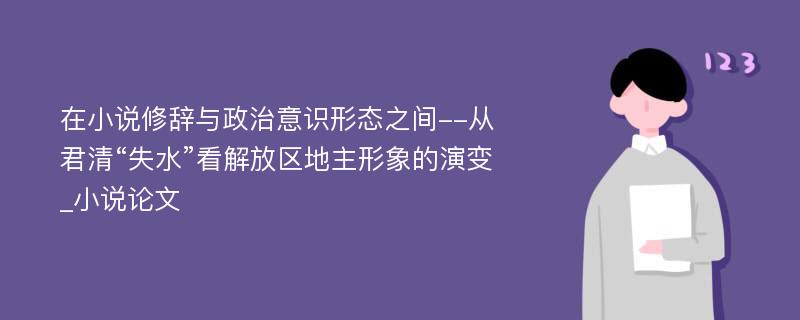
在小说修辞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从峻青《水落石出》看解放区小说“地主”形象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区论文,水落石出论文,修辞论文,小说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区小说塑造了不少人物形象,其中对“地主”形象的书写更是开创了一种写作路数,内含着丰富、颇具玩味的历史内容。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时期,解放区作家对“地主”形象的刻画经历了一种整体性的情感“调整”。
峻青的小说《水落石出》中的地主陈云樵横跨了这两个时期,处于这两个时期的交接处。分析这一作品和人物,有助于我们认识“地主”形象所经历的这种嬗变。
从表层结构来看,《水落石出》写的是一件谋杀案的侦破过程。情节比较曲折,采用了倒叙手法。起首是山东昌邑县积善庄的农救会长陈福一家遭人暗杀,先前上级派遣来的林华同志展开调查,但一无所获。后来,区农救会长老周介入此案调查,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终于揪出恶霸地主陈云樵及其帮凶现任村长陈五。案件终于“水落石出”,原来事实真相是:解放区复员军人郑刚回乡,发动群众欲斗倒所谓的“开明士绅”陈云樵,陈云樵惊恐万分,在“蒋匪军”占领昌邑城时密告了郑刚。后来在“蒋匪军”逃跑之际,伙同时任村长的陈旺以及陈福、陈五活埋了郑刚。但陈福因罪恶感而精神失常,于是陈云樵又同王开杀人灭口,并欲毒死被解放军抓回来的陈旺。这一切阴谋最终被识破,解放区“云散天晴”。
陈云樵这个“地主”形象便是在上述情节中塑造的。在中国,“地主”这个词古已有之,而对“地主”从阶级角度进行直接定义的,却始于1933年10月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他认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①。峻青也正是如此进行地主形象的塑造的,只不过陈云樵这个地主形象,由于处在一个变动的历史状态中,要显得更复杂一些。
一 幕后隐身——台前现形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47年4月的《大众报》,是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书写的“地主”形象,主要写的也是1947年2月间的事情,但故事的时间涉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随后的“反奸清算”运动。
小说分为七个部分,前六个部分的叙述中很少看到陈云樵的身影。他只在枪毙投敌分子陈旺时慷慨陈词,以及在第六部分结尾处在主席台上露过一次面。可以说,他一直是一个“隐身人”。在整个案件的调查进展中,也都与相关人事没有直接牵连。但到了第七部分,在回溯案件中,陈云樵渐渐露出了水面,我们才看清楚陈的种种丑态的“表演”。之后陈本人也主动走到前台。最后他在主席台上被活捉就具有某种隐喻意义:隐身人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现出了原形。一切恰如小说标题所示——《水落石出》。可见,地主陈云樵经历了一个由幕后到台前,从隐身到现形的过程。
陈云樵性情确实也不喜欢抛头露面,日本人占领期间叫陈凤翔出来当村长,八路军建立民主政府又让贫农陈旺做村长,而这些人都受其幕后操控。这一点小说中有清楚的交代:“实际上,他却掌握着积善庄的一切大权。一切坏事,都是他的主意。可是一切诅咒和憎恨,都落在受他支配的人的身上”②。陈云樵仍旧做着“善人”。这一切原本和风细雨。但复员军人郑刚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搅乱了陈云樵的处事方式。陈云樵显然无法从容了,他不能再袖手指挥。他亲自出马,设计将郑刚送进县公安局,但却被无罪释放。国民党军队攻进昌邑时,他写呈文密告郑刚。在国民党军队兵败退走之际,又与同伙亲手活埋了郑刚。陈云樵逐渐走到了前台,并亲手干了这一桩桩罪恶,彰显了地主阶级之“恶”。
这种地主由“幕后隐身”向“台前现形”的姿态转变,无疑容纳着对地主地位的一种重新认定。在解放战争期间,对地主特别是以前被赋予“开明士绅”称号的一群人怎么看,这是当时政治和小说创作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峻青在《水落石出》中对此也做了某种解答和阐释。“幕后隐身”的表现方式显然并非说地主陈云樵没有罪恶,而是指其隐藏得很深,才蒙骗了干部和群众,也才混上了“开明士绅”的称号。但问题是,陈云樵怎么就能在革命政权里堂而皇之地骗取“开明士绅”的称号呢?如果骗取之说是成立的话,那么革命政权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何在?这是个在政治理想、情感逻辑乃至具体的操作技术上都必须直面的问题。
作者也显然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在小说的具体写作中,峻青或明或暗地反复强调遭受蒙骗的干部林华。“说起这个林华,他是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知识分子”,这是作者对登场人物的一句话式的简介。“工作不久”自然不够成熟,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则更令人起疑。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曾做过明确的判断:“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③。知识分子被确认为沾染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各种毛病。小说中的林华就是这样:他脱离群众,工作积极但躁动,思想意志不够坚强等等,这一切最终都被作者指向了“知识分子的架子还没有完全放下”。他为陈云樵的“障眼法”所迷惑。这种身份所显示出的稚嫩和缺点,说明连林华本人都需要改造。
但区农救会长老周却仿佛一个神人,经常未卜先知,他在小说中与其说是来破案,不如说是预知答案后只是前来寻找证据而已。他一登场就逼得陈云樵“台前现形”:“说起这个老周来,他是区上的农救会长,是从群众运动中提拔起来的农民干部。”作者念念不忘地强调其身份——正是这个“有魄力”的农民干部的介入才揭下了陈云樵伪善的面具,其“开明士绅”的称号也被合情合理合法地收回,其中透露出中国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转变、革命对象也随之转变的信息。
从小说中“地主”行为姿态不断明朗化,渐形成一种“石出”的效果,以及为此设计的重重铺垫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一种叙事逻辑、修辞策略的隐然生成,这也为他实现人物形象的合理嬗变搭建了叙述骨架。
二 相对的多面性——绝对的单面性
地主陈云樵在乡里有着“陈善人”的称谓,这个称谓自然被作者赋予否定讽刺的意味,这个人物也被刻画成“老狐狸”形象,那么这只“老狐狸”又是怎么打扮自己、混入“开明士绅”行列的呢?我们不得不看看他的一些“伪善”做法。但悖论的是,这些从正面批判意义出发的闲笔,反而让人或隐或显地看到了陈云樵内心情感的其他方面。
陈云樵做过什么“善举”?“荒年的时候发一点粗粮啦,冬天捐赠几件破棉衣啦,站在街上道貌岸然地讲几句‘公道话’啦,遇到邻居们危急的时候‘解囊相助’等等”,当然,这一切被作者阐释成“小恩小惠的笼络手段”。在“草根吃光了,树叶吃光了,人民束紧肚皮一刻一刻地挨着”,陈云樵又做了什么?“就在这时候,陈善人打开了他自己的粮库,把金光闪闪的玉米一大斗一大斗地分给了穷人”。对此,作者也给予了很好的解释,这使他“混上了个‘开明士绅’的称号”。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开明士绅”的称号不以这些为参考标准,又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名正言顺地获得,而不是“混上”?
这些事情确实可以看出地主陈云樵的其他方面:有一定威信;有着良好的人缘;于人危难处尚能伸出援手,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出于笼络人心。如果这些行为被理解成“伪善”的话,至少说明他还有道德、善恶观念,他还顾惜一些声名。但又有多少人连这种姿态都懒得摆,基本的是非观念都丧失了,堂而皇之地以“恶”示人。
同时,陈云樵也喜欢用一种封建伦常式的人情味对待“自己人”,如重用厚爱侄子陈旺,给潦倒的陈福置地、娶媳妇以致后者渐成其帮凶。
这些点点滴滴,都可以看出陈云樵的多种复杂的情感以及不断变换的身份角色。我们能真切感受到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人物。但渐渐地,这个人物却只剩下“恶”了。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复员军人郑刚回村发动群众,欲斗倒陈云樵。这时,陈自然惊慌不已。郑刚“也曾在青黄不接的饥饿日子里从善人家里领到了一升粗粮而感激得流泪过”,但参军后,他“受到了党的教育,开始认识了真理”④。这个战争中接受的“真理”,让他与地主势不两立。后来,作者峻青在创作谈中也曾明确表示过“老实说,当时(战争期间——笔者注)我们写东西,完全不是为了满足什么发表欲,更不是想当作家,那时我们甚至还不懂什么是作家呢?唯一的就是战争的需要”⑤。
正是这种“战争的需要”让陈云樵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恶魔”。小说写他活埋郑刚时有这样的片段:“‘嘿!小子你还敢嘴硬!我真倒要看看你长的是什么眼睛?’陈云樵一面说着,一面用手爪,噗哧一声,把郑刚的一只左眼挖了出来。”地主陈云樵已经歇斯底里,他的身上只充满着凶残、恶毒,温情脉脉的面纱已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他还窝藏了国民党特务王开搞破坏活动。为了防止走漏风声,伙同王开杀害陈福一家灭口。后来又想毒死被解放军抓回来的陈旺。陈云樵的罪恶在“加码”,完全丧失了人性,甚至连自己亲手栽培的同伙也不放过。他的坏事越做越绝,其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已经罄竹难书。这样,一个大恶霸形象腾然跃出。
其实,人物形象从多面到单面,正是这篇小说叙事策略的必然结果。当陈云樵没有完全暴露时,或者说,由于政治社会因素还不想让他暴露时,他被写成富于人情味的、立体的“开明士绅”的形象,他在小说中的发展似乎具有多种可能性。但到一切明朗起来,到了该尖锐斗争的时候,他性格发展的丰富性便消失了,作者凸显的只是单方面的内容了。水落之后,只剩下简单、僵硬的石头赫显于眼前。
三 开明士绅——恶霸地主
从“幕后隐身”到“台前现形”,从“相对的多面性”到“绝对的单面性”,陈云樵的形象已经水到渠成地由“开明士绅”滑变为“恶霸地主”。至此,峻青完成了一次“水落石出”式的思考和写作。陈云樵的一些善举被视为一种“伪善”,一种欺骗手段,其“开明士绅”的身份和面貌被作者成功地消解。而其“恶霸地主”的面目又从两个维度推进:一是使陈云樵从“幕后隐身”到“台前现形”,这便于作者发掘地主的新旧罪恶,以前没看清的,可以一并在“现形”中得到揭露。这是一个罪恶由暗到明的过程。另一是使陈云樵从“相对的多面性”到“绝对的单面性”,这种叙事策略又可以遮蔽陈云樵的一些情感“支流”,便于凸显其“主流”,从而形成一种在政治正确的认识观关照下的“独流”,它无疑可以加深对地主罪恶的控诉力度。这是一个罪恶由浅入深的过程。
细究一下分散的情节,我们会发现陈云樵的转变有着时间上的对应关系。他的“幕后隐身”、“相对的多面性”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及随后的“反奸清算”运动期间,而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特别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展开使他逐渐走向了“台前现形”、“绝对的单面性”。其中暗藏的恰是具体历史情境下对“地主”政治定位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地主阶级的属性和命运,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对“地主”的策略是不同的:在抗战期间他们属于联合的对象,由土地革命时期的剥夺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对他们在“斗争”中主要讲“团结”。然而随着1946年6月,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和解放战争的开始,尤其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面推行,对地主批判的调子迅速上升,其所犯罪恶“揭露”的程度也在加深,此时“地主”就是一个要被完全打倒的阶级。中共对“地主”政治定位的变化充分体现在这两个时期其土地政策的差异上。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曾承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七条正式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至此,中国共产党正式确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
从解放区的小说作品来看,这一时期的“地主”形象主要是以懒惰、无赖、吝啬、贪婪、奸猾、阳奉阴违的面目示人,如《租佃之间》(李束为,1943)中的金卯、《红契》(李束为,1944)中的胡丙仁、《石磙》(韶华,1944)中的马三爷、《纠纷》(菡子,1945)中的楼志清、《土地的儿子》(柳青,1945)中的尚二财主等。他们贪图便宜、剥削劳动、偷奸耍滑,也搞些傻气十足的小破坏、耍点自以为是的小伎俩,这些缺点很容易和他们的个人性格结合起来,他们是可笑的、可厌的,但与十恶不赦的坏面貌还相差很远。像《纠纷》中的地主楼志清就是一愣头青,他经常耍点小威风,喜欢听别人的奉承话。《红契》中的地主胡丙仁则跟佃户围绕真假减租作了心理和情感的斗法,他威胁佃农“如果你报告农会,我就到你家大门口上吊”⑥。这种口吻本身就具有民间无赖的色彩,还没有后来那种置人于死地的狠毒的味道。《石磙》中的马三爷和佃农石磙也围绕隐瞒土地问题做了交锋,地主开口就声称“我既然是你的爷爷,我就站在爷爷的立场上说话”,⑦即使最后被处罚,结局也仅是“只是,三爷的威风比过去是小些了”。⑧可见,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中对“地主”总体上是扬着嘲弄、讽刺、批评的调子,在“团结”加“斗争”的策略下,还很“宽容”。一些小说有着明显的民间故事中的“地主”与“长工”斗智的痕迹,民间的乡野情调事实上是削弱了阶级对立而造成的紧张。即使在写于1943年的《李有才板话》中,被赵树理确立为批判对象的地主阎恒元,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背景下,他虽然确实在操纵选举、拉拢干部、挑拨分化农民,但他更像一个封建的族长,用着自己的手腕统治着一个村庄,还没有人命血债,而他最终也仅是被罢免职位、减租退钱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时期的“地主”在政治上基本还是安全的。
1939年1月31日,王稼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曾强调:“地主阶级的某些部分在抗战过程中虽动摇叛变”,就其一般地主而言,“还是要争取与推动他抗日”⑨。这集中代表了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开明绅士”(之后其文也有“开明士绅”的提法,两者是一个概念——笔者注)的称谓,指出:“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⑩
小说中也出现了涉及“开明士绅”的题材。如赵树理写于1944年的《地板》,其中主要写了一个叫王老三的地主,他不仅欣然应邀在村里给穷孩子们当老师,还主动现身说法教育其他地主:粮食不是靠地板(土地面积)而是靠劳力换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解放区的整个小说创作中,这一群体极少被描写,更别说从正面意义去处理了(11)。正如前文所示,这一时期的小说,对“地主”这一群体是持暖昧、保留的看法,整体虽是否定的调子,但显得还很“宽容”,夹有轻松揶揄的调子,还没有你死我活之感。
而在《水落石出》中,作者倒也较为少见地明确点出了地主陈云樵曾经的“开明士绅”的身份:积善堂的主人陈云樵“已经不是翰林而是‘开明士绅’了”。也正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由“开明士绅”到“恶霸地主”,《水落石出》是在进行着一种“地主”形象嬗变的极致叙述。其实,在指出陈云樵“开明士绅”的身份时,作者峻青便交代了陈的一些“罪恶”线头,只是还不很尖锐,情感分寸上恰如抗战期间的其他解放区小说对“地主”的处理。但这也就为之后的形象嬗变埋下了可以进行重新挖掘和开发的伏笔。
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内阶级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为适应新的形势,共产党在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将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而这篇《水落石出》写于1947年,正是在“五四指示”之后,在华北地区的“土改”即将全面开始之前。
留心一下,我们会发现尽管小说写的是一件谋杀案的侦破过程,《水落石出》中却多次提到了即将开始的“土改”:“最近,听说要土改了,他又要献田”;“他想: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啊!土地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对于群众的斗争情绪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这么一来,群众更不敢动了”;“对于陈福全家的被杀,林华心里暗想:这一定又是潜伏的特务分子所施行的恐怖手段,企图破坏土地改革”。
小说中如此急促果断地确立陈云樵的“恶霸地主”的身份地位,正是作者及其所属时代政权所隐伏的强大“土改情结”在作怪。漫长的农耕文明熏陶下的中国人对土地有着极其浓厚的感情,土地资源的争夺和再分配也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中,“耕者有其田”就是重要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革命中,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明确的土地政策,而解放战争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更加深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农民为了保护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配合和支持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便是顺势之结果。这一点,在解放区对新的土地政策的宣传中是有鲜明体现的:“使农民认识到大老蒋小老蒋(指地主——笔者注)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12)。这一时期的小说里也有清晰的表露,如《土地和枪》中,一心想入伍的殷红玉就这样“教育”不觉悟的父亲和妻子:“蒋介石是一个大地主,他跟汉奸地主是一伙,那东西要过来还了得?逼着退地退房不说,真得拉掉你脖子”(13)。
这种形势下,即使此前被授予“开明士绅”称号的地主也难逃一劫了。“五四指示”颁发后,主动交出土地和多余房舍的“开明士绅”刘少白仍在千人大会上受批斗并遭监禁40余天,而其弟也在1947年8月被批斗致死(14)。这期间,牛友兰、孙良臣等曾受过毛泽东亲切接见的“开明士绅”也相继遭批斗致死。
显然,此时“地主”已经被作为一个整体而受到革命政权的批判和斗争,而地主个体的“态度”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尽管此后局部地区对此情况也做了某些纠偏,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事态的发展趋向。
与现实形成“互文”的是,这一时期的解放区小说中的“斗地主”题材往往也都有明确的斗争结果,地主或被彻底斗倒,或被镇压。地主也基本是歹毒、淫恶、凶残的,没有丝毫人性,只剩下“恶”,成为妖魔的化身,如《瞎老妈》(洪林,1946)中的何家宝,《回地》(木风,1946)中的张清茂,《村东十亩地》(孙谦,1946)中的吕笃谦,《老一亩半家的悲歌》(梅信,1947)中的许百福,《血尸案》(孔厥、袁静,1947)中的钱康人、钱占新,《庄户牛》(陶钝,1947)中的二秀才,《金宝娘》(马烽,1947)中的刘贵才,《江山村十日》(马加,1947)中高福彬,《村仇》(马烽,1948)中的赵文魁、田得胜,《杜大嫂》(陈登科,1948)中的王九卿等等。何家宝、刘贵才、王九卿等等地主基本都是把农民往绝路上赶,甚至本身就直接负有命案血债的家伙。
与阎恒元阻挠减租减息运动一样,这一时期《暴风骤雨》中的地主韩老六也阻挠“土改”运动,但他显然要“恶”得多,身上背负二十七条人命,极其毒辣凶残,无疑是个恶霸地主的典型。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也是一个一手遮天、无恶不作的地主,甚至连儿子、女儿、侄女也成了他手上的棋子,利用他们的参军、婚恋编织层层为己所用的保护网。再以赵树理为例,这一时期他笔下的“地主”也越来越“恶”,《福贵》中的地主王老万仅因福贵有辱“一坟一祖”的脸面就欲将其“活埋”。
至此,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以“恶霸地主”的面貌来置换全体地主形象(包括以前所认可的“开明士绅”),可以造成农民和地主之间更尖锐的阶级对立,也容易“唤醒”农民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复仇意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小说中的“地主”就经历了由批评讽刺到彻底揭露打击的基调变化。“地主”形象也由偷奸耍滑、剥削吝啬,搞点小破坏转变成凶残狠毒、恶贯满盈、毫无人性。“地主”形象正是立于政策规定下在小说中被不断“塑造”着自己的乡村生活状态,从而也方便作者剥离农民和地主之间错综复杂的乡村伦常关系,进而实现“外来”的革命政权对乡村的直接领导和改造。
《水落石出》最后是一段颇有“点题”意味的议论:“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个几百年来压在人民头上的积善堂完了,这个虚伪、阴险、残忍、狠毒的陈善人完了,这个土匪特务的大本营完了。这个阻碍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完了。”
总之,解放区小说在各个阶段中几近相同的地主“造型”,是在具体时代氛围下中国革命的政策性产物,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到底什么样,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活的丰富性,远逝的历史可能已让我们无法得知,但随着时间档距的拉开,我们或许可以逼近某些被刻意“忽略”的真相。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②峻青:《水落石出》,见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四》,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0页。下文关于小说《水落石出》的引文均见此处,引文较多,不便细著页码。
③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51页。
⑤峻青:《既要坚持,也需提高》,出自《峻青谈创作》,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9页。
⑥李束为:《红契》,见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二》,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904页。
⑦⑧韶华:《石磙》,见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四》,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2796页。
⑨王稼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639页。
(11)这一点与政治上对其进行有条件认可的状况,显然是没有构成同向度的“呼应”关系。在延安时期,文学作为政治的“风向标”,似乎也可以透露出政治本身对这一群体身份定位的犹疑性和焦虑感。
(12)《区党委总结新区土地改革指示继续深入运动方向》,出自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9页。
(13)荒草:《土地和枪》,见康濯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三》,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7页。
(14)具体事件参见《晋绥日报》1946年8月13日、1947年9月2日、1947年9月9日。
标签:小说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峻青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