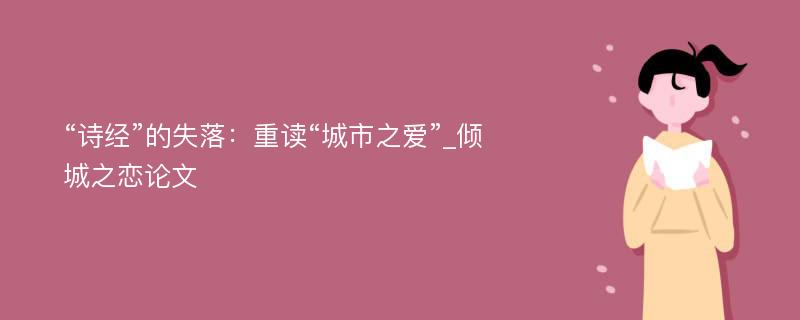
“失《诗经》”:再读《倾城之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之恋论文,再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张爱玲来说,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歌赋,似乎并没有如《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旧小说那样深入地渗透到她的文学理念及创作中;但显然,她对这类诗歌作品也绝非陌生。胡兰成回忆他同张爱玲一起读书(包括古诗),就感觉“那书里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只和她打招呼”①。的确,张爱玲似乎对诗歌中“字句”——字眼、只言片语——的阅读往往是通达透彻的心领神会,或许从一两句诗,她便可以敷衍出一段传奇。例如,
关于小说《倾城之恋》的取材,张爱玲就这样谈到过她从《诗经》中获得的感受:
拙作《倾城之恋》的背景即是取材于《柏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形容:“心里很‘雾数’。”②
这一解说很像是从女主人公白流苏的角度切入的,与张爱玲解释话剧《倾城之恋》之所以受市民观众欢迎是一致的③。然而除了《柏舟》,《诗经》(《邶风》)中的另一首诗《击鼓》在《倾城之恋》中似乎更为重要,男主人公范柳原先后两次提到。第一次是在电话里:
……柳原不语,良久方道:“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④
第二次是两人去登结婚启事,路上看着战火后的香港那“平淡中的恐怖”,范柳原旧话重提,又将这诗念了一半。——可见这首诗对范柳原而言,代表着一种极深的人生情感与价值观念。那么,对于作者张爱玲呢?
一、《击鼓》的两个“版本”
《倾城之恋》等作品发表后,引来了傅雷(迅雨)那篇著名的批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随后不久,张爱玲在颇有些“答辩状”意味的《自己的文章》中,不再假借小说人物之口,而是自己开口再次谈到《击鼓》中的这几句诗:“‘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⑤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对《击鼓》诗句的引用和理解,范柳原和张爱玲的两个“版本”其实是不尽相同的;或者换言之,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对《击鼓》进行了两处“改写”。第一处是字眼的改写,即将“成说”(盟誓)改写为“相悦”。——当然,最简单的理解是由于范柳原“中文根本不行”,但既然引用的目的是要“解释”,那么,相信这一处改写是有其微言大义的⑥;第二处改写在我看来可能更重要,那就是对句读的改写。原诗固然本来没有标点符号,但根据对整首诗的内容及节奏的理解,其通行的现代断句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也正是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中采用的句读方式。按理说,范柳原的“中文根本不行”,似乎更应该采用这种最朴素的句读,但他却偏要很费劲地将其改写为“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要注意,这番话是范柳原在电话里说出来的,以口语方式要表达出那个破折号“——”的转折意义,实在是多少有些奇怪的,这只能说是张爱玲的苦心“经营”。从前者即通行的断句来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以解释为“说”(盟誓)的“内容”,四句诗的大意就是:无论死生离别,我都要同你盟誓:与你牵手,直到永远。但范柳原的断句不仅使惯常的诗歌节奏被打破,更重要的是将语义改变,“与子相悦”遂成为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并列的同类项,共同构成对“死生契阔”的具有张力感的转折,四句诗的大意自然也就变了:死生离别,(可是)我和你相爱,我和你牵手,我和你终老。也就是范柳原所解释的:“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至此,“盟誓”不见了,剩下的是范柳原的哀叹。——所以下文白流苏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她“沉思了半晌,不由得恼了起来道:‘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还得绕着大弯子!……”看来她是听出了第一处改写的意义:范柳原是不要“成说”的。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就指出来:“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末,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⑦——大约这算是漏洞小节之一吧。
两个不同的“版本”,意味着不同的理解。张爱玲与范柳原一样,认可这“是一首悲哀的诗”,但她赞叹此诗的落脚点却在于“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而按照范柳原的说法,这首诗是“最悲哀的一首诗”,因为同生离死别那些“大事”相比,人是渺小无力而不自知的,“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同样读出了“悲哀”,却归结出全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范柳原所哀叹的,是何等的不肯定!
二、“唐·璜”、“颓败者”、“他们华侨”
《倾城之恋》这篇小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篇“复调小说”,它至少有两个各自独立的“声部”:一个是“女结婚员”⑧声部,即白流苏的婚恋“传奇”,一个是海归“浪子”声部,即范柳原的文化及情感“寻根”悲喜剧。前者是张爱玲一再书写的故事,只不过白流苏这个“女结婚员”似乎格外好运,藉由香港城的“倾覆”居然得到成全,成为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虽然依然有着挥之不去的怅惘。后者却可能相对隐晦一些,以至于人们对这个男性人物范柳原有着迥乎不同的评价。
不少读者认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刻画通常比男性更为细腻而且深刻,尤其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几乎就是一个炉火纯青的人物形象了。1940年代的傅雷就正是在对七巧赞叹有加的前提下,指出《倾城之恋》的人物塑造太过缺乏“深刻”,而且认为“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他将范柳原理解为“唐·裘安”(现通译唐·璜),但这个唐·裘安又塑造得草率而苍白,是个完全没有展开的“第二主题”。他质问道:“范柳原真是这么一个枯涸的(fade)人么?关于他,作者为何从头至尾只写侧面?”⑨
与傅雷的评论几乎同时,张爱玲的热烈拥趸者胡兰成则对此提出了鲜明的不同意见。胡兰成认为范柳原是个成功的形象,“柳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说是颓败的人物,不过是另一种的颓败。……这样的人往往是机智的,伶俐的,可是没有热情。他的机智和伶俐使他成为透明,放射着某种光辉,却更见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经熄灭了。”“他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流苏,也不是为了要使流苏烦恼,却正是他自己的烦恼的透露,他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因为怯弱,所以他也是凄凉的。”⑩
无论是“枯涸的”唐·璜,还是“凄凉的”“颓败者”,似乎都是将范柳原这个人物放在与白流苏的“情感关系”中来看待的。除了情感关系,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出一个“文化关系”来。
范柳原是一个华侨。张爱玲笔下常有华侨出现。在她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海归人士王士洪取笑自己的太太娇蕊“他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是欠大方”,“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这种似乎已成常谈的论调引来了娇蕊的抗议:“又是‘他们华侨’!不许你叫我‘他们’!”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也是这样一位非我族类的“他们华侨”,只不过由于他的经济地位,他不会被人取笑,而变成了一个女人们虎视眈眈的“他们华侨”。确实,要塑造现代中国“文化夹缝”中的人,“异乡客”是很贴切很便利的选择,比如郁达夫的《沉沦》,老舍的《二马》;张爱玲深得此道,而且她写得更为左右逢源,她选择上海、香港这样“华洋杂处”的城市,也选择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各色华洋人士。“他们华侨”即其一。
作为在异国出生、长大的华侨,对于故国,范柳原恐怕毫无所谓黍离之悲,他反是对“中国”抱持着一种“罗曼蒂克的爱”。这种故国情怀,多呈现为一种对“古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与向往,承载这种想象与向往的,很多时候可能是文学化的文化典籍,比如《诗经》,构成了“他们华侨”的“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他们华侨”的精神家园。因为是想象,是罗曼蒂克的,必然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至于对《诗经》的诗句“解释得对不对”,那倒是在其次。在《倾城之恋》的语境里,我们不妨粗略地称之为“《诗经》文化想象”。在运命乖蹇之时,这“《诗经》文化想象”可以带来巨大的精神支援,所以范柳原即便在父亲死后因得不到“身份”确认而“孤身流落英伦”,他依然可以对故乡“做了好些梦”。
具有这样的文化身份的范柳原,在与白流苏的情感关系中,可能就不仅仅是追逐美色的“唐·璜”,也不仅仅是“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的“颓败者”,他还是一个苦苦追寻“中国”的“他们华侨”。
与张爱玲的诸多作品一样,《倾城之恋》也写出了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隔膜、情感“错位”,“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11)。作为“女结婚员”的流苏,“她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因为经过了长久的训练,以为自己是可以“懂得”男人,进而“抓住”男人的。小说中,流苏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策略性的退让,都显示出流苏的知己知彼,尤其是她对“好女人”、“坏女人”的解说,更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对男人的了解。然而范柳原似乎始终烦恼于流苏并不“懂得”他,因而也就愈发要求流苏:“我要你懂得我”,即便连他自己也不能“懂得”自己,他还是固执地要求着。那么既然意识到“不懂得”,柳原为什么要爱白流苏呢?答案似乎有些大而无当:因为流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小说中凡写到范柳原对流苏的赞美,无非是:“难得碰见像你这样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你是个道地的中国人。”至于“真正的”、“道地的”中国女人具体是怎样的,却又语焉不详,比较抽象,范柳原只是透露了些许“气氛”:“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似乎在范柳原心目中,流苏不是一个血肉之躯的女人,而俨然成为了“真正中国”的化身与象征,他同这个象征产生了“精神恋爱”。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推断,范柳原同白流苏的虚与委蛇、真真假假,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置换为他同所谓“真正中国”的虚与委蛇、真真假假。
可是,既然有“真正的”“道地的”中国(人),那么,也就意味着还有“虚假的”“伪饰的”中国(人)。范柳原这个“他们华侨”,同“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妨就从他自己说起。他对自己的剖析是:“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可是你知道,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那么为什么“最近几年才渐渐中国化起来”,而且“中国化”得如此“顽固”?小说中范柳原此时三十三岁,而他从英国回国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那么所谓“最近几年”,也就是他回到故国的几年,正是在这几年里,他见识到的“现实的中国”,却几乎要使他崩溃:“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我们把这个过程梳理一下,大致得出的推论是:范柳原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其实是他“梦”中的中国(虚假的中国),他见识到的“现实的中国”(真正的中国)则是他厌恶的“虚假的中国”;而“梦”破灭的结果,则是他“渐渐的中国化起来”;这里的“中国化”大约应该是范柳原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如果这种“中国化”还不足够,他需要白流苏这样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来补足?同样,白流苏这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在范柳原的心目中,就不能是现实中的中国女人,她必须带有“罗曼蒂克的气氛”,她根本就“不像这世界上的人”。
无怪白流苏在同范柳原的来往中,总是“提心吊胆”、“如临大敌”、“战战兢兢”、“煞费踌躇”,因为“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以她“女结婚员”的资历,来充当范柳原“《诗经》文化想象”的偶像,确乎无所适从地难乎其难。更何况另一方面,范柳原对这个“真正的中国女人”,似乎自己也无从要求,流苏也就无从“改进”。比如,他内心里希望有个马来亚的流苏,摆脱了上海白公馆“中国家庭”的束缚,摆脱了香港依然存留的“中国社会”的束缚,甚至摆脱旗袍这一“中国符号”的束缚,“也许会自然一点”,可以在马来亚的“原始森林”里奔跑。但是,这样一个脱去旗袍的流苏,却再也不能承载“很像唱京戏”的“真正的中国女人”这一形象了,这真是一个悖论式的愿望。对“他们华侨”范柳原而言,与其说这是“浪子”“找寻真爱”的尴尬,毋宁说这是“情感/文化寻根”的尴尬。
三、“失《诗经》”与“三底门答尔”
可以说,导致了这种情感/文化寻根的尴尬的,是上述“《诗经》文化想象”的失落与坍塌,——我们或许可以试着将其命名为“失《诗经》”。一个华美蕴藉的“古中国”,一个略显伤感诗意的旧文明,在上海或者香港这样的堕落都市中,无可挽回地式微了。范柳原的“失《诗经》”经验,就构成了一曲哀怨的挽歌,令人无限怅惘。
战争爆发,香港倾覆,白流苏的家政训练派上了用场,范柳原也是“各样粗活都来得”,男人和女人各安其分,于是他们去结婚。在结婚的路上: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流苏嗔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柳原笑道:“我并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脸色,笑道:“不说了。不说了。”他们继续走路。
对于范柳原来说,那种“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的“悲哀”似乎未曾稍减,然而时过境迁,他再也不能以这种貌似深刻的“痛苦”、这种冠冕堂皇的情感来居高临下地压迫流苏了。不同于浅水湾饭店电话里他对流苏的“不耐烦”的粗暴打断,现在换做范柳原被流苏的娇嗔和脸色两度打断,只能陪着笑“不说了”——不说也罢,反正我们已经读出了小说中的某种嘲谑。
这大约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屡屡从张爱玲小说里会同时得出向度不同的两种感受:她是悲天悯人的,她是冷漠无情的。
如果顺着这个“失《诗经》”的思路来阅读张爱玲,我们会发现,这似乎成了她小说写作中的某种“模式”,她很愿意讲述一个作为精神支柱的“想象”如何失落的哀伤故事,同时不无快意,或者甚至不无恶意地指出,这个想象其实是被篡改,乃至被虚构的,从而,读者眼中的“悲剧”实则不过是张爱玲笔下的“三底门答尔”(12)。《金锁记》中有个范柳原式的人物,老留学生童世舫,因为“多年没见过故国的姑娘,觉得长安很有点楚楚可怜的韵致,倒有几分喜欢。”最终他得到的是“异常的委顿”,“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茉莉香片》中聂传庆在心中确立了一个精神上的“父亲”言子夜,这是一位古典文学教授,他穿长袍,使传庆感到“中国长袍的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但最终恰恰是这种“畸形的倾慕”彻底摧垮了传庆。《年青的时候》里的汝良爱上了沁西亚,因为他习惯画的剪影恰巧同沁西亚是一样的,“他从心里生出一种奇异的喜悦,仿佛这个人整个是他手里创造出来的。”他借由沁西亚跟自己厌恶的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然而,“他并不愿意懂得她,因为懂得她之后,他的梦做不成了。”《封锁》更是对这一“模式”进行了极为戏剧化的摹写,封锁在电车里的恋爱,只是因为“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可是,吕宗桢和吴翠远难道不是充分算计着,积极配合着,共同来做梦的吗?这类“三底门答尔”性作品,是悲剧?是喜剧?是仁厚的悲悯?是刻薄的嘲讽?或许真的是众声喧哗吧。
注释:
①参见胡兰成:《民国女子》,收入《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
②张爱玲:《论写作》(1944),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③张爱玲《罗兰观感》:“《倾城之恋》的故事我当然是烂熟的:小姐落难,为兄嫂所欺凌,‘李三娘’一类的故事,本来就是烂熟的。”又,《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倾城之恋》似乎很普遍的被欢迎,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报仇罢?旧式家庭里地位低的,年青人,寄人篱下的亲戚,都觉得流苏的‘得意缘’,间接给他们出了一口气。……”
④张爱玲:《倾城之恋》,收入《传奇》(增订本),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以下引文均出自这个版本。
⑤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⑥陈思和曾谈到过这个问题,表达他对张爱玲的理解。他认为从“成说”到“相悦”的改动是由于张爱玲的虚无主义倾向,说“我最终读懂张爱玲这篇小说,就是发现这两个字有差异”,“张爱玲本人的创作意图跟这个作品所展示的艺术形象之间是有距离的,通过无形中的修改,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人生的根深蒂固的虚无感。张爱玲喜欢调侃,喜欢把庄严的事说得很不堪。但它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张爱玲的骨子里是相信‘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问题是她从她的家庭教育中感觉不到真正的爱情。这样一种理性因素和她内在本能是有矛盾的,……”等,参见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⑦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三卷第11期,1944年5月。
⑧张爱玲:《花凋》:“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⑨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
⑩胡兰成:《论张爱玲》,1944年5、6月《杂志》第十三卷第2、3期。
(11)张爱玲:《论写作》,收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12)即sentimental,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张爱玲作品的一个“关键词”。张爱玲在《谈看书》(1976)一文中论及该词:“郁达夫常用一个新名词:‘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一般译为‘感伤的’,不知道是否来自日文,我觉得不妥,太像‘伤感的’,分不清楚。‘温情’也不够概括。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优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体的情感。另一个解释是‘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近代沿用的习惯上似乎侧重这两个定义,含有一种暗示,这情感是文化的产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夸张强调。不怪郁达夫只好音译,就连原文也难下定义,因为它是西方科学进步以来,抱着怀疑一切的治学精神逐渐提高自觉性的结果。”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292、29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