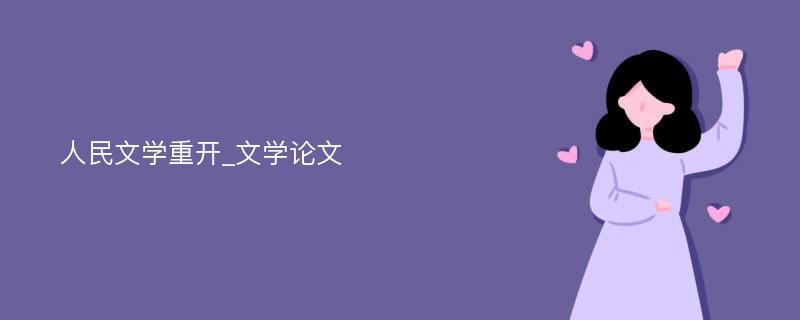
人民文学 重新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主张把“人民文学”重新写上文学的旗帜显然不再是一个时尚话语,但却是一种切中时弊之论。因为长期以来这一不该忘却的艺术原点不断遭到消解或改写,而这一问题不仅事关我们时代文学的宗旨与指向,还直接关系我们的文学因何而立又何以为生的根本命脉。
人民文学,需要重新出发
是的,今日的文学似乎没能赶上一个好时代。影视和互联网等电子媒体的强势覆盖,视听消费资讯全方位渗透带来的图文转向,都市娱乐业膨张形成的大众审美文化的勃兴,以及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导致的艺术经典性与膜拜性的日益丧失,使得曾经倍受荣宠的文学女神一夜间成了脱毛的凤凰。有人认同西方学人的预言,如“作家死了”(罗兰·巴特)、“艺术终结”(阿瑟·丹托)、“电信时代文学无存”(希利斯·米勒)等。也有人基于自己的国情,认定是这些年来持续的市场经济之“热”催生了文学之“冷”,或者是消费社会的文化转向造成了文学的边缘化颓势,以及全球化跨国资本运作的硝烟遮蔽了栖居精神世界的文学旗帜等等。这些识见之论都无不持论有故。问题在于,导致文学疲软的这些外在因素的背后还有没有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深层原因?窃以为,有的,文学对人民的疏离和文学底色上“人民性”观念的淡化,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文学生态已经改变,文学的外在形式失去文化竞争优势时,文学靠什么生存?波谷中的文学怎样才能找回艺术自信并重新赢得历史的尊重?人民文学,是一个需要重新镀亮的文学旗语!
这样的吁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时下的文学症侯。人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对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即最普通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毛泽东曾把“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作为检验过去文学是否具有人民性的基本尺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一些文学创作离人民的要求越来越远。许多被媒体热炒的作品并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底层人民的苦乐悲欢、爱恨情仇,没有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艺术需求产生精神共振和心灵共鸣,而是谄媚市场,迎合时尚,用“圈子心态”狙击人民立场,用“贵族书写”遮蔽庶民诉求。欲望的文场不时热炒的是“身体写作”、“下半身叙事”的“感官秀”,是小资情调的隐私揭秘、“宝贝”表演的欲望泛滥或木子美式的性趣表演。一些作品着力表现的是宾馆酒吧、名车洋房、大款小蜜、明星艳史、跨国婚姻、DJ情事,是三角、多角关系的鸳鸯蝴蝶派话本儿,是肥佬的谄笑和“愤青”、“朋克”一族的“垮掉”情怀。中小学生的书包里装的是《畿米绘本》《涩女郎》《哈里·波特》和《鸡皮疙瘩系列》,大学生的床头总离不了《我的野蛮女友》《此间的少年》和村上春树小说。摆在书店和街头书摊前排的常常是“宝贝”系列、“帝王”系列、“戏说”系列、“美女”系列、“红粉”系列在吸引公众的眼球。虽然近年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已逼近千部大关,但真正能够打动广大读者心灵的作品仍然不多,翻开作品,有踌躇满志的白领丽人,有酒色财气的潇洒先生,有商海角逐的富豪大贾,有宦海弄潮的大小官员,惟独少见普通百姓形象,少有人民的生存现实和心灵表达。于是便有“一部小说两位读者”的尴尬:一是作者自己,另一个是该书的责编。
文艺作品要得到人民的喜爱,必须从情感上贴近群众,倾听底层诉求,用敏感的默契表达人民心声,关注民生疾苦,多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如果你的创作远离现实和人民,必将导致创作无根、文学无本、艺术断奶;如果你的心里对人民的生活失去关注的热情,对他们的现实丧失评判能力,你的作品必将对人民大众失去吸引力和感召力。那样做的结果便免不了使作品变成自话自说的小资文学、白领文学、贵族文学,只能成为“松、软、薄、轻、飘”的绣花裙边和玲珑剔透的琥珀扇坠,而不会是民众性灵的真诚表达或沉雄悲壮的社会忧思。文学要找回尊严,就必须拒绝堕落;创作要有千秋情怀,就必须先有底层悲悯;作家要承担责任,就必须学会愤怒。在所谓“精英书写”的彼岸,我们有理由大声疾呼:人民文学,需要重新出发!
走出“人民文学”的观念误区
什么是“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涵?一直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从唯物史观上讲,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一切艺术活动的源泉和动力。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文艺必须描写人民,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才能从总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艺术论上看,艺术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感情、表现他们的意志与愿望,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才能使“人民文学”真正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因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惟一评判者”(马克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列宁),“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邓小平),作家应该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使文艺作品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从这样的基本观念出发,理解“人民文学”的概念需要区分三点:其一,“人民文学”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能简单地依据作品发行量的多少、读者群的多寡来判定一个作品是不是“人民文学”。木子美的《遗情书》畅销书市,并不能证明它就是“人民文学”。判定作品是不是人民文学关键是看其在内质上是否具有人民性。其二,“人民文学”不单纯是艺术认识论问题,而应该是情感本体论与艺术认识论的统一,艺术是情理交融的,艺术家认识到的东西不仅要转换为情感体验,还要有真诚的吟唱,而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动机和逻辑指涉。其三,“人民文学”是一个艺术概念而不是抽象的思想观念,其作品必须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达具有人民性的思想理念,实现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观念平台,反思当下文坛,有几类现象需要重新甄别:
“写人民”的未必就是“人民文学”。人民文学一般要写人民,像马克思所说的描写“叱咤风云的无产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仅仅在描写对象上“写人民”还只具有文学素材和创作题材的意义,并不具备人民文学所要求的价值内涵的必然性。人民文学除了“写人民”外,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作者必须秉持人民的立场,表达人民意愿,为民代言,以民为鉴,对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伟大历史实践表示理解、同情和支持;二是从思想感情上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爱其所爱、憎其所憎。有了这两个前提,一个作品无论写人民与否都可以是人民文学;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前提,即使是写人民的作品,也未必就是人民文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分享艰难》《苍山如海》这类直接写普通民众生存的作品是人民文学,而《尘埃落定》《白鹿原》并不以普通劳动群众为主人公却并非就不是人民文学。相反,那些专门写隐私、写秘闻、写情色的作品并非没有写“人民”的生活,但它们与人民文学的宗旨却相去甚远。
媚俗大众不是“人民文学”。一些作品格调不高,无非是以媚俗公众的方式媚俗市场,最终谄媚于一己名利。但这类作品通常有一种伪装,即用通俗易懂、低俗诱人的形式去膨胀人的感性欲望,刺激身体快感,乃至以庸俗不堪的情色诱惑蚕食健康的道德防线,遮蔽或麻痹人们健全、高尚的精神品格,用非艺术的方式玷污人的心灵世界,而这一切都可以打着“人民”的旗号和“艺术”的幌子来进行。这样的作品不仅在艺术定性上不再是“文学”和“人民文学”,而且在功能上也不是“为人民”的文学,它们与人民文学应有的价值品格背道而驰。
迎合时尚不是“人民文学”。消费时代,时尚的力量似乎难以抵挡。追逐时尚,跟踪流行,使一些作家改文风、换手笔,眼球跟着市场转;追寻畅销与火爆也使一些读者追风逐浪、躁动不安。这种作者与读者、创作与接受的默契容易让人将时尚写作奉为“人民文学”,将存在当合理,以从众扮新潮,其结果要么是口水化写作,用时髦的话语做秀;要么情感关怀匮乏,以矫饰招徕卖点;要么媚从大众传媒,用时尚迎合炒作。所谓“快餐文化”、“一次性阅读”、“文坛热点招贴”、“文化快捷键”等,都是文学时尚化的表征。在这些时尚的背后,蕴藏的则是拒绝思想、放逐意义、回避责任、逃避崇高,用流行文化的乌托邦许诺慰藉虚幻的心灵期待,把艺术的审美韵味置换为享乐主义的感官震惊。这样的作品只能使普通民众陷入消费文化的欲望圈套,而与人民文学的艺术道义相异云壤。
网络写作不等于“人民文学”。文学走进互联网,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平民化开放视野。网络上自由、兼容和共享的虚拟空间,打破了情英写作对文学话语权的垄断,为每一位愿意上网创作的网民提供了“人人都能当作家”的机会。笔者曾将网络文学界定为“新民间文学”,标志着“文学话语权向民间回归”。尽管如此,网络写作仍然不能与“人民文学”相提并论,因为人民文学并不取决于传媒的公共性和参与的广泛性,而取决于这种文学的人民性审美品格。网络文学的良莠不齐、精芜并存和复杂多样,使它成为大众狂欢的文化空间,而网络文学如果缺少意义承担和审美提升的价值蕴含,它就将无从赢得“人民文学”的艺术厚重。
怎样写作才是人民文学
首先,人民文学是人民喜爱的文学。一部好的作品应该人民爱看、群众好读,能抓人眼神,动人心旌,使人快乐,这样人民大众才会走近它、欣赏它、喜爱它,才能使“人民文学”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学”。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是人民文学尊奉的创作原则。“人民喜爱”既是一种艺术限定,也体现一种艺术宽容,因为它不仅包括了那些直接或间接描写人民的生活、展现人民伟业壮举的主旋律作品,还兼容了那些并非金戈铁马、思想厚重但却内容无害、艺术有益的雅俗共赏之作。特别是在大众文化云卷浪涌、精英文学市场日渐萎缩的今天,一个文学作品如果没有艺术上的过人之处和动人之点,缺少审美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就只能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上遭遇冷眼秋风。媚俗是一种误导,枯燥无异于背弃,艺术首先远离人民,人民才会远离艺术。精心打造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是所有艺术创作的铁律,人民文学不会因为价值立场的限定而降低其艺术要求。
其次,人民文学需要平视审美。创作人民文学必须要有平视审美的平民立场,即毛泽东所强调的“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人民是“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处于社会底层,进入艺术视野时勿须仰视,将他们塑造成为“高大全”式的英雄;也不要俯视,即居高临下,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同情者抑或“救世者”姿态。创作者应该站在人民的同一地平线上,去体察和感悟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岗职工、贫困农民、打工兄弟和期待救助的让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貌、利益愿望,敢于直面现实,深触民众生存的底部,对人民的苦痛应声而出并施以援手,而不是面对沉重时闭上自己的眼睛,或者将苦难的大悲悯化作泛、软、俗的消解性叙事。我们的许多作家已位居“中产”阶层,或把持一定权柄,忝列荣宠身份,客观上已经很难走进社会底层人群,切肤感受他们的汗水血泪,体验他们的苦乐酸辛,很容易在空间、情感、心理上与普通民众保持多重距离。我们看到,与高晓声复出文坛时“半生生活活生生,动笔未免先动情”的创作心态相比,诸如“万里采风”、“挂职锻炼”式的生活考察终归隔着一层,更不用说那些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式的写作了。
再者,人民文学要求千秋叙事。所谓“千秋叙事”是指文学创作要有为时代立心、为人民立言、为社会立照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作者敢于“铁肩担道义”,使自己的创作在关注社稷苍生的历史命运中浸润艺术忧患意识,在表现人民当下的生存境况中体现出人文性的终极关怀,在深度切入人民的情感和心灵时让人感应到那个时代的脉动,表现人民的真善美和精气神,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文章千古事”的历史记忆和“得失寸心知”的心灵铭写。老托尔斯泰倡导“蘸着心血写作”,巴金先生提倡“把心交给读者”的“讲真话文学”,大江健三郎用“灾厄感”将“自己的民族精神升华到一种悲剧的高度”,凯尔泰斯“用血痂做茧”,“揣着恐怖的记忆和绝望的希冀”为奥斯威辛的历史作证,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用残酷的笔描写种族隔离下人们的命运”,这样的人道立场和人文关怀就是文学应有的千秋叙事。大凡历史传诵的精品力作,都是凭着这种真诚的人道情怀和深沉的道义承担感而走进人民的视野,受到人民的喜爱,从而赢得历史的尊重。
还有,人民文学要有坚挺的精神。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根脆弱的苇草,他的全部尊严就在思想和情神。确实是这样,人民文学的质感与美感、支点与亮点、思想与理想、张力与魅力就在于它拥有坚挺的精神,并由坚挺的精神激扬出艺术作品光英朗照的锐气,焕跃出人性的卓绝、生活的亮色和时代的姿彩。但时下的许多作品却风骨不劲,元气虚亏,患上了软骨症。一些创作以休闲、娱乐为指归,以“前卫”、“新潮”而自矜,沉浸于风月脂粉和欲望撒播,着力表现的多是商品拜物的膨胀、腐化贪婪的攫取,或卑微昏噩的生活、阴暗颓废的心理,缺少强健的思想和崇高的理想,没有丰富的情愫和光彩的灵魂,他们眼神的空洞,不是睥睨社会文化或价值造成的,而是空洞本身;他们行为的“鄙德”色彩,不是鄙视传统道德,而只是无聊的自我中心。马克思说过,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而那些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文学作品不能只满足于表达感性冲动和欲望张扬,更不能用诲淫诲盗之作去排斥思想,放逐理想,消解信念,而应该以艺术美德打造灵魂的健康,用坚挺的精神引导和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审美趣味,在艺术的碑碣上镀亮人民文学应有的质素和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