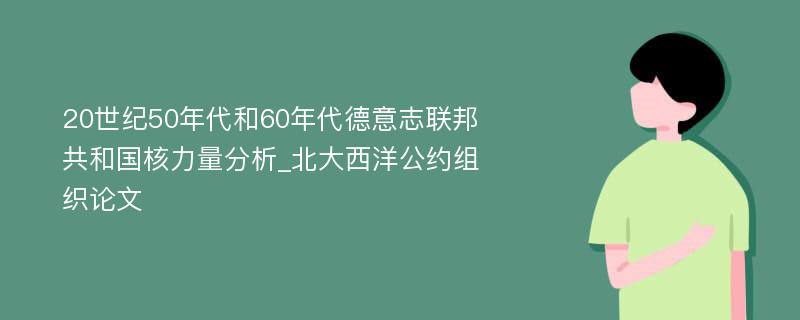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核武装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德国论文,核武论文,探析论文,五六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6)05-0675-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政府以声明的形式主动放弃了在本国制造核武器的权利。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政府在不违反声明的前提下为谋求核武装进行了努力,在谋求核武装的努力失败后,联邦德国政府及时吸取了教训,不再谋求核武装。分析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的背景、过程及失败的原因,有助于了解联邦德国在二战后外交和政治上的局限性。
一
1954年9月28日,在讨论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问题的伦敦九国会议上,阿登纳主动发表声明,放弃在本国制造核、生、化武器。表面上看,它是联邦德国单方面所做的巨大牺牲,实际上,阿登纳作出这一声明是不得已而为之。首先,作出这一声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消法国的疑虑。“如果西德不作这样的承诺,肯定会产生麻烦,特别是在巴黎方面”[1]658。法国一直担心,重新武装起来的联邦德国会对法国再度构成威胁,所以希望能给予联邦德国军备上的监督和限制,为此甚至不惜让伦敦会议陷入僵局。阿登纳作出这个声明,连他自己也承认,“是出于会谈进程的需要”[2]402。其次,北约在1952年里斯本会议上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常规力量以抵消苏联在常规力量上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阿登纳对军事战略的认识。“阿登纳所形成并确信的战略思想,仍旧依据这样一种想法,即加强北约的常规武装力量就有可能击退任何潜在的进攻,而无需诉诸核武器”[3]211。最后,阿登纳的声明还做了相当大的保留,为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留下了余地。这个声明强调不在本国制造和拥有核武器,但并不排除从别国获得或购买核武器,更不包括取得对别国核武器的支配权。
随着冷战对峙的加剧,以及美国在世界战略上进行的调整,联邦德国政府包括阿登纳本人逐渐认识到核武器对联邦德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联邦德国所依靠的是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这让其在安全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担心成为美苏冲突的核战场。1955年5月,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联邦德国、荷兰和北非举行了代号为“全权处理”的军事演习,在这次演习中,假设前苏联深入到联邦德国境内,北约动用核武器进行还击。在联邦德国造成了170万人“死亡”和350万人“受伤”,这还不包括放射性污染所造成的破坏[3]211-212。现代核战争极其可怕的一面呈现在联邦德国政府面前,任何规模的一场核战争,其后果对于联邦德国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另一方面又担心美国在关键时刻不敢动用核武器。1956年,美国在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中提出了“雷德福计划”,按照“雷德福计划”,为了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美国应该削减常规武装部队80万人[4]296。“雷德福计划”于1956年7月13日一经纽约时报披露,立即引起了联邦德国政府的注意。阿登纳认为,雷德福计划对于联邦德国的危险在于,一旦联邦德国遭到来自东方的进攻,“如果实现雷德福计划,美国将会袖手旁观,因为干涉意味着一场原子战争”[5]226-227。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会冒着本土被攻击的危险而动用核武器,如此一来,美国的核威慑效用将大打折扣。对于这种安全上的两难困境,联邦德国国防军总监豪辛格有很好的总结:“一旦发生冲突,这将立即引起一场核战争;一旦联邦共和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报复性打击将变得无用;存在着‘小’的常规战争的危险,东方不用多少准备时间即可动用其远为优势的力量”[6]256。
英国法国建立和加强自己核威慑力量的政策,则让联邦德国政府担心这将使联邦德国在西方阵营内部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同英国和法国拉开了距离,拒绝向英国和法国提供核声援。美国的这种态度让欧洲盟国对其在关键时刻动用核武器的决心感到怀疑。英国着手研制氢弹,法国也不甘落后,开始研制本国的第一枚原子弹。法国总理德姆维尔声称:“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是卫星国。”[7]564这一观点虽然是为法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进行辩护,但让阿登纳政府担心,法国谋求核武器的动机是为了取得对联邦德国的优势地位。阿登纳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西方阵营内获得平等地位。在英国和法国两国大规模发展本国核武器的情况下,正如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罗伯特·鲍伊所说,联邦德国放弃生产核武器的声明,“从长远观点来看……很难说会约束德国不要求享有同联合王国和法国平等的核地位”[1]672。
美苏的核对峙使联邦德国在安全上处于两难境地,英国和法国追求核大国地位的举动,则让阿登纳政府担心联邦德国会在这一领域内失去发言权。1956年年底,在联邦德国政府内部,首次出现了联邦国防军应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用核武器装备起来的主张[8]42。对于这一主张,阿登纳表示同意。在1957年4月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阿登纳声称,战术核武器只是继续发展的炮兵,“显然,我们不能在正常的装备方面放弃我们部队最新武器的发展工作”[5]343-344。
二
要解决美苏冷战背景下核武器在安全和政治上带来的问题,对于联邦德国来说,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建立属于本国的核威慑力量,二是取得对核武器的支配权。联邦德国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尖端技术,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研制核武器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办到。如果联邦德国步英国和法国后尘研制核武器,将违反它在伦敦会议上所作出的承诺。对联邦德国来说,建立属于本国的核威慑力量显然行不通。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主要是在与他国合作的基础上,取得对核武器的支配权。
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首先从引进核运载工具着手。1957年5月初,在波恩召开了北约春季理事会上,杜勒斯呼吁盟国在各自的军队中引进核运载工具——大炮、轰炸机和导弹。这一建议得到了联邦德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决定引进核运载工具。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将会与美国形成“两把钥匙机制”,核武器运载工具由联邦德国部队管辖,而美国则保留对核弹头的控制权。“如果美国人不同意使用弹头,德国人就不能发射。反过来,如果德国人不发射,美国人的弹头也打不出去”[9]287。按照这个机制,美国只能在核武器驻在国的同意之下动用核武器,如此一来,联邦德国将对部署在本国领土上的美国战术核武器的运用取得监控权。
由于联邦议会选举将在1957年9月份举行,为了不让反对党借核问题来赢得选票,阿登纳认为,应该拒绝美国在联邦德国领土上储备核弹头。但他的意见遭到了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坚决反对,施特劳斯没有提到“两把钥匙机制”,从而把联邦德国进行核武装的问题仅仅说成是在联邦德国境内为美国驻军配备核弹头。施特劳斯的一番辩解,总算使具有爆炸性的核武器问题得到缓和。在顺利赢得大选之后,阿登纳政府从美国引进了各种可以搭载核弹头的飞机和导弹。1959年4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装备具备核运载能力导弹的营。5月5日,美国和联邦德国签订了一项核合作协议,其中规定要训练联邦德国部队来使用核武器以及防御核武器,要把“原子武器系统的无核部分,连同有限制的资料”移交给联邦德国[10]149。
尽管联邦德国取得了核运载工具,但核弹头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联邦德国对战术核武器的运用只有监控权。正如基辛格所说:“把中程导弹配置在欧洲所根据的双重否决制度,只给予我们的盟国一种消极的控制权。根据这个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和所在国家的同意,不能发射导弹,而核弹头则仍然完全由美国掌握。因此我们的盟国能够阻止我们进行报复。但是它们不能够迫使我们进行报复。”[11]149
联邦德国通过“两把钥匙机制”取得了对美国部署在联邦德国境内战术核武器的监控权,这并不能完全满足联邦德国军事和政治上的需要,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取得对核武器的使用权。美国所主导的在北约内部建立一支多边核力量的计划,为联邦德国的核武装提供了又一次机会。
阿登纳是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最早倡议者之一。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没有明确表现出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这增加了联邦德国对其核威慑效用的怀疑。“出于这种原因,德国方面感到,在联盟内部实行最大程度的一体化,以及以一支共同的核力量为形式的集体控制核武器是不可或缺的”[12]159。1960年9月初,阿登纳与北约秘书长斯巴克和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尔施塔特将军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达成共识,建议把北约变成“第四核力量”,即建立一支北约中程导弹力量,交由北约理事会监督[6]597。阿登纳等人的建议,使美国政府认识到,美国应在对核武器的要求尚未失去控制时想出自己的解决方案。1960年12月16日,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赫脱向盟国提出了一项建议,该建议包含了多边核力量的主要因素。赫脱建议的核心是,美国同意在1963年以前向北约“转让”5艘各装备有 16枚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以及向盟国出售100至120枚安装在海面舰只上的北极星导弹,然后由这两个因素组成一支“多边核力量。”对于美国的这一提议,阿登纳表示联邦德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就美国建议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参加谈判。
在美国的北约盟国中,联邦德国是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惟一支持者。多边核力量计划遭到了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反对,甚至一些小国也对这个计划反应冷淡,“除了德国以外,反应都很低沉;看来多边核力量计划可能会缩小成为华盛顿与波恩之间的事情,而总统是决不会接受这个局面的”[13]616。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继任总统。与肯尼迪相比,约翰逊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并不热心,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与苏联就核不扩散达成一致。鉴于这种情况,联邦德国政府感到,如果继续推迟多边核力量计划,这个计划就注定要失败。1964年10月6日,阿登纳的继任者艾哈德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建议联邦德国和美国先就建立一支多边核力量签字,以此来推动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加入,但联邦德国政府的建议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这时,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以让北约盟国参与核决策的方式来取代多边核力量计划。尽管如此,联邦德国政府仍然为推动多边核力量计划进行努力。1965年12月20日,艾哈德访问美国,与约翰逊就多边核力量计划进行磋商,但结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联邦德国方面仍然坚持美国政府已经不感兴趣的多边核力量的“硬件”解决方案[12]214。
1966年2月,在华盛顿成立了具有磋商性质的核计划小组,作为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替代品。至此,多边核力量计划寿终正寝。对于联邦德国来说,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失败意味着“德国外交政策想通过参加一支集体的北约核力量,来补偿本国放弃占有核武器并防止欧洲共同体成员及其成员国分裂成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两个集团,或至少是缓和这种分裂局面,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了”[6]596。
三
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论就国内政治氛围还是就国际环境来说,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在国内缺乏群众基础。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民对战争中的杀戮,战后初期的悲惨生活记忆犹新,他们对于和平的向往尤为强烈。正是对战争的惨痛记忆和对和平的向往,人民群众对于联邦德国的军事动向尤为敏感,任何可能把德国重新变为战争机器的举措都会引起他们的警惕。1957年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8%的民众赞成达成国际间的核裁军,51%的人反对联邦德国国防军进行核武装, 56%的人认为核武器将增加联邦德国在未来冲突中的危险性[14]42。阿登纳在1957年4月5日记者招待会上关于联邦德国国防军有可能用核武器装备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各界的反对。反对声音首先来自联邦德国的科学界,4月12日,阿登纳收到了一份由18位著名的德国原子科学家签名的抗议电报。在这个电报中,科学家们声明,如果联邦德国没有核武器的话,它可以更好地为自己和世界和平服务。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该电报的签名者不会以任何方式参与核武器的制造、测试和使用”[14]43。反对的呼声还来自在野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要求联邦国防军放弃装备核运载工具的计划,并进一步要求政府拒绝北约国家的部队在联邦德国储备和部署核武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伦豪尔宣称,如果社会民主党执政,就会阻止联邦德国的原子装备,并负责不使西方盟国把原子武器储存在联邦德国境内[5]346-347。科学家的反对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呼吁,在联邦德国人民当中引起了共鸣,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在“为反对原子死亡而斗争”的口号下举行游行示威[14]121。声势浩大的群众反核运动,让联邦德国政府在谋求核武装的时候不得不低调从事。
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缺乏合适的国际环境。由于自愿放弃了制造核武器的权利,联邦德国只能在与他国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核武装,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政治现实来看,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别国身上,染指核武装的企图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历史罪责。由于纳粹德国的暴行,国际社会对联邦德国心存戒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20年,国际社会还没有忘记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场战争几乎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毁于一旦。甚至西方大国也担心德国民族主义会东山再起,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一个拥有核武装的德国可能会冲破战后大国对它的种种限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第二,实力对比。国际关系是最讲究实力对比的,它决定着国际关系中行为主体的地位。联邦德国把实现核武装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与美国的合作上,但两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决定了它们谈判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虽然联邦德国以加入北约为条件,得到了主权的恢复,但仍然不得不接受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它的种种限制。在重新统一问题上,在东部边界问题上,在柏林问题上,美国都握有最终决定权。军事上,联邦德国的安全严重依赖于美国保护。由于政治、军事地位的不平等,联邦德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回旋余地比较小,只能对美国决策施加有限影响,而不能完全左右美国的外交决策。在核武装问题亦是如此,自始至终,联邦德国只能起到推动作用,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美国手上。
第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追求的基本目标,是确定与他国关系的依据。国家利益决定西方大国不会真心实意支持联邦德国的核武装。美国虽然提出让联邦德国参与核武器的某些决策权并把联邦德国纳入多边核力量,但美国这样做,只是出于对联邦德国打算谋求本国核武器的担心,而并不想认真地赋予联邦德国以在核武器方面的平等地位。美国的军事战略服务它的与苏联争霸的全球战略,一方面,美国要集中西方阵营的力量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这就要求它在某种程度上对盟国进行让步,比如让它们参与核武器的某些决策权。另一方面,美国要极力控制住自己的盟国,使它们不至于挑战自己在西方阵营的霸主地位。在核武器领域也是如此,美国在西方阵营中核武器的超强地位是必须予以维护的。英国和法国对联邦德国的核武装也不支持,虽然在第四共和国期间,法国曾一度在核武器研究方面打算与联邦德国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只是希望借助联邦德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来建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并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建议。这个计划与戴高乐要建立独立核威慑力量的指导思想是相抵触的,所以他一上台后,很快就停止了这一计划的实施。戴高乐认为,对于联邦德国“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它有拥有或制造原子武器的权利——况且它自己已经宣布放弃这种权利”[15]153。与保守党相比,英国工党对联邦德国的核武装尤其抱敌视态度,在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公开反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当他们讲到不许‘更多的手指放在核扳机上’的时候,他们令人毫不怀疑,他们指的首先是德国人的手指”[6]605。
第四,国际形势。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缓和开始成为东西方关系的主旋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一个动机是根源于它在东西方紧张对抗局面下的不安全感。随着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消退,世界整体局势开始走向缓和,核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逐渐成为东西方谈判的主题。局势的缓和表明美国和苏联在面临直接冲突时会选择克制,美苏之间的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美国热衷于与苏联搞缓和,特别是力图与苏联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考虑到苏联的态度。而苏联一向对联邦德国重整军备的活动非常敏感,坚决反对联邦德国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显然有默契。肯尼迪在一次与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的谈话中说道:“美国根据本国的政策……决不会把核武器交给任何国家,而且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西德获得它自己的核能力。”[13]596
如联邦德国学者西奥·萨默[1]679所说,“波恩已将过多的威信投在参与核事务上”。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努力的失败,“这使得他们懂得了他们在核领域的严格局限”。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在谋求核武装的努力失败后,“有各种各样的迹象,德国可能从今以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寻求在核问题上的低姿态而不是高姿态……人们没有理由惧怕或怀疑最危险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将爱国主义与原子武器结合起来”[1]679。正是在吸取了谋求核武装失败的教训之后,联邦德国政府于 1969年11月28日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并在5年后批准了这一条约。
收稿日期:2006-08-09
标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北约成员国论文; 北约代号论文; 核武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