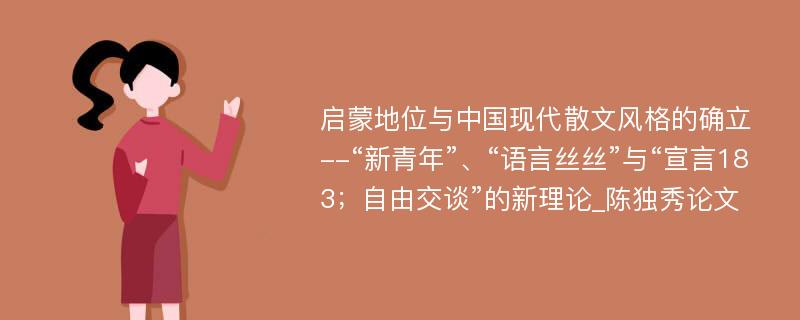
启蒙立场与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确立——《新青年》《语丝》与《申报#183;自由谈》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丝论文,新论论文,杂文论文,中国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同报刊的支撑及推动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在书报出版划定的文化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与之相比拟的新的文化空间了。”① 当然,对于这种文化空间及其文学生成和发展的研究可以多角度的展开。在考察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由萌生到确立乃至成熟的历程时,可以选择系列文学期刊作为考察对象。《语丝》周刊继承了《新青年》的启蒙传统,在思想革命和文学启蒙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于建构192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言说空间有着积极的贡献,同时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个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领域生成文体自觉意识,记录了中国现代文体意识由萌芽到确立乃至成熟的过程,同后来改版后的《申报·自由谈》,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发展史上的文学期刊系列。
《语丝》周刊与《新青年》月刊、《申报自由谈》② 都算是生存时间较长的刊物,出版发行都在数年以上,它们连接一起时间跨度达二十年之久,同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及其流派的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正如陈子展所言:“如果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果论述《新青年》以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又不能不写,这样才说得清历史变化的面貌。”③ 在强调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的《自由谈》对于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和成熟方面的贡献时,也不要忽略《语丝》周刊对于中国现代散文流派整体格局建构方面的价值。在记录中国现代杂文文体意识的过程的维度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新青年》《语丝》周刊与《申报·自由谈》在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背景下所秉承的思想品格。
一、以文学推动启蒙的坚定性
晚清以来,现代传媒在中国整个文学甚至文化的推动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时期,是现代传媒同文学密切合作的黄金时期。某种程度上也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受挫之后向思想文化界战略性转移的开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④,试图通过小说的“熏”“浸”“刺”“提”等文体功能对民众产生巨大的作用。同梁启超的“新民”理想一样,陈独秀“新青年”也是其政治革命受挫之后寻找到的一条民族自强之路。《新青年》试图以传播科学和民主精神为宗旨,试图通过这些西方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来影响“新青年”,达到启蒙的目的,进而实现其政治理想。“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⑤。应该说,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新青年”理想,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作为时代的精英和先锋者所传达的一种新社会、新国家、新民众的乌托邦理想。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是为了生活需求,希望自己能够在上海养家糊口,同时有一个能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根据社会现实和自己的社会实践兴趣,他选择了“以编辑为生”。陈独秀也认识到期刊杂志能够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影响到民众的思想,“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人的思想,须办杂志”⑥。创办之始,陈独秀没有明确的办刊理念,基本上延续了《甲寅》的办刊思路、编辑策略,并且靠《甲寅》的作者群来维持稿源,带有明显的《甲寅》痕迹。从文学作品的刊载来看,前2卷的《新青年》可以说是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拼凑:第1卷有屠格涅夫小说《春潮》《初恋》以及王尔德“爱情喜剧”《意中人》的译文,谢无量的旧体诗歌;第2卷有苏曼殊的文言小说《碎簪记》、刘半农的《灵霞馆笔记》加盟,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陈独秀在这些作品的编后评语中,着重指出内容的重要性,但是《碎簪记》并未摆脱民初上海言情小说的窠臼,可见陈独秀提倡文学的困境。被人多次征引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虽然指出欧洲文艺由古典主义变为理想主义,进而变为写实主义,最终成为自然主义,但这种认识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文学的了解不甚深刻。
直到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的“通信”批评陈独秀刊物主张和编辑实践背离后,陈独秀在胡适的启发下,认识到文学改革的突破口,这便有了后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可以说,真正体现《新青年》同人文学理想和理论贡献的,就是将文学革命推进到语言的层面。“白话不仅仅是文学的语言问题,更是民族的思维变革的问题。因此不仅把白话作为文学的语言工具,更是把它作为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倡导,通过创造获得文学语言来激活民族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话代替文言的主张支撑了思想启蒙运动,通过语言形式的变革延伸了思想启蒙”⑦。如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作为文学革命的具体理论主张;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纲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的积极推动,周氏兄弟的加盟,将文学革命的思潮推向了高潮。
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⑧ 作为《新青年》同人,非常认同这一思路。一般研究者认为《新青年》杂志是一个以政论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刊物:显示文学革命功绩的3卷至7卷,由于与北大教授的结盟,文学和政论相得益彰;其他几卷,文学只是杂志的配角。借助于版面的编辑,凸显政论、学术传统。并就胡先骕针对文学革命实绩的批评持认同态度:
且一种运动之成败,除了宣传文字外,尚须出类拔萃之著作以代表之,斯能号召青年,使立于旗帜之下……至吾国文学革命运动,虽为时甚暂,然从未产生一种出类拔萃之作品⑨。
诚然,《新青年》重在“提倡”新文学而不是“实践”,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也认为《新青年》是一个以议论为主的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看重。陈平原先生敏锐地指出鲁迅受到当时文学史观的影响,认为应当把《新青年》占据主导地位的“议政”“述学”与“论文”看作是文学革命的实绩。“《新青年》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白话诗歌的成功尝试,以及鲁迅小说的炉火纯青;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新青年》同人基于思想革命的需要,在社会与个人、责任与趣味、政治与文学之间,保持良好的对话状态,并因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通信’和‘随感’”⑩。单就“随感”这一议论性的文体而言,它的产生是不能从传统或者西方文体传统的角度来看,而是从思想革命需要的角度来理解。胡适常说他用“札记的形式来思考问题,作为思想的草稿”,这里“札记”就是一些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思想灵感和材料。《新青年》第4卷第4号“随感录”栏目的开创恰恰适应了这一需求。新青年同人在创办这一栏目时并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文体,只是就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平等地交换自己的看法。鲁迅在《〈热风〉题记》中这样评论自己《新青年》时期的“随感”:
除几条泛论以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时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11)。
从具体琐碎的事件入手,用嬉笑怒骂的手法,褒贬抑扬,纵横捭阖,而这些就是后来我们称为“杂文”的显著特征,在《新青年》的“随感录”栏目中已经初具雏形。
20世纪初,《申报》《大公报》《时报》都已经出现了类似杂文的评论性文章,并非《新青年》首创。有意味的是,这种文章主要是知识分子趋向于思想革命、社会改革方面的思考札记,是知识分子与报刊结合后形成的一种写作风格。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迅速在各种报刊上蔓延。“稍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12)。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语丝》周刊创办为标志,出现了杂文创作的繁荣期。此时的“随感录”已经同现代传媒紧密结合,是一种启蒙话语。知识分子都开始重视同现代报刊的关系,如创办同人刊物,主要的目的是借报刊的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语丝》周刊在其《发刊词》中明确地表示:“周刊上的文学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和研究。”语丝同人在提倡的同时,付诸实际行动,使得杂文和小品文同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语丝》周刊上的杂感,在精神上继承了《新青年》的“随感录”,“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对“一切专断与卑劣”的反抗等,都是针对杂感的风格的概述。《语丝》周刊上对于杂感的重视,还体现在栏目的设置上,比如“随感录”栏目发表的文章就达二百三十篇之多。对于杂感的提倡,使得这一文体的写作影响深远。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并不是说仅仅是对这种形式的喜爱,它实际上反映出作者的写作价值取向。作家选择杂文(杂感)这一文体,看中的是这种写作方式的“启蒙”功能,意味着他对大众抱有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通过写作来观察社会、思考人生、针砭痼疾,在同社会、民众的沟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现代作家选择杂文作为说话的方式,既是对现代报刊文体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准确把握”(13)。从这个角度来看30年代改版后的《申报·自由谈》,就很容易理解它在促进杂文文体走向成熟的同时,也使期刊自身获得了文学史的地位。黎烈文在其接编后的第1期《自由谈》的《幕前致辞》中说:
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之涵养,大有赖于文艺,而文艺之应该进步与近代化,需要进步与近代化,乃是当然的事实。
……我们虽然不肯搬演猴子戏,模仿人的作为,以博观众一笑,不肯唱几句十八摸,五更相思,或者哼几句“云淡风轻近午天”,以迁就一般的低浅趣味,而我们也绝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帜,吹起什么号筒,出什么堂堂正正“像煞有介事”的雄师,以宣传什么主义,将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嗜好,来勉强大多数人的口味。我们只认定生活的要素,文艺是应该而又需要进步的,近代化的;同时却也不愿离观众太远,“自敲锣鼓自唱戏”,只在“台里喝彩”(14)。
这些宣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由谈》的批评和决裂。一方面致力于创造进步的、近代化的文艺,注重满足大众的口味,反拨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启蒙传统;另一方面为文坛搭建了一方发表的平台,“文坛景象,正反左右,一时浓缩在《自由谈》上。就报纸副刊而言,《自由谈》确实感应敏锐,包罗万象,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编得相当热闹,相当活泼的一个”(15)。改版后的《自由谈》一时成为刊载杂文的中心阵地,有近百位的作家在上面发表过杂文,但发表杂文最多的是鲁迅,自1933年1月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表近一百五十篇,这些后来辑录成《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个杂文集。鲁迅的杂文可以作为此时《自由谈》的灵魂,反映了《自由谈》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鲁迅运用文艺政论的形式,鞭笞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阴谋,对国民党官报和附庸报刊以无情的揭露,抨击揭露帝国主义、法西斯的反动本质,批判各种病态丑恶的社会现象等,在发扬报刊以文学推动启蒙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报刊杂文文体,促进了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成熟。
二、创作和批评队伍的团结性
《新青年》的成功,得益于大批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主编陈独秀深得用人之道。初期利用《甲寅》旧友,后期利用北大同事。尽管在第4卷前,这是由陈独秀独立编撰的刊物,但是《新青年》是依靠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的支持刊物。这也和当时出版界的潮流有关系。在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扉页上刊载的《通告(一)》:
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勉,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吴稚晖、马君武、张溥泉、温宗尧、胡适、苏曼殊、李大钊诸君,允许担任本志撰述。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地。
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新青年》从第2卷起开始突破皖系为主的格局。第3卷起因陈独秀应聘北大文科学长以及《新青年》编辑部迁入北京,作者队伍迅速增加,逐渐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第3卷至7卷的大部分稿件依靠北大师生,连编务也变成六人轮流主编。“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同人,是个有共同理想、但又倾向于自由表述的松散团体……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16)。研究者经常征引的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须听将令”的一段自白也是最好的证明。《新青年》再次回到上海以后,它的作者群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带领下变成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作者,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骨干成员。这些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虽不是写作以求生活,但借助刊物发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仍可以想象出《新青年》创作和批评队伍的团结性。
《语丝》周刊的出现,应该是“五四”落潮以后有着浓厚启蒙情结的文化界进步力量的再次重新组合和集结。王统照对《语丝》周刊的诞生这样写道:
一二年来国内思想界纷乱可知已达极点,甚至竟可以说是没有好的思想。一般人受了悠缪思想的余毒,到底也洗涤不清;虽也是“新文化”或“思想革命”的大大喊呼,其实几年来所得的效果如何?恐怕大家都瞠目不知所答。因为我们觉得从前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及努力的那样锋利精悍的刊物还是有一样的需要;中国人根深蒂国(应为“固”——引者)的陈腐头脑,绝不是用偶然的针灸的医治方法所能奏效的。今《语丝》的发刊,就是向着冲破批评旧思想,及提倡新的生活的路上走的,自然,我们读过这篇宣言之后,非常盼望它能以坚持的办下去,以自由挥发的意见,来作割决归网罗(应为“来做割断罗网”义——引者注)的锋刃!(17)
《语丝》同人并没有辜负像王统照这样的文学青年的期盼,自觉地继承了《新青年》时期的优秀传统,首先喊出的就是“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的声音,意在为当时沉寂的文坛划出一道亮色。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新青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他们继续使用杂感、小品,来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并且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语丝体”散文,促进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熟。
以左翼普罗作家为主干,团结大批作家,造就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是黎烈文最乐意做的编辑工作的一部分。鲁迅早就指出,《自由谈》不是一份同人杂志,可谓一语中的。《申报》是东南地区有影响力的大报,读者对象多为官绅和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各方面的口味和意愿。它与近代以来产生的政党报刊不同,更多地提倡“中庸之道”。这也是史量才聘请无党派背景的黎烈文主编《自由谈》的主要原因。将有限度的文章结合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作家,这正是《自由谈》成功的地方。黎烈文对作家作者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用人所长”的策略,为《自由谈》著文的,有左联的鲁迅、茅盾、曹聚仁、施蛰存;有创造社的郁达夫、田汉、张资平;有文学研究会的叶圣陶、郑振铎;有语丝社的周作人;有与鲁迅进行激烈论战的林徽音、章克标;甚至有红色作家瞿秋白。我们还可以开出一长串的名单来,这个名单中的人物代表了当时思想界及文坛的各种流派、各种主义。比如陈望道、陶行知、周建人、夏丏尊、巴金、老舍、沈从文、谢冰莹、靳以、芦焚、欧阳山、叶灵凤、陈白尘、胡风、陈子展、周扬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如姚雪垠、刘白羽、周而复、林娜(司马文森)、柯灵、黑丁、荒煤、罗洪等,大都发硎于此。《自由谈》是他们走向成功的起点,也是他们成名后栽花莳木、耕耘播种的园地。在30年代文艺新人走向成功的过程中,黎烈文及他主编的副刊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功不可没,这是《自由谈》对新文学的一大贡献。
三、言说空间建构中的进取性
从现代传媒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认可借助杂志等媒介发动“革命”的思路。吸引知识分子的并不是某种刊物的具体章程,而是刊物自身的凝聚力,刊物为知识分子言说提供的平台的集约性。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发表关于社会、人生、文化等各方面的言论,现代传媒以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叙事、抒情、议论。“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报刊寄予的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报刊成为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平台,构筑了一个言说的空间(18)。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发表《宣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个人持论”的“公共意见”,可见《新青年》也在着意建构自己的言说空间:
本志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19)。
《新青年》初期,陈独秀积极发表自己的言论,占据了较多的篇幅。后依靠北大文科同人,提倡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每一个社员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允许有不同见解,即使后来有关新青年社的分裂的论辩中,尊重个人的意见,仍然视为重要的原则。“公共领域”是以“个人的”声音体现的,“公共领域”是由“一个私人集合成的公共领域”。所谓“众声喧哗”,这才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特征。在《新青年》上,有关文学革命的讨论、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对文学作品现象的批评、旧剧改良问题、白话文学及其相关的学术建设问题等、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个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个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此议论,时有异同,决不足奇,不无所设‘自相矛盾’”(20)。在同人内部追求大致相同的目标下,本着“以涤荡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展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观点,昭示了《新青年》公共论坛建构的进取性。其中较好体现《新青年》言说空间建构的是“通信”栏目,从《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的《社告》明确指出通信栏目“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到《新青年》第2卷第1号登载的《通告二》“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读者的主体性逐渐被培养起来,参与建构到《新青年》言说空间中,构成了五四“文学场”重要的一环。
谈到的《语丝》周刊在建构言说空间方面的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从同人启蒙立场逐渐消解、批评本体色彩逐渐弱化、编辑主体和创作主体由一体到分离、出版策略与文化理想由反抗转变为迎合等阐释了言说空间建构过程的动态性,不再赘述(21)。至于《申报·自由谈》,分析它在言说空间建构方面的特征时,首先要明确这样的前提,“就中国的文学场来说,它不是受制于政治场、经济场,而往往是与它们达成了某种默契,使文学的自主性原则受到政治场和经济场的极大制约。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场与政治场、经济场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生存环境,成为文学生产的必要条件”(22)。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改版后《申报·自由谈》的生存环境不同于《新青年》《语丝》时期。1928年国民党公布《著作权法》,内政部拒绝注册违反“党义”的出版物。1929年公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同年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1930年颁布《新闻法》《出版法》,严厉限制报章书刊的出版发行。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秘密通过“处置共产党条例”,决定对共产党“加重治罪,格杀勿论”(23)。1931年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视“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为“危害民国”,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又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具体阐释《出版法》,使适用范围扩展至“未直接涉及中国国民党党义、党务、党史。但与中国国民党党义、党务、党史有理论上或实际上之关系者”(24)。1932年11月《宣传品审查标准》出笼,指宣传共产主义为反动,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者为“危害中华民国”,凡对国民党政府有些做不满者为“替共产党张目”(25)。同时,国民党政府施行邮政检查,与这些法规相表里。1927年6月20日,国民政府秘书处发文敕令公安局赴邮局严密检查“讨蒋特刊”。1928年国民党中组部成立党务调查科,插手邮检工作,后一度划给中宣部管辖。1929年8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193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是陈立夫)成立,实际控制邮检工作。《自由谈》在“报禁”的夹缝中生存,这对于企图建构言说空间的黎烈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1933年5月25日的《自由谈》刊登了一则编辑室启事: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愿诸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一般论者在分析时多指出黎烈文利用了现代传媒传播效果的“反讽”特征,实际上显示出稍微的偏差:紧跟着的《自由谈》之所以变得热闹起来,只是作者利用了杂文的修辞效果罢了,但是这种面对“文网”破网的策略是杂文隐喻反讽手法等手段的运用。“在这个年头,如果一定要说‘二加二等于四’那就是不合时宜了,如果要我跟着别人说,‘二加二等于五’,那也办不到,于是我只能说,‘二加二等于五减一’”(26)。唐弢的譬喻十分形象,较好地概括了当时建构言说空间的艰巨性。但是,《自由谈》上也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小品文讨论、关于大众语辩论以及后来在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海派”的论战等,集中体现了《自由谈》追求自由独立的品格和建构言说空间的进取性。
注释:
① 杨扬:《文学的年轮》第28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本文讨论的《新青年》指《新青年》月刊,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终刊于1922年7月1日,共9卷54期,至于1923-1926年间陆续刊行的季刊或不定期刊《新青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新青年》第1卷叫《青年杂志》,第2卷才改名为《新青年》。《申报自由谈》刊行长达三十八年之久,同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本文讨论的是黎烈文和张梓生主持该刊的1932年12月至1935年11月期间,一度以集中刊载高质量的杂文而著称,成为1930年代刊载杂文的中心阵地。
③(15) 唐弢:《影印本〈申报·自由谈〉序》第1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④ 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1902年第1期。
⑤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⑥ 任建树:《陈独秀传》第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⑦ 庄森:《飞扬跋扈为谁雄:作为文学社团的新青年社研究》第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⑧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载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9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⑨ 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学衡》1923年第18期。
⑩(16)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3年第1期。
(11) 鲁迅:《〈热风〉题记》,载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147-14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18)(22) 周海波:《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1、18-19、14页,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4) 黎烈文:《幕前致辞》,载《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17) 剑三(王统照):《语丝发刊词》,载《晨报副刊》1924年11月16日。
(19) 《〈新青年〉宣言》,载《新青年》1919年第7期。
(20) 通信:《钱玄同答朱任两——〈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载《新青年》1918年第5号。
(21) 张积玉、赵林:《〈语丝〉周刊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言说空间的偏离》,载《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3)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3卷)第2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 《出版法施行细则》(民国二十年十月七日),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5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25) 柳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如何进行文化“围剿”的》,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3期;又载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26) 唐弢:《二加二等于五减一》,载《自由谈》1933年8月26日。
标签:陈独秀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语丝论文; 申报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黎烈文论文; 甲寅论文; 散文论文; 杂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