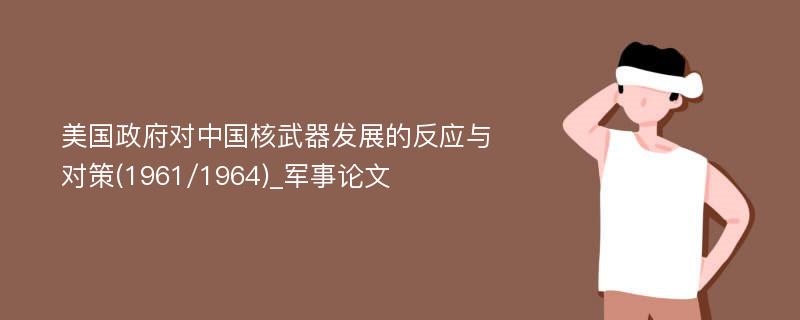
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与对策(1961-196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核武器论文,中国论文,应与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3-0044-010
关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对策,已有的研究基本上强调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的一面,而忽视了或没有充分注意到美国政府在进行军事方面准备的同时,也在准备非军事反应的一面。可以说,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全面显示出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如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张少书的《肯尼迪与中国核武器》①与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高级分析员威廉·伯尔和杰弗里·里查逊的《是否“杀死摇篮里的婴儿”:美国与中国核计划(1960-1964)》②,两文都忽视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内部围绕理性对待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方法所展开的争论及其对策最终确立的过程,或是过多地纠缠于采取军事打击,或是基本纠缠于通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阻止,对于美国政府在中国爆炸第一个核装置后采取了什么对策则没有论及,对于美国为什么最终没有采取军事打击措施,或没有论及,或语焉不详。结果,人们错误地认为签订条约和军事打击就是美国政府的对策,中国学者的研究也有意无意使人们形成这种认识。但实际上,它们仅仅是美国政府形成最后对策过程中的两个选择。
大致而言,美国政府为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曾有以下对策选择:一是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包括与苏联合作或至少苏联默许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或与蒋介石合作进行。二是核扩散,即支持或鼓励亚洲国家,主要是印度和日本发展核武器。三是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四是在不放弃第一种选择情况下,主要通过各种外交和宣传手段,树立美国的强大形象,贬低中国核试验的意义。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考虑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选择,否定第二种选择。约翰逊政府在理性评估中国核爆炸意义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肯尼迪政府时期已经出现,但没有受到重视的第四种选择。
一、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初步尝试
美国政府解密的文件表明,肯尼迪对中国有一种偏见。肯尼迪及其顾问认为,中国比苏联更危险、更有威胁性和侵略性,是特别敌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因此,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前景感到担心和烦恼,认为“60年代最大的事件很可能是中国的核武器爆炸”③,不仅会威胁美国的安全,而且将改变东亚力量平衡,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拥有核武器,就会提高中国在亚非拉不发达国家中的声望,使更多的国家追随中国,这将迫使苏联也采取激进政策,以保持它在亚非拉不发达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华盛顿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发展核武器,1955年以来就跟踪评估中国核武器进展情况,1960年12月6日的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国可能在1963年进行核试验,空军甚至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可能在1961年底进行。肯尼迪从 1961年1月入主白宫到1963年11月22日被暗杀,一直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予以异乎寻常的关注,试图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由于中苏分裂加剧和苏联暗示对中国的核发展潜力感到担心④,肯尼迪试图探寻美苏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肯尼迪在就职20天后,就在白宫召开有副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哈里曼和汤普逊大使、前驻苏大使波伦和冷战理论家凯南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邦迪参加的会议,讨论美苏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顾问们认为:“苏联最怕的不是美国的核武器,而是中国掌握原子弹”,赫鲁晓夫可能迫切想在与西方的外交关系方面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军备控制方面;建议利用中苏分裂努力与赫鲁晓夫就防止中国成为核国家达成谅解,以使苏联同意阻止中国的核试验⑤。这很合肯尼迪的想法。而中央情报局1961年4月12日的评估认为,中共爆炸核装置不是“是否”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⑥。这无疑使肯尼迪更加担心。
但在1961年6月维也纳美苏首脑峰会上,赫鲁晓夫不仅不接受中苏永久分裂的说法,而且还坚定地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支持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当肯尼迪提出中国核问题时,赫鲁晓夫根本不感兴趣⑦。肯尼迪试图利用美苏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第一个努力遭到失败。
1961年6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中共核能力冲击的战略分析》中没有说明中国获得核武器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只是说中共获得核能力将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安全态势形成明显的冲击,建议采取政治的、心理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来应对⑧。同年9月,国务院的研究报告认为,具有核能力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政治和心理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因此,掌握了核武器的中国会使其他国家产生“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而获得“心理上的红利”。对亚洲国家而言,中国拥有核武器会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增加该地区国家接纳北京和疏远与华盛顿关系的政治压力⑨。这些评估对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影响的估计是正确的。很明显,国务院的研究并不像威廉·伯尔、杰弗里·里查逊和国内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严重高估中国核武器的影响及其力量。
但肯尼迪不同意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影响是政治的和心理的。1961年10月,他对《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中国肯定会发展核武器,当中国拥有核武器时,整个东南亚都会落入中国手中。中国在核爆炸后,甚至在拥有有限的核能力后,其外交政策会更加强硬,更有军事侵略性或军事冒险性⑩。那么,如何应对呢?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减轻中国核能力心理冲击的有效方法就是鼓励甚至援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并计划由白宫科学顾问在访问南亚时与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讨论中国核发展计划对印度的影响,以引诱印度向美国求援。副国务卿鲍尔斯同意,但最终被腊斯克否决。腊斯克说,如果我们主张核扩散, “我们将陷入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中”(11)。腊斯克实际上排除了用核扩散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思考。
考虑到中国拥有核武器后将产生的影响,肯尼迪不断敦促国务院制定应对计划。1962年9月 24日,已升任为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乔治·麦吉在《中国核爆炸后影响世界舆论的计划》的备忘录中建议,在中国核试验前发动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宣传运动,强调美国的绝对核优势和巨大的核能力,使亚洲国家注意到“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力量”,说明中国核计划是落后的,以打击中国的自信心,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敬畏心理。在中国核试验后,美国政府应立即发表声明,并通过媒体树立美国的强大形象、通过与美国先进武器相比较贬低中国核试验的意义(12)。腊斯克批准了这一建议,它奠定了此后美国几经争论而最终确定的对华核对策的框架与基础。但还没有证据表明肯尼迪满意这一计划。
二、利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对中国发展核武器越来越担心,不断要求对中国发展核武器进行新的评估。中央情报局局长梅肯认为有关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还不清楚,建议加强在该领域的情报工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邦迪与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协商后,决定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组来处理肯尼迪的要求(13)。此后,美国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得到加强。1963年3月至 6月,美国发现了兰州的气体分离厂和包头的核工厂。7月10日,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提交《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武器能力》的评估报告,肯定中国将在1964年左右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与此同时,肯尼迪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也在努力寻找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途径,决定与苏联签订核禁试条约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肯尼迪曾对梅肯说,中国拥有核武器将“打乱世界政治”,这对美国和西方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将采取“某种形式的行动,除非他们同意停止发展核武器”(14)。他所说的某种形式的行动之一就是与苏联一起签署核禁试条约。
核禁试条约并不是一个新主意,早在1959年美苏英三国就在日内瓦围绕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只是由于三国要求相差太远和U-2飞机事件使谈判没达成任何协议。1962年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又点燃了肯尼迪利用核禁试条约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希望。
关于签订核禁试条约的主要目的,肯尼迪在 1963年1月22日的国家安全会议第508次会议上说:“首要目的是阻止或延缓中国核能力发展”。但他认为只有美苏两国而不包含中国的核禁试条约“不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苏联也和美国一样希望达成协议。2月8日,他向他的高级官员重申了上述思想,并补充说,签署条约的主要原因是它可能防止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则它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他强调说,如果能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他甚至愿意接受苏联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的一些欺骗(15)。政府许多高官都支持肯尼迪的主张。
为促使苏联同意就核禁试条约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肯尼迪首先努力说服英国。在1962年 12月英美首脑拿骚会谈时,肯尼迪说中国爆炸核炸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会产生心理上的重大影响,美国应该与苏联讨论这个问题(16)。英国同意美国的建议。此后英国努力说服苏联就此进行谈判。1963年6月7日,赫鲁晓夫公开表示苏联愿意就有限核禁试与美国在莫斯科进行谈判,这增加了肯尼迪与苏联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希望。
不久,肯尼迪派出以哈里曼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为取得苏联的合作,1963年5月17日,麦·邦迪与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会谈,但多勃雷宁拒绝讨论中国核问题。然而,多勃雷宁的态度并没有使肯尼迪放弃与苏联合作的设想,他固执地对与苏联合作抱有信心。在哈里曼代表团启程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对哈里曼说: “在探讨美苏就中国问题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方面,你要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哈里曼说:“那我就更需要带点甜头去了。”肯尼迪说:“我在西德的银行里还有一笔存款,如果你认为我应该取出来用在这上面,我非常愿意照办。”(17)暗指只要苏联同意与美国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或同意美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美国愿意就西德非核化方面答应苏联的要求。
为确保达到目的,肯尼迪对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予以超乎寻常的关注,所有来自莫斯科的有关谈判情况的电报都要送到他手上,而所有发往莫斯科的关于谈判指示的电报都需要他修改和批准。7月15日,他给哈里曼发电报说:“我相信中国问题比赫鲁晓夫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更严重,你应在与他的私人会见中提出这个问题。我同意只有美苏两家能大量储存,像中共那样相对弱小的国家掌握核武器对我们所有的国家都是十分危险的,相信即使有限禁试也能够限制扩散。”肯尼迪要哈里曼努力“引出赫鲁晓夫本人对限制或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看法和苏联对此采取行动的意愿或是否能接受美国直接采取行动”。为贯彻肯尼迪的指示,中国核问题成为哈里曼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主题。
在会谈中,哈里曼没有使赫鲁晓夫就对付中国发展核武器同意采取共同的政治或其他措施,但他成功地说服苏联签署核禁试条约。1963年7月25日,《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签订。对于条约能否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都表示怀疑。肯尼迪本人也怀疑能否阻止,在拿骚会谈上他就对麦克米伦表达了他的担心(18)。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还要坚持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呢?可以认为,美国是带着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分裂中苏同盟的双重目的参加谈判的。因为,即使苏联不与美国合作或反对美国对中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只要苏联签署条约,本身就表明苏联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利益是冲突的,也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国的立场,这必然会加大中苏分裂。因此,肯尼迪是把禁试条约当做一个有效的和潜在的孤立中国和加速中苏分裂的工具来看待的(19)。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条约签订后,中国强烈谴责,苏联则竭力为条约辩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美国也部分实现了第一重目的,因为条约的签订,确实给中国很大的打击。可以说,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但中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条约。
三、试图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
由于核禁试条约不能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肯尼迪总统于是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试图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对手的核能力发展起来前就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也不是一个新主意。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就考虑过对苏联的核设施和核武器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20),但因为很难发现相关目标最终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随着侦察与瞄准技术的重大进步,美国对这种办法的兴趣显著增长,肯尼迪入主白宫后立即认真考虑这个问题(21)。从1961年秋直到肯尼迪被暗杀,美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寻求与苏联一起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或得到苏联的默许,由美国单方面采用军事手段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即使在苏联多次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肯尼迪政府仍在寻求单方面采取行动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
美国采取与苏联合作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设想约在1963年初形成,当时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用说服、施加压力或强制行动”迫使中国签署禁试条约的可能性。 1963年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柯蒂斯E·李梅将军提交了答复报告,建议采取诸如实施外交压力、宣传等间接措施和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攻击等直接军事行动。直接军事行动包括公开的空中侦察;支持韩国反对北朝鲜;加强海上控制措施,包括全面封锁中国海岸;支持蒋介石集团进行渗透、颠覆、破坏和反攻大陆;采取传统的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空袭中共的核设施或其他设施;利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摧毁中共有关目标。在每一个行动建议中,联合苏联共同行动要远比美国单方面的行动更有效,也比没有苏联参加的多边行动更有效(22)。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苏联合作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政府继续探寻这种可能。在哈里曼动身到莫斯科会谈前,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尼采的助手阿瑟·巴伯为哈里曼准备了题为《破坏中共核能力》的报告,它强调美苏军事合作的可能性,提出了美苏合作的一系列行动,从以苏联为主的“政治说服”到美苏联合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等等。他认为除非华盛顿改变欧洲核政策或对多边核力量计划作相当大的修改,否则苏联不会支持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肯尼迪表示,为防止中国成为核国家,他愿意考虑苏联的任何建议,包括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邦迪赞同总统的看法,但腊斯克强烈反对,因为多边核力量计划牵涉欧洲众多盟国,放弃它是不恰当的(23)。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谈中拒绝哈里曼的建议,不仅没有使肯尼迪政府放弃思考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反而成为1963年夏秋以后美国政府关注的中心。1963年7月31日,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评估采用常规武器袭击中共核武器工厂的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对中共发展核武器计划造成最严重冲击并延迟中共核武器发展。经过几个月的评估,参谋长们认为上述行动是合理和切实可行的,但建议使用核武器代替常规武器发动攻击(24)。据此,白宫制定了“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军事和其他制裁”的详细计划,讨论了苏联对“美苏合作采取激进手段阻止核扩散”的可能反应和影响美苏联合行动的主要因素,计划对位于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据一位政府前高级官员透露,政府实际上讨论了美苏合作对中国核工厂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计划:由美苏各出动一架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飞临罗布泊核基地上空并各自投下一枚核弹,并引爆其中一枚(25)。可能是因为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太大,11月1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提交了《我们如何阻止或延缓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报告,提出用非常规战打击中国核设施,并建议成立一个跨部门小组来“考虑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式和方法”(26)。这一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肯尼迪就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
在谋求与苏联合作或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的时候,肯尼迪也在探寻与蒋介石集团合作的可能性。1963年9月10日,麦·邦迪会见在美访问的蒋经国,在蒋经国保证不发动对大陆的反攻后,双方谈到了中国核武器问题。蒋经国说,台湾已发现了大陆的导弹和原子装置的位置,希望与美国合作除掉它们。邦迪说美国高度重视削弱中共政权的措施,尤其是阻止或推迟其核武器发展,但认为这些措施应得到最认真的研究(27)。11日,肯尼迪与蒋经国就该问题进行会谈。蒋经国要求美国提供运输机运送国民党的突击队到大陆以摧毁大陆核设施。肯尼迪问蒋经国,“空运300人至500人到如此遥远的中共在包头的原子设施所在地是否是可能的,担任运输任务的飞机是否是不可能被击落”。蒋经国回答说,他已与中央情报局官员谈过了,该计划是可行的(28)。实际上,由于担心蒋介石卷入可能会使中苏和好,肯尼迪此后没有认真考虑与蒋介石联合行动的问题。
四、反对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的声音
在肯尼迪政府高层谋求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政府内部各层面的反对声音开始出现,他们大都以较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发展核武器,不主张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
麦吉1962年9月的题为《社会主义中国核爆炸后影响世界舆论》的备忘录,在经过一个跨部门小组研究后于1962年11月17日被国务院批准。它认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影响是心理上的,并提出各种和平方式以把中国爆炸核武器所产生的心理冲击减小到最低限度。当肯尼迪要求哈里曼在莫斯科谈判中探寻与苏联合作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的时候,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罗斯托就不赞成,他对哈里曼说,北京不会因为发展了有限的核力量就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因为美国有“压倒优势的核力量”,而北京“希望保持它的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也会使中国在遇到美国力量时甚至比它今天的行为更谨慎”(29)。而在此前后的国家情报评估也说中国没有对任何东亚国家进行军事征服的企图,并表现出对美国力量的尊敬(30)。
可能是因为肯尼迪不满意,1962年9月以来,一个以国务院东亚事务专家罗伯特·约翰逊为首的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等单位人员的跨部门小组,开始对中国核试验的影响和结果进行一系列严肃研究。1963年10月,题为《中共的核爆炸和核能力:主要的结论和关键的问题》的报告完成。15日,包括国务卿在内的国务院官员、国际开发署、军控和裁军署以及美国情报局的20多名高级官员讨论这份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文件的结论,即对美国而言,“中共获得核武器马上会出现外交或政治上的难题,而不是军事上的难题”,只是加强已经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提出新的安全问题。美国不用对它的政策作出大的改变,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核能力“不会改变主要大国的力量关系或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平衡”。“社会主义中国和美国之间力量的巨大的不对称”将会减小中国的核威胁,掌握核技术的中国仍在美国的打击范围之内,这将迫使中国“考虑美国对大规模的侵略的可能的核或非核反击的危险”。这构成了对中共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中国不会首先使用原子弹,除非大陆受到“严重进攻”。作为应对措施,美国不应偏离现在的政策,只需要采取现在的方针,重点是向亚洲朋友提供安全再保证。不应过分依赖核威慑来应对中国核试验,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来对付非核侵略,只会使美国的友好国家更多地向中国靠近。因此,一旦中国进行核试验,美国并没有必要比现在做得更多。这样就排除了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腊斯克对这一文件相当欣赏,但肯尼迪政府没有批准,不过后来它对约翰逊总统产生了很大影响。
11月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科默对麦·邦迪说:“如果我对上述文件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罗斯托则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评论。不久,国防部和麦·邦迪都同意由5412小组(31)来考虑“阻止中共核发展计划的方式和方法”。但这份文件没有送给肯尼迪,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军事打击路上已经走得很远的肯尼迪不会接受(32)。
虽然这一文件没有使军事打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停顿下来,但它促使一些高级官员对军事打击进行再思考。很快,罗斯托要求腊斯克允许由政策设计委员会的罗伯特·约翰逊牵头来研究直接针对中国核设施的行动方式,腊斯克同意(33)。当这一研究正在进行的时候,肯尼迪被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
五、新的对策选择
约翰逊上台后,对中国的核政策仍处于争论中。1964年2月,罗斯托希望约翰逊总统能了解罗伯特·约翰逊1963年10月的报告的结论,并告诉总统“中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军事威胁,而主要是潜在的政治恐慌”。(34)
1964年4月14日,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前面罗斯托所要求的题为《采取行动轰炸中共核设施的可能性》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对中国核设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的四种方案:美国发动公开的非核打击;由国民党进行轰炸;由在中国的代理人发动秘密进攻;空降国民党大约100名特工破坏中国核设施。报告还分析了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利弊得失。有利之处是:消除中国核能力将减小印度、日本发展核武器的正当性和可能性,消除核扩散的一个重要源泉,剥夺中国的政治和心理优势等。不利之处是:美国不能保证清除中国的核能力,即使完全摧毁了它的核能力,中共由于掌握了核工艺,在四五年内也能重建核设施。美国进行第二回合的袭击政治代价是非常大的,这样,美国的攻击只能推迟中共发展核武器的时间。另外,如果进行军事打击,将遇到许多技术性问题,即美国难于查明中国所有核武器工厂,这样,即使是成功的行动也不能阻止中国在今后几年爆炸核装置,其次是非核空中打击相对麻烦,没有大规模的打击,彻底毁坏那些工厂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即是否需要布置核武器。而且,针对中国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各种程度上的不利的国际政治后果:国际社会认为美国不愿意接受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存在;与美国努力向世界表明的中国的核能力只有有限的军事意义的行动相冲突;它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白人,包括法国人都能发展核武器,但有色人种却不能;它将具有在亚洲突然爆发战争的严重风险,甚至使苏联支持中国。因此,罗伯特·约翰逊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核能力的意义并不能证明采取诸如会有很大政治代价或很高军事风险的行动是正确的。”“对中国核设施直接采取行动是不可取的,针对中国核设施的行动应该是针对中国大规模侵略作出反应的军事行动中的附带行动,这比直接的仅仅针对核设施的行动对美国更为有利。同样,旨在阻止中国威胁的行动不应仅仅只针对中国核设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果中共威胁采取原子行动,对核设施作出有限的威胁反应是可取的。(35)应该说这是一个较理性的结论,但麦·邦迪仍倾向于预防性打击,认为罗伯特关于军事打击的分析太不积极了。4月30日,腊斯克把这一研究的概要送给总统,他说针对中国核设施的军事行动是不可取的,除非是作为对中共重大侵略作出反应的一部分(36)。在外交上对腊斯克的信任有助于约翰逊接受该文件的主张。随着中国核试验的临近,1964年7月20日,腊斯克把1962年的方案发给美国驻亚洲各国使馆,要求各使馆提出建议,以有利于美国政府把中国爆炸核武器所产生的心理冲击减小到最低限度。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在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但对中国核计划进展情况却知之不详。直到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美国仍不能肯定中国何时会爆炸核装置。中央情报局局长梅肯1964年7月24日在与总统的会晤中承认,“我们不能预见中共在什么时候爆炸核装置”,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得出中共会在今后几个月进行核爆炸”(37)。而1964年8月26日的国家特别情报评估说,以前被怀疑的罗布泊就是核试验基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在两个月左右准备好该基地。但又认为中国位于包头的唯一小型气冷反应堆要到1964年9月才完成,至少要18个月,很可能要两年,包头的反应堆才能为核试验作好准备,因此中国“在今后几个月里还不会有充足的可供一次核试验的裂变物质”,1964年以后才能进行核试验。但中央情报局并未排除中国存在另外的生产裂变物质的工厂的可能性,也没有排除1964年底前中国“核爆炸的可能”(38)。
这样一个极为谨慎的评估在中央情报局内外都引起了争论。在中国进行核试验前夕,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也使人有理由怀疑中央情报局的结论。如多勃雷宁曾告诉美国无任所大使汤普逊,中国核试验随时都可能进行,梅肯9月12日将该消息告诉了腊斯克。另外,刚刚访问过中国的马里政府的一位官员也告诉美国,中国会在10月1日国庆节这天进行试验(39)。
中国核计划的进展对美国来说是该由总统决定对策的时候了。1964年9月15日,在有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麦·邦迪和梅肯参加的午餐会上,约翰逊“不赞成美国未经挑衅单方面对中国核设施采取预防性军事打击”,只有在中国发动侵略时才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会议同时决定,将继续寻求美苏“采取联合行动,包括警告中共不得进行核试验,甚至就预防性军事行动进行合作达成协议”,还同意国务卿就此事尽快与多勃雷宁大使会晤。这样,约翰逊确立了第四种选择。
目前还不清楚腊斯克是否会晤过多勃雷宁,但麦·邦迪在9月25日会见了他。邦迪竭力表明中国核武器是真正威胁,表示如果苏联有兴趣,美国准备与苏联进行严肃会谈。苏联大使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没有什么重要性,在亚洲的影响也只是心理上的。苏联的消极态度实际上意味着美苏合作的道路行不通,但美国并没有放弃这种考虑。无论美国对中国核问题多么关心,在离总统选举只有一个月的时候,约翰逊不能不考虑对大选的影响。在10月5日有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麦·邦迪和梅肯参加的讨论中国核问题的会议上,由于担心在大选期间出现冒险事件,约翰逊总统取消了9月15日午餐会上决定的对罗布泊进行U-2飞机侦察的计划(40)。
六、理性应对
根据约翰逊的决定,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政策设计委员会于四五月份准备的题为《中共核能力的意义》的文件中,除建议不应对中国核设施主动发动军事打击外,还提出了在中国核试验后应采取的方针,即更广泛地公开宣布愿意提供核防御;在存在安全义务下向盟国保证;提出一个中立的宣言来磋商;为核防御制定双边计划;万一发生核威胁,布置核武器;探讨与苏联发表联合宣言的可能(41)。它实际上成为美国政府在中国进行核试验后进行应对的指导方针。针对中国随时会进行核试验,9月29日,腊斯克发表声明:“中国随时都可能进行试验,但进行试验并不意味着储存核武器,而且在获得核能力投送系统之前,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完全清楚北京掌握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充分考虑了我们的军事姿态和我们的核武器计划”,这不会影响美国帮助亚洲国家“保护他们反对中国侵略”的能力或意志。他还向中国表明,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将面临世界各国的坚决反对(42)。9月30日,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准备了一份美国政府在中国进行核试验后将发表的声明(43)。10月15日,中央情报局负责科学情报的助理局长唐纳德·张伯伦给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马歇尔·卡特的备忘录摆脱了在中国核爆炸时间方面的混乱和矛盾,他肯定说罗布泊在10月就能为核试验作好准备,认为“在罗布泊的核试验随时可能发生”,即使有各种限制因素,“未来6至8个月内会发生爆炸”(44)。然而在10月16日就传来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消息,美国政府立即启动上述程序,应对中国的核爆炸。
首先,采取措施,努力减小中国核爆炸的心理冲击。这包括贬低中国核武器的意义和分析中国核力量的真正水平。
在中国核试验后,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纷纷出马,或发表讲话,或会见国会领袖,尽可能减小中国核试验的冲击。16日下午1点20分(美国当地时间),约翰逊总统宣读了9月30日准备的声明,他说美国对核试验并不“吃惊”,“不应该过高估计它的军事意义”,因为从核试验到储存能被有效地投送到打击目标的核武器还需要多年时间。他公开说“没有战争的危险”,美国将不考虑中国核力量而坚定地站在亚洲盟国一边(45)。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分析中国核试验后各国的反应。在会上,约翰逊决定于19日会晤国会领导人,并要求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就中国核试验后的形势向国会领导人简报,要求麦·邦迪向新闻界透露行政部门正与国会领导人进行周期性会晤(46)。18日,约翰逊发表广播电视讲话,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努力结束所有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他还保证美国将支持那些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反对任何核讹诈。在重复不应高估中国核武器的军事意义后他强调,当中国拥有核投送系统的时候,毫无疑问,自由世界将继续加强并会强大得多(47)。根据安排,10月19日,约翰逊总统在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等的陪同下,会见国会两党领袖。麦克纳马拉介绍了美国对中国核弹的军事立场,说美国的战略计划充分考虑了中苏境内的目标。在回答议员的核试验的心理冲击与军事意义的问题时,腊斯克说,“我们正采取每一个可能的措施和有关国家协商,以限制心理冲击。在总统的声明中我们也作出了重要保证”。他还说许多大使告诉他,9月29日的声明对限制冲击非常有用。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西博格竭力表明,与美苏英法相比,中国试验的核武器可能是简单的钚装置,而且是某种原始的裂变装置(48)。10月 23日,麦克纳马拉进一步强调中国核技术的落后,把中国的核装置描述成“原始的”和“不实用的”,中国的投送系统还要很多年才能出现。肯尼迪的亲信、前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也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说中国获得核武器并不会改变东亚或东亚以外地区的力量平衡(49)。尽管美国竭力弱化核试验的冲击,但中国的影响还是明显地扩大了,这一点美国不久就感觉到了。
分析中国核力量的真正水平。17日,约翰逊总统和国务卿腊斯克就参加了分析会,会议仍认为中国的核弹是钚弹,与法国最初的核装置所用的钚的数量差不多。关于投送能力,认为中国只有290架飞行范围为600海里、能运送6000镑的过时的伊尔—28型飞机,它们能否运送核弹还有待对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进行分析。总之,中国的成功是初步的,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拥有能对付临近地区的复杂的投送能力。为确定中国核弹的成分,美国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和侦察,派出两架U-2飞机和卫星在中国上空监视。一方面加紧对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进行采样和分析,搭载有特别收集设备的美国气象署的飞机先后30多架次从在日本的基地起飞。 10月20日,西博格向白宫报告说,从放射性尘埃来看,中国的核装置是铀弹而不是钚弹。美国始终不知道中国的浓缩铀来自何方,直到1964年 12月,U-2的侦察才使美国确定在兰州的浓缩铀分离厂一直在生产(50)。
其次,继续寻求与苏联合作或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在约翰逊总统18日的讲话中,除努力贬低中国核武器的意义和向盟国保证外,他还说:“反核扩散符合美苏共同的利益。我们将作好准备与苏联和世界各国合作,防止核扩散。”(51)这实际上是呼吁美苏合作。为寻求苏联的合作,10月20日,美国驻阿富汗使馆官员就与苏联驻阿富汗使馆官员讨论中国核爆炸问题。当天下午和晚上,腊斯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与多勃雷宁会晤,希望美苏合作,阻止中国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但苏联大使的立场依旧未变(52)。然而美国仍固执地认为可以利用日益扩大的中苏分裂。1964年12月,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在《摧毁中国的核能力》的报告中批判了罗伯特·约翰逊的观点,认为中国相对小的核力量也可能摧毁大量资源,因此,“中国的核能力并不能证明美国不采取可能会产生很大政治代价或军事风险的行动是正确的”,建议直接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或至少与苏联讨论这样的行动(53)。但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54)不同意。到了1965年4月,海军又建议击沉中国能发射弹道导弹的潜艇,以防止中国在太平洋袭击美国西海岸(55)。实际上,直到中国进行第四次导弹核试验,美国都一直试图单方面或联合苏联阻止中国进一步发展核武器(56),但都未得到苏联的积极响应。1966年以后,美国决定布置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其主要意图是防御来自中国的导弹袭击(57)。
总之,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核对策,基本经历了从肯尼迪时期的狂热到约翰逊时期的理性回归这样一个过程。在肯尼迪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坚持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或美苏合作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即使国务院认为中国核试验的影响主要是心理的和政治意义的而不会有多大的军事意义,肯尼迪仍坚持己见,其根源是促进中苏分裂和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敌视中国的政策,但此时美国已正确地分析了中国核武器的意义和中国对使用核武器的态度,且认识到军事打击的代价太大且不能防止核扩散,尤其重要的是约翰逊希望在1964年任期届满后能当选为总统,这些都促使约翰逊最终拒绝对中国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
诚然,美国最终没有采取预防性军事打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整个过程中,军事打击一直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应对措施。即使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仍是美国政府的选择(58)。因此,绝对不能忽视美国政府的冒险性和疯狂性,如果没有制衡力量的存在,很难说美国当时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和措施。冷战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足可说明这一点。因此,只有发展起足够强大的威慑力量才可能防止美国的冒险性,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即中国发展核武器是被迫的,完全是为了防御。正如罗斯玛丽·福特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都频繁的核攻击的威胁。”(59)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在成功进行核试验的当天,中国政府就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60)
注释:
①Gordon Chang,"JFK,China,and the Bomb",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4,No.4 (Much 1988).
②William Burr & Jeffrey T.Richelson,"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1960-1964",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No.3(Winter 2000).
③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29.
④Rosemary Foot,The Practice of Power:U.S.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Clarendom Press,1995,p.178.
⑤查尔斯·波伦著,刘裘等译:《历史的见证》,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93页。
⑥Memorandum from John M.Steeves to Roger Hilsman,"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on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Nuclear Capability",12 April 1961,National Archives,RG59,1960-1963,box 4.
⑦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1961- 1963,Vol.XXII,doc.29; 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p.230~232.
⑧FRUS,1961-1963,VoI.XXII,doc.36.
⑨Policy Planning Council Director George McGhee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Anticipatory Action Pending Chinese Demonstration of a Nuclear Capability",Sep 13,1961,National Archives,RG58.
⑩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p.232~237.
(11)Memorandum from Lt.General John K.Gerhart,to Air Force Chief of Staff Thomas White,"Long-Range Threat of Communist China",8 February 1961,Library of Congress,Thomas White Papers,box 44.
(12)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 George McGhee to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Robert Manning,"Program to Influence World Opinion With Respect to a Chicom Nuclear Detonation",24 September 1962,20 Sep 1962.RG 59.
(13)FRUS,1961-1963,Vol.XXII,doc.162.
(14)FRUS,1961-1963,Vol.XXII,doc.162.
(15)FRUS,1961-1963,Vol.XXII,doc.164; 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237.
(16)FRUS,1961-1963,Vol.XXII,doc.304.
(17)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第644页。
(18)FRUS,1961-1963,Vol.XXII,doc.304.
(19)Robert Garso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9.Pinter Publishers,London,1994,p.90.
(20)Bernard Brodie,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Princeton,1959,pp.228~229.
(21)Alain C.Enthoven and K.W.Smith,How Much is Enough? Shaping the Defense Program,1961-1969.New York,1971.
(22)General Curtis E.LeMay,to Secretary of Defense,"Study of Chinese Communist Vulnerability",29 April 1963,RG 59,Files Relating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1954-65,box 4,1963.
(23)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对华政策内幕》,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24)FRUS,1964-1968,Vol.XXX,doc.14.
(25)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p.245.
(26)Memorandum,General Maxwell D.Taylor,to General LeMay,General Wheeler,Admiral McDonald,General Shoup,"Chinese Nuclear Development",18 Nov 1963,National Archives,Record Group 218,box 1,CM-1963.
(27)FRUS,1961-1963,Vol.XXII,doc.185.
(28)FRUS,1961-1963,Vol.XXII,doc.186、188.
(29)William Burr & Jeffrey T.Richelson, "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1960-1964",p.76.
(30)FRUS,1961-1963,Vol.XXII,doc.80、107.
(31)根据1955年12月28日的NSC5412/2号文件建立,故被称为5412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秘密行动。
(32)FRUS,1961-1963,Vol.XXII,doc.193.
(33)William Burr & Jeffrey T.Richelson,"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1960-1964",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No.3,p.79.
(34)FRUS,1964-1968,Vol.XXX,doc14.
(35)FRUS,1964-1968,Vol.XXX,doc.25; Rosemary Foot,The Practice of Power,p.181.
(36)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Johnson,"Items for Evening Reading",1 May 1964,RG 59,President's Evening Reading Reports,1964-1974,box 1.
(37)FRUS,1964-1968,Vol.XXX,doc.38.
(38)FRUS,1964-1968,Vol.XXX,doc.43.
(39)FRUS,1964-1968,Vol.XXX,doc.50.
(40)FRUS,1964-1968,Vol.XXX,doc.55.
(41)FRUS,1964-1968,Vol.XXX,doc.30.
(42)Rosemary Foot,The Practice of Power,p.183; China and U.S.Far East Policy 1945-1967,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1967,p.146.
(43)FRUS,1964-1968,Vol.XXX,doc.57.
(44)FRUS,1964-1968,Vol.XXX,doc.56.
(45)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L.B.Johnson,1963-1964,Book II,p.1357.
(46)Glenn T.Seaborg,"Chairman,Atomic Energy Commission,Diary Entry for 17 October 1964",Journals of Glenn Seaborg,Volume 9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9).
(47)China and U.S.Far East Policy 1945-1967,p.147.
(48)FRUS,1964-1968,Vol.XXX,doc.60.
(49)Rosemary Foot,The Practice of Power,p.186.
(50)FRUS,1964-1968,Vol.XXX,doc.58.
(51)Gearld Segal,The Great Power Triangle.St.Martin's Press,New York,1982,p.126.
(52)FRUS,1964-1968,Vol.XXX,doc.61.
(53)George G.Rathjens,"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Destruction of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ies,December 14,1964".Source:ACD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release.
(54)为研究应对中国核试验后核扩散压力增大的方法,根据约翰逊总统1964年10月29日的建议,11月1日成立了由曾担任代理国防部长的吉尔帕特里克任主席的跨部门专门小组,通常称吉尔帕特里克小组。见FRUS, 1964-1968,Vol.VXI,doc.49。
(55)Memorandum,Rear Admiral Richard G.Colbert and W.E.Gathright,Policy Planning Council,to Walt W.Rostow,Director,Policy Planning Council,"The ChiCom 'G' Class (Missile-Launching Submarine),4 May 1965,RG 59,Policy Planning Council Subject and Country Files,1965- 1969,box 328,Misc.folder.
(56)FRUS,1964-1968,Vol.XXX,doc.76; Gearld Segal,The Great Power Triangle,p.127.
(57)Morton H.Halpefin,"The Decision to Deploy the ABM:Bureaucratic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World Politics,Vol.25,No.1 (Oct.,1972,pp.62~95).
(58)FRUS,1969-1976,Vol.XVII,China,1969-1972,doc.270.
(59)Rosemary Foot,The practice of Power,p.167.
(60)《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7日。
标签:军事论文; 核试验论文; 约翰·肯尼迪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武器论文; 核武器论文; 苏联总统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武器装备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