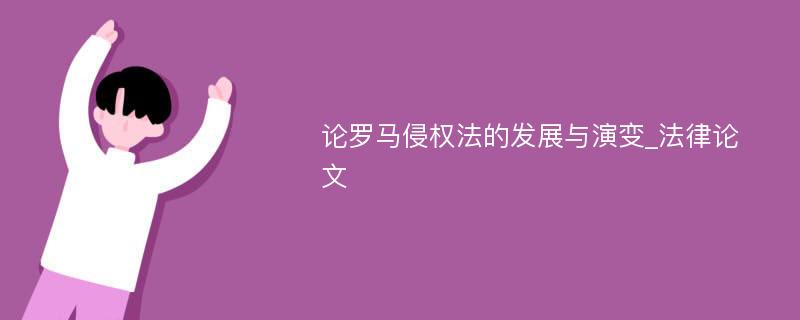
论古代罗马侵权行为法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论文,侵权行为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走进罗马法的世界,阅读其私法丰富的内容,领略其严谨的体系,在赞叹其私法发达完善的同时,人们不能不对其中构成侵权行为法的罗马“私犯”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走进历史的深处,探寻古代罗马侵权行为法发展的轨迹及其影响,对我们进一步深刻的认识罗马法与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考察侵权行为法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侵权行为法与人类法制文明的发生、发展始终相伴而行。在古代东方,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西亚的楔形文字法中,侵权行为法就已经作为人类最早的法律规范之一,以其特有的功能成为调整社会关系保护自由民权利的重要手段。在古代西方,希腊人最早开启了欧洲文明的大门,步入了拥有国家与法的社会,在异彩纷呈并不同一的古希腊法中,我们通过雅典债法中的“自由之债” (即自由协议而生之债)和“不自由之债”(即侵权行为而生之债)的分类,同样可以感受到在古代欧洲法的初创时期侵权行为法的重要地位。
古代的罗马法学家们继承了雅典国家有关债法的分类方法,并从雅典的“不自由之债”发展为古罗马法上的“私犯”制度,从而将人类的侵权行为法带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十二表法》首次提出“私犯”概念,到《阿奎利亚法》关于“违法性”的界定,再至东罗马帝国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细致规定,古罗马侵权行为法伴随社会发展的脚步不断丰富完善,已初步具备了近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基本理念和要素,并由此对后世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侵权行为法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诚然,由于两大法系的风格各异,体系不一,古罗马侵权行为法对其的影响也明显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侵权行为法是与财产法、合同法一起,成为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律。在大陆法系国家,侵权行为法则是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非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此,古罗马侵权行为法对与其一脉相承的大陆法系的影响无疑深刻深远,而对英美法系的侵权行为法则只是程度不一的表现为在基本原理、思想方面的影响。正因如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侵权行为法是以古罗马的侵权行为法即私犯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尽管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法律文明程度的局限,罗马法的私犯概念与制度还有着不少的稚嫩和狭隘,与现代不断拓展日益完善的侵权行为法已难以相比,①但这只是适应社会需要传承革新发展古代罗马侵权行为法的结果。
在古代罗马,公犯与私犯是法律对不法行为的两种分类。所谓公犯,是指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所谓私犯,是指侵犯个人人身或财产的行为。然而在罗马法的发展史上,公犯与私犯的界线并非固定不变,随着某些私犯所针对的“个人利益”性质的日益重要,一些私犯也被上升为关乎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的高度进而纳入到公犯的范畴。如公元前82年左右通过的《科尔涅利亚侵权法》,把原属私犯的一些致人伤害和侵犯住宅的行为纳入了公犯制裁的领域。公犯与私犯行为的区别不仅反映在所侵犯的利益性质不同,二者在制裁方式上也存在重大区别。公犯由国家直接加以刑事制裁,而对私犯的制裁则经历了复杂的发展演变阶段。本文拟通过对古罗马侵权行为法,即私犯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②以期对古代罗马侵权行为法在理论和制度构建上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做出评论。
一、私犯制裁方式和性质的变化反映了古罗马侵权行为法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
与古代法律民刑不分的特点相适应,古代罗马对侵权纠纷最初也采用刑事制裁的方式,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逐步向民、刑制裁并用过渡。总体上说,罗马法对私犯行为的制裁经历了从“私人报复—协议赎罪金—法定罚金诉—(罚金与赔偿)混合诉—损害赔偿诉”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部落公社时期实行的血亲复仇,往往是受害人的家族对侵害人的家族实施报复,“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③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漫无节制的血亲复仇逐步演变成“同态复仇”,即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再允许复仇程度任意扩大。由于当时财产观念并不深化,人们对损害赔偿的意识尚很淡漠,报仇是为了满足被害人或家族感情上的需求,并不关注实际上是否得到补偿。此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的确立,人们对物质补偿的需求终究战胜了对心理快感的满足,于是同态复仇就发展为赎罪金制度,由侵害方对受害方给付一定的金额作为补偿。最初的赎罪金是由双方自由协商确定的,若协商不成仍可实施同态复仇,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协商性赎罪金是私人报复主义的替代物,它的存在也是对报复合法性的确认,显然,其惩罚性要大于其补偿性。由于损害双方往往难以就赎罪金达成协议,于是产生赎罪金法定化的要求,即由法律制度对赎金的数额作出规定。公元前451年《十二表法》则承担了这一使命。该法规定了各种罚金的数额,自由协商的赎罪金开始由法定罚金取代。但此时,罚金与赎罪金性质无异,只不过后者由当事人自由协商,而前者由法律规定。不可否认,《十二表法》仍有同态复仇的遗迹,反映着古代罗马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正如梅因所言:“古代法律提供了其他证据,证明最古的司法官吏模仿着私人争执中人们的可能行为,在决定赔偿损害时,他们以在该案件的情况下一个被害人可能要采取的报复程度作为他们的指南。这就说明为什么古代法律对于现行犯或犯罪后不久被捕的犯人以及经过相当时间后被捕的犯人处以很不同的刑法的缘故”。④随着共和国的不断发展,罚金的性质和数额趋于理性化。从《十二表法》的定额罚金到《阿奎利亚法》规定的最高市价赔偿到裁判官法的实际损失赔偿,罗马法对私犯的报复性惩罚开始向损害赔偿过渡,对私犯包含刑事责任的制裁也逐渐被纯粹的民事责任所替代,从而也反映了私犯的性质日益单一化的趋势。
(一)《十二表法》反映了对私犯的制裁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
《十二表法》对私犯行为采用分别列举的方式。第八表“私犯”共计27条,除18、26、27条,其余各条内容均涉及私犯。此外,第七表第8、9条,第六表第9、10条,第十二表第2、3条也对私犯作了规定。《十二表法》所规定的私犯行为主要有:对人私犯、对物私犯、盗窃、诈欺。对物私犯(主要指侵害财产的行为)在《十二表法》中规定相对简约,除对折断奴隶一骨处150阿斯罚金外,只列举烧毁他人房屋和谷堆、在他人土地上放牧和砍伐他人树木等几种行为。欺诈行为也只限于恩主诈骗被保护人、证人作伪证等情形。而《十二表法》关于盗窃、对人私犯的规定,则直接成为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有关私犯类型的依据之一。
《十二表法》对“盗窃”的规定,反映在第八表第12-17条中。
对“盗窃”行为的制裁,体现三方面特点:
1.私力救济的方式依然保留,但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法律限定杀害行窃者的情形:只能对夜间行窃或虽然白天行窃、但用武器抗拒的行窃者实施杀害,其他情形下不得以杀害作为制裁方式。
2.对“现行盗窃”和“非现行盗窃”区分制裁,现行盗窃的惩罚比非现行盗窃重。“现行盗窃”虽不需要经过审判,但受害人还是要先将行窃者交给执法官,由执法官对窃贼进行鞭笞,然后正式将其交给受害人处理。这一过程显然还是强调公力制裁的必要性。而“非现行盗窃”,将被处以两倍于盗窃物价值的罚金。由此看来,处刑的轻重,以被害人的心理感受为主。“古代立法者无疑地认为,如果让被害的财产所有人自己处理,则他在盛怒之下所拟加的刑罚必将和盗窃在一个相当时期后发觉时,他所满意的刑罚,完全不同;法律刑罚的等级就是根据这个考虑而调整的。”⑤
3.对盗窃的制裁还因行窃者的身份而有所区别。奴隶行窃,处以笞刑后投岩摔死。未适婚人行窃,不论奴隶或自由人,处罚从轻,由长官处以笞刑后,责令其家长赔偿损失。
对人私犯(主要指对人的身体和人格侵害),在《十二表法》中也体现为几个基本特点:
1.侵害行为不仅包括对身体,还包括对名誉和尊严的诽谤和侮辱行为。如第八表第1条规定:“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然歌唱侮辱他人的歌词处死刑”。
2.仍然保留了有条件同态复仇的痕迹。如第八表第2条“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以同态复仇而毁伤其形体”。由于毕竟有了“和解先置”的限制性条件,此处的同态复仇已不同于最原始的复仇。它已从自发的私人复仇变为由社会加以控制的复仇。“社会在某些情况下已强迫受害人放弃同态复仇而接受协议的赔偿,如一定的赔偿金”。⑥尽管这时的赔偿从性质上看还多表现为放弃复仇权利的替代物。
3.对较轻的侵害规定固定数额的罚金。如折断自由人一骨的,处300阿斯的罚金,如被害者为奴隶,处150阿斯的罚金;对人施以其他强暴行为的,处25阿斯的罚金。
可见,作为迄今发现的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十二表法》显然已不再是习惯法的简单汇编,它已经蕴含着立法者的某些法律理念,虽然还非常粗糙,仍不失为法律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标志性作品。就其私犯规定而言,尽管还有原始的私人报复、同态复仇的痕迹,但其范围已大大缩小,其实施也受到了限制。自由赎罪金也开始由定额化的罚金所代替。当然,毕竟是人类早期的成文法,立法技术和法律内容都尚显幼稚,尤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其处罚的宽严失当、定额罚金不合理的缺陷日益突出。
(二)《阿奎利亚法》逐步丰富私犯制裁的内容,并趋于合理。
《阿奎利亚法》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关于私犯行为的专门立法。⑦该法共三章,其中第二章实施不久便被取消,⑧而第一章和第三章则是“对物私犯”的集中规定。关于《阿奎利亚法》的权威性和地位,乌尔比安认为,“《阿奎利亚法》取代了以前所有涉及对物不法损害的法律,无论其在《十二表法》中,抑或在其他法律中,这些法律至此无需引用。”⑨《阿奎利亚法》确定了对物私犯法律制度的基础和框架,其成熟的内容已经蕴含了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概念和思考方式。后世一般认为,大陆法系现代侵权行为法即源自于该法。
《阿奎利亚法》第一章针对的是杀死奴隶和家畜行为,规定:“凡不法杀害他人的男奴隶或他人的女奴隶或他人之四足牲畜者,须以被害物当年的最高价值向其所有主以金钱赔偿”;第三章则强调第一章所未涵盖的侵害行为,规定:“凡不法杀害他人的奴隶和牧群中的牲畜,或杀死、伤害其他动物以及毁灭损害其他物件的,行为仍应按加害之日起30日内被加害动物或物件的最高市价赔偿损失。”
比较《十二表法》,《阿奎利亚法》关于“对物私犯”已创设了较为一般化的制裁原则和体例,但在《阿奎利亚法》中,针对侵害财产的私犯行为的制裁,仍含有刑事制裁和民事责任的双重成分:1.对被告的否认,得请求双倍赔偿;⑩2.以一定时期内物的最高市价做赔偿额,与物的实际损失之间往往有差额,因而也具有惩罚性;(11)3.数人的共同行为,如果对其中一人提起诉讼,其余人不因此免责。“因为根据《阿奎利亚法》,一个行为人清偿,并不免除其他人的责任,这里涉及到罚金问题。”(12)所以,以大多数罗马法学家的观点,依据《阿奎利亚法》提起的诉讼仍是兼有赔偿损失和罚金性质的混合诉。(13)但是,《阿奎利亚法》有两项重要修改,较过去有进步:首先,将原来的定额赔偿,(14)改为按一定期间内的最高市价赔偿,而最高市价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动的,这一变化显然更为合理;其次,对于不确定的给付,按原来的规定不能执行扣押,现定为只要对不确定的给付进行估价,即可适用扣押程序。(15)
(三)优士丁尼《民法大全》进一步完善私犯制裁内容,并基本定型。
公元六世纪的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在总结吸收早期市民法和后来裁判官法有关私犯制裁的内容基础上,记载了四类私犯,即盗窃(furtum)、对人私犯(iniuria)、对物私犯(damnum iniuria datum)、抢劫(rapina)。(16)同时,对上述私犯规定了更为合理的罚金与损害赔偿并存的制裁原则。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采纳了裁判官法的规定,取消对现行盗窃处笞刑后交被害人处理,或罚为债务奴隶或予以杀戮的酷刑,改为处以四倍于盗窃物价值的罚金。对于盗窃之诉,无论是非现行的二倍还是现行的四倍之诉,都只涉及罚金之追究,为典型罚金之诉。所有人还享有对物本身的追究,即损害赔偿之诉,他可以通过请求返还之诉或要求给付之诉达到这一目的。(17)
关于“对人私犯”的制裁,《十二表法》规定严重伤害保留同态复仇,较轻伤害支付固定罚金。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沿袭裁判官法的规定,取消同态复仇,无论是较重的或较轻的侵害,一律改为罚金制裁。允许受害者自己对侵害进行估价,承审员则根据受害者的估价作出判决,抑或根据承审员自己的看法,就较小的金额作出判决。被估价为严重侵害的,一般主要考虑到侵害的行为、地点、及受害者的身份等因素。对严重侵害,由裁判官定一个最高限价,再由承审员在限额内确定具体罚金额,其数额通常与最高限额相差无几。(18)此时的罚金已基本接近赔偿金性质。
与《阿奎利亚法》所规定的“一定时期的最高市价”原则不同,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对侵害物的行为,规定必须估价损失。而损失包括受害人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如,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奴隶在接受遗产之前被杀,计算损失则不仅包括该奴隶的价值,还应将失去的遗产也计算在内;如果杀害了一对骡子中的一头,或四驾马车中的一马;或一对喜剧演员中的一个奴隶被杀,不仅要对被杀的估价,而且也要进一步计算那些活着的贬值了多少。(19)
此外,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还对裁判官所创设的一种私犯——抢劫(即以暴力攫取财产)加以明确化,定性为混合诉。受害人可提起窃物价值四倍的罚金诉,但四倍并非全然罚金,对物的追究在四倍之内。所以,不论抢劫是否是现行,罚金都是三倍。
通过对相关文本的分析,不难看出,在罗马中后期,随着裁判官法的发展,法学家解释活动的兴旺发达以及立法技术的进步,法律对私犯制裁趋于理性化。早期的人身制裁内容已消除,罚金逐渐更多地考虑到赔偿性,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赔偿金过渡。尤其是考虑损失的大小、行为的情节轻重等因素来计算赔偿的规定,已包含了近代侵权行为法损害赔偿规则的基本理念。(20)
二、罗马裁判官的司法实践是促进罗马侵权法发展的主要动力
罗马法的发展离不开罗马裁判官的司法实践活动。在古罗马历史上,裁判官有两类:即城市裁判官(praetor urbanus)和外事裁判官(praetor pereginus)。城市裁判官的职责就是在市民间执掌私法,外事裁判官则根据诚信标准处理罗马市民与外来人及外来人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裁判官并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利,他们在其职责范围内通过发布告示的形式,创造新的诉讼形式或将旧的诉讼形式扩展适用于新的事实。从形式上看,只是创设新的救济手段,而实质上,“告示”却成为罗马法重要的法律渊源——裁判官法(ius praetorium)的基本成分。优士丁尼《学说汇纂》记载了法学家们对城市裁判官告示的评论材料,我们在那里可以了解城市裁判官告示的许多内容,然而,遗憾的是,外事裁判官的告示却没有留下任何材料,“这一定是因为在公元 212年普遍授予市民权后,这种告示不再具有什么实践意义。”(21)
(一)裁判官法创设的私犯
除了罗马市民法上的私犯以外,裁判官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对各种侵害人身和财产的行为创设新的救济手段,形成裁判官法上的私犯。在众多私犯中,除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所记载的抢劫之外,较为重要的还有欺诈、胁迫、诈欺债权人等。
抢劫(rapina),即以暴力手段非法攫取他人财物。早期罗马市民法中并无盗窃和抢劫之分。公元前77年,裁判官路库路斯创设抢劫诉,以区别于盗窃诉,规定凡结队持械抢劫者,无论现行与否,一律按四倍于所劫物价值处罚金。其后裁判官进一步扩大抢劫诉适用范围,不再以结队持械为必要条件,规定只要使用暴力夺取他人财物,即构成抢劫。罗马帝政时期,抢劫诉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
胁迫(metus),即用不法威胁手段迫使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十二表法》并无胁迫之规定,罗马早期法律关系的成立注重形式要件,往往有官吏和证人在场,胁迫情形一般难以发生。其后,随着非要式行为的发展及社会矛盾的日渐尖锐等,胁迫行为不断发生。共和国后期,裁判官创设了胁迫诉,将胁迫正式列入私犯。胁迫诉的特点是被告如满足原告返还之诉的请求,则可以免予处罚,否则,裁判官得判处胁迫人支付四倍的罚金。胁迫人为避免重罚,一般都能满足被害人的要求。此后,裁判官又进一步创设了“胁迫抗辩”和“恢复原状之申请”,即被害人可用胁迫抗辩拒绝履行因胁迫而成立的法律行为,并提起请求恢复原状,免除因胁迫而负担的义务。(22)
诈欺(dolus malus),即以欺骗手段使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罗马市民法上也未规定诈欺行为。公元前66年,裁判官盖路斯创设诈欺诉,诈欺此后被列入私犯范畴。诈欺诉的特点是必须在无其他救济权时才能提起,显然是一种辅助诉或从诉。裁判官法对诈欺的制裁重于胁迫,虽然受害人只能获得实际损失之赔偿,但裁判官要对诈欺人予以“不名誉”之宣告。此后,裁判官又创设了“诈欺抗辩”和“基于诈欺恢复原状之申请”,其作用与“胁迫抗辩”和“因胁迫而请求恢复原状”相同。
(二)裁判官法对市民法上私犯的发展
罗马裁判官通过司法实践,对侵害行为一方面创设新的诉权,形成裁判官法上的私犯,另一方面,通过扩用诉讼(actio utilis)(23)和事实诉讼(actio in factum),(24)丰富市民法上私犯的内容。
就盗窃行为而言,裁判官法除取消对现行盗窃的人身制裁,而一律规定四倍罚金诉权(actio poenalis)外,还创设了四种特别诉权,即拒绝搜索财物之诉(actio furti prohibiti)、(25)查获盗窃之诉(actio furti concepti)、(26)藏匿赃物之诉(actio furti oblat)、(27)拒绝交付赃物之诉(actio furti non exhibiti)。(28)为简化诉讼形式,该四种诉权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不再沿用,所有在明知的情况下收受和藏匿被盗物的人,都以非现行盗窃之诉承担责任。(29)
对盗窃除可提起罚金诉外,还可就损害赔偿提起诉讼(actio rei persecutoria)。裁判官因此创设了返还原物之诉、交出物件之诉、请求返还盗窃物诉等。
《阿奎利亚法》系统规定了“对物私犯”的情形和制裁,但由于其承担责任的一般要件过于严格,(30)不能充分保障受害人得到补偿,裁判官在实践中对此作了重大改进:
1.当损害只是以间接的方式,裁判官允许提起“扩用诉讼”。如让一奴隶饿死;(31)用力推某人致其撞坏他人财物;(32)使骡子负载过重以致骡子身体的某个部位受到伤害。(33)
2.扩大原告的范围。可提起侵权诉讼的不再限于受损物的所有人,善意占有人、质权人、承租人等,均可提起类似于阿奎利亚诉讼的事实诉讼。(34)
3.《阿奎利亚法》原只适用于对奴隶和动产的损害,裁判官将其扩充使用于房子等不动产。(35)
4.对《阿奎利亚法》中侵害的基本要件“非法” (iniuria)进行了个别化的分析和适用,着重强调行为人的不法和主观上的过错,初步奠定了过错为损害的归责原则。
5.通过告示,规定了对不法侵害的损害投偿之诉,(36)即对奴隶实施的侵害物的行为,允许其主人要么承受讼额估价,要么交出加害奴隶而使原告(主人)获得解脱。
(三)裁判官司法实践中创设的准私犯
在古罗马的司法实践中,裁判官除了扩充对私犯行为的救济手段或创设一些私犯诉讼外,还对一些类似私犯而在早期法中没有相应规定的违法行为,通过事实诉讼对受害人给与救济,此类违法行为被称为准私犯。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保留了四类产生于准私犯的债,即:1.承审员的渎职行为致人损害,对此视其过错程度追究责任。如为故意,依照《十二表法》有关规定。若为过失,例如适用法律不当,应罚2倍的误判为4倍,令其赔偿当事人的实际损失。2.投掷物和倾倒物致人损害,由房屋居住者承担双倍赔偿责任。如数人共同居住的,承担连带责任。3.在经常通行之处堆置物或悬挂物可能致人损害的行为,由房屋居住者向告发者承担 10个金币罚金的责任。(37)4.船主、旅馆(或货栈)所有人、马厩商对其奴隶或雇员实施的盗窃或侵害其承担责任。(38)
上述准私犯行为的责任,已无法从裁判官的告示中考察其归责要件。按照罗马时期法学家的解释,认为准私犯通常是替代责任——对他人的过失承担责任,(39)但后世多数罗马法学家认为准私犯为无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
三、过失责任原则的初步确立奠定了现代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的基础
正如我们已知的事实,古代社会早期,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是通过家族间的血亲复仇和后来的同态复仇来实现的。由于存在着个人对家族的强烈依附性,个人受到侵害,被认为是整个家族受到威胁,家族就必须共同对付这些威胁本家族生存和发展的行为。由家族集体对这些侵害和威胁行为实施报复,也就成为一个家族繁衍、生存的必要保障。与之相应,家族也必须集体对其成员所引起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不将侵害人交出,便负有集体保护他的义务。古代社会侵权行为法的这一特征被学者称之为古代社会的共同责任。(40)这种受害人对侵害的复仇本能和需求,以及不问侵害人的心理状态而一律将其责任加在整个家族身上的共同责任观念,导致古代社会对侵权行为实行单一的结果责任(加害责任)归责原则,即只按照侵害结果来决定责任的承担,有损害便有责任,而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即便是到了可以用赎罪金替代复仇的年代,仍然是以损害结果的大小和形态来决定赎罪金的多少。区分过错程度也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已经完全忽视了行为人行为的可责难性。
一切古代社会的法律都采用结果(加害)责任原则,早期古代罗马法也不例外。早期法律之所以将客观损害结果作为承担责任的最主要因素,而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早期社会人们的报复愿望使然。对客观损害结果,报复一方面满足了被害人及家族的心理感情,一方面也起到预防将来损害发展的作用。而实践中这种报复要求又得到法律的承认,这就使纯粹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规则根本无暇顾及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其二,在文明程度极为低下的人类早期,人们所能意识到的也只是客观上的损害,无法认识到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更无法证明主观因素。其三,其时原始的平等观念尚存,加害被视为是破坏平等和平,必须予以赔偿,而不论其主观心理状态如何,此即损害惩罚相应。(41)《十二表法》作为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标志,其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仍是以加害责任为主,反映了同态复仇的残余。如第八表第5条规定:“对他人的偶然侵害,应付赔偿之责。”第6条:“牲畜致人损害,由所有人负赔偿责任,或将该牲畜交与被害人”。这些规定表明,只要造成损害结果,则不论过失与否,都要予以赔偿。但同时,个别条款对损害则区别行为人过错程度,给予不同的制裁。如第八表第24条:“杀人者处死刑;过失致人于死的,应以公羊一只祭神,以代本人。”此类条款说明,立法者已经开始考虑到行为人主观状态对致害行为及责任承担方面的影响。尽管立法者此时不能对过失(culpa)形成一个系统化概念,(42)而仅仅只是通过个别条款表达一种朦胧的认识,但这已是过失责任原则在罗马法的最早萌芽。
《阿奎利亚法》在古代罗马侵权行为法历史上则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与发展,不仅在于它尝试着设计了对物损害的一般化条款,规定了一般要件,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了“违法”(iniuria)性概念,首次明确规定了私犯行为成立的主观标准,即过失责任原则。
“iniuria”一词在《十二表法》中已出现,但当时的意义仅限于“对人私犯”,即“侵辱”。在《阿奎利亚法》中,“iniuria”指“违法”、“不法”,该法规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法,那么,行为人须对此引起的损害负责”。所谓不法,就是“没有权利” (nonjure)。(43)但此时,“iniuria”并不包含过错的含义。后来,通过罗马法学家对该法的解释,认为“iniuria datum”指行为人在实施损害时具有过失 (culpa)或故意(dolus)。因此学者普遍认为,侵权行为法上过失责任原则是罗马法学家在《阿奎利亚法》基础上的杰出贡献。经过法学家几个世纪的不断探讨,过错责任最终在优士丁尼《民法大全》中得到了较为一般和抽象的概念。
关于如何理解“不法”(iniuria),乌尔比安认为,“不可将‘不法’理解成伤害诉讼中一些侮辱行为,而要将其理解为某些不合法的东西。……所以,在此将不法理解为一种因过错所致的损害,即使行为人并未故意去损害。”(44)
何谓“过失”?罗马法学家在诠释过失的标准上,最初采用客观标准。保罗认为,过失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能够预见预防却没有预见和预防,或只是在危险已不可避免时方作出警告。(45)因此,过失是一种客观性的标准,即善良家父(bonus paterfamilias)的标准,(46)如果一个人没有遵守在特定情况下一个具有谨慎性的家父(diligent paterfamilias)所遵循的行为标准,即为过失。此时,并不考虑行为人个体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也不对主观心理状态进行探究,责任是建立在一个善良家父可预见的能力基础上。只要在行为时没有达到该标准,便具有过失。然而,客观过失标准仍然含有某种个人行为的可责难性,即行为人没有遵守人们已经事先确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标准。(47)
当然,因客观情况不同,工作性质不同,善良家父标准所要求达到的注意程度也不同。因此,罗马法学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实例,以一种比较明确的方式解释过失本身内涵的多种多样。他们认为,行为人在行为时缺乏体力或某种技能意味着有过失:如果骡夫因为力弱而未能控制住骡子,使骡子踏死他人奴隶,则骡夫具有过失;(48)如果医生给奴隶做手术时因欠缺技能而导致其死亡,则医生有过失。(49)此外,无经验也被视为过失:如果骡夫是没有经验而不能驾驭骡子,结果踏死他人奴隶,那么他即因有过失而负责;(50)医生虽然手术良好,但因欠缺经验耽误进一步治疗,则被视为有过失而负责任。(51)对一些漫不经心的行为,同样要负责:如某人超量运载,货物抛出而致奴隶死亡,或背着货打滑而砸死他人奴隶,他须对此负责,因为行为人对超量运载货打滑地段毫不经心。(52)
在对具体实例的过失进行个别分析的同时,罗马法学家已经开始不断总结过失责任的一般化意义。如意外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只要行为人无任何过错;(53)正当防卫不承担责任,因为自然理性允许针对危险予以防卫。(54)但防卫过当,如可将其捕获,却宁愿将其杀死,则多数人认为当视其为不法行为;(55)乌尔比安还认为,在《阿奎利亚法》中最轻微的过失也予考虑。(56)此外,受害人的疏忽大意引起的损害,加害人没有过失的,则不承担责任。如,人们在投标枪时砸死一奴隶,需承担责任,但如果是在练习场上掷标枪时这个奴隶由此经过,则行为人不对此负责,他被认为无任何过失,相反地受害人不应此时从练习场走过。(57)
在对过失采用客观标准的同时,法学家也逐渐意识到某些情况下行为主观状态对责任分配的意义,从而提出责任能力问题,认为精神病人及儿童造成损害,不承担责任。(58)特别是罗马法发展到后古典时期,过失的标准已经开始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更注意对侵害人过失的具体分析,只有在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可责难性时,才令其承担责任。到了6世纪,法典编纂者们确立了新的过失标准:一个人本可以以自己的勤勉、注意来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但是由于疏忽或者故意而没有避免,这样的主观心理状态就被认为有过失。(59)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引用法学家彭波尼(Pomponius)的观点,认为虽然某人在其耕地上发现了他人的家畜,但他只能像发现了自己的家畜那样予以驱赶,这样做他便可以对自己的损失获得救济。(60)显而易见,将过失的概念与人们的勤勉义务、注意义务联系在一起,必然对人们提出勤勉、注意的要求,由此使得人们尽量避免损害的发生。
现代学者多认为,除过失责任外,罗马法上也确实存在无过失责任的情形,主要反映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准私犯行为及动物致人损害的有关规定中。如对那些临街的高层建筑上掉下来的物品造成行人损害的行为,只是简单的让住在房屋里的人承担责任,而不考虑其它因素。(61)罗马法学家对此问题的解释主要出于利益衡量方面的考虑,因为保护行人的安全利益更为重要。又如,旅馆的雇员对旅客造成损害的时候,旅馆的主人要承担责任,(62)为了更多地保护旅客的利益,这样规定也是十分合理的。通过对这些情形的分析可知,罗马法上的无过失责任,是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而要求责任人负担一种更为严格的责任,每一种类型的无过失责任都不是作为一般原则而存在的。可以得出结论:在罗马法上,过失责任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只要存在过错并对受害人造成损害,行为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在它之外的确还存在一些客观责任或无过失责任的情形,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例外是典型化的,它们的存在都是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是对一般原则的补充,并不足以推翻一般原则。
然而,我们不能用现代完善的侵权过失责任理论来考量反映在古代罗马法中的过失责任原则,当时的过失责任理论还非常粗糙。比如,罗马法学家并未严格区分过失和因果关系两个概念,甚至二者混淆:在直接的暴力侵害行为中,其行为的“违法性”既包含了因果关系因素又涉及故意过失因素,判断行为与损害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还得视行为人是否有过失。另外,关于过失的抽象化、一般化程度也很有限,大多还是通过对具体事例的个别分析进行阐述。但是,自《阿奎利亚法》确立过失责任原则以来,该原则一直伴随着侵权法的发展历程,为现代两大法系国家所推崇。正如有学者指出,“罗马法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是其‘iniuria’概念的提出。这种概念后来被划分为两种因素,即侵害人注意理由的欠缺和行为的可责难性。这两种观念最终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今天,在罗马法提出该概念以后的两千年以来,人们可以看到,罗马法的此种观念仍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西方世界的各种法律制度中,并且其重要性和它所产生的困难一样存在。”(63)
四、罗马私犯法对近现代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的影响
正如本文开篇所言,由于古代法民刑不分的性质,罗马私犯是犯罪行为和侵权行为的共存体。罗马法对私犯行为的制裁,也是惩罚性手段和赔偿性方式交替使用,相伴发展。过失责任在更多的场合下还处于个别、具体的分析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一般化理论。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日耳曼“蛮族”法主导西欧,虽然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罗马法仍有生气,但作为一种法律体系,从5世纪到10世纪,罗马法在欧洲的发展总体上处于“黑暗时期”:罗马法的过失责任重新被野蛮和粗陋的结果责任所替代,赔偿标准也不再以实际损失计算。然而尽管如此,随着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随着西欧各国对罗马法文本注释与评论的兴起,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发展,罗马私犯法重新获得其强大生命力,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基础,对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近代侵权行为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罗马私犯法在侵权行为法发展史上的承上启下作用。
总体上说,罗马私犯法对近现代侵权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私犯的债法属性影响着侵权行为在近代民法典中的属性和地位。
罗马私法上的私犯和准私犯,与契约、准契约同为债的发生原因,正如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所言:债要么出于契约的;要么是出于准契约的;要么是出于非行的;要么是出于准非行的;(64)罗马法上私犯的这一特性,完全被18世纪开始的欧洲法典化运动中的各国民法典所继受。各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基本上是将侵权行为法放在债法之中,作为债的组成部分或发生原因。如法国民法典,将侵权行为置于“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中第二节,以“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标题出现,与该章第一节“准契约”并存。在此,侵权行为显然是作为债法的一个发生原因存在的。德国民法典实行五编制,侵权行为位于第二编债法之下的第七章各种债的关系中,以“侵权行为”作为该章的最后一节。日本民法典则将不法行为(侵权行为)之债与契约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并列起来,将有关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同合同法律关系等同视为债法内容。总之,罗马私犯法的债法属性,决定了大陆法系各国侵权行为法的属性和在民法典中定位,直到现代,尽管理论上认为侵权行为与合同的个性远大于其共性,尤其是随着侵权行为法的迅速发展,债法已无法容纳其全部内容,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各国立法者大都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立法实践并未与理论同步。
第二,罗马私犯法奠定了大陆法系侵权行为类型二分法模式,并开启了侵权行为一般化的历史进程。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所规定的四种私犯,随着法律的发展,其中的“盗窃”和“抢劫”,逐步脱离侵权行为法,纳入刑法的调控范围。传统观点认为,罗马法上的侵权行为,主要是对人私犯和对物私犯。这些私犯,都是行为人自己实施的侵权行为,责任的承担均以过失为必要条件。关于准私犯的产生,后世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私犯类型已经固定,容不下新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65)然而,我们考察《法学阶梯》记载的四类私犯和四类准私犯行为发现,后者在承担责任时都几乎忽略了行为人的过错。这种分类是否是罗马人有意为之?现代人完全可以如此推测:尽管由于当时的过失观念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无法解释不同的行为为何会设置同样的法律后果,但罗马人已经意识到二者的区别,因而以“准私犯”这样一个新的范畴来与“私犯”相区别。无论如何,后世是根据私犯和准私犯类型,划分现代侵权法中的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私犯被概括为现代意义上的一般侵权行为,准私犯则对应特殊侵权行为类型。所以说,罗马法私犯和准私犯的划分,为大陆法系侵权行为二分法模式奠定了基础,同时开启了侵权行为一般化的历史进程。
法国民法典严格遵循罗马私犯法体例,专设“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一章。在短短的五条内容中,第1382条和1383条规定的便是一般侵权行为,也就是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严格意义上说,是法国民法典正式确立了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而该法的第1384条、1385条和1386条则是准侵权行为的内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1、2款、第826条采用各种诉因类型化的方法,(66)将一般侵权行为概括为对权利的侵犯、违反保护性规定和违反善良风俗三类。此外,该法典还列举了其他特殊侵权行为,与三种诉因的一般侵权行为共同构成德国侵权行为法的基础。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又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产生深远影响。各国对侵权行为的分类和立法模式,分别效仿法国法或德国法而未有超越。
第三,罗马私犯法的过失责任为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对罗马过失责任的继受方面,法国民法典最为彻底。该法典的第1382条确立了一般侵权行为的过失责任原则,该条运用概括性方法,并未对保护的利益范围和法律关系做出具体规定,给侵权行为法的发展留有极大空间。在罗马法中,过错和违法性两个概念基本等同,不做严格区分。法国法完全沿袭罗马法的规定,采纳过错吸收违法的立法方式。同时,法国民法典的过失责任,继承了罗马法的“善良家父”的客观性判断标准,并为法国法系国家民法典所效仿。
德国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虽然就有关归责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议,但法典起草人最终采纳了过失责任原则。只是为避免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没有采纳单一的过失责任原则,(67)而是将侵权诉因类型化,以此来限制侵权责任的范围。
自德国民法典颁布的一百多年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内容的日益复杂化,侵权行为法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一般侵权行为不断扩张到侵害各种人身、财产权益类型,而且各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也大量涌现;归责原则出现多样化,过失责任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归责原则;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性呼声也日益高涨,已经逐渐从债法中分离。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从立法上尝试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分离。尽管有如此迅速的发展,但我们仍然无法否认罗马侵权行为法即私犯法的现代意义。比如罗马法中的一些案例经过若干很小的变化就能够和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很近似;罗马法在设置准私犯责任分配时所体现的“利益衡量”理念,也是现代侵权行为法无过失责任原则核心内容之一。由于我国侵权行为法从整体上主要是继承、借鉴和移植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的传统及制度,因此,罗马侵权行为法也必将在归责原则等方面对中国当代侵权行为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由于古代法律民刑不分,罗马私犯包括现代法中的一些刑事犯罪行为,也包括侵权行为。
②目前国内无论是法律史学界抑或民商法学界,均普遍认为古罗马私犯制度是大陆法系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基础。有关的侵权行为法论著中对此有简短介绍,但对这一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入研究还比较欠缺。
③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5页。
④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3页。
⑤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4页。
⑥米健:《论侵权行为规则原则的两元制定式》,载《月当民商法研究—侵权行为法制立法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⑦原是一项平民会议决议,由平民保民官阿奎利向平民大会提出。关于其确切颁布年代已无从考证,学界经推测,一般认为是公元前 287年左右。
⑧D.9,2,27,4;乌尔比安在其《论告示》第18编中提到《阿奎利亚法》第二章以废弃,而乌尔比安生活在公元2、3世纪之交,可见该法第二章实施时间不长。
⑨D.9,2,1pr.
⑩D.9,2,1.
(11)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62页。
(12)D.9,11,2.
(13)I.4,3,9;l.4,6,19.
(14)如《十二表法》规定砍伐他人树木的一律赔偿25阿斯。
(15)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61页。
(16)本文采用了周枬教授《罗马法原论》中的译文。由徐国栋教授翻译的《法学阶梯》将“iniuria”译为“侵辱”,“damnum iniuria datum”,译为“损害”。黄风教授的《罗马法词典》同此译。参见优士丁尼著,徐国栋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第82页。
(17)I.4,1,19.
(18)G.3,24.
(19)I.4,3,10;D.9,22.
(20)C1,17,21.
(21)[英]巴里·尼古拉斯著,黄风译:《罗马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22)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56页。
(23)将适用于特定情况或关系的法定诉讼形式扩展应用于某些现实的情况或关系的诉讼;这种现实的情况或关系反映着受法定诉权保护的情况或关系的发展和衍生,由于法律来不及为其规定专门的司法救济手段,只好由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以变通的做法参照现有的法定诉讼模式提供司法保护。见黄风著:《罗马法词典》第19页,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4)当某一新的关系不涉及市民法上所调整的权利,并且关系人不能借助法定诉讼程序解决就该关系产生的争议时,裁判官允许针对创造上述关系的事实提起诉讼;在此种诉讼中,裁判官所维护的不是法律明确承认的权利,而是事实上存在的、新的公平关系。见黄风著:《罗马法词典》第11页,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5)受害人怀疑被窃物已被隐藏,它可要求进行搜查,如钩搜查遭到拒绝,可提起四倍罚金之诉。
(26)邀证人在场搜出赃物时,对行为人处以三倍于赃物价值的罚金。
(27)不知情的被搜出有赃物的善意者,在被罚了三倍于赃物价值的罚金后,可依此诉向栽赃者追回所罚金额。
(28)是诸如确认某人盗窃其物,而对方否认时,可提起相当于窃物四倍价值罚金。
(29)I.4,1,4.
(30)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直接使用暴力,有物理、身体上的接触;必须为不法行为所致损害;必须导致原告受到损失:损害物须为原告财产。
(31)D.9,2,9,2.
(32)D.9,2,7,3.
(33)D.9,2,27,23.
(34)D.9,2,11,8;D.9,2,12;D.9,2,17;D.9,2,27,14.
(35)D.9,2,27,31.
(36)I.4,8,4.
(37)I.4,5,1.
(38)I.4,5,3.
(39)I.4,5,1.
(40)张民安著:《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41)米健:《论侵权行为规则原则的两元制定式》,载《月当民商法研究—侵权行为法制立法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42)拉丁文culpa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非法行为本身,相对应的中文术语是“过错”;另一层含义是指判定某人(特别是债务人)承担责任的主观标准,相对应的中文术语是“过失”。从前一种含义讲,“culpa(过错)”也包括处于故意而实施的非法行为;从后一种含义上讲,“culpa(过失)”是一种不同于故意的归责标准,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疏忽,即:勤谨注意的缺乏。参见黄风编著:《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43)米健:《论侵权行为规则原则的两元制定式》,载《月当民商法研究—侵权行为法制立法趋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44)D.9,2,5,1.
(45)D.9,2,31.
(46)即一般人的注意标准。
(47)S.Schipani,Responsabilita ex Lege Aquilia,p131.转引自张明安著:《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48)D.9,2,8,1;I.4,3,8.
(49)D.9,2,8.
(50)D.9,2,8,1;I.4,3,8.
(51)D.9,2,8;I.4,3,7.
(52)D.9,2,7.
(53)I.4,3,3.
(54)D.9,2,4.
(55)D.9,2,5.
(56)D.9,2,44
(57)D.9,2,9,4;I.4,3,4.
(58)D.9,2,5,2.
(59)张民安著:《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60)I.9,2,39,1.
(61)I.4,5,1.
(62)I.4,5,3.
(63)F.H.Lawson B.S.Markesinis,Tortious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 Harm in the Common Law and The Civi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9.
(64)I.3,13,12.
(65)周枬著:《罗马法原论》(下),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03页。
(66)克雷斯蒂安·冯·巴尔著,张新宝译,《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67)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规则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