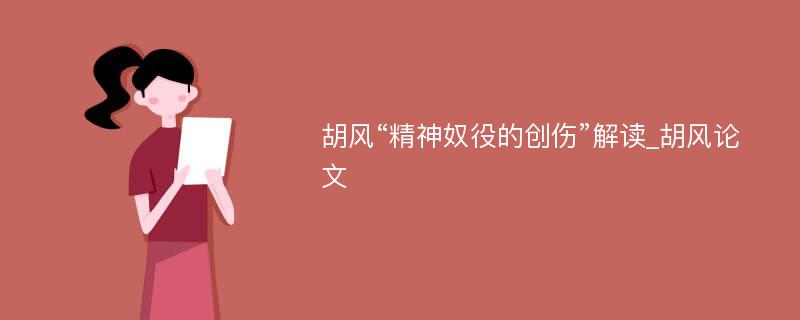
析胡风“精神奴役的创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伤论文,精神论文,胡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1)06-0033-05
20世纪40年代,在《希望》杂志发刊词《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中,胡风提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他指出:“他们(人民,笔者注)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1]189随后,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对“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精神奴役的创伤”从此成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标志性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胡风文艺理论的批评者和研究者对这个命题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这一命题内在学理的爬梳方面,似乎还有较大的空间,笔者试图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敬待大家批评指正。
一、厨川白村:作为意象之“源”
在追溯“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观点的源流时,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显然是绕不过去的,以往学者对此的关注和研究也是很翔实和丰富的,如王向远先生在其专著《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对胡风“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观点与厨川白村关于“精神底伤害”的观点之间的联系与同异就有条分缕析的梳理,似不需再度赘言。不过笔者认为,在厨川白村和胡风文艺观点的深层次的联结上,似乎还有着向前探索的可能。
厨川白村认为,文艺创作,缘起于创造生活的欲求和强制压抑之力这两种力的冲突。创造生活欲求的这种生命力的显现,“是超绝了利害的念头,离了善恶邪正的估价,脱却道德的批评和因袭的束缚而带着一意只要飞跃和突进的倾向”。[2]10而强制压抑之力,则既指外部社会的机械法则和因袭的强力,同时还有主体内部和家族、社会、国家等调和的欲望。厨川白村借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创伤”这一概念,弗洛伊德认为,性欲遭到外界压抑而产生创伤,从而使病人产生歇斯底里的精神状况。治疗这种创伤就是用催眠术或问答法,使病人自由地说出苦闷的原因,从而去掉这种压抑,使精神疾病得以治愈。厨川白村将创伤概念移用到自己的文学批评中,他认为生命力的突进跳跃和强制压抑之力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的伤害,成为人间痛苦的根由。而以象征的方式,从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强制压抑中解放出来,以绝对自由作纯粹创造的,就是文艺。因此,文艺不是再现和摹写,而是表现和创造。
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到康德、席勒的审美理论,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甚至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这些时代相异、观点错杂的西方文艺理论作为奇特的混合体出现在《苦闷的象征》中。在厨川白村笔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观点更多的是围绕“苦闷的象征”这条逻辑红线,进行“六经注我”式的组合排列。在论及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时,厨川白村将其作为被压抑的苦闷的自由表现形式,并没有顾及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涉及到的人神分裂以及寻求和解的主题,以及这种净化所含有的“涤罪”之意。论及康德、席勒的审美理论,厨川白村更多地将其作为创造力自由表现的一块“飞地”,而没有涉及到康德、席勒理论中审美作为解决纯粹理性(知性)和实践理性(道德)之间“天堑”的“拱顶石”功能,在感性形象中象征和暗示着实践理性中的自由意志的实现。厨川白村借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精神创伤的潜隐、发生和治疗过程,却将弗洛伊德理论中所含的现代性主题——身体欲望对理性和宗教的反抗抹去了。
厨川白村笔下创造性的生命欲求,一方面作为脱却道德的批评和因袭的束缚的自由;另一方面又作为评价一切制度和道德的尺度。而这种自由,更多地体现为以个人为本位的主体意志的表达,表征为个体对群体、传统的怀疑、反省、否定和反抗。在阿格尼丝·赫勒的《现代性理论》著作中,这种个体对群体、对传统的怀疑、反省、否定和反抗,被称为现代性的动力,称为“现代社会格局的助产士”[3]。赫勒认为,在欧洲,现代性动力首先出现在雅典,主要代表是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在他们的思想视野里,传统受到了理性的拷问。在理性的辩证法中,每一种经过否定后的肯定,又被新的否定所席卷,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由人格得到了彰显。而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奥古斯丁、阿奎那、马丁路德、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谢林、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等等,在哲学、神学、美学、社会学等多种层面上,无不推进着这场反思、否定、建构、解构的持续的思想运动。《苦闷的象征》中,厨川白村也认为:“一面又有反抗因袭和权威,贵重自我和个性的近代底精神步步的占了优势,于是人的自由创造的力就被承认了。”[2]26而在中国,对于这种从传统社会的信仰和伦理体系中脱出、进行自由创造的主体的渴望,在鲁迅对“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精神界的战士”的呼唤中,在陈独秀对自由、平等、独立的“伦理的觉悟”的提倡中,均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胡风,在《文学上的五四——为五四纪念写》一文中,深情地礼赞了这种觉醒了的“人”,“那里面也当然是为或悲或喜或哭或笑的人,但他们的或悲或喜或哭或笑却同时宣告了那个被铸成了的命运的从内部产生的破裂。”[4]因此,正是基于对脱却“古国”传统思想道德体系的自由人格的渴望这个“期待视野”,使得胡风对《苦闷的象征》有着深度的认同和接受。
从胡风对“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个概念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苦闷的象征》的借鉴和化用。例如在概念的借鉴上,厨川白村认为“精神的伤害”,在沉积的潜在的状态,则是人“就和畜生同列,即使将这样的东西聚集了几千万,文化生活也不会成立的”。[2]13胡风认为“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潜在阶段是一种禁锢麻痹甚至闷死千千万万生灵的力量。例如在对作家的主观精神的论述上,厨川白村认为,在经验着苦闷、参加着战斗的人,“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而同时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凯的欢乐和赞美里的事。”[2]15胡风则认为作家“对于昨天性的诸因素,他痛恨,他鞭打,他痛哭,他甚至不惜用流血的手段;对于明天性的诸因素,他热爱,他赞颂,他歌唱,他甚至沉醉地愿意为它们死去”。[1]561例如对文艺的作用上,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所给予的,不是知识,而是唤起作用。胡风则认为,革命文艺,“就是要从自己的道路上分担唤醒人、影响人、甚至改造人,把人吸引到这个大斗争里面去的意识斗争的任务”。[1]546例如对作家的角色的比喻上,厨川白村认为诗人(作家)在暗示更高更大生活的可能上是预言者,胡风也认为艺术家通过创造某一社会群里刚刚萌芽的典型,从而成为“预言者”。
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胡风对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进行诚恳的认同和借鉴时,又有着批判的保留。在《略谈我与外国文学》一文中,胡风认为厨川白村的思想有着“唯心”的成分。所谓“唯心”,并不是否认厨川白村的理论逻辑本身,而是批判这个理论仅停留在“凌空高蹈”的思辨层面而“不及物”,缺乏翔实、丰富、感性的社会实践内容和“血肉实感”。胡风的批评模式,显然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等对黑格尔理论的批评“路径”。而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概念,将厨川白村的个人的解放欲求与传统思想道德体系的对抗置换为人民创造历史的解放欲求与“各式各样的安命意识”为内容的封建意识的对抗,在这个命题转换中,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成为胡风“精神奴役的创伤”命题的逻辑机理。
二、逻辑机理与美学形态
为回应香港“才子派”的批评,阐发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表作《费尔巴哈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胡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旁征博引和深入阐释,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风范。
在“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概念的阐发中,胡风认为,在封建主义支配下生活的现实具体的人民,一方面担负着劳动的重负,从而产生创造历史的解放需求,然而这种担负,又是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这种安命精神又将解放需求压抑在“自在”的状态。而这造成了人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创伤“激荡着、纠结着、相生相克着,形成了一片浩漫的大洋”。[1]554
其实,胡风的这个论述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辩证法”理论。黑格尔认为,通过生死的斗争产生了主人和奴隶,主人通过支配奴隶、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以征服的姿态获得自我确证。而奴隶则由于感受过死亡的恐惧,对绝对主人的恐惧,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以主人的意识为自己的意识。但在劳动的陶冶中,奴隶通过对自然的征服而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感受到自己的尊严,从而产生人格独立和平等自由意识的萌芽,劳动是奴隶获得精神解放的历史原动力。马克思高度赞扬了黑格尔的这一成就,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120同时,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和人类历史的同步性,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88
那么,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就是人民在劳动的陶冶中产生的解放欲求与对主人的恐惧而产生的安命态度这两者进行殊死搏斗的战场。在当下的中国,这种创伤在一方面,体现为“封建主义旧中国全部存在的力点”,承受着“封建主义旧中国的万钧重量”;另一方面,它是“能够冲出、确实冲出了波涛汹涌的反封建的汪洋大海的一个源头”,[1]556一条精神解放的生路。总之,在精神奴役的创伤上,凝聚了“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1]506。这个主观的思想要求和客观的历史内容,既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又是持续不断的革命实践的过程。
人的精神解放的欲求,既是具体革命实践的开端,同时又是革命实践的精神量度。从历史因袭的重负,到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这个巨大而急剧的转变过程,更集中地体现为创作对象(人民)的“心理状态”或“精神斗争”,而创作对象的形体容貌、外部社会的客观物景,只是表现这种“心理状态”或“精神斗争”的机缘。正如胡风所说,“阿Q的癞疮疤,只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而且这个产物只有活在阿Q忌讳‘光’‘亮’‘烛’‘灯’的心理状态里面,由这引起了和他的周围社会的交涉即精神斗争(且慢见笑吧,这也正是堂皇的精神斗争!)以后,才成为客观对象的真实,也就是艺术的真实的。”[1]556这就要求作家们突入创作对象的精神世界,“一下鞭子一个抽搐的对于过去的袭击,一个步子一印血痕的向着未来的突进”;[1]511而不是“守株待兔地仅仅望着‘细小的政治变动’,甚至不过是权变的政治战术的应付,美其名为反映政治但其实反而是放弃政治所要求的艰巨任务,不过偷懒地向政治应应景,向政治点点卯而已的。”[1]490
胡风认为,要做到深切反映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古希腊文学的单纯和朴素就不够了。荷马史诗中那些静穆和悦、神灵庇佑的英雄,他们自身的活动与家庭、国家和宗教信仰的普遍伦理生活之间和谐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具有内在完满性的封闭自足的世界。正因如此,才成为高不可及的范本,一个不复再来的童年的梦幻,它与现在的,人的日常生活之间具有绝对的和不可跨越的界限。而现在“正处在相砍之世”的我们,作为阶级的、实践的主体,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奴隶,在神退出历史舞台、不再给予我们庇佑的时代,每一次扬帆启程,都是一次与命运的不确定的赌博。同时,作为解放欲求与安命精神之间的斗争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存在,恰恰体现着主人公自己与现实世界的不和谐与不妥协的关系。正如卢卡奇所说,现实主义小说,作为心灵出发寻找自我的故事,其典型风格就是“成人状态的忧郁”,主人公自己的精神无法迅速穿透这个现实世界、化为现实,同时这个现实世界也正因为受到理念的不断的暴动而日益变得虚无。在理念和现实的反讽和悖谬中,“希望只是一个世界即将来临的征兆,它依然是如此脆弱,即使是已存事物之中微不足道的力量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它粉碎。”[6]
与古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美学风格不同,胡风主张“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提出了“受难”的美学观,这个观念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艺术典型在于将普遍力量和具体人物的形象的和谐统一,而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艺术家用一条微妙的线索把他们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见出“人物的行动的根源在于内心方面,但是同时他也要把在这种行动中起统治作用的那些普遍的本质的力量显示出来,加以个性化,使它们成为可以观照的对象。”[7]这条线索就是“情致”。所谓情致,就是“存在于人的自我中而充塞渗透到全部心情的那种基本的理性内容”,[7]288它是艺术表现的适当的区域。胡风同意黑格尔的“情致”观念,认为有无“情致”是区分作品内容真假和艺术生死的标志。
不过胡风将黑格尔的“情致”翻译为“受难”或者“激情”,在关于“情致”的理解趣味上与黑格尔明显不同。在黑格尔的美学视野中,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艺术是最理想的艺术。而在古希腊世界里,人们关注的是存在与流变即“一”和“多”的关系。在万千变化的世界现象之上,希腊人认为存在另外一个可以通过理性的认知来抵达的井然有序的世界本源,即自身不可分割而又衍生整个宇宙的“一”。这个“一”既是至真,也是至善,同时还是至美。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莫不如此。而在古希腊的艺术中,这种观念就体现在人物形象的“个性”上,“它们既不是抽象的特殊,也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许多特殊都从它发源的一般。”[7]233作为表现这种“个性”的情致,则指体现普遍伦理规范的人物心情,因此古希腊艺术才有着“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称誉。而胡风所强调的激情或者受难,更着重指主体在持续不断的革命实践中,其内心的解放欲求与安命态度之间的强烈斗争,更着重表现主体在与历史重负搏战的痛苦,力图超越现实生存的焦灼和对未来救赎的渴念,其中更多地涉及的是有限精神(作为个别的、历史的、具体的主体)与无限精神(作为未来的、完美的、彼岸性的上帝)在历史中的辩证关系。
三、文艺:“施洗约翰”的批判与救赎
胡风坚持文艺对人民群众的唤醒作用,坚持文艺在政治革命实践中的先锋地位,对于作家,胡风同意厨川白村“作为预言者的诗人”的看法。在《向罗曼·罗兰致敬》、《罗曼·罗兰断片》中,胡风更明确地将诗人的角色功能譬喻为出现在耶稣的前驱的施洗约翰:“他自己正是一个他所形容的,一手握着斧子一手捧着头的,身首分离的圣约翰。他自己正是一个他所赞颂的忍受苦难,克服苦难的英雄。”[1]243
据《圣经》记载,在基督开始传福音之前,约翰就在旷野向犹太人施洗,劝勉悔改,声称“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8]2;而他的职责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8]2。而施洗约翰在基督教中的作用,一是“预备人心,为接受耶稣的真理开辟道路”[9]19;二是“悔改的洗礼不仅是仪式,还要求结出果子”[9]20,施洗约翰批判了法利赛人的唯律法主义和撒都该人的只注重外表的做法,提倡用实际行动践行悔改,诸如要求税吏“除了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8]61等;三是“谦卑自己,让主显大”[9]21。约翰坦承自己并不是救世主,而耶稣才是上帝应许的救赎主。“但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8]2施洗约翰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即厨川白村所言的作为“预言者”的诗人),他的装束和言行带有着先前以色列先知的特点,同时又是通向耶稣、通向新约的桥梁。
胡风对“诗人”(作家)的“施洗约翰”的定位,自然不是他的独创。我们在恩格斯对但丁的“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0]的评价里可以发现其渊源关系。而对胡风文艺思想有明显影响的卢卡奇,在其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绝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11]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的左翼文学界,这种直言文艺的先锋地位和作家的“施洗约翰”角色的言论,这种面向未来的现实批判立场,已经显得相当的异端和另类了。
在《罗曼·罗兰断片》中,胡风对罗曼·罗兰的评价隐隐显现着“施洗约翰”的影子。他写到,“罗兰当然是沿着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的道路战斗下来的,但他们不但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要求的那一类,而且正是为了反抗资产阶级,作为通到以主人自居的民众的战斗的桥梁的。精神力量,被当做这样的桥梁,被当做燃起民众力量的火种,它的估计是不怕过高的,但如果以为它可以君临历史道路上的社会物质力量,或者相反地变成良心上的道德的慰藉,那就会降落成立足点不稳的无力的东西。”[1]256正如前面所述的施洗约翰只是让人悔改,预备一颗悔改的心,而不能代替真正的赎罪。
在胡风的作家作品评论中,“施洗约翰”是其中深藏的价值标准,罗曼·罗兰如此,莎士比亚如此,果戈理、契诃夫、鲁迅也如此。在《A.P.契诃夫断片》中,胡风评论契诃夫“用爱和信念工作”,他写到,“向着现实人生的执着,的反抗,的追求,这对于他,一个伟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者,才是坚强而犀利的批判力的根源,才是晶莹而生命栩栩的艺术力的根源”。[1]221对于契诃夫的历史意义,胡风写到,“他的生命通向着他预感到了的东西‘所昭示的前途’,也就是俄罗斯正在走向的前途。他欢呼着这个前途,预言了他的到来‘至迟不会延迟到两三年’。从九十年代跨进了二十世纪,他从幻灭的时代走近了一个新生的时代。在他做了预言的,也就是他逝世了的第二年(一九○五),这个前途的序幕就壮烈地揭开了。”[1]233
从“施洗约翰”这个视点,我们对胡风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可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施洗约翰为了预备百姓迎接那即将来临的神国,他呼唤百姓悔改,这种悔改更侧重在内在心志的升华即“心的割礼”上。施洗约翰认为,没有所谓“义民”(与生俱来就公义的民族),只有那些愿意悔改,并且结出好行为果子的人,才能逃脱即将来临的审判。如果自恃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为这就是得享弥赛亚救恩的确据,那是大错特错的思想。胡风在反驳“才子集团”关于胡风“将人民看成妖魔鬼怪、拒绝和人民结合”的论点时,认为现实具体的人民并不天生“优美”、“坚强”、“健康”,而是有着双重性,既有着创造历史的要求,又有着安命的态度,从而产生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作家的任务就是发现并反映其解放的欲求,使其冲破精神奴役的包围,从“各自抱着被各种各样的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的杠杆所规定的反省和情热的人转变为那个反抗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的总的冲动力的发展要求所吸引、所改变,因而能够为那个发展要求献身奋斗以至献命流血的人”。[1]546也只有觉醒而解放后的人民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国度的子民,他们的阶级、政治的实践,他们用自己的血和火进行的洗礼,才是真正的自我救赎,在这个面向未来的持续不断的自我救赎过程中,所谓的“优美”、“坚强”、“健康”,并不是既成的事实,而是在不断努力趋近却永远无法抵达但在行进过程中不时照亮道路的心灵之灯。
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胡风对文艺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关系的分析中,更明确彰显了文艺作为“施洗约翰”的破旧开新的作用。胡风认为,在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反封建斗争中,革命文艺,就像施洗约翰一样,它起着“摧毁黑暗势力的思想武装,由这来推进实际斗争”[1]532的作用,担负着“就是要从自己的道路上分担唤醒人、影响人、甚至改造人,把人吸引到这个大斗争里面去的意识斗争的任务”。[1]546最终的完成和实现是体现在血与火的阶级的政治的实践中,“在民主斗争的大潮里面,回响着苦难的人民的痛烈的控诉和深沉的渴望,滚动着觉醒的人民的坚强的信念和欢乐而雄壮的歌声”。[1]511
标签:胡风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文学论文; 苦闷的象征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施洗约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