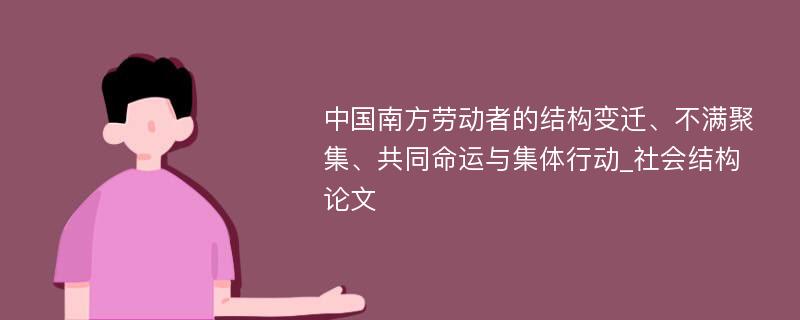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地区论文,怨恨论文,工人论文,集体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73;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7-0079-1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进入2010年以来,广东各地多家企业发生停工群体性事件,与过往不同的是,工人不再是工资支付这种权利诉求,而是要求增长工资的利益诉求。场景中工人似乎开始觉醒,他们发现了团结的力量,工人个体行动正在逐步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集体行动。广东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大省,率先步入中等收入水平,从而成为中国最早遭遇转型压力的地区,工人渴望分享发展成果的利益诉求增多似乎成为一种趋势。所以,我们需要正视工人对于工资增长的诉求。如果处理不好,工人集体行动不仅会拖累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导致社会失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因劳资问题引发的工人集体行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末,随着国企改革推进和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的重建,原有的“铁饭碗”被打破,许多国企工人面临下岗、失业的困境,甚至有一部分工人被推到了生存边缘,在急剧社会变化中一时无法适应的国企工人则发动了许多集体行动。客观现实推动了学术研究,它需要理论上的回应,以解释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逻辑。我国学者对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研究多是在非阶级行动前提下进行的,研究议题主要是行动发生原因,并试图用自尊、不公正、道义经济、政治伦理、相对剥夺等来解释其发生逻辑。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开始突破单一的结构和理性主义分析,过程分析和建构主义分析逐渐增多,如刘爱玉用情境-过程方法来分析工人行动①;田毅鹏用“典型单位制”的社会框架来解释国企工人行动②;佟新解析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对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价值③。同时还出现研究取向和方法的融合,于建嵘对安源工人行动研究即是一种尝试。他强调工人行动不仅仅是所谓理性选择,而更多则受制于家庭和情感纽带,其对工人阶级意识主体性建构、工人与干部及知识分子关系等的研究引人入胜。正因为此,裴宜理称其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④。此外,有关工人行动研究不再拘泥于行动逻辑的解释,包括工人行动策略、空间环境等议题也得到了关注,如吴同研究的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⑤,李怀的“单位空间环境”对集体行动影响研究等⑥。
在农民工集体行动方面,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行动产生因素及解释框架等问题上。李静君认为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差异推动农民工发出反歧视的声音,集体动员极易在仲裁庭和法庭争议中流向街头,合法行动往往转化成直接的街头行动⑦。潘毅则将阶级、性别、家庭等要素置于工人行动分析中,她指出:由于一个有组织的打工阶级形成受到阻塞,他们会展开短暂的、自发的罢工等集体行动。作为一个主体,其行动不能简化为阶级斗争,其抗争既是打工者对资本、制度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⑧。黄振辉等用底线正义来解释农民工抗争行动⑨。谭深借用生存文化来解释农民工集体行动,她认为作为弱势的女工在与资方对抗中主要采用的是“忍”这样的生存文化,忍是一个蓄积过程,是一个底限:在忍的一侧,是生存的文化+反抗的隐藏文本;超过了这个底限的另一侧,就可能是反抗的公开文本。而反抗者之间的关系,是集体行动的基础,是反抗行动的中介⑩。蔡禾则对转型中国农民工集体行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整体上讲,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规的认知水平、社会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在投诉和集体行动的方式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11)。而谢岳用蒂利等人的政治过程理论来解释农民工集体抗议行动。他认为尽管有关劳动关系的司法改革给他们带来了行动的政治机遇,但是,由于这些政治机遇并不能保证他们行动的成功,相反,借助司法改革这个行动机遇,行动者却经常遭遇行动的失败。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农民工时常将温和的“司法动员”转变为激进的“街头抗议”(12)。
在国外,劳工运动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对于工人行动特别是集体行动的探讨,西方学者更多将其放入集合行为、社会运动中来研究,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所说社会分裂创造了动员潜能成为社会怨愤理论源头,列宁对党的先锋队即组织的重视成为资源动员理论源头,而葛兰西创造工人阶级文化构想成为集体认同理论源头(13)。有关集合行为理论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心理学,心理状态或者情感分析成为集合行为研究的取向,它强调集合行为来自于各种异常心理状态,如不满、疏离感、挫折等。到20世纪50、60年代,许多社会学家借助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来解释集合行为,相关理论归结起来主要有感染理论、趋同论、突发规范理论、政治抗议论和加值理论等(14)。与此同时,伴随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学者意识到当人们的集合行为变为一种有结构和秩序的行动时,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即公众为推动或阻止现有规则制度变化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行动(15)。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相对剥夺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运动领域。随后,在批评相对剥夺理论中资源动员理论迅速崛起并占据主导地位(16),研究民权运动的学者Wilson与Lipsky认为,抗议多来自弱势群体,他们缺乏体制内资源,无法以正常方式来争取他们的利益,抗议是弱势者所运用的政治资源。由于将抗议视为弱势者的资源,也一并被视为是资源动员论的先驱(17)。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麦卡锡和扎尔德,他们分析了社会变化导致流向社会运动部门的资源,如社会富裕使不少动员者时间、金钱增多,还有社会媒体发展等。随后相继出现以蒂利、麦克亚当等为代表的政治过程论和以甘姆森、克兰德尔曼斯等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研究内容可归结为政治机遇、动员结构、集体行动框架和斗争手法等几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是结构主义、理性主义、现象学和文化的分析。从历时性看,经历了从宏观解释到中观直至微观的研究,从一般分析到因果机制和过程研究,从结构分析到建构分析的过程。
总之,从历时性看,有关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理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或革命发展有什么规律。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而近些年则主要是探讨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发展规律尤其是其中观和微观机制(18)。在国内,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集体行动研究重点在于解释其发生的原因,还较少有学者去探寻其发生中观和微观机制,而刘能的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集体行动模型则被誉为切合转型中国社会现实的本土化集体行动模型(19)。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后劳资双方“共渡难关、共克时艰”的蜜月期结束,劳资矛盾逐步凸显,并呈群体化、复杂化、尖锐化的趋势。以集体上访、停工为主要形式的职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规模越来越大。仅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后广东各地停工事件就超过100起。工人群体性事件频率加快、规模升级,已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几成常态,是社会结构使然,是工人共享知识型构下的类型化,还是理性行动抑或建构行动意义?探讨工人集体行动发生原因是问题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厘清其发生发展的中、微观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它是如何动员起来的?了解其脉络有利于我们将其纳入制度化轨道之中,从而避免可能的社会动荡,这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二、社会结构变化:动员机遇
按照社会运动著名学者麦克亚当的观点,社会运动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社会变化,它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机遇。当社会变化影响社会权力结构,导致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时,社会运动就可能产生。这是一个涂尔干式思路,它说明社会运动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某一时期集体行动多而另一时段却较少的缘由。
首先,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开始步入社会矛盾高发期。一般认为贫穷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贫穷和动乱之间没有肯定的直接比例关系,在20世纪50、60年代,发生暴力冲突最多的并非是赤贫国家,而是相对富裕的国家,一旦转入较为富有国家行列,暴力冲突的数量又会明显处于下降趋势(20)。按照世界发展规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是这个国家的社会矛盾凸显期。2001年我国开始进入这一阶段,2003年至2008年,正是我国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2010年我国人均GDP是4000美元,而广东已经突破7000美元,率先进入社会矛盾高发期。这种矛盾又是在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的时间过长,富人奢华和穷人贫困之间的强烈反差激起了社会的紧张情绪。劳动者与资本之间围绕利益分配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并成为当前诸多问题中最敏感的矛盾之一。一些社会底层群体面对利益矛盾时往往采取激化、尖锐、甚至恶性冲突的方式,从而使社会矛盾表现出多样化、暴力化、群体化特征。而目前个别地区因劳资冲突演化成群体性事件的案例层出不穷。正如阿尔蒙德所言,“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21)广东如果不适时处理好劳资冲突不仅会拖累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产生社会运动,导致社会不安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日渐断裂。从社会分层结构来看,改革前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以政治身份为标志的社会结构日益为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分化机制所取代。受原有身份制体系影响,无论是原国企工人还是农民工,从总体上讲由于其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缺失,在社会分化中成为社会底层,在整个国家体系中完全边缘化。与此同时,我国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日益吞食社会公平正义。1994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2000年为0.458,2006年已升至0.496,目前基尼系数可能在0.5左右,远远超过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从劳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过多注重效率,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资本获得了超越劳动的分配。“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 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22)工人工资没有与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实现同步增长。不仅如此,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以及企业内不同岗位工资差距过大,一线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偏低。许多农民工不仅无法充分享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而且其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增长过慢,他们并没充分从GDP快速增长中分享发展成果,整个社会日益处于断裂状态。
最后,社会分层、贫富分化下政治机会结构固化使集体行动成为工人利益表达方式。按照美国学者Eisinger观点,抗议出现与政治机会结构(即我们常说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在极端开放或在极端封闭的政治机会结构中抗议不可能出现,抗议更多出现在开放与封闭混合条件下。当前我国社会分层、贫富分化结果就是使政治机会结构固化,社会底层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如果“在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之间存在强大的纵向社会和政治联系的话,那么底层阶级之中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导致抗议运动的动员进程”(23)。而当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强化,上下层联系纽带削弱之时,抗议活动则有可能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我国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场景。同时,这一阶层边缘化状况使其基本处于国家常规政治过程之外,由于缺乏组织,当他们选择现行利益表达渠道等常规政治策略时,很容易被忽略掉,而群体性骚乱却很难被忽略,因为它给社会稳定造成现实威胁。
总之,在转型中国,“社会变化为政治动员决定着结构的和文化的潜力,政治动员只要不被政治化就会保持潜伏状态”(24)。随着社会分层结构日趋定型,利益分化日益明显,断裂社会使得社会集团出于利益差异以及结构和文化的理由而对立起来,农民工等群体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利益诉求从潜伏处显露出来。和其他集体行动一样,工人抗议起源于现有体制的不公平,并表现出行动主体改变现状的集体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国家可能成为抗争对象,迫使其将弱势群体纳入政治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国家也可能被工人作为一种杠杆工具,来平衡劳资利益。而政府包容或排斥的不同战略则决定着其权利诉求能否进入制度化渠道,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减或增加机遇。
三、怨恨积聚:动员的社会心理
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的早期解释融入了太多的社会心理学如著名的相对剥夺理论等。随着资源动员理论的出现,社会运动研究中组织理论和功利主义经济学模型占据主导地位,资源、组织获得了更多关注,并被注入工具主义的理解。“用工具性术语对集体行为理论所做的批评,是不是由于排除掉了对价值、规范、意识形态、计划方案、文化以及认同感所做的分析,而犯了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误呢?”(25)实际上,主体意识尤其是怨恨往往充当了集体行动的情感动因,如“恨”在表达韩国工人日常体验并使之具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恨”这种语言通常能强化有过同样苦难经验的人的受压迫感觉,促使他们形成强烈的亲近感,从而在形成工人集体行动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催化剂作用(26)。无疑,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但作为行动的主体,并非完全按照剧本行动的木偶式的演员,他们具有主体意识,尤其是受歧视、社会不公正以及利益受损而产生怨恨集聚,当这种情感压抑接近一定限度时,怨恨即会产生巨大能量而冲破现有的制度框架,衍生出集体行动。
对工人怨恨可从两个维度来检视:一是日常体验产生出来的怨恨,这种怨恨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农民工时常遭遇社会歧视、污名和妖魔化,怨恨多由此而生。农民工身份是国家户籍制度安排的产物,而身份相关的社会事实的成立和维持,不仅有赖于国家制度上的安排,还与相关群体在日常互动中的建构和广泛认同有关(27)。农民工身份类别通过和城市居民日常交往,政府、知识分子及大众媒体的话语而被建构和符号化,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28)。作为一群外来者,与有“品位”的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总是表现得有些“土”和“脏”。而类属和身份是人们对认知世界、区分角色的有效途径,人们总是会对类属和身份贴上标签,赋予其某种意义。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与此同时,媒体将农民工形象妖魔化,他们被建构成破坏市容卫生、素质太低、野蛮粗俗、愚昧无知的形象,这些贬损性评价构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形象的评价图式。社会治安、刑事犯罪,甚至是疫病控制等问题出现,都会被认为与农民工高度相关。这就是一种社会污名,即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贴上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该标签的人有一些为他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农民工也认识到城市居民对其污名、妖魔化,“别人的眼光让我们感到低人一等”。无疑,社会污名、妖魔化使农民工形象被贬损,羞辱性的形象建构深深刺伤了农民工自尊心,在一幕幕场景展现中,怨恨被刻入农民工记忆之中。当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引发劳资冲突时,农民工记忆中的怨恨会迅速燃烧起来,并通过冲动、情绪化甚至是暴力方式的集体行动来释放。
二是工作场所体验产生出来的怨恨。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不仅意味着农民工空间的转换,他们还必须接受工业劳动生产体制。它一方面将农民工锻造成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类型,即那种温顺、服从、勤勉、任劳任怨的类型;另一方面,我国华南地区中小型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者多来自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有一部分来自日本,它们主要是上世纪80、90年代从东亚经济中转移到中国内地的家族企业,他们强调传统儒家观念,在管理中要求工人绝对服从与忠诚(29)。这些中小型企业通过各种符号确立起企业主在工作场所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构建出等级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产业关系。
首先是企业通过符号控制建立工作场所甚至是社会生活中的等级主义。20世纪80年代,广东承接港台地区以及日韩等国的服装、鞋帽、玩具、电子等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心,其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内地年轻农民,他们被称为“打工仔”和“打工妹”。这些工人基本都被要求穿上标有企业名称的工厂制服,在进出厂门时还需佩带厂牌。普通的员工工厂制服较为简单,尤以蓝底工衣最为常见,而职位较高的员工制服则美观了许多。除此之外,企业会为职位较高的员工提供独立的食堂和宿舍,而这些所谓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只能流连在拥挤不堪的食堂和宿舍。所有符号差异都是为了强化“打工仔”和“打工妹”与管理方之间身份的区别,强化工作场所甚至是社会生活中的等级主义。
其次是构建起工厂专制的劳动生产体制。按照布洛维的观点,资本主义工厂政体分为专制政体和霸权政体。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强制占据主导,生产体制大多都是专制体制。在当代,“同意的重要性上升了而强制的则下降了,实际上,强制的运用本身也变成了同意的对象”(30),劳动生产体制由专制转向霸权。但在华南地区绝大多数工厂仍是专制政体。在工作场所,资方管理人员拥有高度权威,他们通过肆意呵斥、辱骂甚至是殴打、搜身等方式,撕掉“打工仔”和“打工妹”的自尊,来让这些外来工接受工厂管理控制。
最后,通过以计件为基础的薪酬体系制造甘愿加班,形成“赶工游戏”。在当代产业分工中,原有的以垂直分工为主导的国际分工被复合网络型的新型国际分工取代,国际分工不再是产业、产品的国家分工而是产业内、产品内工序分工。国际产业分工的内部化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行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所占据的环节上(31)。在代工企业集中的广东,由于处于产业价值链最底端,为获取国际产业链中微薄的利润,超时工作成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惯用手法。相关资料显示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以内的仅占13.70%,在8-9小时之间的比例达到40.30%,在9-10小时和10小时以上的时间段分别占23.48%和22.50%(32)。劳动密集型企业薪酬设计主要是以底薪加计件工资为主,加班费成为工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获得更高收入,员工自愿加班,形成“赶工游戏”。“因为现在控制了,加班时间在80个钟以下,但据我们调查,80%的员工都希望加班,而且时间是在110小时以上。”(33)“工人很乐意加班……如果工人不加班,只能拿到基本工资,就会觉得待遇不好。”(34)如同具海根所言,在给予适当收入,在他们身体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工人是欢迎加班的,有些工人甚至喜欢选择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35)。为了城市的梦想,为了生活,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会忍受工作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辛。
时代变迁让老一代农民工逐步隐退,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主体。“可能每个人都是寻梦的,80后、90后的梦想跟老一辈员工来比,更加接近城市。他们跟城市小孩有同样的梦想,他们希望融入城市。”(36)但高昂的房价,自身能力欠缺让他们很无奈,“感觉很迷茫”。与60、70年代出生的工人相比,新生代员工有着更鲜明的特点。他们不太喜爱企业严格的管理和相关规章制度,这制约了他们的自由;作为一个消费性群体,企业工资往往难以支撑其巨大的消费支出;他们不希望是城市看客,制度性约束使城市成为他者的世界,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鲜明的个性特点使他们不再成为企业简单的管理控制对象,而是企业管理控制的挑战者。一旦资方行为损害其利益或者不符合其意愿,怨恨积聚到一定程度,抗议行动就会产生。
从南海本田事件来看(37),工作场所怨恨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工资过低以及工资增长极其缓慢,工人并没有分享企业快速增长带来的利润。南海本田一线工人工资:基本工资(675元)+职能工资(340元)+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65元)+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1510元,扣除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到手的工资为1211元。若每月除去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日用品100元、工会费5元,每月仅剩456元。工资数额不仅低而且增长缓慢。许多员工反映:我在本田干了两年半了,第一年工资涨了28元(理由是公司刚起步很多项目还没投产);第二年涨了29元(理由是公司部分项目尚未完全投产);到了第三年在项目全部投产后也仅加了四十多元。第二是不同工人间工资差距过大,加剧了工人怨恨。与中国工人的拮据相比,公司有一批特殊的工人——日本支援者,他们却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公司一个二十多岁的日本支援者曾自称每月工资有5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令人艳羡的补贴和福利。以部长为例,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本那边经常会派支援者过来,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还有三百多美元的补助,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在10个支援者中,可能有4个是年轻人,有的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干的事许多中国员工也能做,说不上为公司作出了多大的贡献。这成为引发工人不满情绪的主要原因。2010年佛山市将最低工资标准从770元提高到920元,资方把工人的工资收入中的330元补贴扣去150元算入底薪,工人实际月收入保持不变。工人提出近来物价上涨导致生活紧张,希望能把工资提升到2000-2500元。在工人合理诉求遭到拒绝之后,因不公正引发的怨恨开始升温、蔓延,最后终于引发了停工事件。
四、共同命运:组织缺失下的认同动员
在集体行动中,怨恨集聚为行动的出现提供了情感支撑,但此时的怨恨大多还是个人层次的怨恨,这种个人怨恨还须转化为集体怨恨,集体行动才有可能。除此以外,即便是有了怨恨集聚,集体行动并不一定会发生,或者说剥夺只是充当了背景因素的作用(38)。正如扎尔德所言,“不满情绪或剥夺并不能自动或轻易地转化成社会运动,尤其是高风险的社会运动”。作为参与的个体要权衡成本和收益,对参与集体行动要有理性评估和选择。同时,集体行动产生需要组织、资源等,“资源需要被动员出来并组织起来,因此组织行动十分关键”(39)。因为持续的抗议或抗争,需要组织基础和持续的领导(40)。但在珠三角等地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中,往往是李静君所讲的“野猫式罢工”,绝大多数工人抗争是自发和无组织的,并且其抗争目标主要是经济利益诉求(41)。由于资源动员理论所强调的组织、资源等社会运动要素是植根于欧美国家制度化院外政治、利益表达背景之下,在公民社会中组织可以自由设立,而现行中国工人缺少资源动员理论所需要的资源、组织等,或者说按照资源动员理论来看,工人集体行动是很难发生的,但事实是它不断发生,所以我们必须阐明在组织缺失背景下,个体怨恨如何转化成集体怨恨并被建构起来,这种共同命运感如何激励集体行动并导致其发生的。
集体认同感就是从成员的共同利益、体验和团结中演化而来的群体的共享定义,它包含边界、意识和对话三个要素(42)。通过组织这一载体,在个体互动社会情境中集体认同被建构起来,从而使集体行动变为可能。而在中国语境下,绝大多数集体行动是没有正式组织的,所以与其说是集体认同的建构还不如说是共同命运体的建构,即个体通过一系列行为建构起共同的命运感。
首先是群体类别化或边界的确定。身份认同往往是在类别与边界的互动中完成:通过确定群际关系和群际边界,类别得以区分;类别化则又从主观层面使边界得以强化。一般而言,种族、性别、阶级等是一种最为显著的边界标记,“边界标记既可以是地理的、种族的和宗教的特征,也可以是更为象征性地建构起来的差异,比如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中国独特现代化历史进程形成了城市和乡村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分野,并由此形成相应的社会制度。农民工对其主体地位的认知是深嵌于现行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他们知道“农民工”是一种社会身份的符号标记,区别于城市居民、本地居民的标记。除此之外,农民工可以说是用人单位中最底层的雇用者,他们明显又区别于资方和管理层。在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社会中,农民工完成自我类别化,形成打工仔/打工妹这样的身份认同。
其次是群体意识的形成。“边界把人们划为某个群体的成员,但是只有群体意识才赋予集体认同感以更重要的意义。”(43)群体意识建构是通过语言文字、行动等来传递群体意识,在互动中被锻造出来的。这与汤普森所说阶级意识形成似乎有些相似,阶级和阶级意识不是一种固化结构的产物,而是在动态中形成,是工人阶级自己锻造了自己,而不是被锻造出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而阶级意识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44)。与传统国企时代的工人相比,对于市场化变革下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而言,其阶级身份认同是模糊不清的。阶级身份模糊阻塞了工人集体意识形成,这使得工人群体意识在一种悖论中被锻造出来:一方面,利益和地缘观念对群体意识形成及稳定却有着双重碎片化作用;另一方面,当工人全都受到利益损害时,不分彼此的共同利益使群体得到认同。为降低双重碎片化对群体意识影响,组织资源、行动或象征性符号成为激发共同命运感、促成群体意识的形成的催化剂。在南海本田停工事件中,2010年5月17日上午,变速箱组装科的员工宣布停工。据了解,停工动员组织资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运输工人上下班的班车,另一个是手机和网络。南海本田一般由汽车接送工人上下班,工人平时在上下班的车上聊天,大家都对工资很不满,怨气很大,一说就有共鸣,这为以后停工动员奠定了基础。到17日早上,组装科两位停工事件核心员工号召工人停工,“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最后几十个工人到厂区的篮球场静坐示威。工人在篮球场静坐时,罢工的消息通过短信在工人中迅速传播开来。到中午时分,网络论坛上也出现有关南海本田工人停工事件报道,工人甚至为此动员工人停工建立QQ群,网络成为他们动员的重要手段。在网络的互动中,共同命运感在不断集聚,最终建构起集体认同。
最后是对话的展开。有了边界区分和群体意识,集体认同还需要日常行动对话来建构这种认同,完成由个体向群体的转换,或者说集体认同是在沟通与对话的个体中创造出来,而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创造出来的。同时,在中国特殊背景下,抗议的社会建构无法发生在公共话语层次和运动的劝说性沟通层次,它更多是在行动的一幕幕进程中意识得到提升。在个体对话中,群体边界、群体意识以及对集体行动成功的预期都被建构出来。“这些预期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相信集体行动将获得成功的个体,其人数越多,则集体行动就越有可能实现,而当局也越有可能做出回应。”(45)首先,在上下班的汽车中,工人个体间对话,使得对资方共同的怨恨在工人胸中不断堆积,推动了南海本田工人集体认同的形成;其次,停工中统一行动强化了集体认同。从最初停工行动开始,在核心工人推动下,工人有了初步统一行动。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却成为再次停工的起点,5月22日工厂的广播宣布公司解除两个核心工人劳动合同,直接促成工人统一行动。这些工人戴着口罩、身穿白色工装,潮水般涌向篮球场,高唱国歌、《团结就是力量》,并形成统一的口号:“不达要求,罢工到底!”这些都成为集体认同动员符号。在无数的对话与沟通中,集体认同感、对集体行动成功的预期被成功建构出来,大规模集体行动也就在所难免。
五、宿舍公共空间:动员空间环境
在集体行动中,除组织建立、集体认同形成外,空间环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组织和空间环境往往形成一种反比关系。由于“组织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网络往往能更为有效地进行动员活动,以人群聚居而形成的空间环境就不太可能成为运动动员的主要因素。简而言之,因为一个组织能运用它的资源来更有效地进行社会运动动员,组织性较好的社会运动动员方式将较少可能性以空间环境为基础”(46)。在当代工人集体行动中,组织匮乏以及阶级意识模糊,使得空间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的重要性超过其他要素。
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在我国华南地区许多工人劳动、生活空间是同一的。他们不仅在工厂工作,还住在由工厂提供的宿舍中。其居住的劳动宿舍以及基于宿舍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则成为工人最主要的动员手段。有学者认为劳动控制与抗争的辩证关系在工厂的宿舍空间中被充分地呈现出来,劳资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通过对这个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居住与劳动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的资源,并有助于动员工人向工厂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47)。在这里,宿舍劳动被作为跨国劳动生产过程的空间政治而得到更多的关注。虽然这种体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为生产服务,但工人集中居住的环境却为可能发生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动员空间。
在由公司提供的宿舍中,一般要住12-16人,宿舍拥挤不堪、通风不畅、灯光昏暗、没有隐私和个人空间(48)。这种由公司提供的工人劳动宿舍在珠三角地区比比皆是。虽然企业通过全景敞视空间以及强制纪律来强化对工人的控制,但它将工人这一群体置于同一空间下,则又促进了工人之间主动或被动的人际交往,从而有可能形成某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一方面它有可能为异乡工作的工人提供经济上、生活上和感情上的依靠,成为他们持续流动、改善生存境遇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在与资方的对抗中,由于利益的一体化则又可能促成他们的团结,构建起较强的社会关系。当然,资方因害怕工人有组织行动,人为地将工人队伍分割开来,并制造一种结构性障碍阻止有组织的工人抗争。其中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将有共同地缘、亲缘的工人分住于不同宿舍,工作于不同流水线,减少其交流互动的机会,加上工人高流动性,使这种非正式网络建构变得异常艰难。但即便是社会网络的缺失,宿舍大量聚居也为工人建立集体认同以及采取集体性行动创造了条件。因为许多集体行动发生并不需要资源动员理论所说的群体密集而持久的横向关系,它所要求的是技术资源、空间环境而非组织资源。“生态环境不但促进了以组织和网络为基础的运动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它把大量思想和经历相似的人员聚集在同一社会运动空间内,从而为一个一哄而起的运动创造了条件。”(49)
虽然宿舍劳动体制为工人建立组织和网络提供了便利,但现实是在宿舍空间中工人组织化还是很弱,他们更多是原子化的个体。所以,在南海本田的停工事件中,篮球场则代替宿舍成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空间。4月底,停工事件的核心员工谭某准备辞职,而这时他心中蕴藏一个想法:要领导一次罢工,迫使资方提高工资待遇,走之前为工友谋点福利。5月17日早晨,谭某像平常一样坐班车进入厂区。7点50分,到了开工的时候,谭某按下了流水线上的紧急按钮,流水线被锁上,他号召大家不要做了。几十个员工走出车间,走向车间外的篮球场静坐示威。协商失败后的5月22日和23日,在谭某号召下,篮球场聚集的工人达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集体行动基本上是在没有组织和网络的情况下,在篮球场这一生态空间情境下资方行动等消息很容易在工人中扩散,对资方的怨恨积聚也容易传播,工人的行动也容易受到相互影响,“以行动者和事件为出发点,可以把微观水平看成每个行动者控制着一个事件,即行动者自身的行动。如果出现集体行为,则意味着如上情况发生了变化,即行动者已经把对自身行动的控制转让给他人”(50)。在篮球场上,工人间相互砥砺,集体行动得以持续。
总之,中国目前已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工人集体行动随处可见。由于缺少结构性条件及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中国在短期内不会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或革命。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一般而言,组织化水平与行动中暴力程度成反比,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大多缺少组织化,虽然大多都比较理性,但破坏性不容低估。因为,“当一个社会中各种成分缺乏有组织的集团,或无法通过现成的有组织的集团充分代表自己的利益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或一个领袖的出现都有可能触发人们蓄积着的不满,并会以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方式突然爆发”(51)。显然,我们需要将工人纳入工会体系中,避免工人行动无组织化带来破坏,以消除其对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
①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4页。
②田毅鹏、陶宇:《“单位人”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
③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④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
⑤吴同、文军:《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社会》2010年第5期。
⑥李怀:《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集体维权行动的建构》,《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⑦Ching Kwan Lee.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pp.160-161.
⑧Pun Ngai.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4-75.
⑨黄振辉、王金红:《捍卫底线正义:农民工维权抗争行动的道义政治学解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⑩谭深:《弱者的反抗——围绕一次搜身事件中女工集体行动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和工运”研讨会论文,2003年。
(11)蔡禾:《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12)谢岳:《从“司法动员”到“街头抗议”——农民工集体行动失败的政治因素及其后果》,《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
(13)[美]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7页。
(14)Neil J.Smelser.Sociology.N.J.Prentice-Hall.1991.pp.402-406.
(15)Thompson,William E.Society in Focus: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New York:Longman.1999.p.604.
(16)Gurney,Tierney.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A Critical Look at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3(Winter 1982).pp.33-47.
(17)何明修:《政治机会结构与社会运动研究》,(中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报》第37期(2004年),第37页。
(1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0页。
(19)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
(20)[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40页。
(21)[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
(22)杨军:《2010,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南风窗》2010年第1期。
(23)[美]莫里斯等:《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24)[瑞士]克里西等:《西欧新社会运动》,张峰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25)[美]莫里斯等:《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26)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27)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8)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社会》2007年第6期。
(29)Ying Zhu.Globalizati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Labor Relations and Regulation:The Case of Chin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Volume 16/1,5-24.2000.pp.17-18.
(30)[美]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页。
(31)汪斌:《全球化浪潮中当代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33)2011年4月11日广州市总工会座谈会JP企业代表发言。
(34)2011年3月30日在深圳科技园与SS*LED科技人力资源部经理的访谈。
(35)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36)2011年4月18日在东莞对WJ企业工会主席的访谈(工会主席自己是80后女性)。
(37)程元、李亚蝉:《本田佛山中日员工工资相差50倍,数百人罢工》,《每日经济新闻》2010年5月20日。
(38)McCarthy,Mayer Zald.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Morristown,N.J.:General Learning Press.1973.pp.1-20.
(39)[美]莫里斯等:《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40)Oberschall Anthony.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2.p.119.
(41)Lau,Raymond W.K..China:Labor Reform and 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king Class,Capital & Class(61).1997.p.46.
(42)(43)[美]莫里斯等:《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8、131-134页。
(44)[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5)[美]莫里斯等:《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46)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47)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
(48)Pun Ngai.Women workers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China,Gender and Development Vol.12,No.2,2004.pp.29-36.
(4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50)[美]詹母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51)[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
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工资结构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农民工论文; 打工妹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