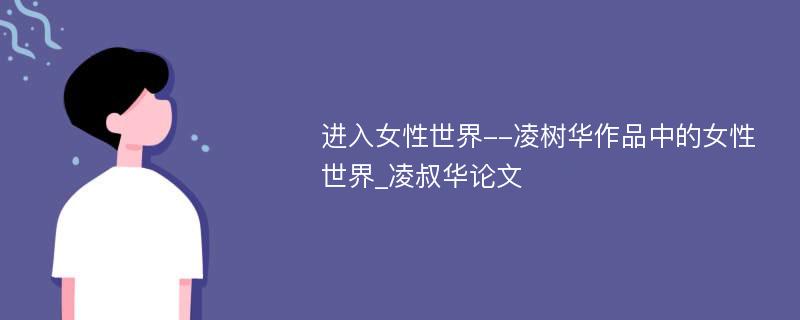
走进女性——凌叔华笔下的女性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笔下论文,世界论文,凌叔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复苏。伴随着一批有才华的女性作家的脱颖而出,表现女性意识觉醒,关怀女性生存价值的女性文学第一次“浮出历史地表”。如果从女性写作的角度,比较当时的几位女作家,那么庐隐、冯沅君等的创作更多地以女性发自肺腑的呐喊,争取着女性的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呼应了反封建、反礼教的时代大潮;而凌叔华的小说则通过反映那些“小姐们”、“太太们”、“母亲们”的现实生存状况,揭示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女性人生的强制性规定和深深的戕害。庐隐、冯沅君等的小说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战斗性,显示了社会解放、个性解放的迫切要求,而凌叔华的创作则更具个性化、女性化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女性自我意识、自我价值追求在女性解放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女性解放的艰巨性、长期性。
五四现代女性作家是在男性先驱者的引导下向封建礼教、父权制发起冲击的,她们的潜意识里还未完全摆脱对于男性的依附。这使得她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无意识地沿用男性价值标准来评判女性,或者沿用传统的男性话语模式进行文本叙述。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凌叔华的女性系列形象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生命的自省意识、自我存在价值以及这些形象所暴露出的作者潜在的男性文化视角。
一
凌叔华笔下的“闺阁”小姐,是一群在时代变迁之际处于现实和传统夹缝之中的旧式小姐。现代文明之风虽然忽如一夜春风来,在那些闺房小姐的心灵掀起微微波澜,但终究未能吹开她们少女的心扉。这群在传统礼教中长大的女子,具有良好的修养,知书达礼、美丽温柔,但她们封闭凝固的旧式生活,她们对传统角色地位的认同,导致了她们与外面世界的深深隔膜和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绣枕》中的大小姐,花了整整半年时间,精心刺绣了一对漂亮的大靠垫。靠垫绣好后,她的父亲把它送去了白总长家,因为“白总长的二少爷二十多岁还没找着合适的亲事。”靠垫寄托着大小姐对美好婚姻的憧憬和向往。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对寄托着大小姐款款深情的靠垫在送去的当晚便被喝醉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让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又有人干脆把它当作脚垫用。最后,靠垫被佣人捡了去,又转送给了大小姐女佣的小妞儿。小妞儿把这一切通通告诉了大小姐,已被拼成一对绣枕的靠垫就这样回到了大小姐面前。一个少女的青春之梦就这么破碎了,她的心就像靠垫一样遭到了践踏。小说中,绣枕不仅成为女主角命运的象征,而且成为传统女性命运的一个暗示。在封建男权社会中,任人践踏、任人主宰是女性的共同命运,哪怕是像大小姐一样从外表到内心都非常“优秀”的女子,同样逃脱不了精美绣枕的遭遇。
《茶会以后》中的阿英、阿珠两姐妹,比《绣枕》中的大小姐要幸运一些。她们已经可以出入大型的社交圈,也比大小姐见多识广。但她们受传统礼教熏陶的时间太长,和男子说话,“觉得不舒服,样样都得小心”,虽然她们心里羡慕那些“同男朋友那样起劲的说笑”的小姐们,但她们自己却缺乏这样做的勇气,她们不适应这种新的社交方式。在她们身上,反映出那些双脚跨出了闺房,但又不知踏向何处的旧式少女的普遍心态。旧的、熟悉的生活方式已经逝去,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是那么陌生。她们的将来,很难令人乐观。
再看《吃茶》中的芳影小姐。“正当芳菲的时候,空在‘闺阁自怜’”,一旦接触到留洋学生王斌,即为他的高雅、热情、殷勤打动,错把王斌的洋式礼节误认为是多情的表示,因而坐卧不宁,暗怀期待。不料一周后接到王斌婚礼的请帖,女主角只有泪洒衣襟。那样一种出自青春生命向往异性的本能的正常情感因为自己的“误会”而成为一道心灵的创伤。
面对一个个娇弱柔媚、蕴藉含蓄而又聪慧多情的大家闺秀形象,不由令人扼腕叹惜。在她们身上,有着太多的“女性味”,而感觉不到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自主意识。在争取爱情自由、个人幸福方面,她们没有任何主动的表现,一个个都是等待“君子好逑”的淑女,在等待幽怨中虚度光阴。对命运的顺从,构成了她们枯寂无味的人生。虽然文明之风的吹拂,使她们睁开了紧闭的双眼,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但她们没有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摆脱不了紧紧束缚她们的传统礼教,因此只能在困惑、迷惘中体验现实与传统脱节而带来的心理波澜,感受将要被时代抛弃的凄凉和恐惧。这是一群在新旧文明夹缝中找不到出路的迷途的羔羊。她们的命运提醒人们,女性要摆脱封建传统束缚,争取独立自主的命运是何其艰难。
二
和凌叔华笔下的闺阁小姐相比,作者对旧式家庭已婚女子生存状况和现实处境的描写更加细腻深刻。从初为人妇的女子到拖儿带女的主妇,凌叔华以其女性经验的敏感和直觉,将一般男性作家不易窥透的某些女性生活画面、女性情感活动展示在读者面前,描述了女人的一生,勾勒了一幅老中国女儿们或痛苦、或麻木、或绝望,逃不出命运轱辘的生存图景。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初为人妇的青年女子,可以视之为《绣枕》中已经出嫁的大小姐,或者是《茶会以后》、《吃茶》中的阿英、阿珠和芳影们。这些“大小姐”经由她们的父亲之手转交给各自的“丈夫”后,她们的遭遇实在也不比那对绣枕更幸运。《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婉兰,一如那对绣枕般典雅、精美,但她的容貌、举止和文化修养仿佛只是她能够嫁得出去的一个筹码,并不能为她在夫家的地位增色。为了生存,她必须讨好老婆,取悦丈夫:她劝丈夫收丫环做偏旁,劝他去那里过夜,丈夫不领情,说她贪图“贤德”之名,婆婆骂她假惺惺;丈夫在外面逛堂子、玩窑姐,她根本不敢过问,还要替“荒唐”丈夫收藏那些所谓的定情之物;婆婆不怪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反怪她看不住自己的丈夫,整天闲言闲语,气得她“没有一天不哭两三次的”。婉兰后悔自己嫁了一个这样的“荒唐”丈夫,她对父亲的三姨太——一个同样苦命的女人说:“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小学了本事,从小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婉兰的这番话,说明她已经看清了自己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但她似乎没有勇气摆脱这种命运,因为她认为她已经太晚了,而且女子没有法律的保护,没有谋生的本事,也就很难独立自主,不依靠家庭,所以她只能在无奈和心酸中认命。
凌叔华的创作温婉、含蓄、绝少发议论。此番婉兰的议论实际是作者的见解。她清醒地看到了女子被男人当作玩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女子如何摆脱“玩物”命运这点上,作者似乎也有点困惑。虽然她已认识到女子没有法律保护,所以没有人身保障;而且觉得女子从小就应该学本事将来才能不依靠家庭,但是否这样就可以不当“玩物”了呢?从婉兰的“认命”看,作者似乎不能指出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出路。
从《中秋晚》中的那个因丈夫团圆节不吃团鸭而耿耿于怀的太太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对自己的婚姻毫无把握,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所不同的是,这篇小说着重从敬仁太太的女性心态发掘入手,更多地揭示了女性对待自己命运的麻木、不觉悟,竟然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某种仪式化的标志上。在夫妻新婚的第一个中秋节晚上,敬仁太太精心准备了一桌团圆宴——这里包含着她对婚姻生活的美好祝福:“吃了团圆宴,一年不会分离。”特别是那团鸭,一定要吃,否则就是恶兆,但丈夫还是因为去料理干姐姐的后事而没有吃上团鸭。丈夫回家后,夫妻发生口角,并且打碎了供过神的花瓶。太太将这一切均视为恶兆,从此夫妻失和。敬仁终日在外游荡,放浪不羁,太太连接两次怀孕后流产。到第四年,家道败落,夫妻流离失所。到了这种地步,敬仁太太(包括她母亲、婆婆)却仍旧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第一年的中秋晚就是一个不祥之兆。如果说上一篇中的婉兰对自己的不幸命运还有所认识的话,这位太太则是一个封建迷信思想熏陶出来的、尚未觉悟的家庭妇女。他一心想保全、维护自己为人妻的地位,但又没有丝毫的把握和安全感。这位太太的不幸令人同情,但她的愚昧和麻木却又令人感到可笑而可叹。
在凌叔华笔下的旧式太太中,还有一群俗不可耐、无事生非的灰色形象。她们的麻木、庸俗,反映了女性自甘堕落、无可救药的一面。她们的存在,不仅对女性的改造,而且对整个国民劣根性的改造都是一种警示。
《太太》中的太太,既不关心丈夫,对孩子也毫无怜爱之心,把所有心思都集中在牌桌上。为了表示自己输得起,不惜当掉丈夫唯一的一件体面衣服和一块金表,去追求赌场上的虚荣。这种畸形的虚荣心态,反映了这类女性内心的空虚和庸俗。
寄生的生活产生出畸形的生活方式。这群太太既然无法进入社会,就只能寻找和她们一样的太太、姨太太“物以类聚”。她们大把地花钱,经常与丈夫争执,与下人怄气,无可救药地染上了一身市民的庸俗作派。《送车》就是一幅客厅里女人的众生相。这里充满了太太们尖锐的调子和得意的笑声。她们聚集在一起,谈论一些共同的话题:如何暗察丈夫的不忠和负心,如何防止佣人的偷懒和揩油,如何应付孩子的胡搅蛮缠。谈论佣人问题是她们最得意的话题,好像没有她们的精明能干会计算,家早就让佣人掏空了。她们在家庭中是丈夫的奴隶,是儿女的保姆,只有在对佣人的无休止的挑剔中,才能感觉到当主子的优越感。所以她们聚在一起,也就只能飞短流长、说东道西,比排场,比阔气,比丈夫的地位,比对佣人的手段。同时,时代大潮的涌动也使她们感到了自己在家庭中依附地位的不稳固。对此,她们对那些经自由恋爱结婚的新式太太既鄙夷又嫉妒,虽然以自己是“明媒正娶”来自我平衡,维持表面的傲气,却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和不安。
旧式太太的麻木、庸俗,不仅来自封建礼教的戕害,而且来自她们内在的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她们的言行举止,凸现了麻木的国民灵魂,让人们感到,在新文化大潮的涌动下,这个时代的女性生活还有阴暗、可鄙的方面,她们是女性自我解放的重大障碍。
三
凌叔华除了描写旧式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她们的可笑、可鄙与可怜外,写得更多的,是新式家庭中的知识女性。
爱情,是现代女性文学涉足最多和最深的主题。在大多数五四女作家的笔下,新女性在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中,首先要争取的就是恋爱的自由和爱情的胜利。凌叔华笔下的新女性走得更远;她们不仅争得了恋爱的权利,与志同道合的爱人组成了新的家庭,而且在维护小家庭的温馨、浪漫过程中,进一步体现了女性对爱情生活的理解,对女人生存价值的追求。
鲁迅在创作《伤逝》之前,曾做过一个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其中最精采的见解就是:“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突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后来塑造的子君形象就是“回来型”的——子君在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并且勇敢地和自己所爱的人涓生结合后,最终无奈回到了奋力逃脱的封建家庭,在“严威和冷眼的包围”之中忧郁地死去。《伤逝》写出了子君“回来”的悲剧。凌叔华的创作则在鲁迅所说的或“堕落”或“回来”以外,探索了极有可能的第三条路:她们像子君那样在爱情中寻找自我,但并不像子君那样又在爱情中迷失了自我,而是努力保持女性的独立、自主,时时创造,使爱情得以不断更新。当然,她们在经济上都是幸运儿,她们无需像子君那样为柴米发愁,为家庭的生计发愁,她们有着较为优裕的生活环境。
凌叔华的《酒后》、《春天》、《花之寺》等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上述问题。《酒后》描写在一次家宴之后,男主人公陶醉于良辰美景、娇妻暖屋,但妻子采苕却怜惜那个醉卧于客厅的子仪——她一直心仪的有才华却已有妻室的人,要求丈夫让她吻一下子仪。丈夫虽然不很情愿,但最后还是答应了。然而,当采苕走到酣睡的子仪面前时,又失去了勇气,不想"Kiss"他了。与此篇相近的还有《春天》。霄音无意中听到一段凄恻动人的琴声,不禁勾起心事,想到自己从前的男友君健如今正患病,而且穷困潦倒,不禁痛心流泪。她决心提笔写信问候。在这两个故事里,都出现了一个男性“第三者”,而这“第三者”无论是子仪还是君健,都不是那种坚强有力,给人以依赖感、安全感的男人。子仪文弱、斯文,有一个无爱的家庭;君健穷困潦倒,卧病在床。他们的状况,激发了女主人公的恻隐、同情之心,忍不住想要去安慰、关心他们。当然,这两个故事显示给读者的含义远不止这么简单,它既体现了一种五四式的母爱情怀,一种女性的怜悯、同情之心,又包含着女性的少女情怀和婚后爱情生活的复杂与微妙。采苕想去亲一下自己一直仰慕的人,或许就是想了却一段埋藏在心度的美好情感;从深层看也包含着想要争取一个女性除妻子身份以外的另外一种权利——她仍然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仍然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感情天地和人格意志。从这个角度看,凌叔华的小说揭示了人的感情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种丰富性和多元性是客观存在的,也同样是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体现。对此,作者的态度是既不回避,也不扼杀,而是进行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从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举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采苕怀着“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想接近子仪,霄音则因昔日友人的憔悴不堪而伤心流泪;但当采苕走近子仪身旁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时却又“三步并两步的走向永璋(丈夫)身前”,霄音也在丈夫到来时将信揉碎抛进字纸篓。她们最后的举动给人以“发乎情,止乎礼”的感觉。实际上,采苕也好,霄音也好,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们的举动,并非是要破坏改变夫妻关系,而是出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女性心理,想要在妻子的角色以外,仍然葆有一个独立的“自我”,从中也体现出一种“我是我自己的”、我可以这么做的自主意识。
《花之寺》与上两篇有所不同,主要讲述了妻子燕倩在发现丈夫对家庭生活产生厌倦情绪以后,为维护小家庭的和睦、温馨,设计了一个小圈套——以另一个女子的口吻给丈夫写了一封信,约他在花之寺相见。丈夫怀着做一次“奇美的梦”的热望按时前往,结果发现原来是妻子同他开的一个玩笑。信中出现了一位女性第三者,这实际就是女主人公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在信中,女主人公以崇拜、赞美的口吻把丈夫比作园丁,说他甘泉似地浇灌了她这棵小草,使她开出美丽的花朵,并希望自己的灵魂永远驻守在他那里。信中的“她”,也就是婚前的“她”。那时,她崇拜他,他是她的“园丁”。婚后,妻子不安于当“小草”了,她对“信中的我”作了巧妙的自我解嘲,因为她已经意识到,除了是妻子,她还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主见的自我。在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主动调适夫妻关系的积极态度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她不想坐视家庭生活的沉闷、无聊,于是就想了这么一个巧妙的办法,激活丈夫对爱情的向往,使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爱情得以更新。同时她也想让丈夫明白,不是成了夫妻以后就没有爱情了:“我就不明白你们男人的思想,为什么同外边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对自己的夫人讲,便没有意思了?……”暗示自己想成为既是妻子又是恋人的角色。这是一个聪明、有思想的新女性。由恋人成为妻子后,没有停留在“小草”的依附角色上,而成为一个有主见、有独立性的女性。这就比前两篇小说更进了一步,表明女性除了在夫妻关系中必须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外,还要积极努力,使爱情得以时时创新,维护家庭的温馨、浪漫。
理想的爱情,幸福的家庭是新女性追求的目标,但生命的全部意义是否仅止于此呢?除了爱,女性是否还可以有其它的追求呢?《绮霞》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绮霞》中的绮霞和丈夫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绮霞酷爱音乐,但婚后为了全心侍候爱人就再也没有摸过琴。在友人的支持和外国小提琴家演出大获成功的刺激下,绮霞终于又拿出了心爱的小提琴,并在经过了多次的内心冲突以后,给丈夫留下一封家书,离家到国外学琴去了。五年后绮霞回来,琴艺大有长进,可是丈夫已和别的女人结婚了。绮霞只得夜夜拉琴,用琴声陪伴自己渡过漫漫长夜。
作为一个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女性,绮霞为了心爱的小提琴牺牲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在这里,作者似乎告诉我们,爱情和事业是不可能兼而得之的。在那个时代,这确实就是事实的真相。因为历史还不能够为女性的这种双向发展提供足够的条件,大多数女性只能选择其一。从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角度看,绮霞较其他女性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当别的女性还在为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努力奋斗的时候,她已经触及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女性自我价值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绮霞不满足于仅仅拥有爱情生活,她还渴望事业的成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用一技之长为别人带来快乐的人。书中有一段话写出了她的心声:“以前自己对男女平等问题,自己曾经如何的唱高调,讥诮闺阁女子易于满足,故学艺不能与男子比并,现在自己怎样呢?自己为了卓群竟至如此……”她终于想清楚,自己再这样下去,一味地依附丈夫,围着丈夫团团转,那就跟旧式闺阁女子没有两样,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最终也就谈不上男女平等。在这种认识的支持下,她摆脱了理智与感情的痛苦纠缠,终于决定:舍弃爱情,离家出走,去实现自己的音乐之梦。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作出这种选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她这样做了,而且执着地坚持着,就是在得知丈夫再婚的消息时也依然不改初衷,仍在学校教琴育人,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在她身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五四现代女性追寻人格独立、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
同样是新女性,有的不甘心沉湎于家庭,而勇敢地跳出爱的巢臼,去追求自我生存的价值;有的则完全为家庭,为“母爱”的名份所累,成为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和儿女们的奴隶。《小刘》一篇清楚地揭示出一个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女孩怎样变成一个平庸、琐碎的母亲。
十几年前的小刘活泼可爱,聪明机灵,经常带着同学大闹课堂,嘻笑怒骂地批评“三从四德”,是女伴们公认的“刘军师”。可十几年后的小刘,却分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脸色蜡黄,神情呆滞,衣着油腻,说话有气无力。作者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原因使小刘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通过描写,我们知道,她为一个平庸的丈夫、几个粗野没教养的孩子、一个脏乱的家耗尽了自己的青春。这里最起码有两点值得人深思:一是从她现时的形象看,她是心甘情愿地沦为如此一个“母亲”角色的。她对儿子的偏袒,谈论儿子地口吻和眼神,对5个孩子的疲于应付都是绝对“母亲”式的,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传统的母亲形象。其二,小刘是个颇有些新思想的新女性,因此她的沉沦更具悲剧性。从一个方面看,生活的逼迫使她成了生育机器和儿女们的奴隶,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恐怕在于她少女时代对封建礼教的抨击只停留于表面和皮相,而未能真正在思想上引起共鸣。小说中描写她少女时代经常带着同学对结了婚的小媳妇来学校读书冷嘲热讽,虽也表明了她对“三从四德”的不满,但仍流露出她对传统礼教的认同:她认为结了婚的女人就应该在家服侍公婆、打点家务、侍候丈夫和儿子们。也许正是这种埋藏在深层意识中的传统观念致使她后来沉溺于传统的母亲角色而不能自拔。小刘的遭遇令人同情,这种可悲既是小刘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存在的不彻底性。在祖祖辈辈因袭下来的强大的、完整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面前,新的思想、新的道德价值观念显得非常脆弱,并没能成为大多数人反封建、反压迫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人对之一知半解,遇到实际问题就束手无策,只好又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小刘的遭遇就显示了传统母亲的角色规定对女性的强有力的束缚。小刘虽然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但这些并不足以抗拒传统母亲角色对她的影响和浸染。看来,女性要真正走出传统的樊篱,摆脱封建纲常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恐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四
五四时期,歌颂母爱的小说非常多,冰心、冯沅君、苏雪林等的创作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母爱进行了描述。凌叔华的小说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但她没有随声附和,仅仅着眼于母爱的伟大和神圣,而是以女性的敏锐和体验写出了她眼中的母爱,并对自己塑造的人物持温和的保留态度,由此带给我们的思索是沉重的。母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存在价值?
《杨妈》的主人公,是从农村出来当女佣的妇女。她勤劳善良,靠帮佣挣钱养活自己,供养儿子,希望儿子有出息。但那儿子却是非常地不争气,常常惹事生非,并且与流氓为伍,找杨妈就是要钱,给慢了就瞪眼,最后干脆不辞而别,抛弃亲娘而去。就是这么一个儿子,杨妈却深深“痴爱”着,到处打听、寻找,到报上登启事,夜夜给他缝制棉衣,最后还不顾体弱多病,踏上寻找儿子的路途。杨妈的母爱执着、绵长,但却令人困惑不解。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她活着一点都不为自己,仅仅是为儿子。儿子好也罢,坏也罢,在她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是她的儿子,是她感情寄托的对象。也许,杨妈只有通过对儿子无止境的溺爱,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才能确立自己生存的价值,但是这种靠依附别人而显现出的影子般的“价值”又到底有多少值得肯定的地方呢?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女性的生存环境根本不可能为她们提供做一个有自主意识、独立人格的人的可能性,为了保全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女性只能把自己的全部生存目标定位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上,母性就成了她们生命的全部立足点。都说母爱是无私的,或许在这无私的背后就是无我;特别是盲目的母爱,是一种彻底的抛弃自我、丧失独立人格的行为。通过杨妈的故事,作者是否想告诉我们,母性,不应成为女性成长途中的障碍。
《有福气的人》为我们塑造了另一类母亲形象。年近七十的章老太太是一个即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老祖母。她一生精明能干,治家有方。丈夫有功名,自己私储富足,儿孙们竞相孝顺。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命好”、“有福气”。然而在这表面的“和睦”、“福气”背后,是儿孙、媳妇的互相猜疑、互相欺骗。章老太太在一次无意中听到大儿子和媳妇的私房话后终于明白,儿孙们对她的“孝顺”是想哄骗她的珠宝钱财。她的“福气”,她在大家庭中的尊贵地位也是她用钱财买来的,等到儿孙们反它们一一哄骗到手,她自己便一无所有,没有利用价值了。作者用微讽的口吻叙述了老太太对自己有“福气”的得意心态,也使她最后的悲伤显得更加真切和绝望。
杨妈贫穷,章老太太富有,但她们都是失败的母亲,有着相同的悲哀。章老太太作为旧式家庭的女性典范,说到底也只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玩偶,一旦支撑自我形象的外在因素倒塌之后,她的一生的光荣历史也就成了对她的最大的讽刺。杨妈也好,章老太太也好,她们都是封建社会的“物”的牺牲品,是父权文化下丧失自我、丧失独立人格的玩偶。
五
女性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从因袭封建传统的旧式女子到半新半旧的过渡型女子,再到赢得婚姻自主的新女性,凌叔华笔下的女性用各自的声音,诉说着女性的情绪、女性的感受和女性的各种生存体验,揭示了中国妇女由女性→人→女人的艰难历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至今仍在继续、发展的过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一种自然存在,只有性别特征,是男人泄欲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她们没有精神上的独立,更没有主体意识可言。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和启蒙精神之光的烛照下,一大批女性觉醒了。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纲常名教的斗争中,她们喊出了“女人首先是人”的口号,迈出了由女性→人的第一步”。这时的女性解放,首先是一种人的解放,和男性解放一样,同样是五四反封建伦理、争取人的解放思潮的组成部分。因此,女性首先争取的是摆脱传统礼教束缚、做一个自由的人、独立的人的资格,而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作为一种个人自由和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便成为广大女性的自觉追求,也在许多女性作家笔下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虽然,没有女性的解放构不成完整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但这种人的解放又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因为它把女性自身特殊的性别经验和心理体验等几乎全部融化于社会意识之中,使女性的主体意识没能充分的成熟与觉醒。五四现代女作家的许多创作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她们同男子一样,共同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在探讨妇女问题时,着重于为人生、为社会的一面,较好地反映了女性反封建传统,争取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精神风貌。和这些女作家相比,凌叔华的创作少了一点时代的阳刚之气,却多了几分女性的阴柔气息。她以女性的细腻、敏锐,从各个角度表现了传统女性被压抑、被欺凌的生存状态,凸现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女性的心绪、感受以及女性对命运的体认,呼唤着母性、妻性、女儿性的精神发展,并以此表明她对女性主体意识、生存理念和自我价值等问题的看法。
从“人”走向“女人”,中国妇女又向前跨越了一步。凌叔华的创作走进女性,记录了女性从“人”到“女人”最初的沉重步履,并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女性如果没有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没有主体意识的充分觉醒和成熟,没有精神上的真正解放,即使有了物质、经济保障,甚至有了法律的保障,都还不能算得到了真正的、完全的解放。
如前所述,五四现代女作家是在男性先驱者的引领下踏上反封建的革命征程的。因而,她们一方面像男性作家一样以笔为武器,承担起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她们自身的先天不足:潜意识里还未摆脱对于男性的依附。中国女性几千年的屈从、依附地位使女性解放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意识觉醒为前提的运动。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中国妇女解放不可能依靠女性自身的力量来完成,而必须借助外力,与男性结成同盟,并以社会解放为妇女解放的前提。因此,五四女作家投身时代潮流,匆匆上阵时,无暇考虑自身的问题,她们的思想、心理、话语的准备明显不足,也就难免出现像凌叔华这样一方面呼吁妇性的精神成长、精神解放,一方面又在作品中显示出自身精神上的某些不足的现象。就凌叔华而言,她潜意识中的男性文化视角,使她往往不自觉地用男性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塑造和评判女性。
翻开凌叔华的作品,一个个温柔可爱、端庄典雅、美貌聪慧的小姐、太太扑面而来。柔弱、娇媚是她们的共同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社会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不管是高门巨族中的闺阁小姐,还是初为人妇的年轻少妇;不管是旧式女子,还是新式太太,她们的形象、外表都充满了这种典雅蕴藉的传统美。《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婉兰,未出嫁前活脱一个《红楼梦》中的病美人——黛玉。她“身穿凝杏黄衫子”,半坐在贵妃床上,“长眉细目,另有多病佳人的风致”。再看《酒后》中采苕在丈夫(一个男性观察者)眼中的模样:“这腮上薄薄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又说她的眉:“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浅浅的眉,微红的腮,温柔缱绻、慵懒娇憨的神态,给人一种朦胧、梦幻的感觉,特别能激发男性“怜香惜玉”之情,也正是男性欣赏的淑女、佳人形象。
不仅她们的形象,她们的性格特征也表现出了为男性社会所认可的宽容忍让、温柔敦厚。即使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也是“发乎情,止乎礼”,最多是在礼教允许的范围内适可而止地表达一点幽怨和不满:大小姐的绣枕遭人践踏,希望之梦破灭,她的不满仅表现为“只能摇了摇头算答复了”;芳影的情爱之梦在收到洋学生王斌的结婚喜帖后破碎,但也只是用“一弧冷冷的笑容”来含蓄地表示自己的痛楚和绝望;婉兰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嫁错了人,但依然认命,不作任何抗争;燕倩在和丈夫谈恋爱时,把自己视为依附于园丁的小草……这些含而不露、哀而不怒、小鸟依人、花草般柔弱的女子从整体形象上看体现了传统的含蓄美、古典美,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但作者笔下无论旧式小姐还是新式太太都一律“惋顺”的形象以及作者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这类形象的怜惜、偏爱,确实说明作者在潜意识中是用男性的价值标准评判女性的。
千百年来,女性已经习惯于用男性的审美和价值标准来规范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娇弱柔媚、蕴藉含蓄成为女性自我形象塑造的标准。这种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特征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积淀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凌叔华创作对女性形象和情感的弱化,突出了女性的温柔和顺从,由人物传达出了一种缺乏独立精神的依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潜意识中男性文化视角的外化,说明作者确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个首先觉醒的知识女性,凌叔华深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并用手中的笔,参与社会实践。她写自己熟悉的社会和熟悉的事,探索着历史转型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但同时,本是大家闺秀的她又摆脱不了大家庭中浸染的闺秀气,摆脱不了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犹如凭栏唱晚的诗人,她一方面赞美五四大潮的汹涌澎湃、一往无前,另一方面又伤感过去的一切如滔滔东流水一去不回头。这种矛盾心态使她笔下的人物既体现了新时代的风采,又不可避免地夹带有旧时代的文化气息。当然,这不是凌叔华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旧时代带给一代新女性的集体无意识症结。而凌叔华,虽然因袭着传统的负担,却在新旧文化的缝隙处开辟了一地属于自己的女性天地:诉说女性的自我,呼唤女性的成长,并创造了一种适合女性表达的叙事方式。本世纪20年代还不是女性成长的成熟期,但凌叔华的努力却使女性文学由“人”开始走向“女人”,并为第二代、第三代女作家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础。凌叔华对新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贡献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