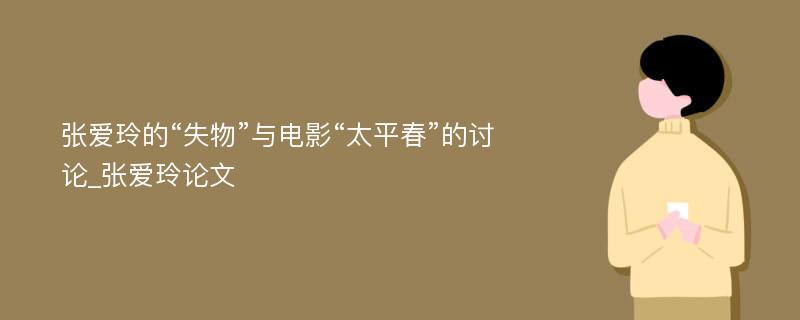
张爱玲《亦报》佚文与电影《太平春》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论文,电影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亦报》,意外发现张爱玲的一篇佚文:《年画风格的〈太平春〉》(以下简称《年》),署名“梁京”,发表在《亦报》1950年6月23日第3版。兹辑录如下,以飨“张迷”和研究者,对于“还原”一个立体的张爱玲,也将大有裨益。
我去看《太平春》观众是几乎一句一彩。老太太们不时地嘴里“啧啧啧”地说“可怜可怜”。花轿中途掉包,轿门一开,新娘惊喜交集,和她的爱人四目直视,有些女性观众就忍不住轻声催促:“还不快点!”他们逃到小船上,又有个女人喃喃说:“快点划!快点划!”坐在我前面的一个人,大概他平常骂骂咧咧惯了的,看到快心之处,狂笑着连呼“操那娘”!老裁缝最后经过一番内心冲突,把反动派托他保管的财产交了出来,我又听见一个人说:“搞通了!搞通了!”末了一场,老裁缝在城隍庙看社戏喝彩,我从电影院看戏出来,已经走过两条马路了,还听见一个人在那里忘情地学那老裁缝大声叫好。又听见一个穿蓝布解放装的人在那里批评:“这样教育性的题材,能够处理得这样风趣,倒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与群众的心情这样合拍,真痛快极了,完全淹没在头两千人的泪与笑的洪流里。有一场气氛非常柔艳的戏,是小裁缝要写封家信,报告他将要结婚的消息。因为他不识字,这封信是由他的未婚妻代笔的。正在油灯下写信读信,忽然“有吏夜捉人”,砰砰敲起门来了,裁缝店的铺板门剧烈地震动着,那半截玻璃上映着他们俩的惊恐的面影,也跟着动荡。我看到这里,虽然是坐在那样拥挤而炎热的戏院里,只觉得寒森森的一股冷气,从身上一直冷到头皮上。
这一类的恶霸强占民女的题材,本来很普通,它是有无数的民间故事作为背景的。桑弧在《太平春》里采取的手法,也具有一般民间艺术的特色,线条简单化,色调特别鲜明,不是严格的写实主义的,但是仍旧不减于它的真实性与亲切感。那浓厚的小城空气,轿行门口贴着“文明空气,新法贳器”的对联……那花轿的行列,以及城隍庙演社戏的沧桑……
我看到《大众电影》上桑弧写的一篇《关于〈太平春〉》,里面有这样两句:“我因为受了老解放区某一些优秀年画的影响,企图在风格上造成一种又拙厚而又鲜艳的统一。”《太平春》确是使人联想到年画,那种大红大紫的画面与健旺的气息。
我们中国的国画久已和现实脱节了,怎样和实生活取得联系,而仍旧能够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这问题好像一直无法解决。现在的年画终于打出一条路子来了。年画的风格初次反映到电影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
文章将近900字,这在《亦报》可就是长文了。熟悉该报的读者都知道,《亦报》上的文章多半在四五百字之间。
“梁京”为张爱玲1949年后离沪赴港前的化名,就专业读者和“张迷”而言,已属ABC之类,毋需赘言。需要提醒的是,那段时期,张爱玲并非只在发表文章时才用“梁京”一名。1950年7月24日上海《解放日报》登出《出席本届文代大会代表名单》①上的“梁京”;1952年持香港大学复学通知书出境去国的“梁京”,以及在《亦报》写连载小说的知名作家“梁京”,都是同一个人。笔者视“梁京”为张爱玲之化名而区别于笔名,原因在此。
或许有读者会问,何以见得《亦报》上发表电影评论的“梁京”和写小说的“梁京”就是同一个人?谁能保证没有同名、重名的可能。略述背景,可知《亦报》上写文章的“梁京”,就此一人而已。
1950年3月21日《亦报》第3版登出广告:“名家小说,日内起刊,梁京作:《十八春》。”“梁京”一名见于《亦报》,此为首次。广告连载4天。其间略有变动,23日那天,改“日内”为“后日”,24日又改为“明日”,这天的报纸还在第3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叔红”的文章——《推荐梁京的小说》,全文如下:
一向喜欢读梁京的小说和散文,但最近几年中,却没有看见他写东西。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写作的意念,也许他觉得以前写得太多了,好像一个跋涉山路的人,他是需要在半山的凉亭里歇一歇脚,喝一口水,在石条凳上躺一会。一方面可以整顿疲惫的身心,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回顾和思索的机会。
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他的写作态度的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在风格上,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他独特的面目。他即使描写人生最暗淡的场面,也仍使读者感觉他所用的是明艳的油彩。因此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有时觉得他的文采过分穠丽了。这虽然和堆砌不同,但笔端太绚烂了容易使读者沉溺在他所创造的光与色中,而滋生疲倦的感觉。梁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并且为此苦恼着。
就一个文学工作者说,某一时期的停顿写作是有益的,这会影响其作风的转变。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的文章比从前来得疏朗,也来得醇厚,但在基本上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
我虔诚地向《亦报》读者推荐《十八春》,并且为梁京庆贺他的创作生活的再出发。②
言辞之中满含殷殷之情,显然出自知根知底的朋友手笔。
3月25日,《十八春》正式登台亮相,“梁京”及其作品迅速成为《亦报》读者的看点。自此,梁京与《亦报》如影随形,皮毛相存。《十八春》分317次载完,起于1950年3月25日,止于1951年2月11日。随后,《亦报》社趁热打铁,一面催促梁京修改《十八春》,准备出版单行本,一面鼓动其再给《亦报》写稿。大半年后,梁京再次露面,千呼万唤拿出一部中篇小说,是《小艾》——张爱玲离开中国大陆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该文从1951年11月4日起刊,至1952年1月24日止,全文共分81次载完。推出《小艾》之时,即是《十八春》单行本问世之际。《亦报》同仁为制造市场效应,吸引起读者眼球,搅起垂怜“梁京”的爱才之心,委实费了一番苦心。
《十八春》逐日刊登的那段时期,长于纸媒体经营的《亦报》编辑与爱玩噱头的读者联袂,唱和相随,一如梨园捧角,放言梁京的小说、十山(周作人)的散文、子恺的漫画,堪称《亦报》“三绝”,言下之意仿佛一颗文坛巨星将冉冉升起在《亦报》上空。“梁京”为《亦报》大牌作家,已是不争的事实,倘使有人再用“梁京”的名字给同一份报纸写稿,则负有欺世盗名之罪了。
若说《年》文发表在“梁京”声名鹊起之前,而以上结论则是建立在“梁京”名噪一时之后,故仍需进一步推敲。
再查1950年6月23日《亦报》第3版,《十八春》连载至第91次,竖排在右边第二条,接着就是《年》文。“梁京”的两篇文章紧紧挨在一起,约占版面三分之一,前者用手写体签名,后者署名铅字排印。署同样名字的两篇文章登在同一天同一版的报纸上,出版界并非绝无仅有,不过以新闻报道为多,副刊则少见。一般说来,同一刊物用了名字相同、身份不同的两位作者的来稿,简要介绍一下各自不同的身份,是编辑处理稿件时的常规,也不容忽视的责任。在著作者权益还受法律保护的1950年代初期,《亦报》编者没有任何违规操作的理由,何况“梁京”的连载小说,已经刊载91次之多。《年》文作者“梁京”即为张爱玲,至此,已经毋庸置疑。
综上,张爱玲在上海解放后至出境前公开使用化名“梁京”的事实一清二楚,而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梁京”只是张爱玲用过一次的笔名。③
前面所录《推荐梁京的小说》一文作者“叔红”,乃是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桑弧(1916-2004)的笔名。④
桑弧与张爱玲本来就是一对很好的搭档。1946年夏秋之间,上海文华影片公司甫一成立,即聘黄佐临、桑弧等为导演。为了拍片,柯灵介绍桑弧和公司负责宣传策划的龚之方一起去找张爱玲,请她为文华影片公司写剧本。次年,文华影片公司出品的处女作《不了情》问世。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陈燕燕、刘琼领衔主演。影片十分卖座,片商与主创人员深受鼓舞。一片喝彩声中,张爱玲再接再厉受桑弧之邀,一气呵成,写成轻喜剧《太太万岁》。1947年末,《太太万岁》就上了银幕,⑤观众好评如潮赞不绝口。桑弧与张爱玲因拍片而频繁交往的事实,就被好事者演绎为两人恋爱的绯闻,并迅速在沪上影剧娱乐圈和桑弧的朋友中间悄悄地传播。⑥
而《太太万岁》上映后(1947年)至《十八春》(1950年)发表前,张爱玲无声无息,研究界语焉不详,实际上另有隐情。笔者在《〈亦报〉及其重要作家研究》一书中另有论述,在此不赘。
桑弧推荐“梁京”新作,并说:“我虔诚地向《亦报》读者推荐《十八春》,并且为梁京庆贺他的创作生活的再出发。”桑弧替张爱玲鼓劲的话,也不妨视为作者的自励。政权易手、社会文化转型之际,哪一个作家、艺术家不面临着重新选择和“创作生活的再出发”呢?
如果说张爱玲“创作生活的再出发”从《十八春》发端,那么,《太平春》则是电影导演桑弧艺术生涯的一个“拐点”。⑦
读者耳熟能详的《十八春》,毋需在此饶舌。介绍一下如今除中国电影史研究学者外鲜为人知的《太平春》,倒是很有必要。
浙江东部某小镇一间缝纫店的老裁缝刘金发夫妇与女儿刘凤英一家三口带着住店学徒张根宝,凭手艺谋生,以忠厚传家。根宝与凤英,两小无猜,亲如兄妹。男的勤奋肯干上进好学,女的楚楚可怜朴实纯情,全家老少其乐融融。老裁缝把爱女许配给身边的徒弟,乡绅赵老爷觊觎凤英,却无从下手,勾结军官王团长暗设奸计,强抓根宝充作兵丁。凤英忍辱含垢,骗过赵老爷,救出张根宝。赵家派人来接凤英,花轿中途掉包,根宝带着女友逃走。老裁缝和暗中支持根宝的街坊被赵老爷投进监狱。
解放军的渡江战役打响,赵老爷一家急于逃命,赵太太释放了老裁缝,说了许多好话,送他不少钱物,金银细软托他保管。小城解放后,根宝和凤英都回来了,失散的一家重又团聚,开始了新的生活。糊涂的老裁缝一直当赵太太为“救命恩人”,恪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古训,死心塌地替她保管财物。根宝与凤英婚礼前一天,根宝家乡遭国民党匪机疯狂轰炸,亲娘死于非命,家园夷为平地。噩耗传来,执迷不悟的老裁缝在现实教训下终于觉悟。如数交出赵家嘱他保管的钱财,政府给了一笔奖金,全部买了折实公债,一个旧人物完成了向时代新人的蜕变。
恶霸强占民女的母题,民间故事中常有,桑弧巧运匠心,将事件置于抗战结束后到华东解放的背景中,植入识字运动、反轰炸、推销公债等特色鲜明的时政元素,强烈的现实感扑面而来。编剧的意图是借老裁缝的际遇表现旧人物在新旧交替时代的转变。
江山易帜之际,以满腔热情投身新时代的青年导演,无疑期待着重现举座哗然的喝彩,一如当年《不了情》、《太太万岁》上映时万众瞩目、精彩纷呈。就桑弧而言,新的艺术旅程刚刚开始,往后的路很漫长。意外的是,编导桑弧却在《大众电影》第1卷第2期发表近乎检讨的《关于〈太平春〉》⑧一文,就该片作自我批评。字里行间弥漫着无法言说的沮丧,自认这是一部失败之作,说影片“并没有把所谓新旧道德标准交替这一主题适当而尖锐地给表达出来”,故事和人物缺少生活基础,真实性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此其一;掺进现实素材太多而缺乏筛选和提炼,浮光掠影取代了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此为二。挖出思想根源在于“创作态度不够严肃”,以“避重就轻”为“藏拙”,而这种“躲懒的办法”实在不足为训。作者最后表示:“热切地期待着观众对于《太平春》的各方面的批评,我并当益自奋勉,以冀今后能呈现出比较进步的作品。”⑨
张爱玲的《年》文描绘影院现场的“观众是几乎一句一彩”。她“从电影院看戏出来,已经走过两条马路了,还听见一个人在那里忘情地学那老裁缝大声叫好。又听见一个穿蓝布解放装的人在那里批评:‘这样教育性的题材,能够处理得这样风趣,倒是从来没有过的。’”
或许有人认为,极平实的事件,在富于煽动性的张爱玲笔下,都能给人极强的感染力,因之,张爱玲的记述,大可不必过于较真。然而,假如能够证之以官员在公开场合的意见,读者就不必怀疑《年》文不事铺陈的写实性。
1950年6月25日《文汇报》社举办本市文化首长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夏衍部长和姚溱副部长应邀出席,两位主要官员都在会上公开谈论《太平春》,明确表示意见,夏衍肯定“本片在小市民中起过很大的教育作用”,“姚副部长说:据我所知,广大小市民观众不但喜欢这个片子,而且也能够接受它的政治内容。”⑩
一边是观众叫好又叫座,一边是导演如临如履诚惶诚恐地自我检讨、深刻反省。就此推断,桑弧自觉失败多半不是出于艺术追求的自觉,而是受制于敏感的政治嗅觉。《关于〈太平春〉》是导演的创作谈,全文几乎不讨论与电影艺术本体相关的话题,反省的精神指向在于电影艺术家怎样才能正确运用阶级论原理,重建符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创作价值观,并以此指导自己的一切艺术活动和文化实践。简言之,离开电影的大众文化属性,单纯强调影片的社会价值、教育作用和宣传意义,是桑弧此文的要旨。
桑弧的履历告诉我们,走进摄影棚之前,他是一名银行职员,受好莱坞电影氤氲长期熏陶,熟悉文化市场的基本法则,尤其是执导《不了情》、《太太万岁》取得巨大成功后,更是积累了丰富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从艺多年的一个职业电影导演,忽然抛开曾经十分娴熟的语码,改用完全陌生的一套话语系统,不难推断,这种反常现场并非来自主体内在的精神自觉,源于执政当局压力的可能性很大。
如前所述,夏衍和姚溱对《太平春》都发表过积极的肯定性意见,一般都能体味到保护桑弧的用意。6月26日,柯灵写给黄佐临、桑弧的信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而且,他们的讲话就是针对6月24日发表在《文汇报》上批评《太平春》的两篇文章,即梅朵的《评〈太平春〉》和黎远冈的《对〈太平春〉的几点意见》。
梅朵的文章,言辞非常激烈,严厉批评影片编导不了解反动阶级的罪恶本质,犯了温情主义的错误,违背生活逻辑和人物的阶级属性,“失掉了对赵老爷及赵太太的这一类的阶级应有的立场”。概括地说,影片人物虚假,胡编乱造,耍弄“趣味第一”的商业噱头,偏离了教育和改造落后小市民的目的。(11)
调门一致的黎远冈认为,编导“没有深入体验现实生活”,不能看出“这新的社会带来的质的变化”,“不少情节依然是在上海亭子间里的凭空臆造”,无论其主观上怎样努力选择一个正确的主题,但由于缺少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作支撑,仍不免陷入“用动听的口号”践行主观说教的概念化泥淖。(12)
如果说声称与桑弧且有一面之谊的黎远冈,是否代表组织,尚难找到证据,那么,负《大众电影》主编之责的梅朵在文章中表达的意见就不仅仅是个人见解了。这些,恰好也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桑弧因编导《太平春》所遇到的压力果真不小。
所幸的是,桑弧背后还有夏衍的支持。柯灵1950年6月26日写给黄佐临、桑弧的信告诉我们,夏衍直截了地指出,“《文汇报》上梅朵对《太平春》的批评是不正确的”,“以桑弧过去的作品来看,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应当肯定地加以赞扬。它有些小毛病,但并不严重。”姚溱则认为,“这是私营电影公司出品中的一个很大的成功。”并说,对桑弧应该大力鼓励。(13)
山雨欲来的批评,因上海市最高文化长官的干预,悄然之间平息了,剧组人员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张爱玲作为一名普通市民观众,写作影评全然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她与桑弧曾因编剧和导演的成功合作,建立起极好的友谊,并且,桑弧还为她“创作生活再出发”击鼓摇旗。桑弧迎接新时代的第一部影片问世之时,以同样的热情回馈对方,正是人情之常。
尤其须要重视的是,张爱玲的影评发表在桑弧的检讨之后,梅朵等人的批评之前。
可以肯定张爱玲不可能事先获知政府当局对《太平春》的态度,因此,她或许只是从桑弧自我批评的文章中敏感地察觉到,编导似有解不开的心结。于是,借发表影评分轻一点桑弧肩上沉重的精神包袱。张氏抓住桑弧文中所谓“我因为受了老解放区某一些优秀年画的影响,企图在风格上造成一种又拙厚而又鲜艳的统一”做文章,不无夸张地赞誉电影《太平春》在“年画上终于打出一条路子来了”。
自诩“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的张爱玲,(14)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敏感的聪慧女子。因此,她提取关键词“解放区”、“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盛赞“年画的风格初次反映到电影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并以此证明桑弧在新时代面前努力学习,积极改造的成效。张爱玲在激励桑弧,欣赏影片拍得有趣的同时,又真正做足了迎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姿态。
以上所述表明,1950年6月关于电影《太平春》的讨论,旨在消弭上海电影观众的好莱坞趣味,赋予国产电影服务工农兵,教育、改造市民群众的价值规范,以国家意识形态教科书的知识性、工具性取代大众文化产品的娱乐性、休闲性和商品性,预示着一种新的艺术规范和美学原则正在悄悄生长。这场讨论其实也是1949年后,文化市场构建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受行政权力掌控的知识/文化生产新机制最早的文化实践活动之一,在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转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熟谙文化/艺术生产规律和法则的夏衍,是上海和华东地区主管意识形态生产的最高行政长官。艺术家率性而为的气质和文化官员的双重身份,成为他力排众议,坚持按文化市场规律维护创作自由的思想动力。但是,夏衍并不能真正逆转大局,只能极有限度地延缓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转型的进程。后面随之而来的关于电影《武训传》和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和核心人物直接介入,行政手段强行进入,夏衍也不得不作公开检讨。知识/艺术生产新机制的美学实践很快被顺利推进到全国各地,到1952年底,知识/文化生产新机制的转型全面完成。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关于电影《太平春》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国家新的政权建立之后,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转型中一次不很成功的演练。
张爱玲撰文评影,源自其对桑弧的感念,本意不在辨明是非对错,然而,却与桑弧向读者郑重推荐《十八春》的文章,构成参差对照,为破解张氏与桑弧之间的秘密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从《推荐梁京的小说》一文很容易推知,《十八春》正式发表之前,桑弧事先已经读过,即便是边写边登,未能事先读到全书,至少业已获知全书的结构、思路和人物命运的走向、结局。不然,桑弧凭什么得出结论,“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还振振有词地说:“我觉得他的文章比从前来得疏朗,也来得醇厚,……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
异曲同工的是,短短几百字的《年画风格的〈太平春〉》一文,也释放出密集、丰富的历史信息,坦然率真的言语之中,鞭策激励奖掖褒扬兼而有之,适度的张扬称赞,证实张氏有意携手桑弧解除精神苦闷走出情绪低谷度过精神和艺术的双重危机,惺惺相惜之意清晰呈露。可见,《太太万岁》完成之后,张、桑两人虽然未有继续合作,但两人之间一直保持出入相扶、精神守望的情感关系,却是毫无疑义。据此,张、桑相恋的传闻,是否确如知情者所言,冤枉了桑弧,(15)便须重新考量。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推断,张爱玲与桑弧即便没有坠入爱河,起码也曾有栽花之意。名噪一时的女作家与才华出众的电影导演情缘不了,不但于他们的形象无损,反而有助于重建江山易帜之际的历史现场。张氏生活、思想的复杂性和波动性及其多维繁复的相貌,因而得到更好呈现,并为揭开女作家神秘离开大陆的谜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注释:
①指1950年7月24-29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根据《出席本届文代大会代表名单》,“梁京”的名字列于“文学界”代表中,按姓氏笔画排序如下:“唐弢、师陀、倪海曙、梁京、孙大雨、孙席珍、孙福熙、郭绍虞、许杰”等。
②作者用“他”而不用“她”,实为“别有用心”。
③杜英在《从〈十八春〉的修订看解放初期的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梁京”是当时张爱玲“仅用过一次的笔名”。
④陈子善:《〈亦报〉载评论张爱玲辑录》,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4月号,参见陈子善著《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7~138页。
⑤《太太万岁》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石挥、蒋天流、张伐领衔主演。1947年12月14日在上海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同时上映。
⑥(15)龚之方:《离沪之前》,见关鸿编选《金锁沉香张爱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⑦《太平春》是上海文华影片公司1950年的出品。桑弧编导,石挥、上官云珠、沈扬领衔主演。他们在片中分别饰演刘金发(老裁缝)、刘凤英(老裁缝之女)和张根宝。
⑧《大众电影》(半月刊)1950年6月1日上海创刊。主编:梅朵、王世桢;编辑委员:夏衍、于伶、叶以群、顾仲彝、柯蓝、梅朵、王世桢、张可奋、刘北汜、金欣等。
⑨《大众电影》第1卷第2期的出版时间是1950年6月16日。
⑩(13)唐文一编:《柯灵书信集》,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112页。
(11)梅朵:《评〈太平春〉》,《文汇报》1950年6月24日。
(12)黎远冈:《对〈太平春〉的几点意见》,《文汇报》1950年6月24日。
(14)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张看》(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