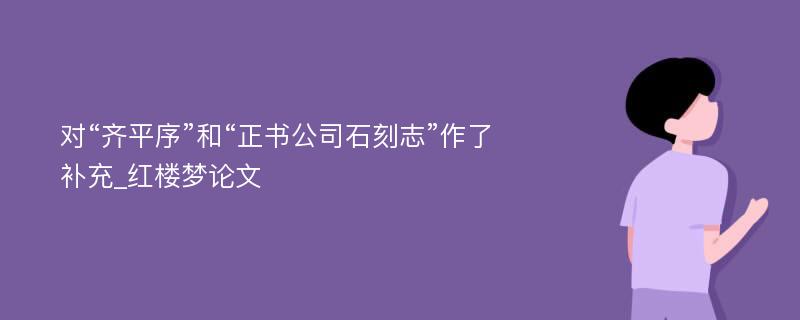
有正书局《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底本补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本论文,书局论文,石头记论文,戚蓼生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的特殊地位,学界早有共识,毋须赘述;其文本(包括评、批)价值,自鲁迅先生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小说史略》有关引证悉以此本为据,素来得到广泛关注。这样一个重要版本的“来历”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是理所当然的。
1954年一粟《红楼梦书录》首先著录,指出“此本俞明震旧藏,后归狄葆贤,据以石印”,这就是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有正书局印行面世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大字本(上半部),下半部于民国元年(1912)出齐。
周汝昌1963年4月旧稿、1973年4月稍加扩展的《戚蓼生与戚本》作为《红楼梦新证(增订本)》附录(1976年4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进一步指出,石印戚本的底本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俞明震旧藏。一说乃夏曾佑(穗卿)旧藏,售于狄手,狄付石印”。
1975年冬,上海古籍书店书库发现十册《石头记》前四十回的抄本,魏绍昌先生亲加目验复多方审核,撰文认定“此抄本确确实实是有正本据以翻印的底本”,文章先在南京师范学院《红楼梦版本论丛》刊发,后于1979年第二辑《红楼梦学刊》正式发表。文章对抄本所钤四方印章详加考证分析,指出此本初为安徽桐城官僚世家、相国后裔张开模珍藏,后经辗转归于有正书局狄平子(葆贤、楚青)所有,始得石印面世;同时对从张开模到狄平子转手过程之中曾经收藏此本者或说俞明震(恪士)或说夏别士(曾佑)这“两种说法”作了较为详尽的客观介绍。
笔者对上述“两种说法”分别进行查考,陆续发现几项材料,认为可以肯定由张到狄之间的一位“二传手”,只能是俞明震,而不可能是夏别士,后者的“疑案”可以完全排除。特作“补证”,公诸同好。
现已查明,一粟《红楼梦书录》所说,有正底本原系俞明震旧藏,源自王伯沆,初见于王氏对“王希廉本”“读法”所加四条批语之后的一段记载。这一记载提供的信息,出自王伯沆与俞明震的直接交往,属于亲目所睹的第一手证据,确凿可靠,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笔者发现的几项材料与之互为参证,可以进一步予以证实。
王批王希廉《新评绣象红楼梦全传》今藏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共二十四册。第一册“卷首”原缺,用1905年王希廉、姚燮合评《增评补图石头记》补配。王氏对此本精读二十遍,历时二十四载,分用五色笔五次作评点。卷首《读法》王氏以绿笔加批四条,其后又有一段独立成段的墨笔记载〔1〕。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全文照录如下:
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本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读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语与恪士,恪士亦谓然也。(重点笔者所加)
《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1985年1 月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曾参加“王批”的部分过录。以上所引见于原书第一册第二页正面,江苏古籍版第二页。
这里有几点值得特点注意。
首先,据魏绍昌先生介绍,1973年1 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艺林丛录》第七编吴则虞《记夏别士》一文说:“有正书局影印戚本《红楼梦》,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别士……”;又,郑逸梅说,包天笑在香港发表的《钏影楼回忆录》则说,狄平子是从北京购得。虞说言之凿凿,不仅卖方买方俱全,而且列出价格金额。包天笑曾受聘于狄平子的时报社和有正书局,一度共事而朝夕相处,所言应当有根有据。但是虞、包二说不一,甚至存在矛盾,令人难免莫衷一是,信谁是好?王伯沆却说得明明白白:“余曾见之”,既有对抄写字迹的评价,还有对装帧的具体描绘。细加比较不难判断,虞、包似乎仅只耳闻,其可靠性可信性自不能与王氏之目睹——“见之”相比。
其次,王氏子“见之”之后紧接着写道:“后恪士以赠狄楚青”,文气上下贯通。俞恪士“以赠狄楚青”的同“余曾见之”的是同一部书,是为前因,其直接后果则是“遂印行”。于是,俞之所藏与狄之所印,二者的承传关系也随之交代得清清楚楚。
再次,惟其因为王氏深悉“来龙”,所以更加关注“去脉”,有正本一旦出版,他即得此本而与自己所藏的王希廉本“互读之”。比较的结果:其一是“已非原稿影印”,这是指有正本已经经过书局的某些技术处理,当然还应当包括多出来的狄平子所加若干眉批;其二是根据王氏的阅读、接受,印象是有正本“竟不逮百二十回本”。经过互读比较的评价,迫不及待地告诉原藏书者,既合情又合理,是乃顺理成章。“曾以语与恪士”结果是“恪士亦谓然也”,英雄所见略同并无强加之嫌——像今天似的。所有这一切表明,如果这有正书局印行的八十回本的底本不是俞氏旧藏,王先生的文章决不会这样写。
以上各项必须具备同一前提:王、俞之间定有非比一般的深厚友谊。事实正是如此。
王伯沆名瀣(1871—1944),是著名学者,是“博通经史小学、各体诗文、下逮说部,莫不精究”(受业弟子王焕镳语,见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3.4合期), “举世共仰”的“一代通儒”(唐圭璋语,见同上1982年7.8合期),早已名满大江南北。 俞明震字恪士号觚庵(1860—1918),以光绪十六年(1890)三甲六十二名进士授选庶吉士,后署赣南道;是康梁变法的积极支持者,戊戌(1898)后任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鲁迅就读该校时曾看见他手上拿着《时务报》坐在马车上看, 当属候补道中的新派人物。 宣统二年(1910)调任甘肃提学使迁布政使,入民国为肃政使。在他任职南京时,出于对王伯沆声望学识的敬重,聘为学堂教习。两人相交甚笃,过从甚密,时相唱和。王诗《初夏偕友登扫叶楼颇感旧游,晚循冶城至图书馆小饮,因赋三首》其一,有自注云:“与陈伯严(三立)、刘幼云、胡漱唐、俞觚庵(明震)、陈苍虬诸人屡游此”。“同光体”代表诗人陈三立(伯严)《散原精舍诗续集》有《癸丑(民国二年,1913)五月十三日至焦山,同游为陈仁先、黄同武、胡漱唐、俞恪士、寿丞兄弟,越二日王伯沆自金陵来会。凡三宿而去》诗,正可对参。直到1918年俞明震逝世,王伯沆还作有《挽觚庵》七律二首:“把君乳酪三旬别,夸我西湖百态浓。……青溪又是梅花发,忍挂霜镡吊冷踪”。其中寄托了无穷哀思,同时表明他们之间的交谊时间之久,如果初交始于俞之供职南京,那么在俞明震西去甘肃以及其后称病归里以后,他们都还保持着联系,过从不断,一直延续到俞之逝世。
王伯沆与俞明震、陈三立两家同时相洽,更有另一层因缘。俞陈两家三代世交又是两代姻亲,陈三立续弦夫人俞明诗是俞明震胞妹,则堪称联结两家之“关键”。陈三立光绪二十七年(1901)移家南京定居之初,曾设立家塾延师课子,王伯沆以久负诗名入选而聘为西席。陈寅恪先生作为三立公之子正是于此时执经受业。王氏后来受聘于俞明震并从而成为好友,很可能就是由于至亲之举荐绍介。
诚然,王氏以墨笔补记此事,可能在1927年之夏也可能在1932年冬,相去有正本初版面世已历十几二十年;但是比起吴则虞之《记夏别士》和包天笑之《钏影楼回忆录》却早出整整四十年。由此不难引出结论:博闻强记而享有盛名的一代通儒,后来成为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中央大学著名教授的王伯沆,以其同陈俞两家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一部抄写甚精、而行世后产生巨大影响的戚序本《石头记》原收藏者的记忆,实在没有理由提出怀疑与异议,更何况这是一部他“曾见之”而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呢!更须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段“补记”并不是突然心血来潮无的放矢的随意笔墨,而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是针对王、姚合评的《增评补图石头记》读法第二十五条“有谓此书只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与?”而作。先是,已用绿笔批道:“此书(后)四十回确系高兰墅先生所增,见张船山《诗》注,高与船山相友,此言必不妄。”是对“此何言与”针锋相对的回答。相隔数年之后,再次精读细批,重读“绿批”感到意犹未尽,才又以墨笔补记。尽管依于伯沆的阅读感受,认为八十回本“不逮百二十回本”,但是他尊重事实而并无偏见,所以郑重指出确有八十回本在,而后四十回“确系”高鹗增补,是对“是何言与”的再次回答。这样才引出俞恪士所藏原书“以赠狄楚青,遂印行”的一段故实。这段“补记”之中正凝聚了一位真正的学者的严谨学风,其以确凿事实为论据的严密论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令人钦佩。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笔者还发现一条虽有人提及却未予足够重视的材料,堪称一条重可千钧的铁证。
王伯沆受业弟子、俞明震的嫡亲外甥、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首章,在述及该书编著缘起时,有一段话恰与王伯沆殊途而同归,把有正本底本原藏者都“归”到俞明震的名下: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舅伯山阴俞觚斋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自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3页
陈寅恪先生八斗五车之才学,早已名震海内外,兹仅略举一端。自称与寅恪先生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的俞大维,在台湾出版的《陈寅恪先生论集》卷首《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以如此超乎常人的记忆力,述及撰著《柳如是别传》缘起,是由于从伯舅俞氏藏书中读到钱遵王注《牧斋诗集》“大好之”,从而深入研究钱、柳情缘所致;那么,当他同时忆及当时还读过另一“精本”戚序《石头记》,显然不是随意涉笔,而是出自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于“四十年前”则是取自成数。《柳如是别传》完稿于1964年,开始着笔则在1954 年。 有正本分上下两集各十册先后出版于1911 年和1912年,下推四十年已是五十年代,时间衔接是大体无误的。
据蒋天枢先生编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01年陈寅恪随父陈三立定居金陵时,年方十二岁,十八岁考取上海复旦公学,其间十三至十六岁随兄衡恪(师曾)东渡日本留学,十五岁暑假回国考取官费,冬初返日,次年冬复因病回国休养。则仅十二岁一年时间较为集中,便于家塾课读之余终日埋头家藏极富的珍贵古籍,并且为了宽释幽思“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于是就近到衡宇相望的伯舅家遍览精本,接触戚本当在此时:所以选择了“年在童幼”的准确措辞。其时,八国联军强侵北京的硝烟初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海外积聚力量、建立组织,逐步形成革命政纲,辛亥革命在表面的暂时平静之中酝酿。“海内尚称安,而识者知其将变”的时局判断与当时的形势发展完全吻合。因此,当时虽在童幼之年,却已有所觉察,有所感触,故能深深铭记而久难忘怀,直至五十年代仍似记忆犹新。至于所述俞氏收藏之原委,更令人确信不疑:时间——官翰林即被选授庶吉士之时;地点——京师海王村,正是著名的书肆集中所在;价格——三十金。伯舅亲口所说,外甥亲耳所闻,消息来源真实、具体,当然更加可靠。相形之下,郑逸梅转述的包天笑所谓狄平子“从北京购得”的传闻,吴则虞所谓“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别士”之所据,自然成了乌有乡故事,又怎能与可以背诵大部分十三经的陈先生的记忆同日而语!
再考俞明震的宦迹履痕, 此公离江南而西去甘肃是在宣统二年(1910)。王伯沆所说,俞以所藏戚序本“赠狄楚青”,当然只能在此之前。狄得此本,由珍爱而起意印行,进而进行策划、准备、到技术处理、上石付印,在本世纪之初的条件下,这一过程不可能太短;加之他煞有介事地要在原有批评之外加上他的若干眉批,恐怕少不了须经一番苦读苦思,斟酌推敲,决不能一挥而就。假设以上两个方面所需时间在一年以上,大概不能认为是过宽的估算。有正本上集十册出版于宣统三年,下集十册出版于次年。那么,俞之“赠”狄肯定还在俞西去甘肃之前的某一年或者更早,这样,王伯沆的“见之”、陈寅恪的“纵观”,也就完全接榫而合符了。
以上“补证”,管窥蠡测,尚祈方家教正。
注释:
〔1〕王氏“五色批”卷末一一注明年代, 始于1914 年夏, 终于1938年冬, 绿笔作于1921 年春1922 年冬之间, 墨笔批语一次完成于1927年6月,一次完成于1932年冬, 这里所引“墨笔”记载的确切年代难以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