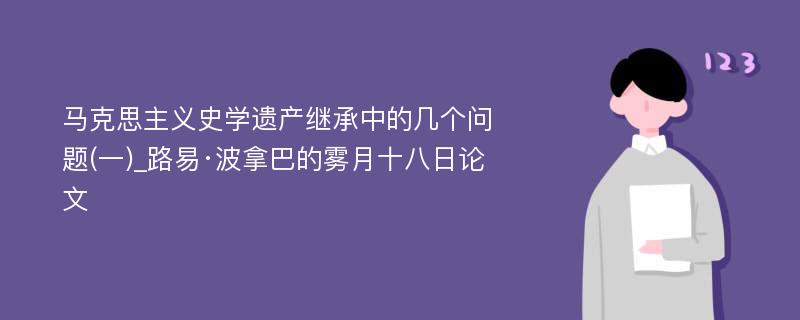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在马克思留给后世的宏富的精神遗产中,也包括他为我们留下的一份丰厚的史学遗产,这正如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1]。我个人以为,无论是对马克思史学遗产的深入发掘,还是对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认真盘点,都是颇有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试作论述马克思的史学遗产;第二部分就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第三部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的发展,侧重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取向。拙文旨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作些补白,鉴于这方面学力不逮,祈望识正教正。
一
何谓史学遗产?前辈学者白寿彝多有论述,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连续发表的几篇著名的深入浅出的“答客问”,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2—p5]。时贤瞿林东进一步对“史学遗产”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2—p1]倘此义可取,本文所说的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也是他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与积累。不言而喻,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的名字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他的生涯中,也有“史学活动”,也有为此而作出的具体的史学研究工作。
毋庸置疑,马克思留给后世的史学遗产,应当包括他的历史理论,就其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而言,这当然指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可以这样认为,由马克思所奠立的唯物史观,是世界史学史上最为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观),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一种科学的归纳与总结。
但倘若我们把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仅仅归结为唯物史观,这是不够全面的。在丰富的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中,还包括他的史学理论(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的史学理论研究兴矣。在学术讨论中,史学界人士感到有必要把历史理论(关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问题)与史学理论(关于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相区别,把史学理论单列出来,以获得专门的关注。当然,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它们因各自研究的对象不同而有差异,但又互有联系。参见当时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这里所说的“史学理论”,指的是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大体说的是历史认识的主体(主要为历史学家)和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的客观实在性)之间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学界,似乎还缺乏从这一视角论述作为历史学家马克思的卓著业绩与杰出史才。(注:即便是国际学术界,也不多见。例如G.A.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Clarendon Press,Oxford,1978.),涉及的也多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意在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辩护,而鲜有探讨马克思的史学理论(本书已有中译本,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我们在《西方史学史》第七章近代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节中,论述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而非狭义的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史学理论),这也是有待增补的(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第267—279页)。)
拙文有意在这方面作些补充。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他一生写下了诸多的历史著作或准历史著作,在这里,我只能采取“管窥蠡测”的方式,选择被恩格斯称之为“天才著作”[3—p582]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个案,我以为选择这部著作以了解马克思的史学活动与史学才能,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从中可以观照马克思的史学理论,可以知晓马克思是如何运用丰富的材料和已有的知识,去认识与分析事件和人物,可以领略马克思是如何运用历史编纂的才能撰写历史,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
1851年12月2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次年1月通过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这个事变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好比是“晴天霹雳”,“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注:见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写的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写的第二版序言中,曾提到与他同时出现、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两部著作:一是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他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雨果的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一是蒲鲁东著的《政变》,他对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0页)。)。而马克思则不同。由于他对法国历史了然于胸,对相关史料谙熟有加,更在于马克思对当前所发生的事变有一种深刻的考察。因此,当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或即将终结时,马克思就能从总体上考察它的进程,预测它的结局,既不为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为它的迂回曲折所惊愕。这只有天才的历史学家才能做到。在西方史学史上,古希腊时代卓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具有这样的史才,这种为后人所叹服的才干,他的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确可“垂诸永远”的[4—p18]。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确可与修昔底德相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这种令后世历史学家叹为观止的才干,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为“活生生的时事”(第582页);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则译为“当前的活的历史”(第601页)。两相比较,似乎1972年版的译法——“活的历史”更为精当确切一些,不过以下译文大体上仍是依据1995年版本,在个别字词句上酌情采用1972年版本的译法。)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3—p582]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即时史”(当代史)。当代法国新史学家让·拉库蒂尔在《即时史学》一文中指出,即时史学不是研究“已完成的变化”,而是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学科(注:让·拉库蒂尔:《即时史学》:载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另,让·拉库蒂尔在列举即时史的作品时,显然提到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即如恩格斯所说的“活的历史”。马克思适时地将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写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名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不仅是一部阐发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文献,而且也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史学研究工作,用法国这一时段的历史研究成果去验证他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史观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亦即历史著作的编撰原则与撰史技艺,则关乎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这当然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倘若我们有意从历史著作的角度,重读这部名著,就可发见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禀赋。笔者眼力不健,仅就个人管见,在丰润的马克思史学睿智中,撷取数项,以见一斑。
叙事有条不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共七节,以时间为序,逐一写来。结构详略得当,略处惜墨如金,如对二月革命时期的情况,仅用1页;详处不惜笔墨,如对立宪共和国和立宪国民会议时期的描述,篇幅甚多。尤其是它的开头与结尾更是匠心独具,令人心往神驰。全书以人们现已熟知的黑格尔之论开篇,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紧接着写道:“他(黑格尔)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5—p584]这种开篇,出手不凡,紧紧地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部著作的结语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5—p688]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已经实现了。头尾衔接,天衣无缝,行文有序,一气呵成。
叙论结合。马克思在书中的议论,不是孤立的,它组成为整个叙述中的一个有机整体;论断与叙事的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又常有神来之笔,恰到好处。诸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5—p585]、“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5—p585]、“历史真能捉弄人!”[5—p619]“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翻译成“人生观”,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翻译成“世界观”(第629页)。“人生观”“世界观”这两种译法似乎是依据德文“Weltanschauung”一词而来。虽然单纯从文字上来看,“Weltanschauung”译成“人生观”、“世界观”都是可以的,但是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之中,译成“世界观”似乎更妥当一些。)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5—p611]等等,现都已被反复征引,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段)了。
叙事中的历史比较。由于马克思对西方历史了如指掌,在行文中不时穿插历史的比较,主要是把当前事变与西方古代以来的历史作比较,把近世欧洲历史与罗马古史作比较,把近代法国历史人物与英国历史人物作比较,运用这些历史比较方法,有力地强化了叙事中的历史感,往往可以达到难以忘怀的阅读效果。
叙事中的修辞艺术。在这方面,有两点尤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借助修辞学上的比喻(譬喻)辞格,那真是通篇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尤其是马克思活用古希腊罗马神话,书中的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5—p600]、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5—p628]、像“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5—p589]等比喻的运用,举重若轻,信手拈来,令人过目不忘。另一是借助修辞学上的排比辞格,那更是“通篇俯拾皆是”,限于篇幅,这里只引两例,足资说明。例一,为了说明《十二月十日会》这个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秘密团体之混杂,马克思这样写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5—p635]在这句里,除了马克思连用的两个“除了……”介词短句,接下竟连用19个定语以修饰“人群”,这个“群体”之驳杂、之浑浊、之污秽,跃然纸上!例二,马克思还擅用由虚词如介词、连词等组合的复句,进行排比,书中不断出现的“不是……而是”、“既不能……又不能”、“由于……”、“于是……”等开首的分句,常常连用五六个以上,这种修辞效果强烈而又痛快,读者更是欲罢而不能。
好了,我们不再作繁琐的援引,还是让我们去读一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吧。由此看来,马克思不愧为叙事高手、编撰巧匠、修辞行家、语言大师。简言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体确如当代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所说的,是一种“漂亮的风格”[6—p147]。什么“漂亮的风格”?伊氏未作论述。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著作,不只是在这里集中举例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包括他的其他历史著作,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乃至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其行文特点(或“风格”),倘仿照与学习马克思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可否作这样的描述:厚实而不失畅达、庄重而不失幽默、犀利而不失清逸、丰润而不失大气。伊格尔斯在说到马克思文体“漂亮的风格”时,说它的“解释”与“风格”胜过了奥·梯叶里、弗朗索瓦·基佐、路易·勃朗和洛伦茨·冯·斯泰因昔日按照阶级冲突对法国政治的分析[6—p147]。其实何止于此。马克思虽不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但就马克思个人而言,作为历史学家的他,其史才确可与前述伊格尔斯所说到的几位西方史家相比肩,还可与兰克、蒙森、米涅和巴克尔等19世纪西方一流史家相媲美,遑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历史著作中,他所淋漓尽致发挥的史学才华,完全是为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服务的。换言之,即是为了更透彻地阐明正在发生的“当前的活的历史”,为了更精确地刻画路易·波拿巴这个政治小丑和“骄横的流氓无产者”[5—p643]的形象,技巧与立场相关,手法与情感粘合,历史文本的内容与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这是我国史学上用来称赞史家才能的话,可见“叙事”与“良史”是紧密相连的。倘借用这句话来评价马克思的史才,也是适用的,马克思的确“善叙事”,他无愧为“良史之才”的称号。
二
马克思之后(注:本文所指马克思,往往也包括恩格斯在内,正如时贤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但又是同一种思想体系的共同创始人,这当然包括恩格斯对创立和捍卫唯物史观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参见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又,上个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出现了贬低恩格斯的思潮,同时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神话,显然是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参见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拙文在这里所说的,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与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陈述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笔者的思绪随历史的纵向推进而凝聚,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的进程中摭拾一二,略陈管见。
其一,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辨析与重评。
辨析意味着陈见与新知的变换,重评意味着真理与谬误的识别,辨析与重评是革故鼎新,是学术争鸣与学术研究工作双向回应的提高过程。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需要如此。我这里略举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年代里的一些事例以资说明。(注:本段所说的“辨析与重评”及下文所要说到的“回顾与总结”、“开掘与深化”,实际上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的各个时段中。这里所分,主要是为了说明题旨,出于写作的需要,但也兼顾到各个时段(或各个地区、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主要是它的唯物史观,开始在欧洲各国传播,德国的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法国的保尔·拉法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诸家,对此都作出过各自不同的贡献。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视角来看,他们对马克思史学遗产的传承与弘扬,由于众多的历史原因,对我们而言,或不甚了了,或曲解误读。这就需要我们辨析,作出新的评价。
例如对考茨基。关于考茨基,列宁的确早有定评,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这样写道:“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注: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和1972年第二版的《列宁选集》第3卷中均翻译为,“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1960年版,第675页;1972年版,第653页)。我们注意到1985年版的《列宁全集》第35卷中没有“可靠的”一词。在这里,引文虽然依据新版的译法,但俄文原文是否有“可靠的”这一意思,待考。)的财富。”[7—p269]然而,令人疑虑的是,在1914—1916年的战争以前,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考茨基,对于他的《基督教的起源》、《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社会革命》等“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的那些作品,有谁从历史学的角度作出过认真的辨析?考茨基这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已被“叛徒考茨基”恶名的单面性所掩盖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史学业绩因而也更被“叛徒考茨基”的恶名所掩盖了。对此,难道不需要我们从学科史的视域作出清理予以重新评价吗?
普列汉诺夫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因为他早年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贡献卓著。在史学界,也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传世名作。但倘若进一步追问,普列汉诺夫的史学思想是怎样的?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建树又怎样?这就有点若明若暗或一知半解了,这当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要紧的是,普氏的某些理论,如他与列宁的不少争论(如他所忧虑的“亚细亚复辟”等),似乎被一层历史的迷雾遮盖着,需要拨开迷雾,重新认识。(注:例如,1906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论争,以及随后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关于亚细生产方式的一些思考,都与列宁论见相悖。此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普列汉诺夫关于“亚细亚复辟”的忧虑果真是杞人忧天吗?对此,参见启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思考》,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4期。另,近又翻阅普列汉诺夫的名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不仅就如何估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发挥个人作用,普氏作出了精彩的阐述,捍卫与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本书虽经移译,其出色的文体与语言风格依然令人称羡。)
由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两例,还使我联想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那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倘不分前后(如不分早年的与晚年的)、不加分析(如不分政治的与学术的),一刀切下去,不作实事求是与历史主义的分析,焉能不错?在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行程中,倘用这种态度对待诸如像考茨基那样既背上“叛徒”恶名又负有“史家”身份的历史人物,那么就很有可能错失或遗漏很多有用的东西,而有误于我们的传承大业。
其二,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回顾与总结。
回顾意味着过去与将来的对接,总结意味着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回顾与总结是反思重建,是学术积累与学术研究工作互相影响的提高过程。传承马克思史学遗产也需要如此。我这里仅以20世纪苏联史学的兴衰得失作一说明。
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中,苏联史学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史学界曾拥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世界现代史学尤其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8]。如今,苏联这个国家虽已解体,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份遗产,并不为之消失,对我们来说,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如刘家和所说,“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验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极有价值的理论遗产。”(注:见陈启能、于沛、黄立茀:《苏联史学理论》,专家推荐意见书(一,刘家和),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回顾与总结苏联史学和史学遗产是一个值得重视而又颇具难度的学术课题,目前出版的陈启能等三人合著的这本专著,和陈启能等多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还只是初步,仍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因此,为了回顾与总结,这里截取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的若干断面,略见这种前行中的坎坷,发展中的磨难。
断面之一:一桩冤案。
这里所说的“一桩冤案”,指的是波克罗夫斯基冤案及其平反昭雪[9]。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其中他的《俄国历史概要》曾得到列宁的赞许。事实上,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波克罗夫斯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当然,在他的史学理论中也有不少错误和缺陷。早在20世纪30年代,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最后由思想批判发展为政治斗争,波克罗夫斯基俨然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使不少历史学家遭到了灭顶之灾。直到1961年,苏共22大才为波克罗夫斯基恢复了名誉,推翻了当年加在他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
波克罗夫斯基的冤案,令后人生发出许多感慨:能用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上线的非学术手段解决学术问题吗?在这种不正常的批判中,那种用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更不知桎梏了多少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的智慧;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也不知伤害了多少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心灵。从这一绵延将近30年之久的事件中,我们觉察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进的同时,曾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
断面之二:在“解冻”的冰层下面。
1956年,苏共20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在思想文化领域,首先在文学领域出现了“解冻”。在史学界,也开始清理与消除个人崇拜及教条主义在史学中的影响,其高潮是1962年12月举行的全苏历史学家会议。“拨乱反正”的清风,曾一度激活埋在冰层下的细流。不是吗?如历史方法论(注:在苏联史学中,所谓“历史方法论”,其内涵与外延较为宽泛,它常与历史认识论有重复,甚至还包括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E.M.茹科夫著的《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就有一半以上谈论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出现研究热潮,又如比较研究方法、计量研究方法等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鲜有突破。实际情况是,苏联历史学家即使在“解冻”时期,他们仍在苦苦求索,更不必说在斯大林高压政策时代下的历史学的境遇了。
须知,包括史学文化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繁荣,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是,在它那里老是阴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几番急风暴雨,催落花枝凋零,遑论于风雨憔悴中煮字烹文。多年来,苏联历史学家正是在这种“阴晴不定,冷暖失常”的学术环境中,备受折腾,努力地寻求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价值与自身地位,痛苦地挣扎,坎坷地前行。这种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断面之三:“历史热”。
苏联史学中出现的“历史热”,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在戈氏改革“新思维”的推动下,“重写历史”与“填补空白点”的舆论,由上而下,由于媒体的渲染,扩之社会,延及全民,日见张扬,至1989年达到高潮,连那些行动迟缓的历史学家也被时代的浪潮裹挟进来了。短短几年,被发现的“空白点”如此之多[10—p289~292],以至苏联历史都需要重新改写。对此,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道:“正是在苏联官方的鼓动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10—p289]由“历史热”所不断引发出来的“空白点”,致使人们疑团丛生,思想混乱。后来,这种“历史热”也伴着苏联的解体,宣告结束,大潮退后,剩下的是历史的泡沫,也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历史热”?这真是热昏了头。戈尔巴乔夫不过假借“历史热”,为他的政治改革摇旗呐喊,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历史能“热”吗?大凡“历史热”之日,可能就是社会动荡与政治风暴的山雨欲来之时。历史研究的常态应当是“平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解体之前的“历史热”告诫我们:“历史热”可以休矣。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从以上几个断面,我们不也可以从中领略到在苏联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苏联那种“史学政治化”的“特色”;由此而暴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的确应为我们所吸取。因此,经历了艰辛与坎坷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后人值得认真总结与传承的史学遗产,对它采取全盘否定(如同过去的全盘肯定)的态度是不足取的。
其三,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开掘与深化。
开掘意味着拓展与创新的交汇,深化意味着视界与识见的增添,开拓与深化是蹊径另辟,是学术进步与学术研究工作彼此促进的提高过程。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需要如此。我这里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说点意见。
专题研究。
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史的研究,已有不少概论性的作品见世(注:从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到朱政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载陈启能等多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到蒋大椿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都可为之佐证。),当然有深度的综论还是很少。这种“盘点”对于我们传承与弘扬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基础性的和必要的一项研究工作,接下来的任务是需要开掘,需要深化。我这里要说的是专题性的研究,那当然是开掘与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重要途径。笔者近日参加一个名为“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的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个人以为这个专题立意甚好。如果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不朽灵魂”[11]的话,那么从史学遗产的角度,研讨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的互动关系、史学遗产对当代史学发展的意义,不是也可从中察觉这个闪烁与蕴藏在史学遗产中的中华文化的“不朽灵魂”吗?此类专题无疑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化。不过,当下中国学界这种有创意与开掘性的专题研讨会并不多见,我们还需要在专题研究方面下功夫。
中外(西)史学交流的研究。
关于深入开展中外(西)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笔者已另文详说[12]。这当然也是一种专题性的研究,这里单列出来却别具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经出世,就以其开放、求真、经世、批判等品格,卓立于西方史学之林,并向外辐射出它强韧的生命力。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也输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从外面输入进来的,那么从接受史学的角度,考察其通过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倘说它是“借道”苏联,那么进一步问,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输入中国的,传入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在我国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又有哪些值得认真记取的经验教训,如此等等,我以为这正是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搞清楚的重大问题。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中国化吗?倘漠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东来及其所发生的影响的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国化”也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反之,我们也要关注中国史学,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至域外及其所发生的影响。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发挥其主导作用与主流影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看其能否以正确的认识与积极的态度,主动融汇于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中,并显示出自己的优势。这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有力挑战,也是我们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开掘与深化的时代命题。
期盼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早日问世。
马克思自19世纪40年代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自此至今,它的起源与繁衍,它的传播与变异,它的危机与前景,论者纷纭,在漫长的世界史学发展史上,这一百六十年的历史,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凝重的历史篇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迄今仍未有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著作问世,每每念此,忝列其中的本文作者不免感到汗颜(注:相比之下,我国哲学界走在了前面,粗粗查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十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见世,其中有煌煌八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主编,北京出版社,1991—1996年),又有“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单卷本面世。这自然与哲学这一学科的性质有关,但历史学在它面前,也显得过于滞后了。)。倘若不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还谈什么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还谈什么守护与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中的主导地位,开掘与深化更成了一句空言。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代世界发生的深刻变革,国际史学也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从20世纪初就开始的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步伐,由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当代技术革命新浪潮的冲击而在战后更加快了它的发展进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其成长繁茂的气候和土壤,因而发展迅速。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其西方的社会实践,而与同时代的西方新史学(从阶级含义来说,实为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纠纽粘连,从这一意义上讲,它或许可以归入西方新史学的派别之列。然而,两者在互为影响的同时,又“和平共处”,各自独成一派。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毕竟姓“马”(尽管姓的是“西马”),但随着“西马非马”政治裁决期在我国的消解,人们确实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现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既有脉络相互承接的传统本性,也有张扬个性特征的时代品格,昭示出一种新的史学发展趋向。总之,“西马亦马”,归根结底,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类型。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现时代、跨国界、多层次的发展特点:所谓“现时代”,指的是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生长的时代背景,身居的是繁荣与衰朽兼存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说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时代性”;所谓“跨国界”,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蔓延,遍及欧洲,流传北美,兼及欧美之外,说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宽纵与广泛的“世界性”;所谓“多层次”,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成员的结构,新旧交替,长者与年轻接榫,说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代代相传的“延续性”。
应当说,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与日积月累,它也是我们需要传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一种类型。为此,揭示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取向,兼及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联,应当是时下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研究工作的题中之义。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展开,暂胪列以下几点,以说明论旨。
标签: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文; 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路易十八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读书论文; 拿破仑·波拿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