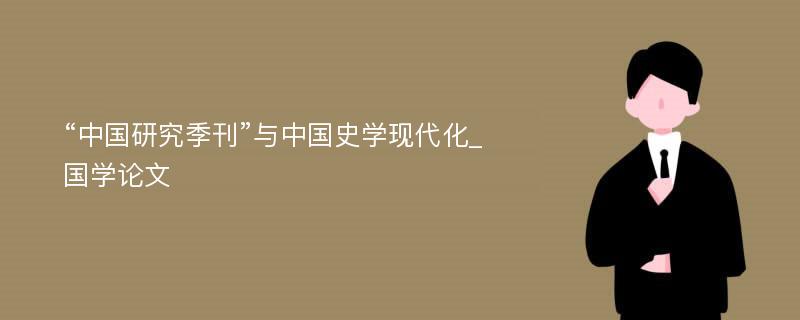
《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季刊论文,史学论文,国学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学季刊》(以下简称(《季刊》)是北京大学于本世纪上半叶编辑出版的、以表现北大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的一份刊物。《季刊》上承《北京大学月刊》(注:见宋月红、真漫亚:《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为文科研究所)的专门刊物(注:2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学制分为预料、本科、研究所三级。研究所是为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而设立的。1921年12月4日,北大的学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规定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4门。至1922年初,已成立了国学门。1929年研究所改为研究院。1934年又改为文科研究所。),目的在于“发表国学方面研究所得之各种重要论文”(注:《国学门研究所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定于每年1月、4月、7月、10月各出一期(号),全年合称一卷。创刊号出版于1923年1月,终刊号为1952年12月出版社的第7卷第3号,共出版了7卷27期(注:《国学季刊》因时局和经费等原因经常不能按时出刊。1923年1月创刊后,当年出版了4期。1924年因经费原因未出刊。1925年出版至第2卷第1号后因时局原因停刊。1929年12月恢复出版第2卷第2号,1930年出版了第2卷第3、4号。1931年没有出刊。1932年出版了第3卷的4期。1933年没有出刊。1934、1935年分别出版了第4卷的4期和第5卷的4期。1936年出版了第6卷的第1、2号后停刊。1950年出版了第6卷的第3、4号。至1952年,出完至第7卷第3号。)。胡适、朱希祖、魏建功都曾出任过《季刊》的编辑主任,沈兼士、周作人、顾孟余、单不广、马裕藻、刘文典、钱玄同、李大钊、马衡、陈垣、刘复、姚士鳌、罗常培等人在不同的时期出任过编辑委员。《季刊》既标志着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水平,也展示了北大的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因《季刊》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内容涉及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分支——历史学的研究,伴随着同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脚步声,它在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了当时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趋势。百年北大,《季刊》是其辉煌历史中的一页,曾与《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称四大学术刊物。世纪回眸,史学近代化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过渡的重要转折。把《季刊》放入北大的学术发展和史学近代化的大趋势中加以考察,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出其自身的价值。
一、《季刊》与“国学”、“整理国故”
北京大学曾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但是《季刊》却以“国学”命名,以“整理国故”作为“发刊宣言”的中心思想。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发生在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京大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联系到“国学”含义的变化与“整理国故”口号提出的时代背景,则更可以说明产生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
“国学”这一概念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其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构成了传统学术的主要内容。经、史、子、集是传统学术分类的代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被历代所遵循的传统治学模式。这并不存在用“国学”来统称学问的必要。变化产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不断涌入,对所谓“西学”的介绍和传播逐渐形成声势,借鉴和使用西方学术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的所谓“新学”也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为了与势头强劲的西学、新学相抗衡,也为了与其有所区别,人们把中国的传统学术称为“古学”、“中学”或“国粹”、“国学”。对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荡涤之后,对于国学含义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去掉了很多抱残守阙、顽固僵化的成份,而增添了一些兼容开放、冷静客观的内容。具体而言,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术,即区别于西学及其它新兴的社会科学,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本国之学。用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去看待、整理和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五四以后对国学的新的理解,也是《季刊》赋予国学的崭新内容。
蔡元培担任校长后,对北京大学的学校体制和学科设置进行了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改革。创办研究所的目的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范围是国学,对于国学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复杂工程,因为人们面对的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演变而来的传统学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而承担这一任务。
与带有激烈反传统色彩的、由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等杂志不同,也与刻意守旧的、由北大旧派学者主办的《国故》杂志不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新的与旧的、激进的与保守的、前进的与倒退的两种观点和情绪的尖锐对立冲突之后,《季刊》反映的是趋于平稳、冷静和理智的风格。同时,作为北大学术的一个标志,《季刊》也力求比较全面平实地体现作为北大整体的学术研究状况,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上。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将传统学术与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何借鉴西方的思想观点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如何完成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的历史转变。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学府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对此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为北大创造了重视学术研究和追求思想自由的风气,集大批一流人才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北京大学,表现出的是具有扎实功底的传统学术素养和兼收并蓄的、开放的思想观念。北大的学术风格绝非保守僵化,但也不是标新立异。“整理国故”口号的提出,在当时是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和比较可行的措施。
《季刊》编委会主任胡适在1919年曾经阐述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在《季刊》的创刊号上,胡适撰写了《发刊宣言》,对他所提出的整理国故的倡议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是一篇十分著名的有关整理国故的宣言。胡适在文中首先描述了在“西学”冲击下所表现出的悲观情绪:“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到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向迷信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国学的处境并不乐观,盲目地自大、简单地提倡、消极地僵守,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胡适在总结了自清代三百年以来学术研究的成绩和缺点后,论述了研究和整理国故的方法与原则。第一,扩大研究范围。打破以往国学的狭隘范围,主张国学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打空了”。第二,注意系统整理。具体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第三,要进行比较研究,反对学术上的闭关自守。“向来学者误认为‘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研究’的功用。”“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谈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经解释,自然明白了。”
这篇《发刊宣言》使《季刊》在创刊伊始就明确表明了整理国故、研究国学的方法和目的。《季刊》之于国学和整理国故的态度,在当时和以后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季刊》反映的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特点
中国史学近代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打破了传统史学相对封闭的藩篱,与西方史学思想与方法的接触、碰撞和融合。一方面,继承和坚持传统史学,特别是乾嘉历史考证学的无徵不信、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借鉴、接受和引用西方先进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妥为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其结果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课题的变化、治学观念的扭转和治学方法的更新。如前所述,北大所形成的学术风气和研究体制,《季刊》所倡导的整理国故,对于史学近代化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季刊》在诸多方面都明显地反映出了这种发展趋势。
(一)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丰富研究课题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从《季刊》的内容上看,涉及到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内容更加广泛,视野更为开阔,其中尤以宗教史、民族史、思想史、历史地理学等方面最为突出。
陈垣的宗教史著述《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分别发表在《季刊》第1卷的第1号和第2号上。宗教史是近现代以来在学术界颇被重视但又公认为艰难的一个领域。陈垣涉及这一领域,并取得了被称为“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的突出成就。上述两文即“古教四考”中的“二考”。火祆教、摩尼教都是流行于唐代的外来异教,文章对于两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过程、发生的转变以及与佛、道等大教的关系作了详细考证,注重从宗教与社会政治的变化而产生相应变化这一角度立论。这是首次对这些宗教的系统研究。其他宗教史方面的力作,还有汤用彤的长篇论文《竺道生与涅槃学》(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叙述了人乘涅槃的翻译、传译、修改过程,考察了竺道生等人对此的研究和阐释。王维诚的七万余字的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2号,1934年。),在比较详尽地掌握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对老子化胡说作了全面性的考证,论述了自东汉老子化胡说之由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诸朝对此说的辩论和禁毁过程。汤用彤的另一篇文章《读〈太平经〉书所见》(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1号,1935年。),通过对《太平经》和《太平经钞》的对比,得出两书的卷帙版本状况,认定其为汉代之旧书,还论及了《太平经》与道教及佛教的关系。孙楷第的《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裁》(注:《国学季刊》第6卷第2号,1936年。),论述了唐代佛教传输的有关情况。
民族史研究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愈来愈显得重要,学者们利用不断发现的新材料,运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研究、看待民族史,使得这个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绩。《季刊》对此非常重视,相继发表了多篇有份量的论文。陈垣的代表作之一《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编)最早发表于《季刊》的第1卷第4号上。这部著作征引书籍200余种,对元代文化发展状况作了全面探讨,涉及元代西域人在儒学、佛教、史学、礼俗、文学、美术等多方面的成就,通过阐述元代西域各族接受汉文化的事实,纠正了明以来轻视元代文化的倾向。该文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蔡元培语)。全书以专著形式出版时,陈寅恪在为之作的序中写道:“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落,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著作,渐能摆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39页。)方壮猷的《鞑靼起源考》(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1932年6月。)论述鞑靼与柔然、突厥、室韦等族的相互关系,得出了鞑靼族属柔然苗裔、于元明期间壮大起来的结论。张鸿翔的《明北族列女传》(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号,1934年。),仿传记体裁,把上起洪武初年、下迄崇祯末年的明朝270年间北方各族妇女关于政治、习俗、通婚、生活等历史状况分族别记述下来,包括女真、鞑靼、兀良哈、瓦剌、哈密、沙洲、土鲁番以及种族未详者。其独出心裁的选题和全面周详的论证,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傅乐焕的《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4号,1935年。)对宋辽关系作了相关考证。
《季刊》对于思想史领域也有涉及。1924年适逢清代思想家戴震诞辰200周年,次年出版的《季刊》第2卷第1号为戴震专号,刊载了胡适用了近两年时间完成的论著《戴东原的哲学》、魏建功的《戴东原年谱》以及容肇祖的《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这期专号对戴震的生平、思想、学术作了一次深入详尽的研究。胡适《颜李学派的程廷祚》(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年。)、钱穆《龚定庵思想之分析》(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3号,1935年。),分别对清代思想家程廷祚和龚自珍的思想进行了论述。另外,《季刊》还发表了钱玄同为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所作的长序,篇名为《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2号,1932年6月。)。文章阐述了作者对于经今古文学问题的成熟看法,“是站在古代语文学的立场来考辨‘古文经’,只是‘求真’,两不偏袒”(注: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载于曹述敬《钱玄同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第1版,第185页。)。钱玄同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们今后解经,应该是以‘实事求是’为鹄地,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剥下经学神圣的外衣,剔除后人的穿凿附会,才是正确对待经学的态度。
重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近代以来,边疆史地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季刊》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如谢国祯的《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4号,1930年12月。),对清初东南沿海一带迁界的经过、各省边界的划定、有关迁界诗文的记载以及建界后对台湾的利害关系一一作了论述。孟森撰写的《建州地址变迁考》(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32年12月。)考察了满洲建州卫地址的变动过程。建州时期的历史及有关史料被立国后的清朝君主所忌讳,此文对搞清历史真相有一定帮助。另如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1号,1935年。)、黄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唐兰《昆仑所在考》(注:《国学季刊》第6卷第2号,1936年。)等文,也属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章。
(二)历史考证学的新成就考证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着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传统的考证(考据)学已由清代乾嘉学者总其成而成就卓著,但却是与经学联系在一起的。本世纪以来的考证学与以往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它已经基本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与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我们称之的历史考证学。史学的学科独立化趋势,是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考证学史学化,从而形成的近代历史考证学,在本世纪初至40年代末是史学界取得突出成就的一种研究方式,也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中西史学较好结合在一起所体现的史学近代化的特征。《季刊》所发表的大量的历史考证学论文充分表现了这一状况。
前述之《季刊》关于民族史、宗教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即属于运用了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方式,反映了历史考证学领域的扩大,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文献考证的局限。
除此之外,《季刊》也发表了对史书、史料和史家的考证文章。如朱希祖的《萧梁旧史考》(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汉十二世著纪考》(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汉唐宋起居注考》等。其他如李正奋《魏书源流考》(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2号,1929年12月。)、王重民《千顷堂书目考》(注:《国学季刊》第7卷第1号,1952年。)、陈乐素《徐梦莘考》也都是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考证学成果。顾颉刚在《季刊》上撰写发表了《郑樵著述考》(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和《郑樵传》(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两文。南宋史家郑樵的史学思想及其《通志》的价值,曾长期不为人所注意。顾颉刚很早就对郑樵发生兴趣,认为《通志》是一部有“创见”的书,郑樵是一位有独创性的史学家。他说郑樵是引导他走上怀疑古史的道路上的古人之一,“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注:顾颉刚:《我是怎样研究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1页。)。
从《季刊》所发表的历史考证学成果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即考证学正在摆脱旧有的窠臼,考证也并非仅仅是为了考证,而是更多地联系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问题。而下面所提到的对新史料的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历史考证学的发展。
(三)重视介绍和使用新发现的史料重视新史料,利用新史料研究历史,这一现象为当时的史学近代化注入了生机。陈寅恪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注: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236页。)《季刊》非常及时地反映出了这一潮流。本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最重要的新史料是甲骨文、敦煌文书、秦汉简牍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对这些新史料的研究和运用这些史料进行相应研究,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课题。《季刊》对这四种新史料都有涉及。容庚的《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12月。),对于甲骨文从被发现到引起重视及至被视为重要的地下材料的全过程作了叙述,对将甲骨文考释的大致情形分别作了说明。《季刊》还分期登载了伦敦博物馆和巴黎图书馆所存的敦煌书目(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卷第4号、第3卷第4号。),在第3卷第1号刊物上影印了8页敦煌石室存残刻本韵书,以飨读者。1934年,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后,设置了考古室、明清史料整理室。考古室收藏了5000余种古器物,两万余份文献资料和金石拓片。考古室还与其他单位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一带发掘了一万多件汉简。对于这些文献及实物资料的研究成果以及科考报告,陆续发表在《季刊》上。如马衡《记汉“居延笔”》(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黄文弼《“兽形足”盆形像考释》(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3号,1932年9月。)等文章就是西北科考后的研究论文。明清史料整理室购入清内阁大库所藏有关明清史档案60余万件,由孟森主持对这些史料的整理、研究和付印工作。研究成果也多在《季刊》发表。
(四)介绍和引入西方有关学术成果和资料,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整体中加以考察以一种开放的历史观重新审视自己,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又一个特征。《季刊》发表有西方学者的论文,如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伊凤阁的《西夏国书说》(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1923年12月。)等,还有罗福苌译的存于英国和法国的敦煌书目。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姚从吾的《欧洲学者对匈奴的研究》(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全文达六万余字。文章首先概述了冒顿阿拉提在欧洲史上的地位和对匈奴研究的经过及最近趋势,然后详细叙述了法国学者得几内关于“匈人即是匈奴”的推论、德国学者夏特的“窝耳迦河的匈人与匈奴”的说法、荷兰学者底哥柔提的纪元前的匈人的观点。文后附有从欧洲学者专著到普通百科中所见到的匈奴研究的情况介绍。让中国学者了解国外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向中国学术界介绍外国学者及其学术观点,该文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陈受颐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注:《国学季刊》第5卷第2号,1935年。),认为以往论者过分注重西方科学知识和器械的输入而忽略了双方传统文化的双向交流和渗透,他在文中特别指出:“其实两方思想上的交换,问题甚大,不该看作西洋历算介绍之附庸。耶稣会士不特传播西洋思想和文化于中国,同时也传播中国思想和文化于西洋。在十七八世纪西洋思想史当中,……中国文化都曾供献过相当的材料和观点。”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意义。
(五)提出新问题,阐发新见解具有持续性和时效性功能的学术刊物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近代化的一种形式。《季刊》在为学者提供了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之外,也不失时机地刊登一些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问题和新见解的论文或讨论文章。胡适在崔述的《崔东壁先生遗书》刻成100周年纪念日前夕,在《季刊》上撰写了《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一文,首次积极地肯定了崔述史学成就的意义。他写道:“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必须先跟上崔述。”崔述对古史辨派产生了直接影响,《考信录》至今仍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胡适对崔述学术的阐发,在近代学术史上有一定意义。
罗尔纲的《上太平军书的黄婉考》(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2号,1934年。),将王韬的《读书随记》和以黄婉的名义上太平军书的内容相互对照,从笔迹、遣词用语等方面证实黄婉就是王韬,王韬曾经给太平天国起义军上书。这个结果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影响。
孟森就是否禁毁《清史稿》这个在当时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在《季刊》上撰写了《〈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1932年12月。),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甚重。即使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尚论。”孟森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他的意见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沈兼士在《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倡议中国语言文字需要改良,即使从历史上看,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胡适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作的序,以《校勘学方法论》为题在《季刊》上发表(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3号,1934年。)。他称赞“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胡适对陈垣校勘学方法的肯定和总结,对于校勘学的最终确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季刊》出版到第7卷的时候,时间已进入20世纪5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研究状况,也在刊物中反映出来。第7卷第2号发表了郭沫若的《中国奴隶社会》,这是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阐述其殷周奴隶制观点的著述。文章列举材料证明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存在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殷代和周代就是奴隶社会。第7卷第3号发表了徐特立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撰写的《研究历史的目的与方法》一文。这一期也是《季刊》的终刊号。
《季刊》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语言、文字、语音方面的论文,其中以著名的语言学家刘复和魏建功最为突出,充分反映了北大在该研究领域的雄厚实力和出色的研究成果,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三、《季刊》的编辑特色
《季刊》的编刊宗旨和内容上的特点已如上所述。再从编辑的角度来观察,《季刊》也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地方甚至对我们今天改进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仍有启发意义。
《季刊》十分重视用图影来配合刊中学术论文所论及的内容。多数刊物用铜版纸印上相关图影随刊一同发表,多者每期达二十余页。这大约可分为三种情形:一种就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某些不常见到的或新发现的珍贵史料的影印件,供读者观赏和研究。如北京大学藏“顺治八年追尊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诏”(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清太宗天聪四年(1630)伐明以七大罪誓师谕”(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另一种是以文附图,即用图影来作为论文的补充和附录。如唐兰的《寿县所出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号,1934年。)一文,配发了多达13页30幅的图影。罗尔纲的《上太平军书的黄婉考》,为说明黄婉就是王韬,附上王韬《读书随记》原文图影和黄婉上太平军书字迹,以资对照。谢国祯的《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附上迁界地域形势变迁图。还有一种是以图附文,即重点在图,因图影而由专家撰写说明或考证文字。如第3卷第3号发表了辽碑9种17幅拓影,然后由孟森跋尾,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探讨创造条件。果然在下一期刊物上就发表了对孟文中存疑之处进行研究的文章。《季刊》的这些做法,既可使刊物图文并茂,增加说服力和可信度,也可使编者、作者和读者三方相得益彰,共同交流,拉近距离。《季刊》编者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丰富刊物内容、为读者着想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学术刊物附以多页图影,这在今天仍不多见。
及时报道学术界动态、学术消息和新的研究成果,也是《季刊》编辑方面的特色之一。《季刊》属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因此在附录中不断报道国学门的重要纪事,包括其学术活动、组织机构、刊物、研究课题、人员配置等方面的内容。由于考古学是当时一门十分活跃的新兴学科,《季刊》对考古学界的活动和发现十分重视,如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蒙新旅行之经过与发现(注:《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1930年9月。)、燕下都发掘报告(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等等。1927年5月,由北京大学、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央观象台等单位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了为期3年半的科学考察,《季刊》发表了两篇这次考察的论文(注:《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季刊》还不断登载《清华学报》、《社会科学》、《暨南学报》等学术刊物的论著目录,及时刊布北大出版的教授著作目录。
《季刊》对于来稿坚持只问程度、不问资格的使用原则,只要文章有质量,就可以采用发表。《季刊》作者以北大教授为主,发表率较高的有胡适、陈垣、朱希祖、孟森、刘复、魏建功等人。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脚的年轻学者顾颉刚、容庚、郑天挺等人也有论文发表。《季刊》还选择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以“本校研究生成绩”为栏目名称发表,并在文前附有该生指导教授对论文的“审查书”,如由孟森指导、张鸿翔撰写的《明北族列女传》,由汤用彤指导、王维诚撰写的《老子化胡说考证》等。
按照蔡元培的建议,《季刊》的版面文字均从左向右横排,采用新式标点,文字不拘白话文言,封四附英文目录或提要,间或编有所发论文的目录索引。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杂志中都是独创的,因而更显得别具特色。
《季刊》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学研究的状况与变化,也反映出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和特点。《季刊》所发表的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对推动和促进研究中国的学术文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季刊》所创造的成绩,不仅是北大百年历史中出色的一页,而且从整个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来考察,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回顾《季刊》的成就及其所反映的史学近代化特征,对于研究北大学术和20世纪中国史学均有重要意义。
标签:国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大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北京大学论文; 胡适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北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