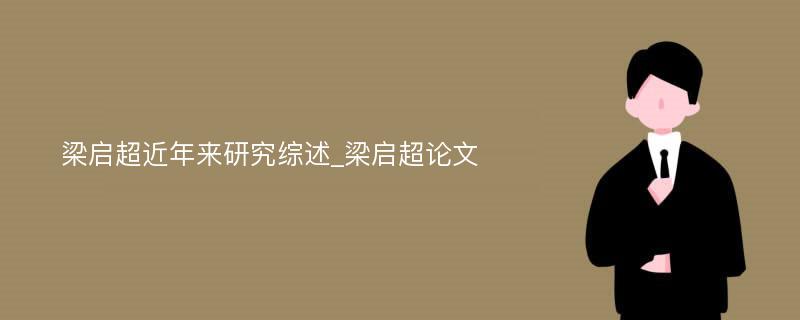
动态与综述 近年来梁启超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态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动态与综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学术家。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不断深入,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第一,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据统计,5年来累计有80余篇论文发表, 其中不少思路开阔,有一定学术价值。第二,出版了几部研究著作。主要有宋仁编著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易鼎新著的《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美国人张灏著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尤其是李喜所、元青著的《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第三,编辑出版了一些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资料。如夏晓虹主编的《梁启超文选》(上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召开了以此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总的说来,近年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晚年政治活动
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就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和晚年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较多的阐述。郭驰认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倡导革命言论,并不是他的一种狡猾的伪装,也不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信任,而是时势所使然,从根本上说是他自身认识深刻变化的结果,是完全真实和可靠的〔1〕。刘云波则认为,梁启超在20 世纪初鼓吹革命,固然有顺应大势的理智色彩,但更多似是因客观外界刺激而引发的非理智性表露或称情绪性冲动,不能看成是其思想本质的表现,与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论不具有同样的意义。他鼓吹革命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知识界对满清王朝的愤怒情绪,以免遭致舆论界的反对,是为了使年轻的知识分子从“革命”即等于暴力革命的错误认识中醒悟过来,走上自己所倡导的“革命”之途〔2〕。宾长初也认为,即使梁启超在1902 年前后一度宣传“革命排满”主张,但他始终没有摆脱他所代表阶级和政治纲领的束缚,跳不出保皇的圈子:在思想上没有抛弃改良的思想体系,在感情上偏向于康有为等保皇党人物〔3〕。
1903年梁启超北美之行后,不再倡导“破坏主义”而极力主张实行“开明专制”。董方奎、吴春梅等同志认为导致梁启超这一转变的主要根源是外在的因素,包括: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劝诫他“革命共和”的严重危害性;在美国考察了共和政体的优劣,反省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原因是民智未开,认识到美式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思想上深受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理论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尤其是日本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4〕。 郭驰则认为梁启超一生的思想从未脱离过“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爱国之心、立宪之志和新民思想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不变的三个因素。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急切的救亡之志除了使他产生过“虚君共和”之类的保守主张外,也曾经促使他产生过激进的革命共和主张。在救亡图存的爱国前提之下,梁启超从不局限于某一种主张,他既不绝对地反对“革命共和”,也不僵硬地坚持“立宪改良”。他坚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同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异常薄弱的现实所产生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导致他时而倾向革命时而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5〕。
对梁启超1903年后提倡的“开明专制”主张,学术界历来褒贬不一,多有分歧。近年来研究者大多认为,对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不应以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民主共和论为参照系而一味地指责他是“保皇”、“倒退”、“流质多变”,应当客观地予以看待,肯定其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所起的作用。董方奎认为,近代世界各国的开明专制都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准备了条件。这种过渡稳而不乱,似慢非慢。梁启超放弃美式共和国方案而主张通过开明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在追求民主宪政的目的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只是认为以开明专制为过渡更适合中国国情。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破产,生动地说明美式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梁启超的转变是进步的〔6〕。彭南生也认为,梁启超主张的“开明专制”主要是以“客体”(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它虽然采取了封建专制的外壳,但注入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内涵,是对封建大一统主义的一种否定,它弥补了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7〕。
从事政党政治,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是梁启超晚年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界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姜波认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和实践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一是理论上他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两党制,民初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政党政治的理论宣传,但实践过程中却不能象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那样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过程中去求同存异而走上轮流执政的道路,他在帮助袁世凯击败国民党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所努力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与国民党一同走向失败。二是梁启超拥袁的目的是要将袁世凯带上民主宪政之路,最终实现改良派掌握国家政权的愿望。但实际上他却不自觉地帮助袁世凯走上了独裁专制之途〔8〕。林家有认为, 梁启超与袁世凯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思想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梁袁双方共同排拒同盟会在政权中的地位,由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控政权,瓜分肥缺。或者说,梁启超依附袁世凯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事情,而主要是他们所代表的立宪派与旧官僚联合起来反抗革命派,争取统治权的结果,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相信而依附他,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工具,相反在建政和治国等关键性问题上,他们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潜伏着危机。他们的结合是暂时的,分裂则是长期的。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人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他便成为袁世凯身边第一个公开揭起反袁护国旗号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的倒袁是被迫的,也是自觉的,以斗争求生存是梁启超反袁的思想基础〔9〕。
过去史学界一般认为,本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两个对立的派别。近年来不少人对这一说法提出不同看法。侯宜杰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同一个阶级之间的事情,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为了救亡图存,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目的相同,从事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他们的分歧不在宗旨目的,而在策略手段〔10〕。对于梁启超提出的“政治革命”论,刘云波认为它是梁启超20世纪初年所倡导的革命论的延续和完善,绝不能视为反动思潮加以否定。因为在他看来,革命派所致力的暴力革命实质是复仇性质的种族革命,是一种无秩序的自然暴动,它不仅不能达到实现共和政体的目的,反而只会导致武人争权、外国干涉和新的专制等一系列后果,而实行“政治革命”(即“立宪救国”)就可以避免这些危害〔11〕。
本世纪20年代,我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争论中,梁启超在由他任主编的《改造》杂志的“社会主义研究”专栏中发表了《复张东荪书社会主义运动》,该文集中表明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应学犁认为,他主张在中国实行渐进的社会主义是以思想上的尽性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三元结构为基本特征。不过,梁启超信奉的是进化论而不是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深入他骨髓的是儒家伦理和内圣外王的精神,因此他的社会主义不仅要靠发展实业来完成,而且要靠思想革命来实现。可以说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尔特主义、儒家学说的混合体,除了要救中国、使中国强盛、人民自由平等幸福的宗旨不变外,就其学说本身却没有一个体系。正因如此,他受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肃批评是必然的。但历史证明了梁启超在2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承担着“被当时所否定、被历史常记起”的双重角色〔12〕。徐光寿、王鸿雁则认为梁启超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矛盾,徘徊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倾向于资本主义。他反复强调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明确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应该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实质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这种理论本身注定会破产,其政治实践也必然会失败〔13〕。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提出了民权学说。在其理论来源上,刘振岚、管彦波等认为是梁启超借用我国古贤圣哲的“民本”思想来探讨变法本原、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4〕。宝成关则认为是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深受自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各种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尤其是卢梭的《民约论》中“人民主权在民说”启迪的结果〔15〕。如何评价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观点。刘振岚认为,梁启超用民权思想否定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君权至尊,主张“以群术治群”实现“人人有自主之权”,这些为中国社会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接触了近代文明的真谛,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6〕管彦波不同意此说,认为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担心不兴民权便无以服众,难以变法。另方面担心在中国兴民权又会导致人民的革命。他是为了实现其改良,想通过宣传兴民权争取民众,为了防止革命又把兴民权巧妙地转化为兴民智,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和限制人民革命〔17〕。
2.梁启超的文化思想
梁启超文化观念的最大特点是几经变化,从早期托古改制的“全变”思想到中期“教无可保”的西化思想,再到晚期中西精神——物质两分互补的文化主张。经历了对西方文化由醉心到冷漠,对传统文化由离异到回归的过程,始终徘徊于感情与理智、历史与现实的两难之间。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梁启超的这一文化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刘福祥认为,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士大夫阶层向西方学习,不是来自对西方文化理性思考后的肯定,而是为了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因此带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和功利主义色彩,不可能形成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又由于传统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使他们学习西方“不能学其所长而尽袭其短”,产生了许多异化现象〔18〕。关健瑛则认为造成梁启超文化观矛盾善变的主要根源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和调和主义的文化原则。一方面他的善变是“为国而善变”,另方面无论是他提倡的以中学为主还是主张以西学为主抑或是复归传统,他都主张对中西文化进行调和更新〔19〕。
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梁启超终生在孜孜以求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景。马永山认为,梁启超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理论实是对“中西融合”观念最精采、准确的阐释,是与“醉心西风”和“墨守故纸”两种思潮根本不同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新改造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和应付外来文化的挑战,“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就是吸收外来文化之“长”补传统文化之“短”〔20〕。张跃先根据梁启超的“碰撞”理论,分析了他对未来文化的设想,认为梁启超从东西文化各自面临的困境出发,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这种努力是“前驱先路”,他的一系列成果是中国文化思想乃至于人类文化思想史的宝贵财富〔21〕
梁启超晚年对传统文化的“复归”,李大华认为是一种“今胜于昔”的举动。梁启超早期基本上是以进化论为圭臬,以破坏、否定为己任来爬罗中西古今文化的,对本土文化的肯定是不自觉的,而现在他是以自由意志为特征的文化观念为指导,以建设、肯定为己任来清理古今中西文化的。他的“回复”实际上是一种翻新和进步,是新的历史下的整合〔22〕。高力克则认为,梁启超游欧后对“科学进步”信念的逐渐放弃,标志着他已告别文化启蒙主义而开始转入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域。他的“西方物质”与“中国精神”、东西文明“融合”理论实质上仍未跳出文化调合主义藩篱。他在扬眉吐气地批评西方文化的同时,心安理得地赞扬中国文化,他也不再以一个为国家救亡而对西方屈尊俯就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以一个胸怀人类的世界主义者的语调说话〔23〕。
在梁启超文化思想矛盾善变的背后,研究者大多认为有一以贯之的主调,这就是他心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关健瑛认为不论梁启超的文化言行是激昂的、隐晦的还是怀旧的,他的主旨都是“为国而善变”,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始终未曾改变过〔24〕。张跃先也认为,梁启超将爱国主义作为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25〕。
3.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
戊戌政变后短短几年中,梁启超撰写大量文章,热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过去对梁启超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了梁启超启蒙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范岱年认为梁启超是一位集编辑、政论家、教师、学者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做的大量启蒙工作,教育了不止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26〕。焦润明认为梁启超所从事的社会启蒙活动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他是戊戌启蒙运动的理论骄子,是中国的“伏尔泰”〔27〕。俞祖华、张宝明、张全之则分别就梁启超与严复、梁启超与陈独秀、梁启超与鲁迅三位启蒙运动大师的启蒙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梁启超不愧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者〔28〕。
在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中,他倡导的“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其实质是要把传统中国人塑造为近代国家的“新民”,成为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主体力量和社会基础。研究者充分肯定了梁启超的“新民德”、改造国民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贾云平、杨文银认为梁启超的国民精神批判理论,在思想领域具有重要的开拓性,不仅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孕育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激进反传统的思想家,同时也启发了新型改良主义者梁漱溟等人走向农村实践之路,去激发国民的智慧和觉悟,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29〕。
4.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
向西方学习,寻求中国近代化之路可说是先进中国人对“救亡图存”这一历史主题的必然选择之一,从魏源、林则徐到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在探索国富民强的道路。过去,史学界对梁启超探索中国近代化之路的研究不多,近年来人们从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人的近代化和文化思想近代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张锡勤认为梁启超为如何实现中国近代化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全面、正确的方针,这就是他所从事的兴民权、清算国人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使中国人变奴隶为国民,实现人的解放以及开展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这些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贡献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30〕。耿云志就孙中山与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道路选择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梁启超的方案主要是政治上拟定出代替专制主义的立宪制(这成为清政府后来的“预备立宪”的最初蓝本),经济上应当鼓励增值财富的正当欲望,思想文化上既肆力介绍宣传西学又对中国古代文化做剔抉发展的工作。这些使梁启超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无可争议的先驱者〔31〕。
5.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近代新史学思想是梁启超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史学界对他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重要史学著作进行了分析。蒋俊、龚郭清等认为,他的以进化而非循环为历史演变模式、以民族而非王朝或家族为历史本位、以国民而非帝王为历史主体等等新理论,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他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32〕。黄敏兰认为《新史学》绝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主要是或者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梁启超是借批判旧史学的弊端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赞誉西方史学来宣传西方民主政治和民权思想。可以说《新史学》是梁启超救国救民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戊戌变法的继续,是他政治斗争和政治理论的体现,可称之为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政治批判著作〔33〕。
陈丰认为梁启超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年鉴派”的史学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谓不谋而合。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强调今昔之间的关系,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历史的投影。二是主张从研究人们的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深入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社会的精神状态。三是主张开放历史研究,让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联袂,从而开阔历史研究的视野。四是带有全球性的眼光探索本国历史,把本国历史置于全人类的历史之中〔34〕。王也扬认为梁启超是我国最早对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给予重视和研究的学者,他第一次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主体意识,并肯定其在历史认识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写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求得真事实”始终是梁启超整个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灵魂〔35〕。
6.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
李喜所认为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困顿,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撰写了一批研究佛学的学术著作。梁启超如此笃信佛学,一方面是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精神武器,另方面是为了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但他学佛信佛,绝非盲从而是从理论上加以发挥,形成自己的系统观点,构架了一套佛学理论。不过由于偏爱,使他对佛学只有颂扬没有批评,更谈不上发展〔36〕。天祥也认为,梁启超笃信佛学,既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经世救亡的需要和理论思维的渴求,同时又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他不仅用佛理补充儒学之说,形成了他的东方人生哲学和佛教救世主义,而且在向传统折返的同时,从学术的角度把佛教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输入、发展盛衰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广泛的研究。可以说救世是梁启超佛教研究的宗旨〔37〕。
与佛学相比,基督教义及西方传教士对梁启超的影响则要明显得多。赵春晨就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其态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梁启超及乃师康有为等维新思想的形成和他们的变法活动都曾受到基督教义和来华传教士们一定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教的信徒,相反地他们对基督教从整体上始终抱一种拒斥的态度,并努力筹划抵制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渗透的良策方案〔38〕。
7.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与其他方面相比,近年对梁启超哲学思想的研究显得薄弱得多。研究者只就他的历史观和心学进行了分析。闾小波论述了梁启超的历史观,认为20世纪前后,梁启超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开民智”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历史观是“民智史观”。就社会价值来说,在当时它比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在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性的大变革时期,广开民智,改造国民性即从精神上救人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如果说恩格斯曾肯定过近代法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都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那么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古国要成功地进行一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更要有一个彻底的哲学革命作前导〔39〕。关于梁启超的心学,吴雁南认为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把心学的思想资料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结合起来,力图把人们从种种“奴隶心态”中解放出来,树立奋不顾身的进取冒险精神和为天下国家献身的志向并陶铸刚毅坚韧不拨的气质,这对长期在封建桎梏下的国民起着发聩震聋、解放思想的作用,对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0〕。
与过去相比,近年来学术界在梁启超研究上表现出几个明显特点:一是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如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问题、梁启超的佛学思想等可说是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社会启蒙思想和晚年政治活动等方面在理论上都有新的突破。二是研究方法上较多地采用了比较研究法,将梁启超与同时代同类型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能更好地展示梁启超的思想及其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作用。三是研究者始终坚持“双百”方针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和前人之说,一切从事实出发,对人物的褒贬都有理有据。
当然,由于梁启超是位思想庞杂、“流质多变”的历史人物,加上目前关于他的原始性研究资料还不完备齐全,因此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分析,如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人生观、近代国家学说等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关于他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党政治和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等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注释:
〔1〕〔5〕郭驰《也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 《学术月刊》1992年第7期。
〔2〕刘云波《论梁启超二十世纪初鼓吹革命》, 《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3〕宾长初《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评析》, 《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3期。
〔4〕董方奎《梁启超为什么放弃美式共和方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吴春梅、 方之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6〕董方奎《梁启超为什么放弃美式共和方案》,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7〕彭南生《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新探》,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
〔8〕姜波《梁启超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 《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9〕林家有《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0〕侯宜杰《应为康梁和立宪派正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1〕刘云波《试析梁启超的“政治革命”论》, 《学术研究》1994年第3期。
〔12〕应学犁《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中的角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5年第2期。
〔13〕徐光寿、王鸿雁《陈独秀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异同》,《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4〕刘振岚《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民智思想》,《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管彦波《梁启超民权思想》, 《晋阳学刊》1992年第4期。
〔16〕刘振岚《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民智思想》,《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
〔17〕管彦波《梁启超民权思想》,《晋阳学刊》1992年第4期。
〔18〕刘福祥《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东岳论丛》1990年第2期。
〔19〕〔24〕关健瑛《试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内在一贯性》,《求是学刊》1993年第3期。
〔20〕马永山《梁启超改造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实践》,《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汉文版·社科)1991年第4期。
〔21〕〔25〕张跃先《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初探》,《甘肃理论学刊》1991年第3期。
〔22〕李大华《梁启超文化观寻迹与反思》,《江汉论坛》1994年第4期。
〔23〕高力克著《历史与价值的张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26〕范岱年《梁启超——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先驱》,《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
〔27〕焦润明《论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 《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2期。
〔28〕俞祖华《启蒙的两种类型:严复梁启超比较论》,《烟台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张宝明《梁启超与陈独秀启蒙思想比较》, 《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 张全之《论鲁迅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思想》,《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
〔29〕贾云平《论梁启超国民精神批判》,《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5期;杨义银《梁启超改造国民性构想之评说》, 《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
〔30〕张锡勤《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北方论丛》1993年第5期;李华兴《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 《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1〕耿云志《孙中山与梁启超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选择》,《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32〕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 龚郭清《梁启超新史学与“究当世之务”》,《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
〔33〕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4〕陈丰《不谋而合:“年鉴派”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读书》1993年第12期。
〔35〕王也扬《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的探讨》,《长白学刊》1994年第2期;《康梁与史学致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36〕李喜所《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37〕天祥《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学术研究》1993年第2 期。
〔38〕赵春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与基督教》,《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2年第1期。
〔39〕闾小波《梁启超与孙中山历史观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40〕吴雁南《梁启超的维新观与心学》,《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近代史研究论文; 袁世凯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新史学论文; 革命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