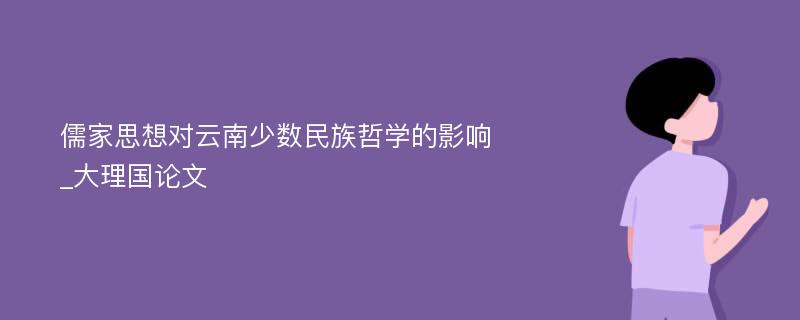
儒学对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云南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07—0057—06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当今云南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和傈僳族等,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汉族和汉族文化有着深远而多种多样的关系。其中儒学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形成发展中,呈现出逐渐增强的传播影响趋势,以致云南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哲学和思想文化渗透着深厚的儒学文化基因,考察和追溯云南少数民族这样的哲学和思想文化景观及其重要原因,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多样性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云南少数民族的演进及其与儒学的联系
云南是我国世居民族最多的一个地区,当然也是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地区。云南的少数民族共有26个,占云南省人口的46%,其中白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崩龙族、基诺族、独龙族等14个民族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都居住在云南。
当今云南的彝、白、纳西和傈僳等少数民族在我国秦汉时期,称为夷人、僰人、滇人或滇僰。云南称为滇。因境内有滇池,战国时昆明一带属滇国,故称为“滇”。据《史记》载,战国末期,楚将庄蹻率数千楚族士兵入滇,以其众而成为滇池地区部落联盟的酋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1](P.2993)战国楚将庄蹻为用兵而来滇,应当说均为男子,不会有眷属随来。既然回不了楚国,就要在滇池居住下来,会与当地土人结婚,第二代就混血了,表明战国时居于滇的少数民族就有与汉族血统融合的情况。据悉,今云南“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P.2993)。秦始皇时期就派有官吏,西汉时始置郡县。汉武帝“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牁、越巂各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2](P.2846)。全在今云南省境内。益州郡的中心在滇池周围,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滇”,又称“滇僰”,即滇池的僰人。考古学家认为,僰人原属西北地区的氐羌族群,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他们向西南移居,到达今四川西南、贵州西部和云南境内澜沧江以东、红河以北的辽阔地区,并与这些地区的土著居民融合。[3](P.17)之所以称为僰人,据许慎《说文》的训解:“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西南僰人、僬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所谓“顺理之性”,应该说是具有符合中原文化的“儒理”之性。郦道元《水经注》之江水注说:“东南过僰道县北……县本僰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① 说明僰族在西南夷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最高的,与汉族群及其文化最为接近,所以其民族名称被特别地写为从人。滇中是僰人的主要聚居区,故有滇僰之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今云南和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的区域,称为“南中”,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南中夷人”。其间,东汉末到三国时,滇东和滇中地区的主要居民称为“叟”,史家认为叟人和秦汉时期的滇僰分布区域大体相同,在血缘上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关系。叟人中的贵族称为“叟帅”或“夷帅”。夷人、叟人,连同前述的僰人,则是当今云南彝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的先民。自东汉至魏晋时期,由于内地汉族向南中的大量迁入,其间的豪门大姓与夷人、叟人的首领、贵族相互联姻,成为当地的统治势力,史称“南中大姓”。因此,“南中大姓”可以说是“夷化”了的汉族,也是“汉化”了的夷人(少数民族先民)。这些“南中大姓”如孟氏、高氏、雍氏、爨氏和霍氏等,他们既是少数民族,保持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当时的夷人、叟人中具有颇大影响,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内地文化素养,因而逐渐成为南中地区的统治阶层。
唐宋时期,属于氐羌系统的各族群逐步形成为乌蛮、河蛮、松外蛮、白蛮、和蛮、裸形蛮、栗粟、么些、路蛮、庐麓蛮、锅锉蛮等,其中河蛮、松外蛮、白蛮逐渐形成了白族;乌蛮逐渐形成了彝族;和蛮逐渐发展为哈尼族;寻传蛮发展为阿昌族;裸形蛮衍为景颇族;么些逐渐衍为纳西族。此外,唐宋时有部分吐蕃人入居滇西北,后来成为聚居在云南的藏族。唐时的云南属于南诏政权,以乌蛮、白蛮为主体,即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南诏治下包括当今云南各民族的先民。唐王朝屡派大量将士征伐南诏,征战的官兵大都流散于洱海区域的白蛮之中。唐与南诏的臣属关系曾有破裂,南诏贵族屡次发兵掳掠巴蜀,大量四川男女技工被掠到洱海周围地区,他们也逐渐融进白蛮中,后代就成了白族成员。宋时由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屡有所犯,无暇像唐王朝那样对云南实行较为直接的控制,但设置众多羁縻州②,以“德化”而及之。两宋时期的云南基本上属于大理政权,其统治者是出身洱海区域的白蛮大姓段氏,大理国是以白蛮为主体的多民族联合体。
元明清时期,云南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分布与族称同现在大体相近。元灭大理国之后,云南建行省,地方割据政权从此不复存在,现今云南各少数民族及其地域分布大体形成。
二、儒学对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的影响
据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看,儒学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约始于两汉时期。西汉武帝时,以“滇”国之地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命其“复长其民”。[1](P.2997)同时武帝采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王朝思想文化的这种意识形态变局,也会远播云南边陲,产生一定传播和影响。因为汉武帝所派官吏,司马迁南巡等,其思想行为不可能不携儒学文化以播撒。《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肃宗元和(公元84~86年)中,蜀郡王阜为益州郡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肃宗即东汉章帝。该时期的益州郡太守王阜,《东观汉记》载其“少好经学”,11岁时赴犍为学经。晋常璩《华阳国志》述其察举孝廉。以此来看,王阜在益州郡兴建学校,所授内容的主体应为儒家文化,进而在当时当地影响所及,“渐迁其俗”。此外,当时儒学在滇东北的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地区),也因乡绅兴学而广为流布,深有影响。“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4](南中志)因犍为的儒学水准颇高,当时多有以儒学致仕者,亦曾有几位犍为人士任朱提太守。受此影响,儒学在当时的播化就可想见了。
在哲学宗教层面,儒学于云南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影响,下述三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标志性特征。
其一是云南纳西族的东巴经。“东巴经”是纳西族特有的原始宗教——东巴教的经书,约产生于公元11世纪以前,是由东巴(“东巴”纳西语意为“山乡诵经者”,即东巴教的“经师”)书写、念诵的经书,纳西语称“东巴久”,即“东巴经”,有纳西族古代社会“百科全书”之称。东巴经是由纳西族的民族语言文字东巴文或格巴文书写而成。
在东巴经中所体现或包含的哲学和宗教观念内,阴阳五行观念具有非常突出显要的地位。阴阳观念在东巴经中汉文音译为“卢”、“色”。“卢”即“阳”,“色”即“阴”,“卢色”也就是汉语中习惯称为的阴阳观念。浓厚的原始崇拜和自然崇拜是云南纳西族民族的观念特征,纳西族东巴经中的阴阳观念,或许主要是通过直观地观察认识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和自然界中的雌雄两性生活习性、生理作用及各自的特殊地位而获得。男女、雄雌交合而生后代在东巴经中称为“奔巴别”,由此又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皆是雄雌、阳阴交合而生,这是东巴经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朴素宇宙观。如东巴经《什罗祖师传略》中说:“天(男、阳)和地(女、阴)……奔巴别,一个海子出现了。”③ 东巴经《多格绍·本绍》说:“在岩头的司把吉补和岩洞的司把吉母两个‘奔巴别’……贤能的九个男儿由此产生,贤能的九个姑娘由此产生……云和风来‘奔巴别’,多格尼神也由此产生。”④ 东巴经中这种阴阳和合的思想观念,大约至明代前后,被纳西族创造并使用的“格巴文”中出现的“_ _”和“__”即阴阳符号所代替,就是说“__”、“_ _”分别代表东巴文中的“卢(阳)”、“色(阴)”,包括“卢、色”的读音和含义都完全地移植到了“__”“_ _”这两个符号上。“__”、“_ _”是汉文儒典《周易》的基本卦画,阴阳交错、对立统一而生变化,是《周易》的基本思想观念,因此可断定,儒学《周易》文化的阴阳观念明显地影响了古代纳西族的“卢(阳)”、“色(阴)”观念。⑤ 因为纳西族的“卢、色”即阳阴观念,从东巴经来说,其最早形成也在我国的唐宋之际,而《周易》阴阳交感而生变化的观念,在此前的千载之上就形成了,并且从上述云南纳西族等诸少数民族的形成演变及与汉族融合的历史状况分析,也能够曲折地反映出纳西族先民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迹象。
与“卢色”即阳阴观念紧密相联系的是东巴经中的五行观念。五行在东巴经中按音义结合译为“精威五行”或“精威五样”⑥。精威五行从内容和性质来说,指的就是通常所说的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东巴经认为,精威五行是由世界混沌未分之气,分为阳(神)阴(神),即“卢神”、“色神”,也即“上面的佳声”和“下面的佳气”,二者结合变化而形成的。东巴经《驮达给金布马超度吊死鬼之经》说:“很古很古的时候,最初……先从上方出了佳声,从下面出了佳气。佳声、佳气结合变化,出现了最初的精威五行。”⑦ 东巴经有五行、五方和五色相配的观念。东方属木,木色青,故为青色;南方属火,火色红,故为红色;西方属铁(即金),铁色白,故为白色;北方属水,水色黑,故为黑色;中央属土,土色黄,故为黄色。东巴经中有这种五行、五方和五色,甚至还有天干、地支等互相联系和结合的观念,这里我们至少需要提出和考察两个问题:一是纳西族东巴经何以能够产生和形成这样的五行、五方等观念?二是纳西族东巴经的这种观念又何以与儒家五行五方等的观念完全一致?进行这样的理性思考,似乎仍然只能从两种文化的历史发展联系中来寻求回答。战国至秦汉间形成的儒典《礼记》,其中《月令》篇的一个重要观念,即春夏长夏秋冬五时分别属于木火土金水五德和东南中西北五方,并且有青赤黄白黑五色。董仲舒《春秋繁露》说:“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5](五行之义)不难看出,从先秦至汉代,阴阳五行的观念在华夏文化中已经相当普遍地流行,深深地蕴藏于人心,构成为一种文化景象,特别是在庙堂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这样的观念文化,必然会随着中华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渗透融合和交流而发生传播影响作用,由此仍然可以判定,纳西族东巴经“卢色”和“精威五行”(即阳阴和五行)文化观念的产生和形成,就不能排除是受到了儒家文化阴阳五行观念长期深入影响的结论。东巴经是纳西族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文化中包含着儒学文化的内容和成分,或者说其中有些内容或文化成分与儒学文化是相同或基本一致的;儒学文化的辐射传播,影响所及,也渗入和流淌到了纳西族这一少数民族的文化血液里。
其二是云南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儒释”和“释儒”。云南大理地区的白族在我国唐宋以后举族信佛,苍山洱海间有“佛国”、“妙香国”之称。⑧“滇之佛教,传闻于汉晋,兴隆于唐宋,昌于元,传于明,而衰落于清。”[6](卷一○一)据文献载,云南白族所传佛教在元代以前的南诏大理国时期主要是密宗阿吒力教,在南诏大理一度具有国教地位。南诏以来大理地区的佛教,是从印度和我国内地传入的,然而其佛教典籍却多为汉文。南诏史籍中多有“遣使入朝受浮图像并佛书以归”和“所诵经律,一如中国”的记载。近年来在大理地区发现的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的佛经写本,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自心印陀罗尼法咒语》等密宗经典,皆为汉文写本。大理国亡后,密宗随之衰落。至元代代之而起的是从中土传入的禅宗佛教。
奇特的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僧侣被称为“师僧”或“儒释”。这是因为这些僧人往往是饱读儒书的佛教弟子,同时他们在佛寺中又教儿童念佛经,读儒书。佛寺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成为传授弘扬儒学的地方。元郭松年《大理行记》载:“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7](P.23)师僧即儒释。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僧侣虽然是僧人而却用俗姓,崇释同时习儒,有“其流则释,其学则儒”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儒释”或“释儒”。“儒释”之称最早见于《南诏图传·文字卷》,曰:“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辨今之流。”这些儒释显然在现世的活动是既佛学修行,又儒学修身;既出世事佛,又入世从政,是集儒、佛于一身的僧人。现存于昆明的大理国经幢《造幢记》,就是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其记曰:“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部众洞明儒释慈济大师段进全述。”据题记可知,石幢是大理国“议事布燮”袁豆光所建造。《新唐书·南诏传》载:“官曰坦绰,曰布燮,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决国事轻重,犹唐宰相也。”即袁豆光是一位官居相当于宰相之职的“释儒”僧侣,而段进全则明确被称为“儒释”、“大师”。现存于云南省姚安县的《兴宝寺德化铭》亦即《褒州阳派郡嵇肃灵峰明帝记》,则是大理国元亨二年(公元1186年)大理崇圣寺时任“粉团侍郎”的僧人杨才照所撰。杨才照自称“释儒”,即碑刻有“皇都崇圣寺粉团侍郎赏米黄绣手披释儒”。元朝时,在滇弘扬佛教禅宗的雄辩法师,曾长时期在中原学佛,具有较高的汉文化功底,归滇后在他的弟子中有位名玄通者,据悉是“赋性聪慧,辩博渊敏,于吾儒经史子传,百氏之书,靡不研究”[3](P.110)。明朝时,大理荡山寺(感通寺)法师无极,能知性学,兼通辞章,透悟宗旨,博通儒书。他们也可以说是后来的“儒释”。
值得研究的是,云南南诏大理国时期儒释何以得以形成和存在发展?首先恐怕要归因于当时政治上的开科取士制度。此种制度与同期产生、流行于隋、唐、宋三朝的科举制度有一定差别,即大理国“开科取士”的标准是“通释习儒”,既懂佛教义理,又谙儒家典籍与理念的佛教徒,是科考录用的对象。“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是大理国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其次,要归因于中原统治者“用夏变夷”观念和策略的推进,以及当时云南地区逐渐形成的儒学风尚。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8](滕文公上)南诏从建诏之初就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历代南诏王都积极学习汉文化,唐王朝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屡次将《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赐给南诏,南诏王异牟寻“颇知书”[9](P.7489)。唐天宝间的儒官郑回,流寓南诏后,被礼聘为师,任清平官,积极派遣大批贵族子弟赴成都、长安学习儒家典籍,儒学因而在西南盛传。《旧唐书·南诏传》云:“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甚受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另教其子寻梦凑。”又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也捶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新唐书·南诏传》也说:“郑回者,唐官也……阁罗凤重其淳儒……俾教子弟。”
其三是成就了一批云南少数民族儒士。据云龙纂民国《姚安县志》载:“逮至明季,邑中先哲,袭宋明理学,阳儒阴释,力事提倡。”姚安位于滇中偏北,是彝、白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秦汉以降,逐渐地既有佛教兴盛,又有儒学昌隆,除上述的儒释者外,元明清诸时期尚有不断涌现出来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儒官、儒士,形成了云南历史上又一道儒学弘扬的文化景观。元代世祖时任云南平章政事的赛典赤,回族人,治滇期间以儒家“德政教化”为宗旨,行“宽仁之政”,重视兴办教育,倡导儒学,于公元1276年在昆明五华山右,建成云南第一座孔庙——昆明文庙,开云南庙学风气之先,当地少数民族“虽爨僰亦遣子入学”,使儒学在云南得到倡扬。李元阳是明代白族中的一位颇有影响的宿儒,嘉靖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辞官返乡后归隐多年,读儒释道三家之书,潜心性理之学,著述颇丰,亦可称之为是一位释儒。清初姚安知府高奣映,白族,凡经史百家,先儒论说,佛教典籍,辞文诗赋,皆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特别是治宋明儒学和佛学,很有建树,著作丰厚,影响所及,几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比肩⑨。清代云南另一白族知名儒士王菘,可谓是白族史学家和经学巨擘,曾主讲山西晋阳书院,受到敬重,回到故乡云南洱源,整理自己长期研究儒学的心得,著述丰裕,且在白族乡民中影响深广。
三、儒学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思想文化的主要原因
儒学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思想文化中逐渐广泛深入地传播和影响,从根本上说是该地区少数民族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对儒学文化的价值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文化前提和思想观念基础,否则儒学文化不可能得到传播和产生影响作用,甚至只能是受到拒斥或者抵制。纵观和综察该地区少数民族发展之情状,政治上的治乱统分、文化上的高下明暗、社会上的和融与邪乱、道德上的长幼尊卑观念等等,基本上或至少大多是以儒家思想为其评判标准的。如云南历史上有较多与少数民族有关的碑刻,所反映出的内容常常以儒家思想为主。立于东汉桓帝永寿年间的孟孝琚碑言其碑主——“南中大姓”孟孝琚“十二随官授韩诗,兼通孝经二卷”;晋代南中大姓的大小爨碑不仅把爨氏祖先追溯到炎黄,而且碑文中“孝”、“弟”、“忠”、“信”等观念充溢其间;唐时的南诏德化碑有“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的碑文,南诏的乌蛮、白蛮上层通过碑文表明其明日月阴阳、君臣尊卑之道,希望唐王朝“容归之”,恢复臣属关系;宋时的云南大理国经幢,虽是佛教石雕,刻有汉文《造幢记》,儒家思想仍然浸透其间,例如刻有“君臣一德,州国一心”,“尊卑相承,上下相继”,“至忠不可无主,至孝不可无亲”等文字内容。明代白族学者杨黼的《山花碑》,是奇特的汉字记述白族语音的“白文”碑,文中有“才等周文武”、“敬孝”、“仁礼”、“尧天”等儒家思想相贯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云南的南诏政权异牟寻时期,在之前与唐王朝交恶几十年后,曾认识到“中夏至仁”,南诏“人知礼乐,本唐风化”,“业为蕃臣,吞声无诉”,异牟寻是一位“颇知书”识礼之王。宋时的云南大理国,“大理”之名来自“大礼”⑩,“礼”、“理”皆儒。大理国的国王有名“思平”、“思良”、“素顺”、“素廉”、“连义”、“正淳”,及年号为“文德”、“文经”、“至治”、“明德”、“广德”、“正治”、“正德”者,儒家文化的价值思想观念溢于其间。
儒学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思想文化中逐渐广泛深入地传播和影响,又是儒学文化领先和高于该地区少数民族哲学观念和思想文化的结果。与我国各少数民族一样,历史上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远远落后于内地汉族社会,当我国的封建社会有了长足发展的情况下,其还处于原始社会或者农奴社会的状态,作为社会的经济、政治等的精神反映的哲学和思想文化观念,当然也是比较原始或者落后的。人们通常从文化的“势能差”来说明看待先进之于落后、高端之于低位的关系,我们觉得从反向来认识这一问题,处于落后、低位的哲学和文化状态下者,也具有一种对于高端和先进文化的期盼、接受、容纳、景仰、融摄的态度和心理。因此总体来看,历史上儒学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影响是逐步呈现增强效应的。
儒学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和思想文化中逐渐广泛深入地传播和影响,还在于二者之间多向度的思想文化交融激荡,产生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种多向度的思想文化交融激荡中,包括经济的、贸易的、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等等,其中政治文化之间的密疏关系始终是具有决定性和主导性的方面。政治亲密,臣属羁縻,或置郡县治理,在云南少数民族进步中,往往儒学亦兴盛,文化亦发展。反之,二者政治疏远甚至交恶抗衡,儒学传播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则极其不利。但是尽管如此,汉文化或儒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涵化整合、沟通交流,仍然能够通过经济、贸易、宗教等其它形式或途径而发生。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称:“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乱之世,尝与中国抗衡。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7](P.20)元李京《云南志略》云:“天运勃兴,文轨混一,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圣化溥博,何以臻此。”[7](P.84)从云南的大理国时期来看,云南与宋王朝官方间政治文化的交流大为减少,而民间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增加。大理国曾主动热切地希望发展与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关系,然而宋朝则以自身安全为由,拒之千里之外,多次阻绝大理国的友好通使,致使云南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交往缺乏宋朝官方的大力支持,官方政治文化交往的通道被阻绝后,势必造成中原汉文化传输云南的衰减,云南难以及时地得到和吸收中原文化的最新发展成果。然而,两宋王朝为了得到大理国的战马,曾经通过广西大量购买大理马,大理国商人也利用卖马的机会,到广西采购中原文化用品和典籍,以此补充通过官方渠道传入中原文化的不足。如“乾道癸巳(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10](四裔考六)。不难发现大理国人求购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是汉晋时期儒家经解和史注之书,如《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等,它们都是唐代以前中原儒家学说研究的代表作品,即汉学论著;二是学习汉语所需的文字声韵工具之书,如《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等等。在我国的儒学发展史上,汉晋至隋唐时期,主要以训诂和考订儒家经典的章句文字音韵为主,这一时期的儒学也被称之为汉学;两宋时期,儒学的研究则发展为解说儒家经典中的义理为主,被称之为理学。在唐代以前,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受到王朝官方的支持和保护,交流频繁,文化传输不仅量大,而且迅速,中原文化发展的最新成就和变化都能很快地传入云南,而大理国时期中原儒学发展到以儒家义理为宗旨的理学阶段,理学之书却难以在云南的大理文化中找到踪迹,以至大理国商人专程到广西求购中原文化书籍的这份书单,也还仍然停留在唐代以前儒学研究的“汉学”阶段,这不能不让人结合两宋王朝对大理国的方针政策,考虑到这一时期官方政治关系断绝,给文化交流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形成了历史上中原文化传输云南的一个衰减期,以至于赛典赤治滇,初入云南时强烈地感受到“云南子弟不读书”、“不知尊孔孟”。其实云南子弟非不读书也,是没有读当时盛行的理学之书;非不知尊孔孟也,是没有像这一时期中原内地那样,在理学强烈影响下,竭力抬高孟子学说的地位和研学程朱之学。至于云南大理国时期的“释儒”文化现象,则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成为大理国统治文化的趋势。大理文化将儒、释融合为一后,积极吸收土著文化,主动适应统治需要,并促成了来自中原的汉(儒)文化、来自南亚、东南亚的海洋文化和当地的土著文化相互涵化、融洽、整合,达到统一,进而推进了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1-04-20
注释:
① 僰道:今四川宜宾市区。
② 羁縻州,唐、宋两代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
③ 和正才(讲述)《什罗禅师传略》(周耀华译)[Z].丽江:丽江县文化馆,1963.转引自萧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2页。
④ 和芳(讲述)《多格绍·本绍》(周汝诚译)[Z].丽江:丽江县文化馆,1964.转引自萧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第252-253页。
⑤⑥⑦ 参见萧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2-253、272、273页。
⑧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云:“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明)谢肇淛《滇略》(卷四)载:“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教人捐配刀,读儒书,讲明忠孝五常之性,故其老人皆手捻念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一岁之中,斋戒居半。”
⑨ (民国)云龙纂《姚安县志》载,“清季北平名流有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
⑩ 《新唐书·南蛮中》载,南诏第12代王世隆,“其名近玄宗嫌讳”,唐即停止了对南诏王的册封,于是世隆“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后来段氏段思平取得政权而得国,沿用“大礼”并改称“大理国”,且都城亦在原址并改羊苴咩城为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