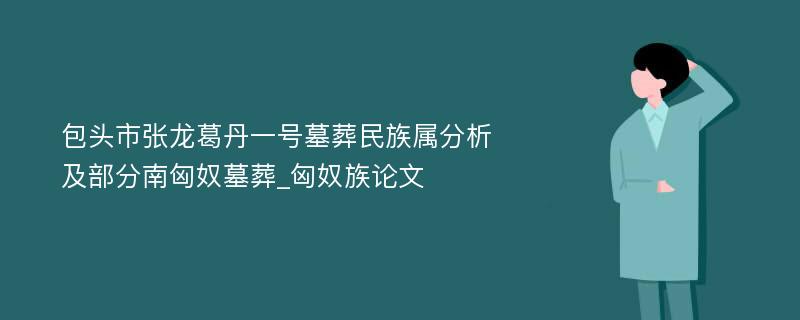
包头张龙圪旦一号墓的族属及部分南匈奴墓葬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头论文,墓葬论文,匈奴论文,张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6-0137-07
张龙圪旦墓地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南郊麻池乡麻池村西,东北距麻池汉代古城约1公里,1995年包头市文物管理处清理了位于该墓地西北方的张龙圪旦一号汉墓。该墓为多室砖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及其左右耳室、中室及其左右耳室、后室组成,甬道中间另有一小室,该多室墓以甬道为中轴线左右列布。该墓地上有封土堆,墓道在北,方向357度;墓室(含甬道)总长17.6米,总宽13米,是包头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墓室最多的汉墓,其时代约在东汉后期[1](P266-274)。前室至中室的甬道和中室四壁壁面上残留有壁画,可辨认的有带题榜的人物形象。另见一画像砖,图案刻画相对奔驰的二马形象,风格粗犷。
该墓被严重盗扰,出土的40余件随葬品以汉式器物为主,多为陶器,仅见泡钉和2件带銎小件铜器,有较多的石器如石屋、石碑、石虎础和虎头残件、砚等。陶器基本上与同时期中原地区汉墓所出者没有差别,如彩绘陶盒、陶罐、豆、灶、楼、案、樽、耳杯、盘以及人物、动物俑等明器。关于该墓葬的族属,发掘者最早提出“这种典型明确的殉牲习俗,反映了东汉后期包头地区各民族间错居杂处相互交往、融合的史实”[1](P266-274)。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张龙圪旦一号墓从墓葬形制到空间布局、随葬品的种类以及石屋的意义均符合典型的汉人墓葬的特征,“认为该墓在营造时突出了对墓内祭祀空间的重视,体现出东汉后期中国丧葬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其文化属性应为汉墓”[2]。
的确,东汉时期的匈奴墓因其汉化程度之深几乎难以辨识,墓葬形制、随葬品、壁画、石碑、享堂等汉代丧葬文化对匈奴的同化是全方位的,几乎使其民族丧葬习俗的特性丧失殆尽。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M1为东汉末期砖室墓[3],如果不是出土一枚标明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墓葬从内而外几乎没有丝毫反映墓主人民族身份的匈奴传统文化因素。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双室砖室墓,穹隆顶,有棺椁葬具,地面有圆形封土堆,出土有连弧纹铜镜、五铢钱及陶质罐、壶、仓、灶、井等明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均与中原汉墓无异。仅因出土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驼纽铜印章而被确定为南匈奴墓。墓地中其他墓葬尚可见到一些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印迹,如M3出土的银壶和石饰、M8出土的指环及殉牲马牛羊狗骨的现象等;墓地出土的铜带扣、环、玉石、玻璃、琥珀、骨质筒、簪等装饰品和刀、削、镞等小件器物以及马衔、马镳、铃等马具,颇具少数民族特征;除此而外,墓葬形制、葬具及陶明器组合等绝大多数随葬品均与东汉晚期汉人墓相同。据以判断墓主人族属的依据主要是随葬品中零星的匈奴特征器物和殉牲的习俗等。后经三例头骨鉴定显示出墓主人以北亚人种为主而兼有东亚类型的特征,反映了其主要遗传基因来自北亚蒙古人种,说明该墓主人确为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后裔,只是他们经过百余年与汉人的错居杂处,从习俗到人种都已汉化很深。墓主人在体质特征上融入少量汉或当地羌人的血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陕西神木大保当[4]东汉早期到中晚期的匈奴墓地,同样汉化极深,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基本与内地汉墓完全相同,亦可见到汉人流行的画像砖(石)墓,仅见少数墓葬随葬个别匈奴文化常见的波浪纹陶罐、骨勺、骨筷等器物,据其地域和时间范围,两汉时期这里是安置降汉匈奴人的地方,也可能有部分南匈奴人入居这里,再加上上述零星匈奴文化特征而判断其为匈奴墓。根据人骨鉴定结果,其人种表现出与北亚类型者明显接近,东亚成分的混杂是在分裂以后南匈奴入居汉地与汉人错居杂处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的。所以这两例汉化匈奴人墓葬的身份鉴定,通过人类学鉴定结果得以验证。同时可以肯定的是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后期,匈奴墓葬从形制到随葬品已基本汉化,但反映其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的深层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内容还相对较多地被保留下来。因此,根据零星保留下来的殉牲现象和少量匈奴特征的器物而判定墓葬主人的匈奴族属,在实践中是可行的,有科学依据并且是得到以往考古发现验证的。
南匈奴人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优厚待遇,经济上仰赖汉的援助和赏赐,政治上成为汉王朝管辖的一部分。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汉人朝夕共处、长期交往,自然会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自此百年之后,南匈奴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匈奴文化迅速融合、同化于汉文化当中,成为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匈奴上层集团,因更多和更深层次地接触和吸收汉文化,对汉文化的钦慕更甚,汉化程度也更深。南匈奴人常年派遣质子于汉都城,接受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使其具有很深的亲汉倾向。在长期的交往共处过程中,匈奴人与汉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东汉政府恩威并施的管理策略,也使得南匈奴人对汉朝既感恩戴德又充满惶恐。正如章帝章和二年(88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向窦太后上书所言:“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惭无报效之地。”[5](卷89)单于安国时期的左谷蠡王师子勇黠多知,多次将兵出塞,与汉将配合掩击北庭,受到天子赏赐和特殊待遇,因而与单于安国之间产生嫌隙,单于每龙会议事,师子辄称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而南匈奴“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可见当时南匈奴人心皆向汉。延光三年(124)夏,南匈奴发生“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反叛,胁(温禺犊王)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南匈奴人向化归慕之心、效忠之义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是被汉政府授以官职爵位的匈奴上层贵族,不论其出于主动归化还是被动同化,其民族传统的因素越来越少是不争的事实,表现在墓葬特征上则是自内而外、从墓葬形制结构到随葬品完全的汉化。
南匈奴作为丧失了政权独立性和民族自豪感而依附他人生存的遗民心理和投降归化的外族特有的惶恐心态,对于故国旧俗都不得不表现得更为健忘和鄙弃,反映在史书中则出现了归附鲜卑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自号“鲜卑兵”,再者匈奴民族性格中具有非常务实逐利的一面。如战斗,“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生存法则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追随强者,他们崇尚勇猛、弱肉强食、贵壮贱老,没有汉人所谓的气节、操守、孝悌、伦理观念,以通俗的语言讲即“有奶便是娘”,这也是南匈奴在特定环境下投靠汉朝、追随汉朝、学习模仿汉人的根源,这与自号“鲜卑兵”、迅速鲜卑化的匈奴人如出一辙。不难想象,投向汉朝的南匈奴人必定不再有其祖先曾有过的“胡者,天子骄子”的自豪与光荣。而在墓葬的形态和埋葬礼仪制度上则表现为恪守汉人礼仪制度过犹不及,往往表现得比汉人更像汉人,正是这种外族降者特殊心理的折射。这是东汉时期南匈奴贵族墓葬形态结构几乎无法区别于汉墓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表层文化的背后,在不显眼的细节之处,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内核、蕴涵民族记忆和民族情感、民族意识和审美取向的某些传统习俗,即使已变得支离破碎,但也仍然在个别匈奴人当中被小心的保留下来,诸如反映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的殉牲、肩饰波浪纹的陶罐、多样的匈奴风格的装饰品等较多地被保留下来。一般而言,相对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往往具有更持久的牢固性和稳定性,它渗透在人们的血液中,根深蒂固,比起表层的、物化的特征,这些习俗不会轻易地被改变。所以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最能真实地反映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这些遗迹遗物中殉牲习俗和服饰装束显然与中原民族截然不同,虽然在物质上已经很大程度地汉化,但仍可从中看到自身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绵延。因而即使当匈奴文化被淹没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这些匈奴人与汉人错居杂处,甚至其墓室的修造都可能是出自汉人工匠之手,但他们依然在墓葬内部不明显的细节处,小心而虔诚地保留下来某些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印迹。当这些细节从多个方面汇集到一起时,则显然不是偶然和巧合了。
检视张龙圪旦一号汉墓中细微之处表现出的民族特殊性,可以看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汉人墓葬,从而显示出匈奴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特征。
1.墓室中使用牛、马、羊头骨殉牲。前室四角各置二羊头骨,后室中部放一牛头骨、一马头骨,填土中还见较多零散的动物骨骼;以马牛羊头蹄殉牲是信仰万物有灵的匈奴萨满教动物崇拜的产物,是匈奴典型的葬俗和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这是匈奴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体现。而包头地区又是南匈奴王庭和匈奴主体活动的中心范围所在,在墓葬和填土中所发现的殉牲种类和使用兽头的形式与典型匈奴墓葬所见者完全一致,恰恰反映了匈奴人在葬礼和下葬后祭祀活动中反复强调的这一信仰主题。
2.出土人骨下垫有皮革状物残片。文献记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6](《匈奴传》)。墓中这些特征几乎就是匈奴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无不与畜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3.画像砖所刻画的相对奔驰的二马形象、头对头身体扭曲的双马形象从题材到表现手法都为匈奴惯用的艺术题材和表现手法;石屋屋顶垂脊上装饰的双兽尾尾相对,与匈奴墓葬常见的动物纹饰牌构图亦有相似之处。
4.墓葬附近采集有肩部饰有波浪纹的夹砂陶罐残片,这是匈奴文化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在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墓中普遍随葬这种造型和装饰的陶罐,在宁夏同心倒墩子和李家套子、内蒙古鄂尔多斯补洞沟、准格尔旗大饭铺等匈奴墓中均出土有几乎完全相同的陶罐。
5.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头向北是最为普遍的葬式。匈奴人“长左而北向”,以东为上、以北为尊的观念反映在墓葬上则是墓向绝大多数为南北向,头向北或略偏西北、东北。而汉人墓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后者往往墓道在南,死者头朝南,包头和周边一带发现的数百座汉墓基本也是这种情况,头向北者极其罕见。但张龙圪旦墓葬头向北的现象就显得十分特殊。即使受到所在地地形地势的限制,也不可能如此巧合。
6.随葬陶俑中的一件标本M1:11为一发型奇特的披短发的所谓男性胡人俑,与汉代常见的陶俑形象殊异。与这种发型几乎完全相同的披短发男俑在杭锦旗乌兰陶勒盖[7]、鄂托克旗凤凰山M1[1](P161-175)中也有发现;在包头召湾汉墓也出土了一件戴帽男俑,头顶、两鬓发向后梳,前额、脑后披发。此类俑主要出现在包头、鄂尔多斯及其周围地区,年代均在西汉晚期到东汉后期。西汉以来这一带就是汉政权安置匈奴降人的地方,东汉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匈奴归附汉王朝后,又先后建庭于“去五原郡(包头市)西部塞八十里处”和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西河美稷县(鄂尔多斯准格尔旗),所以这里是南匈奴活动的腹地,此类披发陶俑的出土地点集中于此,当不是偶然。而按文献记载,匈奴人的发型主要是“披发椎髻”。
张龙圪旦M1在包头的发现并非孤立现象,作为匈奴降人与南匈奴活动的核心地区,鄂尔多斯及包头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多发现有零星的匈奴文化因素,如殉葬牛马羊头蹄的葬俗、出土胡人俑及常常伴出反映汉匈关系的“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等文字瓦当以及“汉匈奴栗借温禺鞮印”等由汉颁发的官印。上述地区曾经是匈奴故地,西汉中期匈奴北撤之后,又是安置降汉匈奴人的属国地界。汉武帝时设天水、安定、上郡、西河、五原属国都尉等机构管理归附的匈奴人,南匈奴回归后,先安置在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后移置云中、西河美稷,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处列置诸部王,匈奴人口增长迅速。到公元90年前后,已达二十三万七千三百人。他们与汉族错居杂处,已经逐步从事农业生产,汉化的程度相当深。上述墓葬均在南匈奴的活动范围内,并或多或少带有典型的匈奴文化遗痕,大多与各时期人居汉地的匈奴人及其后裔相关。同时期的汉人墓可能在某一个细节上受到其点滴的影响,在这里汉人墓中流行的壁画和画像砖的表现手法也沾染和流露出匈奴遗风的点滴痕迹,比如鄂托克旗凤凰山M1壁画墓中,戴宽沿圆顶帽的壁画人物形象、尾尾相对的动物图像并伴出披发男俑等,明显受到匈奴文化艺术的影响[8]。召湾汉墓M91填土中发现零碎的动物骨骼、某些类似于匈奴器形的陶器,但因其出土有残墓志而判断其为汉人墓。而这些墓葬中所见的零星匈奴文化因素,可能是墓主及其家人习染胡俗,甚至很可能是在绘制壁画或下葬过程中有习染胡俗者参与等偶然因素所导致的,而其前提条件则是存在像张龙圪旦一号墓一样具有更集中、更丰富、更典型的匈奴因素的墓葬作为其效仿的对象。目前所见该地区范围内绝大多数具有匈奴因素的墓葬无一比张龙圪旦一号墓所见匈奴因素更为集中。如张龙圪旦M1诸多特殊的具有匈奴特点的因素集中出现在一座墓葬当中,则应排除其可能性和偶然性,当属于墓主特殊的民族身份决定其有意识地用多种方法隐晦地表现其文化信仰和传统,故而出现诸多零星的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和痕迹汇聚于一墓之中,这实属必然。
如果说生活在匈奴聚居地的汉人长期处于浓厚胡文化的熏陶之下而习染胡俗,也不排除他们可能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而在死后也有可能效仿匈奴人以动物殉牲,甚至随葬一两件具有匈奴风格的饰件、留下点滴具有匈奴特点的痕迹都是可能的。但前提是同时期的匈奴人还大量保有自身的这些传统,使汉人有模仿的文化氛围和对象。如果张龙圪旦M1墓主属于汉人,则应有更多的至少比张龙圪旦M1具有更典型的匈奴因素的墓葬在包头及其附近地区大量存在,但是迄今除了周边地区发现的东胜补洞沟[9]、准格尔旗大饭铺[10]、陕西神木大保当以外,张龙圪旦M1算得上包头地区迄今所见蕴含匈奴文化最为集中的墓葬。以目前该地区发现汉墓的地点和数量与当时人口比例相对照而论,说其中没有南匈奴墓葬或南匈奴墓葬尚未发现是说不通的。退一步讲,假设张龙圪旦M1的主人真的是汉人,在匈奴人已经汉化极深且绝大多数旧俗在墓葬中已消失殆尽的情况下,这个大墓的主人作为一个有一定地位甚至地位相当显赫的汉族官吏,反而逆势而行将匈奴人已经摒弃的习俗奉为正朔,郑重其事的在庄严神圣的葬礼中使用落后民族的葬俗、随葬具有匈奴艺术风格的陶器和画像图案也是不可理喻的。
东汉时期匈奴文化已经走向衰落,而入居汉地的南匈奴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性,在领土上失去了自主权,任由汉朝廷随意调遣,连单于王庭也被反复更换迁移,先是五原后到云中,再到西河美稷,直至建安时期被一步步分化瓦解,南匈奴单于也被曹操扣留邺城。处于强大的汉民族优势文化的包围之中的南匈奴,仰赖汉朝供给、援助和保护而生存,不仅其所处之地汉朝政府设有郡县、行政长官和军队,而且还有针对匈奴部落的管理机构和军队,先后有西河长史、中郎将和度辽将军等,管理和监督南匈奴各项内部事务,参辞讼、察动静,一切军政大事都牢牢掌握在汉人手中,南匈奴单于在大事上几乎毫无自主权,甚至南匈奴单于及其上层贵族的升迁沉浮、生杀予夺等都牢牢掌握在汉人手中。如单于安国在汉兵追击下被手下所杀;去特若尸逐就单于及其弟左贤王因平定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叛乱不力,被五原太守陈龟逼迫自杀;伊陵尸逐就单于亦因被责不能统理国事而被中郎将张奂拘押;单于呼徵刚即位一年因与中郎将张脩不合,被张惰斩杀,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等。在这种情况下,匈奴自身的文化传统已丧失了存在的土壤,只能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迅速汉化并被融入汉文化,这种融合不仅仅限于物质文化的层面,而且其深层的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等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传统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萨满信仰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如匈奴人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的龙城大会,不仅祭祀天神,还兼祠汉帝。不可否认,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是相互的,但其背后起作用的却是各自的实力。匈奴文化在其最繁荣的时候,其文化在交流中处于强势和主体地位,曾极大地影响了鲜卑、乌桓、西域诸文化,对中原文化也曾造成不小的影响,匈奴骑术、射击、服饰如动物纹金属饰牌的确远播内地,在山东洛庄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甚至远及广州的南越王墓中都发现有匈奴风格的动物纹饰牌。但在匈奴日渐衰落特别是南北匈奴分裂后,其文化的主体地位也随之衰落。当时其东方曾经是匈奴附庸的鲜卑崛起,占领了匈奴故地,鲜卑文化的影响和扩张逐步增强,这时的匈奴文化已被动地处于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和客体地位。如补洞沟匈奴墓中所出铜鍑就明显受到鲜卑文化的影响。文献记载匈奴人十余万落并入鲜卑,皆自号鲜卑兵[11],更连自身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都完全丧失了。匈奴与鲜卑原本就有很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文化特征,但前期是以匈奴文化为主导因素对鲜卑文化造成影响,到东汉时期匈奴则成为被动的受体,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鲜卑文化的较大影响,直至完全的鲜卑化。同样,匈奴与汉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也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而变化。作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南匈奴上层,也竭力攀附汉室,自称刘邦之后,改汉姓、取汉名,效仿汉人读儒家经典。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匈奴墓已经完全采用了汉式风格和丧葬制度,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保存自身一些零星的传统已属不易,其文化的影响力当十分有限。当时绝对强势的汉文化在逐渐同化消弭匈奴文化的过程中,怎可能如此反其道而行且大量采用弱势的、正在消亡的匈奴文化因素呢?
如果说像张龙圪旦M1这样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不属于南匈奴墓,那么目前在国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几乎找不到一座更可信的南匈奴人的墓葬了。已确认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匈奴墓和陕西神木大保当匈奴墓葬也都没有如此多的匈奴因素,前者除了有一枚印章、后者除了较多的骨器和零星的陶罐外几乎完全汉化了。相较之下,张龙圪旦M1所包含的墓主人的民族身份的信息,在同时期可考的南匈奴墓中应是比较丰富和明确的。在匈奴人的活动地域和时间范围内,又出现了较多的匈奴文化特征,如若不是匈奴墓,那只能说到东汉后期匈奴这个民族就已完全消失、被同化为汉人了。但这又不符合历史事实,东汉末南匈奴单于羌渠、於扶罗、呼厨泉等仍统领自己的部众,匈奴贵人仍是其首领,直到南北朝时期匈奴部众仍具有相对独立的活动范围并具有自己的民族统帅和领袖,民族意识还相当强大,成为逐鹿中原的“五胡”之一,曾先后建立汉-前赵、北凉、大夏等多个政权。
据文献记载,附汉的南匈奴部众为四五万人,在单于屯屠何在位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永平二年(90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5](卷89)。曹魏时,分匈奴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帅刘豹统辖万余户,居太原郡故兹氏(今山西临汾);右部六千户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北部四千余户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南部三千余户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中部六千户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上述共计三万余户,人口近二十万,至少有数万匈奴人口。那么这些南匈奴人墓葬在哪里?而相比于西汉,东汉时期五原等地的汉族人口却是大大的缩减了。《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五原郡人口达到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云中郡人口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定襄郡人口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从王莽执政到东汉初年,匈奴的侵扰再起,羌人卢芳割据朔方,饱经战乱的边郡人民颇多内徙。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五原郡人口从西汉时的二十三万余骤减至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七,复置的云中郡人口减至二万六千四百二十口,定襄郡人口减至一万千五百七十一口[5](卷19)。正如学者张海斌所关注到的:在汉族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迄今发现的东汉后期墓葬数量与西汉时期墓葬相当,其中必定包括了汉化的南匈奴人墓葬在内,并且应占相当大的数量。仅仅因为匈奴人汉化速度极快、汉化程度也相当深,致使我们很难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反映的主流文化因素当中将其辨别出来。在1998年出版的《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一书公布的80年代末以来在巴盟、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和乌盟地区发掘的251座汉墓中,仅在可数的几座墓葬中残留有匈奴文化因素。这一考古发现反映出匈奴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的丧失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再一次验证了中原文化强大的兼容性和凝聚力。
依据墓葬结构判断文化属性的方法显然对于南匈奴这一特殊群体不能适用,在整体汉化的大背景下,甚至这些墓葬建筑本身都很可能由汉人工匠来完成,体现民族身份的元素已被减少和隐藏到最微小和隐蔽的细枝末节之中。即使在匈奴聚居地我们也只能从当地汉墓中一些与一般汉墓风格迥异的出土物——披发胡人俑、鹿羊虎等动物形金箔、桦树皮器、骨筷、骨勺、骨鸣嘀、带有华丽的枝状角的鹿形器物等蛛丝马迹中去寻觅匈奴人存在的痕迹。匈奴传统在整个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已经完全处于弱势。但终汉一代,匈奴传统文化中那些融入民族血液中的因素并未绝迹,如包头市郊张龙圪旦[1]、东胜市补洞沟墓地[9]、准格尔旗大饭铺墓葬[10]、神木大保当墓地等,都集中蕴涵了匈奴文化因素。
还有学者以张龙圪旦M1与召湾91号墓、观音庙M1的相似性推导其墓主人族属为汉族,因后者发现“下祁令平原相杨允好……”“孝廉”字样墓碑。但汉化的匈奴人改汉姓、取汉名、习汉字、融入汉俗的情况也十分常见,早在西汉时期降汉的匈奴人中就有改用汉姓氏名号的,如休屠王子被汉武帝赐姓金、名日磾、字翁叔,其子有金赏、金建,其孙有金当;日磾弟金伦,其子金安上,安上四子名常、敞、岑、明,都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封侯、拜相、担任汉朝重要官职的也不在少数。如金日磾就曾封“马监”“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武帝死后遗诏封其为“秺侯”,其死后谥曰“敬侯”;金安上被封为“侍中”“关内侯”“都成侯”“建章卫尉”,死后谥曰“敬侯”;金敞三子分别为涉、参、饶,金涉任“侍中”“骑都尉”“奉车都尉”“长信少府”,金参任“关内都尉”“安定、东海太守”,金饶为“墟骑校尉”;金涉两子名汤、融,皆侍中、诸曹、将、大夫。而涉之从父弟钦举明经,为“太子门大夫……太中大夫给事中”“泰山、弘农太守”“大司马司直、京兆尹”,“……以家世忠孝为金氏友。徙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钦从父弟迁为“尚书令”。武帝时期的赵信,“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后来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失败后又投降匈奴,为匈奴单于谋划“益北绝幕”以及修建储藏大批军粮的赵信城。元朔二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篡位,“太子于单亡降汉,汉封于单为陟安侯”。此类职官名称在南匈奴人中更为普遍,见于文献记载的南单于取汉名的就有“长”“宣”“安国”“师子”“檀”“拔”等。后来的三国两晋时期逐鹿中原的匈奴人更是打着汉室宗亲的旗号以博取人民的支持,如建立“汉-前赵”政权的刘渊及其叔祖刘宣、父刘豹及其子孙刘聪、刘和、刘粲、刘曜、刘暇、刘集等;建立大夏政权的刘勃勃(后改为赫连勃勃),字屈孑,文献记载其为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其父刘卫辰、祖刘豹子、曾祖刘武。现在一般学者认为常见的匈奴改汉姓者有:先、聂、靳、安、盂、毕、隗、郁、次、郎、赵、郭、李、张、陈、范、赵、乘、王、郝、高、都、马、冯、秦、曹、伊、董、成、武、韩、黄、彭、刘、陆、路、姚、伏、封、兰、金、公孙、义渠(渠)、乌氏(乌、邬)、挛鞮(虚连鞮、栾)、呼延(呼衍、呼、胡掖、胡)、须卜(卜)、乌洛兰(兰)、丘林(乔)、隆(龙)、唯徐(徐)、仆固、滹毒(夫、复)、浑(昆)、稠(周)、沮渠(且渠、大且渠、渠、沮)、当于(当)、栗藉(利)、奥鞬(欧)、尸逐(史)、尸寇鞮(寇)、尸末螣(末、莫)、吟乐(乐)、贺兰(贺赖、贺)宇文、綦母、赫连(铁弗、铁伐、弗、杜)、驹连(驹、车)、费连(费)、破六韩(破落汗、破六汗、潘六奚、步六汗、韩)、万俟、拔列兰(梁)、黜门(楚)、独孤(刘)、贺遂(贺悦、贺术、忤城、贺)、盖楼(盖)、娄邱(娄)、仇末仇(仇)等。可见,仅以汉族姓名、官名来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汉代墓葬墓主人的民族身份同样不可靠。若以墓中发现墓碑而论,东汉晚期的南匈奴至少已在汉境内生活了百余年,历经数代,与汉人共存共荣,模仿汉人以墓碑入葬也是情理中事。北周、隋、唐时期的粟特人(安伽、史君、康业、虞泓等)、来自罽宾国的婆罗门(李诞)都使用了汉人的姓名,并在墓葬中均使用墓志,有的仅仅是来华的第一代外国人,在葬俗上还保持较多的自身因素,但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汉人的姓氏和碑铭墓志。所以,以姓氏、官衔判断族属也殊不足信。
东汉时期,包头、鄂尔多斯、陕北一带作为南匈奴驻牧的中心地带,这里应有较多的匈奴遗迹保留,除了以马、牛、羊的头蹄作为殉牲的习俗和随葬品中零星出土的典型匈奴文化遗物(如肩饰波浪纹的陶罐)以及“长左北向”的丧葬习俗表明其匈奴文化特征外,在墓葬形制和结构上已完全汉化了。当然,因为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及归附汉朝的时间先后不同等,使其汉化程度也不完全一致。目前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匈奴墓中,除个别可以根据文献确认属于西汉时期投向汉朝的匈奴人及其后裔墓葬外,大多暂定为南匈奴墓葬,特别是东汉后期的墓葬。宁夏同心李家套子墓地[12]可以认定属于西汉时期匈奴降者的后裔,该墓地在宁夏同心县西北9公里,1983年清理了5座匈奴墓,其中3座形制明确,分别为土圹竖穴木椁墓、长方形砖室墓和1座坑壁和底部用石板铺砌的石棺墓。这座石棺墓因被一条现代水渠破坏了一部分,残高0.40米-0.50米,方向北偏东5度,墓坑四壁用10厘米厚的平整石板砌筑,墓底部也用平整的石板铺砌,葬具和人骨皆不存,但是在墓底发现了6枚五铢钱。由于墓地中还发现了王莽时期的货泉,故李家套子匈奴石砌墓的年代被断定在东汉初期(公元1世纪初)。墓地还出土有镂空铜环、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罐、骨弓弭、海贝等典型匈奴文物,以及汉式车具(车軎)、剑具、镦、环、带扣、饰牌、泡饰、铁鍑、骨器、海贝、绿松石、玛瑙、漆器(奁、耳杯)、货泉和五铢钱等,在附近采集到了长方形透雕青铜饰牌,反映出该墓地墓主人身份等级较高,汉化程度也较深。据文献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首领浑邪王杀休屠王归附汉朝,被封为“漯阴侯”。汉武帝在缘边五郡设属国安置匈奴降者,为汉朝戍边,五属国即在天水、安定、西河、五原、张掖五郡之内。据考证,安定属国都尉治所设在三水县,《水经注》有“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13]的记载。按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县北)[6](《地理志》)为基点,以地望推之,三水县在今同心县境内,那么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墓地应和倒墩子墓地一样是西汉缘边五郡的匈奴移民及其后裔的墓地。李家套子匈奴墓地汉化程度较深,说明这部分匈奴人到东汉初期已在汉地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与公元48年分裂归附的南匈奴无关。
目前被确认为南匈奴的墓葬主要有东胜市补洞沟[9]、准格尔旗大饭铺[10]、青海大通上孙家寨[3]、神木大保当[4]、山西朔县部分汉墓[14]、西安北郊岗寨村M13[15]等,除补洞沟、大饭铺墓葬保留较多匈奴人的传统特征外,其余这些墓葬在形制、埋葬礼仪和出土文物上都与汉墓无异,多为砖室墓、带斜坡墓道、墓向不固定、多有封土等;一般为多人合葬、仰身直肢,随葬品汉化特征十分显著,有汉式陶罐、壶、熏炉、灶、房屋等明器模型及铜钱、漆器、装饰品实用器等。具有草原民族特征的马具、腰饰牌、兵器等物品很少出土,据以判别其为匈奴墓葬的依据主要是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及近底部钻有小孔、肩腹部饰弦纹和波浪纹的典型匈奴陶器和墓内殉牲、墓主人体质特征区别于汉族等。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几乎很难把它们与一般汉墓区别开来。显然,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其民族的整体意识逐步瓦解,匈奴文化也失去了立足的基础,逐渐被强大的汉文化所解构,其传统特征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殆尽。从考古资料来看,其葬俗的汉化程度是相当深的,表明此时的匈奴民族文化已融入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中。这也与史籍记载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
在南匈奴聚居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山西、青海等地发现的汉墓中,必定有一些是我们无法辨认或尚未辨认出的早期匈奴降人或南匈奴墓葬。以内蒙古中南部汉墓为例,其中随葬的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陶罐、俑及殉牲马、牛、羊头蹄习俗的考古学现象,表明有一部分墓葬很可能是汉化了的匈奴民族的墓葬,这种习俗自西汉以来至东汉晚期在该地区一直传承不绝。但因为汉文化特征占据主导因素,已经无法辨认其族属特征了。如包头召湾汉墓,分别于1954年以来多次发掘,共发掘97座墓葬,在附近采集到大量的“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四夷尽服”“千秋万岁”等文字瓦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后期的墓葬中,多次发现有家畜骨骼及方形铜扣饰和马、虎的画像砖,还有较多的随葬陶罐,一些器型种类与补洞沟、神木大保当、张龙圪旦同类器相似。包头地区汉墓中也发现殉葬有完整的狗、羊、骆驼等骨骼及铁项圈饰物,这是匈奴族流行的饰物;墓中出土的陶俑鬓角头发披垂,也是少数民族流行的发式,与史载匈奴人披发椎髻相合。
内蒙古中南部汉墓中发现披发胡人俑的墓葬也较为集中,其所属时代均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这些胡俑的装束和发式皆不同于汉人,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族特征,或反映的是汉代生活在这里的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形象。在这些汉墓中,较多的动物纹金银装饰品、马具、骨器、桦树皮器等北方游牧风格的器物也时有发现。这些异族文化因素相对集中地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有的甚至在同一座墓葬中同时出现多种因素。
在这些具有零星匈奴文化因素的墓葬中,西汉早中期者可能与早期幕南活动的匈奴有关,西汉中期以后者则可能与匈奴降人及其后裔有关,西汉晚期者同时常常伴出反映汉匈关系的“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等文字瓦当,见证了呼韩邪单于归汉的历史事实,东汉以后的则可能与南匈奴有关,在此地采集有“汉匈奴栗借温禺鞮印”等由汉王朝颁发的官印。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一部分是习染胡俗的北方汉人使用殉牲的习俗,他们长期浸染在胡人中间,畜牧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匈奴人相互通婚、逐渐融合,在生活习惯、饮食特征和丧葬习俗等方面相互影响也是必然的。
这些墓葬因其所含匈奴文化因素零星散乱,墓主人到底属匈奴降者后裔、南匈奴抑或是习染胡俗的汉人尚不确定。如果属于后者,那必然应有更多的、较之更具典型匈奴文化特征的匈奴墓葬存在。匈奴下层平民中或许保留的匈奴传统文化因素较上层者更多,而上层者如果还保留较多的匈奴文化因素必定则较平民更为隐蔽。由此,推测张龙圪旦汉墓为东汉后期汉化了的南匈奴上层人物墓葬当可成立。以后若有条件进行人骨鉴定则是检验此结论正确与否的关键。
收稿日期:2013-0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