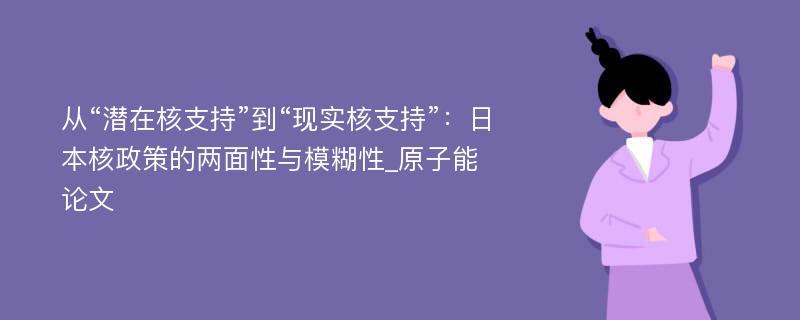
从“潜在拥核”到“现实拥核”:日本核政策的两面性与暧昧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面性论文,日本论文,暧昧论文,现实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是世界上拥有大量“钚”的国家,也是唯一拥有完整核工业链条的“非核武器国家”,目前在从“潜在拥核”向“现实拥核”转向的条件方面,尚无与之匹敌之国。早在1950年代初期,日本的核问题①就已被学界纳入研究视野,而近年来由于以下三个因素更是掀起了新一轮研究热潮。其一,在日本国内,主张“核武装”的言行日益凸显。“核武装”一词在战后初期一度被日本社会认为是“不道德”、“禁忌”、“极其敏感”的词汇,但近年来却成为某些团体、政客的公开倡议。②上述变化客观上向学界提出了怎样理解与认识日本将“无核三原则”作为“国策”的真实性问题。其二,新史料不断被发掘。近年来,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③、当事人日记的公开④以及亲历者回忆录的出版等,⑤都为学界深入分析与解释日本核政策的演进路径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其三,迫切的现实要求。21世纪以来,日本政治家一方面迎合国内右翼势力、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并诱导舆论及国民向“右转”,试图通过对侵略历史的翻案来树立大国意识。加之,日本囤积着大量研发核武器必不可少的钚材料,使得国际社会对其用途和去向普遍感到担忧。这一现实要求也促使学界有必要尽快剖析厘清其真实的核取向。 其实,既往学界已从不同学科的范式角度围绕日本的核政策问题进行了一些深入研究。在历史学领域,现有成果利用美、日两国公开的档案资料进行相互印证,揭示了日美间两次“核密约”的根源、过程与内容。⑥在政治学领域,既有从建构主义的身份认同等角度分析日本“无核三原则”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的矛盾性,又有从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环境的角度解析日本核政策的演进。⑦在文化学方面,则有研究认为日本政治在本质上是文化与人的产物,其文化的独特性潜在地影响并制约着日本人对核武装问题的思考模式与行为方式。⑧这些成果在资料、方法、视角和观点等方面,为进一步认识与理解日本核政策的真实诉求以及未来走向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完整意义上的日本核政策链条,是由以“国是”方式存在的“无核三原则”、以隐蔽方式存在的日美“核密约”与以外交方式存在的“核不扩散政策”等构成的。现有研究中尽管不乏对前两者较为深入的著述,但是对后者的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国内学界鲜有对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⑨的过程、方式和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事实上,战后日本的核选项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存在多个,然而为什么最终选择美国主导的NPT呢?进而言之,学界亟待分析与揭示日本在加入NPT历史过程中的核选择是“被选择”还是“自选择”?若是“被选择”,那么是基于价值理性的“被选择”,还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被选择”?同样,若是“自选择”,则这种选择是基于价值和道义上的“自选择”,还是基于工具和策略上的“自选择”?对此,通过挖掘和揭示日本加入NPT的历史过程与演进逻辑。不仅能够客观把握和准确回答上述问题,也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理性判断日本多元化的核政策取向及其实践行动。 一、“有条件”的“被选择”:基于国际视角的分析 二战后,美国在东亚权力结构、国际秩序中始终扮演构建者、主导者的角色。日本签署与批准NPT的历史过程,从国际政治层面而言是“被选择”的结果,即美国以非对等同盟关系中的“上位者”身份施压“下位者”的日本以期满足自身战略需要。当然,日本在以“被选择”方式加入NPT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味顺从,而是通过交涉并巧妙利用美日同盟关系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多元化。 (一)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日本的“被选择” 美国根据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战略取向的变化,其核政策的目标与内涵亦相应有所调整,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⑩理论上,日本从战后到加入NPT,在核选择方面具有多个选项,(11)但是囿于日美同盟等因素,难以跨越或脱离美国主导的核政策框架体系。 1945-1948年间,美国制定了严格的核不扩散政策。其逻辑起点是美国试图独享核武器及其战略效应,保持称霸世界的优势资本。“曼哈顿计划”(12)的成功实施以及原子弹的首次爆炸,(13)标志着核武器将会“在整个世界文明中激起巨大的军事乃至更大的政治利益”。(14)鉴于原子弹的破坏力和杀伤力,推行核技术保密政策、防止核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一环。早在1944年,玻尔(15)曾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为便于在战后实行对原子能的国际管制,避免出现灾难性的核军备竞赛,应该把原子弹研制情况尽快通知反法西斯盟友苏联。”然而,罗斯福政府不但未予采纳,反而对苏联采取了严格保密的政策,美英签署了以控制世界铀矿和钍矿等资源为目的的托管协议与声明,(16)美国在国内颁布了“禁止与任何国家进行有关原子能技术交流”的《麦克马洪法》(17),提出了旨在主导并控制原子能的“巴鲁克计划”。(18) 在这一阶段,表面上日本处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管辖之下,但实际上主要是由美国直接管制。最初,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彻底改造日本,以确保其无力再次挑战和威胁美国的战略安全。(19)在核武器方面,1945年8月11日,美国组建了由45名专家构成的“原子弹调查团”和11名专家构成的“科学情报调查团”,负责对日本的原子弹研究、设施和人员等情况进行调查。(20)其调查报告结论认为,“应该明令禁止日本从事一切与核相关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包括最基础的物理研究。”(21)11月,美国把日本的理化研究所、大阪帝国大学以及京都帝国大学等科研机构制造的五个用来分离普通铀的回旋加速器全部毁坏后扔进东京湾。(22)显然,在当时背景下,日本连内政和外交上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都不具备,遑论被允许发展核武器。进而言之,即使日本抱有“如果其他国家有核武器,理所当然我们应该也拥有”(23)的想法,美国无论是在策略层面还是在战略层面,也都不可能放任其独立发展核武器。因此,在美国推行严格控制核技术不扩散的轨道上,日本只能扮演“被选择”纳入的角色。 从1949年到NPT条约生效前,(24)美国之所以逐渐放弃先前的“严格核不扩散政策”,而改为“有限放任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主要是由于其谋求绝对核优势地位的政策思想被两个国家相继打破。一是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原子弹,打破了美国“核垄断”。二是1964年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改变了东北亚地缘政治中的“核格局”。如果说1949年之前主要是美国一国主导下推进核不扩散政策的话,那么1949年之后,其主要是在美苏两个大国,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演进的。美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25)也属于美苏博弈的产物,该计划不仅表明美国防核扩散的方法和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向”,(26)而且客观上为后来NPT赋予了“和平利用”的内涵。 因而,在此阶段,美国对日核政策与战后初期相比也凸显变化,即美国同意日本进行有关原子能的和平研究,并与其签订合作研究协定。1951年9月8日,美日《旧金山和约》中未涉及禁止或限制日本从事核能研究等方面的内容,此举标志着美国解禁了对日核能研究的限制。1955年1月11日,美国向日本提交了一份包括8个援助项目的备忘录,(27)涉及建立核反应堆学校、同位素知识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等内容。11月4日,美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日美原子能研究协定》。(28)其第三条明确规定,“美国向日本提供6公斤20%浓度的铀-235,用于原子能的科学研究”,(29)此举意味着日本在原子能研究中遇到的核材料匮乏以及相关技术难题将在与美国的合作中得到解决。然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美国积极支持日本进行原子能研究,并不意味着任由其自由发展,而真正意图是将日本作为核不扩散进程中的支持者和拥护者,纳入自己的核战略框架。(30) 综合上述,美国对日核政策并非是依循日本的“核偏好”和“核取向”形成的,而是以“是否符合美国战略利益”作为前置条件而制定、调整与实施的。在冷战背景下,美国的战略诉求是把日本打造成应对苏联的“远东堡垒”,防止“红色共产主义扩散”的“东方堤坝”,因此在核政策方面并不会对其释放过多的选择空间。可见,就国际层面上表现出的“外在逻辑”而言。日本加入NPT则是“被选择”的结果。 (二)在NPT缔约中的“选边站队”与外交交涉 尽管日本在美国主导的核不扩散政策下进行核选择的空间相当逼窄,但从其加入NPT的历史路径而言,并非完全顺从美国,(31)亦非无条件地“被选择”,而是在充分考虑到本国的战略诉求与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与美国巧妙地进行“讨价还价”,以期谋求利益最大化。从身份角度而言,在围绕NPT的政策博弈过程中,日本是以“非核武器国”与“美国的同盟国”的复合身份进行“选边站队”和外交交涉的。 作为非核武器国家,日本对构建NPT的公开立场是,“应该充分考虑各国的安全保障,无论是核国家或者无核国家都应做出牺牲来讨论和推进NPT”,(32)该观点与“非同盟八国”(33)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965年11月8日,“非同盟八国”就构建NPT的相关问题向联合国提出以下“五原则”,(34)即:(1)不论以何种形式(直接或间接),都不允许在条约中出现容忍缔约国核扩散的纰漏;(2)在条约中必须明确规定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责任与义务;(3)条约是以达成彻底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手段而存在的;(4)条约应明确规定保证其实效性的条款项;(5)条约不得影响已签署无核地区条款各国的权利。日本政府一方面对非核国家提出的“五原则”持赞同意见,另一方面又以同盟国身份,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主动向美国表达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当时,美国约翰逊政府为挽回在越南战争受损的国际形象,极力想促成NPT的签署。美国客观上也需要日本作为潜在核发展国的支持。由此,美日两国在各自利益诉求的驱使下,围绕构建NPT等相关问题展开了交涉。(35) 在“非核国家的安全问题”上,美国提出的是“积极安全保障”模式,即非核国家一旦受到核武器的威胁或攻击将给予其援助,苏联提出的则是“消极安全保障”模式,即核国家不得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进行恐吓与攻击。(36)包括日本在内的非核国家普遍赞赏苏联提出的模式。(37)而美国结合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及其舆论导向判断,如果日本赞同苏联模式,则其对载有核武器的战舰与战斗机进出日本港湾的态度,将由最初的暧昧与默认转向限制和抵制,(38)进而弱化自身驻日军事基地的实用性。(39)因此,为避免日本的立场选择影响到自身核战略,美国与日本进行了多次沟通与交涉。从结果来看,日本做出了有限让步,即对苏联模式的态度由原来的“赞成”改为“不积极支持”。显然,日本暧昧的表达方式由于并未抛弃非核国家的身份,既可站在非核国家一边赞同苏联的“消极安全保障”,获得核武器国家不对非核国家攻击的承诺,同时作为美国的同盟者身份,亦可获得美国的核保护,最终实现“两头通吃”和“双向获利”。 在NPT时效问题上,美日两国也持不同立场。美国最初主张把NPT的有效期确定为无限期,并由三分之二缔约国通过。对此,日本表示强烈反对。1966年10月,日本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应该限定NPT的有效期,并确保所有国家拥有针对当前事态自由讨论的权力,希望制定供所有缔约国针对条约实施状况及核裁军等相关问题进行经常讨论的规定。”(40)显然,日本所担心的是一旦NPT的有效期被无限延长并以制度化形式固化的话,那么作为缔约国将失去合理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不平等待遇也将被长期“锁定”,进而将对日本“独立拥核”形成掣肘。尽管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非核国家之间存在分歧,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41)美国被迫同意并接受了“NPT有效期定为25年,并每隔5年对核国家履行核裁军情况进行会议讨论”的建议。(42)1968年7月1日,美、英、苏及59个非核国家分别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共同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显然,核武器与核讹诈在支撑美国、苏联追求霸权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国曾主导构建的NPT由于“鲜明地反映了美苏两国的利害关系,是美苏协调体制下的法律与制度的认知体现”,(43)因此NPT在公平、地位和责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绝不能以NPT存在的缺陷去遮蔽其本身所具有的为人类共同命运,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规避核战争的价值理性。从安全角度出发,国际社会签署NPT的主要目标就在于避免爆发核战争,消除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实现世界的长久安全与稳定。就和平利用核能而言,NPT规定,“所有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为和平利用核能而交换设备、材料和科学技术情报……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地区的需要应给予应有的考虑。”(44)而历史已经证明,NPT的签署对防止核武的“横向扩散”和“纵向扩散”都起到了明显的遏制作用。NPT签署后,其缔约国中间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核武器国家。从1945年到1968年,核武器国家从无到有、从一个扩散到五个国家只用了约20年时间,而NPT生效后至今的45年来,并没有出现公开表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45) 显然,既然构建NPT本身具有人类正义、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全等价值理性,那么日本以“被选择”的方式加入NPT亦然。换言之,不论日本以何种方式加入NPT,也不论日本以何种真实诉求加入,就其结果本身而言,毋庸置疑客观上对核不扩散具有积极意义。 二、“策略性”的“自选择”:基于国内视角的分析 日本签署并批准NPT的历史过程与演进路径,如果就国际层面的“外在逻辑”而言是“被选择”的话,那么在国家层面上表现出的“内在逻辑”,则是日本“自选择”的结果。当然,“自选择”方式并不意味着日本在核选项方面的真实诉求,是心甘情愿地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命运“弃核”,而是基于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等三种思想的综合考虑,做出的具有工具理性特质的“自选择”。 (一)核选择中的多元化目标诉求 日本作为迄今世界上唯一遭到核爆的国家,本应更积极、更鲜明地加入NPT,但事实上日本并未第一时间出席1968年的NPT签字仪式,直至1970年2月3日,才同意签署NPT,而在时隔六年后的1976年国会才最终予以批准。(46)显然,三个时间节点的错位,折射出的是日本在核选项方面的选择困境与执拗心理。那么,在核问题上日本到底有什么样的真实诉求呢? 日本在加入NPT的过程中,围绕“拥核”还是“弃核”的问题有过广泛而深入的论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应选择“弃核”并尽快加入NPT。1968年,正值核不扩散条约开放签署期间,外相三木武夫表示,“核不扩散条约与我国的主张基本相符,应该签署。”(47)1973年,外务省在《我国现阶段关于批准NPT的态度》报告中指出,“批准NPT的优点在于:一是减少核战争的爆发,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二是消除外界对日本的猜疑,让国际社会理解日本的和平外交;三是便于获得核燃料。”(48)此外,政界也顾虑日美关系受到影响,“有必要通过批准NPT进一步提高美国的信任”,“任何犹豫将直接触碰双方的互信底线,进而损害双边友好关系”。(49)与此相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签署NPT后将对“独立拥核”形成束缚,进而永远“沦落为二流国家”。(50)持上述立场者还担心,日本如因加入NPT而放弃“核武选项”的话,一旦日美安保机制失效,无疑会将自己暴露在两个核大国(苏联和中国)的家门口。而且,“对于日美安保条约,只要美国想废除的话,一年左右就能解除,但是批准加入NPT后,需要遵守长达二十多年之久,倘若日美安保条约在此期间作废,日本则有遭到核武器攻击的危险。”(51)由此可见,“拥核”(52)是日本在讨论签署NPT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前置性观点。 本来,以永久放弃战争为精髓的《和平宪法》,允许和平利用核能的《原子能基本法》,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以专守防务为重点的军事方针及以“重经济轻军事”为核心的国家战略,都从不同制度层面制约着日本不能重蹈对外侵略之路,“核武装”之类的词汇更是一度被视为“忌语”。“军事大国”与日本俨然成为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其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然而,对于“拥核”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日本部分政治人物通过“解释宪法”的方式提出了“核武合宪论”。首相岸信介曾表示,核武器存在划分种类问题,一概认为核武器不合宪是不准确的,因此“用于防卫的核武器是合宪的”。(53)1967年,防卫厅长官增田甲子七认为,“根据宪法的解释,战术性的核武器或者说纯防御性的核武器,既不会对外国构成威胁,又能保护日本本土安全,因而是可以考虑拥有的,诸如反弹道导弹等防御性武器,宪法并未禁止”。(54)1969年,佐藤荣作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也曾宣称,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中的前两项是可以突破的,拥有与制造核武器并非彻底违背宪法。可见,制度体系的约束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拥核”思想将永久被封存,也不代表“通过拥核保障国家安全”的观点被彻底抹杀。 事实上,“认为NPT是遏制发展核武器的条约”(55)的观点对日本政府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1969年,隶属外务省的“外交政策企划委员会”认为,“关于核武器,尽管目前采取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但是不论是否加入NPT,也都要在经济、技术上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潜力,对此不应掣肘。”(56)日本在签署NPT前发表的政府声明中也明确提出,“日本政府会特别留意,条约第10条‘每个缔约国如果断定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危及其国家的最高利益,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应有权退出本条约’的规定。”(57)可见,日本即使签署NPT,也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核选项;只要其认定有损于国家安全利益,仍会选择退出NPT,并通过“解释宪法”等方式进行独立核武装。 当然,日本在选择加入NPT时的真实诉求,除“通过拥核保障国家安全”之外,也存在以下三个目标:一是获得核材料、核技术。NPT第四条第二项规定,“所有缔约国承诺促进并有权参加在最大可能范围内为和平利用核能而交换设备、材料和科学技术情报。”(58)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核电产业的发展,日本对核燃料的需求量日益增加,(59)然而由于其国内核燃料匮乏,需要通过日美两国间的核能协定直接从美国进口。因此,日本面临着“如果不加入NPT,核燃料的供给有可能被断绝。若是浓缩铀的进口渠道被切断,将无法发展核电工业”的困境。(60)此外,外务省认为,不签署NPT,除核燃料供给成问题外,还可能失去国际核技术交流平台。二是在日美同盟关系中获取利益最大化。由于NPT是由美国主导的,日本认为如果不积极配合,则会有损日美同盟关系。更为重要的是,NPT签署时正值美日“归还冲绳”谈判,日本如果在NPT问题上与美国僵持不下,势必会影响两国同盟关系;而适当在签署NPT问题上让步,则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同盟关系,促进冲绳顺利返还。对此,在提出“无核三原则”的一个多月后,佐藤荣作又发表“核四政策”(61),淡化“无核三原则”的刚性规定,此举旨在为两国签订核密约(62)铺平道路,从而在冲绳返还交涉上追逐利益最大化。三是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战后日本一直致力于摆脱战败国的身份,努力谋求增强国际政治影响力。日本认为,“如果不在NPT生效前签署,与印度、以色列等不签字国家站在统一立场上,将会增加外界的疑虑。”(63) 总之,日本在围绕核选项方面的真实诉求是多元化的,既考虑到“拥核”,即“通过核武装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又在“弃核”选项中设定了“获得核材料和核技术”、“在日美同盟关系中逐利”以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等目标。而这种多元化目标取向,显然杂糅了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等思想。 (二)核选择中的结构性障碍及其突破策略 理论上,日本如果试图同时达到“通过核武装实现国家安全”、“获得核材料和核技术”、“在日美同盟关系中最大化逐利”以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等多元化目标,必须突破多元化目标之间存在的两个结构性障碍。一是目标之间的不可公度性。四个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与后三个目标之间并不存在能用同一个单位进行衡量的工具,因此也不可能累加计算。换言之,在多元化目标之间,不存在通过一种价值向度的政策选择同时达成四个目标的可能性。无论日本做出怎样的核选择,都不可能同时实现上述多元化的目标。二是目标之间的矛盾性。在四个目标中,第一个目标与后三个目标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即如果签署并通过NPT,日本将会实现后三个目标,同时也意味着放弃“通过核武装实现国家安全”的诉求。反之,如果日本选择通过发展核武器保障国家安全的话,则意味着其放弃NPT(64)中规定的提供和平利用的“核技术和核燃料”,并影响和撕裂日美同盟关系,且将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显然,日本在谋求多元化目标的过程中,由于“不可公度性”和“矛盾性”这两个结构性障碍的存在,加之民意基础、政党内争等因素,其每一个政策选项及目标都很难达到最优,因为目标的价值取向是多元化的、制约决策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影响判断的价值标准是多元化的、决策后果的承担者也是多元化的。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日本为同时最大化地实现上述多元目标,在选择加入NPT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先签署后批准”的方式,即在外交层面上于1970年先签署NPT,但在国家内部层面则暂不批准。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先签署”呢? 事实上,日本采取“先签署”的策略,旨在舒缓以下五个方面的压力,并谋求相关利益:一是签署NPT,意味着能获得核材料和核技术,缓解燃料被中断的压力;(65)二是舒缓在核选项问题上来自美国的压力,有利于在两国同盟关系中分享更多的红利;三是缓解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论争,稳定政治局面;四是迎合国内民众反核的潮流,(66)稀释社会上的反核压力,在政治上获得更多民众支持;五是签署NPT本身,就意味着日本将与绝大多数国家一道致力于世界和平和无核世界,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既然日本“先签署”NPT存在上述理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签署与批准在时间节点上的长期错位呢?就日本政府的立场而言,(67)拖延批准时间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顾虑NPT的公平性问题;二是质疑国家安全保障问题。 在确保和平利用核能的公平性问题上,日本担心的是核查问题。早在1970年签署NPT时,日本就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保障措施,尽量不要阻碍我国日益发展的核电产业活动”,(68)并希望能获得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同等的“自我核查”待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保障措施涉及五个方面:一是要求被审查国报告核物质转移的情况;二是提交原子核反应堆等使用设施的设计资料;三是保留核反应堆的运作记录以供核查;四是总结并提交库存情况及各种报告书;五是接受IAEA检察官对核反应设施的实地审查工作。(69)上述核查内容或多或少都会对核反应堆的正常运转造成一定干扰,因此1953年成立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加入NPT时明确表示,不愿放弃“自我核查”机制。对此,NPT在诸多方面特许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自我核查权。日本的核能设备检查,一直都是根据提供核燃料与技术的美、英、加等国形成的双边协定进行的,检查内容颇为严格。如果能与IAEA达成新的协定,对日本政府的审查资格予以认证的话,将会大幅减少国际核查的次数,且方法和过程也将化繁为简。(70)基于以上考虑,日本以“先签署但不批准”的方式与IAEA进行交涉。最终,1975年2月,日本与IAEA达成共识,“获得了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相同的保障措施特权”。(71)可见,日本拖延策略的目的之一是寻求在核查方面获得自查权利。然而,获得“自我核查”权力的日本在核燃料利用、核技术发展的取向方面,是专注于和平利用还是“民转军用”,无疑存在很大的自主性与隐蔽性。 在安全保障问题上,日本最为担心的是对独立核武装的替代品——美国核威慑的疑虑。自NPT提出到生效,日本国内围绕核选择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究其实质是怀疑日美安全保障机制的可靠性问题。(72)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越顶外交”的实施对日本震动很大,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对美国的信任感骤然下降。1974年,印度拒绝参加NPT并随即进行核试验,此举对NPT机制的可信度无疑又是一次重创。加之美国公开宣布将向埃及和以色列提供核反应堆,造成一种美国已不再重视核不扩散的印象。(73) 然而,日本基于“现阶段还不适宜发展核武器”这一结论迟迟不批准NPT,目的还在于获得美国清晰、明确的核保护承诺。1975年3月,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发表《国际形势的长期展望与NPT的签署问题》,批评自民党内部坚持主张保留核武器选项的官员,认为只要日美安保条约下的延伸威慑仍有效,日本不论是发展战略核武器抑或战术核武器均无必要,批准NPT对强化日美间互信关系有着重要作用,(74)“实现独立与安全主要基于国民的爱国意识、自卫力量、日美安保条约,而这些都必须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力量。”(75)8月,首相三木武夫在与福特总统会谈时,进一步表达了“希望获得美国明确、清晰的核保护的承诺”的要求。随后,美国发表声明公开承诺“无论是核武器抑或常规武器,只要日本受到武力攻击,美国将提供防卫”。(76)1976年,日本在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也申明主张,“将通过日美安保条约依靠美国的核威慑……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军事观点出发,我国都没有必要进行核武装。”(77)至此,对于日本而言,一方面被纳入美国核政策框架并获得核保护承诺,另一方面以批准NPT为标志正式站在了核不扩散政策的起点上。由此,美国继续向日本提供浓缩铀,并容许其将利用后的核燃料运往欧洲处理,将分离出的钚再运回日本存储以供今后用于增殖反应堆。(78) 可见,尽管日本没有使每一个政策目标都达到最优,但是通过“先签署后批准”策略,在各种目标之间求得了一种合理的平衡、妥协、调和、互让与折中,从总体上最大地满足了日本真实的核诉求与多元化的核目标。 (三)“自选择”的工具理性 日本加入并批准NPT的决策选择,在国内层面呈现为一种“自选择”过程,是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党派、团体、学者和媒体之间展开争论与博弈后的均衡结果。从价值逻辑而言,日本批准NPT,并非是真心想彻底地放弃核武装,而是在没有与二战“拥核”思想完全切割的前提下,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在进行调查研究、权衡得失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先签署后批准”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质。 其一,继承了“拥核”思想的历史DNA。二战时期日本曾为制造核武器制定了“仁计划”(79)和“F计划”(80),但是最终都因缺乏浓缩铀等问题以失败告终。战后日本虽一度将核武装话题束之高阁,但“拥核”言论在政治高层却屡见不鲜。战前海军出身的中曾根康弘,在战后步入政坛后的1951年,就迫不及待地主动向美国提出“解禁原子能科学研究”,(81)并多次表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拥有核武器”。1957年,岸信介公开表达了“拥核”观点。(82)1961年,池田勇人明确对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宣称,“在内阁里有核武器支持者,尽管是少数。”(83)佐藤荣作在1964年认为,“如果其他国家有核武器,理所当然我们应该也拥有。”(84)1969年,在日本内部发布的政策大纲中也提及,“要保留发展核武器的技术及经济手段,在必要时进行开发,并附言不管面临外界多大压力都要进行核武装。”(85)可见,日本战时的“拥核”思想并没有因为战败而彻底消散,而是作为一种战争遗产得到了继承与延续,尽管这种思想有时仍是以潜流和暗流的形式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政策选择时不会作为重要因素而加以考虑。 其二,“先签署后批准”的策略意味着日本的核选择并非出于价值理性。日本通过“先签署后批准”的方式,在各目标之间力求取得一种合理的平衡、妥协、调和与折中,进而最大化地满足了自身的真实核诉求,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以获得美国核保护的方式替代“独立拥核”。日本囿于国内外条件所限,在无法实现“通过拥核保障国家安全”目标的情况下,做出“次优选择”,以美国承诺的“核保护”作为“独立拥核”的替代。二是以“和平利用”方式谋求“潜在拥核”。日本国内极其缺乏铀资源,加入NPT可使其规避核燃料被中断的风险。和平利用与制造核武乃是一体同源,越界与否关键取决于“政治意愿”。三是以实现“核自查”的方式在核能利用方面拓展更大的空间。日本通过“后批准”策略,争取到“核自查”权利,获得了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相同的待遇,进而为核燃料、核技术是专事和平利用还是派做军事用途留下更大回旋空间。 其三,功利性的调查研究。日本对核选项的调查和评估本身,标志着日本加入NPT并非基于道义、和平上的伦理价值选择,而是在“成本—收益”框架下基于功利性目的的工具理性选择。1967年,佐藤内阁暗托内阁调查室,对日本是否需要拥有独立的核武力量进行评估,(86)最终形成了“1968/70报告”。(87)第一份报告主要从制造核弹的技术、生产核物质的技术、导弹火箭技术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少量的原子弹是能够并且比较容易制造出的,但是在搭载、人才、制造等方面也存在诸多技术难题”。(88)第二份报告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日本独立“核武装”的政治环境及战略成本。(89)一是通过分析国际形势认为,中国的拥核对日本虽然是威胁,但是由于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因此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二是在对核武装的战略成本进行评估后指出,由于人口与工业的密集、国土狭窄,日本抗核打击能力是脆弱的。三是对日本核武装的外交与政治成本进行评估后认为,亚太形势不同于欧洲,不能走法国的“拥核”道路,日本的核武装将不仅引起中国的警惕,也会刺激美苏,最后必然导致外交孤立。综合两份报告的结论可看出,日本在核武装问题上“就技术而言没有障碍”,(90)“核武装作为一种政治选择有考虑的价值,但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并不意味着核武装后就增强了。”(91)换言之,日本加入和批准NPT,并非是在人类公理和道义基础上的选择,而是在“成本一收益”框架下,按照“不需要时不选择,需要时再选择”的逻辑方式祭出的权宜之计。 三、多元化的政策实践:日本加入NPT后 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本应成为“核不扩散政策”的“推动者”、“践行者”和“维护者”。然而,自1976年批准NPT到现在的40年间,日本的核政策形成了一个由三种不同取向构成的“对立图式”结构,即:一是积极标榜并提倡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反核”政策;二是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依核”政策;三是潜在追求制造核武器能力的“拥核”政策。前两者是日本公开的、外化的政策路径,后者则是其在NPT框架中内化的、隐蔽的政策路径。“反核”、“依核”和“拥核”在同一时空中的互构与切换,不仅共同造就了日本多元化核政策的实践逻辑,而且深刻揭示了其在推行核不扩散过程中的矛盾性、虚伪性和两面性。 (一)“反核”与“依核”共存 总结与解读日本自批准NPT以来公开的《外交蓝皮书》、《军缩·核不扩散外交》、外交声明以及官方政策等文本资料中有关核政策的内容,不难发现其核不扩散立场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日本在NPT框架内积极致力于核裁军、核不扩散的“反核”政策立场;另一方面,日本在安全上又持“依核”政策立场,接受美国的核保护。理论上,日本将强化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的日美安保体制作为批准NPT的条件,意味着其背离了NPT的主旨和精神。(92)然而,日本却认为,“当前依靠核威慑来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追求核裁军并无任何矛盾”,(93)日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在安保条约框架下的美国核力量,作为防止对日核攻击的主要威慑力量”(94)并无不妥。显然,日本并不认为“反核”与“依核”之间具有结构性矛盾,而是将“依核”作为“反核”的前置条件。 日本这一矛盾、纠结的立场,可通过其是否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得到进一步验证。1982年,苏联在第二届联合国裁军会议上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倡议。对此,美国与日本均未予以呼应,反而态度冷淡,(95)并称“政策的宣言与执行是两回事”。(96)事实上,对于是否赞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问题,日本在出席此次会议前业已形成明确的认识:“既然世界和平与安全是依靠核威慑力,因此日本只通过不使用核武器的规定是无任何保障的。”(97)换言之,日本的安全要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因此不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998年,日本拒绝加入由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南非和瑞典等国组成的支持核裁军、反对核扩散的新议程联盟(NAC)。对此日本宣称,“在新议程联盟的共同声明中,涉及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但是日本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能否保证国家安全表示担忧,在目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最重要的还是依靠包括核威慑在内的日美安保体制。”(98)1999年,在东京召开的核裁军不扩散会议上,日本仍未赞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提案,其反对的理由同样是“当前环境下,并不具备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成熟条件”,(99)“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存在的今天,日本需要依靠美国核威慑来确保安全,因此不考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00) 2009年,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演讲中提出“无核世界”,并明确表示将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与俄罗斯就削减核武器数量进行谈判。(101)在理念上,核不扩散政策与“无核世界”本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日本一方面公开支持奥巴马的倡议,另一方面却表示“通过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来谋求日本的安全保障是不现实的”,(102)“只要核武器仍存在,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对日本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103)此外,2010年以来,在日本的要求下,“延伸威慑”(104)问题被纳入日美历年召开的“2+2”机制框架中加以讨论。 可见,日本在高调宣扬废除核武器、提倡核不扩散政策的同时,却又崇尚核武器、迷恋核威慑,这种处事原则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行为。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相机行事,一方面将“反核”作为行动目标对外标榜和宣传,另一方面却在“反核”之下坚定执行“依核”政策,在二者之间“左右摇摆”和“自由取舍”。显然,日本既“依核”又“反核”的矛盾政策立场,本质上已经完全背离了NPT的宗旨与原则。 (二)“宣传”与“行动”背离 日本加入NPT 40年以来,在标榜和宣传“核不扩散政策”过程中,一直将自己打扮为核爆受害者,且总以“核不扩散”贡献者与推动者自居。然而,日本在对外宣传与实际行动之间却存在诸多背离。 其一,在核武器问题上公开迷恋“核威慑”。美国和苏联在围绕《中导条约》(全称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INF)谈判期间,首相中曾根康弘曾于1982年公开表示反对苏联“INF条约仅适用欧洲地区”的主张,并强调INF条约不应只考虑欧洲,还要考虑亚洲的安全保障。甚至应扩至全球。如苏联坚持条约仅限于欧洲的话,日本则将参与筹划在欧洲配备美国导弹(潘兴Ⅱ战术及巡航导弹)。(105)可见,日本借支持美国核威慑来维护自身安全的行为模式,无疑与其公开标榜和宣传的核不扩散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立和矛盾。 其二,在核裁军问题上担心弱化美国的核保护能力。日本认为,美国“无核世界”的提出以及从数量和战略上削减核武器的计划,将会降低美国的核保护能力。理论上,美俄如能就削减核武器达成共识,既符合日本不扩散政策的宗旨,也有利于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日本基于核地缘政治的考虑,认为自身处在核武器国家较为集中的东亚,且与坚决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相邻,因此担心美国如减少核武器的保有量,将会影响和动摇对自身的核保护。(106)另外,2010年美国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提出:“美国将继续加强常规兵力,减少使用核武器来遏制非核攻击的作用,并将对盟友的核武攻击作为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目的。”(107)对此,日本则希望美国将核威慑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应对非核武器的攻击。事实上,扩大核威慑不仅对削减核武器没有任何促进,相反还会助长核威慑的滥用。 其三,在核扩散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在朝核问题上,日本一直坚持美国的核保护伞也应适用于应对生物及化学武器的攻击。而在对待印度核试验问题上,日本却全然不同。2015年12月,日印两国就《日印原子能合作协议》达成原则性共识。(108)日本表示,这是“因为印度与美国、日本同属尊重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国家”。然而,日本作为NPT的缔约国,与作为非成员国的印度之间在原子能方面进行合作,(109)并为其提供技术、设备,不仅在行动上违反了NPT的规定和宗旨,而且还助长了“横向核扩散”。(110)显然,日本的“双重标准”意味着其在核不扩散政策中明显存在虚伪性。 (三)“反核”与“拥核”兼具 按照日本同时持有“反核”与“拥核”的核逻辑,既然将核不扩散的前提条件建立在依靠美国核威慑的基础上,那么是否意味着其将会放弃“独立拥核”的政策选项呢?其实不然。在“反核”和“依核”矛盾立场的相互交织下,却隐藏着日本谋求实现潜在拥核能力的真实意图。在日本始终存在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核保护伞只不过是自身“独立拥核”的替代品,是一种“不确定性”和“非自主性”的“间接拥核”方式,甚至将其戏称为“没有骨架的核保护伞”和“打不开的伞”,(111)因此有必要进行“独立核武装”,(112)实现自我保护。然而,日本囿于国内外环境条件,一方面不得不在法律及政策上进行“无核化”的自我规制,公开宣扬不进行“核武装”,另一方面却在“反核”宣传下隐蔽推行“潜在拥核”的发展模式。 通常,一个国家要实现拥有核武器的诉求,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结构要件:一是高浓缩钚或铀;二是工艺技术流程;三是搭载核弹头的投送工具:四是政治意愿与决断。前三个条件可谓制造核武器的“物理性”要件,而后者则是作为国家行为的“政治性”要件。那么,迄今日本是否具备上述条件呢? 在“物理性”要件方面,日本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一是日本存储着大量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材料钚。根据日本原子力委员会2015年公开的资料计算,日本的钚持有量(仅分离出来的量)共约为47.8吨,分别储备在国内(10.8吨)、英国(20.7吨)、法国(16.3吨)。(113)如按每8公斤钚制造一枚核弹来测算,目前日本持有的钚可以生产5000多枚核弹,足以毁灭整个人类。二是日本拥有完整的“核电产业”体系。(114)战后,日本在“国策民营”发展模式下,原子能的研发水平及其产业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形成了核研发、生产及其工艺流程的“核产业”技术体系。(115)三是日本拥有世界上先进的搭载投送技术。通常而言,一国即使能生产出核弹头,但如果没有很好的搭载投送技术的话,也无法实战,更遑论形成核武器本身所具有的战略威慑力和杀伤力。战后,日本特别重视航天工业及其固体运载火箭的技术研发。(116)目前,日本已积累了开发洲际弹道导弹所需要的数据,并且拥有可以随时发射的世界最高水平的固体燃料火箭。 可见,日本业已满足制造核武器的“物理性”结构要件。然而,一个国家是否制造核武器,最终仍将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意愿。数十年来,日本打造“政治性”要件的取向日益凸显。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右倾保守化”的政治逻辑由原来的“慢车道”转向了“快车道”。当前,安倍政权一方面迎合国内右翼势力、保守主义、民粹主义,(117)另一方面鼓动民族主义并诱导舆论和国民向“右转”,试图通过为侵略历史翻案来树立大国意识。在此政治逻辑驱使下,日本对核武问题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其一,故意拖延向美国归还钚材料。美国从2010年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开始,就催促日本归还冷战时期向其提供的331公斤武器级钚。而日本长时间拖延不还,也没有向国际社会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其二,右翼势力高调抛售“拥核论”。右翼分子以中国、朝鲜为假想敌,不断高调提出“独立核武装论”。石原慎太郎曾扬言“日本不能永远生活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118)岸田文雄则表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是有道理的,这是每个国家自我保护的权力。”(119)然而,日本舆论对此不再强烈批判,政府似乎也对“拥核论者”刻意保持沉默。其三,“无核三原则”名存实亡。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公开提出了“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但是,1969年,佐藤在访问美国时,却暗地与尼克松签署了一份允许美国向日本运进核武器的“密约”,又称《冲绳密约》。日本外务省第三方委员会2010年3月提交的调查报告称,日美两国间存在“核密约”,即默许载有核武器的美国舰艇停靠日本港口。可见,日本早已背离了既有的承诺,“无核三原则”只不过是掩民众耳目的花招。 四、结语 揭示和挖掘日本加入NPT的历史过程与演进逻辑,是客观把握、准确理解其真实核诉求的重要基础。从国际层面表现出的“外在逻辑”来看,日本加入NPT是其在难以僭越或脱轨美国核政策框架下的“被选择”。而就国家层面表现出的“内在逻辑”而言,日本加入NPT既是日本国内不同党派、团体和学者之间进行争论与博弈后的“自选择”,也是其在尚未与二战时的“拥核”思想进行完全切割前提下做出的带有工具理性特质的“自选择”,更是在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这三种思想叠加与互动基础上的策略和权变。尽管“外在逻辑”中的“被选择”与“内在逻辑”中的“自选择”的关系呈现为对立与矛盾的“二元图式”,但正是这种形式上的逻辑悖论才真实演绎并客观铺陈了日本在核抉择过程中始终呈现的两面性与暧昧性。 日本加入和批准NPT的政策取向是多元化的,既有“拥核”选项中“通过核武器保障国家安全”的目标,又有“弃核”选项中“获得核材料和核技术”、“从日美同盟关系中逐利”以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等目标。理论,上,由于“拥核”与“弃核”本身是一对不相容的矛盾体,二者具有不可公度性和矛盾性,因此日本难以同时实现多元化的核政策取向。现实中,日本通过“先签署后批准”的方式,在各目标之间力求取得一种合理的平衡、妥协、调和,进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的真实核诉求。 在其批准NPT后的40年间,日本的核政策实践同样也呈现出了一个由不同政策取向构成的“对立图式”结构:一是在NPT框架内积极标榜并提倡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反核”政策指向;二是在日美安保框架下接受美国核保护伞的“依核”政策指向;三是潜在的发展制造核武器能力的“拥核”政策指向。前两者是日本公开的、外化的政策,后者则是其在NPT框架中内化的、隐蔽的政策。“反核”、“依核”和“拥核”在同一时空中的互构与切换,不仅共同造就了日本核政策的实践逻辑,还深刻揭示了其核政策的矛盾性、虚伪性和两面性。 可见,日本批准NPT前的核政策选择与其之后的核政策实践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批准前,有条件的“被选择”与策略性的“自选择”相结合,为日本创造了在NPT框架内对核能的“和平利用”与“军事目的”进行相互切换的操作空间,以较低的风险实现了收益的最大化。批准后,日本推行的“反核”与“依核”共存、“宣传”与“行动”背离和“反核”与“拥核”兼具的政策逻辑,为其在核能的“和平利用”与“军事目的”之间“左右逢源”和“多重获利”提供了最大公约值。换言之,日本签署和批准NPT,既非意味着其将认真遵守NPT的各项规定,亦非意味着其将专心致力于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更非意味着其将彻底放弃“独立核武”选项。与其说日本的核诉求被NPT所规制,毋宁说NPT逐渐成为其安心发展并隐性保持制造核武器潜力的屏障。 可见,“日本如果在某个时间点上认为有必要的话,将会进行核武装”的言论(120)并非空穴来风。日本从“潜在拥核”到“现实拥核”的临界点既非技术障碍,亦非民意阻力,更非资金问题,需要的只是“时间窗口”和“政治借口”。美国对日核政策的纵容、国家安全压力的上升、国内政治右倾化的加速以及“黑天鹅事件”的爆发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日本跨越或突破独立核武装的“最后一公里”。对此,学界急需对与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具有同一属性的“日核问题”进行学理的分析与探讨,并从司法、技术和政治等层面解读与揭示“日核问题”缘何没有成为国际性核问题的内在理路。 注释: ①本文所言及的“核政策”主要侧重于与“军事利用”相关的政策。 ②相关内容可参见:岸信介「自衛権を裏付けゐ必要な最小限度の実力であれば、私はたとぇ核兵器と名がつくものであっても持ち得ゐとぃぅことを憲法解釈としてはもっております」、第26回国会参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二十四号、昭和三十二年五月七日、第21頁;池田勇人「米驚かせた「核武装論」池田·佐藤元首相が打診」、『朝日新闻』、2005年8月1日;安倍晋三「核兵器使用は違憲とは思わなぃ」、『サンデ一毎日』、2002年6月2日、第25頁。 ③有关档案解密资料主要有:Embtel 267,Tokyo to SecState,January 14.1969,Pd Political &Aff.&Rel.Japan-US 1/1/69.Box 2249,RG59,CF,NA.; Embtel 9410,Tokyo to SecState,"Ushiba Says Japan Will Sign NPT",November 12,1969,DEF18-6,11/1/69,Box 1747,CF,RG59,NA;総合外交政策局軍縮不拡·科学部軍備管理軍縮課「不拡散問題」、1968年1月、SC1/5/3、2015-0957;北米局北米第二課「佐藤栄作·ニクソン米国大統領会談」、1970年9月、SA1/2/2、2014-4129。 ④有关日记资料主要有:楠田實『楠田實日記—佐藤栄作総理首席秘書官の二○○○日』、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9月;佐藤栄作『佐藤栄作日記』、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1999年。 ⑤有关回忆录资料主要有:中曽根康弘『政治と人生:中曽根康弘回顧録』、東京:講談社、1992年;中曽根康弘『天地友情:五十年の戦後政治を語ゐ』、東京:文藝春秋、1996年;岸信介『岸信介回顧録』、東京:廣済堂、1983年。 ⑥相关研究主要有:崔丕:《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与对策》,《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第4-20页;崔丕:《美日返还冲绳施政权谈判中的核密约问题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45-61页;小池洋子「非核三原則と米国の核抑止力——核搭載艦船の日本寄港が担った役割と今日的課題」、『RESEARCH BUREAU論究』、2012年12月第9号、第75-86頁;黒崎輝『核兵器と日米関係——アメリカの核不拡散外交と日本の選択1960-1976』、東京:有志舎、2006年3月30日、第75-269頁;西連寺大樹「日本の核兵器不拡散条約調印·批准過程と日米安全保障条約Ⅱ」、『政治経済史学』、2004年1月、第20-37頁;John E.Endicott,"The 1975-76 Debate Over Ratification of the NPT in Japan",Asian Survey,Vol.17,No.3,March 1977,pp.275-292。 ⑦相关研究主要有:赵宏:《战后日本核政策的建构主义分析》,《大平洋学报》,2005年第4期,第91-97页;徐万胜、付征南:《日本核政策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第22-25页;黒崎輝「佐藤政権の核政策七とアメリカの「核の傘」」、『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平和研究所』、2002年10月16号、第73-93頁;黄大慧:《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5-173页;Gregory Kulacki,"Japan and America's Nuclear Posture",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Global Security Program,March 2010,pp.1-7; Satake Tomohiko,"Japan's Nuclear Policy:Between NonNuclear Identity and US Extended Deterrence",Austral Policy Forum 09-12A,May 21,2009,pp.1-10。 ⑧李军等:《文化因素与战后日本的核政策》,《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3期,第125-129页。 ⑨NPT是英、美、苏等59个国家于1968年7月1日缔结签署的一项国际条约,共有11条。“核不扩散”、“核裁军”和“核能的和平利用”是该条约的三大支柱。目前除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等国外,多数国家已加入该条约,详细内容可参见http://www.state.gov/t/isn/trty/16281.htm。 ⑩国内外学界研究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相关著述颇丰,但在其核政策目标与阶段划分上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为便于分析和论述日本的核政策,本文作出如下划分:第一阶段(1945-1948),美国制定的是严格核保密政策;第二阶段(1949-1970),美国执行“有限核放任”政策;第三阶段(1971-1990),美国采取“有限管制”政策;第四阶段(1991-现在),美国奉行“严格管制”政策。 (11)理论上,日本具有“独立拥核”、“潜在拥核”、“完全弃核”、“替代拥核”等选项。 (12)“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研发与制造原子弹的一项巨大军事战略工程。 (13)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核打击。 (14)"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to President Trume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Vol.2,Gene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tters,pp.41-42. (15)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年10月生于丹麦,1962年11月逝世,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有《论原子构造和分子构造》、《各元素的原子结构及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等。 (16)美国认为切断核材料的流通是防止核扩散的有效手段,只要垄断制造原子弹必不可少的铀资源就能防止核扩散。美英之间签署的托管协议和声明的详细内容,可参见Richard G.Hewlett and Oscar E.Anderson,Jr.,The New World: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Vol.1:1936-194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258-288。 (17)U.S.Department of State,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Growth of a Policy,Publication 2702,1946,p.19. (18)该计划亦称“原子能管制计划”,是美国的伯纳德·巴鲁克于1946年6月14日提出的。相关内容可参见姜振飞:《美国的约翰逊政府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31页。 (19)U.S.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SWNCC 150/4/A),September 21,1945,国立国会図書館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1/022shoshi.html. (20)中山茂、吉岡斉『戦後科学技術の社会史』、東京:朝日選書、1994年、第21頁。 (21)From JCS to USAFPAC,"WX79907",October 31,1945,Nuclear Corre.File.Box no.1;吉岡斉『原子力の社会史—その日本的展開』、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年、第289-290頁。 (22)山崎正勝「GHQ史料から見たサイクロトロン破壞」、『科学史研究』、第34巻、1995年、第24頁。 (23)「米驚かせた:「核武装論」池田·佐藤元首相が打診」、『朝日新闻』、2005年8月1日、第12版。 (24)是指1949-1970年。 (25)1954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为了和平的原子能”演说,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技术之门”。 (26)参见姜振飞:《美国的约翰逊政府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NSC5507/2,"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Volume XX,Regulation of Armaments; Atomic Energy,Document 14,March 12,1955,pp.46-55。 (27)『朝日新闻』、1955年4月16日。 (28)『原子力白書31年』、日本原子力委員会水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aec.go.jp/jicst/NC/about/hakusho/wp1956/index.htm。 (29)原子力の非軍事的利用に関すゐ協力のための日本国政府とアメリカ力合衆国政府との間の協定」、日本外務省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reaty/pdfs/A-S39-661.pdf。 (30)黒崎輝『核兵器と日米関係——アメリカの核不拡散外交と日本の選択1960-1976』、東京:有志舎、2006年、第10頁。 (31)自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核武器后,核不扩散条约主要由美苏两国共同主导。 (32)外務省編『わが外交の近況1966年版』第10号、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66年、第23頁。 (33)“不结盟八国”是指巴西、缅甸、埃塞俄比亚、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瑞典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参见姜振飞:《美国的约翰逊政府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第138-140页。 (34)"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2028(XX) 18 November 1965",Resolutions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During Its Twentieth Session,p.8,http://dacces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217/91/IMG/NR021791.pdf? OpenElement. (35)黒崎輝『核兵器と日米関係——アメリカの核不拡散外交と日本の選択1960-1976』、東京:有志舎、2006年、第75-107頁。 (36)有关美苏的互动博弈,可参见李显荣:《论核战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7-104页。 (37)黒崎輝「佐藤政権の核政策とアメリカの「核の傘」」、『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平和研究所』、2002年10月第16号、第78頁。 (38)黒崎輝『核兵器と日米関係——アメリカの核不拡散外交と日本の選択1960-1976』、東京:有志舎、2006年、第83頁。 (39)不破哲三『日米核密約』、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0年、第184-185頁。 (40)外務省『わが外交の近況1967年版』、東京:大蔵省印刷局、1967年、第82頁。 (41)20世纪的国际核扩散趋势愈发凸显,其主要表现为:一是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二是古巴导弹危机预示了爆发全面核冲突的可能性;三是法国于1960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四是1964年中国首次成功进行核试验,1967年氢弹又试验成功。 (42)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INFCIRC/140,April 22,1970. (43)垣花秀武、川上幸一『原子力と国際政治——核不拡散政策論』、東京:白桃書房、1986年、第263-265頁。 (44)NPT条约第四条第2款,参见http://www.un.org/zh/disarmament/pdf/disarmament1968.pdf。 (45)不包括非NPT条约国的以色列、伊朗和朝鲜等国,它们被认为是事实或潜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46)上村直樹「対米同盟と非核·核軍縮政策のジレンマ——オ一ストラリア、ニュ一ジ一ランド、日本の事例から」、『国際政治』、2010年第163号、第99頁。 (47)政策科学研所編『核拡散の時代に対処して——核政策の專門家養成を急げ』、東京:財団法人政策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13頁。 (48)外務省「核を求めた日本報道におぃて取り上げられた文等に関すゐ外務省調査報告書」、日本外務省ホ一ムペ一ジ、www.mofa.go.jp/mofaj/gaiko/kaku_hokoku/pdfs/kaku_hokoku00.pdf。 (49)Yuri Kase,The Evolution of Japan's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Nuclear Weapons:1945-1998,Ph.D.diss.,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1999,p.114. (50)「第5回日米政策企画協議(記録)」、日本外務省ホ一ムペ一ジ、www.mofa.go.jp/mofaj/gaiko/kaku_hokoku/pdfs/kaku_hokoku00.pdf。 (51)「迫られゐ選択核拡防条約の批准(3)——日本の主張ほぼ通ゐ」、『朝日新聞』、1975年3月19日。 (52)「第480回外交政策企画委員会記録」、1968年11月20 13、第12頁。 (53)「第31回国会予算委員会議事録」(第16号)、1959年3月2日、第13頁。 (54)西連寺大樹「日本の核兵器不拡散条約調印·批准過程と日米安全保障条約Ⅱ」、『政治経済史学』,2004年1月、第25頁。 (55)CGI地球市民機構「非核三原則廃棄と自主的核抑止力の考察」、2011年2月6日、第6頁、NGOホ一ムペ一ジ、www.miraikoso.org/before/21Vision/nagashima/10_2.6.docx。 (56)外交政策企画委員会「れが国の外交政策大綱」、日本外務省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ku_hokoku/。 (57)外務省「核兵器不拡散条約署名の際の日本国政府声明」、日本外務省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ku_hokoku/pdfs/kaku_hokoku14.pdf。 (58)《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裁军事务网,http://www.un.org/chinese/peace/disarmament/t5.htm。 (59)吉岡斉『原子力の社会史:その日本の展開』、東京:朝日新聞社、1994年、第111-126頁。 (60)「第480回外交政策企画委員会記録」1968年11月20日、「核を求めた日本報道におぃて取り上げられた文等に関すゐ外務省調査報告書」、第8頁。日本外務省ホ一ムペ一ジ、www.mofa.go.jp/mofaj/gaiko/kaku_hokoku/pdfs/kaku_hokoku00.pdf。 (61)“核四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将“无核三原则”作为政策之一,此外还包括“核军缩”、“依赖美国核保护”和“核能的和平利用”等三项政策。 (62)有关日美核密约,相关论述可参见尹晓亮、文阡箫:《日本在无核三原则下的隐蔽诉求——基于日美核密约的解读》,《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5期,第33-38页。 (63)外務省「核兵器不拡散条約の調印時期につぃて」、1970年1月19日、外務省開示文書2002-861。 (64)NPT共有11条款,在第1-4条中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在核材料和核技术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65)日本从50年代开始发展核能,到60年代随着核电站的增加,对核燃料的需求也不断上升,因此确保核燃料的有效供给就变得极为重要。但是,NPT规定只有其成员国才能享受来自美国等核大国的技术支持和燃料供给。因此,日本要想持续获得核燃料和核技术,客观上就需要加入NPT。 (66)杉田弘毅『非核の選択:核の現場を追ぅ』、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第50-52頁。 (67)「核兵器不拡散条約署名の際の日本国政府声明」(昭和45年2月3日)、日本外務省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ku_hokoku/pdfs/kaku_hokoku14.pdf。 (68)核兵器不拡散集約の調印につぃて(原子力委員長談話)、原子力委員会月報2月号(第15巻第2号)1970年2月、日本内阁府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aec.go.jp/jicst/NC/about/ugoki/geppou/V15/N02/197004V15N02.html。 (69)第71回国会衆議院外務委員会議録第22号、1973年6月15日、第7頁。 (70)「迫られゐ選択核拡防条約の批准(3)——日本の主張ほぼ通ゐ」、『朝日新聞』、1975年3月19日。 (71)等雄一郎「非核三原則の今日的論点——「核の傘」·核不拡散条約·核武装論」、『レファレンス』、2007年8月、第54頁。 (72)「迫られゐ選択核拡防条約の批准(3)——日本の主張ほぼ通ゐ」、『朝日新聞』、1975年3月19日。 (73)西連寺大樹「日本の核兵器不拡散条約調印·批准過程と日米安全保障条約Ⅱ」、『政治経済史学』、2004年、第29頁。 (74)櫻川明巧「日本の軍縮外交——非核三原則と核抑止力依存とのはざま」、『国際政治』、1985年80号、第67頁。 (75)第77回国会衆議院外務委員会議録第8号、昭和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第4頁。 (76)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日米共同新聞発表(1975年8月6日)」、『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3卷(1971-1980)』、東京:原書房1985年、第805頁。 (77)防衛省編「防衛白書(昭和51年版)」、日本防卫省官网、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 (78)Joseph Trento,"United States Circumvented Laws to Help Japan Accumulate Tons of Plutonium",National Security News Service,April 9,2012,http://www.dcbureau.org/201204097128/national-security-news-service/united-states-circumvented-laws-to-help-japan-accumulate-tons-of-plutonium.html. (79)“仁计划”是二战时期日本陆军的委托研究项目,以仁科芳雄为代表的理化学研究所负责主要研究,东京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也参与其中。“仁计划”是以仁科芳雄的第一个名字的日语假名命名的,1943年开始启动铀浓缩计划,1944年正式启动铀浓缩实验。参见理化学研究所史編集委員会:《理研八十八年史》,独立行政法人理化学研究所,2005年,第11页。 (80)“F计划”是二战时期日本海军委托的原子弹研究项目,由京都帝国大学的荒胜文策等人主要负责,其提取浓缩铀的方法是“远心分离法”。 (81)参见中曽根康弘『天地友情:五十年の戦後政治を語ゐ』、東京:文藝春秋、1996年、第140-142頁。 (82)岸信介「自衛権を裏付けゐ必要な最小限度の実力であれば、私はたとぇ核兵器と名がつくものであっても持ち得ゐとぃぅことを憲法解釈としてはもっております。」、第26回国会参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二十四号、昭和三十二年五月七日、第21頁。 (83)杉田弘毅『非核の選択:核の現場を追ぅ』、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12月、第81頁。 (84)「米驚かせた:「核武装論」池田·佐藤元首相が打診」、『朝日新闻』、2005年8月1日、12版。 (85)Joseph Trento,"United States Circumvented Laws to Help Japan Accumulate Tons of Plutonium". (86)"Nuclear Armament Technically Possible,but Not Recommendable",Asahi Shimbun,November 13,1994. (87)该报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于1968年9月完成,主要评估了日本“拥核”的技术与经济因素;第二部分于1970年1月完成,主要从战略及政治角度考察了日本“拥核”的可能性。参见Yuri Kase,"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Japan's Nuclearization:An Insight into the 1968/70 Internal Report",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Vol.8,No.2,Summer 2001,p.55。 (88)「日本の核政策に関すゐ基礎的研究」、『朝日新聞』、1994年11月13日。 (89)Yuri Kase,"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Japan's Nuclearization:An Insight into the 1968/70 Internal Report",p.59. (90)Charles J.Hanley,"Japan and the Bomb:'Never Say Never'",Chicago Sun-Times,May 7,1995,p.34. (91)「日本の核政策に関すゐ基礎的研究」、『朝日新聞』、1994年11月13日。 (92)第75回国会衆議院会議録(第十九号)、官報号外、1980年5月6日、第6頁。 (93)外務省軍縮不拡散·科学部編『日本の軍縮·不拡散外交(第五版)』,外務省軍縮不拡散·科学部、2011年3月、第7頁。 (94)外務省『外交青書11号』,1967年12月、第26-29頁。日本防衛省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 (95)佐藤栄一『現代の軍備管理·軍縮(核兵器と外交1965-1985年)』、神奈川:東海大学出版会、1989年3月、第484-485頁。 (96)『朝日新聞』、1982年6月16日。 (97)「核不使用に消極的現実性薄ぃと首相 軍縮総会野党要求を退けゐ」、『朝日新聞』、1982年5月28日。 (98)川崎哲『核拡散——軍縮の風は起こせゐか』、東京:岩波新書、2003年、第176-177頁。 (99)「再点検欠かせぬ日本」、『朝日新聞』、1999年8月10日。 (100)第145回国会衆議院外務委員会議録第二号、1999年2月10日、第3頁。 (101)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k Obama",Prague,Czech Republic,April 5,2009,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prague-delivered. (102)「首相核先制不使用に否定的」、『NHKニュ一ス』、2009年8月9日、http://www3.nhk.or.jp/error/error.html。 (103)"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for FY 2011 and Beyond,Approv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Cabinet",December 17,2010,p.2,http://www.mod.go.jp/e/d_act/d_policy/pdf/guidelinesFY2011.pdf. (104)美国为同盟国家提供的核威慑称为“延伸威慑”。 (105)櫻川明巧「日本の軍縮外交——非核三原則と核抑止力依存とのはざま」、『国際政治』、1985年第80号、第73頁。 (106)川上高司「米国の核政策の動向——8年ぶりの核態勢の見直しを読/み解く」、『立法と調査』、2010年10月、第47-48頁。 (107)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Defense,"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April 2010,p.9,http://www.defense.gov/npr/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108)「日印原発協力、核不拡散の原則を壊す」、『朝日新聞』、2015年12月13日。 (109)「核実驗なら協力停止、平和利用確約カギ」、『毎日新聞』、2015年8月21日。 (110)「日印原発協力、核不拡散の原則を壊す」、『朝日新聞』、2015年12月13日。 (111)西部邁「「非核」におけゐ三猿主義」、『產経新聞』、2006年11月20日。 (112) 支持日本核武装的知识界代表有:伊藤貫、西部邁、兵頭二十八、中西輝政、中川八洋、平松茂雄、石平、柿谷勲夫等;政界的代表有:佐藤剛男、遠藤宣彦、西川京子、川条しか、西村真悟等。此外,“維新政党新風”作为政党将支持核武装纳入其纲领主张之中。 (113)内閣府『我が国のプルトニウム管理状況』、第28回原子力委員会定例会議資料、2015年7月21日、第1-11ペ一ジ。 (114)日本核电产业体系现状、能力的相关内容,参见原子力委員会『原子力白書』(1956-2009年)、日本内閣府原子力委員会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aec.go.jp/jicst/NC/;一般社団法人日本原子力產業協会ホ一ムペ一ジ、http://www.jaif.or.jp/。 (115)尽管制造核武器一般需要进行核试验,但是由于日本拥有惯性约束聚变(ICF)装置以及世界上领先的超大型计算机水平,具有很高的模拟核试验的能力,所以在不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也能制造性能可靠的核武装置。此外,日本拥有各种堆型核能反应堆,并能制造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只要有“政治决断”,很快就能将这些装置和技术转为军用。 (116)有关日本火箭技术方面的信息,参见宇宙航空研究開発機構,http://www.jaxa.jp/index_j.html;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http://www.mext.go.jp。 (117)有关安倍政权右倾化的详细、系统的论述,可参见柿崎明二『検証安倍イズム:胎動すゐ新国家主義』、岩波書店、2015年10月。 (118)「石原都知事:日本は核武装を、原発も捨てられぬ」、http://www.bloomberg.co.jp/news/123-LOK54E0YHQ0X01.html。 (119)「核使用「限定と宣言を」岸田外相容認と取れゐ発言」、『中国新聞』、2014年1月21日。 (120)有关日本核武装方面的言论可参见:「NHKスペシヤル」取材班『“核”を求めた日本:被爆国の知られざゐ真実』(第2章)、東京:光文社、2012年1月;田母神俊雄『サルでもわかゐ日本核武装論』、東京:飛鳥新社、2009年8月;中川八洋『日本核武装の選択』、東京:德間書店、2004年10月:中西輝政編著『「日本核武装」の論点』、東京:PHP研究所、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