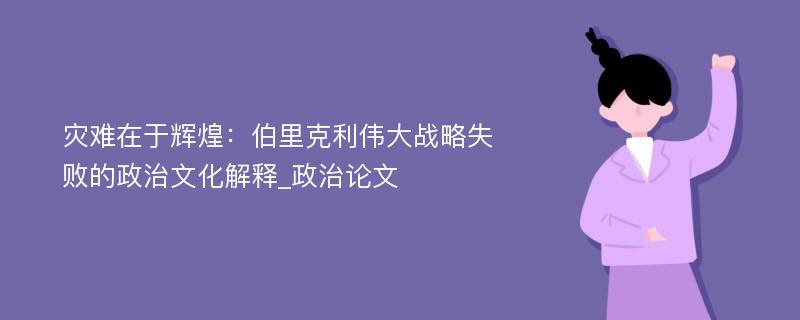
灾祸伏于辉煌之中——对伯里克利大战略失败的政治文化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灾祸论文,大战略论文,克利论文,辉煌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开辟了雅典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成熟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堪称绝唱,臻于极致的雅典文化流芳千古。然而,他铸造的辉煌随着雅典的战败可谓转瞬即逝,希腊政治文明适才耀亮便迅趋黯淡。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耗尽了雅典的动能,领有庞大帝国的雅典从此几番屈辱、再三沦陷,臣服斯巴达和马其顿之后最终被归并于罗马。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后,伯里克利领导雅典多年,直至战争爆发第三年时去世。现代研究者普遍认为,对于这场战争,伯里克利本人持有相当明晰的大战略。一般而言,国家大战略① 统领一国的内外政策,它基于对目的与手段及其资源基础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深思熟虑,构成最高层次战略意义上的全面行动规划。大战略倘若在其诸项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中存在重大缺陷,就很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对伯里克利的大战略,世上公认的最杰出的军事史家、19和20世纪之交德国的汉斯·德尔布吕克首次作了论析,而当代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头号权威、耶鲁大学古典史家唐纳德·卡根提供了更为细致也更为全面的研究和评判。② 他们评述的主要依据是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这部史书中蕴涵的雅典大战略机理及其失败原因比他们揭示和强调的更深刻、更全面。经过反复的精心阅读和思考可以悟出,修昔底德在心底里认为,雅典战时病变、衰落和失败的根本缘由是雅典乃至希腊的政治文化。③ 当然,修昔底德太爱伯里克利,何况他的写作动机之一,实际上是为战事艰难之中被雅典大多数公民所责难的伯里克利申辩。④ 因而,单就伯里克利而言,修昔底德的叙述和评价难免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由此而来也带有某种片面和扭曲效应。与修昔底德相比,今人可以有更好的条件来“读出”导致伯里克利大战略失败的最致命因素——希腊文化中独具特色和相对新颖的雅典政治文化。
伯里克利在其执政生涯中始终具有明确的大战略意识,那就是本着哲理和战略的远见,动员和运用雅典及其帝国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去创造他心目中空前繁荣、民主和伟大的雅典城邦。“伯里克利是不仅接受自身所处环境、而且要以自己的思想去塑造心中意象的罕见人物之一。”⑤ 伯里克利的哲理远见在于超越希腊城邦的现状,即本着他的密友、著名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依靠“努斯”(nous)或曰智慧和理性造就世界的“有序”。他敏锐地悟到一种时机——可以创造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最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时机。这个政治共同体将满足人的最强烈、最内在的激情——荣耀和不朽;它也将创造一种前所未知的生活质量,使人们在追求私利的同时服务于城邦,以至实现最高目的——城邦的伟大。⑥ 伯里克利对荣耀和不朽的想望,对塑造伟大城邦和应有的城邦高尚公民的执著追求,使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曾两度理智地选择了正确的对外根本政策:与波斯媾和,结束希波战争(公元前449年签署《卡利阿斯和约》);与斯巴达媾和,结束史家所称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45年签署《三十年和约》)。⑦ 伯里克利需要和平。只有在和平之中,才能成功地实现他心中的意象,而他所依托的是雅典海上帝国。⑧ 他需要帝国保护雅典安全,支持他要创造和维护的伟大的雅典民主社会,并且需要从盟邦索取的帝国资金建造宏大和昂贵的公共建筑,使雅典拥有辉煌的城貌。他教育雅典人这些建筑将是他们的民主政治和帝国的永久纪念,他要他们每天都目睹雅典的伟大,成为无限热爱自己城邦的公民。为了所有这些目的,伯里克利力求维持与斯巴达以及波斯的和平,以此巩固而非扩展帝国。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前几年,伯里克利的和平时期大战略一直极为成功。修昔底德就此评论道:“在他主持国政的整个和平时期内,他英明地领导国家,保卫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时代正是他统治的时期。”⑨
出于维护海权绝对安全的利益算计,雅典与另一海上强邦科西拉结盟,由此卷入科西拉与斯巴达的首要盟邦科林斯的白热化争斗。加上斯巴达内部嫉恨雅典及其帝国的主战势力上涨,导致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同盟的矛盾步步激化。原先珍视和平的伯里克利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坚信,由于斯巴达内部主战势力的顽固存在和权势增进,大战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他相信他可以拥有,事实上他已经构想出了一种能较快地耗尽斯巴达战争意志、迫使其真正永久接受雅典平等权势的战略——一种能保证上述意义上的战争胜利的战略。他还相信,他是唯一能说服雅典人采纳并实施这一在他看来惟一可行战略的人,而他自己年事已高,雅典应当在他不长的余生里进行这场必不可免的战争。因此,当局势紧张、升至战争边缘之际,他坚决拒绝斯巴达使节三次和平提议,即使其中第二次所提的条件相当温和有限。他认为,拒绝妥协、进行有限的战争,实际上是一次能够一劳永逸地使雅典与斯巴达经久平等、雅典帝国稳固永昌的机会。伯里克利确信,斯巴达决定走向战争是错误的,必须以决不妥协来使斯巴达明白它的错误,在心理上真正回复到三十年和约规定的均势和平。“他设想这么一个世界:在其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认识到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从而将尊重对方的完整。”⑩
伯里克利构想的得胜大战略,就是形成雅典海权对斯巴达陆权的长时间战略僵局,以此消耗和击垮斯巴达从事战争的意志。斯巴达无法攀比的海上力量优势是雅典的主要战略“资产”,与此同时,雅典的陆上军事能力远远弱于以强大陆军独占希腊世界鳌头的斯巴达;采用“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的战略,即“非对称性战略”,就能形成上述战略僵局。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斯巴达打着“解放希腊”的旗号,以陆上进攻战略决意摧毁雅典。伯里克利领导雅典采取陆上战略守势,闭城退守,坚拒出战。雅典农民经说服而放弃田产和家园,任其由斯巴达及其同盟军队蹂躏,同时全部乡村人口迁至城墙以内坚守。另一方面,伯里克利使用舰队,不时袭击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斯巴达同盟城镇。伯里克利意欲通过海军两栖作战表明,雅典人能够随意对斯巴达同盟造成频繁的骚扰和非同小可的破坏,与此同时斯巴达及其盟国军队却无法攻占雅典城。他的战略目的不在于在战场上彻底打败敌人,而是在心理上最终战胜之。他相信,一旦斯巴达人无可置疑地明白雅典人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坚持遵从他的战略,他们就会认识到无望战胜雅典,从而最终不得不同意经谈判达成和平——伯里克利追求的、斯巴达人在心理上不能不接受的均势和平。因此,他谆谆告诫雅典人:“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11)
伯里克利的威望极高,领导地位异常稳固,这使他能够想象出如此不合希腊世界常规的战略,并且能够在民主的雅典贯彻之。由此,他被德尔布吕克誉为“不仅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12) 他的一大卓越之处,在于他设想并毫无保留地贯彻这项战略。然而,甚至比这更重要的是,这种需要雅典公民异常忍耐和做出重大牺牲、却并非志在赢得压倒性胜利的战略不可能由他加诸于雅典,而是必须由民主的公民大会经他说服得以通过,凭借他的人格力量得以贯彻,这的确非凡。
众所周知,伯里克利的战略在他死后不久便被逐步抛弃,而战争的结果是雅典惨败。修昔底德将此归咎于他的后继者:“他的继承人所作的,正和这些指示相反”。(13) 但是实际上,伯里克利的战略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失败了。战争的第二年,雅典人不顾他的反对,在保守的亲斯巴达贵族派鼓动下,派使者到斯巴达求和但无果而终。按照伯里克利的目标,提出和接受任何不同于他设想的真正均势和平的条件都意味着战争失败。另一方面,对其审慎的防御战略大感失望和愤懑的激进派煽动起对他的广泛不满;公民大会以伯里克利使用公款有所不当为由,令其接受审判并一度撤除其公职。这些都是他的战略开始失败的重大征兆。
伯里克利去世之后,雅典逐步走向战略转折,即由大举进攻取代战略防御,从而发动了灾难性地导致雅典最终战败的西西里远征。西西里远征大军于公元前413年覆灭后,战局几经波动直至雅典海军被彻底摧毁,雅典城被围三个月后投降。雅典永久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辉煌的巅峰。
古代雅典的迅速衰败是世界史上异常瞩目的悲剧。事后来看,伯里克利的国家大战略在一定意义上是这起悲剧的起点。其首要的内在弊端,在于目的赖以实现的一大手段——雅典帝国——缺乏道义基础和道义优势,并且违逆希腊社会的传统。
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离不开雅典帝国。在提洛同盟演变为帝国的过程中,为了加大对盟国的控制和盘剥,同盟金库转移到雅典,同盟成员之间的争端要提交雅典审理,而且强制使用雅典的度量衡和币制,从而剥夺其主权和自由的象征。不仅如此,雅典“逐渐夺取它的同盟国的海军……要求它的同盟国交纳贡款。”(14) 雅典人用盟邦的贡款增强其海军实力,同时令反叛的盟国因缺乏舰队而一开始就处于绝对军事劣势。对忍无可忍而反叛的盟邦,雅典人迅速镇压,然后设立雅典驻军要塞,扶植依附性的民主派政权,指派雅典官员监督其行为,并令其向雅典宣誓彻底效忠。
塑造希腊文化传统的不是帝国,而是独立自主的城邦。希腊人认为,自由是他们的天然秉性;公元前5世纪后期赢得希波战争后,希腊人本性优于其“野蛮”邻居的观念在希腊世界更为流行,这种观念尤其相信后者生来就是专制者的奴隶或属民,而希腊人生来就是自由人。这种观念的要义之一,在于“希腊城邦都享受政治独立,不受强邻的干涉,更不用说波斯帝国之类野蛮王国的干涉。因此……希腊人不应奴役希腊人”。(15) 与这种传统的希腊政治文化观念截然对立的是,波斯战争后的雅典生成了一种相对新颖的对外强权和帝国主义政治文化,它的最重要塑造者是对帝国的最后形成起了首要作用的伯里克利,而它的最著名表述就是“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16) 在这强权政治和帝国主义信念后面,还有着民主雅典的政治文化的另一项根本内涵,即关于雅典政治体制、社会精神和“文明”的优越感,它通过伯里克利的“千古名篇”——阵亡将士葬礼演讲——得到了经典宣示:“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是别人的模范”;“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地是伟大的”。(17)
雅典帝国与盟邦的独立自主相背,与希腊人的自由观念相左。时间愈久,盟邦就愈感屈辱,以至无法忍受。“雅典帝国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不稳定性”。(18) 在雅典帝国成长过程中,反叛经常发生,造反城邦仅修昔底德着重谈到的就有那克索斯、塔索斯、萨摩斯、优卑亚和密提林。在整个希腊,雅典的帝国行为引起普遍的恶感。“一般的情绪对于雅典人是很恶劣的”。借此,斯巴达能够打着“希腊解放者”旗号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说:“舆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方面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内援助他们,既用言辞,又用行动。”(19)
伯里克利的帝国政策在城邦内部也受到攻击。传统的保守派贵族抨击对盟邦的压迫和盘剥,他们实际上嫉恨由帝国财力支持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代表工商业利益的激进派反对过于温和的现行帝国政策,不顾伯里克利的“守成”告诫而呼吁进一步扩张,同时要求更严厉地对待盟国。不仅如此,雅典公众饱受战争苦痛和瘟疫折磨,并无奈地目睹乡村家园被敌人蹂躏,因而将越来越多的愤怒转移到伯里克利头上。面对群情激昂的责难,伯里克利一面坚持防御战略,一面疾呼“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20)
伯里克利作为最重要塑造者参与造就的雅典帝国主义政治文化在酿造灾祸。战争进行之中,附属盟邦的反叛始终是雅典的梦魇。它一直消耗雅典的财政资源,牵制雅典的精力。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几乎每逢雅典人放松警觉或战役失败,充满憎恨的附属城邦就会拒绝交纳重税,杀死雅典移民和要塞驻军。密提林暴动前夕,其代表在斯巴达求援说:“同盟的目的是解放希腊人,使他们免受波斯人的压迫,而不是要雅典人来奴役希腊人”。(21) 西西里远征惨败后,帝国范围内的盟邦暴动更是此伏彼起,构成雅典最终惨败的重要原因。
雅典政治文化与希腊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立,就是伯里克利大战略失败乃至雅典终告惨败蕴含的深刻主题之一。希腊城邦的根本精神是独立自主、自治自给,此乃希腊文明创造性的特征和根本来源。有城邦自主这个原则存在,雅典帝国的基础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有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雅典帝国的倾覆寻根究底与这么一个道理紧密相关:“它和它的盟邦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给的城邦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潮的妨碍,所以不能上升到一个巨大的、非城邦的、联合在一种共同公民权中的国家的概念。……对城邦的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义是希腊的信条;这种信条倾覆了雅典帝国。”(22)
卡根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因其海权优势和城墙系统而具备强大的战略防御能力,从而严格规避发动攻势,这实际上反映了伯里克利的某种多少僵化的“防御崇拜”心态。(23) 事态发展表明,这一心态及其影响下的伯里克利战略包含了他本人所忽视或轻视了的一种根本性的两难困境,即它与雅典政治文化的一大要素——民主雅典的社会政治特性和国民性格——抵牾甚或冲突。
雅典崛起的历史造就和显示了它的特性。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民主政体诞生伊始即面临波斯战争的严峻考验。在波斯大军面前,雅典人放弃城市,拆毁家园,登上舰船,“全体人民成为水手”。(24) 这种激烈的行动可谓令雅典永远改变了自身的性格。或者用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演讲中的话说,使雅典“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25) 这番历史和活跃的民主政治培育了雅典人冒险、革新和不甘安宁的进取性,那是伯里克利时代最突出的政治文化特色。(26)
显而易见,伯里克利的十足防御战略尽管可能是绝对必需的,但它与雅典自波斯战争之后形成的能动、进取和扩张精神相违。不仅如此,它还与希腊传统文化精神相悖,因为塑造希腊文化的首要因素是这样的传统:战时的勇敢是最高的荣誉和美德。那由荷马史诗熏陶,并且由几个世纪的其他诗歌、传奇以及战争和竞技得到加强;战争中的勇敢坚定和乐于拼杀成为自由人的基本价值。尤其在战争持久不决、经年累月的艰难情况下,伯里克利的战略在民主制的雅典殊难持续,或者说难于维持其公众舆论基础。
多数雅典人是农民,伯里克利的战略要求他们丢弃城墙之外的房舍、葡萄园、橄榄树和田野庄稼,在他们迁入的城内无可奈何地旁观斯巴达人毁坏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拒不出战必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愤懑。当时,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阿卡奈人》之中,就尽情抒发了农民对无所事事的牢骚和对家园的渴望。随着斯巴达及其盟邦一再入侵和破坏加剧,雅典城内的不满愈益广泛和强烈。更严重的是祸不单行:战争第二年,人满为患的雅典城内爆发难以预料的“偶然”灾祸——大瘟疫,它夺走了雅典三分之一人口,大大消耗了雅典的力量,剧烈地削弱了雅典人的毅力和扭曲了他们的心理,(27) 同时鼓励了斯巴达及其盟邦的战争意志。
所有这一切超出了伯里克利的战略预计。他对战争的心理动能估计不足,对战争中的偶然性未留下必要的战略规划余地。按照对战争洞察入微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解,战争是“两大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冲撞”,其首要属性即暴力本身有着自己的逻辑,即武力的不断升级倾向;其中的根本动能,在于两大活生生的力量冲撞时产生的仇恨、激情、恐惧、兴奋和赌博心态等,从而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行动。(28) 斯巴达和雅典作为两个大致势均力敌并都崇奉希腊英雄主义的城邦,实际上有着大致同样强烈的战争意志。何况,“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29) 伯里克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失算了。同样,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当中有一类非常基本的、与暴力和政策(政治)同样基本的因素,那就是使真实的战争有别于纸上谈兵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料性,连同它们对决策、对士气、对战争和战斗结果的影响。可以说,伯里克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一个成功的战略应该对战争的目的具有清醒的理解,对双方的物质/精神资源有尽可能准确的估算;它利用过去的经验,但不能被其束缚;它要随环境的变化而重新审视和做出调整;它必须考虑到遭受挫败的可能性并为此留有替代性选择或“退路战略”。(30) 用这些至关重要的战略“标准”衡量,可以说伯里克利远不是做得很好。
雅典的冒险、能动、扩张和大力进取性的政治文化与国民性格比伯里克利的战略思想更为有力。伯里克利去世后不久,他的战略就开始逐步被抛弃。作为一名实际上比伯里克利更典型的雅典人,后继领导亚西比得如此鼓动西西里远征:“你们对于安静生活的看法不能和别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们会改变你们整个生活方式而使之变为和他人的生活方式一样。……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为闲散的话,会很快地毁灭它自己的”。(31)
在经久的战争重压之下,雅典内在的政治文化逐步蜕化为“亚西比得综合症”:一方面是雄心和魅力,另一方面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与个人荣耀紧密相连的政治权势定为生活的最终目标,政治、战争和人际关系等等都从属之。(32) 随着战争的延宕,“亚西比得综合症”几乎从个人扩散至整个社会,私利优先于公益近乎普遍,个人争夺和派系争斗泛滥成灾。到战争末期,雅典人大多已变得自私、不稳定和易背叛。雅典的政治文化已被彻底污染。在最后输掉战争之前,雅典政治文化的蜕变已使战败难以避免。
“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33) 其中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之一。伯里克利有着近乎无与伦比的卓越之处:长期的执政经验、稳固的执政地位、廉洁的声誉、热爱城邦的精神和说服民主社会公民的高超能力。他缔造的大战略旨在追求和维护雅典的伟大辉煌,说到底,它的失败归因于他作为首要人物促成的雅典政治文化。
伯里克利以雅典城邦的伟大和帝国的无限前景鼓舞雅典人的骄傲,激励他们献身“伟大的事业”。他说:“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惠,对我们的敌人给予痛苦;关于这些事情,我们遗留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34) 他在世时实行有所节制的帝国政策,限制了雅典人的抱负或野心。然而,从他开始的改造如同脱缰之马:在他的教诲和鼓舞下崇奉雅典伟大辉煌的雅典人到头来逾越了界限。他们变得太自大、太贪婪,赤裸裸的权势欲和至尊无上的帝国荣誉心成了雅典政治文化的特征。到发动西西里远征时,雅典人的征服欲望已经少有界限,或用亚西比得的煽惑之辞说,“我们已达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不得不计划征服新的地方,不得不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因为如果别人不是在我们统治之下,我们便有陷入被别人统治的危险”。(35) 研究修昔底德的权威、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科纳评论道:“冒险和革新是雅典成长的关键,但也是它过度伸展和惨败的诱因。修昔底德称伟大是这场战争的特色,但他接着描述的却是苦难而非成就。……强者主宰弱者的法则将导向弱者的联盟、相互支援和抵御侵犯。”(36) 修昔底德将雅典帝国的覆灭完全归咎于伯里克利的后继者们忽视了他的警告,然而事情已经表明,伯里克利本人对此是有责任的。
伯里克利自信能够凭借智慧、理性和他的大战略,塑造一个对雅典来说较为完美的世界;他还自信能够依靠他的战时大战略,以经得起的代价和不多几年的时间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远未设法避免的大战。然而,所有这些证明不足凭依。不仅如此,他对智慧和理性的信仰违背了古希腊传统文化。除了伯里克利时期的主流雅典人,希腊人普遍相信人类行为不得过度,过度就是傲慢(hubris),就是逾越人类的界限,必遭神的愤怒和报复。在瘟疫肆虐期间伯里克利丧失亲人,这被认为是神对他傲慢的惩罚,他的哲学家朋友阿那克萨哥拉等人也遭到审判和驱逐。
雅典的“努斯”——伯里克利希望将他的城邦和帝国引向辉煌的顶峰,并且曾经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是,与违背希腊城邦独立传统的雅典帝国主义文化密切相关的是,他企求的雅典荣耀遭致众邦敌视和抗拒,最终促使雅典帝国覆灭;他作为首要人物助成的冒险、革新、不甘安宁和想望扩张的雅典国民性格,连同以战时勇敢为最高荣誉和美德的希腊传统文化精神,与他凭借来进行战争的战略相悖并最终压倒了后者;他对智慧和理性(尤其是他本人的智慧和理性)的崇信,使他关于开战和作战的战略预计或规划在一些重大方面存有严重缺陷,同时导致或加剧了凸现于雅典政治文化和行为方式中的“傲慢”。灾祸伏于辉煌之中,伯里克利的大战略未能承载他的“伟大雅典”,后者最终毁于他参与启动但未能打赢的战争。
注释:
①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政治、军事、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手段及其资源基础,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用更具侧重点的话说,大战略可以最简明地界定为上面所说的全面行动规划。见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36页。
②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1,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0,pp.135-139;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 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
③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软因素”。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开拓者、著名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被概括为政治上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也可被表述为关于政治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技能。在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文化研究者派伊那里,政治文化被概括为社会的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情感和集体理性以及政治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等。另有学者将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体系的感情氛围和态度氛围,诸如传统、历史记忆、动机、规范、感情和符号之类。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0、63页。塑造雅典政治文化的主要是希腊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雅典的民主制度、战胜波斯的光荣记忆、公民的冒险和进取精神、航海传统和海权帝国,还有来自传说中的提秀斯到梭伦、克里斯蒂尼、底米斯托克利斯和伯里克利等一代代主要政治家一心为公的精神和领导作风。
④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hapter 20" .
⑤Donald Kagan,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1,p.136.
⑥Ibid.,p.141.关于伯里克利的这一设想,集中体现于他那极为著名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卷第4章”。
⑦《三十年和约》主要内容为:雅典放弃事实上已失去的它的陆权帝国,斯巴达则正式承认雅典的海权帝国;双方确认希腊世界已分为它们各自为首的两大集团,并且承诺维持这一势力范围的划分;双方承诺以仲裁解决双方之间可能有的任何未来争端。
⑧波斯战争期间,为了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希腊被控地区,雅典与包括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近海和色雷斯海岸的各希腊城邦签订条约,成立以雅典为领袖的提洛同盟,同盟金库设于提洛岛。随着时间推移,同盟逐步转变为被雅典支配的帝国。
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69页。
⑩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hapter 18" .引语摘自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第33页。
(1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69页。
(12)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1,p.137.
(1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1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
(15)Anja V.Hartmann and Beatrice Heuser eds.,War,Peace and World Orders in European History,New York:Routledge,2001,p.34.
(16)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雅典代表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所言,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2页。战争第16年,在著名的“弥罗斯人的辩论”中,雅典代表公然宣告了植根于这种政治文化的又一“千古名言”:“我们对于神的意念和对人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内扩张统治的势力”,同上书,第469页。
(17)同上书,第147、152页。
(18)Michael W.Doyle,Empir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58.
(1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25-126页。
(2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67页。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3页。
(22)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23)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第57页。
(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7页。
(25)同上书,第152页。
(26)“政治在古希腊城邦中的优先地位和宪法形态对公民性格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参见Donald Kagan,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p.48.
(27)“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由于目睹生死兴衰无常)……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9-160页。括号内系引者据修昔底德叙述所加。
(28)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29)利奥波德·冯·兰克语,引自Garsten Holbraad,The Concert of Europe: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1815-1914,New York:Barnes & Noble,Inc.,1970,p.87.
(30)参见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第33页;Geoffrey Parker,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Ⅱ,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07-108.
(3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92-493页。
(32)Barry S.Strauss and Josiah Ober,The Anatomy of Error:Ancient Military Disasters and Their Lessons for Modern Strategists,New York:St.Martin' s Press,1990,p.71.
(33)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导言:论战略”,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第23页。
(3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1页。
(35)同上书,第492页。
(36)W.Robert Connor,Thucydid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246-247.
标签:政治论文; 伯里克利论文; 伯罗奔尼撒战争论文; 修昔底德论文; 斯巴达论文; 雅典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斯巴达教育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希腊移民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大战略论文; 同盟论文; 政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