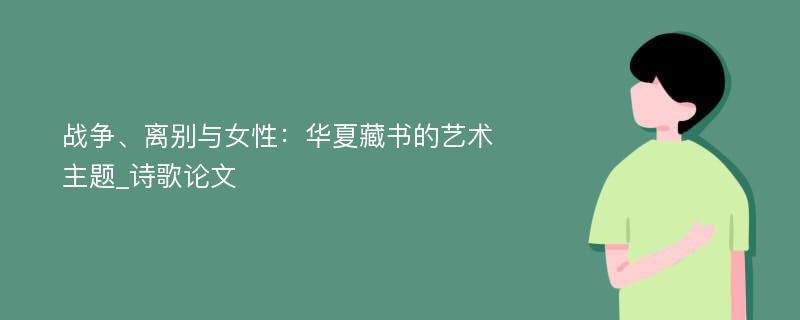
战争、离愁和女人——《华夏集》的艺术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夏论文,离愁论文,战争论文,艺术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同的艺术之间实在具有“某种共同的联系,某种互相认同的质素”。
——庞德(Ezra Pound,1885—1972)
一
在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现代派文学运动中,意象派(Imagism )以其“坚挺、明晰、严谨”的美学特征和“清新、简洁、自然”的创作风格,成为反拨19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和过于罗嗦、过于渲情的诗歌的一支“生力军”。
意象诗是突破传统格律的自由诗,为了对抗维多利亚时期出现的感情极度张扬的浪漫主义诗风,意象派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作为“武器”,并从中吸收了大量有效成分。锐意革新诗歌的庞德是该运动中的一名“主将”和“旗手”,但由于他本人不懂汉语,无法阅读汉语原诗,所以只能借助别人的译作,结合自己的领悟进行艺术性的再创作。受曾在日本教书的汉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遗孀的委托,并参考费氏生前所作的有关中国古诗的笔记,庞德于1915年出版了收有19首(注:其实1915年4月首版的《华夏集》只收录了15首, 1916年9月以《祓除》重印,并增添了4首。)经过删削、润色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译集《华夏集》(Cathay),这是他在积极倡导并热情参与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中的一部有影响的翻译作品。其实若严格按照翻译学的“信、达、雅”三原则来考证,《华夏集》很难算得上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译作”,倒不如说它是庞德在参照中国古诗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为此台湾学者余光中先生贬之为“偷天换日式的‘翻译’”(注:余光中《翻译与创作》,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43页。))。因为庞德的译诗完全打破了原诗的严谨格律, 而且他“自以为是”地做了大量改动,好多地方甚至与原诗毫无瓜葛。鉴于此,国内译界人士和海外华人学者对《华夏集》多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对汉语原诗的误解甚至扭曲。然而,《华夏集》一问世即受到英语读者的普遍欢迎,更得到文人的好评, 如美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他的经典著作《通天塔》(After Babel,1975)一书中,花了好几页的篇幅推崇《华夏集》,认为它“比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译本更能反映原作的风貌”(注:乔治·斯坦纳《通天塔》,庄绎传编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105页。);T.S. 艾略特甚至盛赞庞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创造者”(注: Ezra Pound,Selected Poems,ed.T.S.Eliot,London: Faber & Gwyer,1928,p.14.)。
《华夏集》之所以能在西方得到肯定和接受,主要是因为庞德以其“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现代化了”的翻译方法打破了时空差距,使英语读者读到这些诗时没有因为几百年或几千年的跨度而产生隔膜感。翻译是两个文化系统之间互通的“桥梁”,在翻译实践中,必然牵涉到两个文化系统和语规的协商调整,从而必然涉及到双重的意识形态,一名好的翻译者应在这两者的相遇里作出种种协调,以求达到两种意识形态最大程度的交融。国内学者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华夏集》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加以评判,但这种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为翻译而翻译”上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妨碍读者对《华夏集》整体意义和全面价值的理解与把握。本文不拟再对《华夏集》进行翻译上的优劣得失的探讨,而是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等角度入手,结合庞德创作《华夏集》的时代背景,着重分析《华夏集》的具体内容和深层主题。
二
作家在创作时大多假设一群要接受他作品的读者,并从读者对其作品可能产生的接受和领悟程度出发,来确定作品的题材范围和语言策略。那么,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时有着怎样一种创作心理呢?他心中又存在着怎样一个读者群呢?《华夏集》于1915年4月在伦敦出版,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爆发近一年,英国是参战国,战争使英国人民受到强烈而混乱的冲击:家庭遭到破坏,群体受到摧残,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是满腹哀伤。当时庞德侨居伦敦已有数年,所以他能够切身感受到战前的骚乱以及战争的爆发给人民带来的种种苦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华夏集》已不单纯是一部翻译作品了,其所覆盖的内涵,渗透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因而它的社会意义,至少在其问世之际,远远高于它的学术价值。
从具体内容上看,《华夏集》中的诗篇大多阐述了怨恨、孤寂、离别等一系列和战争有关的伤感主题,这正切合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怀念亲人、憎恨离别的心情。因此研究庞德的权威学者休·肯纳(Hugh Kenner,1923 —)中肯地评价道:“《华夏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关于战争的作品……它所描述的背井离乡的弓箭手、无人体贴的妇女、被击溃的王朝、动身去遥远的地方、孤独的边疆战士、昔日的光荣、美好的回忆,正是出于作者对当时四分五裂的比利时和动荡不安的伦敦的敏感,这些题材才被从费诺罗萨遗稿的众多诗篇中挑选出来……”(注:Hugh Kenner,The Pound Er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202.)。1913年底,费诺罗萨的遗孀托付给庞德代为整理的其夫的遗稿中包括约150首费氏生前已采用直译法翻译过的中国古典诗歌,而庞德后来从中仅精选了19首进行再加工,这种在数量上的严格把关足以表明庞德的选择有其明确的目的性——他以当时英国严峻的社会背景作为参照,只选择能够恰当反映这一背景的题材,他试图营造一种1915年前后英国读者和中国古诗之间共通的心理结构,并力求借助于形神兼备的、含蓄而有力地表达了幽思、别愁和暗恨的中国古诗,来抒发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抨击以及他对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的同情。
在1914年,许多英国士兵是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心甘情愿走上战场的,有的人甚至对战争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心里说:“谢天谢地,现在可让我们时来运转啦!”然而,在战壕里体验到的战争的残酷很快就把这种幻想一扫而光。(注: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英国现代史》,秦士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7页。)为了反映这种失落的情绪,庞德有意选择了几首描绘古代中国戍边战士对战争的抵触情绪和对家人思念之情的诗篇。《华夏集》开篇第一首诗就紧紧抓住了战争期间英国读者的心,它是从《诗经·小雅·采薇》译过来的(庞译“Song of The Bowmen of Shu”)。 原诗《采薇》的前三节回忆久戍不归的思家之苦,四、五两节回忆疆场奔走战斗之劳,末节以景物烘托情感,使情感融化于景物之中。庞德在翻译过程中紧紧把握住了原诗的要旨,把士兵的悲怆用很口语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谁要是提到“回家”这两个字,所有人都心情低落/一肚子苦闷,我们又渴又饿/……我们没工夫休息,一个月内连打三次仗/……我们出发时,春风吹拂着杨柳/归来时,雪花纷飞/步伐缓慢,我们又渴又饿/一肚子苦闷,谁知道我们的哀伤?
李白的《古风·胡关绕风沙》(庞译“Lament of the FrontierGuard”)描绘的是一幅由于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而造成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士兵怨声载道的凄惨画面: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堵墙。白骨横千霜,……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边人饲豺虎。
庞德在译这首诗时更加重了其哀悼的色彩:
荒芜的城堡、天空、大漠/这个村庄已无片垣残存/层层秋霜盖着累累白骨/……阳春变成了嗜血的秋天/战争的混乱,波及王国的中部/……我们边疆战士们被喂了虎狼。
只有联系当时的战况和时局,我们才能更好地体会庞德选择此诗的深刻含义。一战初期的主战场在法国境内,英国最初派出的远征军不但未能扭转法国的战局,反而损失惨重;到1914年底,西线英军约有27万人,但伤亡已近10万;1915年以后英国本土防卫部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前线(注: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华夏集》中另外一首和战争有关的诗译自李白的《代马不思越》(庞译“Southfolk in Cold Country”), 原诗先从北方的马不愿去南方、南方的鸟不留恋北方说起,从而引出士兵不堪远赴异地他乡的征战之苦,同时还进一步表达了士兵对“徒劳而无功”的感慨和无奈:
……虮虱生虎曷,心魂逐旌旗。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
在此基础上庞德的译文正好道出了参战士兵对当时愈演愈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无聊赖的心声:
虱子如蚂蚁般寄附在我们的装备上/理智和精神随着战旗前驱/苦战得不到奖赏/忠诚到底为何物?
庞德选择的这三首和战争有关的诗歌,都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鼓吹将士是如何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而是站在战争中身心交瘁的将士们的立场,以他们的口吻表达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通过这三首译诗,庞德申明了他本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参战士兵的关心和体恤。这一部分诗歌是如此符合1915年前后作战将士艰苦卓绝的情形,以至于有人特意将《华夏集》带在身边,把它作为战争期间精神上的安慰物——“我把这本书装在口袋里随身带着,我用它里面的诗篇来给同伴们鼓劲。我尤其喜欢其中的《采薇》和《胡关绕风沙》两篇,它们太适合我们眼下的情况了。”(注: Hugh Kenner,The Pound Er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202.)从这个意义上讲,庞德似乎可以被称为这些士兵的“代言人”,因为英国当时从前线寄回的经过严格检查的“欢快的”家书,不得不有意隐瞒了战争的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误认为“大兵们”是“快乐的杀手,永远兴高采烈,喜爱战争的热闹场面,有机会打仗就开心”(注:W.N.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张毓文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5页。)。庞德通过《华夏集》给持这种观念的人讲述了一些事实真相,也使这些人对战争的野蛮和残酷有了一定的正确认识。
《华夏集》中另一突出的主题是“离别”。围绕这一主题,庞德选择了四首唐代诗歌,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刻画了送别双方的感伤心理,这在1915年时的英国人读来一定有强烈的认同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到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穷人富人概无例外,人人均有亲朋好友参与其中。有道是“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梁·江淹《别赋》),何况战争还意味着伤亡,这就更给离别罩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
庞德翻译的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庞译此诗时未加英文标题)开篇描绘了一个令人留恋的清新的分别时节:“小雨压着微尘/小客栈院子里的柳树将愈加青葱”,在这样的氛围中,“但是您,先生,最好走之前饮了这杯酒/因为当您到了异乡,就没朋友在您身边了。”送别两依依,纵有万语千言也诉不尽内心的留恋,只好举起杯劝酒以壮行色。但毕竟一去祸福难料,要走的人心头总有顾虑,于是送行的人安慰道:“人生来都有各自的命运/没必要再去问占卜者”(译自李白的《送友人入蜀》,庞译“Leavetaking Near Shoku”)。海军是一战初期英国出动的主要兵力,因此英国的码头上常有壮观的送别场面,庞德所译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庞译“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正好体现了当时人们极目张望远去的战舰时的失落心情:“他那片孤帆遮蔽了远方的天/现在我只看得见长江,滔滔江水涌向天边”。李白的另一首名篇《送友人》(庞译“Taking Leave of a Friend”)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庞德也以这一手法利用客观景物渲染离别的感伤:
在此我们必须分别/(你)将穿越数千里的茫茫荒草/心绪有如一片浮云/日落就像老朋友鞠躬揖别的情形/我们的马儿也因我们的离别而相互嘶鸣。
战争使人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因而对离别也就更加重视。
《华夏集》中这四首送别诗以简练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反映了人们离别之际的真实心理,因此读来让人觉得格外熟悉和亲切。庞德翻译这四首离别诗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直接宣泄离别的伤感,而是借助于景物的烘托和具体细微动作的刻画,把感情或由景物引起的经验的激发点提升到某一种高度和浓度,于是使人读来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一切尽在不言中”的韵味。
如果说《华夏集》中讲述战争的诗歌主要和男人有关的话,那么这本译集中另一些诗则描写女人,最为典型的是三首“闺怨体”中国古诗。一战使英国大量男子应征入伍,客观上造成了男女(主要指丈夫和妻子之间,情人之间)空间上的大“鸿沟”,而且由于一战之前的英国妇女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言,经济上基本不能独立,这就更加重了她们对丈夫的依赖和思念,此种状况类似于中国古代“以夫为纲”的妇女的处境。庞德曾因在谈诗歌创作时流露出明显的“性别歧视”(sexism)而一度被称为是“公然厌恶女性的作家”( openly misogynistic writer)(注: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No Man's Land:The War of the Word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148.),然而他在《华夏集》中所体现出的对待妇女的态度却与他先前所持的态度截然相反——在此他对女性寄予极大的同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庞德深刻认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女性造成的严重的心理创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代她们抒发受压抑的情怀。因此,在这三首译诗中,庞德将妇女放在一个比中文原诗和费诺罗萨的笔记所暗示的更突出的位置,并且赋予她们更多、更直接的发言权。
李白的《玉阶怨》是一首写得剔透玲珑的闺怨诗,其艺术特色在于不正面写“怨”,而以细微的动作神情体现出“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庞德的翻译强调了它的意蕴深远、含蓄不露的“暗示性”:
嵌着宝石的台阶已闪着露水的白光/夜色深沉,露水浸湿了我的罗袜/我放下水晶帘/透过朗朗的秋夜遥望明月。
原诗并没有出现主语,庞德却在译诗里有意加了一个第一人称“我”做主语,从而突出了女主人公的声音,鲜明地强调了女主人公秋夜里“望月怀远”的幽怨心情,所以虽然女主人公没有直陈怨情,但“此时无声胜有声”,读者能立刻进入她那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情感世界。
《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二首“青青河畔草”(庞译“The Beautiful Toilet”)是写思妇伤春的,前半部分用河畔的青草、园中的绿柳作为春天景致的象征,映衬出妆束艳丽的思妇的神态和面貌;后半部分刻画思妇的出身和伤春的缘由——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注:倡家女,指从事歌舞的女艺人;荡子,指“游子”、出行在外的人。此处的“倡家女”和“荡子”并无贬义,并非后世所说的“娼妓”和“浪荡子”。)。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庞德在翻译过程中将第二部分的意思做了完全的改动,这一改动有助于英语读者更强烈地感受到“独守空房”的思妇的不幸遭遇:
她从前是官家的歌妓/后来嫁给了一个酒鬼/她丈夫现在醉醺醺地出去了/只留下她一人孤苦伶仃。
联系一战中英国妇女的实际状况——她们中大多数都被遗弃在家而不得不独立生活——庞德选择这样一首诗显然是针对当时英国这一很普遍的情感问题的,同时他也意在指明战争的危害涉及到了每个人,不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
李白的《长干行》(庞译“The River Merchant's Wife:A Letter”)写一个年轻商妇对久别丈夫的想念,从头至尾均为商妇的独白,诗中通过亲切的叙事,生动的写景,深刻地揭示了她的内心活动,热烈地表达了她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庞德在翻译时着意将原诗东方女子的形象和她所表现的感伤移置于一个类似的西方的情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英国的许多夫妻离别,丈夫远赴欧洲打仗,妻子念夫心切,禁不住时常登高隔海远眺,所以当时在英国沿海建造了不少专为此用的“了望塔”。《长干行》中恰有一处同此相似的情形,也是讲“望夫台”的(“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于是庞德顺手拈来:“但愿你我的骨灰融合一处/永远,永远,永远/我又何必攀上那了望台呢?”通俗而又形象地表达了妻子对丈夫的热切盼望和忠贞信念。妻子同时更希望丈夫能凯旋归来,她宁愿为此不辞劳苦地去迎接他,庞德借译《长干行》中的最后两句道出了当时英国士兵的妻子们这一情真意切的心声:
如果你要穿过长江的狭窄处顺流而下/请事先告知我/我会一直赶到长风沙去迎接你。
三
庞德着手翻译汉诗的初衷是想从中国诗歌这座“山”中取出合适的“石”,以“攻”英语诗歌、特别是意象派诗歌之“玉”,他的努力客观上极大促进了中国诗歌在英美人民中间的推广,因此庞德对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功不可没。根据中国学者在美国所做的大量实地调查,美国学人,特别是作家,多多少少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的大有人在,从庞德起的几代美国学人绝大多数也都是通过《华夏集》获益的。(注:张子清《20世纪美国诗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7页。)另一方面,庞德出于他自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心疾首, 从而确定了《华夏集》的基调和主题。在他看来,大战葬送了千百万优秀人才,败坏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只不过是“为了两箩破烂塑像,/为了几千本破书”(“For two gross of broken statues,/ For a few thousand battered books”)(注:庞德《休·塞尔温·莫伯利》(Hugh Selwyn Manberley,1920)第一部分第五节。)。休·肯纳认为,《华夏集》所包含的是一组阐释战争的挽歌体的诗篇,类似的诗篇在《华夏集》问世前尚无人写过;时隔50年,在所有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诗歌创作中,《华夏集》仍属于最经久耐读和富有活力之作。(注:Hugh Kenner,The Pound Er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202.)为了客观全面地评 价《华夏集》,我们不应忽视它所包含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
通过上面的探讨,我们不难看出,庞德翻译《华夏集》所坚持的原则是“古为今用,中为西用”,以古代的中国映衬1915年前后的英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夏集》可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产物;但凡文化互相交流时,产生的现象异常复杂,有融合,有分解,有接受,有拒绝。庞德通过《华夏集》的翻译实践,很好地把握住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这为他日后更加喜爱和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通常情况下,一种文化传入另一国以后,往往有一个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接受的过程,而庞德的从实际出发、为现实服务的《华夏集》,因为能与当时英美读者的语言和感受达到共识,所以很容易地缩短了这一过程。《华夏集》所反映的艺术主题,即“战争、离愁和女人”,即使在今天读来也并没有老化或过时,因为“摆脱战争,热爱和平”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民族的共同心愿。
标签:诗歌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战争论文; 文化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长干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