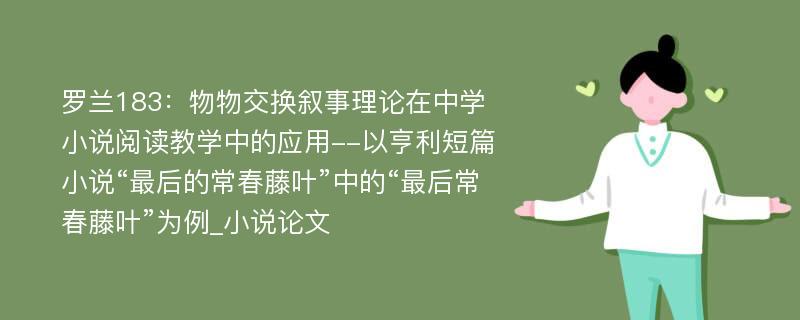
罗兰#183;巴尔特叙事理论在中学语文小说阅读教学中的运用——以欧#183;亨利短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常春藤论文,为例论文,短篇小说论文,中学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兰·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曾提出叙事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主要以小说文本为主。小说阅读教学的传统模式通常从分析小说的背景、人物、事件开始。如此分析,往往会使小说的阅读教学陷入俗套之中。本文尝试运用罗兰·巴尔特的叙事理论来解读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短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 每一个叙事作品均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层面:一个是故事(内容)层,即由小说人物参与构成的故事情节;另一个是话语(形式)层,主要包括叙述时间、叙述人称、叙述视角。罗兰·巴尔特叙事理论也由这两个主要层面组成,只是他将故事层又细分为“功能”层与“行动”层,并与话语层一起构成了一种对叙事作品的分析方法。 一、“功能”层:确定故事情节的最小叙述单位 “功能”层,“它是对叙事作品的叙述话语做切分,目的是确定最小的叙述单位,而这些叙述单位要能体现叙事作品的意义”[1]。通俗点理解就是在小说文本阅读过程中发现那些令阅读者深有感触或玄妙多端的词语、句子及片段。以《最后的常春藤叶》为例,作者开篇介绍故事发生的环境时写道:“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街道仿佛发了狂似的,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在这段叙述中,请注意这个“狂”字。一方面作者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表现出“巷子”多到何种程度,仅就叙述的表象环境已隐隐地透着一种病态的气息;另一方面,“狂”的岂止是街道的“巷子”,还有下文中那迅速蔓延的“肺炎”病毒以及小说最终要表现的人物老贝尔曼先生的疯狂善举。一个“狂”字暗示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曲折发展。在阅读文本之初,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多发现类似情节中的“闪光点”。 接下来在文本分析过程中将发现的“闪光点”做些区分。巴尔特用“功能”和“标志”这两个名称加以命名。像上例中的“狂”字,它本身构成一个最小的叙述单位。经过分析发现这个“狂”字实际为小说的情节发展作了暗示。既然是暗示,就说明还需要通过小说下文的叙述进行印证。像这样的小叙述单位便是巴尔特所说的“标志”性叙述单位。所谓的“标志”,“不是一个补充的和一贯的行为,而是一个多少有些模糊的,但又是故事的意义所需要的概念”[2]。再如老贝尔曼先生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对于他的出场作者有这样一段叙述,说他是一个失意的画家,已年过六十了,还没有任何艺术造诣,只能通过给像苏艾与琼珊一样的年轻艺术家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老是说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这不禁会让人觉得,这到底会是一幅怎样的杰作?下文会不会告诉我们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暗示,使读者具有更多的阅读期待。除了标志性叙述单位之外,还有功能性叙述单位。例如小说写道:“她们是在八马路上一家名叫德尔蒙尼戈的饭馆里吃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于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了那个画室。”正是因为有苏艾与琼珊合租画室,才有了小说所有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发展。而像这样对于小说故事情节具有缺其不可的叙述单位便是巴尔特所称的“功能”性叙述单位。 在小说阅读教学中分析“标志”性叙述单位和“功能”性叙述单位,可以使学生了解“功能”性叙述单位构成一部小说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叙述框架。而小说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吸引性,这是由“标志”性叙述单位构成的。理解这两种叙述单位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对小说文本的故事情节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学生小说文本创作能力的提高。 二、“行动”层:展现小说故事情节的深层结构 罗兰·巴尔特的“行动”层概念,也属于故事层面的分析。如果说“功能”层是对故事情节的浅层把握与分析,那么“行动”层就是对故事情节深层结构的把握与分析。因此“行动”层较“功能”层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巴尔特看来,任何一部叙事作品的情节结构都包含六个行动要素:主体/客体、发送者/接收者、帮助者/反对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处于发送者与接收者的交流关系和帮助者与反对者的对立关系中。在《最后的常春藤叶》中,主体是苏艾,客体是琼珊。实际将整个小说抽离到最后即是主体苏艾成功解救客体琼珊。但这个主体寻求客体的过程并不顺利,其间遇到许多波折,而这些波折正是由发送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反对者所构成的交流关系与对立关系完成的。正是由于这些关系的存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才会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在小说开篇之初,刚获知琼珊不幸染上严重的肺炎病时,医生作为发送者,发出需要有人帮助琼珊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这一信号,它的接受者是苏艾。而此时的帮助者是医生与苏艾,反对者是琼珊。随着发送者与接受者、帮助者与反对者行动的推动,情节不断深入,当得知琼珊将自己生的希望寄托在窗外所剩无几的常春藤叶时,苏艾便发出寻求帮助的信号,接受者变成了老贝尔曼先生。此时老贝尔曼先生成为帮助者,而窗外所剩无几的常春藤叶成了反对者。最后帮助者与反对者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在此行动的作用下将小说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老贝尔曼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幅也是最后一幅杰作——最后一片常春藤叶。小说在高潮中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与回味,琼珊也因此重获新生,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关系也得到了解决。 在小说阅读教学中,适当运用“行动”层概念对小说结构进行深层挖掘,可以更清晰地将小说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的多重矛盾呈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进一步体会小说文本的魅力正是通过这些复杂交错的矛盾来实现的,它们是小说文本创作非常重要的部分。 三、“叙述”层:呈现小说故事情节的策略 如果说前面所述都是关于小说文本故事层面的探讨,那么“叙述”层便相当于小说文本话语层面的探讨。当然,对于小说话语层面的分析离不开之前故事层面的分析,它是建立在故事层面分析之上的。因为话语层面主要是从技术角度分析小说的故事情节是通过何种形式得以表现的。在叙述层面,关注最多的是小说文本是如何被叙述的,主要涉及叙述者的人称和叙述视角的问题。 叙述人称主要分析小说的叙述者是用第一人称“我”、第二人称“你”或是第三人称“他”之中的哪一个或哪两个来叙述的。叙述视角主要分析小说的叙述者是以什么观察角度来叙述整个故事情节的。热奈特在《叙述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中,将视角称为“聚焦”,并区分了三大类聚焦模式[3]:第一,“零聚焦”,即无固定观察角度的全知叙述,其特点是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第二,“内聚焦”,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第三,“外聚焦”,即仅从外部客观观察人物的言行,不透视人物的内心。通常叙述人称与叙述视角是组合在一起分析的,因此在“叙述”层中运用不同的叙述人称与叙述视角会对表现小说的故事情节产生不同的效果。 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在叙述人称上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在叙述视角上主要采用了“零聚焦”即全知的叙述视角,对于表现小说故事情节产生了如下效果: 其一,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视角更便于介绍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与背景。由于叙述者是全知的,所以在叙述上没有任何视角的限制,叙述自由,跨越时空。在小说的开篇,全知视角从一个客观而全面的角度交代了故事发生在一个独特的“艺术街区”,给读者一种犹如电影全景镜头般的效果。镜头首先对准广场西面街区的特色街道;紧接着镜头又切换到在此街区生活的人群: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怀着对艺术不懈追求的人们,对艺术的热爱使他们汇聚到这里;进而镜头又拉近至小说故事的两位人物苏艾和琼珊,简单地介绍她们的相识。同时叙述者以一种独立于小说之外的旁观者的姿态,以一种略带调侃的“语调”引入了小说至关重要的一个“不速之客”——肺炎。如果不是以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视角来介绍发生在艺术街区里严重的肺炎病毒,而是以小说中某一人物的有限视角来介绍,就不会收到小说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这种叙述方式所带来的效果。在客观中立中又带着诙谐幽默,使悲剧与喜剧在此叙述视角中完美融合,以喜衬悲,更加渲染了悲剧的气氛。 其二,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视角有利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如果小说一开始是以琼珊的视角来叙述整个事件,那么,苏艾与医生见面这个场景就不可能被叙述出来,因为以琼珊的视角,这个场景是她所不能看见和听见的一幕,然而正是以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视角,才使读者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场景,也是在这一叙述中,我们才知道此时可以挽救琼珊生命的人不是医生的治疗,而是好姐妹苏艾如何使琼珊重获生的希望。当然,当小说的叙述再次聚焦窗外的常春藤叶时,一切谜底均在全知视角的叙述下得以揭开,这样的叙述使读者与人物一起感受了出人意料的高潮与结局,使在现实中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变得如此真实而又震撼心灵。这一效果也是采用任何有限视角所无法达到的。第三人称全知的叙述视角就像是一部电影的导演,他自如地调动人物的出场,有序控制故事情节发展,从而使整个小说的情节充满悬念又值得回味。 诚然,就整篇小说叙述来看,并不完全只是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其间也穿插使用了人物的有限视角。例如当小说写到经过一晚的时间,当琼珊再次让苏艾拉开窗帘的时候,此时完全是由琼珊的视角叙述窗外的一幕:“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这种叙述视角的变换,明显突出了小说意外、惊喜、不可思议的情节效果,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悬念,从而更强烈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除了关注叙述层面中的叙述人称与叙述视角,还可以关注叙述时间。在叙事作品中,实际存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故事时间”是指所述事件发生所需的实际时间,“话语时间”是指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后者通常以文本所用篇幅或阅读所需时间来衡量。两者在时间长度上的差异,可以突出或增强所要表现的故事情节的效果。在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中,有一处明显的“省略”,即叙述时间为零,而故事时间无穷大。那便是老贝尔曼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画最后一片常春藤叶的情节。在话语时间的叙述上直接从“一天早晨”到了“第二天早晨”。省略了故事时间即以自然时间为标准的老贝尔曼先生整晚画常春藤叶的全过程。而这一“省略”便形成一种“叙述空白”,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上构成了极大的悬念,同时也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在此意义上使读者变成了第二作者。 综上所述,在小说阅读教学中,教师若能运用这样一些叙事理论,会使课堂教学不仅仅停留在对小说“故事”层面的感受上,还能在此之上有一定的提升,使学生了解那些吸引他们阅读的故事情节背后的表现手法。通过对小说文本“故事”层面到“话语”层面的分析,也使学生了解小说文本创作的相关知识,并为学生从小说文本的阅读到小说文本的创作架起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