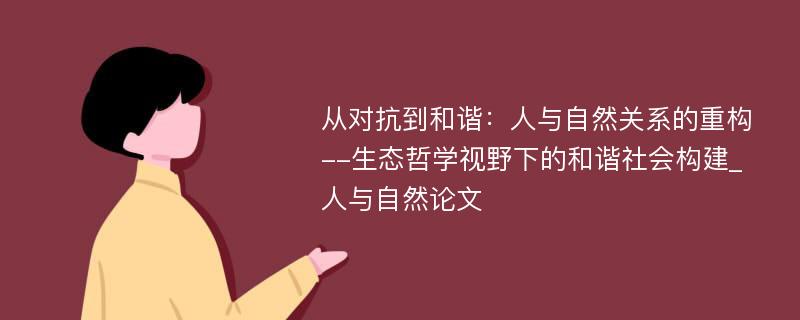
从对抗走向和谐: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从生态哲学看和谐社会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自然论文,和谐社会论文,重构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决策,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就当前面临的任务而言,关键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谐。
1 人与自然对抗及其具体表现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其中,人与自然统一的根本基础在于: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不仅来源于自然,而且其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了与自然进行物种、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只要人类还存在,不管发达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这一铁的事实,而只要还是自然的存在物,人与自然就具有天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统一性。然而,人又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还是社会的存在物,这就是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人才与动物区别开来。人与自然的对立也正是从此开始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由良性对立逐渐发展成为恶性的尖锐对抗。早在1992年,就有1670名科学家(其中110位是诺贝尔的得奖者)向全球发出警告:“人与自然正处于迎头相撞的险境”。人与自然间的这种尖锐对抗或者“迎头相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人类征服、改造甚至疯狂掠夺自然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完全可以说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史、改造史,甚至是疯狂掠夺史。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自然完全成为了人的主体性张扬的场所,成为了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工具。我们始终认为,生产力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马克思曾用“自然力的征服,机械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77页)来描述人类征服和开发自然的规模和速度。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等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人们也越来越相信“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其对抗程度也达到了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树立生态自然观,发展生态经济,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才成为当代全球共同的心声。
1.2 自然加倍报复人类
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使去了水分的积蓄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83页)不幸的是,人们对此置若罔闻,在同自然环境对抗的路上越走越远。
就中国来说,对安全最大的威胁,是哺育中华文明的两条母亲河—黄河与长江。1997年7月到9月90天的丰水期,黄河利津站到黄河入海前最后一座水文站之间竟断流72天。1997年全年,位于山东的利津站记录的黄河断流天数总共达226天。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断流。断流意味着大部分泥沙都留在了主河道里。一旦洪水来临,水道堵塞,就会发生漫滩,出现险情,这就更容易出现水小险情大的不合常规事情。在人口稠密的中下游地区,黄河历来以“中国的忧患”而闻名。它是高悬在黄河流域人民头上的一把达摩科利斯之剑。与沙漠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另一个威胁是水土流失。1981年,美国《公元2000年全球情况调查报告》的主编巴尔尼博士来华访问后,曾说:“黄河流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平均每年流沙量高达16亿t,这不再是微细血管破裂,而是主动脉出血。”他如此深刻而尖锐的告诫,不仅是对我们中华民族而且也是对全人类敲的一次有益的警钟。与黄河不同,长江洪涝闻名。长江流域面积180万km[2],年径流总量约为10000亿m[3]。流域拥有占全国36%的人口,40%的粮食,33%的棉花和47%的淡水产品,40%的GDP。长江流域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长江流域1998年出现1954年以来最严重的水患,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当然,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不仅仅表现为沙患、风患以及各种水涝干旱,还表现为源自动物的各种病毒的侵袭,生态难民也不仅仅是指那些为逃避沙化、水灾和旱灾而流落他乡的人,而且也包括因躲避瘟疫而流亡的人。由于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围海造田等原因,各种动物,尤其是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生存空间被压缩,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人与动物接触的可能性和频率,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人与动物交叉感染的可能性,提高了人与动物共享同一病源的概率。结果是,旧的病种还没有克服,如艾滋病(HIV),新的病种又接踵而来,如尼巴病毒、SARS病毒等。
1.3 人类与动植物争夺生存环境
由于人类破坏了动物的生存环境,使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食物来源也变得越来越贫乏,为了生存,动物就不得不向人类讨还生存环境,人与动物间的生存环境争夺战就这样开始了。据报道,近两年就出现了成千上万的乌鸦进驻沈阳市的现象。每当夜幕降临时,就有一群群乌鸦飞进城里,第二天早晨飞离都市。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周边林地的减少,使乌鸦失去了栖息地,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美化措施的加强,森林覆盖率的提高,又为乌鸦创造了一个理想的栖息地。然而,乌鸦的进城给沈阳市民带来的不是景观,而是一场灾难,“粪雨”固然给市民诸多麻烦,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而一些潜在的“后遗症”,如由此引起的与乌鸦有关的各种疾病,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历史上就存在过类似的先例,早在1918年,席卷全球并在不到一年时间就造成了2000万~4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有关专家认为,鸟也许是将这种病毒传染给人类的罪魁祸首。
1.4 人类与动物相互伤害
人类与自然相互对抗的结果必然是相互伤害,人与动植物对抗的结果必然是双方共同走向毁灭。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双方都是受害者,对人类来说,我们所遭受的自然灾害既包括有形的,如环境污染、水灾、旱灾、风沙等,也包括无形的,如各种疾病的侵袭,2002年登革热疫症,2003年的SARS。而人类对自然的侵害也是广泛的和深刻的,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更是突出。研究表明,由于各种化学物、各种激素滥用,一些物种发生了畸变;环境的恶化,使各类动物的生存状态日益下降。此前中国科学家对长城站所在的菲尔德斯半岛上的鸟类进行了多年的考察,结果发现,南极巨海燕总体分布量减少90%,繁殖率下降了40%。而最近,他们又发现有80%左右的贼鸥,主动放弃繁殖权利,甚至南极的企鹅也患了鸡瘟。
2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
人与自然的对抗,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必须走出当前人与自然紧张的状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2.1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
人与自然的对抗,源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将人与自然的对立绝对化和极端化的结果。人类的许多灾难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人与自然相互对抗的自然观。这种对抗既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程度不够的结果,因为这种人与自然对抗的自然观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必将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所取代。因此,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走出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环境伦理意识,既承认自然的工具价值,同时又要承认其内在的价值。这既是当今人类减少种种灾难的根本途径,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2.2 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观
要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谐,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观,积极发展生态经济,努力实现经济生态化。所谓经济生态化是指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更替中,通过建立与推广应用与环境协调的技术体系、能及时准确收集与处理有关环境与发展信息的动态监测与预测预警体系、能灵敏反映自然资源及其诸种功能变化经济后果的市场价格信号体系、能引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规范体系以及民主化、科学化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体系。简而言之,经济生态化即人类经济活动日趋符合生态规律要求,日益实现在生态上合理的过程。其本质和核心内容即:使基于劳动的经济过程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及其产物,逐步比较均衡、和谐、顺畅与平稳地融入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物质代谢之中的过程。因此,只有发展生态经济,才能彻底克服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状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重新实现天人合一。
2.3 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观
尽管非典、禽流感等继续威胁着人类,然而,食用野生动物的口腹之欲仍未杜绝。因此,倡导文明饮食文化,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观,戒掉吃野生动物的陋习,有利于自己,有利于他人和社会,有利于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同时也有利于子孙后代。
2.4 加强环境立法,增强环境执法力度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除了依靠经济手段,建立新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生态经济;建立新的可持续消费观,倡导绿色消费等等,还必须借助于法制手段,建立和健全环境法制机制,完善环境立法制度,使人与自然的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优化的统一有法可依。
2.5 加强生态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
人们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中,认识到要变革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要对工业文明中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拨乱反正,把人与自然的尖锐对抗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还必须实施和推行教育改革,发展生态教育事业,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生态化教育是和构建未来生态文明相一致的新型教育体系,它可以分为学校生态教育和公众的生态教育。对于学校而言,要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构建教育的理论、观念、价值、政策、目的、内容、方法等,并致力于解决教育过程中人类与自身、自然之间的时代性矛盾,从而致力于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质的新人。对于公众教育而言,要致力于提高公众的绿色意识和参与生态环保的自觉性,积极参与解决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之间产生的生态危机,从而推动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