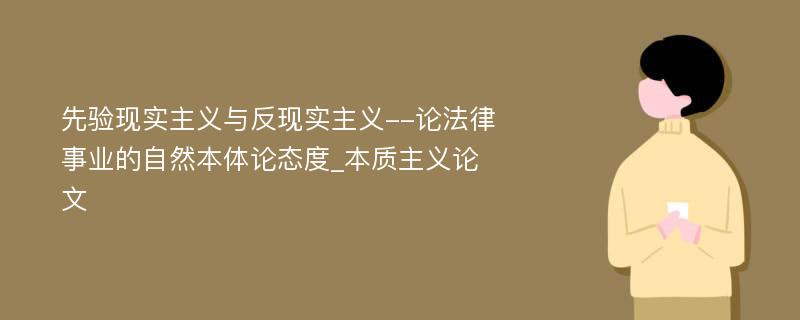
超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A.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本体论论文,态度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自然本体论态度(NOA)既批判实在论也批判反实在论,法因自称为后现代的非实在论。它主要包括:(1)世俗的真理观。(2)开放的科学观。(3)反本质主义。本文详细介绍了NOA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对法因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NOA的超越实际上是一种“消解”。法因的反本质主义因缺少辩证思维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虚无主义。
关键词 NOA 非实在论 后现代科学哲学 统一描述 建构经验论 反本质主义 反科学哲学
NOA是自然本体论态度(Natural Ontological Attitude)的缩写。对此,法因(A.Fine)曾作过几点说明:(1)为了有别于科学哲学中林林总总的“主义”,他用了“态度”①。(2)NOA发音与Noah相同,NOA的信奉者Noaer的发音与Knower相同,前者暗示NOA将会成为拯救科学的方舟,后者则企图使Noaer与“知者”之间构成某种联系。(3)NOA既不是实在论(realism)也不是反实在论(anti-realism),而是一种“后现代”的“非实在论(non-realism)”。
既然法因已作了这番说明,我们不妨顺着他的思路,先看看他如何批判“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然后再了解一下NOA到底是些什么货色。最后笔者将给出对NOA的批判,并指出,法因的“超越”企图是失败的。
一、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批判
法因曾申明,“实在论已亡”。②“亡”的根据何在?在于他对实在论三个层面的批判,其一是“总体论证策略”,其二是“极少数(smallhandfull)”问题,其三是“近似真(approximate truth)”问题。
反实在论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做真理买卖”的真理贩子们;二是以范·弗拉森为代表的“新经验论”。
所谓“真理的贩子”,是指这么一些人,他们都认可“作为可接受性的真理(truth-as-acceptance)”的真理观。这种真理理论可表述如下:“命题P的真理是指在某种条件下,某类主体会接受P”。③对主体和条件的不同设定就出现了真理贩子的三种变体:(1)如果为了方便知识的交流而假定主体是“完全理性的人”,条件也是“理想化”的,那么我们得到的是普特南(H.Putnam)“内在实在论”④。(2)如果主体不是完全理想的人,而是一些对事物抱有责任感及意向的人,再假定条件就是为达成意见统一而进行的一种重要的对话,我们得到的便是罗蒂(R.Rorty)称为“认识论行为主义”的维特根斯坦派的观点。⑤(3)假设我们的主体沉浸在某种范式的基体中,并且范式的价值和规则也涵盖接受的条件,那么我们便面对库恩的与范式相对应的真理概念。
反实在论的另一阵营是“建构经验论”。这种新经验论坚持一种科学理论的语义学观点,把科学理论视为一族模型。它对真理要求一种字面上的诠释。该理论最关键的概念是“经验的适当性”(empirical adequacy)。某理论只有在描述了可观察对象的所有真理模型后,才是经验上适当的。如果把关于可观察的事物的真理称为“现象”,那么一个理论唯其拯救了所有现象之后,才是经验上适当的。总之,建构经验论独具个性的反实在论观点有二:其一是认为科学的目的是提出经验适当的理论(而不是真理或近似真理)。其二是接受一种理论只涉及到理论在经验上是否适当这一判别标准(实在论认为接受一种理论就是相信那一理论是近似真理)。
让我们以R表示实在论(realism),以EB代表认识论行为主义(epistemological behaviorism),以CE代表建构的经验论(constructive empiricism)。不难看出三者之间有以下共同之处:
(1)R、EB与CE的真理观具有共同的形而上学。R是想得到力不能及的东西,拼命地往“客观世界”里面钻。EB则是躲到“主体间”的小天地中,也是拼命地往回缩。CE虽然反对真理观,实际上是在“主体”“客体”之间的中间地带开辟“租界”。三者都想找出一块“安全的”的、永恒的乐土,其结果都是身陷循环。
(2)R和EB都认为,提出一种真理理论,或一种“真理描述”是恰当的。我们可以承认某种真理,但无需视之为“自然类”,R和EB对真理持着本质主义的看法。
(3)反实在论的两大阵营EB和CE,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看作一种罪恶,为了避免这种罪恶,他们又走向另一种形而上学。“真理贩子们”一旦转向行为主义就让自己和实在论者一道跳起了形而上学的“双人舞”。CE也回避科学自己的话语,走进自己的法庭,在那儿宣布,科学在此处可信,在彼处不复如此等等。CE所做的是拆认识论的东墙去补形而上学的西墙。
(4)R、EB和CE都企图对科学进行整体的、统一的、本质的描述。他们把自己的“主题”硬塞进科学之中,不尊重科学,不信任科学、不耐心地去倾听科学自己的话语。
打个比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把科学看成是一场宏大的演出,一出大戏、一台巨型歌剧。这台大戏的进行需要指挥和演奏,他们之间则在为谁“演奏”得最好而争论不休。法因提醒人们:“如果科学是一场演出,它也是一场观众与演员的‘联袂’。甚至表演的说明书也是节目之一。如果对这个那个的意义或目的抱着疑问,怀着猜测,那么这些猜测和疑问在表演中同样占一席位置。而且,剧本永远不会完善,任何过去的对白都不能决定以后的演出。演出决不会在整体上受某种见解和阐释的制约,它随自己的发展将产生与自己相适应的局部解释”⑥。
鉴于这种开放的科学观,人们采纳的态度就既非实在论,亦非反实在论,而只能是非实在论的NOA。
二、NOA(自然本体论态度)
NOA作为一种“非实在论”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纲领,在真理问题上着墨最多。除此之外,它还对科学和科学哲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据笔者归纳,NOA可以列出四个要点:(1)世俗真理观。(2)开放科学观;(3)反本质主义;(4)自身可错。
(1)世俗真理观
a、NOA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某个信念为真,这意味着调节某人的实际的和理论的行为去适应这些真理。在真理集中,有些对我们的生活是决定性的,有些则不那么要紧。如果我弄错了我在哪儿,这可能比我对粲夸克的错误信念更会影响我的生活。与这种世俗的、简朴的思路一致,某些科学信念比另一些来得重要。甚至某些日常生活信念比科学更为关键。当从简朴的理由出发应接受某些科学结论时,我们就可信以为真。我们可以按重要性(centrality)和可信度对待真理。
b、必须对科学真理和日常生活真理一视同仁。同接受生活中被充分支持的主张一样去接受科学中被确证的结论。这并不是说,一个派别不能区别出科学和生活中确证度较弱的主张,也不是说不能划分出特定的推理模式,它强调的是保持科学和生活真理的平等。这种平等有双重含义,其一是对科学和生活采取同样态度,科学并不是知识的典范和知识的唯一源泉。其二,像对待身边的时好时坏,时轻时重的信念一样去对待科学。
c、自然地对待“真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把科学真理置于“核心地位”,然后附加上他们各自互不相同的内容。反实在论所加的是对真理概念的特殊的分析,或者一些方法论的苛刻的限制。实在论附加的就是拍桌跺脚地大喊一声“真的!”真的存在着某种粒子!真的存在客观世界。NOA既不把“科学真理”置于特殊地位,也不加上任何内容,让科学去作出判断。
d、真理是不可通约的。“一个语句为真,仅当被指称的实体存在于指称关系之中”。⑦NOA承认普通的指称语义学,承认由科学理论所指称的真理、特性和关系的实在性。对这种实在的信任与对科学其它部分的信任一样,有强有弱。可信度(drgee of belife)将由确证和证据支持(附属于通常的科学规范)的原始关系来限定。Noaer作为一个科学家工作在传统的语境中,在此时他会相信理论所指称的实体的存在。一旦传统变化,他就会在延续时不复相信那一实体。NOA和库恩一样持理论或传统之间“不可通约”的观点。NOA不认为科学的变化是作为进步的“同化”,即通过变化,我们对同一事物的了解会更加准确,NOA认为变化是整个范围的指称关系的变化。“事实上,‘不可通约的’是真实的,而指称的恒定性是不能成立的,NOA认可指称和存在陈述,但它不把科学史限定在特定的模式中。”⑧
法因还补充说:“现在的知识不仅对过去的判断重新分布真值,而且现在的知识也要求重新评估过去活动的整个性质;无法预料它将来的情况,因而无法对真理的意义作即时性的特征描述”。⑨
e、NOA拒斥关于真理的所有阐释性理论。真理概念是语义学的基本概念,它用的历史、逻辑和语法,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充分确定的,能局部地按目录分类,但无法给出对它的“说明”或“解释”,除非陷入循环。并且它也不需要诸如此类的说明。真理的概念不会终止,它要随科学一道发展。特别的问题(它真吗?有什么理由相信它是真的?我们是否能弄清楚它是真的?等等)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加以论述。上述诸问题的答案的重要意义根植于真理判断的实践与逻辑之中。
f、外部世界。法因认为:“实在论者,站在竞技外面看着游戏的进行。然后以外在的观点来判断。这是自欺欺人。他不能位于竞技场外,也不能通过审视游戏场之外的区域而指出什么是游戏”。⑩NOA的态度是,对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比如电动力学,除了承认它是关于电子的理论外,我们找不到其它东西来判断电子理论谈论的是什么。这有别于看图造屋或按图索骥,我们自己身在世界之中,精神和物质二方面都沉浸其中。我们存在于科学研究对象之中,我们用以判断的概念和程序自身就是科学世界的一部分。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是“在(科学)世中(being-in-the-world-of-science)”。
(2)开放的科学观。所谓“开放”,就是对科学充分信任。NOA对科学的“检核、复核、再复核”的研究程序充分信任。不仅如此,NOA也相信建构科学体系的种种防卫系统。因此,“如果科学家告诉我,真正地存在着分子、原子及ψ/J粒子,甚至夸克,它们就存在着。我信任他们,因而必须承认果真存在着这类事物,以及伴随的特征和关系”[11]在这一意义上,noaer是一个十足的实在论者。
NOA主张努力按科学自身的主张去对待科学,不试图把某些主题硬塞进科学中。对科学的总体性说明,科学哲学的形形色色的“主义”,都是科学的空洞的外壳,它们没必要、无根据、甚至是无法理喻的。科学有自己的历史,并深深根植于日常思维之中。
法因认为,NOA最大的优点是提醒人们,一个充分的科学哲学可以弱到什么程度。在这方面,NOA可以比做艺术中的抽象主义运动(minimalist mevement)。NOA认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所塞进科学的东西已包含在被看成与科学真理等同的日常真理之中,包含在我们接受二者皆为真理的态度之中了。没有什么其它附加物是合法的、是必要的。
在这种意义上,NOA是一种反科学哲学(Anti-Philosohy-of-Science)。它努力让科学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不必依赖形而上学的助听器就能获得我们所需的信息。
(3)反本质主义。法因说:“对NOA感性认识的最快捷的途径是把它理解成对解释观念以及相关的永恒观念的唾弃。”[12]换言之,NOA最鲜明的特点是拒斥整体说明的形而上学渴望和反本质主义。法因认为“NOA的反本质主义是内容极其广泛的观点,它可适用于科学中所有概念,甚至包括真理概念”[13]。
整个科学的发展无需齐一性。科学的历史与现状组成了一幅内容丰富和意义深远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目标或目的或意图问题的出现是自然而然和局部的:使用某一特别的工具是为了什么目的?这里为什么要用钨丝而不用铜丝呢?建造产生超过10[4]Gev能级的加速器为达到什么目的?在分析康普顿散射时为什么可以不考虑引力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有一种目的论倾向,很可能只有目的、目标这类术语才能给予确切的回答。不过当有人问我们什么是科学本身的目标时,我们就深感困窘,就像有人问我们何为生命的目标一样。NOA认为对这些问题不需要给出统一的答案,相反它们需要一种有效的分析以便使人们了解问题的根源和情境。
(4)NOA是自身可错的,是不完备的。法因承认:“虽然NOA可能使科学变得非常可理解和合理,但NOA可能是错误的。”[14]NOA将保持不断的修正和开放。
整体上说,法因从未放弃为NOA唱赞歌的机会。他曾这样来评论自己的纲领:在爱因斯坦眼里莫扎特的音乐显得是如此自然,以致相形之下,其它作曲家的曲子听上去都有些扭捏作态,矫揉做作。那些“做作”的作曲家就是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而浑如天籁的莫扎特的音乐无疑就是NOA了。“NOA就像加里福尼亚的风光一样自然”。[15]
三、结语:对NOA的批判
由于NOA采取“消解”科学哲学的态度,由于对科学的“拯救”和“信任”。这一纲领被认为是“后现代”代表之一。被法因批判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对NOA作出了响应,同时,NOA也得到了后现代同志罗蒂(R.Rorty)与罗丝(J.Rouse)的激赏。正如法因的批判一样,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的辩解与反驳是十分精彩的,笔者不仅同意而且折服。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几点自己的见解。
(1)法因对“溯因法”的看法是过于苛刻的。实在论者波依德(Boyd)认为,法因对“溯因法”的攻击是一把“双刃剑”[16]。该剑一面欲刺实在论,另一面就必损“经验论的反实在论”。为什么在回击时要拉出建构经验论?法因刺在何处?这里大概可归纳出四层意思:第一,法因对人类的知识探索限制太多。“如果扔掉溯因法,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哲学、历史及其他)恐怕手头就没有什么方法可用了”。[17]第二,溯因和归纳,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不可观察的”对象,后者面对的是“可观察的”。波依德详尽的分析说明,如果前者不合法,后者也强不了哪里去。而一旦连归纳也该扔掉,法因估计连学问都做不下去。第三,波依德说,不能逻辑地、抽象地、孤立地去谈论溯因法,而应走自然主义的道路,即从人类知识探索的背景中“相对地”去评价。第四,波依德的辩护策略很朴素,因而也更为可取。好比挨克的小学生,总是狡辩说别人也做了此事云云。似乎“错”是分子,做的人数是分母。如果分母足够大,“错”就会近等于无,甚而转变为“德性”。实际上,“量”一直是“对”与“错”之间评定和转换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如果不坚持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评价”观是十分明智的,十分人道的。再者,法因搬出希尔伯特也无道理。既然哥德尔已证明了希氏的“理想”不可行,为何还“对”呢?“不可行的”东西“对”在何处?为什么?法因未置一词,这里显出他的独断来了。
(2)比法因更激进的罗蒂还从反面看出了问题:“法因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们已经知道了科学独有一种叫做‘溯因’的方法”。[18]罗蒂不认为科学具有什么独特的方法,任何方法一旦发现或形成,其他文化领域都会借用,科学无特别的方法。除此之外,罗蒂把法因视为后现代同路人。他尤其赞赏法因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超越态度。他曾表示“他的目标与法因相同”[19]。并且认为,戴维森(Davision)也是一位超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哲学家。他说:“就我的理解,戴维森的观点与NOA高度吻合”。[20]
(3)关于“近似真”批判也大有问题。法因简单地把近似真理T与T′之间的关系视为合取。其实,T与T′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可以是相互补充,可以相互印证,也可以是相互抵消。总之,其间发生的远非逻辑的合取。如果依照法因的观点,近似真的“历史事实”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叠加,岂不变得等于谎言了。法因人为地设定对手,然后施以批判,这无疑在打自己扎成的稻草人。
(4)在批判反实在论时,法因所依据的两件法宝:其一指出对手有循环论证;其二说理论与史实不符。这正是所谓“历史一逻辑”的方法。细究之下,不难看出,二者都不如想象的那么牢靠。“语境实在论(contextual realism)”提出者施拉格尔(Schlagel)指责法因在运用史料时,主观取舍甚多。[21]不过从施氏对法因的反驳看来,他同样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以及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官司打到原始材料这个层次,就只能悬着。因为恐怕谁也不敢担保他掌握了最“客观”,最“真实”的材料。或许爱因斯坦某日发表了一通有实在论倾向的言论,又在某日表示了一通相反的见解。我们只需反躬自问就发觉这种反复应属正常。再者书写爱因斯坦传记或玻尔研究所历史的作家,肯定是存在着某些想法、某种信条的,这就是“理论渗透”。问题在于,像法因这类对“客观”、“实在”视之如粪土的哲学家,不应该显出对“历史真实”的特别“信任”,否则就会让人抓住口实,即当你对“历史”如此信赖时,难道不允许别人对“实在”也去相信吗?“历史真实”背后难道不是也是一种“实在”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循环”。自亚里士多德为逻辑设立了几条“规则”以来,循环论证一直是学者们的泥淖。但人们又发现,稍有“深度”的证论都会出现循环。法因指责实在论、反实在论都有循环论证,而他自己的NOA同样不可避免。既然如此,我们似乎应重新认识循环了。按照丸山(Magoroh Marugama)的看法,系统科学诞生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互为因果(循环)的认识论是对亚氏逻辑的革命。复杂系统都具有不同层次的循环网,对这种互为因果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看待世界。同时,互为因果的形式化的表述也可丰富我们具有的朴素的辩证法。由此可见,法因的两大法宝,都是经不住推敲的。除此之外,他对认识论行为主义三种“变体”的划分也是武断的。拉什奇克(E.Lashyk)指出,法因把库恩的主张归入真理的可接受性理论体系是欠妥的,因为在库恩的著作中,真理概念并没有正面意义。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只三处有了“真”和“假”这种术语,而且还是在拒斥它们的意义上提及的。法因又一次扎起了稻草人。
(5)法因在总结R、CE和EB时,指出三者共同的企图是对科学进行“统一的说明(unified story)”。揭示出“科学的本质”。罗丝认为,科学哲学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就在于是否赞同“统一描述”。他说“NOA在把信任和怀疑作如下的结合时是后现代的:既信任局部的科学实践又怀疑对科学作任何整体描述的合法性”。[22]法因的“信任”和“怀疑”能和谐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信任”。
当法因说“信任”科学,而又说科学是不可定义的,是不能作出统一描述或者是与日常生活的信念浑然不分时,人们要问,“信任”的对象是什么?法因曾说:“对磁单极……将产生从彻底的不可知到强烈的信念诸种态度。NOA乐意它们中的任何一种。NOA所坚持的一切就是,人们对待磁单极的本体论态度,以及能在科学领域内聚集在一起的所有其它因素(不管是否可观察),都受与科学自身所运用的完全相同的论据与归纳标准的制约。NOA能容忍所有各不相同的观点,以及所有各种科学所能容忍的怀疑和怀疑论”。[23]对这番话,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质疑:a、NOA将“信任”从正极到负极一个区间内所有理论,但如果T[,1]和T[,2]是相矛盾时,NOA也不作出选择,都加以“信任”。这种“和事佬”意义的“信任”,要么是虚伪的,要么是不可能的。b、既然NOA对一切理论都是“信任”,它为什么不可以信任“实在论”与“反实在论”?c、当法因说,如果科学家告诉他存在某种粒子时,他完全信任。但在此之前,他必须断定此人是科学家。如果一个巫师以科学家自居而向法因兜售某种伪科学理论时,他也会“信任”么?“信任”细节也好,“信任”历史随机性也好,总该有一个整体的对象。
这便过渡到“怀疑”。
法因曾说,NOA最根本的主张是“反本质主义”。基于此,他才“怀疑”各种对科学主题化的企图。所谓“统一描述”,即认为科学有一个本质,该本质或是“政治学”,或是“社会建构”,或是“认识论”,或是其他什么。笔者完全赞同法因的这种态度,问题出在我们对“本质”怎么看?按照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认识论,“本质”是齐一性,是同质之质,是“事物的决定性因素”。NOA的反本质主义认为,科学无统一目标,无统一方法,无统一的形而上学,有的是形形色色的,有“语境”的,局部的目标和方法。这就是科学的“本来面目”及“终极状态”。难道科学就是一堆“异质的”残片吗?科学能不能形成整体性呢?科学有没有独特形态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异质”的局部可以形成“共生态”和“新的模式”,它不具有解析的,同一的“质”,但它具有整合性和内在运作机制。这是一种相互作用因而不断发展的质。拒斥“互为因果”就不会把科学看成一个系统,而只是一堆互不联系的碎片。由此可见,法因没有根本上解决“信任”和“怀疑”的冲突。这是因为他虽然在表层上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不同,深层却遵守相同的基本预设。
法因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批判有许多精妙之处,但总的说来“超越”是不成功的。首先,正如拉什奇克指出的那样,即使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批判有些地方是合理的,也不能从前提中推出NOA,因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在发展,都将提出新的见解。其次,像其他后现代哲学家一样,法因所要“超越”的实际上是要“消解”的东西,即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某种形而上学的建构。最后,最关键的是,法因的反本质主义因缺少辩证思维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虚无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超越,而不是消极的“信任”。
标签: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本体论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认识论论文; 科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