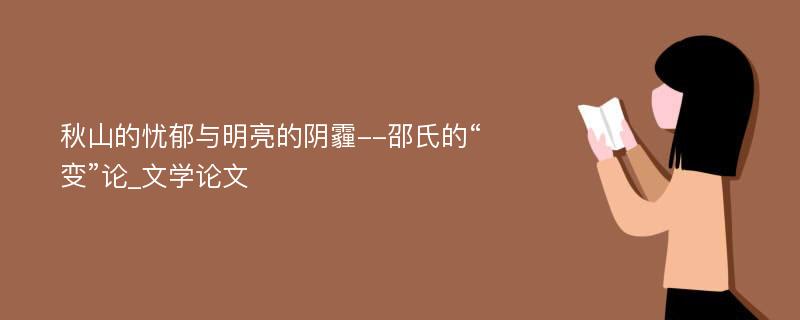
秋山方郁郁 璀璨起烟霞——邵诗说“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烟霞论文,璀璨论文,秋山论文,邵诗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邵燕祥归入“归来者”或“复出”的诗人群。在1980—1985年的六年间,邵燕祥一手写诗,一手为文(杂文),成为那段时期最活跃的中年诗人之一。其诗人之名,常常与公刘、白桦、流沙河、胡昭、孙静轩、昌耀等有着共同成长经历和政治遭遇的诗人列在一起,而其杂文家之名,更已为人熟知。单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杂文《论不宜巴望“好皇帝”》和《人是有尾巴的吗?》似乎已超过了诗作《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与《愤怒的蟋蟀》。不过,在这六年间,邵燕祥出版的诗集是八种,杂文集却还尚未问世,从创作数量上看他主要还是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归来者诗人”。
可是随后,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在1986—1996年的十年间,邵燕祥却出版了十九种杂文随笔集,而只有四种诗集。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作为诗人的邵燕祥已然渐渐淡出,作为杂文家和思想者的邵燕祥方才步入炉火纯青之境。以至于在将近二十年之后,王伟明对诗人进行访谈时,提出了因访美而“弃诗就文”的疑问。
即使是在1997—2006年的又一个十余年间,就出版的著作说,邵燕样的28种回忆录与杂文随笔集更是远远多于两种诗集(香港版的《短诗选》和大陆版的《打油诗》)。如果说“变”,不知这算不算创作文体与数量比例方面的“变”?
另一方面,也还存在一种说法,就是王伟明在访谈时间到过、诗人本人也数次提到过的“杂文比新诗好”以及“旧体诗比杂文好”。无法核实说这些话的人提到的“新诗”是作者哪一阶段的作品,也不知道说这些话的具体背景。而在诗人,却有着属于自己的苦衷和辩解:“我以为,在我的写作生涯里,首先是自由诗,写了大半辈子,虽有很多败笔,其中毕竟有我的梦、我的哀乐、我心中的火和灰……”(《自序》,《邵燕祥诗抄·打油诗》)
那么,如何看待诗人邵燕祥在1986年以后诗集出版远不如文集出版的数量这一现象?又如何理解所谓“杂文比新诗好”的评价以及诗人自己的辩解呢?
不错,在1986年之后,邵燕祥在言论、思想方面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诗人身份,写作的重点也的确已不在诗歌方面。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正如诗人回答王伟明提问时所说:“那段日子没有弃诗就文(以后也从未弃诗就文)”,在临近1990年代以至此后的二十年(1988—2006)里,其对现代诗的写作反而呈现出令人惊讶的自觉状态。只不过除了《也有快乐也有忧愁》和《邵燕祥诗选》,绝大多数新作没有单独结集出版而已。如果说,在言论、思想方面的自觉大幅度提升了邵燕祥杂文思想力度的话,那么这种自觉同样对其诗歌写作产生了重大推动力,可以说,从早期单纯、热情的“政治抒情诗人”,此时的邵燕祥已经因年龄、思想、艺术等诸种因素的影响而成为一个沉思型的思想者诗人。一个诗人的成就显然不能仅仅从诗集数量的多少加以评定。
至于“杂文比新诗好”,也还有需要推敲的地方。一是所谓“好”,其含义是什么?是思想性更强因而社会影响力大还是艺术上更具功力?二是这里所说的“新诗”是邵燕祥所有的新诗作品还是某一阶段(比如50年代至60年代或者70年代至80年代)的新诗作品?这里不去推测其具体所指,且说个人对邵诗在近二十年间思想、风格、艺术表现诸侧面嬗变的点滴印象。
还在1980年代之初,邵燕祥回忆过自己作为新中国建设者和青年诗人对当时所谓“政治抒情诗”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个人经验,由人民日报文艺组的来信使他“比较明确了‘政治抒情诗’这个概念,力求从政治的高度来处理工业建设之类的题材了”。此后,尽管这种全心全意的忠诚并不被理解,甚至反复遭到质疑和诘问,其从事写作的“政治的高度”还是保持到诗人“归来”后的1980年代。因为在“归来”之初,虽已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依次出现,而“伤痕”还只是与“时代”同步、对政治创伤浅层次的个人倾诉,“反思”也不过是站在主流政治的角度以今日之“是”反思昨日之“非”而已,离“五四”文学的宗旨尚远,更遑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启蒙主义或理性式反思。因此,对1970年代末直至1980年代初邵燕祥类似于“伤痕”、“反思”式的抒情诗,我以为仍然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政治抒情诗”的延伸。
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启蒙主义或理性式反思,客观上固然需要形成滋养启蒙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文化环境,但更需要的是主体个人的启蒙与自觉。以这个标准检验当代诗人甚至所有从事文学写作的当代文学家,不管他是工农兵文学家还是知识分子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人能够经得起检验。
大多数人只能做到在外在文化环境的推动下逐步由蒙昧状态开始自我启蒙,在“归来者”当中,穆旦、蔡其矫可能是最早摆脱政治迷信的诗人,而在1980年代,整个文学、文化界开始大声疾呼“人道主义”、“文学现代化”、“主体性”的气氛中,邵燕祥从先驱和后进那里获取精神资源,逐渐成为在“思想解放”(姑且借用那时的流行语)方面走得最远而又义无反顾的一个。不过他所使用的不是“思想自由”或“启蒙主义”这些术语,而是以“良知”或“良心”透视社会历史特别是当代社会。而且,这种“思想解放”也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逐步深化、由情感体验渐趋理性思考的。
“良心”、“良知”,现代版《辞海》均以《孟子》为典范例句,并说明前者谓“本然之善心、仁义之心”,后者“指天赋的道德观念”(所谓“不虑而知者”)。可知属于儒家学派的道德术语。而在今天,一般说都不是特指,比如“良心”乃指“存在于内心的是非、善恶之认识”,却仍然属于道德范畴。至于这道德所含的具体的是非标准,是否与“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一致,则应到邵燕祥的诗中去寻找答案。
1979年12月9日的诗《地平线》已经出现了“人”的形象:“每一个普通人/都要像人那样生活。”1980年2月写的《谜语》标举出了“良心”两个大字;1982年的《长城》提出了“天地间/只是一个问题:/作人/还是作奴隶?”1986年元旦写的《拟哈姆莱特》又一次提出了“是人?是畜类?/这还是一个问题”的问题。这种种宣告与提问,就如年轻一代的北岛所要求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固然是另一种意义上“时代的最强音”,但从艺术的角度着眼,却显得浅显、浮泛,“人”只是一个影子,没有血,也没有肉,而且缺少具体的历史背景,感觉不到切入“当代生活”的灼痛感。反而不如1956年的《贾桂香》那样真切,尽管那个“呐喊”还属于生命本能而非自觉的反应。
在1994年“百花”版的《邵燕祥诗选》中,我以为压卷之作《最后的独白》是以人道主义的“良知”为典范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这是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袖的一首诗,独白者是与这位领袖共同生活了十几年而终于郁郁寡欢开枪自杀的年仅31岁的妻子。作者称其为“剧诗片断”,令我揣想,若是写出全剧,该是多么宏伟的史诗!且说这个“片断”,有九段是主人公的“独白”,最后一段是“诗人的话”,似乎只是轻描淡写地提示:“一个不期望历史理解的/三十一岁的俄罗斯女人的魂灵/在人海里发现了寻找她的眼睛。”实则暗示了时间(历史法则)对暴力和专制必然的审判。在主人公的九段“独白”中,透过柔弱、孤独但却选择了独立的倾诉者对那位“克里姆林宫里的疯子”最后的告别词,“我憎恨你/像你憎恨世界”,女性的尊严和暴君的冷酷渲染出的戏剧般的紧张感扣人心弦。奇特的是,除了少数直白式的宣告(“也许能忍受没有爱情的家庭,但不能做不受尊重的人”“我走我自己的路”),这首诗主要由女性化的、柔韧细腻的心理性语言构成,力量饱满而又有节制,反而更能触动阅读者的心弦。
表面上看,《最后的独白》是一出“家庭剧”,其所涉及的却是当代社会历史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制度自身的问题与领袖人物个人的政治作风、个性特征与道德品质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社会政治制度及其领袖人物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之大,不得不使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相似的历史教训,更促使人们深思制度本身与领袖品质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最后的独白》以诗的方式,从家庭或女性的视角进入这一问题,让读者看到一个政治上的“疯子”在家庭当中又是如何地粗暴、冷酷,究竟是这种个人品质影响了其政治决策还是政治制度的缺陷强化了个人品质?
那么,这种问题仅仅是当代政治才会遇到的吗?似乎正是为了回答这个提问,邵燕祥在写出《最后的独白》将近十年之后,又写了《金谷园》。巧合的是,该诗也是一个政治和道德题材的诗,其主人公也是一位与政治人物有特殊关系的女性“绿珠”,不同的是,悲剧主人公绿珠是距今一千六百多年的东方女子,不为“自尊”而是为“野蛮”殉葬、“生逢乱世的一个出身寒门的弱女”。绿珠坠楼殉节,或许不失为一个具有东方传统道德内涵的美丽故事,然以理性的、人道主义的道德观视之,则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生命悲剧,它映射出的也只是男权文化以及与其互为表里的专制文化对女性尊严的践踏与剥夺。只是,诗人似乎不希望绿珠仅仅作为殉葬品而死去,他试图赋予绿珠以某种对自我、对生命的自觉:
听项羽唱到“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知道到了必死的时刻
一下认清了西楚霸王这个英雄
你也从“奈何奈何”认清了石崇
人生短暂而痛苦殊多
做富贵者的玩物,算什么人生
与其再沦于缇骑,不如撒手
告别曾经做过的那些好梦
在那样的时代,绿珠这样一个出身寒门的弱女,能否像20世纪的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以死亡捍卫女性的自尊,是令人怀疑的。但诗的重心似乎并不在这里,而是对逼使绿珠做出殉葬选择的那种野蛮文化的道德性反思。一方面是:“一颗闪现又委弃在荒烟蔓草的明珠/诉说千百万被蹂躏的草根的无辜”,另一方面则是:“活着,不得不为主人取悦客人/死了,谁说是情愿以身命相殉?/我要问历史:是自杀还是他杀/历史告诉我:夺色谋财又害命。”还有,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表达了对艺术的期待:
但,经过了八王之乱以至奥斯维辛之后
世间仍有诗,诗比野蛮更长久
不妨把1956年的《贾桂香》和这两首长诗并置在一起考察,同与不同,变与不变,也许会显得更为清晰。诗人笔下的三个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尽管有着“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距离,而命运却惊人地相似,这固然值得深思,而更值得思考的也许还是诗人在写作这三首诗时的观念性或日思想性动力。
在1950年代,邵燕祥接受的文学观念,要求诗人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实则是从文学工具论出发去从事写作,但另一方面的诗教却又告诉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还有一点,也许是诗人自己并未意识到的,即作为一个具有潜在自觉性的“人”的天然的道德力量的支撑,才使写出了《贾桂香》那种从“人”的立场出发的诗作。
故而,当邵燕祥以白居易和别林斯基的理论为《贾桂香》辩护反而被“嗤之以鼻”的时候,诗人“陷入深深的困惑”实在是自然不过了。革命的理想是美丽的,革命的实践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复杂。鲁迅早就说过:革命是教人活而并非教人死的。然而一旦涉及具体的人,无论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贾桂香》有发自生命深处的激情的呼吁,但缺少的是透彻的、坚韧的思想的力量,而几十年后的《最后的独白》与《金谷园》,已经是革命者和人道主义者的作者在道德自觉和理性建立之后的思想性产物。相比之下,后两首诗的厚重、辩证显而易见。
思想本身并不就是诗,然而如果没有对人和历史的深度思考作支撑,诗的灵魂似乎也就无所依托。
最近阅读一部关于当代启蒙文学的著作,其所引述的康德一段话不妨照抄在这里作为理解邵诗的参照:“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的内心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4页)内心道德律的要求使人性最终抵达启蒙人格的完成,故作者接着申说:“人性启蒙的过程于是成为自由与自律相统一,理性与信仰相统一,欲望与意志相统一的过程。完成了这一过程,人就不复是单纯由欲望决定的人,即‘欲望的人’,不复是单纯由情感决定的‘情感的人’,也不复是单纯由理性决定的‘理性的人’或‘单面的人’,而是真正成为启蒙了的、道德的和自由的人。”(张光芒《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
这当然是极高的精神境界,但毕竟是属于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只要一个人不甘于被蒙蔽,还有着对自由的追求,则其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总会突破种种内心的欲望和外界的压力而助推整个人格的启蒙与自觉。这大概也就是“知识分子改造政策”“虽然有效、然而有限’并最终失败的原因。不错,时至今日,仍然有大量的所谓“知识分子”道貌岸然地捍卫着令他们丧失良知与判断力的东西,但这种现象,除了暴露出其蒙昧和膨胀的私欲而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欲望与无知压倒了道德意识,人格的启蒙也就谈不上了。
再说邵诗之“变”。我以为,1950—1980年代,邵燕祥的“政治抒情诗”其实并不仅仅是政治责任的产物,也是作为诗人的内在真诚的产物,因而至今读来,也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某种真实感,《贾桂香》是如此,《地球对着火星说》也是如此。问题只在于,这种“真诚”还只是单纯的信仰、情感而不是上述“自由与自律相统一,理性与信仰相统一,欲望与意志相统一的过程”。到了1980年代后期,或者从《我的乐观主义》、《关于犹大》甚至《也有快乐也有忧愁》这部诗集开始,那种单纯的热情渐渐退去了,随之出现的是对世界、对生活丰富性、复杂性的体认。《最后的独白》、《金谷园》写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女性的柔弱与自尊,而柔弱与自尊的背后则是共同的“野蛮”,“野蛮”不应当是人的本质。然而在人类的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中,“野蛮”却又如影随形地影响着这些活动。这就是社会生活“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和难度,更是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困难。对这一切,前苏联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切身的体验,如果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苦难”之后最终以人格的启蒙获得理性,从而找到超越、摆脱这种困境的路径,或许就是对人类文明极其有意义的贡献。我愿意将邵燕祥的杂文和诗看做是对此一路径的个人性的探索。
也只有在获得这样一种思想力量和人格力量之后,才能谈得上诗的升华,由此获得的风格的成熟和诗艺的提高才具有了意义。不错,与《贾桂香》比较,《最后的独白》、《金谷园》以及不少的抒情短章,在整体抒情风格上,在细微的诗艺构成上,也都有了容易感知到的新的语调、新的色彩、新的成分。当我说到“新”的时候,多少有点犹豫,因为“新”的含义在这里并不确定,以之描述邵诗之“变”是否准确尚需斟酌。因为这“新”是相对于“政治抒情诗”时期的邵诗而言,对于整个新诗传统,这种“变”毋宁说是“旧”的,或者说是一种奇异的“回归”。譬如说诗体,较之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最后的独白》所用的戏剧独白形式与《金谷园》所用的十四行形式是最传统的;譬如说语调,较之早期激情的直白式的“前进”,1990年代以后《五十弦》、《母语写作》那种对“失败人生”的沉思和絮语,更像是无奈的“退却”。自然,有些因素是无所谓新旧的,譬如修辞和整体风格方面的“变”,诗章内的跳跃、空白增多了,诘问和辩难增强了诗思的张力,沉郁和澹定融汇为秋日黄昏般的苍茫诗境。诗人似乎说过:“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作为诗的读者,我是那种情感型,而不是理智型的。”(《读任洪渊》)然就其近年的诗作来说,仅仅以“情感型”视之似已失之简略。特别是2000年以后冠之以“母语写作”的数十首抒情短诗,虽仍不失“抒情”的本分,然这种“情”的根柢却基于对社会历史、对生命、对自我的理性沉思。人渐沉着诗渐老,如果“老”并非一定意味着进化论意义上的“落后”乃至“无意义”,而是生命与艺术境界的臻于自由,则我愿意用这个字表达对邵诗之“变”的理解。
“老”,是完成但不是终结,是生命最高的和谐与一致。
我不否认对这些诗句的喜爱:
战后三十年,陈尸现场/只为了证明真诚之为虚妄/一个游荡的灵魂隐入书里/找来找去,找不到失踪的自己
归来啊灵魂,走向末日的审判/曾经交给了上帝还是撒旦/沧海横流,日月穿梭一瞬/愚蠢的单恋,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早慧的诗人,不结果的谎花/谁能告诉我,自杀还是他杀/做破了的梦,再不能忍受强奸/未来:能不能把梦做得好一点
矛盾。悖论。自我的冲突与纷争。一个真实的生命感受到的紧张与无奈。但最后的转折:“惟一的安慰把心撕裂/手上没沾过别人的鲜血”,却没有把这种紧张保持下去,反而重新归于平衡,顿然使诗情的浓度和诗章的结构出现了松动之感。这固然不只是诗艺问题,只是这现象究竟算不算一个“问题”,却还需要细细推敲。
逐日青春路,
苍茫看菊花;
秋山方郁郁,
璀璨起烟霞。
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美丽黄昏。
标签:文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邵燕祥论文; 绿珠论文; 诗歌论文; 杂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