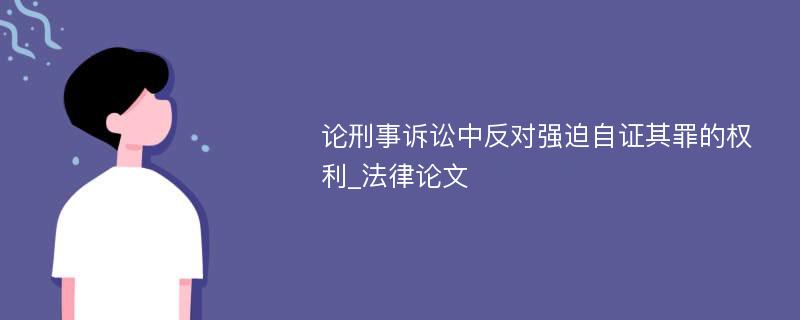
论刑事诉讼中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事诉讼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 Privilege Against Self —incriminalion )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衍生而来的当代刑事诉讼中一项最为重要的权利法则。其观念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老的一句格言“人民不自我控告”(nemo tenetor prodereor accuareseipsum)。16 世纪,英国宗教法庭(ecclesiastical courts)在审理异端案件时, 这一古老的法则最先作为辩护理由用于对抗宗教法庭,不人道的审讯方法。从此,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逐步确立了其基本形态并为近代刑事诉讼所采纳。特别是美国将其进行移植之后,此项制度得到了极大发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将其上升为宪法原则,明文规定“在任何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将其作为公民一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制止司法机关采取违反宪法此项权利的手段取得有罪供述,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业已或正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刑事诉讼构造中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制度。
一、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特征分析
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是一定范围内刑事诉讼参加人拥有不得被强迫提供自陷于罪的证据的权利。其因被使用暴力、强制或其他非法手段而进行的陈述、坦白或承认,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则有权拒绝提供自己所知道的事实或证言,由此作出的有关案件事实的言论,亦不能用来作为证据。《布莱克法律大词典》将此项权利解释为:“反对被迫自证有罪之权利源于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以及其州宪法。 该权利要求政府在查证罪案时,不能将被告人提供的反对自身的证言来针对被告人。然而其仅仅保护言词证据,而不保护诸如指纹、笔迹之类的实物证据。因此在审判过程中抑或是陪审团听证和调查过程中,使被告人违背自愿原则而被迫作出的证据均归于无效。但是当被告人自愿改变态度后,其权利是可以放弃的。”(注:参见"Back'sLawDictioary withPronunciation" (Fifth Edition)P.1078.)就理论本身进行分析, 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它的主体具有限定性。纵观各国法律与判例,其权利主体主要包括两类:(1)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指控人)。 此类主体从初次被关押起就享有了此项权利。在英美法系中,如果没有刑事诉讼或没有被告人,只是大陪审团调查或立法、行政机关的调查,被调查人不享有此项特权,这一点与证人作为主体的权利内容是不同的;(2)证人。 此类主体享有权利的外延较广泛,不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大陪审团调查等诉讼程序,而且适用于立法、行政机关等一切广泛的听证、调查和询问程序中被召唤作证的人。此外,这种权利是针对自然人设定的,法人或非法人团体、组织没有资格使用反对自证有罪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团体、组织中的个体工作人员,只要被要求提供的证据是其组织的资料,尽管其有信守秘密的义务或者可能导致自我归罪,也不得以此权利作为辩护理由,因为这些记录并非是显示其个体人格的资料。
2.它是一项非常人格化的刑事诉讼权利。 这与英国刑事诉讼中的Crown Privilege(政府特权或王室特权)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所谓Crown Privilege是指政府拥有绝对权利得以以违反国家利益为由,拒绝提供有关文件由法庭进行查阅、质询。假如政府提交的特权申请的主体不是政府机构, 则法庭在审理有关案件时仍然得以应用其文件 (注: 正是因此缘由, 某些学者提出: 严格而言, 此特权不属于一种Privilege.Crown Privilege是一个用词错误。 因为作为特权是可以放弃的,而Crown Privilege在一般状态下不存在放弃的问题。 参见J.D.Hydon:"Evidence—Case V.Materials" (Second Edition),p.417.)。这一特权的渊源、性质以及所保护的客体均与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不同。后者权利保护的核心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白的任意性、自愿性和合法性。因此,其构成自白证据排除法则的前提和权利渊源,在程序的正当中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而前者则注重在程序的正当中保护政府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后者的任意性意味着权利主体可以依据自治意志进行主张、行使或者放弃,而前者则在许多场合中表现出近乎于一种政府的义务,与意志自由相去甚远。
3.它涉及的证据仅限于言词证据。因为此项权利与刑事诉讼中的沉默原则、直接言词原则、任意原则直接关联,所以言词以外的实物证据则被排除。例如采用一定的手段使被告人接受合理的精神或身体检查(诸如提取指纹、血样等),均不受此项权利的限制。
4.它的内容具有多重性并且可以放弃。此权利不是仅局限于因受到犯罪指控而被提交的判决的反对权,而且还包括被指控者在审理之前被迫提交的反对其自身的各种证据的反对权(此类证据可以支持对他的犯罪指控及有罪判决)。从归罪证据作用的角度分析,其权利内容可包括反对提供犯罪事实线索的权利、反对供述犯罪事实的权利以及反对提供加重情节的权利。另外,作为诉讼构造的组成部分,其内容与结构的多重性与违法证据、自白证据又是相一致的(注:参见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但作为一项权利,二者之间无论独立关系主体还是性质、目的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二、反对强迫自证有罪权利的诉讼构造分析
在现代刑事诉讼的权利与规则中,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是一项特点鲜明并在世界各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法律传统的差异性,使得各国对此项规则规定的模式及其内容带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既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刑事权利体现在基本法之中,同时又得以作为刑事权利或证据法则体现在刑事诉讼的规则或案例中。英美法系国家对此项权利的设定显示出有序的层次性。其具体体现在:
1.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宪法性权利。在英美等国,公民的许多基本刑事诉讼权利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寻得了宪法的保护。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 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此即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宪法依据。美国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又随之规定,各州不得制定剥夺公民之特权与豁免权的法律,对于确认被告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从而解决了适用该项权利时各州法律之间及其与联邦法律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问题。
2.证据成文法具体规定了这项权利。英美法系的国家大多没有成文的刑事诉讼法典,但在大量判例的基础上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规则、法例。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即被设立在《刑事证据规则》(美)、《刑事证据条例》(美)、《证据条件》(英)、《刑事诉讼条例》(英)等法例之中。例如英国《刑事诉讼条例》规定,证人拒答权利分为自陷于罪特权、婚姻特权以及法令职业特权等(注: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其中自陷于罪的特权是指证人如果回答了该问题就会自我归罪,则其可以拒绝回答,法庭虽然可以根据案情决定是否允许,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得强迫证人作答。
3.通过判例对这项权利进行修改、补充,派生出许多证据规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Miranda原则。 由于证据往往与刑事追诉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刑事追诉的可能性又与保障社会安全密切相关,因此,依据现实需要,判例对权利的修正分别作了扩展或限制的固定,为刻板的法例条文提供了伸缩的现实可行性,从而使反对自证有罪的权利规则愈加趋于成熟。
大陆法系对反对自证有罪权利的规定表现出以成文法典为核心的模式及特点。具体表现在:部分国家基本法或宪法的直接与间接的规定是此项权利的渊源。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2、20条指出,任何人都没有协助证明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义务。《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对自己不利的供述。”此外,欧洲联盟国家与1950年颁布的《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即《欧洲人权公约》)也体现了这一规则。由于公约效力高于各国国内法律(如《法国宪法》第55条之规定),从而使得该项权利国际化了;刑事诉讼法典对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从诉讼过程中的诉讼权利以及证据规则等环节上作了具体规定。如1994年10月修改颁布的《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询问被告人)、第163条第3、4款(公诉之准备)、第193条第4 款(审判)均规定了被告人的沉默权以及必须告知其享有沉默权,从而免除了被告人自证有罪的责任。1988年9月重新起草、 制定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对此则表达得更为详尽。该法第63条规定,如果未受到控告或未接受调查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以及司法警察面前进行了陈述,而该陈述表明其具有犯罪嫌疑,那么,有关的诉讼机关应当中断询问并告知其可能因此而受到调查,告知其以前所作的陈述不得用来作为认定对被询问人进行指控的证据。反对自证有罪权利的其他补充方式,因各国刑事诉讼构造的不同,其补充形式也各不相同。日本因为二战以后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其规则方式及规则内容更多地反映了两大法系融合的特点。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存在着相对独立的法律,为保持法律适用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判例与例外规则均有较多的适用。
三、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诉讼价值分析
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作为一项诉讼制度,自形成以来,不断地在司法实践中被提及、争议、修正,其实质是如何理解诉讼目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希望实现的并非绝对是法律通过强力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同时还希望法律能够促进公平,即使法律能够减少暴力行为,人们也希望它在公平的基础上加以适用”(注:[英]彼德·斯坦、约翰·香德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在刑事诉讼中演化为对实体真实(犯罪控制)和程序正当的取舍。在此,我们不妨将其作为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所谓诉讼效益最大化,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存在着不稳定的利益系统,各个利益系统追求的诉讼目的不同,该诉讼无法同时满足各类利益主体的需要,无法使各个系统同时走向有序安排。因此,其价值冲突便不可避免,而诉讼的结果只能是在某项利益得到较为完整体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兼顾其他系统的利益。最终得以实现的只能是最大程度的公平。诉讼效益最大化的契合集中在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制度中。 西方诉讼理论中的权衡原则 (GrundsatzderVerhaltnismaikeit)最初的司法渊源正是法律规定的此项特权( 注:所谓权衡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将维护的个人利益与有关刑事诉讼的国家利益进行衡量比较,侵犯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所得的证据应当禁止适用,但对于重大犯罪,前者应当让步。参见宋英辉著:《刑事诉讼目的论》第五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1964年德国联邦法院审理哈根案中,认为被告人日记属于被告人内心领域,违背其本意将其用作证据是不合适的,因而撤销了该项原判。其依据就是此项宪法特权,但由此确立起来的则是刑事诉讼中的权衡原则。
应当看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是各国刑事诉讼致力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历史背景、诉讼文化、诉讼价值以及诉讼构造等方面的差别,由此衍生出各国立法及学者对诉讼效益定位的差异。一些国家的学者认为,“法院如果十分注重程序中的不适格行为,有罪的被告就会被作为无罪。这是从社会功利主义出发得出的结论,其本身是为了更大的社会正义实现的目的”(注: A.S.Goldstein,The State and the Accused:Balance and Advantage in Cnminal Procedure,YaleL.J.Vo169(1961)p.1149.)。某些国家的学者甚至走得更远, 如日本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就曾明确提出“程序乃实体之母”(注:[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在极为注重程序正当性的理论中,往往倾向于对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扩张解释。而较为温和的理论则对这项权利提出了相对严格的限制。后者尽管在限制程度上存在着差别,但在当今的刑事诉讼中则表现得相对较为稳健,比前一种理论更富有现实性。前文提及的权衡法则即规定,对于重大的犯罪,根据社会功利的要求,个人的某些权利应当作出让步。在某些情形下,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将不足以作为上诉的理由。
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因违法证据排除法而得到修正。我国学者李心鉴在其所著的《刑事诉讼构造论》中提出,美国自白排除法则表现为“三进三出”,其背景与实质便是权能观念的嬗变导致自白排除内容得到拓宽或限制。与之相承,权利内容则由此而被修订。1984年美国联邦法院针对证据过分强调程序正当所产生的犯罪指控的不足,确立了违法证据排除法则的两项例外:“最终必将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前者是指即使司法官员不采取违法手段收集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其证据最终或必然将被发现。只要起诉方能够证明这一结果,非法证据就不应被排除;后者是指只要非法搜查是“善意”的,其获取的证据就应从非法证据中加以排除。以上两项例外是针对违法证据排除法则的,但同时也适用于自白排除法则。 这就对构成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的 Miranda法则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此外, 1968 年Ominibud CrimeControl and Safe Street Act中,规定自白只要是任意的, 即具有证据效力,未提及Miranda法则中的其他权利, 事实上也削弱了原来存在的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条件和内容。
辩诉交易的出现对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放弃同样起到了疏浚作用。自美国1971年联邦最高法院对Santoubaler 一案最终消除了辩诉交易是否合法产生的疑虑后,被告人自认有罪的情况越来越多,而检察官也将许多较为严重的犯罪降级起诉。因此,实践中的多数案件主张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现象由此大量减少,正如美国大法官司徒尔特所言:“事实是表示份额悔罪经常与之相随的认罪求情协议是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当地加以管理对有关方面均有益处,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刑事诉讼得以完善。”(注:引自布莱克里V.哈里森,413U.S.63(1977),玻顿克斯V.哈依斯,434U.S.357(1978).)可以想象,辩诉交易制度的形成,尽管对其公平理念仍需研究,但至少其对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效益性问题的解决不无益处。
四、我国刑事诉讼中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可存性分析
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我国1996年经修改的新刑法吸收和借鉴了联合国关于刑事司法的标准与原则,符合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新刑诉法仍需进一步完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仍然受到限制。问题的症结在于以非法形式获取的口供是否能够作为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以及是否应当具有效力(中外理论界对此均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查明真实情况而取得的证据且各种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的,则视为证据具有可采性,应承认其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注: 美国brewey一案中,被告供出了被害人尸体埋藏处并由此找到了尸体,但因警察的诱供行为,因而侵犯了被告人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导致案件以被告人无罪了结。在著名的Maiiory一案和Miranda一案中控诉证据也因同样原因而变的无任何意义。引自美国M.Danaska,Structures ofAuthority and Compat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84Yale L.J.(1975).),但应设置例外法则;第三种观点认为, 应该建立我国的违法证据排除法则,并在排除了非法证据材料后应对被处置者慎重处理,如果其他证据仍足以认定其有罪,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注:参见宋英辉著:《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我们认为最后一种观点较为合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当今时代是走向权利的时代,权利实现的广泛程度是衡量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毋庸置疑,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法治体系的基础和法律体系价值的核心所在。因此,宪法不仅应当表达调整各种社会利益的原则和价值倾向,还应直接将许多重要的权利明确规定在宪法的基本规范、基本制度之中。这既是法律体系有序性的前提,更是各种基本权益得以实现的保障。宪法中规定的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实质上正是刑事诉讼规则的立法依据。同时,刑事诉讼中非法收集证据对公民的人身权利所可能形成的严重危险性和严重危害性,也为构成宪法的基本规范提供了必要性依据。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了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法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被迫自证有罪亦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所以,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自1982年至今,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快了诉讼的民主化进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比基本法更具有实质意义和超前性。因此,为了体现宪法的基本作用,满足时代需要,有必要将包括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在内的基本诉讼权利归之于宪法性权利。
1996年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为设定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首先,新刑诉法确立了反对自证有罪权利的直接法律依据,该法第43条再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其重点在于防止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任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禁止非法收集有罪或重罪证据,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以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供述,证人在自愿的前提下作证。其次,新刑诉法补充了一系列保护权利的有关制度,如无罪推定合理因素的吸收、律师的提前介入等。它们均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自证有罪提供了可行的保护措施。
与此同时,新刑诉法中还存在着一些与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相冲突的因素:
1.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有如实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的义务。尤其是该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意味着证人、犯罪嫌疑人有如实提供证据、回答司法机关提问的义务,否则就属于对抗司法机关的侦查,裁判时可能对犯罪嫌疑人从重处罚。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以及证人证言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证据,而且有可能自陷于罪,因此,只有在任意性的前提之下,在诉讼参加人自愿的基础上,此类证据才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证人不如实回答问题,将置自己于法律不利的地位;如果如实回答提问,也可能自陷于罪。这就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法律责任而作虚假供述,其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便值得怀疑了。另一方面,上述两条规定直接成为司法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依据。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证人不具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司法机关为了使其如实回答,务必想方设法让其开口,从而造成司法机关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滥觞,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迫自陷于罪。
2.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的效力未作明文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则其效力仍然得到承认并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直接证据。这同样在客观上助长了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追求实体真实,为了查清“事实”,而不惜牺牲程序的公正,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不自愿的环境之中,最终导致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取消。
鉴于新刑事诉讼法奠定了一系列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现实性前提,刑事诉讼过程中应该确立此项制度,明确规定公民有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确定明确的取证原则,明确刑事司法人员依法取得证据的必要权限以及必要的取证手段,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能够合法地运用侦查权、取证权,也能够使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对证据依法作出正确地取舍,有针对性地否定司法机关通过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的效力,尤其是言词证据的效力,否定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在此,有必要正确分析不同类型证据的不同特性,区别对待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和非法收集的其他证据。言词证据的主观任意性较强,其客观性往往受到制约,证据虚伪的可能性也较大;另一方面,实物证据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当事人的沉默权的问题。故证据排除过程尤应注重自白证据的排除,这也是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的体现。事实上,我国刑诉法的规定对此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确认,如规定了仅有被告人的自白不足以定罪等。但仅仅这些显然是很不够的。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致力于创造一个任意性的人证和口供的环境,减少讯问(或询问)中的被迫因素,如建立我国有关证人的刑事责任豁免制度,减少证人担心提供证言后的自陷于罪的后顾之忧,减免其法律责任,使证人自愿作证,变强迫为任意,从而避免案件久施不决。我们认为,这既有利于追究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也有利于保护诉讼参加人不因被迫而自证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