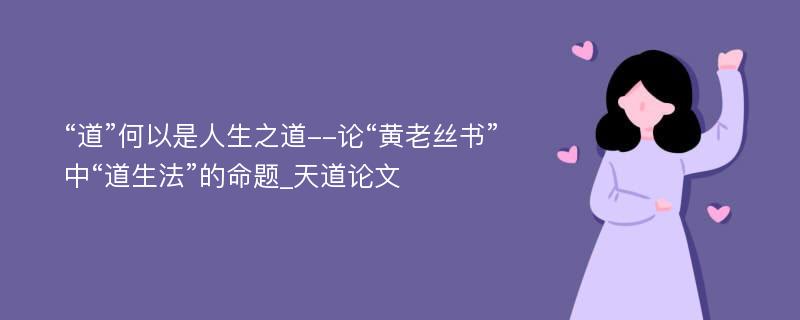
“道”何以“生法——关于《黄老帛书》“道生法”命题的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帛书论文,生法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828(2004)02-0018-06
在1973年底由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属于黄老道家的重要著作《黄老帛书》(注:包括《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等四部分。学界多因唐兰之说,称之为《黄帝四经》。)(下文简称帛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道”与“法”的关系论成为帛书思想内容研究的核心问题。学界的讨论主要围绕“道生法”命题展开。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道生法”意在“强调法是从‘道’中产生的,这就使法具有神圣的意义”[1],系“从宇宙观的高度为法治找到了理论依据”[2],或者是“从‘道’之本体论高度对‘法’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予以充分肯定和接纳”[3]。另一种观点以为这一命题是“道家无为主义与法家的法治主义相结合的产物”[4],或表现为“以道家哲学论证法家政治”[5]。再一种看法将此命题与老子的思想联系起来,认为老子的道作为一种从本原上探讨治世的原则,必须从超越现实的高度返回现实层面,才能实现其初衷,“为此,就必须在道与治世间寻求一种中介”。老子的后学,包括文子和《黄帝帛书》等正是为着把老子超越理论落实到现实层面,而引进了法[6]。或许是帛书这一命题的基本观点至为明了,论者的评价大多着眼于它的作用与功能,很少就其合理性——即“道”何以能“生法”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本文仅采取一个审究的态度看待这一命题,在对“道”与“法”的实质作必要考察的基础上,将之放到帛书的思想体系中加以辨析,发现在帛书中,真正充当“法”之源母的是“天道”(或“天地之道”),而不是“道”。且二者并非同指一实。个中矛盾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
一
从析理的角度对帛书“道生法”命题加以追问——“道”凭什么派生“法”?我们将难以回到该命题,因为,在帛书中,“道”并没有派生“法”的内在理据。
先看“法”。“法”从根本上讲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系统,它通过规定人们的相互关系、制约人们的行为,维护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秩序。规范是表,关系认定是里,二者之统一即可求致一定的社会秩序。正是出于对“法”的规范性和追求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的理解和把握,帛书总是把“法”与度量相提并论。
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黄老帛书·经法·道法》,下引该书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为底本,只注篇名。)
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巧验。事如直木,多如仓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同上)
规之内曰圆,矩之内曰[方],[悬]之下曰正,水之曰平。尺寸之度曰小大短长,权衡之称曰轻重不爽,斗石之量曰少多有数。八度者,用之稽也。(《四度》)
有仪而仪则不过,恃表而望则不惑,案法而治则不乱。(《称》)
度量器具之为用所依据者即自身的标准性、统一性、方便性、绝对性和权威性等品质。申言之,正是因为具备这些品质,“八度”才能在把握事物真相和裁制非规则状态事物的过程中起到稽式的作用。帛书或直接以量具之用解说“法”的功能,或用渲染的方式来凸显规度的必要性以衬托“法”之于为治的重要性;或用参比的手法,由仪表之于测量的功能申发出“法”之于止乱的必然性。虽不直言法,但关于法的观点已大体表达出来。法与量器之所以具有可比性,就在于二者除了适用的领域不同之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因为规、矩、悬、(绳)、水、尺寸、权衡、斗石等是为“度”,法也可称为“度”,合而为“法度”。与“八度”一样,法度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度量器,尽管是无形的,却是天下之大量器、治国之仪表,人主据“法”而为政,即如“左执规,右执矩”(《五正》)一样。在帛书作者看来,如果说“八度”是裁量万物的稽式,那么,“法”则充当着为治之稽式。案法而施治就可以达致“治”的秩序状态,并在这种秩序状态下实现制约各级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功能。“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表明帛书作者对法的规范与秩序化功用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法律秩序状态必须依靠法律规范才能求致;另一方面,法律的规范功能也只有在秩序状态下才能体现出来。“度量已具”表现为法的实施,指法律规范在社会活动中被贯彻的过程和活动,即将法律规范的一般要求和抽象意志转化为人们的具体行为和现实关系;“治而制之矣”则属于法的实现之范畴,指向这一活动的结果,“制”所强调的是法律规范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落实,即义务被履行和禁令被遵守等。就帛书提供的话语来看,法的规范作用具体表现在:一、纠偏正行,所谓“引得失”、“明曲折”者是也;二、辩断是非,此《名理篇》所称“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再看“道”,帛书中的“道”首先被规定为本源,万物都从这里产生和开始。此《道法篇》所谓“虚无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和万物“同出冥冥”。从虚寂无形、窈渺冥冥的道体中所产生的只能是实然性的事物,或飞鸟或游鱼或走兽或草木。也就是说,“道”生万物是由虚而实,从无到有的过程。《观篇》曰:“群群□□□□□□为一囷,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行法循□□牝牡,牝牡相求,会剐与柔,柔刚相成,牝牡若形。下会于地,上会于天。……乃萌者萌而孳者孳。”这个过程的起点是混一无偶的整体存在,渐而分判为对立而统一的阴阳,并由此而构成循环相替的四时,最后才是万物的萌生。不难看出,“阴阳”在这一大化流行的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道”作为本源不仅要通过阴阳释放出来,而且还要凭借之展开牝牡、柔刚复杂的运动,方能汇成万物之流。离开了“阴阳”,“道”则会与万物相悬隔而失去本源之意义。“恒无之初”便只是“恒无”,“迥同太虚”就永远是“太虚”,故《果童篇》谓“阴阳备,物化变”。
其次,“道”还被认定为基质,为万物所包含并赋予万物以内在规定性。《道原篇》曰:
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
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蚑行蛲动,戴根之徒皆取生,道弗为益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多。
一度不变,能适蚑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
应该看到,“万物得之以生”与上引“万物之所从生”似乎传达着相同的思想,但却透显着不同的规定。后者所作的是本源论的表述,“道”与万物有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处于此种关系之中的“道”无论被描述得如何玄虚都必须具有实存性,《道原篇》明之以“精”和“实”,谓“恒—而止”的太虚是“精静”而“不熙”;强调“知虚之实,后能太虚”。但“精”、“实”并不以具体形态表现出来。帛书即以“无形”突出“道”的实有性[7]。于前者,“道”则不再是万物生成的实然之源,而成为万物能否生成的决定者和规定者。万物只有于此获得其本质方能进入现象界。并且万物在经历自身的运动历程后,又从具体形态复归于虚寂之道。“道”于万物生成至归寂的过程中担当着基质的作用,不因为万物“皆取生”和“皆反焉”而产生数量上增减、多少之变化。因此,它只能是“一度不变”的逻辑上的抽象规定,既是万物始终的发动者和承载体,又决定着万物的性状:鸟飞、鱼游、兽走,以及物之大小等无一不是受着它的规约。此种意义下的“道”必须是“剔除了物质性的、无法感知的超验性存在”[8]。故《名理篇》和《道原篇》均称“道”“莫知其名”、“莫见其形”
如此,“道”与“法”之间派生和被派生的关系便似乎缺少必要的内在联系。唐兰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一困难,故他特别解释:“道这个名词,是应当作客观规律来讲的,法是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制定的,所以说‘道生法’。”[9]但是,根据“规律”的定义,是解必须满足“本质”和“必然趋势”这两项条件(注:《辞海》关于“规律”的定义是:“亦称‘法则’。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具有普遍性、重复性等特点。”(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6页。)。前者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关系。显然,“独立不偶”、号称为“一”的“道”本身并不具备关系性的特质;它为万物所摄取和包含也并不以关系的形式存在和展开。后一项条件只有在对象处于运动变化的状况下才能成立。而帛书之“道”又是“一度不变”的,它“无形无名,先天地生,至今未成”(《行守》),“在阴不腐,在阳不焦”(《道原》);“天弗能覆,地弗能载。……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同上),“建于地而溢于天……大盈终天地之间”(《名理》)。胡家聪先生曾注意到帛书中的,“道”与《老子》中的“道”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指出在《道原篇》作者看来,原始道体是“恒一而止”、“精静不熙”的存在,这与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等说法不一致,偏离了老子所规定的“道”的循环往复转动不止的本意。是“走了神”[10]。依本文,正是这一“走神”使得帛书之“道”失去了规律的内涵,从而也失去了“生法”的功能。
二
“独立不偶”、“一度不变”之“道”不能像“适规”万物那样赋予具有规范性质的“法”以本质之意义。换言之,体现着一定关系的“法”不能同万物一样从“虚无形,其裻冥冥”的道体中产生出来。那么,在帛书中,承当“生法”大任的又是什么呢?本文以为,应该是“天道”或“天地之道”。《道法篇》于“道生法”后,接言“执道者生法”,承认“法”的人为规定性。尽管“道”似乎依然是生法者所依据的原则或参照系,但从该篇末尾“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执道者”所执掌的“道”并不是无形之太虚,而是体现为“反”的天之道、“分”的君臣关系和由始至终的万物化变,它们都具有规律、法则的意义,可以作为“生法”的依据。《道原篇》还声称:“故唯圣人能察无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太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即圣人只有先把握道(虚)之“实”、凭藉“天地之精”,方能周遍、通彻一切领域之事理。
“天道”所以能够成为“法”的稽式,是因为“天道”包含着周期性和对立性两个基本法则。《论篇》曰:
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则壹晦壹明,□□□□□□□□〔天〕定二以建八正,则四时有度,动静有位,而外内有处。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者,天之所以为物命也。此之谓七法。
周期性法则即《姓争篇》所谓“天稽环周”、《四度篇》之“周迁动作”、《四度篇》”极而反,盛而衰”、《论约篇》“四时代正,始而复终”。就此引《论篇》这段话语而论,它主要表现为日与月的出入与生死、星与辰不失其行和四时的环替相代、轮转不息。如果说周期性法则是由天体运行的圆形轨道抽象出来的规律,其前提是,只凭据轨道上的某一点把握天体运移的特征,那么,透过两个对立点加以审视,环周式的位移只是两极对待而已,周期性法则即转变为对立性法则。不仅四时环替相代可归为始——卒、立——废、生——杀、终——始的对立,日、月、星辰三者运动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若日之出与入、南至与北至,月之生与死、进与退,星辰之动与静、处内与居外等。它首先表现为天与地的反对;其次则表现为天体运行的不同阶段及其性征的相互排斥。帛书中的“阴阳”即是表达对立性法则的基本概念。因此,《论篇》“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中。“一”即指“道”。“明三”、“定二”是天之道的主要内容。“明三(日、月、星辰)”昭示周期性法则;“定二”则彰显对立性法则。而“八正”基本上不出此两项内容。“四时有度”侧重于季节的循环转替,“动静”、“内外”明显地是从“对立”为说。不管是周行还是对立,天体各当其时,各处其位,各显其性即为“正”。“七法”则试图从七个方面对天之道加以进一步的抽象概括,揭示出天体运行的当然性、适度性、准确性、回反性和必然性等规则。
在天道的两个基本法则中,“阴阳”所表达的对立性法则对于“生法”起着主要的式规作用。《称篇》提出“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又根据“阴阳大义”明确主张“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这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基本认定必然成为制定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从而“天道”也顺理成章地充当着“生法”的稽式。
其实,帛书常常把关于人事活动的构想附列于“天道”和“天地之道”的后面加以表述,使后者居于对前者的统摄和支配地位,让人事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获得不可动摇的依靠和合理性证明。
天道寿寿,播于下土,施于九州。(《三禁》)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姓争》)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道法》)
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动静]之位,外内之处,天之稽也。高下不蔽其形,善恶不匿其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其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四度》)
帛书作者相信,以日月为代表的程式化的宇宙之行背后有一种永恒的、对人事具有普遍导范价值的法则,它弥纶天地之间,渗透于一切人事之中。人类组织中的社会等级关紧,包括管理主体内部的君臣关系和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君臣士民关系,以及诸多复杂关系交织成的由人所参与的活动,都要参照并受规于天地之恒常或“天之稽”、“地之稽”。人类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不过是天地之道的摹本,掌握天地之恒常即能预测人事当下之休咎和未来之吉凶,《成法篇》曰:“与天地同极,乃可以知天地之祸福”;天地之道即是人道之标准样式或衡量人事成败得失之标尺,《姓争篇》指出:“夫天地之道,寒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居则有法,动作循名,其事若易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居则无法,动作爽名。”用“天地之道”这柄标尺纠人事之偏过,就是要求人们效法之,让人事回到它所规定的原则上来。这是负面评测中必然包含的正面答案。
进而,帛书要求一国之主必须法天重地,把参合天地之道当作国家最高管理者的首要条件。因为天道能否向人道推衍最终取决于后者的主动选择和自觉仿效。对于人道来说,天道只是一个自在体,不可能自动地派生出社会领域内的各种规范。《论篇》曰:“人主者,天地之□也,号令之所出也,□□之命也。不天天则失其神,不重地则失其根。”认为人主由于能够把握天地法则而成为国家号令的发出者。换言之,号令如果失去天地之道的支持就会因缺乏可信度而不具权威性。逻辑地,“倍(同背)天之道,国乃无主”(《论约》)。同样,圣人也是因为能则天法地(《国次》)、“合于天地”(《前道》)、“麋论(读为弥纶)天地之纪”(《称》),才被帛书作者所推崇。
三
回到本文开头所列的关于帛书“道生法”命题的三种观点。从帛书作者之主观意图看,第一类看法显然是深中肯綮的。但是,进一步的追问使我们发现,帛书作者凭“道”之名而用“天道”之实来派生“法”的做法,其实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据唐兰先生考证,帛书成书于战国中前期之际。这一结论已广为学界所接受。黄老之学是道家中倾向于干世的流派,而由老子所确立的道家核心范畴“道”又具有相当的超越性。借助上引第三种看法的问题意识,解决“道”与治世相悬隔的难题,就成为帛书的首要任务。于是,帛书便回到老子之“道”的原型“天道“上去(注:“天道”是史官学派的重要概念,老子的“道”实即“天道”的抽象形式。详参拙文《老子之“道”——“天道”的抽象形式》,《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但同时又极力坚守老子所开创的“法道”的道家立场。从而,帛书既宣扬“天道”或“天地之道”对于人事的导范作用(上文已述),又强调人主“抱道”、“执道”以为天下。应该说。这一矛盾体现了一个学派理论范式转变的探索过程。持第二种看法者试图从学派的互动关系解释这—命题,视角是独特的,但须以帛书之晚出为前提;而且,法家固然重“法”,但“法”并非法家之专题,作为国家统治的方法和手段,当它进入国家管理活动之域时(大约始于春秋末期而普遍化于战国初期),即成为致思于治道的“议政”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故此说难脱勉强之嫌。第三种解释看到了此命题所蕴涵着的从“老子”转向“黄老”的用意,但将“法”当作“中介”联结老子之“道”和现实之治世,似乎缺乏根据。因为,如上文所述,“法”本身即为治世之器。
帛书在“执道”和“合于天地”以为治之上的矛盾,引发了其后战国黄老学派关于治道理则的两种诀择。以《管子·心术》(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等四篇为代表的稷下黄老学派注意到帛书在“道”的方向上的偏离,试图重新回到老子“道”的立场上去,同时也认识到老子之道的玄虚性妨碍了它干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的可行性,于是便对“道”进行实然性的改造,使之摆脱超验的形式获得实在的规定,成为一种物质性实体。以便于为人们把握并向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和方面推衍。改造的方法主要是将道与具体物质“气”相沟通。这一点,已有的研究论述颇详,无须赘墨。本文要关注的是稷下黄老学派据“道”以施治的事实。《管子·内业》说“道也者,……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将人事成败系之于道。而且持道、从道的程度还决定着事功的大小,“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贼”(《白心》》。稷下黄老学的其他家(派)也同样表现出据道论治的倾向。慎子被认为是道法结合的关键人物(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慎子》谓“道德是为刑名(法),此其(指慎到)转关”;金建德据此提出今存《慎子》中的《因循》等篇属黄老,而《威德》等篇转向刑名。(参金著《先秦诸子杂考》,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丁原明则将慎子的道法结合的转向同《管子·法法》诸篇的道法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参丁著《黄老学论纲》第三章第二、三节)),故可以推定其治道理论基始于“道”;尹文子申称“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大道上》)。凭“道”而治是为理想,退而求其次则以“道”统摄、融合各家学说而为治。
确立“道”为治道理则只是稷下黄老学派之主流,《侈靡》和《形势解》等篇还表现出不同于此的、以天道为根本法则的倾向(注:若《侈摩》曰“可以王乎?请问用之若何?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必因天地之道”;《形势解》曰“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乘马》曰“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枢言》曰“有天道胜无天道”等等。)。这种倾向一方面是对《黄老帛书》治道思想的直接继承,另一方面导致了庄子后学中的黄老学派对“道”与“天”位序的重置。表现在《庄子·天道》(下引该书只注篇名)诸篇将“天”规定为高于“道”的存在。如:
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天地》)
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天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同上)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天下》)
刘笑敢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指出“这里讲的道常常是天地之道,老子的‘天法道,道法自然’变成了以天为宗,以道法天”。但他局限于观念形态的分析最终将这一转变仅归结为“先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影响又相互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11],未能从战国黄老学的发展历程中予以把握。本文以为,庄子后学中的黄老学派意识到此前黄老之学关于治道理则的分歧,自觉而明确地表明立场。《在宥篇》曰“何为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将虚玄之道与实然之天道、人道融通起来,从而使得脱离天道或人道论说“道”的做法成为不可能,而人道也只能与天道相对应。这与其他篇的治国王天下论也相一致。如《天道篇》曰“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天运篇》则有“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之说。
庄子后学中黄老学派的这一立场后来又为《吕氏春秋》(下引该书只注篇名)所坚持,此可以从《序意篇》中看出,作为主编的吕不韦在叙其总体构想时曾指出:“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清楚地表明该书所展示的思想是从天地法象而不是“道”中获得的,天地之道便顺理成章被标树为最高法则。《圜道篇》曰“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人类社会管理秩序的建立即是仿效天地之道的结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人间安排是由天地之道派生的。逻辑地,不同等级的人(群)只要各执所法,他们所构成的组织便能处于和谐的互动状态。“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
同样,在《鹖冠子》中(下引该书只注篇名),“道”也不再是最高范畴。一方面它被下放到具体存在中予以确认:“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博选》)离开此四者,“道”便无处依存。当然,《鹖冠子》并无意消掩“道”的功用,只是倾向于突出所稽者的辅成和落实的功能。“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能天》)“道”也不再是全能的,从而给人之能预留了展示的空间。“故圣,道也;道,非圣也。道者,通物者也;圣者,序物者也”(同上)。另一方面,又引进了“气”概念取代“道”之于万物的始基地位。“精微者,天地之始也”,“故天地成于元气”(《度万》),“动静无非气者”(《环流》)。由此,我们似乎看到在《鹖冠子》的思想体系中交织着上述两种取向,但事实上,《鹖冠子》一书论及“道”的文字之少,远远不能满足作为理论最高范畴的要求。取而代之并频繁出现的是“天”或“天地”。因为天(天地)既是道之“四稽”之首,又是“气之所总出也”(《泰录》)。而且,从治道角度看,其书中的“天地”也具有至上意义(注:这方面的论述可参看丁原明《黄老学论纲》第121页。),与《黄老帛书》、《管子·形势解》等篇、《庄子·天道》诸篇,以及《吕氏春秋》同属一脉。
收稿日期:2004-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