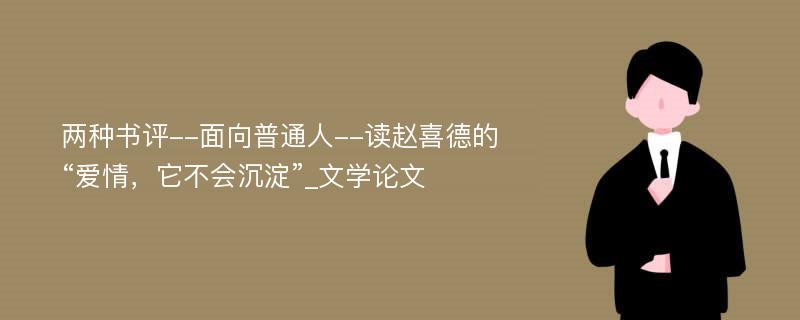
书评二种——面对平民——读赵熙德《爱,是不会沉淀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民论文,二种论文,书评论文,读赵熙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物欲横流、精神衰颓的“人文危机”,当下的文学有两种极端的表现。其一是所谓“抵抗投降”、“抗战文学”,作家将周围的世界看成是“肮脏的污团”,把“大众”看作是一群“庸众”,要“直接说出我对你们的藐视”;他们决不“投降”,而要“抗击媚俗”。他们愤世疾俗、独立风标的精神毕竟表现了他们的操守与勇气,他们孤独的呼喊也确有发聩振聋、启人警世的人用。然而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他们“反大众”的宣言却又是倚靠大众媒介和畅销书的手段得以传播、得以宣泄、得以“走红”的。这不能不使“抵抗投降”陷入某种悖论与怪圈之中。
另一个极端则是所谓的“痞子文学”。这类作家与作品以反传统、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反主流话语为特点,蔑视权威,蔑视一切文明成果,公然摆出与“庸众”同流合污的姿态,甚至比“庸众”更“庸”:“我是流氓我怕谁!”“痞子文学”是对伪崇高、伪英雄、伪文化的极端化反动,对于极权与专横的精神统治,无疑有强力的揭露和破坏作用。但“痞子文学”在泼掉污水的同时把盆里的婴儿也泼掉了;他们甚至否定知识分子精神,乃至否定人类生存意义本身。靠这样的文学不可能使人文精神得到重建,也无法寻觅人类的精神家园。
于是,当下文学必然面临这样一个任务,即以一种入世的姿态,面向大众,而又能发扬文学的“精神灯火”的功能,烛照人世,与大众携手进入新的精神王国。这样的文学并不以“精英”的面目出现,而又绝无“媚俗”之处。既不像“抵抗投降”那样以民众为敌,更不像“痞子文学”那样公然宣称与庸俗合流。它应是视大众为友朋,与大众抵膝而谈,在一种平等、友善、推心置腹的气氛中营造文学的精神领地。
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赵熙德的《爱,是不会沉淀的》,庶几可作为这样的面对平民作品的一个代表。
粗略看去,《爱》是很可能被排除于眼下大量上市的“散文精品”之外的。作为一本“抒情美文集”,实际上它并无多少华丽的外形。如今散文文体革新发展很快,构思、立意、结构、语言等,都有了显著的变异。而《爱》的叙述方式、行文方式大体上还很传统,有些地方甚至稚拙。这乃是因为作者被汹涌的爱心激荡,无暇顾及如何在文体上翻新,只一路平实写来,能达意即可。而就在他平平常常的文笔下,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向我们娓娓而来。这中间有母亲,有恋人,有妻子,有儿子,有同窗,有同事,有师长,有挚友。作者以个人与家庭为中心,表达内心情感,讲述人生感受。作品充满了无伪饰的坦诚、直率和近乎天真的爱心。这种直率的情感既非高蹈超越,又不媚俗合污;而是以大众一员的面目出现,面对平民,向他们讲述那些关于青春与理想、友谊与爱情、事业与人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几乎全都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他甚至原封不动地整篇引用当年与恋人来往的书信和日记,充份表达了他对读者的信任和亲爱。在近乎纪实、如实道来的篇什里,作者无伪饰、无雕琢地向人们展示一种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人伦之美,爱心之美。这种亲情之美正是千家万户千万平民所关注、所渴求的。
这样,《爱》就与一些超前的先锋性作品保持距离。《爱》不与读者讨论那些过于形而上的议题,既不追寻所谓的“终极意义”,也不强调佛、道、禅一类的玄机。《爱》中没有灵与肉的冲突,没有生与死的苦恼,没有自我拷问的创痛。它探讨人的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上的现实的、观世的、实际的生活课题:童年、少年、青年,学业、事业、理想,恋爱、失恋、婚姻、家庭,孕育、流产、保胎、分娩,以及孩子的成长、教育、成熟,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确认《爱》的最鲜明的特色是它的平民精神,是它面对平民的善意与深情。在这“精神滑坡”的转型期,离开了对平民的友善与真情,所有埋怨与愤慨都无济于事;所谓“重建人文精神”,归根结蒂得从具体的人和事入手一点一滴地切实进行。
然而,《爱》又绝非言情小说,亦非曾经广为流行的“新××”一类的作品。言情小说刻意营造一个充满浪漫情调却离现实很远的虚幻世界,以满足幼稚者和市井阶层的心理需要;“新××”一类作品则主要在对琐屑的平庸无聊的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揭露人性恶的一面,尔虞我诈,玩弄权术,居心叵测;甚至父子、母女、兄妹、姐弟间亦暗藏杀机。言情小说为大众提供一种精神寄寓的有效方式,不同程度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新××”一类作品诉说人的内心苦闷,提示生存的艰辛和社会生活的浓重阴影,亦有相应的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但虚幻的梦总要醒来,过于龌龊的图景又不免污人眼目。人总企望拥有一个健全、美好的人生,企望拥有切切实实的辛福,切切实实的光明。《爱》正切合了读者的这一需要,似可与半个世纪前影响过一代中国人的《爱的教育》一书相通。赵熙德笔下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无情的揭露,没有对卑劣与黑暗的展示,没有自我忏悔与拷问,也没有对他人和自己悲天悯人式的同情。他自称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写的散文全是人性美的一面。”(第184页); 他甚至不无武断地宣称“命运的安排总是最好的,最合理的。”(第161页)。 赵熙德以一双唯美的眼睛看待生活,即使是失恋,即使是生离死别,他都要从中挖掘出人与人的相知相善和亲爱来。他为人与人之间的情爱感动得常常流泪,而他流的泪绝不苦涩,绝不伤感;那是一种因爱与被爱深深感动的泪,是一种沉浸于巨大幸福之中的泪(他把与亲爱者一道感受不幸也看作是一种幸福)。赵熙德有意不去注视那些苦难的东西,生活中的苦难太多了,描绘苦难的作品太多了,赵熙德不愿或不忍再去触及生活的过于沉重的一面。即使涉及50年代的政治风暴,60年代的物质匮乏,文化革命的全面动荡,他的笔也总是轻轻掠过掉头而去。在赵熙德看来,无论外界如何风起云涌,只要有亲情,有人伦,有爱,那就都是幸福,都能转化为美;越是在波折中,人与人的亲爱越能闪耀光采。这样的心态在当下作家作品中很不多见,然而这恰恰是多数普通平民,特别是中国平民对待命运、对待生活的通行原则;《爱》这样的作品因之会被很多人当成生活的教科书。赵熙德“总是微笑着对待生活”(第169页), 然而这和那些向桃源境界寻求寄寓的作品不同,也和那些以50年代的“美好”反衬当今社会的“污浊”的言论不同。虽然赵熙德在作品中深切怀念他的青春岁月,甚至敢于断言“只有我们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才真正拥有过无怨无悔的青春”;然而《爱》中并无“怀旧”的迟暮气息。一般的怀旧,是由于人们负荷太重,疲惫的心灵要借怀旧得到休憩。而赵熙德念念不忘50年代大学生活,则是要从青春岁月中发掘美。他的偏爱往往先就“醉”倒他自己;从陶醉中醒来后,他更热爱生活,更执蓍今天,心情更为明朗,精力更加充沛,60多岁的人了,他却觉得自己永远是十八岁。这就与一般怀旧者的伤感或淡淡的哀愁或含泪的微笑完全不同。赵熙德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甚至连他儿子都表示异议:“爸爸,你在你的散文里把人性写得太美了。其实,现实中的人性并不真的这样美。”(第101 页)然而,赵熙德仍然不倦地挖掘生活中的爱与美,即使是生离死别,他也只专注于生离死别在心中留下的深刻记忆,而不去追寻导致生离死别的原因。这不是逃避现实,也并非粉饰太平。赵熙德要从任一种现实中发掘美和善,发掘普通人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情爱。这种如杨绛所说“乌云的金边”的光亮,甚至将许多不如人意之处都隐蔽了,只留下亲情、友情、爱情,时时滋润人的心田。这种对人情美、人伦美的冀求是与众多平民相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赵熙德与平民大众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契合。因此,《爱》能够突破年代限制而被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所接受,而又以中年知识妇女为最。《爱》出版后,很快为平民阶层所注意。有人撰文称:“最近,沪上知识妇女界盛传一本书:《爱,是不会沉淀的》”,“作者的纤细动人之笔,娓娓道出了中年人被日常琐事压迫在心海最底层的那片心事,无疑这就是真情的所在。”(宋路霞《真情的魅力》,《新民晚报》1995年2月1日)《爱》之所以特别在“中年人”和“知识妇女”中盛传,正因为这部分人构成了平民阶层的大部。中年人,知识妇女,对婚姻、家庭、人伦、人情有最切身的体会。赵熙德将人文精神化为一种世俗的可操作的具体规范,把抽象的人生意义、生命意义具体化为事业、友谊、爱情等人所共有的切实话题。这样的话题既是高尚的,又是平民的;既是严肃的,又绝无沉重之处;既是世俗的,又能让人潜将默化向美向善升华。读者只以平常心读他那些平常的经历,无大起大落,无惊风雨泣鬼神,无泣不成声、痛不欲生之感。进行文亦不作渲染,文字朴素到近乎无色。它只是一点一点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一滴一滴浸润读者心灵、《爱》中没有超前的文体实验,文体意识很不鲜明;作者不追求形式的奇美,也不作探索与实验。文中没有时空倒错、条块分割、因果位移、空白跳跃、意识流动、内心独白之类的现代技巧,倒是平白的居多。这种形式上的平易也是全书基本精神的体现,平易的形式易于被更多的普通读者所接受,也符合自传式、纪实式内容的需要。
如果苛求一点的话,如果用文体艺术的要求衡量,《爱,是不会沉淀的》一书中一些篇章尚有进一步剪裁的必要,某些地方还可加强构思的功夫、营造的功夫,文笔亦有可润饰之处。在涉及生活沉重的一面时,也可以作一点直接的反映;有了阴影,就有了比照;有所比照,闪光的东西是只会更加耀目的。
1995年12月8日于贵阳花溪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