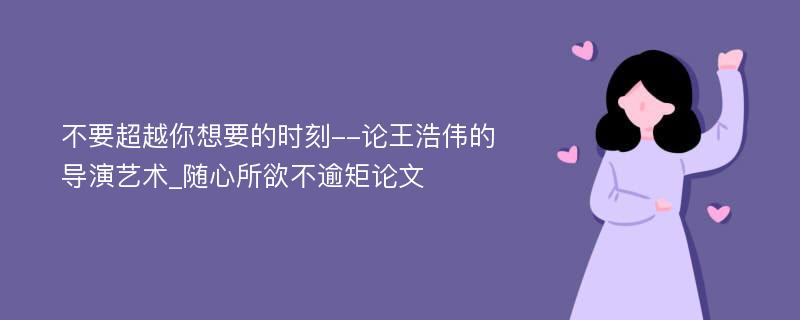
随心所欲不逾矩——王好为导演艺术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随心所欲论文,导演论文,艺术论文,不逾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让·雷诺阿说:‘一个导演一生只拍摄一部影片。’一个批评家的任务是去发现它。” 〔1〕在一个导演一生所拍摄的影片序列中,一定存在某种共同的深层结构,而每部影片都是这一共有结构的变体。本文旨在运用这一基本思想对导演王好为及其作品作出分析。
王好为开始独立执导影片是在1979年。1979,无论在中国政治史、还是文化史上都是极为醒目的一个数字。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提出,使中国社会感到一种全新的律动,艺术也呈现出一种空前的超负荷状态。第四代电影艺术家正是在这时异军突起。如果仅仅依据年龄层和创作年代划分艺术家群落,王好为无疑是“第四代”中的一个,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当她的同伴们在“伤痕”泪海中进行对现实政治和主旋律艺术规范的大突围、借助个人风格和空间造型元素构筑新的电影话语和符号秩序的时候,王好为却似乎避重就轻地选择了平静,她以流畅的线性叙事和经典的镜头语言在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结构出一部部健康、乐观的社会情节剧和轻喜剧,使她的影片成了新时期“主旋律电影”的范本之一。她是第四代通例中的一个例外。
王好为曾清楚地开列她的知识结构清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反映论为哲学体系和方法论;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即是美”为美学观;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以再现和表现相结合以叙事蒙太奇为表现手法,镜头运用“根据内容需要,力求不露痕迹,不耍技巧。”〔2〕这里,王好为的传统、 正统与主流色彩清晰可辨。然而,她并非不加思索地因袭或无力创新而退守,她不盲从,亦不矫情,这是她清醒地看取人生,分析自我之后做出的真诚的选择。她的影片,不曾沦为单纯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不是题材的宏大与宣传术语的直露,而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娓娓动人循循善诱地讲一段平常人的故事。历史只是背景里遭遇的叙境,而人的选择,是亘古就有了的。她的“主旋律”与其说是“政治主旋律”,不如说是“文化主旋律”,她的价值取向永远是“中、正、平、和”。“中、正、平、和”是理想秩序向每一个个体提出的要求,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唯其是理想,才永远不可企及,唯其不可企及,王好为才在她的影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苦心劝世。她对前辈的尊敬与对传统的固守,使她不至一鸣惊人,脱颖而出。但她秉着一股内力,坚持言说自己,言说生活,这也正是她导演的一部“中正平和”的人生的影戏。她不故意引人注意,甚至有些有意不引人注意,尽管她未尝不在生活中看到触目惊心的倾轧,你死我活的争斗,但她习惯了以“中、正、平、和”之心观察,以“中、正、平、和”之心叙说,于是在她的话语里,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惨酷与悲剧感,她瓦解了深度,但并不流于肤浅,她是沿着另一条思路,走向了地平线上有光的高处。
人掌握了语言,而后被语言所掌握。有些话,久不说,便会渐渐淡忘,竟至无论怎样随意地信口说话,都不会说出来。王好为的影片序列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因为虔敬与笃信而不仅不觉其限制,反而愈来愈轻松自由,得心应手,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第四代导演是在中年已至时开始其创作生涯的,他们的被历史话语定义为“虚掷”的青春使他们在第一期创作中不约而同地讲叙“缺憾”与“丧生”的故事。在《青春祭》、《城南旧事》、《沙鸥》、《小街》中,“无论是社会恶势力、浩劫还是自然力,都无疑在叙事的表层结构中构成了一种非人的、异己的毁灭性力量。它无情地剥夺,而将主人公置于无从反抗,无可行动的情况之中。……叙事语调呈现为清纯,凄婉而缠绵,一种痛楚而低回的青春韵味”。 〔3〕而王好为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却出人意料地是一部轻喜剧——《瞧这一家子》。除了一对革新的青年与保守的车间主任之间健康透明近乎高尚的矛盾,片中还有一对喜剧人物,他们的幼稚和轻浮频频制造笑料,在笑声中迎来革新成功婚姻美满的大结局。这一以五十年代“技术改革”为基本被叙事件的喜剧片,用“赢得”取代了“丧失”,用“完满”取代了“缺憾”。它无意自欺欺人粉饰现实,也并非无视历史悲剧的质问与反思,而只是不再反复检视创口的血迹。如果痛苦的每一次重复与回忆都强化了悲伤的体验,王好为似乎宁可背负了“笑忘”的责难,平和地构造一派乐观气氛。从这个或许过于平和的故事,人们毕竟可以笑着走向未来。
《潜网》1981年是一部以“求爱受阻”为母题的典型的“链锁连环牵相思”式情节剧。以女主人公罗弦的爱情婚姻为线索,以父母之命门第观念为对立面,看上去很容易成为一个“抗议女性”文化文本而构成对父权秩序的威胁。然而我们注意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何侃。他起初被安置在一个并不重要的不利的受动者位置上,并且远洋轮的工作使他在叙事链中忽隐忽现出没不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实际上是真正的秩序与权威的化身。如果说由罗弦父母代表的旧家长旧秩序早在“五四”时就已不堪一击,那么出走的娜拉/罗弦却在几十年以后仍然“无枝可依”。罗弦有新观念,但她凭借更多的是热情与任性,在她负气离家并发誓不嫁何侃时,她不知道在她以为被她抛在身后的秩序中,有门第观念,也有她在其中生其中长的关于幸与不幸的界定。她嫁给郭汾,不仅没有获得归属的安定感,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她的困惑无依。父母的“家”和自己的“家”的无可寄托把她推向社会,她将在事业上寻求寄托。然而事业的辉煌永远无法弥补感情缺憾,她早已被告知没有“家”的女人是不幸的、可悲的。故事就要走入残酷的现实——罗弦父母永尝“失女”的悔恨,罗弦忍受无爱的“家庭”,何侃也不得不迁就于无奈的婚姻——一场灾祸如期而至,郭汾舍己救人光荣殉职。他的退出,使无法拆解的矛盾倏然消失。这是一个契机,已为人母的罗弦重新获得了母亲,人伦秩序得以恢复,而何侃及时走入,看似与罗弦一起反抗已成败势的“旧观念”,实则把女人重新拉回家庭,使秩序重归稳定。我们不妨回忆,在高潮尚未到来,矛盾悬而未决的时候,何侃对罗弦说了“爱,就是去做”。在关键时刻,何侃是真正的施动者,罗弦去追踪陈志平的时候,她实际已是走入了何侃所代表的秩序中。只要权力的交替更迭还在父子之间进行,只要女人走回家庭,就撤去了颠覆性的威胁,就有把握获得稳定的秩序。有趣的是,以《潜网》为题,无论作者初衷何在,都不可避免地可被解释为内在秩序的不可见和无可破毁,从而成为对影片主题和结构一个有意味的反讽,这也许倒是导演始料未及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潜网》中“郭汾之死”成为全剧的转机,导演似乎在回避无法调和的矛盾,不可救赎的沉沦,回避更为可能的惨酷的真实。如果说“郭汾之死”是生活允许的不多见的巧合之一,或是被剧作提供的先在的情节所决定,不足以见导演的用心,那么《村路带我回家》(1987)年则呈现为一个惊人的相似性结构。女主人公乔叶叶同样面临对三个男人做出选择,同样阴错阳差地嫁给了最为苍白无力的一个。而这一个——同样是老实人的盼雨——同样及时地,而且更为轻描淡写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去的,只在闲谈里听说他病了,不久以后,结婚时两条毛巾的空镜头变为一条毛巾轻轻摇入摇出。王好为的“平和”追求,使她淡化情节,淡化死亡。盼雨之死,同样是全剧的核心。乔叶叶不必一生背负嫁给无能者的错误选择;宋侃有机会用承诺弥补过去;金召也有时间铺垫感情;甚至死去的盼雨形象也受到保护——不必由一个憨厚可爱的幸者转为一个累赘可厌的不幸者。于是,我们看到,生活未至底限便开始好转。似乎只是一段时间流过,思想解放经济发展之后,乔叶叶拥有了思考力和重新选择生活的权利。
更有意味的是乔叶叶的选择。她选择了金召,选择了社会主义新农村,选择了“会种棉花,心里踏实”。她并没有急于纠正“扎根农村”的历史错误而不加思索地回城,偏激地走向历史的反动,而是保有她一贯的“平和”。毕竟,历史流过每个人都不可能不留痕迹,正如罗弦父母虽未促成“理想婚姻”,但终究使罗弦未能遂愿,“扎根农村”的奖状也使叶叶隔膜了城市,使乔母“习惯”了叶叶的缺席,使企盼仅仅成为永久悬置的企盼,而现实是,乔叶叶真的“扎根农村”了,就象《潜网》中,罗弦竟终于走到何侃身边。尽管现在的双方早已不负载当初的意义,但客观上,绕了一个大圈之后,她们的确回到了出发的地方。这并非导演宿命,而是从某种意义上与对立面的折中与调和,不必走向绝对的反面,而达成一种新平衡,“中、正、平、和”仍是最后的姿态。结尾处,我们看到罗弦抱着孩子,与宋侃并肩走在现代城市象征新秩序的立体交叉桥;乔叶叶和孩子坐在公共汽车后排座位,向骑着摩托跟随的金占挥手微笑。道路在延伸,选择在继续,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图景,是何其和谐与充满希望。
矛盾可以转化,冲突似不可免,但象是唯恐正面冲突破坏苦心经营的“平和”一样,在视听层面上,王好为小心翼翼地让“恶”隐去,而呈现给我们干干净净的感受。《村路带我回家》中,盼雨拎着斧子去找金召,一场恶战势不可挡。导演却让他们厮杀进屋里,而摄影机并不凑热闹跟进,相反很有把握地固定在俯拍的机位,我们只看到静止的屋外全景,听到闹剧般的声响,当人物再次出现,“战争”已经结束,只剩一个轻松幽默的收场。无独有偶,决定乔叶叶命运的“扎根农村”的公社书记讲话一段,导演同样省掉了不得不做为反面形象出现的人物镜头,我们只看到一双穿皮鞋的脚和几个香烟头。乔叶叶在公社、县委礼堂、地委礼堂做“报告”,文学本都有乔叶叶的具体形象,以及大队支书、县委书记在场“自我感觉良好”的具体形象,而影片中,画面上只是三个礼堂的大门和门口停放的车辆。“眼不见为净”导演保护了人物形象,保护了全片的和谐,保护了观众的视觉记忆。
《夕照街》(1982)年是部群戏,20多个人物,人各有貌,引出种种矛盾。但一如其他的作品,王好为淡化冲突,并不设计敌我矛盾,甚至不纳入善恶报应的叙事模式。她不要拳来脚往剑拔弩张,而是期待“多行不义必自毙”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小人”李鹏飞虽然自作自受弄巧成拙,但两个随地扔废纸的镜头首尾呼应,“小人”依然故我。我们还看到《村路带我回家》中,尤端阳自私自利工于心计,但她在她的路上毫发无损春风得意。这类人物的设置与其说是可与交锋的对抗性因素,毋宁说是擦肩而过的一种参照。人与人会有遭遇,但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人格超越于事件。王好为坚持的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影片的心平气和的“开放性结尾”因而实际上只是“类开放性结尾”,在表象上,并没有一一救治、完满封闭,实则早已通过作用于观众情感投注而完成道德批判。
在和谐的视觉表象后,王好为同样压抑着欲望与激情。《夕照街》中,周燕燕与吴海波的感情始终躲躲闪闪欲说还休,吴海波两次从镜子中无意窥视到周燕燕,也只是提供一个感情的信息,绝无欲望的目光,直到最终发展成为隐忍的英雄式的情境,才从道德上结合在一起。《潜网》的“文学剧本中,何侃告诉罗弦自己补了票专程送她后,‘二人相视,默默垂下了眼帘,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而在影片中导演改了几句台词,“彻底抹掉了何、罗感情上的暖昧色彩。” 〔4〕王好为像是一个传统观念的卫士,理智控制感情的热度,不使沸腾。超我的强大在抑制情欲的恣肆,因为滥情纵欲使人不可理喻,使行为出格越轨,使事情不可收拾,须克己复礼,才能中规中矩。
王好为的影片并非为具体政治要求服务,没有粗浅直露的说教,而是以一套完备的表现手段和技巧,精致严格地传达导演意图。依时间顺序的线性叙事,丰富的细节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获得了观众无阻碍的认同,从而以渗入镜头语言字里行间的“中、正、平、和”的姿态最终巩固和稳定内心秩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影片。
如果说,人格面具的庞大和超我的过度表达使王好为影片虽然真诚但难免有些矫饰,冲突的淡化与激情的压抑虽然和谐但多少有些缺欠,那么《哦!香雪》(1989)中,乡村少女保有的人之初的纯净和散文体式的冲淡含蓄使王好为得以挥洒自如、从容不迫,她的天性和气质第一次如此清晰,充分地流露在影片构成中。《哦!香雪》是王好为影片序列中的力作,也是中国影坛不可多得的一部散文电影精品。
当改革的光波声浪涌入第四代导演的视野,“古老中国与现代中国”、“文明与愚昧”、“城市与乡村”成为此间第四代影片的全部主题。现代中国(工业文明、城市文化)与古老中国(农业经济、传统价值观与生存方式)的冲突构成了此类影片的叙事施动,也成了影片的叙事表层结构,形成视听层面上两种造型体系的对立。这种对立背后,是第四代导演面临的一种新的两难困境。“一边是理性的,对文明、进步的渴望与呼唤;一边是情感之中的,对古老中国生存的独特韵味,人情淳厚、坚实素朴的迷恋……这使得第四代导演的二期作品呈现出一种矛盾,游移的叙事基调。”〔5〕
这一次,王好为加入了主题,却再一次以散文体式安详地拒绝了冲突的表述,以诗意追求愉快的游离出同伴们的困境。她把我们引向一片净土,这里,只有几个天真可爱的少女,一对老年农民夫妇。影片开始我们看到蜿蜒的铁轨上歪歪扭扭走着的女孩子们,火车轰鸣而来,在她们的注视下,长长的列车显得匆促而短。一个经典的视听层面上象征现代工业文明的符号,走入她们的世界,是那样充满好感与新奇。而火车带来的一系列现代文明的表象,是“北京话”,是画家,是女大学生,他们端正、文雅、有教养,平易而富于爱心,她们是“友好使者”,他们接纳的像是善意地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让你浑然不知还有出血的撞击和痛楚的失落。惟一一次与“现代文明”的摩擦,是香雪在省城中学里同学们的炫耀和潮笑,然而富有美德的香雪很快恢复了自尊和勇气,战胜了自我,更何况与之较量的,不过是现代物质文明轻浮虚荣的渣滓,原本不足为敌。在传统和现代化的比重上,王好为显然立足传统,她巧妙地利用故事物理时间和人物心理时间上两者的比例——火车到站一分钟的庆典和漫长的等待,使叙事时间与之同步,用大量笔墨细细铺陈农家的日常生活。在叙事层面上,为庆祝女儿上中学在菜中加两滴清油,在女儿入睡后烙一张白面饼换掉女儿书包里的黑窝头,女儿在父母未醒时又将白面饼放回去……一系列以情动人的细节,构成父母慈爱,子女孝顺的人伦情理。视听层面上,一方面频繁地使用全景,远景呈现山峦,湖水,人与自然的和谐,用镜头搜寻擀毡的舞蹈,满席子上黑花椒籽、红花椒皮的风俗版画,一方面大量的无言的镜头使沉默的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里不似都市的喧嚣,没有现代人的语言垃圾的侵扰,每个人都静静地,沉浸于各自至善至美的心事,梦娇之珍藏香皂纸,香雪之立坑上试新鞋,父亲之刨木做铅笔盒,用碗茬里的颜料画素朴的花儿,母亲之磨面编席,拣每一颗温热的鸡蛋。最为人所称道的“父女开荒”一段,在拣石头、搬石头的无数次复沓之中,凝聚了父慈女孝、勤劳互助的传统美德和锲而不舍改造自然的精神,是“愚公移山”神话的视觉翻版,长达五分种的铺陈,不仅不觉单调乏味,反而淋漓尽致结实有力。王好为选择的,不是撞击时的巨响而是撞击后的异化和思辨,而是“前撞击状态”宽容的启蒙,当现代文明已是一个巨大的在场的时候,让已趋浮躁疲惫的我们看到一份久违了的期待的甜美、憧憬的幸福和轻易的满足,那么清新、健康,让人留连不去。王好为巧妙地进行了古老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又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净化”的使命。
和《哦!香雪》做为一次厚积薄发如期而至不同, 《离婚》带给我们的是一份惊喜。王好为的镜头离开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城市乡村,第一次转向旧中国。随着摄影机镜头,摇过漫画般堆着笑,一本正经而又自作聪明应酬着的人们,我们的目光渐渐有些温情地凝聚在一个人——一个看上去方正克已,带敏感气质而略有苦楚之色的普通人,小人物老李身上。我们情愿他因他的“苟活”却“不甘心”而成为正面人物,但他终于力不从心,因“不甘心”却依然“苟活”而不堪此重负。他“不甘心”妻的俗,念《荷塘月色》给她听,却因她无心领会这份“诗意”,一心惦记孩子待补的裤子和炉上烧开的水而做罢。妻仍止于俗,然而开水不能不灌,裤子不能不补,于是“苟活”。他“不甘心”象同事一般昏昏噩噩,因而兢兢业业准时上班,不意却迎来更为昏噩的所长之青睐,升迁之传闻与同事之谄媚,虽“视之若敝履”而不能弃,于是“苟活”。他“不甘心”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出面出力为张大哥救子。如此豪侠之举却不过是低声下气去求卑鄙之小赵,营救的不过是无用的张天真,报答的不过是主张“婚姻救国”的张大哥。在“苟活”的掌心里翻了跟斗也逃不出“苟活”,于是“苟活”。甚至他的理想——马婶,“好像是一个新女性的样子,好像是有自立精神,想改变现实,实际上,他丈夫回来,尽管那么不堪,结果她还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6〕
于是,第一次,银幕上没有一个闪烁着理想光彩的人物;第一次,暗涩取代了明朗,有为等于无为。这看似一次主流向边缘的涉渡,一个突兀的错位。然而,些微的诧异之后,我们随即明白——其实是早已明白的——正如果戈理所说,笑,是惟一的正面人物。从这部影片,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却更加清晰地看到王好为艺术自我的深层结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表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是“为人生”的艺术传统的直接体现,同时仍表现出“中、正、平、和”的理想对王好为艺术自我深深的渗透。老舍原著的力度与王好为的电影叙事功力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否定的不只是旧制度——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史前史而注定要不彻底的的革命的产物;也不只是孱弱的知识分子,落后的国民性、而是否定一种“惰性”的人生态势,否定将传统文化至大至刚,极高明的中庸之道长期误读为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中主义和苟安主义,排斥“乡原”赞美“狂狷”,为“中、正、平、和”正名。
于是,在“笑”的 哈哈镜前,呈现的是灰色扭曲的群像。有人群,照例有事端,然而这一次,不是老李们与小赵们的遭遇战,而是从摄像机后面向“灰色人生”开动的一次全方位的阵地战,老李与小赵,都未能幸免。尤为可喜的是,王好为于幽默原本就有着得天独厚的感应,除了导演喜剧片,王好为在她的影片中几乎都成功地使用了喜剧因素。此番借助大师老舍的幽默,使“笑”这一正面人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不仅看到张大哥之照相自备镜框,方墩之赴西餐宴等噱头,而且从对老李的不忍嘲谑中,看到老舍原著“含泪的喜剧”之神髓,从对小赵之死的“净化处理”看到王好为不动声色的幽默。小赵被杀,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荡水处,水波荡漾,荷时亭亭,“谋杀”不是血腥暴力,一个人消失反倒息事宁人。我们所熟悉的“淡化死亡”在这里重视并升华。
毫无疑问,《离婚》是一部制作精美的影片。在这部影片中,王好为赋予这旧日京城一个角落的小四合院以一片黄昏时的辉光,一份旧唱片般悠然流转的韵味。虽非挽留,总是一次告别,虽已靠岸,毕竟曾经流逝。那个逝去的世界,象一张发黄的旧照片,在“神话讲述的年代”里人们曾如此这般生活过。每个人都会成为过去,在这个“讲述神话的年代”里,观者诸君,或可也有思索罢。
因此《离婚》不仅不是偏离,相反是一次精巧的对位,它与《哦!香雪》,一正一反,交相辉映,成为王好为艺术人生的点睛之笔。
更值得欣喜的是,现在还远非总结王好为导演艺术的时刻,她正步上她导演生涯的高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部艺术的未了录。我们期待她以她美好的愿望和不枯竭的创造力,为她的作品序列续写更新的篇章。
注释:
〔1〕转引自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
〔2〕马德波《创作与天性-王好为论》,载于《电影艺术》1991年第4期
〔3〕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
〔5〕王好为《<潜网>导演琐记》
〔5〕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
〔6〕宝光《王好为、李晨声访谈录》,载于《电影艺术》1993年第5期
标签:随心所欲不逾矩论文; 王好为论文; 村路带我回家论文; 潜网论文; 离婚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