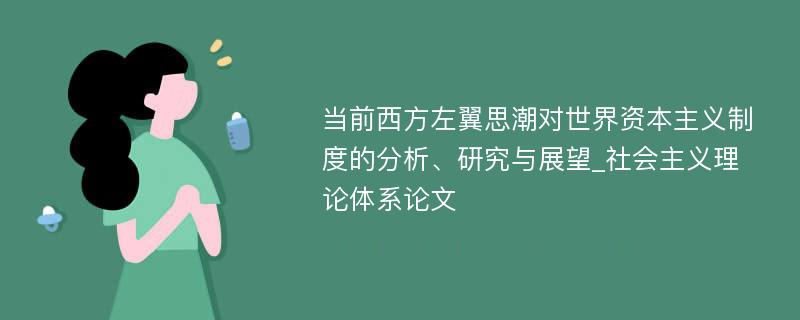
当前西方左翼思潮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研判和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思潮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体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5)07-0081-09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剖析和谋求变革社会现实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冷战结束后,西方主流理论大都指出,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自然永恒的人类制度。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一度沦为极度边缘化的左翼思潮。但2008年爆发于美国、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粉碎了全球化时代的黄金神话。“21世纪的世界简史”似乎一夜之间由宽阔平坦的大路回到了陡峭弯曲的险途,①新世纪初那种弥漫全球的乐观情绪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疑虑或担忧,各种诊断和剖析资本主义病症和问题的论文著述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问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开始重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诊断,重温马克思的理论洞见和历史预言,或者将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性的道路或方案,试图给出左翼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回应。 一、当前西方左翼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若干诊断 2008年世界国际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美元体系为轴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和可能被撼动的危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衰退和萧条的边缘徘徊,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尽管西方主流舆论认为这一体系依然可以运转下去,只是需要进行或深或浅的调整和转型而已。但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越来越普遍地成为西方知识界和舆论界关注的焦点。 (一)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根本原因的诊断 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往往表现为金融危机、信用危机或债务危机,但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代表现形式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基本分析。 2008年之后,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分析纷纷出现。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于2009年出版的《僵尸资本主义》(Zombie Capitalism:Global Crisis and the Relevance of Marx),就是在2008年危机之后对这场危机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诊断的力作,②作者之所以起名为《僵尸资本主义》,乃是因为该书继承了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是“死者”对于“生者”、过去对于现在、死劳动对于活劳动的支配。③该书指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不是正统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金融部门的过度自由和去管制化所导致的,而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导致危机的因素并没有为后30多年的世界经济繁荣期所化解,而是被其所掩盖、积累或推延——在21世纪的今天的深化和延迟爆发。[1](p.304) 在众多解释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及其经济衰退的左翼著述中,安德鲁·克莱曼(Andrew Kliman)于2012年出版的《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BIG FAILURE:Capitalist Production the Root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④则是一部恢复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LTFRP)——这一规律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效力的著述。与其他左翼学者的观点不同,克莱曼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是否成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如果这一规律不成立,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再具有脆弱性,就没有必要废黜资本主义体系;那么,被危机提上日程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案,而是凯恩斯主义的方案。[2](p.67)克莱曼的《大失败》的基本意义,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利润率下降规律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力,因而也就恢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判断,使得“克莱曼的理论在当前众多关于危机的解释中脱颖而出”。[3] (二)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表现形式的分析 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实体和金融资本严重的过剩积累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初系统性危机出现以来,伴随着利润率的深层次问题,资本主义出现了一次新的长期过剩积累期。这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入上升阶段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的转折点,爆发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并非单纯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进入所谓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的作用进程,而是标志着这一长波周期的结束,标志着衰退、萧条和危机的真正来临。[4]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等左翼学者就在探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未来是否会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那种渐趋停滞的、日益靠债务杠杆的金融和信用活动来支撑的经济,是一种无法自我修复的制度,由此所引发的问题必然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在30年后的今天,这些学者的论证可谓“一语成谶”,“资本主义经济的失败”已经成为今天的根本事实。[5]对于这场危机,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撰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的实体性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实体经济的停滞意味着经济生活日益依赖金融业务的扩大与货币资本的积累,“金融化是资本应对实体经济停滞的措施”,但金融化根本无法脱离实体经济的约束无限制扩张,所以,“金融化的危机不过是实体经济停滞的外化”,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金融化和虚拟化必然导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美国和世界金融危机。[6] 这场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债务危机,所以,对债务资本主义(indebted capitalism)的批判也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债务纽带——反对公共善的借贷》一书中指出,债务不仅是一个狭义的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广义的社会概念。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债务是攫取的工具,也是人与人相互依赖关系的纽带和渠道,“一切未来之道都是借助巨大债务的叠加”,债务在不断的资本化乃至货币化的自我增殖中,本身就蕴含着无法自我偿付的危机,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途径或方法,用以克服债务体系带来的偿付危机。[7] (三)对资本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反思 在反思资本主义的金融、债务和衰退危机的西方舆论中,越来越多的文章在关注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也提出了或保守或激进的各种形式的替代方案。 一是以温和的立场谈论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修正和适度的调整。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显而易见: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全球化的金融危机、各种反全球化和反资本主义的运动,等等。因此许多学者指出,尽管世界历经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没有节制的过度的资本主义”越来越被视为造成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防止“过度的资本主义”,使这一体制变得有节制,有社会、环境和人文的包容性,从而克服自身的弊病,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普遍繁荣的有效机制。[8]美国学者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和琳恩·罗斯柴尔德(Lynn F.Rothschild)撰文指出,资本主义把世界经济引向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也存在着严重的机能不良,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那么资本主义便会陷入危险境地,随之消失的将是人类对经济增长和繁荣的热切憧憬。因此,资本主义必须变革它自身的模式或运行机制,将其变更为诸如自觉资本主义(conscious capitalism)、道德资本主义(moral capitalism)和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9] 二是以激进的立场谈论资本主义的病症、问题和可能的替代性议程。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4年8月刊文分析,21世纪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金钱游戏横行和金融日益庞大,不仅如此,21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呈现出它的衰落或终结特征:其一,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中心”扩张或增殖的“周边”空间;其二,利率的低下标志着资本的利润率极低,资本很难进一步扩张和自我增殖。这两点表明资本主义已经遭遇自身的局限,不得不面临模式转换的问题。⑤西班牙《起义报》2014年刊文指出,21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15年,目前的情况是:世界资本主义正在面临彻底终结的危机,这场危机很可能引发一场普遍的战争,同时导致环境问题的恶化,但也可能催生一个新的世界。“缺乏资本主义替代模式”的撒切尔主义已经被西方世界各主要社会主义政党所接受,导致共产主义和其他左翼政党陷入孤立无援状态。如果中国能够摆脱新自由主义陷阱,防止市场无序状态,并将重点放在谋求中国和世界的福祉上,那么,中国将会在西方左翼的重新定义中发挥主导作用。[10] 二、当前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的洞见、预言和方法的重温 在西方世界,每当资本主义疲态尽显,马克思的幽灵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复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左翼的社会替代方案总是或隐或显地回到政治的前台和舆论的中心。2008年以来,西方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开始重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与诊断、理论洞见与历史预言。 (一)对马克思主义时效性的理论辩护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潮,它曾经是一场世界性的社会政治实践。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式微,尤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了历史的古董。然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雄辩地证明了我们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问题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愈演愈烈。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英国《金融时报》在2011年刊登的一篇书评中写道:“如果马克思将成为新世纪的‘下一个大思想家’,那么,就有必要对马克思给出一个真实的评价。”[11] 对此,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2011年出版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时效性、理论本质和政治等问题展开专门论述。在该书中,作者总结罗列了十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常见的批评,并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或回答,以“申辩”的方式阐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甚至有人干脆将伊格尔顿罗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个问题及其相应回答称为理性回归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十诫”。⑥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是少有的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思想家,他“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他的不可超越的贡献就是“对资本主义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12](pp.2、6-7)当代的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反全球化等激进运动,尤其是反资本主义运动,它们根本谈不上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根本性的决裂,在根本上也都没有超越马克思,反而都是从马克思那里汲取力量,在各自的视域内都无法回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反而是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所以,马克思仍然是我们同时代的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同时代的思想。 在一次访谈中,伊格尔顿明确指出:“让马克思主义或至少社会主义回到议程的因素是资本主义危机。”⑦因此有学者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13]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洞见的理论重温 2008年之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洞见和历史预言,已经不仅是左翼思潮的重温对象了,而且也成了西方主流媒体的话题。2014年,美国《纽约时报》专门发表一组题为《马克思说的对吗?》的笔谈,⑧围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判断和预见展开对话。 这组笔谈指出,21世纪以来,马克思声称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诸多力量——财富的集中与全球化、失业的长久持续、工资的下降——再度成为令人不安的现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看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实。21世纪的世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回归,倘若不采取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就很难理解当前令人沮丧的经济现实;同时,如果我们无法开出医治资本主义的药方,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就会不幸地成为当下的现实。所以,马克思尽管是19世纪的思想家,但马克思预见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认识到金融资本主义对整个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和它的破坏潜力,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衰退和经济危机,这都是极富洞察力的。 回顾和重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论断的另一主要表现,就是一些西方学者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的特征、病症、危机的成因及其表现形式。此外,葡萄牙学者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在《马克思的理论、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废黜》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不是相同状况的永恒循环,而是一个历史的驱动,每一次危机相比前一次危机都是在具有更高的积累率和生产力的前提下爆发的,每一次危机都呈现出新的特征,但是资本主义始终有它的内在限制,这一内在限制就是资本本身。[14]所以,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动力、矛盾和内在限制的理论,它对于今天资本主义的特征、动力机制、矛盾,以及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的分析具有永恒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拓展的空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自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同样也是未完成的”,有待后人继续书写。[15] (三)《21世纪资本论》——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致敬 近几十年来,世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而且在可以预测的将来,这种状况还将持续恶化,马克思所说的“财富的积累”必然伴随着“贫困的积累”这一资本主义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越演越烈。21世纪的历史正在向19世纪回归,正在倒退回“世袭资本主义(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时代。这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013年出版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描绘的灰暗前景。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以资本与不平等为主题的著作。该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核心主题就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几个经济变量或等式,来分析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3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差距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U字的变化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存量的提高,贫富差距反而是扩大了。皮凯蒂所揭示的这一基本事实恰恰是对库兹涅茨倒U字曲线(Kuznets curve)、卡尔多特征事实(Kardo's Stylized Facts)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等均衡模型的证伪和否定,从而向主流经济学的流行信条发出了挑战。皮凯蒂的研究还发现,真正通过劳动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人群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存在。这就意味着,唯有在极高的资本或财产存量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极高的收入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资本论》揭示出“我们正在倒退回世袭资本主义的年代”。⑨在这一时代,社会的阶层已经被固化,基层民众已经很难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社会的层级流动和代际流动的停滞,必然会带来社会活力的下降,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不平等螺旋”在社会层面的危机效应。 《21世纪资本论》自2013年8月出版以来,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不经意间引来了东西方各国知识界的热议和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称该书引发了“皮凯蒂恐慌”,《纽约时报》先后发表3篇书评来评论“皮凯蒂现象”,甚至有刊物发表评论,将皮凯蒂与马克思、李嘉图等人相提并论,称之为“当代的马克思”⑩或“当代的李嘉图”,(11)因此《21世纪资本论》也是向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致敬。 三、当前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之替代性方案的展望 社会主义作为对科学和人道等启蒙价值的继承,它源于对资本主义矛盾、危机和问题的剖析或诊断。唯其如此,它才能作为现代性的理论、政治和历史实践,给出变革不合理的现实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诸种社会主义方案。所以,伴随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之替代性的议程、制度和方案,又开始由边缘性的话题上升到各主要思潮和舆论的焦点。 (一)数字社会主义或网络共产主义 随着互联网、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与3D打印技术的兴起,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或“工业4.0”等所展现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机器自组织化等产业前景,激发了西方左翼思潮对于数字社会主义的想象,对于网络共产主义这一替代性方案的探索。 对于数字或网络等新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理想的实现,英国学者理查德·巴尔鲁克(Richard Barbrook)在《高技术的礼品经济》(The Hi-Tech Gift Economy)一文中有着比较经典的分析。[16]他指出,数字技术所成就的经济其实是公共品经济,信息和知识是典型的公共品,这种形式的公共品一旦上升为生产要素,就成为不断积累的知识资本或社会资本,而这种资本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共享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产品都是私人的和排他性的商品,但在数字化的礼品经济下,信息和知识等数字产品大都是公共性的和共享的社会产品。所以,数字化催生的经济的这种“共享”状态将使资本主义受到越来越明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演变”,逐渐进展到“网络社会主义和数字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致使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的“数字鸿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合作”的“数字共享关系”。 巴尔鲁克的“礼品经济”或“公共品经济”所阐述的数字或网络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社会资本主义”,或者是“智本(知识资本或社会资本)主义”,在这种主义中,资本的或智本的就是社会的,传统的资本与社会的对立因为“智本”的出现而真正消解。 2009年,美国《连线》杂志(WIRED)创刊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封面要闻里写了一句话,即“数字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除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中央集权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它使过去的争辩变得毫无意义”。他在《新社会主义:全球集体主义社会正在上线》一文中将其描述为一个“非资本主义的、资源开放的、基于普通人的集体生产的”新的社会;随着教育、医疗、保障和其他线下服务都走上云端的那一天,网络数字技术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数字技术的出现和资源的公共化,它使得“自由市场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传统解决办法渐趋失效,使得那种基于“合作的、共享的、开放的、自由定价的和透明的”“经济和社会形式得以可能。[17]对于凯文·凯利和他的《连线》杂志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或网络共产主义”,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刊文将其称为“新的数字社会主义或点击共产主义”。(12) 数字社会主义或网络共产主义给出的一个诱人的前景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挑战时可以逐步缩小“数字鸿沟”,缩小在财富和知识上的差距,以谋求全球社会共同发展、共同受益和共同繁荣。当悲观主义者认为信息化是资本主义化和西方化时,一小部分乐观主义者却认为信息化是共产主义化和世界化。如果把“数字鸿沟”放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看,它的焦点问题就是:信息化成为现代化的最新内涵,它究竟是造成通向全球资本主义的“数字鸿沟”的分化和两极化加大,还是造成走向“信息共享”和“数字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数字社会主义或网络共产主义将新社会的理想寄托于知识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发展,它秉承了古典的启蒙理性对于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信任,认为知识的进步、技术的发展,最终会带来社会的繁荣、道德的改善和人类的幸福。这一信念也深深影响了社会主义传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圣西门就确信,知识和新技术发展的最大潜力是不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实现的,而是对于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突破和改写。 不过,对于耽溺于信息和技术想象的诸如共享经济、数字社会、网络社区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潮,也有学者提出了批评。美国《新共和》杂志编辑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就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或“网络共产主义(website communism)”是在华尔街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悬殊之际,硅谷的技术精英开出的“一剂完美的解药”,试图“帮助弥合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伤痕”。但这只是一个童话,在社会资源不平等配置的现实前提下,互联网提供的这种资源的共享平等使用,更多时候会加剧而不是缓解社会总体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你把硅谷开创的未来世界叫做什么,‘数字社会主义’显然不是个恰当的名字”。[18] (二)生态社会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生态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的体制性问题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人们对于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一直在上升。尤其是2012年以来,在诸如“生态主义”、“生态正义”、“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等标签下,舆论对国家、市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资本主义体制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与分析批评。 一是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生态问题,将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视为资本主义危机和问题在自然、环境、生态领域的表现,从而引申出对于生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寻求对生态问题的替代性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生态社会主义萌芽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和论述,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形成了一支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思潮。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对于生态危机的原因分析。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而非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进步,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资本只有不断进行扩张,才能维持利润增长,但是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因而“生态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整体上表现出的相互作用”。[19](序言p.1)第二,对于生态危机出路的分析。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资本主义本身并不能克服生态危机,克服危机的唯一出路和最佳选择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只有在生态学的意义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才能超越经济理性,服从或回归生态理性。[20](p.32)《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作者、美国学者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在2013年12月撰文指出,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巴西,它的核心观点就是“资本积累,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功能是生态危机的原动力”。它源于“资本的最基本的特性,即由‘自我增殖(self-expanding value)’所组成,在货币流通中通过商品交换表现出来的有效原则”,因而资本主义的自我生产、增殖和扩张模式最终导致自然界和人类文明陷入毁灭的深渊。生态社会主义要求在理论和最终的政治实践层面超越资本原则,解放劳动,恢复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力,“通过整个生态系统的生产阐释置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21] 二是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经济学。这一思潮与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它试图从现存的市场、国家和资本主义体制内寻求生态和环境问题在经济层面的制度或技术解决。从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并非截然对立,我们可以在制度、操作或技术上通过市场、价格和产权机制,创新生态产品,定价生态资源,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形成囊括生态文明的绿色资本主义。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零边际成本社会:物联网,协同合作与资本主义的消失》(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The Internet of Things,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一书中分析指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我们所熟知的、那种被类型化的资本主义不是终将消失,而是正在消失,“它在很多关键领域正在消亡”,随着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出现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一种更加崇尚分享和共享的合作经济模式正在出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合作的或共享的资本主义,“它高于传统的竞争的产生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在这一合作共享的资本主义模式中,自然、生态或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给予有效解决。(13) 针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诸种方案,美国学者理查德·海因伯格(Richard Heinberg)指出,关于替代经济模式总是有价值的,但它们“在较大维度上很快被接受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22](p.247)澳大利亚学者凯拉·廷哈拉(Kyla Tienhaara)在《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2014年第2期撰文认为,绿色资本主义(green capitalism)所提出的议题是,现代市场、国家和社会所驱动的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而且也有生态现代化的议程。绿色资本主义有着各种版本的倡议,诸如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绿色刺激(green stimulus)、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等等。这些倡议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资本主义模式,它们之间的差异一般体现为“国家干预市场的不同”,在市场、国家、金融部门、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不同的权重或侧重。[23] (三)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社会主义是消除社会不公正的最佳解毒剂。然而自19世纪以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矫正的历史实践并不理想,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实践的突然终结,迫使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不得不重构蓝图。所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主要流行三大社会主义思潮,即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以及随着网络和新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诸如数字社会主义或网络共产主义,等等。在诸如此类的理论、观念和思潮中,21世纪的社会主义应当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轮廓?或者说,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以何种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或替代性版本,在21世纪将会在什么样的历史和政治主题下分享各自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些问题都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法回避的基本议题。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西方左翼学者近年来有了新的思考和探索。爱尔兰学者维多里奥·布法切(Vittorio Bufacchi)在《社会不公正:政治哲学论文集》(Social Injustice: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一书中集中讨论了21世纪西方的社会主义几大主要思潮所分享的基本历史和理论主题。(14)作者指出,在过去20多年间,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创造性和深度方面都带来一些显著的成效,形成了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这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自由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左翼形式。这一思潮认为,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道德理想,达成这一理想的最佳途径是自由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因而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尤其在把握社会公正问题上存在着一致性。其中,罗尔斯所构建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论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拥有共同的平等理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其实是民主在整个社会领域的自然延伸,它将基于自由、平等、合作和团结的民主原则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国际乃至生态自然领域,而不是局限于政治社会或国家,因而要达成全方位的真正民主,就必须首先信仰社会主义,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来自对民主的信仰。 三是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社会化思潮是近年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的最具争议性的思潮。这一思潮一反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观点——左翼将社会主义视为对市场或资本主义体系的废黜,右翼将市场视为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结——将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体系结合起来,以践行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理想。 维多里奥·布法切认为,这三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既非完全排斥,又不完全等同,它们都有共同的核心观念——平等原则、团结和共同体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的支柱。 对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对此,日本学者伊藤诚在《21世纪和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到处充斥着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到政治危机等各种灾难性的危机,我们必须反思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种种思潮和实践。古典或现代经济学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基础,其弱点在于无法洞悉“资本之谜”,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实践所要解决的核心议程,没有对“资本之谜”或“资本主义问题”的洞察,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就无法找到科学的理论基础。[24]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与罔顾资本主义问题有着内在的关联。苏联的失败往往被认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然而在探求“资本之谜”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恰恰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所继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以,该文认为,在展望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中,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不能缺席的。不论是民主的、市场的或生态的等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还是诸如此类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协同,它们倘要找到自身的理论基石和实践的发力点,就必须在理论议程上回到马克思主义。 ①这主要是针对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和美国学者戴维·斯密克的《世界是弯的》这两本分别在金融危机前后疯行的畅销书而说的。前一本书站在“21世纪简史”(该书的副标题)的高度宣告经济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的来临;而后一本书却令人忧虑地展示了全球化时代作为“21世纪简史”,隐藏着各种暗礁和风险。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世界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世界不再是平的”,人们不得不反思,“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得全球化的世界“在前一分钟运作良好”,“而在接下来的片刻之间,世界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参见[美]戴维·斯密克:《世界是弯的》序言,陈勇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Lee Sustar,"What are the Roots of Capitalist Crisi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August 2014. ③马克思在他的著述中就将资本主义比喻为吸血鬼(vampire),“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所以,哈曼将资本主义体系比喻为“僵尸”,他的著作就是揭示这一“僵尸体系”的历史和本性,继而形成一个完全维护马克思理论的相关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④1989年,布热津斯基(Kazimierz Brzezinski)出版了《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THE GRAND FAILURE:The Birth and The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宣判了共产主义的失败,其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史似乎永远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克莱曼出版的另一种版本的《大失败》(BIG FAILURE:Capitalist Production the Root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却是在宣判资本主义的失败,重新复活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危机而最终走向失败的基本论断。 ⑤引自[日]寺岛实郎、水野和夫:《资本主义的局限于未来》,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4年8月19日。参见《参考资料》2014年第167期。 ⑥参见《先知马克思归来,“十诫”的理性回归》,《凤凰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第81期。 ⑦参见Alexander Barker & Alex Niven,"An Interview with Terry Eagleton," The Oxonian Review,4 June,2012.Issue 19.4 ⑧Doug Henwood,Michael,R.Strand,Eve.Smith,Tyler Cowen,“Was Marx Right?-Room for Debate," http://www.nytimes.com/,March,3,2014. ⑨引自[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正走向拼爹时代》,《纽约时报中文版》,2014年3月24日。 ⑩引自"Capitalism and Its Critics:A Modern Marx and Bigger Than Marx?" The Economist,May.3.2014。 (11)引自Tyler Cowen,"Capital Punishment:Why a Global Tax on Wealth Won't End Inequality," Foreign Affairs,2014.No.5-6。 (12)引自Kevin Kelly,"WIRED:New Digital Socialism and Dot-Communism," www.aei.org.February,29,2015。 (13)参见Jeremy Rifkin,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The Internet of Things,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Palgrave Macmillan,April 1,2014。 (14)参见维多里奥·布法切:《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选自维多里奥·布法切:《社会不公正:政治哲学论文集》,洪燕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标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美国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