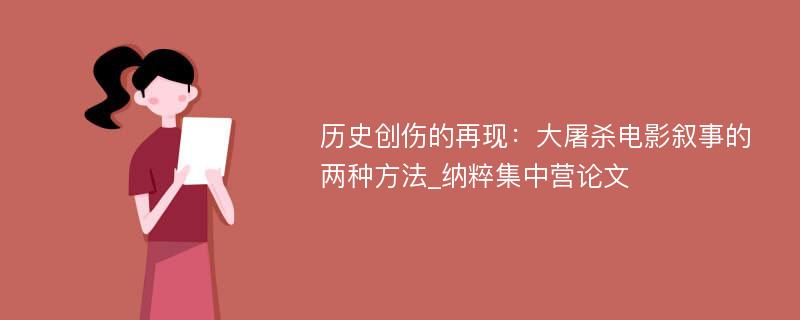
历史创伤的再现——大屠杀电影叙事的两种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创伤论文,方法论文,历史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创伤与艺术传达之难题
人类自诩为有别于动物的最高级存在,但纵观历史长河,却可以从中发现人类自相残杀的种种绵延不绝的惨象。由此联想起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对人类的绝望使他居然将野猢(yahoo)即人类列为比诸如马之类的动物还要低等的物种。然而斯威夫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人类自相残杀的事件却越演越烈,其残酷的程度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至于即便以艺术的手法对之进行再现,依然会令人不寒而栗。然而再现历史真相始终是历史学家、思想者和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不过,也正如一名犹太教哈西德派拉比所说:“有些真相由言语就可以传达,有些更深层的真相却只能由沉默来传递;而在另一层面上,则有一些真相连沉默都无法去表达。”①拉比的断言迫使人类不得不面对语言、影像等媒介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媒介的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以有限的符号表达无限的内容,因此这一功能本身就是悖谬的,它注定了媒介无法完全、精确地再现世界的纷繁无序与人心的复杂多样。古今中外,许多哲人从各种角度讨论过这一不可再现的再现所面对的艰难。亲历过纳粹迫害的哲学家阿多诺就深知,苦难并不容易得到表达。大家都知道必须承认苦难的存在,要想法为苦难留出空间,但问题是,每当我们试图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苦难的时候,苦难始终无法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因为进入概念之中的客体永远都会留下一些残余。在苦难的概念化过程中,总是有些东西不被听到,得不到表达。在阿多诺看来,难言之痛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行为。他说:“有必要让苦难发出声音,这是一切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是一种客观性,它沉重地压在主体之上;它的最主观的体验,它的表达,是要以客观的方式来传达的。”②根据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人类体验是无法化约为概念和范畴的,但人类的状况却是由这些概念和范畴界定的,它们就是人类所能认识的东西。与此同时,那幽灵般纠缠着概念化的非同一物使得我们无法通过表达来触及真实本身。无论我们有着多么高超的叙事技巧,在人们的痛苦体验与所能表达出来的东西之间,永远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比如我们无法保证痛苦体验与痛苦述说之间能够完全同一。“当前,每一种表达行为都在歪曲真理,出卖真理。同时,无论用语言做什么事,都会蒙受这种悖论之苦”③。
更严重的是,除了媒介自身的痼疾和再现者自身的能力之外,还存在着别的危险:叙事方式的常规化和模式化。“大屠杀文学”研究专家劳森菲尔德指出,此类作品已经呈现出一套为人熟知的文学程式(formula)。读者能够迅速地、轻而易举地从中辨认出整个模式来,比如:“战前的常态生活与麻烦的即将来临;反犹太宣传攻势的启动以及人们的宗教般的热情;起初针对少数人后来针对多数人的威胁;恐怖行为的官僚化以及不断发展的‘罪恶行为的平庸性’;奴役般劳作的剥削与拐卖儿童的出现;无处不在的疾病与饥饿;各种打击行为以及抵抗的暂时性表现;集中营;尸横遍野;少数幸存者等等。”④这些程式的形成严重威胁到创伤文学的可信度,因为任何掌握了这些手法的人都能够写出一部催人泪下的作品,但这样按照程式创作出来的作品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阉割,是对人类眼泪的亵渎。
历史创伤的再现还面临另一个危险,即艺术传达很可能会将残酷的场面审美化和娱乐化。这种危险使得艺术家在再现血腥场面的时候就特别谨慎。比如英国作家艾米斯(Martin Amis),在他的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小说《时间之箭》(Time's Arrow)出版后,他在访谈中提及自己选择这个主题时说:“我自己都纳闷,这怎么成了我的题材。如果两年前你问我,我是否会写关于大屠杀的东西,这是我一直都感兴趣的东西,但我会说,在还活在世上的作家当中,我或许最没有资格做这件事的人。”⑤艾米斯出生的时候,大屠杀早就结束了,但是大屠杀事件一直折磨着他,因为他和那些作恶者都是雅利安人,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是“兄弟”,所以他说:“我觉得,身为雅利安人,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责任。那是我与这些事件之间有着种族上的联系。它不是与受害者的联系,而是与作恶者的联系。”⑥为了摆脱这种纠缠着他的负疚感,艾米斯动笔写了这本关于奥斯威辛大屠杀中的作恶者的小说。然而,为了避免粉饰罪恶,为了避免让自己的负疚感娱乐化,艾米斯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做法,采用时光倒流的彻底逆序的手法,阻断读者的阅读快感,迫使读者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和理性思维能力来重构事件的发展以及作恶者的一生经历。艾米斯希望籍此引领读者一起反思人类文明何以走向人类大屠杀。
因此,选用哪种恰当的手法来再现苦难、诉说创伤,就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本身的纯技术问题,而是关涉到道德伦理的问题。
二、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与真实
纳粹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民族进行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共有超过六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与之前的各种大屠杀相比,纳粹大屠杀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集中营的建立。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兴建了六个杀人的集中营,当中的地点包括奥斯威辛(Auschwitz)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落实“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后,纳粹德国开始在这些集中营中用氰化氢气屠杀犹太人。大屠杀的另一特点,就是当时纳粹德国官僚机构的几乎每一个分支都卷入了大屠杀的后勤服务之中,就是说,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在为这场大屠杀服务。用一位大屠杀研究专家的话来说,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种族灭绝国家”(a genocidal state)⑦。大屠杀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秘密性。一切都是在秘密中执行的。在由克劳德·兰兹曼(Claude Lanzmann)导演的纪录片《浩劫》(Shoah,1985)中,有个曾担任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警卫的受访者是这样描述集中营的:
带刺的铁丝网与松树的枝桠缠绕在一起……被称为“伪装”……这样,所有的一切都被遮盖起来了。人们无法看到左边或右边的任何东西。什么也看不到。你无法看穿。根本不可能。⑧
大屠杀的秘密性不仅在于集中营的隐蔽性,更在于其对证人的消灭。所有被关进毒气室的犹太人都被毒杀,连他们的尸体都被烧得一干二净,失去其可见的物质性。更不可思议的是,纳粹德国甚至不准人们使用“尸体”一词:“德国人甚至禁止我们使用‘尸体’或‘受害者’之类的词语。死去的人是木头,是狗屎。德国人要我们用‘人体’(figuren)来指涉那些尸体”⑨。德国人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以至于连毒气室的存在都被掩盖得严严实实。铎利·劳布(Dori Laub)甚至说大屠杀“没有证人。实际上,纳粹不仅努力灭绝其罪行的物质性证据,而且这一事件固有的不可思议的、欺骗性的心理结构也阻止了见证”⑩。结果,甚至有不少严肃的历史学家也质疑这些毒气室的存在。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弗里逊(Robert Faurisson)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1)。事实上,有不少历史学家甚至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存在(12)。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因此发出这样的哀叹: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居然有上百种书籍在传递这样一种思想:大屠杀是虚构故事,它从未真正发生过,纯粹是犹太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而编造出来的。(13)
屠犹事件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在此,我们不想纠缠于这个问题上,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根据铎利·劳布的叙述,一位六十多岁的妇女在耶鲁大学大屠杀证词档案中心讲述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经历的一场犹太人起义的经过,讲着讲着,她激动起来:“突然,我们看到四根烟囱冒出火焰,爆炸了。火焰直冲天空。人们到处乱跑。真不敢相信。”劳布接着描写当时房间里的情形:“整个屋子安静下来,而这个妇女的话则在这死寂中大声回荡……这不再是奥斯威辛的死一般的永恒性。炫目的、非凡的时刻从过去像流星般扫过凝结的、寂静的、坟墓般的大地,进发为洋洋洒洒的景象和声音。”(14)然而,几个月后,耶鲁大学召开了一次由历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艺术家参加的学术会议,与会者在观看完这个妇女作证过程的录像后开始了激烈的辩论。有历史学家指出,该妇女的证词不准确,因为烟囱的数量与实际不符,只有一根烟囱爆炸了,因此她的证词是不可信的。铎利·劳布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重要的不是有多少根烟囱爆炸:
在奥斯威辛,一根烟囱爆炸也好,四根烟囱爆炸也好,都同样让人难以置信。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爆炸的事实……这位妇女借助自己的证词打破了集中营的框限:她的讲话本身就使她冲出了奥斯威辛。事实上,她不是来证实烟囱的实际数量的,而是来证明抵抗行为,证明生存的肯定意义,证明死亡框限的被打破的。(15)
就此事件而言,历史学家与精神分析学家铎利·劳布的不同反应实际上关涉着如何再现大屠杀历史真相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要追求精确的历史真实性呢?还是要从有限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再现中重新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三、现实主义方法
前面所说的问题显然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按罗斯伯格的观点:“所谓的现实主义,我指的不仅是认为大屠杀是可知的这样一种认识论主张,也指一种再现性主张,即这种知识能够转译为熟悉的摹仿空间……所谓反现实主义,我指的不仅是那种认为大屠杀是不可知的、或只有在全新的知识领域中才可知的主张,也指的是大屠杀无法按传统的再现模式来捕捉。”(16)罗斯伯格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归为前一类,而将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专家归为后一类。就艺术而言,对现实主义手法的追求,就是力图以图像、声音、文字等手段来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惨景。然而,要说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应该是纪录片,但对于大屠杀而言,纪录片同样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就是说,绝大部分图像资料都是源自于施害者纳粹分子。有部分纳粹士兵拿起了照相机或摄像机,但他们或想自我娱乐、或想给亲朋好友留影纪念、或服务于戈培尔的宣传。总之,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可能忠实地记录一切,他们的镜头是不可信的。诚然,大屠杀受害者的态度是可靠的,但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可能去记录,因此,这个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也不可能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么,我们所关注的现实主义艺术,恐怕只能是指那些努力追求“按照事物所是的样子来描绘事物,就是说要客观地、具体地描绘实际生活的可观察的细节”(17)的艺术作品。
具体到关于大屠杀的艺术作品,人们追求的是要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出德国纳粹分子是如何残酷屠杀犹太人的。许许多多艺术作品都试图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影视作品。它们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强调客观性,力图尽量少地人为干涉事件的呈现,让这些酷烈场面自然而然、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让人震撼不已。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就曾指出:
对恐怖所作的镜像反映就是目的本身。由此,这些镜像召唤观众领会吸收,并因此将那些由于太可怕而在现实中不忍目睹的事物的真实面貌融入记忆之中。通过对电影中杂乱堆放在纳粹集中营中的遭受过酷刑的人类肢体……的体验,我们得以将恐怖从其隐藏在惊惶和想象的面纱的不可见性中重新释放出来。(18)
在对纳粹大屠杀的再现方面,影视作品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包括笔者本人,主要是通过屏幕画面来认识纳粹、犹太人以及前者对后者所施行的种族灭绝行动的。在这个世界上,偷懒的人从来就不在少数,愿意一头扎进历史复杂性中挖掘事实真相的人绝对不多。杰弗里·山德勒(Teffrey Shandler)在他的《美国在收看:电视与大屠杀》(While American Watches:Television and the Holocaust)一书中证明,许多年来,电视将有关大屠杀的认识带入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他认为:“从最早开始,电视就为美国观众把大屠杀树立为熟悉的事件而起到了建构性的作用。”(19)山德勒指出,在电视处理大屠杀事件的历史中,有两件事可谓“主要的分水岭”:1961年阿道夫·艾克曼大审判在美国首都城市广播公司(Capital Cities Broadcasting Corp.,ABC的前身)电视转播以及1978年4月NBC《大屠杀》(Holocaust)系列剧的播放。这两次播放最终使得大屠杀成为美国公共文化中的常客。由于前者是对事实进行报道,所以我们在此不打算多做讨论,而只把注意力放在《大屠杀》这部四集文献电视系列剧之上。
《大屠杀》由马文·乔姆斯基(Marvin J.Chomsky)导演,詹姆斯·伍兹(James Woods)、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迈克尔·莫拉蒂(Michael Moriary)等主演。该剧以一个与雅利安人通婚的犹太人家庭1935年以后的十年遭遇为主线,全景式地再现了德国纳粹兴起、华沙起义、纳粹屠杀计划的“高效”、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酷烈场面、隐蔽在森林中进行抵抗的游击队员等等。应该说,这部系列剧在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震撼了无数西方人。据统计,超过两亿人观看过这个节目。仅在当时的西德,就有一千五百多万人。该片的高收视率说明,有相当多的人对纳粹大屠杀的认识受到它的影响:
从现在开始,美语单词“Holocaust”丰富了德语。该词涵盖了犹太人种族灭绝事件、该文献电视片及其私人化的悲剧故事,以及该片所激发的情感与政治反应等等意义。这五天的集体情绪似乎已经使得年轻一代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奥斯威辛创伤及犹太人。这一角度可称为“大屠杀教学法”。(20)
但是,尽管这部片子可能实现了克拉考尔所说的功能,尽管无数人从中深刻地理解到大屠杀的残酷可怕,但它依然遭到许多批评家的攻击。《纽约时报》的电视批评家奥康诺(John J.O'Connor)尖锐地指出:“这个事件(指纳粹大屠杀——引者)要求情感的高强度以及尖锐的洞见。NBC的《大屠杀》这两者都没做到。”(21)一家德国杂志撰文批评道:“《大屠杀》作为文献电视片模糊了事实,将事件琐碎化,既未启迪又未迫使人们思考这些事件。”(22)这些批评指出现实主义手法的悖谬。事实上,无论艺术家如何客观,想要将可见的世界编织进艺术作品中,主观建构永远都会存在。人为地掩饰这种主观建构,必然会带来极大的问题。著名的剧作家查耶夫斯基(Paddy Chayesky)曾经以强烈的反讽口吻挖苦《大屠杀》:“我说,这个体裁太让人痛苦了,我无法写。不过如果我要真的同意去写电视剧,那我也会不得不把它写成一部肥皂剧。你得写出情绪强烈的场面,有规律地,因为你一直都有该死的十分钟广告间隔时间。你永远也无法真正积聚力量;你得将许多情感凝练起来,你得过分戏剧性地表达事情。事实上,批评家就是用‘琐碎化’一词来评价《大屠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公平的批评,尽管很准确。琐碎化就是电视的本性(Trivialivation is television)。”(23)这段批评使得自诩在追求客观再现大屠杀事件的编剧和导演感到难堪。的确,煽情、琐碎化的做法绝不是在追求客观真实。
不过,在众多批评者中,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是影响最大的。作为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大屠杀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德国犹太作家,对大屠杀事件的艺术再现,他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就在NBC播放《大屠杀》之后不久,他在记者采访时说:
(该片)是虚假的、伤害人的、廉价的……是对那些已经死去或存活下来的人的一种侮辱……它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事件转化为肥皂剧……我们看到犹太人排成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队伍走向巴比山谷……我们看到倒在血泊中的裸体死尸……可这一切都是假的……大家会说,同样的技巧也运用于战争电影和历史娱乐中。但大屠杀是独特的,而不是另一个事件……这部片子将大屠杀处理为另一个事件而已。奥斯威辛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也是无法得到形象化的。大屠杀超越了历史……死去的人握有的秘密,是我们活着的人不配、也无法找回的……(24)
威塞尔的批评深刻地指出了现实主义手法面对真实的大屠杀时的尴尬。无论人们怎么费劲地想方设法重现过去的场面,都难以描绘这场浩劫的独特性。这些批评深刻地指出了影视作品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再现大屠杀时的苍白无力。
四、非现实主义方法
那么,纳粹大屠杀是不是就无法被再现?不!即便严厉的威塞尔也认为:“有别的方法,有更好的方法来维系记忆。如今,问题不是要传递什么,而是怎样去传递。”(25)他列举一些成功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法国导演阿伦·雷奈(Alain Resnais)于1955年拍摄的《夜与雾》(Nuit et brouillard)。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Francois Trauffaut)大概在二十年之后如此评价说:
《夜与雾》是一部杰出的影片,讲述的是难以讲述的事情。我们几乎不可能用电影批评术语来谈论这项作品。它既不是纪录片,也不是控诉,也不是诗歌,而是对20世纪最重要的现象的一种沉思。这部电影的力量……植根于其总体效果之中:可怕的温柔。当我们看了这些古怪的、七十磅重的奴役工之后,我们就明白,看过这部《夜与雾》之后,我们将无法“感觉更好”,恰恰相反。(26)
其实,雷奈一开始并不愿意接手这部影片的制作,因为他与集中营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在我看来,要想拍摄关于集中营的电影,你得曾经是其中的囚犯,或曾经因为政治原因而被驱逐过。我接手的条件是,由让·凯罗尔(Jean Cayrol)来撰写剧本,因为他本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有凯罗尔作为蒙太奇和图像画面的保证,我就答应去拍摄电影。”(27)雷奈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正如威塞尔所说的:“大屠杀是终极事件、终极神秘,永远也无法为人所理解或传递。只有亲历者才知道它是什么,其他人永远都不可能知道。”(28)雷奈犹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拍摄困难的估计。如果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去模仿,那必然意味着你要将这些支离破碎的、超现实的感觉进行整理,赋予整饬的形式,而这是对死去的人的亵渎。此外,动用知名影星和电影特技效果,必定能够制造出栩栩如生的写实效果,但那是虚假的,而历史的真相无法容忍虚构。
《夜与雾》与前面所说的《大屠杀》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导演毫不掩饰自己的剪辑。事实上,这部纪录片极具个人风格,主要由访谈、田野摄影及新闻短片组成。该片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转换于黑白与彩色之际。整部片子有十四段彩色画面,记录的是拍摄电影时的奥斯威辛,穿插其中的,是十三段时间更长的黑白历史镜头,但它有虚构性电影所具有的叙述骨架、诗意情调,有剪辑的脉动,也有深刻的个人化的画外音。镜头随着一个现代旅游者的眼光,记录了和平年代奥斯威辛的各种风景。不断穿插叠加的,是用蒙太奇手法来展现的堆积如山的尸骨、数不到边的女人的头皮与头发、“死亡之墙”上的累累弹痕。电影并没有以戏剧化的手段渲染暴行,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没有动听的音乐,没有曲折的剧情,有的只是在彩色和黑白的交替转换中,用平静的记录手段,给观众呈现了让人无比震撼的罪恶事实与证据。
《夜与雾》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画面与声音之间强烈的情感对照,包括叙述者在镜头外所作的叙述和背景音乐。当镜头充斥情感效应的时候,比如出现被砍的头时,背景音乐非常柔和,甚至难以听到。当画面非常宁静安详的时候,比如出现奥斯威辛景色时,背景音乐则恰恰相反。这些音乐是由德国作曲家汉斯·艾斯勒谱写的。雷奈是这样解释艾斯勒的音乐的:“画面越暴力,音乐就越柔和……艾斯勒想表明的是,人类的乐观与希望总是存在于背景中的。”(29)雷奈在1966年说过,这配音让人感受到“命运威胁的氛围”。此外,叙述者的声音在追忆、探究、给观众报数据、提供见证的时候,始终是干巴巴的,不带多少感情色彩。当镜头摇摄奥斯威辛全景,并伴随黑白历史镜头时,画外音的叙述是冷漠而又遥远的,与画面令人发指的形象截然相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镜头出现焚化炉废墟、带倒钩的铁丝网、颓败的了望塔和毒气室、坍塌破裂的混凝土结构等场景时,画外音没有丝毫的感情,单调乏味。当运送犹太人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渐渐远去,镜头切换到今天杂草丛生的铁轨中,我们只听到画外音平淡无奇地说:
如今,在同样的车轨上,阳光普照。我们沿着它缓缓地走过。在寻找什么?在车门打开来时掉下的尸体的痕迹?还是在狗叫声中最早下车、被赶到集中营门口的人们?在刺眼的探照灯中,远处遥遥可见的,是尸体焚化炉的羽状烟柱。(30)
在这里,雷奈似乎是在响应让·雷诺阿的原则:“素材越是激动人心,处理就越不带感情。”(31)
事实上,雷奈采用的技巧很简单,就是在历史与现在之间不断转换,集中营过去残酷的场面与现在的宁静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切迫使观众去思考: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一件事?与现实主义手法不同,雷奈采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手法,显而易见地倾注了大量的个人情感。画面的剪辑是明显的,现实在蒙太奇中被重构。叙述者的声音将这些碎片连贯起来,使其焕发出新的意义,但与诸如《大屠杀》之类作品刻意掩盖起来的人为建构行为不同,雷奈并不过分戏剧化,也不将事件琐碎化,而是让证词自己说话。作品并不直接将集中营中的暴行当作处理的直接对象。雷奈从不掩饰自己的主观建构痕迹,他将现实打碎、切割,然后重组起来给我们看。结果如何?过去与现在不仅仅鲜明地对立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两者还被深层的同一性联系了起来:过去的屠杀,今天还会再发生吗?
现实主义手法能够最大限度把残酷可怕的场面重现在人们眼前,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历史创伤的真实。相比之下,非现实主义手法则能够引导人们超越画面,追究历史事件的根源。孰是孰非,见仁见智。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屠杀作为人类的历史之痛,是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
注释:
①Cf.Elie Wiesel,"Foreword",Annette Insdorf,Indelible Shadows:Film and the Holocau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xi.
②③Theodor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NY:Continuum Press,1987,pp.17-18,p.41.
④Alvin H.Rosenfeld,"The Problematics of Holocaust Literature",in Confronting the Holocaust:The Impact of Elie Wiesel,ed.Alvin H.Rosenfeld & Irving Greenberg,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pp.172-73.
⑤"Martin Amis interviewed by Christopher Bigsby",in New Writing,ed.Malcohn Bradbury & Judy Cooke,London:Minerva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Council,1992,p.173.
⑥Eleanor Wachtel,"Eleanor Wachtel with Martin Amis:Interview",Malahat Review,114(March 1996),p.47.
⑦Michael Berenbaum,"The World Must Know",in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useum,2006,p.103.
⑧⑨Claude Lanzmann,Shoah:An Or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the Complete Text of the Fil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110,p.13.
⑩Dori Laub,"An Event without a Witness:Truth,Testimony and Survival," in Testimony: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 History,ed.Shoshana Felman & Dori Laub,New York:Routledge,1992,p.80.
(11)弗里逊在不少论文和访谈中都断然否认毒气室的存在,如:“Witnesses to the Gas Chambers of Auschwitz”,in Dissecting the Holocaust:The Growing Critique of "Truth" and "Memory",ed.Germar Rudolf,Chicago:Theses & Dissertations Press,2003,pp.133-144.
(12)这一修正派历史学家甚至还专门开设了专门的网站http://vho.org/,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免费下载到一些相关书籍。
(13)Bill Moyers,"Bill Moyers Interviewed: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Studying the Holocaust and the Nuremberg Trials",interview with Margot Strom,in 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Newsletter(Fall 1986),p.7.
(14)(15)Dori Laub,"Bearing Witness,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 in Testimony,ed.Felman & Laub,p.59,p.60,62.
(16)Michael Rothberg,Traumatic Realism:The Demands of Holocaust Represent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p.3-4.
(17)Alice R.Kaminsky,"On Literary Realism",in John Halperin(ed.),The Theory of the Novel,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17.
(18)Siegfried Kracauer,Theory of Film: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306.
(19)Jeffrey Shandler,While America Watches:Television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
(20)Jean-Paul Bier,"The Holocaust and West Germany:Strategies of Oblivion 1947-1979",New German Critique 19,Special Issue,"Germans and Jews" (Winter 1980):29.
(21)Joh n J.O'Connor,"Diverse Views of Nazi Germany",New York Times (Arts and Leisure),September 9,1979,p.41.
(22)Cf.Andre S.Markovits and Rebecca S.Hayden,"Holocaust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Reactions in West Germany and Austria," New German Critique,p.58.
(23)Cf.John Brady,The Craft of the Screenwriter,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1,p.65.
(24)Elie Wiesel,"Trivializ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Times,16(April 1978),2.
(25)Elie Wiesel,"Art and the Holocaust:Trivializing Memory," The New York Times,Jun 11,1989.
(26)Francois Truffaut,The Films in my Life,trans.Leonard Mayhew,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78,p.303.
(27)Cf.Annette Insdorf,Indelible Shadows:Film and the Holocau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01.
(28)Wiesel,"Trivializ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Times,16(April 1978),2.
(29)Roy Armes,The Cinema of Alain Resnais,London:A.Zwemmer Limited,1968,p.50.
(30)Cf.Andre Pierre Colombat,The Holocaust in French Film,London:the Scarecrow Press,1993,p.127.
(31)Cf.Gilbert Adair,Movies,Penguin,1999,p.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