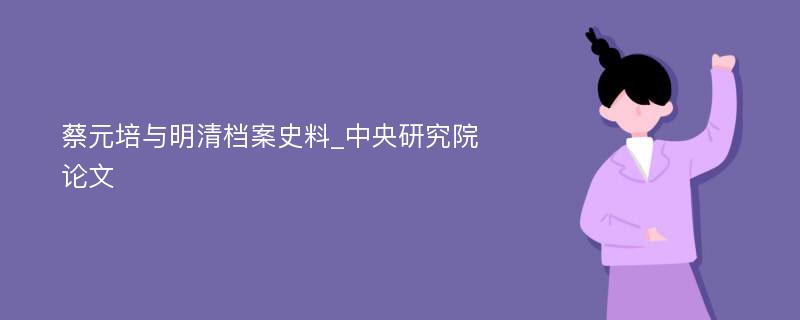
蔡元培与明清档案史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明清论文,蔡元培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①。研究蔡元培的政治、教育、哲学、美学思想的文章很多,但论述蔡元培为抢救、保护明清档案史料作出贡献的文章尚极少见。有众多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蔡元培长期致力于明清档案的抢救、保护工作,大批珍贵的档案史料得以保全,他居功至伟。蔡元培又是我国较早提倡建立档案保管机构的学者,他的档案学思想是我国早期档案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拟对以上加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共同关注。
一 蔡元培对明清档案史料的保护
蔡元培保护明清档案史料的最大贡献,是他创立了专门学术机构,使档案史料能够永久保存。蔡元培中西兼容的学术背景,使他成为20世纪初较早具有公共意识的学者。国外的学习考察经历,使他对西方档案馆的公共性,对大学与档案馆的关系都有切身体会。对国外各国都有大规模的档案馆十分羡慕,认为只有专门设立档案收藏保存机构,史料与修成之史才“有并存共在之可能”②。此外,国内大量珍贵史料档案的流失,引起蔡元培的愤慨。他谴责造成档案流失之人“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价值”③。强烈的公共意识促使蔡元培积极投身于专门学术机构的建设,并借以保存史料及明清档案。1924年4月,蔡元培就在英国呼吁将各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特别提到要建立一个科学博物院④,这所科学博物院包括“陈列、实验、演讲、研究、编印新图书杂志等事”⑤。他对档案保存机构的设想是紧密结合整理与研究,集保管、开放、利用为一体的西方档案馆性质的学术机构。类似的学术机构在民国时期先后出现过三个,分别是北大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这三个机构先后参与了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且都与蔡元培有密切的关系。他先后担任过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才能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机构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为明清档案史料建立了永久的保存机构,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最后得以归还公有的关键性人物。
1.建立北京大学国学门,推动其收纳历史博物馆原存清内阁档案。
成立于1922年1月的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有赖于蔡元培的积极提倡与规划。1916年底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积极筹备成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由于这三个研究所成效并不显著,北大评议会在1921年决定全面改组研究所。同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构概况。这次考察,蔡元培特别重视各种研究所的内部组织机构。回国后,重新草拟《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规定“本所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本所设所长一人,由大学校长兼任”⑥。蔡元培以校长身份兼任所长,负起研究所所务的责任。到各门筹办时,国学门由于进展最快,因此最先成立。蔡元培亲拟了一份国学门委员会名单,除所长蔡元培、教务长顾孟余、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当然委员外,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为委员⑦;在人员、环境、经费等方面,对国学门也特别关照。1923年蔡元培旅欧途中,还致函代理校长蒋梦麟,务必增加国学门的经费。
蔡元培心目中要把国学门建立成为一个包罗多种功能的学术机构,他在《国学门概略》的序言中,对国外大学的研究所特色非常赞赏:“外国大学,每一科学,必有一研究所;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杂志。”⑧本着这样的建所方针,国学门下设三室五会,要建成一个“大学附属之博物院”⑨。当“八千麻袋”事件⑩发生时,国学门正对近世史料求之不得。因此,蔡元培以北大校长名义,专递呈文,使教育部将存放在历史博物馆的剩余档案拨归北大国学门。
这篇呈文表达了蔡元培对档案史料的价值、史料与修史关系的认识,文中提出的整理档案方法,已是北大国学门相关工作方法的雏形。
文中首先强调近代史的重要性,“窃惟史学所重,尤在近代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外国中等学校历史教科书,自古代以至近世史占其半,最近世史亦占其半。吾国史学,首推司马迁,其作史记,自皇帝以至秦楚之际,篇数占其半,汉代亦占其半;班固首创断代史,实亦为其最近世史。自是厥后,每当易代之际,首以修前代史为最要,诚知所重也”(11)。接着阐述北大国学门欲修近世史之目的:“方今吾国最近世史,自当起于清代,民国以来,虽有清史馆之设,然前代修明史,约经六十年而后脱稿,清史之成,恐亦遥遥无期,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及史学系知近世史之重要,特设专科研究,现在广搜材料,用科学之方法,作新式之编纂”(12)。随后对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价值做出高度评价,认为“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謄黄、报销册、试卷等……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13)。但是,整理档案工作既艰苦又耗费时间,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整理多年,迄未蒇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数具有兴会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克期成功”(14)。由上述理由,蔡元培恳切提出:“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15)。最后对国学门整理史料方法做了概要介绍:“由史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以副众望;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如此办法,较为轻而易举”(16)。
这篇呈文言简意赅,逻辑清楚层层递进,充分表达了北大国学门对史料殷切盼望的态度,同时对这批档案的整理规划作出可行性建议,使该文具有很强的说服性。这份呈文送到教育部后,得到教育次长陈垣的理解与支持。教育部10天后就给北大答复,认为蔡元培的建议“可有裨于史学,且可使该馆所存有问题的历史材料,亦得具有统纪,用意甚善”(17)。因此,“除令知历史博物馆派员协同办理外,仰即派员至该馆接治拨交事宜,并明定期限于暑假内将目录克编宣布,一俟整理成书,仍将原件送达该馆”(18)。
虽然明发教育部部令,但这批档案并没有迅速转移到北大。教育部同意将历史博物馆存内阁档案拨归北大在1922年5月22日(19),直到1922年6月17日,北大国学门才将这批档案共61箱1502袋运回北大(20)。这其中的几番波折,虽然无法确切考证,但可以想见,这批档案最终拨归北大蔡元培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因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奔走,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搬运过来”(21)。
内阁档案归属北大后,蔡元培召集沈兼士、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15位学者讨论整理档案的方法,并建议组成档案整理委员会,对档案进行整理分类刊布。虽然蔡元培没有参与具体的档案整理工作,但是北大国学门整理档案会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离不开蔡元培的支持。整理档案会成为“近乎档案馆一类的组织”(22),显然是实践了蔡元培效仿国外大学研究所中特设陈列所的设想。
2.成立中央研究院,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入“八千麻袋”档案筹款。
中央研究院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夏。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国家规模的科学研究机构,它“综合先进国中之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各种意义而成”(23),蔡元培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央研究院的主要创始人。
1927年5月9日,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上,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共同提议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北平和浙江3个研究院,首先建立中央研究院。此后,蔡元培与李石曾提议,效仿法国经验,试行大学区制,教育行政委员会改为大学院,蔡元培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10月1日,大学院成立,蔡元培宣誓就职。蔡元培在《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把“设立中央研究院为全国学术之中坚”、“实行科学的研究”作为大学院的三大使命之一(24)。1927年11月20日,蔡元培主持召开“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1928年4月,蔡元培亲自委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在广州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10月份史语所正式成立。
1928年9月,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9月11日,蔡元培接傅斯年函,信中称李盛铎(25)从罗振玉手中购买的“八千麻袋”内阁大库档案因无力保管,急于出售。“去年冬,满铁公司将此件订好买约,以马叔平诸先生之大闹而未出境,现仍在京。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护,恐归损失”(26)。由于傅斯年无法筹集购买这批档案的经费,因此请蔡元培想办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27),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蔡元培当时已经辞去大学院院长之职,但是为留住这批珍贵档案,即于9月12日致函大学院总干事杨杏佛,“欲大学院以二万元购李盛铎所藏之档案。如能腾出此款,当然甚好。但几日内有法筹出否?”(28)此后,杨杏佛从大学院拨款替史语所购回这批档案。蔡元培对于这部分内阁大库档案最终得以保存在史语所,并得到迅速整理、研究、刊发,功在头筹。
3.领导故宫博物院,为文献馆整理明清档案工作保驾护航。
蔡元培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虽未直接领导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工作,但是他为文献馆的工作顺利展开作出了卓越贡献。
首先,蔡元培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又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主持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召开,审议通过故宫博物院的经济、人事等重大问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组织机构、工作内容、历次收购明清档案的款项,皆需通过常务理事会审批。
其次,故宫博物院最初的业务骨干多来自于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提供了有力的干部和人才储备。1924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被驱逐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1月成立。善后委员会由政府各部部长的代表、社会名流及北大教授组成,最初参与筹备委员会的干事28人,大部分是北大教授。这些人中,以国学门委员及明清史料整理会成员为主体,如蒋梦麟、胡适、钱玄同、顾孟余、马裕藻、沈尹默、陈垣、马衡、皮宗石、朱希祖、徐炳昶、单不庵、顾颉刚、李宗侗、胡鸣盛、罗庸、黄文弼等(29)。清室善后委员会下设的“事务会”,由4位北大国学门的助教任职,分别是董作宾、魏建功、潘传霖、庄尚严,其中魏建功和潘传霖都是北大整理档案会成员(30)。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设立专责保管明清档案史料的文献馆,沈兼士任副馆长、馆长,陈垣和朱希祖任导师。北大国学门的助教及学生庄尚严、朱家济、单士元、傅振伦、董作宾、魏建功、潘传霖、刘儒林等都在故宫博物院任职。北大明清史料整理会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做了人才储备。特别是沈兼士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部第一任主任就是蔡元培的意见,足以看出蔡元培在促使档案收藏保管专门化方向的努力(31),以及他对文献馆工作的重视。
再次,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档案,是北京大学国学门“整理档案会”的延续。沈兼士在《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中将民国以来保存档案的重要事迹列表:
“(民国)十一年五月北京大学因罗振玉收买库档,请准教育部,以历史博物馆库档委托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整理。
十一年七月,北大接收档案完毕,规定整理计划。
十二年三月,北大史学系学生参加整理档案以资实习,其他考古学风俗学等实地调查之风,同时并起,一洗从前文科徒托空言之弊。
十二年六月,北大史科整理会议决,暑假期间不停止工作。
十二年十一月,北大研究所由第一院迁入第三院工字楼,档案始有陈列室九间,计分要件、题本、报销册等类。
十三年十一月,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故宫。
十四年十一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设文献部,集中宫中档案,于外东路辟陈列室。
十四年十二月,故宫博物院接收宗人府档案。
十五年一月,故宫博物院请准国务院移交军机处档案归其保管。至是始完成同人倡议之内外庭档案整个保存联合整理之计划。
十六年十月,开放大高殿,展览军机处档案。
十七年六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接管旧清史档案。
十八年九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接收旧刑部档案。
二十年一月,开始点查整理内阁大库档案。”(32)
在该报告中沈兼士特别指出北大国学门整理档案的失误,即太注重形式,忽略档案的内容;只注意档案本身,忽略档案之间的联系;只注重搜求奇珍史料,忽略多数平凡材料的普遍整理(33)。并以此作为借鉴,调整文献馆整理档案的工作方法,摒弃零星摭拾挂一漏万的方式,要“以全力注重普遍之整理”(34)。由上述记录,可以看出北京大学国学门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整理明清档案工作上的延续性。蔡元培创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提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35)的学风贯穿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工作当中。文献馆对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分类、保存、出版与研究工作,能够吸取前人的经验得失,在整理分类保存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方法。在档案研究方面,文献馆的工作人员充分利用档案,以档治史,为清史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蔡元培领导的上述三个学术机构对明清档案史料的抢救、整理,与此前北洋政府倒卖内阁大库档案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蔡元培为抢救、整理明清档案史料作出的贡献,是20世纪初具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挽救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垂范作用,蔡元培也因此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学者之一。
二 蔡元培的档案史料思想
蔡元培的档案史料思想,是蔡元培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当时史学界对档案的普遍认识,折射出近代史学对档案学发展的影响。
1.肯定档案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础,认识官方档案与私家档案的不同价值。
蔡元培认为史料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成果。他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两部分,“历史中直接的材料与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以前修史者之滥用间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是一件不幸的事,应该是以后治史学者所急当纠正的”(36)。蔡元培认为档案是修史的直接材料,“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37),不同于实录碑传这样的间接材料,“史料愈间接愈不可靠”(38)。已往的史书就是忽略了对直接史料的运用,才会读起来“千人一面,千篇一腔,一事之内容不可知,一人之行品不易见”(39)。蔡元培“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40)的思想,对近代档案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此后很多学者论述档案的价值多从档案与史学密切关系的角度展开。
此外,蔡元培认为官府和私家史料同等重要,虽然“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41),但是这两种史料“合综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42)。私人记事,由于多是凭借传闻、个人好恶等原因,往往失之于诬。而官府文籍,多局限于一类的事迹,不如私人记载内容丰富。私人著述由于没有官府的立场,因此十分宝贵。官府文籍虽然“只说一面的话,而有些靠不住”(43),但许多繁琐的程式化的事情只有官府会留下记录,“我们可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44),所以官府记载“仍不失为史料大源”(45)。蔡元培对于官方档案与私家记载的并重,体现了当时学界对材料扩张的积极态度和对史料价值的客观性认识。在他看来“守质者懒惰着专依赖官书,好奇者涉猎着专信些私家不经之谈,都不算是史学的正轨”(46),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47)。
2.提出档案专门化管理,积极开放利用档案。
蔡元培主张著史与保档相结合,希望建立大规模专门性质的档案管理机构。他痛感“吾国历来史书不可为少,其所根据之材料,皆散失不穿,无由比照对勘,良为可惜”(48)。这种“轻视史料,无意保存”(49)的习惯应该马上改变。他认为“近世学者对于基本史料,如档案一类,愈益重视,而保存编目各方法,亦日渐精密。于是,故各国皆有大规模之档案馆”(50)。蔡元培认为只有建立档案管理机构,史料与修成的史书,才能共同保存下来。
但是蔡元培并不一味认为凡是档案史料皆藏,而是强调进入档案馆的文献必须经过认真挑选。他认为历史上的档案之所以散失殆尽,也有“数量太多到无法保存”(51)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档案开放利用的观点。他认为整理档案的目的,一是要更好地保管档案,二是公布于世,用于学术研究。他反对档案秘不示人的做法,介绍国外的经验,“欧美国家,除必须守秘密者外,多由政府随时刊行。而外交部档案慎重保存,常亦对学者开放,以资研究。此不但有助于国民外交常识之普及,抑且供给历史学家以多量正确之史料”(52)。他身体力行,亲自撰写序言以鼓励档案史料的刊布。如1928年为《清季外交史料》作序,肯定该书对于清代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意义。1930年为《明清史料档案》作序,对史语所的内阁大库残余档案进行介绍。1936年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准备联合出版《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蔡元培欣然为之作序,对该书出版的意义大加褒扬。当这本书历经战乱到1947年出版时,距离蔡元培去世已经7年整。
蔡元培的档案史料思想来自于整理明清档案的实践,他对于档案史料的认识是创立时期的中国档案学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虽然他未明确提出档案学的名称,但他从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出发,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提出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档案,注意档案及时刊布,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是近代档案学的思想源泉。傅振伦指出:“近世考古学上历史学上有四大重要发现:一为殷商刻辞甲骨;二为两汉魏晋南北朝之竹木简牍;三为唐至五代之方献图籍;四为明清之档案史笔。潜研之士,发明甚多,皆大有裨于历史文化,然四者亦皆当时之案牍也!”,(53)围绕着这四大发现,史学界产生了很多著述。特别是蔡元培领导的明清档案的整理,有力地推动了档案学的产生,是档案学创立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蔡元培不以治史学名世,但他“萃中土文教之精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衍于物外”(54)。他的档案史料思想建立在对传统中国史学的深刻认知,对西方文化广泛见识的基础上。他对档案保存机构的设想实践于北大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蔡元培领导北大国学门首开学术机构整理明清档案的先河,他敏锐地抓住了学术的“预流”(55),推动了20世纪初学界对档案史料整理的热潮,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催生出史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蔡元培对明清档案作出的种种贡献,无不显示出他一代学术大师的宏阔视野,无愧于时入对他“树之师表,风被当世”(56)的评价。
注释:
①《新华日报》(重庆),1940年3月8日。
②(48)(49)(51)蔡元培《〈清内阁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序》,《文献论丛·论述一》,1936年。
③(36)(37)(38)(39)(40)(41)(42)(43)(44)(45)(46)(47)蔡元培《〈明清史料〉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简称《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1930年,第1、2页。
④⑤蔡元培《致英国庚款委员会函》,《蔡元培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⑥蔡元培《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
⑦蔡元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会员提案》,《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33页。
⑧蔡元培《国学门概略序》,《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北京大学1927年版,第2页。
⑨沈兼士《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4页。
⑩“八千麻袋”事件: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成立历史博物馆,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存放于博物馆。1921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除留下一部分较好的档案,将其余部分约八千麻袋档案贱卖给纸店,准备化成纸浆。学者罗振玉得知消息后,以重金购回这些档案,并对其中部分加以整理、出版。罗振玉后因财务原因将这批档案转卖给知名藏书家李盛铎。这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11)(12)(13)(14)(15)(16)蔡元培《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1—623页。
(17)(18)《教育部指令第九九九号》,《北京大学日刊》1038号,1921年5月27日,第1版。
(19)(20)《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先生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第1056号,1922年6月1日,第2版。
(21)赵泉澄《北京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第2卷第2期,第226页。
(22)傅振伦《记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9页。
(23)蔡元培《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发刊词》,《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第1期,1928年7月,第1页。
(24)《〈大学院公报〉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25)李盛铎(1859-1935年),字义樵,又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清末至民国初年历任显职,是中国近代知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
(26)(27)《傅斯年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28)《致杨杏佛函》,转引自李光涛《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134页。
(29)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0页。
(30)吴十洲《紫禁城的黎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31)覃兆刿《蔡元培档案思想浅议》,《北京档案》1998年第5期,第22页。
(32)(33)(34)沈兼士《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文献特刊·报告》1936年。
(35)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1920年编,第227页。
(50)蔡元培《〈清季外交史料〉序》,《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53)傅振伦、龙兆佛《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5、76页。
(54)(56)《〈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撰文人共上蔡先生书》,《傅斯年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页。
(55)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中有“一时代之学术,必然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此材料以研求学问,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